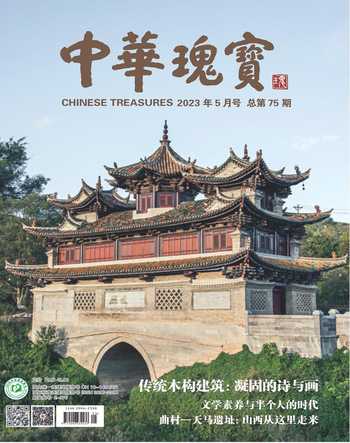吟咏讽诵 感发善心



《诗集传》为元、明、清时代影响最大的《诗经》学著作,是《诗经》研究从经学走向文学的关键环节,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属性、推动《诗经》的文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漫长的《诗经》学史上,从汉代毛亨的《毛诗故训传》算起,留存下来的笺《诗》、注《诗》、解《诗》之作数不胜数,更有一些著作或因学者学识获得后人尊崇,如郑玄的《毛诗笺》,或因统治者的支持而成为主流,如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朱熹的《诗集传》则于二者兼而有之。
去《序》言《诗》
朱熹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面對内忧外患不断的南宋朝廷,他曾有入仕之志。宋孝宗即位之后诏求直言,朱熹即上书直陈反佛崇儒、反和主战、任贤使能等主张。但时局复杂,其主张终未被采纳。此后,他将重心放在了悟道、讲学、著述之上。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问津书院,或因朱熹重建而复兴,或因朱熹讲学而闻名。作为宋代理学道统的传人与集大成者,朱熹成为南宋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被尊为“朱子”。绍熙五年(1194年),受当时执政大臣赵汝愚的举荐,朱熹出任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因此被卷入赵汝愚与韩侂胄争权夺利的斗争当中。在历时六年的“庆元党禁”之祸中,朱熹被斥为“伪学魁首”,落职罢官,至庆元六年(1200年)去世。两年后,学禁弛解,朱熹被宋宁宗追谥为“文”;至宋理宗时,又被追封为信国公,后改封徽国公,故世称其为“朱文公”。
朱熹一生门生众多,著述等身。据学者统计,其著作共144种,涉经、史、子、集四部。其中《诗经》学著作存世者主要有《诗集传》《诗序辨说》《诗传纲领》等。朱熹去世之后,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仪礼经传通解》等书即被立于学官。到了元代,《四书章句集注》等被确定为科举考试的课本,朱子学说遂成为由元迄清维护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诗集传》这部在当时即因朱熹学识见解而闻名于世的著作,之后又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成为元、明、清时代影响最大的《诗经》学著作。
根据《朱子语类》的记载,朱熹作《诗集传》,曾两易其稿。两稿最大的区别集中表现在对待《诗序》的态度上。其初稿尊《序》,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朱氏曰”就保留了初稿尊《序》解《诗》的部分文字。二稿则受郑樵废《序》之说影响很深,认为《诗序》实不足信,明确宣称解《诗》“须先去了《小序》”。对于这一变化发生的过程,朱熹在回答“《诗传》多不解《诗序》,何也”的疑问时,说得比较详细:“某自二十岁时读《诗》,便觉《小序》无意义。及去了《小序》,只玩味诗词,却又觉得道理贯彻。当初亦尝质问诸乡先生,皆云《序》不可废,而某之疑终不能释。后到三十岁,断然知《小序》之出于汉儒所作,其为谬戾,有不可胜言。东莱不合只因《序》讲解,便有许多牵强处。某尝与之言,终不肯信。《读诗记》中虽多说《序》,然亦有说不行处,亦废之。某因作《诗传》,遂成《诗序辨说》一册,其他谬戾辨之颇详。”(《朱子语类》卷八十)这里提及的“东莱”,就是曾与朱熹往复驳辩,评价朱熹“唯太不信《小序》一说,终思量未通”的吕祖谦。
正是因为认定《诗序》之不可信,所以朱熹提出了以“诗”言《诗》的解读方法:“学者当兴于《诗》,须先去了《小序》,只将本文熟读玩味。”又说:“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朱子语类》卷八十)他主张以“自作此诗”的态度,通过吟咏讽诵、熟读玩味来体会诗歌的意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之立教
这样的读《诗》态度与方法,让朱熹从《诗经》中发现了“里巷歌谣之作”:“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诗集传》原序)《诗经》中一直被包裹在“美刺”观念背后的男女情思,就这样被真切实在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朱熹认为:“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诗集传》原序)因此,这些男女相与咏歌的作品中存在“有邪”的情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朱熹解《诗》时也坦然地认可了这一类作品的存在:
《邶风·静女》:此淫奔期会之诗也。(《诗集传》卷二)
《卫风·氓》: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诗集传》卷三)
《郑风·山有扶苏》:淫女戏其所私者曰:“山则有扶苏矣,隰则有荷华矣。今乃不见子都,而见此狂人,何哉?”(《诗集传》卷四)
《郑风·狡童》: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言悦己者众,子虽见绝,未至于使我不能餐也。(《诗集传》卷四)
《郑风·褰裳》:淫女语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则将褰裳而涉溱以从子;子不我思,则岂无他人之可从,而必于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谑之之辞。(《诗集传》卷四)
除了在具体的诗作下指认“淫诗”之外,于《诗集传》卷四之末总说《郑风》时,朱熹还比较了郑、卫两国“淫奔之诗”的不同:
卫诗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诗才四之一;郑诗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辞,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创之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之淫,有甚于卫矣。
对于深具怀疑精神的宋儒而言,废弃《诗序》甚至指出《诗经》中存在“淫诗”并不困难,真正的困难在于确认《诗经》中存在“淫诗”之后,如何解释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朱子语类》卷二十三中所保存的大量关于“思无邪”的问答,可知“淫诗”一说所带来的冲击。在回答该如何理解“思无邪”的问题时,朱熹坚持了“教人思无邪”“读之思无邪”的“《诗》之立教”的立场:
此《诗》之立教如此,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逸志。
《诗》有善有恶,头面最多,而惟“思无邪”一句足以该之。上至于圣人,下至于淫奔之事,圣人皆存之者,所以欲使读者知所惩劝。其言“思无邪”者,以其有邪也。
“思无邪”,乃是要使读《诗》人“思无邪”耳。读三百篇诗,善为可法,恶为可戒,故使人“思无邪”。若以为作诗者“思无邪”,则《桑中》《溱洧》之诗,果无邪耶?
《诗》恰如《春秋》。《春秋》皆乱世之事,而圣人一切裁之以天理。
以“天理人欲”的理学思想为基础,朱熹站在“《诗》之立教”的立场上,虽然努力化解“淫诗”说引发的解释问题,在自己的理论系統中实现了解释上的圆融,但其后续影响仍然是巨大的。一方面,是以王柏为代表的激进的理学家提出删去“淫诗”的主张;另一方面,是对朱熹“淫诗”说前赴后继的批评。如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中就多次出现“朱子改为男女相赠答之辞,无稽甚矣”一类的评说。清初学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一书中,也对“淫诗”一说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集传》纰缪不少,其大者尤在误读夫子“郑声淫”一语,妄以《郑诗》为淫,且及于卫,且及于他国。是使三百篇为训淫之书,吾夫子为导淫之人,此举世之所切齿而叹恨者。(《诗经通论·自序》)
《集传》使世人群加指摘者,自无过淫诗一节。其谓淫诗,今亦无事多辨。夫子曰“郑声淫”,声者,音调之谓,诗者,篇章之谓。迥不相合。(《诗经通论·诗经论旨》)
尽管如此,朱熹所倡导并在《诗集传》中得到充分运用的“吟咏讽诵”“只玩味诗词”的读《诗》方法,还是获得了姚际恒的认同与发展。
以文学说经
在朱熹的基础上,姚际恒提出了“惟是涵泳篇章,寻绎文义,辨别前说,以从其是而黜其非,庶使诗意不致大歧”的解诗方法,希望以此保留“原诗之真面目”。诚如顾颉刚《诗经通论·序》中所言:“姚首源先生崛起清初,受自由立论之风……实承晦庵之规模而更进者,其诋之也即所以继之也。”顾颉刚充分肯定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在方法上对朱熹的继承所带来的开创性贡献:“以文学说经,置经文于平易近人之境,尤为直探诗人之深情,开创批评之新径。”
《诗经通论》与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因为“以文学说经”受到了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重视。他们所采用的“体会经文,即词以求其意”(《读风偶识》卷一),“反覆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诗经原始·自序》)的读《诗》方法,均与朱熹“只玩味诗词”的“吟咏讽诵”一脉相承。因此有人把《诗集传》视为《诗经》研究从经学走向文学的关键环节,也有一定的道理。
除了在读《诗》方法上开启了“以文学说经”的先河之外,朱熹在孔颖达“三体三用”说的基础上对“六义”也进行了重新定义。“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颂者,宗庙之乐歌”,精练准确地道明了“风”“雅”“颂”三类作品的来源与属性;“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以彼物比此物也”“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则简洁明了地总结了“赋”“比”“兴”作为修辞方法的突出特征。这些认识,对于深化《诗经》文学属性,推动《诗经》的文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通经致用
朱熹的《诗集传》是一部经典的经学著作,“通经致用”的经学立场决定了他对待《诗经》的基本态度。因此,在确认《诗》中存在“淫诗”之后,他仍然要坚持“《诗》之立教”,要强调“《诗》之功用能使人无邪”。同样,也是“通经致用”的经学立场,造成了他一方面明确宣布“《小序》无意义”,要“去了《小序》”,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在实质上绕开《小序》来说解诗义的矛盾。激烈批评“淫诗”一说的姚际恒,明确指出了朱熹对待《诗序》时存在的深刻矛盾:“其从《序》者十之五,又有外示不从而阴合之者,又有意实不然之而终不能出其范围者,十之二三。故愚谓,遵《序》者莫若《集传》。”(《诗经通论·诗经论旨》)
俞平伯在其《葺芷缭蘅室读诗札记》(《古史辨》第三册)中说得更加尖锐:“朱熹为攻击《小序》之祖师,但他实往往做《小序》的奴才。”这种实质上的“废而不弃”,让《诗序》在经历了《诗集传》被立为科举取士课本的元明两代之后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影响力。清代之后,毛、郑诗学重新昌盛,朱熹的《诗集传》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连乾隆皇帝读《诗》也发出了“晦翁旧解我生疑”(《七十二候诗·虹始见》)的感慨。《毛诗稽古编》《毛诗后笺》《诗毛氏传疏》等尊毛重《序》的《诗经》学著作相继出现,《诗集传》的经学影响才逐渐式微。
马银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