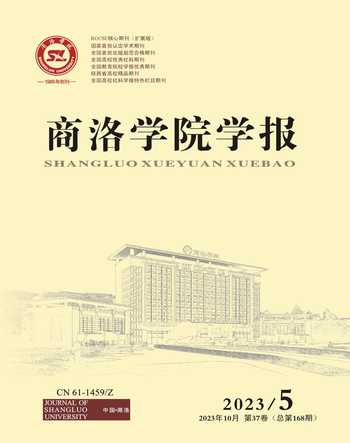贾平凹小说的抒情美学
刘飞 范天园
收稿日期:2023-05-17
作者简介:刘飞,男,湖北房县人,硕士研究生
doi:10.13440/j.slxy.1674-0033.2023.05.004
摘 要:贾平凹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一方面深受废名、沈从文和孙犁等现当代抒情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积极从屈原、庄子和苏轼等人的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学习、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抒情传统。生命的“破缺”是贾平凹缘情而发,抒写《秦腔》的情感动因。他以秦腔戏架构起小说的“天窗”结构,以实写虚、体无证有,建立了以秦腔为核心的象征体系,并在这一象征体系中融入了个人史、当代史和古代史三个维度的历史,将当代乡愁编织到“伤逝”的母题中,建立起天地人合一的人生观和观物方式。由此,现代中国乡土的裂变成为人事在天地间的轮回出演,呈现出沉郁顿挫的抒情境界。
关键词:抒情;《秦腔》;破缺;“天窗”结构;乡愁;伤逝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033(2023)05-0023-09
引用格式:刘飞,范天园.贾平凹小说的抒情美学——兼论《秦腔》的乡愁书写[J].商洛学院学报,2023,37(5):23-31.
The Lyrical Aesthetics in Jia Pingwa's Novels
——With the Nostalgia Writing of Qin Qiang
LIU Fei1, FAN Tian-yuan2
(1.College of Literal Art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Hebei; 2.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ili Normal University, Yining 835000, Xinjiang)
Abstract: Jia Pingwa is a writer with the temperament of a poet. On the one hand, h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yric writers such as Fei Ming, Shen Congwen and Sun Li; on the other hand, he has learne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hinese lyric tradition through active absorption of spiritual nutrition from classical culture such as Qu Yuan, Zhuang Zi and Su Shi. The "breaking of life" is the emotional motivation for Jia Pingwa to create Qin Qiang. He constructs the "skylight" structure of the novel with Qin opera, and establishes a symbolic system with Qin opera as the core. In this symbolic syste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history - personal history,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ancient history - are integrated, and nostalgia is woven into the theme of "sorrow for the past". In this way, the outlook on life and the way of viewing things are established. As a result, the fission of modern Chinese countryside is similar to the reincarnation of human being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howing a depressed lyrical emotion.
Key words: lyric; Qin Qiang; breaking of life; "skyligh" structure; nostalgia; sorrow for the past
賈平凹是一位深具诗人气质和古典文化素养的当代作家,他的创作兼具古典韵味和现代意识。随着国学热的兴起,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角度研究贾平凹的创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然而从抒情传统角度研究的成果尚显不足。王建仓[1]的《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将贾平凹的小说称为意象叙事,即转意成象,以实写虚。该文洞察了贾平凹以实写虚的抒情特质,但过多聚焦于“商州”系列作品,对贾平凹的境界追求重视不够。王德威[2]在《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中指出《古炉》暴力叙事与田园景象的对话,是贾平凹有意借抒情笔调发掘暴力背后的“有情”历史。杨辉[3]的《贾平凹与“大文学史”》认为贾平凹兼具“史诗”与“抒情”之双重特征。吴义勤等[4]的《抒情话语的再造——〈山本〉论之二》论述了《山本》通过历史书写再造了抒情话语。研究者们敏锐地洞见了贾平凹创作中“叙事”与“抒情”的对话,对读者具有启发意义。本文以《秦腔》为中心,从抒情传统的角度考察贾平凹对当代乡愁的抒写,探索中国乡土、现代性焦虑和抒情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抒情面向。
一、现代性焦虑和抒情传统的相遇
贾平凹的创作实践接续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抒情文脉,融通着古典抒情传统,扩展了当代文学的抒情美学。贾平凹的诗人气质与才情,使他天然地亲近抒情作家。遭遇现代性的焦虑,使贾平凹和中国现当代抒情作家选择了适宜于“后发国家”的诗化文学创作。同时,贾平凹从古典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接续着古典抒情传统的“境界说”与“体物说”,拓展了当代文学的抒情艺术。
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伊始就有着抒情品质,这种品质在京派作家的开启和拓展下,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的序言中描述乡土文学时,敏锐地捕捉到乡土文学抒写“胸臆”和“隐现着乡愁”[5]9的抒情意绪。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作品,在启蒙视域内浸透着个人的悲凉感受,诗集《野草》更是将空虚、绝望的悲哀写得淋漓尽致。鲁迅精准地把握了废名小说的抒情特质,他直述废名的自白“从他们当中理出我的悲哀”,从率直的读者立场批评废名“就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5]6。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把“五四”运动到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视为“抒情”到“史诗”的过渡[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认为“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促进或限制了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7]。陈平原与普实克的观点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两位学者均深刻地洞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质素和诗化渊源。严家炎的《现代小说流派史》从文学流派的角度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文脉,认为废名、沈从文、凌叔华、林徽因和萧乾等作家的京派小说 “把写实、记‘梦、象征熔于一炉,使抒情写意小说走向一个新的阶段”[8]。他认为废名是最早的京派小说家,沈从文的成就最高,影响最大,而汪曾祺是京派小说的传人。
当代文学的抒情,一方面拓展了新的领域,另一方面又接通发展了古典抒情传统。新中国文学的前30年,流行着“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成为抒情的重要面向。孙犁的小说中革命与抒情完美融合,引领着荷花淀派的创作。李扬把1950年代新中国文学描述为“抒情时代”,指出“‘人民性的歌颂”有着“强烈的抒情与浪漫风格”[9]。新时期之后的文学有意接通古典抒情传统,扩展着当代的抒情艺术。1980年汪曾祺发表《受戒》等风俗小说,成为“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10]。1984—1986年的寻根文学运动重拾现当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并试图跨越与古典文化的“断裂带”[11]。
新时期之初,贾平凹在无意识中汇流于寻根文学潮流,他以《卧虎说》和“商州”系列作品致敬抒情传统的创作,成为抒情文脉的接续者与实践者。贾平凹的诗人气质和才情,使他从情感和认知上主动地接受了抒情作家的影响,“我不是现实主义作家,我应该算作一位诗人”[12]110。贾平凹认为作家有两种类型,“一类作家是政治倾向性强烈的,一类是艺术性强烈的”[13]56,艺术性强烈的作家是抒情主义的。他認为汪曾祺是一个抒情主义者,贾平凹1981年创作的《朝拜》是对《受戒》的摹写和致敬之作。“我学习废名,主要是学习他的个性……我写作个性上受废名的影响大。但他气太小。”[13]59贾平凹学习废名的个性,却警惕着废名“气小”的不足,而转向“气大”的沈从文,“沈从文之所以影响我,我觉得一是湘西和商州差不多,二是沈从文气大,他是天才作家。”[13]59贾平凹在地方情感和经验上已先和沈从文亲近,他第一次读到沈从文小说时,“觉得是我那些年看到的最好的小说”[13]157-158。在艺术认知上,贾平凹认为沈从文有四性,即阴柔性、温暖性、神性和唯美性[12]136-140,提倡在阅读中品味、感应、体悟和学习沈从文。贾平凹很早就学习孙犁的语言,模仿孙犁的创作。“文革”期间,贾平凹辍学回乡修水库看到一本没头没尾的书,就模仿着在笔记本上写作,“后来上了大学才知道是孙犁的《白洋淀记事》”[13]157。
贾平凹和抒情作家们面临着相似的历史境遇,严峻的现代性焦虑是贾平凹选择抒情性的诗化文学的现实动因。薛毅、吴晓东等研究者洞见了现代性焦虑与现代小说诗化特征的内在联系:“诗化小说可能从根本上涉及了一个后发国家的文学抒情性问题”[14]77。中国文学带着双重的文化和美学特征:“一方面是现代性的焦虑,其中交织着对现代性的既追求又疑虑的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面临本土的传统美感日渐丧失所带来的怅惘体验和挽歌情怀。诗化小说总体上的美感和诗意正生成于这种挽歌式的意绪在挽歌中蕴涵着天然的抒情性和诗意品质。”[14]77在现代作家沈从文这里,《边城》《长河》等抒情性小说在建构沈从文的“希腊小庙”时,把现代性焦虑带来的乡愁上升到民族国家的层次,使其成为民族国家的现代寓言。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之后的文学,现代性焦虑在现代化进程中呈进一步加剧的趋势。贾平凹延续沈从文的乡愁书写,架构了另一个“湘西世界”,即“商州世界”,“读沈从文,就觉得写的是我的故乡商州的故事”[13]179。面对寓言成为现实的情况,贾平凹的《秦腔》将乡愁书写推向了极点,以此来观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乡土的裂变。郜元宝采访时直呼“写《秦腔》的你对故乡有深情的回忆,但主要是无可奈何的‘告别”[13]243。可见,《秦腔》从鲁迅所说的“隐现着乡愁”和“有限的哀愁”走得更远,它是为行将消失的故乡树起的一块碑子。乡愁母题本身就是现当代文学乡土书写的源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当代乡愁更加弥漫出挽歌意绪和“伤逝”美学。贾平凹有着艺术视角的自觉,“长期坚守两块阵地,一是商州,一是西安,从西安的角度看商州,从商州的角度看西安,以这两个角度看中国”[12]207。《秦腔》深化和发展着“商州”视角,接续废名、沈从文以降的乡愁母题,瞩目于当代的乡土裂变,为当代乡愁留下“一曲挽歌,一段情深”[15]。
贾平凹在抒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在继承现当代抒情文学时,他自觉地接续中国古典抒情美学。“诗言志”是中国抒情诗学的源头,“志”囊括着“志向抱负”和“情感”两个维度。周作人以降的一批现代学者以“诗缘情”厘清了抒情传统的“情”之一维。王德威也指出,“诗缘情”传统重在两个向度:一是“诗可以怨”的“发愤”观念;二是从六朝“物色”与“缘情”论发展而来的“境界说”[16]。他作品中的神秘、想象与屈原及其代表的楚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屈原主要是学他的神秘感,他的诗写得天上地下,神神秘秘”[13]59 。贾平凹推崇屈原、庄子、苏轼等人的古典文学作品,贾平凹向庄子学习境界,“庄子是他的哲学高度,学他的那种高境界,站得高,看问题高,心境开阔”。同时,他还向苏轼学习自在,他倾慕于苏东坡的文格与人格, “苏东坡主要学习他的自在”[13]59,“他的诗词文赋书法绘画又应该最能体现他的人格理想吧”[17]。贾平凹自称“我的天资里有粗犷的成分,也有性灵派里的东西”[12]109,但他却警惕于性灵一路渐巧渐小的弊端。单论对美学和文化资源的态度,贾平凹对抒情传统的“境界说”有着个人的感悟与认知,“作品境界要学习西方的,实际上就是人类意识”[13]131。贾平凹1982年创作的《“卧虎”说》中作出了“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18]21的感悟,是其追求“境界”的早期论断。1988年,贾平凹提出作品的“大境界”:“现在,重新提出‘建立,是需要一种大境界的作品出现,大气的作品出现”[12]44。贾平凹在艺术实践中力求人性和境界的融合,“如果在分析人性中弥漫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浑然之气,意象氤氲,那正是我新的兴趣所在”[12]128。无论其创作是否达到理论上的“境界”一说,但其对“境界”的提倡和实践是毋庸置疑的。杨辉评价贾平凹小说在民族性追求、水性与文道的融通和“全息”现实主义图景三个维度已具古典特征[19],许爱珠将贾平凹的《怀念狼》《病相报告》等小说称为意象小说[20],这些批评都可视为对其抒情美学的肯定。
贾平凹的创作还涉及抒情传统“物”之一维。陈世骧以降的抒情传统研究建立了“情”之维度上的“感兴”论述,任树民依据中国古典诗歌“表现”和“描写”(也即“缘情”和“体物”)的两元,提出抒情传统“物”之维度上的“体物”论述[21]187。“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 “随物婉转,曲尽物貌,求情感、情景、情事之妙的‘体物诗艺是中国诗学传统中一个重要维度”[21]256。贾平凹“随物赋形” “道法自然”的写作手法暗合着任树民提及的“体物”诗艺。贾平凹指出技巧“是认识世界的方法,随物赋形,这就是技巧吧”[13]405。阅读《吉檀迦利》时,他感悟到“泰戈尔之诗文……如中国的屈原、太白、东坡。他们天性自在,随物即赋形也”[22]。贾平凹追求随物赋形的自在书写,“随物赋形,以形写意,迁想妙得,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低者皆宜。”[23]贾平凹以大实大虚、拙朴、混沌著称的作品,建立在其扎实的描情状物能力和写实功底上,《古炉》《老生》《山本》等达到随物赋形、曲尽其妙的境界。这些可以视为贾平凹对抒情传统的继承与开拓。
贾平凹的文学实践有着抒情的质素,呈现出复杂而丰富的形态和意蕴。从抒情传统角度考察《秦腔》等作品具有可行性与学理性,它能够呈现贾平凹对当代乡愁的抒写,探索中国乡土、现代性焦虑和抒情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展和深化当代文学研究的抒情面向。
二、缘情而发与以实写虚的艺术实践
生命“破缺”是贾平凹发愤抒情的动因,“天窗”结构是贾平凹抒情写意的艺术途径。贾平凹借助小说的“天窗”结构以实写虚、体无证有,把一己之痛上升到民族国家的乡愁之悲,实现了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
《秦腔》是贾平凹缘情而发的创作,它是在“惊恐”与“痛苦”中完成的。吕正惠从“发生学”的角度指出“感物”的起点是“叹逝”,也就是说“感兴”起源于“情”之本体,这与“缘情”说是内在一致的[24]50。《秦腔》源于贾平凹“内部化”于故乡的个人之痛,“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25]563。“父”的缺失是贾平凹抒写《秦腔》的触媒与契机,“父亲的去世使贾家氏族在棣花街的显赫威势开始衰败,而棣花街似乎也度过了他短暂的欣欣向荣岁月”[12]152。父亲对贾平凹的影响极重,他一生的经历使贾平凹有了苦难意识和奋斗精神。贾平凹的人生道路承袭着父亲的期望,“我永远忘不了父亲的那次眼神。他原本对我寄托了很大的希望的,只说我会上完初中,再上高中,然后去省城,成为贾家荣宗耀祖的人物”[26]。贾平凹的一生也在主动回应着父亲的期望,1974年《深深的脚印》被《西安日报》刊发,“当天夜里,平娃给父亲写信,报告了这一重大喜讯。信上说,我开始有了脚印了”[27]。贾平凹不仅在《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头发》《祭父》《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我的父亲》《四十岁说》《我不是个好儿子》《我是农民》等作品中多次写到父亲,而且在《废都》《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小说后记中屡次提及父亲对其创作的影响。父亲的逝世是贾平凹难以抹除和消解的痛苦,“每次回老家,肯定要去父亲的坟上烧纸奠酒,父亲虽然去世已有18年,痛楚并没有从我心上逝去,一跪到坟前就止不住的泪流满面”[12]180。贾平凹还会向父亲“汇报”个人创作,特别是涉及父老乡亲的创作。“我流着泪正喃喃地给父亲说:‘《秦腔》我写了咱这的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现在《高兴》又写了他们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12]181。写作《秦腔》涉及“家族内部的事情”,“以前我不敢触及,这牵涉到我的亲属,我的家庭”[13]246,父的缺失造成了贾平凹的生命残缺,也成为他抒写棣花街的触媒和契机。
“家”的“破缺”是“父”的缺失的直接现实,也是破碎现实的重要构成。父亲的逝世造成贾平凹家的破缺,这和1992年贾平凹婚姻破裂对他的影响极为类似。《废都》被贾平凹视为“唯一能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12]63的作品,创作《废都》时,贾平凹婚姻破裂,妹夫离世、父母病重、单位是非、流言蜚语接踵而来,“几十年奋斗的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12]55。家的破缺是贾平凹“生命之链”在40岁“断脱”的外化,“求缺”内蕴着曾经营造的世界变为破碎的现实。这部“止心慌之作”是贾平凹“生命之轮运转时出现的破缺和破缺在运转中生命得以修复的过程”[12]64。《秦腔》是贾平凹另一部安妥灵魂之作。创作《秦腔》时,贾平凹面临着更为严峻的破碎现实,“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的没了”[12]152,“这就像是在单位受了气,回家找老婆、孩子安慰,宣泄。但现在没有这个出口了……这种现状,就让人想回家,却回不去了”[13]243。家的破缺导致避风港湾不复存在,现实破碎使贾平凹只能借助写作宣泄情感、安妥灵魂,“《秦腔》的写作使我的灵魂得到了一种安妥”[12]147,“是我的宣泄”[12]143。《秦腔》是贾平凹的生命体验,也是他生命的另一种形式,是其生命完滿自足的出口。《秦腔》“是我对中国大陆在世纪之交社会巨变时期所做的一份生活记录,也是对我的故乡我的家族的一段情感上的沉痛记忆”[12]146。不难看出,贾平凹的痛苦还源于与社会进程同步的融会贯通,他的个人情感与父老乡亲一代人的社会情感是相通的。抒情主体先已是社会的产物,抒情的自我诉求,也必然透露着社会的情绪。贾平凹并未停留在个人的悲痛之中,而是将个人和父老乡亲的乡愁之痛升华到民族国家之悲,“当年拟《废都》是斜着翅膀飞翔的,这本《秦腔》可能还依然是贴着地而在飞”[12]144。抒情主体的情感之痛即是乡愁的见证,也是时代的病征。贾平凹的个人之痛是如何上升为父老乡亲的悲哀的?贾平凹的故乡之悲又是如何上升为当代中国乡土之悲的?当代中国乡土的悲哀是否是贾平凹乡愁书写的终点?这些问题都聚焦于秦腔戏如何联结着《秦腔》的实与虚、有与无、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
在形式上,秦腔戏的嵌入构成小说的“天窗”结构,实践着贾平凹以实写虚、体无证有的抒情美学。“在《秦腔》那本书里,我主张过以实写虚,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12]217。贾平凹将整个小说比作房子,小说的实像实境构成房子的实体,小说的虚像虚境犹如房内的阳光和空气,而它们是透过天窗进出的,这个“天窗”实际上就是小说虚实相生的路径——秦腔戏。贾平凹很早就有将戏曲引入小说的艺术实践,《浮躁》《商州》引用1次、《土门》3次、《白夜》29次。《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高兴》《天狗》《废都》《五魁》《鸡窝洼人家》《小月前本》《腊月·正月》等作品也涉及戏曲。据不完全统计,小说《秦腔》引用戏文74次,嵌入的戏曲构成小说由实到虚、抒情写意的有效形式。
在戏曲之外,贾平凹还引碑文、歌谣、短信、山海经等内容入小说,使“天窗”结构有着丰富而多维的艺术空间。《商州》每章的第一节对地方风俗人情的描绘,颇有地方志特色。《古堡》中交叉叙述商鞅变法的故事,使现实变革与古人的开创精神交相辉映。《废都》中破烂老人吟唱着破烂歌谣,隐喻着西京变为破烂的“废都”主题。《白夜》中《目连戏》人鬼同台的演出,暗示着人情世态的混杂。《高老庄》中的碑文记录着村庄历史,暗含了“文化僵死,人种退化”[13]286的现代焦虑。《病相报告》中四幅画纸记录的屏风文字,组合地讲述着“人病”的故事。《高兴》中插入锁骨菩萨的碑文,隐含着刘高兴等底层人“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12]180的精神意蕴。《怀念狼》中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古炉》中闪烁着善人的“说病”,《带灯》中镶嵌着发给元天亮的抒情短信,《老生》中以山海经及问答引领着小说精神,《极花》中描绘着水墨画般的乡村,几乎每部长篇都实践着“天窗”结构,这种结构联结着具象与想象的两端,沟通着有形的日常生活与无形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和文化世界,实现着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
“天窗”结构是贾平凹在以实写虚、体无证有的艺术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感悟。1990年的短篇小说《太白山记》是贾平凹以实写虚创作风格的肇始。《太白山记》“第一回试图以实写虚,即把一种意识,以实景写出来,以后的十年里,我热衷于意象,总想使小说有多义性,或者说使现实生活进入诗意,或者说如火对于焰,如珠玉对于宝气的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结合”[12]114。可见,在转型试验之初,贾平凹就有着抒情写意的追求,即通过张扬意象,以实写虚,体无证有。然而,贾平凹对以实写虚的感悟尚处朦胧阶段,并未摆脱“生硬”与“强加的痕迹”[12]114,也未能觅得适宜的门径。
《怀念狼》中贾平凹对小说的“天窗结构”有了初次的觉悟。画家贾克梅蒂感悟水性而放弃传统写实主义的故事,让贾平凹“觉悟了老子关于容器和窗的解释,物象作为客观事物而存在着,存在的本质意义是以它们的有用性显现的,而它们的有用性正是由它们的空无的空间来决定的,存在成为无的形象,无成为存在的根据”[12]115。贾平凹首次提出“窗”所连接的有与无、实与虚的辩证,“窗”成为由实通往虚的法门和通道,这是小说“天窗结构”的理论雏形。然而,贾平凹也注意到“当写作以整体来作为意象而处理时,则需要用具体的事物,也就是生活的流程来完成”, “如此越写的实,越生活化,越是虚,越具有意象”[12]115。《怀念狼》将情节处理成意象,在整体意象的营造中“以实写虚,体无证有”[12]115成为其兴趣所在。
201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古炉》对“天窗”结构有着清晰而准确的认识。《古炉》与《秦腔》密实的流年式叙写一脉相承,它采用写实的方法把烧瓷的古炉村写活了,“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是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12]217。在《古炉》后记中贾平凹以“房子” “阳光” “空气”等物象隐喻小说《秦腔》的“天窗”结构。如果说《怀念狼》关于“天窗结构”的论述尚处于初步感知的阶段,那么到了《古炉》,它已成为贾平凹有意识的艺术自觉。在《古炉》中善人的“说病”直接构成小说的“天窗”。“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28],善人的“说病”构成与现实暴戾空间相对的另一个和谐空间。
《山本》中,贾平凹对“天窗”结构的运用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2017年的长篇小说《山本》的写实手法与《秦腔》《古炉》具有“血缘宗亲”关系。在《山本·后记》中,贾平凹明确表达了对“开天窗”的追求,“另一种让我好奇的是房子,不论是瓦房或是草屋,绝对都有天窗,不在房屋顶,装在门上端,问过那里的老乡,全在说平日通风走烟,人死时,神鬼要进来,灵魂要出去。《山本》里,我是一腾出手就想开这样的天窗”[29]544。《山本》中沟通实虚的法门不是戏曲或说教内容,而是陆菊人和陈先生的谈话。如果说在长篇小说中嵌入戏曲、民歌等内容,具有明显的拼贴痕迹,那么在写作《山本》时,贾平凹已能够将形而上的哲思融入到人物日常的谈话之中,克服了与“道法自然”相矛盾的文艺腔和说教腔。
《秦腔》是賈平凹“天窗”结构的典型文本,秦腔戏勾连着鸡零狗碎的日常生活与抒情写意的诗意空间。那么,它又是如何升华贾平凹的抒情写意的?贾平凹又是如何通过秦腔将个人的、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内容融进自己的象征体系的?
三、“伤逝”美学与天人合一的文学境界
秦腔戏联结着个人的地方认同、当下的现代焦虑和积淀的历史情感,贾平凹通过秦腔这一象征体系将当代乡愁编织到“伤逝”的母题之中,建构了循环的天地人合一的人生观和观物方式,中国乡土的裂变不过是过去的经验和过去的事件乃至未来的希望在天地间的当下呈现。秦腔戏联结着个人史、当代史和古代史三个维度的历史,把“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29]545熔于一炉。秦腔的移情作用,构成贾平凹及普通个体的地方认同和进入小说的通道;秦腔的衰落映照着中国乡土的分崩离析和现代文明尚未孕育新路的当代现实;秦腔积淀着深广的历史情感与文化记忆,传达出哀挽的“伤逝”之情,应和着人事在天地间巡演的历史之感。
秦腔链接着个人与地方的情感和文化认同。贾平凹担心个体能否“进入”小说,而秦腔戏使贾平凹及广大个体“内部化”于地方,成为个体进入小说的有效途径。诺伯·舒茨指出,“内部化” 就是“存在于某处,并远离外部性”[30]81-82,内部化就是个体不断地属于某个地方,并与该地方相认同。听曲看戏是贾平凹深度体验地方的重要形式,戏曲拉近了他与地方的距离,达成对地方的情感应和与文化认同,“我有一癖性,大凡到了一地,总喜欢听本地戏文,因为本地戏剧最易于表现当地风土人情。但听听别的戏文,仅仅是了解罢了,秦腔却使我立即缩短了陌地陌人的距离”[31]226。秦腔本身包含着物质环境的内容。词、乐、舞一体的戏曲调动着观众的视听感官,感性的参与伴随着移情作用,引发情感的共鸣。秦腔还承载着鲜活的日常行动。庆玉建房时,“秦腔一放,人就来了精神,砌砖的一边跟着唱,一边砌砖,泥刀还磕得砖呱呱地响。搬砖的也跑,提泥包的也跑”[25]61。这种物质环境与人物行为的结合提供了事物的功能效果,普通人在戏曲中回到自己熟悉而亲近的日常生活,又在日常生活场景中找到唱词中普遍而共通的集体情感。秦腔还内蕴着秦人的文化意义。苏珊·朗格指出“地方是由文化来定义的”[30]47。彼得·伯格认为文化的同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行为层次,即行为上不带任何情感、以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到某种文化。二是移情层次,保持着客观意识将自己的行为与情感投入到某种文化,且不让自己成为文化中的一员。三是认知层次或“成为本地人”[30]79。秦腔是秦地人生活方式、生存模式的意义系统。听曲看戏这种沉浸式的生命活动,进入到移情和认知层次,将地方认同的原材料(物质环境、人的行动和意义)有机结合起来,构成地方认同的基本结构关系,使个人与地方互相认同,人成为地方的一部分,地方也成了人的一部分。秦腔作为最鲜活、最生动的地方文化载体,在普通人的实有世界构成现实的共同体,在虚在的精神世界形成想象的共同体,两者构成个人情感参与和文化参与的张力场,成为个体进入小说的路径,而《秦腔》也成为父老乡亲、秦地人乃至一代人的乡愁代言。
《秦腔》映照着当下普遍存在的现代性焦虑。父母是贾平凹与故乡的纽带,“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 “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的次数减少” “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12]154爱德华·雷尔夫指出,地方经验中总存在着对特定地方的紧密依附与熟悉感[30]60。贾平凹与故乡联系渐少,说到底是对故乡情感依附的弱化和熟悉感的消逝。贾平凹走过棣花街,父老托生的面熟之感,是其寻觅地方熟悉感的情感惯性。“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失去的父老的托生”[12]154。随着亲人、熟人的离世,贾平凹对故乡的依附和熟悉感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形态,故乡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待到“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同辈人“也开始在死去”[12]154,“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态”,故乡“越来越陌生” “都再不属于我”[12]154-155。父亲的逝世是故乡消亡的开始,父的缺失、家的破缺和故乡的破碎是同构的,也是同步的,贾平凹的哀悼也必然有着复杂的意蕴。然而,故乡的消失是以秦腔的衰落为表征的,“秦腔是地方戏曲,它的另一种意思是秦人之腔”,“他的衰败是注定的,传统文化的衰败也是注定的”[13]240。贾平凹通过秦腔这一文化符号扩大了故乡的所指,勾连起整个秦地人的生存状态,而《秦腔》的土性与民间性,使其成为当代中国乡土破碎的写照。“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12]152。贾平凹既焦虑着现代化摧毁旧有乡土带来的生存难题,又对现代文明尚未孕育新路充满忧虑。《秦腔》开篇,夏风和白雪的婚礼现场,疯子引生却本真地捕捉到乡土分崩离析的命运,“眼看着你起高楼,眼看着你酬宾宴,眼看着你楼塌了……”[25]9一曲沉郁凄怆的“哀江南”成为当代中国乡土“废乡”的寓言。王蒙认为李杭育寻根文学中的渔佬儿和画师、弄潮儿等人物“像上一代的遗民”[32],贺桂梅将这些人物称为“最后一个”[33]。《秦腔》也塑造了当代中国乡土的最后一个传统农民。夏天义热爱土地,秉持集体主义,信仰传统农业,是乡土传统文化“义”的代言者。七里沟於地失败,作者以一曲《韩单童》唱出了夏天义的孤独与悲凉:“我单童秦不道为人之短,这件事处在了无其奈间……你言说二贤庄难以立站,修一座三进府只把身安”[25]257。夏天义的失败是传统农民和传统农业方式被现代化淘汰的真实写照。
秦腔的另一端联结着现代性的流行歌曲。夏天智、夏天义等父辈热爱秦腔,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夏风、夏雨等新生一代赞赏流行音乐。过去唱秦腔是做人“最体面”的事,而土生土长的夏风非常厌烦秦腔,“瞧我爹,啥事都让他弄成秦腔了!”“我就烦秦腔”[25]10。夏风眼中,秦腔是“农民的艺术”,歌星演唱会是时髦、文明、现代化的“城里人的艺术”。夏雨酒楼开业,上午演秦腔,下午和晚上唱起了流行歌曲,“清风街的年轻人都跑了来,酒楼前的街道上人挤得水泄不通”[25]261。酒楼开业仪式中,汇聚着巨大的声音空间,观众在秦腔与流行歌曲之间出现认同分裂。流行歌曲以柔性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促成群众对现代化的情感认同。中星卖力宣传秦腔,听众的热情已经淡漠;陈星的吉他声一登场,就招揽了大量顾客,把农贸市场的山货一扫而空。流行音乐携带的销售力量隐喻着现代化的市场交换逻辑,也隐喻着村鎮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进程。然而,现代化并没有孕育出乡土的发展出路,夏雨的酒楼成了钱色交易的场所,“村镇里没有了精壮劳力”,老弱妇孺留守故土,“死了人都煎熬抬不到坟里去”[12]154。进城的姑娘们回乡后打扮得花枝招展,问起职业都缄口不提;进城的男性如五富、高兴(《高兴》)等成为流落街头的拾荒者,落得背尸还乡的结局。
秦腔积淀着历史的情感记忆。对贾平凹来说,写作是情感的抒发,记忆的镂刻,是“生命的一种形式”[13]106。故乡的消亡是生命记忆的消逝,贾平凹试图以艺术的形式保存曾有的生命经验,求得生命的完满与自足。“我只是想把自己一直憋着的感情抒发出来。所以我写《秦腔》就像完成一个交代,心灵的交代”[15]“现在我为故乡写这一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记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竖起一块碑子”[12]155。以秦腔的衰落为表征,词、乐、舞一体的秦腔,带来直观鲜活的视觉感受,声乐的穿透力能够穿越时空,引发人们的历史联想,唤醒人们久远的历史记忆,触发深广的历史情感与集体无意识。《秦腔》开篇的《哀江南》是传奇《桃花扇》余韵里的曲子,“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25]9。《哀江南》中,明清易代之际的笛师苏昆生混迹秦淮旧院,重游南京故地,面对废池乔木,缅怀旧日繁华,抚今思昔。苏昆生的歌哭唱尽黍离之哀情,这里的悲情是吉川幸次郎所说的“物”的“推移的悲哀”[24]51。吉川幸次郎认为这种推移的悲哀有三类:一是“对不幸时间的持续而起的悲哀”;二是“在时间的推移中由幸福转到不幸的悲哀”;三是“感到人生只是向终极的不幸即死亡推移的一段时间而引起的悲哀”[24]54。《秦腔》呈现了“由幸转向不幸”的悲哀,故乡像“一个苹果烂了,没办法再救它,你挖,把坏的刨掉,第二天,那个地方又坏掉了。像病来了,排山倒海就来了,这个专家那个专家开药方,出主意,都不济事”[13]248。贾平凹把《哀江南》作为乡土破碎的挽歌,借《韩单童》为难以安身立命的农民扼腕叹息。《韩单童》源于《隋唐演义》,隋末唐初瓦岗寨众兄弟顺应时势投靠新朝大唐,独单童投了洛阳王世充,洛阳沦陷后单童成为旧朝遗民,英勇就义。《秦腔》中夏天义表征着难以安身立命的农民,商品经济大潮把夏天义推到时势的对立面,垂老迟暮的夏天义不合时宜地想向人们证明“土地是不会亏待人”,却迎来了众叛亲离、生命消殒的落寞命运。尘归尘、土归土,七里沟埋葬了中国乡土最后一位传统农民。“我单童秦不道为人之短,这件事处在了无其奈间……你言说二贤庄难以立站,修一座三进府只把身安”[25]457。将自己燃烧的单雄信和被时代搁置的夏天义,有着相通的遗民韵味,《韩单童》唱出了当代“遗民”的悲凉。
“哀江南”的主题源于屈原,经由后世文人的继承性创作,成为反复出现的“母题”,沉淀着更为深广的民族情感与文化记忆。屈原去国离乡,招魂怀王——“魂兮归来,哀江南”,尽显山河破碎的大悲哀。南朝庾信出使北朝,被侯景之乱隔绝,滞留北方,直到隋朝建立仍难以还乡,“虽位望显通,常作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34]。庾信《哀江南赋》有着“缅王室、述祖德、叙时事、寄哀情”[35]的深广意蕴。后世文人不断加入“哀江南”的主题创作,使其成为表达故国之哀、乡关之思的“母题”。后世的谢翱(《续琴操·哀江南》)、谢榛(《哀江南诗八首》)、毛奇龄(《续哀江南赋》)、孔尚任(《桃花扇·哀江南》)、金应麟(《哀江南赋》)、王闿运(《哀江南赋》)和陈樵(《哀江南效李义山》)等人亦有相类作品,更有杜甫(《北征》《八哀诗》)、李华(《吊古战场文》)、夏完淳(《大哀赋》)和章炳麟(《哀韩赋》《哀山东赋》)等人的创作继承庾信“哀挽江南”的精神。抒情主体在一己之时代,以个人切身经验,应和前人的哀挽和叹息,在“感物”当下与“感悟”古人的对话中形成了“哀挽”的抒情母题与精神,滋生“伤逝”的抒情美学。
《秦腔》通过戏文应和“哀江南”的思乡母题,将当代乡愁融入历史的“伤逝”之情,应和着古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历史巡演。郜元宝把《秦腔》看作贾平凹“情感上对这个世界的埋葬与告别”[13]244,贾平凹哀挽着“从此失去记忆”和“不能回去了”[13]242的故乡,体会到人生、时代必将走向终极的死亡,“没有人不死去的,没有时代不死去的”[36],这正是吉川幸次郎所谓的“推移的悲哀”,也是“叹逝”之情。故乡的消失是历史事件、经验以及未来的希望在当下的呈现。秦腔扩展了小说的空间,能为“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代言的“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31]240。秦腔延伸了小说的时间,秦腔起于西周,成熟于秦,是“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31]235。人们谈及盛世,必首称秦汉大唐,秦腔作为秦文化符号是中国盛世文化的代表,这使盛与衰的变迁增添了几分张力。贾平凹有意借助秦腔的土性与民间性为中国乡土代言,“秦人自古是大苦大乐之民众” ,“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31]240。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守候在天空之下、大地之上的秦人,犹如中国乡土的当代遗民。借助时空的延伸和民间的土性,《秦腔》呈现着中国乡土与传统文化失落的当代图景。
“尊四时以叹逝,瞻万物以思纷”。贾平凹在心会古人的对话中,目睹故乡传统形态的消亡,将叹逝之情编织进“伤逝”、思乡的母题,将中国乡土与传统文化失落的当代图景嵌入历史的长河,当下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断片。“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历史的经验与未来的想象在当下联合出演,贾平凹在感物与感悟的对话中察觉自己的渺小与无能为力,从而跳出进化的时间观,建立起循环的天地人合一的人生观和观物方式。《老生》写出中国的百年史,跳出狭隘的“乡愁”,看到任何人与时代终将死去,时代的更替,如同高楼的起落,主体的抒情不过是历史的抒情。《暂坐》结尾曾经“活力充满,享受时尚,不愿羁绊,永远自我”的现代女性作鸟兽散去,热闹一时的茶庄爆炸了,“蘑菇状的黑烟隆起” “响着一连串的崩坍声,玻璃和瓷器的破碎声”,新生的现代都市在坍塌中“留给我的只是叹息”[37]。《山本》涡镇变成了一堆尘土,“一堆尘土也就是秦岭上的一堆尘土么” “屋院之后,城墙之后,远处的山峰层峦叠嶂,一尽着黛青”[29]539。这毋宁是“哀江南”之后的超然,“鬼魅狰狞,上帝无言”[12]54,一时的人事不过是天地间轮回出演的一幕大戏。贾平凹将当下嵌入历史,将人事纳入天地的范畴,展现出阔大而旷达的抒情境界。
如果把《秦腔》比作贾平凹书写当代乡愁的抒情诗,那么秦腔戏就是这首抒情诗中反复吟咏的典故。它将个人的、自然的、历史的、文化的内容纳入到天地人合一的象征体系,当代中国乡土的裂变成了过去、未来和当下在天地间联合演出的大戏,在人事与历史的交融激荡里发出了沉郁顿挫的“伤逝”之声。《秦腔》将个人史、当代史和古代史融入现实破碎的当下语境,将个人嵌入历史的众生,将当下嵌入历史的长河,个人不过是历史的一叶扁舟,当下不过是历史的断片,人事不过是天地间的戏曲。由此,贾平凹超越线性时间,建立起循环的天地人合一的人生观和观物方式,看到历史的轮回演出,在人事、历史与天地的交相辉映中,奏出一曲沉郁顿挫的穹音。
参考文献:
[1] 王建仓.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的境界叙事和意象叙事[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189-243.
[2] 王德威.暴力叙事与抒情风格——贾平凹的《古炉》及其他[J].南方文坛,2011(4):22-24.
[3] 杨辉.贾平凹与“大文学史”[J].文艺争鸣,2017(6):83-97.
[4] 吴义勤,王金胜.抒情话语的再造——《山本》论之二[J].文艺争鸣,2018(6):116-124.
[5]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35.
[6] 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4.
[7]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220.
[8] 嚴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231.
[9] 李扬.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路”(1942—1976)研究[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145.
[10] 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234.
[11]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J].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85(9):179-180.
[12] 贾平凹.关于小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3] 贾平凹.访谈[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14] 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67-80.
[15] 陈思和,杨剑龙,王鸿生,等.秦腔:一曲挽歌,一段情深——上海《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J].当代作家评论,2005(5):33-37.
[16] 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77.
[17] 贾平凹.极花[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210.
[18]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第12卷[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8:15.
[19] 杨辉.大文学视域下的贾平凹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39-238.
[20] 许爱珠.守望中的裂变:贾平凹长篇小说创作论[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77.
[21] 任树民.艺术特质视域下中国抒情传统研究——以两汉诗学接受为中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22] 贾平凹.做个自在人——贾平凹序跋书话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8:272.
[23] 何丹萌.见证贾平凹[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1:131.
[24] 吕正惠.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5] 贾平凹.秦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6] 贾平凹.我是农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19.
[27] 孙见喜.贾平凹前传·鬼才出世[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44.
[28] 贾平凹.古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605.
[29] 贾平凹.山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30] 爱德华·雷尔夫.地方与无地方[M].上海:商务印书馆,2021.
[31]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散文:第1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32] 王蒙.葛川江的魅力[J].当代杂志,1985(1):235-237.
[33] 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底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253.
[3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6-159.
[35] 何世剑.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表征及内蕴[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96-101.
[36] 贾平凹.老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295.
[37] 贾平凹.暂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274.
责任编辑:王维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