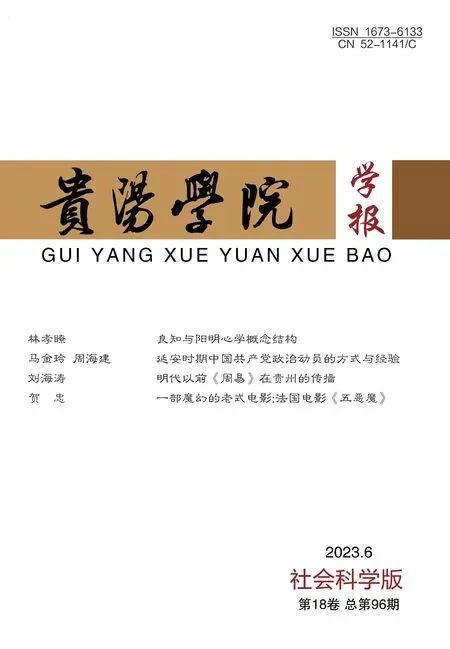良知与阳明心学概念结构
林孝暸
(中国计量大学 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阳明以“良知”替代“天理”,并通过对程颐“体用一源”学说的一元论诠释,最终突破了朱熹理学的概念结构的束缚。具体而言,阳明以“良知”这一“心之本体”为核心概念,围绕心与物、心与理、心与气、心与事、心与性、心与身、心与学、心与善、心与意、心与知、心与行、心与圣等关系问题,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心学一元论概念结构。
一
“良知”是阳明心学最核心的概念,所以阳明会说“吾平日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1]1092,还说“‘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1]80。阳明以“良知”为心学宗旨,有一个发展的过程。黄宗羲评价阳明学说时曾指出,“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2]《王阳明全集·年谱二》中亦云:
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曰:“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曰:“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1]1412
“存天理去人欲”,是朱熹理学的核心命题。所谓“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如也”,可见阳明此时虽然还以“天理”为思想宗旨,但已经转向“自求之”的心学内求路径①(1)①“龙场悟道”是阳明从理学外求路径转向心学内求路径的标志性事件,即所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王守仁:《王阳明全集》(吴光、钱明、董平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54页)。。相应地,阳明对于“天理”的理解已经与朱熹有所不同,只是缺乏恰当的概念予以表达。所谓“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是说阳明经历“宸濠忠泰之变”以后,在讲学上开始以“良知”替代“天理”。阳明还曾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1]1290据此,阳明在龙场悟道后虽然已由理学转向心学,但还未能以“良知”来概括其心学宗旨,这也正是其所谓“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之意。当阳明以“良知”替代“天理”,并将之作为心学宗旨后,才真正冲破了朱熹理学概念结构的束缚,建立起新的心学概念结构。
首先,阳明将“良知”理解成“心之本体”[1]69。“本体”在阳明心学中与“工夫”相对,亦即传统体用之辨中的“体”。程颐就曾以“体用”这对范畴来诠释“心一”,说:“心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3]609关于“体用”,程颐在《周易程氏传·易传序》中还提出过“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理学重要命题。后来,朱熹一方面继承程颐“体用一源”的说法,另一方面却以“两物”来解释“体”与“用”的关系,说:“体用是两物而不相离,故可以言一源。”[4]朱熹还将“体”与“用”的分别理解为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说:“至于形而上下,却有分别。须分别得此是体,彼是用,方得说‘一源’……若只是一物,却不须更说一源、无间也。”[5]朱熹将“体”与“用”理解为“两物”,不仅将“心”与“物”理解为“两物”,而且将“心”二分为“道心”与“人心”,这与程颐“心一”的主张有所不同。阳明则以体用不二来理解程颐的“体用一源”,说:“夫体用一源也,知体之所以为用,则知用之所以为体者矣。”[1]165因此,“良知”作为“心之本体”,亦是体用不二,即所谓“体即良知之体,用即良知之用”[1]71。
其次,阳明还以“一”来规定“良知”,说:“夫良知,一也。”[1]70阳明因此肯定程颐“心一”的主张,反对朱熹将“道心”与“人心”截然二分的理解,说:“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1]8这里,阳明把“人心”说成“道心之失其正者”,正是将“人心”理解为“道心”之用。可见,阳明此处所谓“心一”是就体用不二而言。另外,陆九渊曾以“心即理”反对朱熹将“理”归之于“天”的思想,说:
天理人欲之言,亦自不是至论。若天是理,人是欲,则是天人不同矣。此其原盖出于老氏。[6]
阳明认可陆九渊对朱熹天人二分的批评,强调“人心天理浑然”[1]13,还说:“朱子所谓‘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即物穷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1]50在阳明这里,“心一”也意味着“心即理”。他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以其条理而言谓之理。”[1]48可见,阳明主张“心即性,性即理”[1]17。
阳明将“良知”这一“心之本体”与“一”这一概念相联系,使其心学思想具有鲜明的还原论特征。阳明心学存在两个概念体系:一个属于本体(即“体”)的概念体系,如性、理、天、道等;另一个属于工夫(即“用”)的概念体系,如意、知、行、事、物等。阳明讲“体用一源”不仅在体用关系上强调体用不二,而且在本体上主张“一体”(即只有一个本体),如所谓“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1]122。阳明“体用一源”的还原论思想,不仅体现在前述的“心一”主张上,而且体现在“理一”“性一”等主张上。比如,阳明说:
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1]86-87
这里阳明将“性”理解为“理之凝聚”,将“心”理解为“凝聚之主宰”,这是从一体的本体论讲“理一”;将“意”理解为“主宰之发动”,将“知”理解为“发动之明觉”,将“物”理解为“明觉之感应”,这是从体用不二的体用观讲“理一”。另外,阳明还讲“性一”②(2)②陆九渊曾说:“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陆九渊集·语录下》)陆氏这里所谓的“言”即阳明所谓的“名”,近于现今“所谓”的概念。早在先秦的“名实”之辩中,《庄子·知北游》就已经提出“异名同实,其指一也”的主张。可见,阳明“性一”的主张与其对名实关系的理解亦密切相关。,说:
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1]17-18
阳明认为,天、帝、命、性、心、孝、忠等虽然是不同的概念,却都只是“一性而已”。其中,天、帝、命、心均是“一性”,体现的是阳明“一体”的本体论;而孝、忠作为“心之发”,亦只是“一性”,体现的则是阳明体用不二的体用观。概而言之,“体用一源”的一元论构成了阳明建构其心学概念结构的基本方法论。
阳明借助“体用一源”的一元论诠释,将“良知”概念不断地形而上学化,并最终确立起了新的心学概念结构。“良知”这一概念最早由孟子提出,即所谓“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7]。阳明继承了孟子对“良知”的理解,说:“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1]1070但需要注意的是,“良知”在孟子哲学中只是一个表示主体具有先验道德意识的普通概念。“良知”能成为阳明心学的核心概念,离不开“良知”概念的形而上学化。其中,阳明以“心之本体”来规定“良知”,是“良知”这一心学概念的形上地位得以确立的根本原因。此外,阳明将“天理”也理解为“心之本体”,所谓“夫心之本体,即天理也”[1]212。进而,阳明会说:“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1]81阳明通过“良知即是天理”这一命题,使“良知”这一概念具有了与“天理”相当的形上地位。阳明不仅主张“良知即是天理”,而且认为“夫良知即是道”[1]78,“道即是良知”[1]120。阳明将“良知”与本体、天理、道等传统的形上概念相联系,这正是“良知”这一心学概念形而上学化的具体表现。金岳霖认为“道”是中国哲学中最上的概念,阳明将“良知”等同于“道”,也就赋予了“良知”心学中最上概念的地位。
二
心物之辨,是阳明心学本体论的核心问题。围绕心物之辨,阳明不仅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等重要的心学命题,还将“良知”与“天、物、理、气、精、神”等本体论概念相统一,建立起具有浓厚的唯我论特征的心学本体论。
阳明通过“心外无物”这一命题,赋予“心”这一概念以宇宙本体论的意义。早在《易·彖传》中,已经有“天地之心”的说法。后来,二程亦云:“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3]13阳明亦将“人”理解为“天地万物之心”,说:“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1]238阳明是从“人”这一主体来理解“心”,进而主张“心即天”。“良知”是“心之本体”,所以“天即良知也”“良知即天也”[1]125。阳明甚至主张天地万物亦是从“良知”而出: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1]119
钱穆认为阳明这是“把良知说成是天地万物后面的一个绝对实体”,“人的良知乃与上帝造物一样”。[8]其实,“良知”在阳明这里“与物无对”,并不是一个与物相对的绝对本体或造物主。
“良知”之所以“与物无对”,是因为“良知”是“神、气、精”的统一体。阳明说:“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谓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谓之气,以其凝聚而言谓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1]70其中,“气”正是人与万物一体的本体论根据。阳明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1]122与此相应,阳明反对朱熹理气二分的理解,强调理是“精一之精”,气是“精神之精”,从而理是“气之条理”,气是“理之运用”。所以,理气在阳明这里是不二的,因为“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矣”[1]70。另外,阳明在主张人与天地万物“同此一气”的基础上,还从感应上讲天人一体,说:“你只在感应之几上看,岂但禽兽草木,虽天地也与我同体的,鬼神也与我同体的。”[1]141阳明不仅主张天人一体,而且认为“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1]122。
阳明心学中的“良知”虽是本体,却不是实体。在宋明理学中,“实”与“虚”是一组相对的概念。二程曾说:“皆是理,安得谓之虚?天下无实于理者。”[3]66朱熹继承了二程“实理”的主张,说:“理一也,以其实有”[9],“天下之物,皆实理之所为”[10]。阳明虽然以“良知”为“心之本体”,却以“虚”与“无”来诠释“良知”,说:“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1]121阳明在强调“良知”为虚无的同时,对“仙家说虚”“佛氏说无”的思想进行了辨析。一方面,阳明肯定了仙家与佛氏的虚无立场,说:“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另一方面,阳明认为:“仙家说虚,从养生上来;佛氏说无,从出离生死苦海上来,却于本体上加却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了。”[1]121阳明要求扬弃仙家、佛氏对本体虚无的见解,说:“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思在。”[1]121阳明在强调良知以虚无为本色的同时,又肯定良知作为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天地万物都依赖良知而存在,[11]阳明以“生生不息”理解“良知”,正是源于易学传统。所以,阳明会说:“良知即是‘易’。”[1]142“良知”作为“心之本体”具有生生不息且虚无的特点,进而阳明提出“心无体”的主张,说:
目无体,以万物之色为体;耳无体,以万物之声为体;鼻无体,以万物之臭为体;口无体,以万物之味为体;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1]123
阳明主张“心无体”并不是取消“良知”的本体地位,而是否认“良知”是与物有对的实体。所以,阳明在肯定“心无体”的同时,又指出心是“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黄宗羲《明儒学案·自序》中所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12],正源于阳明“心无体”这一思想。
在阳明心学中,心物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天人之辨,也涉及身心之辨。在身心之辨上,阳明强调“无心则无身,无身则无心”[1]103。其中,身是心的充塞处,如耳、目、口、鼻、四肢;心是身的主宰处,如视、听、言、动。阳明在这里不仅将心视为“身之主宰”,还将“意、知、物”理解为心的“发用流行”,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6阳明基于对身心关系的上述理解,进一步将物视为“意之所用”,主张“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1]53。进而,阳明提出了“心外无物”的命题,说:“心外无物。如吾心发一念孝亲,即孝亲便是物。”[1]28阳明这里讲“孝亲便是物”,与其主张“物即事”的思想有关。阳明说:“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1]53所以,“心外无物”也就是“心外无事”。阳明还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1]2可见,阳明“心即理”的思想,亦源于“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主张。阳明“心外无物”的主张,在当时就受到了质疑。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1]122
在这里,友人强调花树作为自在之物,是一“自开自落”的本然存在。阳明则将花树看作为我之物,认为其明白呈现离不开人的观看。与此相应,阳明强调主体精神对世界的主宰作用,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1]141在阳明这里,自然世界的意义依赖于主体精神,自我精神的消失也就意味着其生存世界的消失。所以,阳明会说:“今看死的人,他这些精灵游散了,他的天地鬼神万物尚在何处?”[1]141其实,自我的生存世界是意义界与本然界的统一,并不存在独立于本然世界之外的意义世界。以世界为实在,不仅是儒家哲学的主流,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阳明以世界的为我意义消解世界的自在意义,从而呈现出鲜明的唯我论特征。
三
知行之辨,是阳明心学工夫论的核心问题。在知行之辨上,阳明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知行分离说,主张“致良知”的知行合一说。阳明将“知”与“行”都理解为“一念发动处”,进而主张“心外无学”,认为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1]312。阳明以“心外无学”这一命题为基础,将“良知”与工夫论域中的“善、意、知、行、圣”等概念相联系,建立起知行合一的心学工夫论。
阳明晚年曾以四句教来概括其心学工夫论,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133阳明以“无善无恶”来理解心体,与其以“虚无”为心体本色的思想有关。阳明曾说:“心之本体原无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恶恶,便又多了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书》所谓‘无有作好作恶’,方是本体。”[1]39与此相应,阳明不将善恶归之于心体,而是归之于意欲,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1]33另外,良知作为“心之体”虽然“无善无恶”,却有“知善知恶”的能力。阳明亦由此强调“意”与“良知”的不同,说:“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1]242“良知”与“意”的差别,正是本体与工夫的不同。概而言之,四句教中的“无善无恶”是就本体而言,“有善有恶”“知善知恶”“为善去恶”则是就工夫而言。
阳明的四句教与其对《大学》的诠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四句教中的“心、意、知、物”这四个概念正对应于《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与朱熹以穷理诠释格物不同,阳明以“为善去恶”解释格物,格物因此亦由朱熹理学认识论的概念转变为心学工夫论的概念。在阳明心学中,本体与工夫虽有不同,但亦是“体用一源”。与此相应,《大学》中的“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等概念在阳明心学工夫论中亦获得了统一的理解。其中,“意”是阳明诠释《大学》的关键概念。在阳明看来,“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1]1070。所以,正心必须就意念之所发而正之。具体而言,“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1]1070。这样,正心与诚意就获得了统一,即所谓“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1]1070。另外,诚意又有赖于致知。阳明说:“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焉。”[1]1070致知并非悬空无实,而是实有其事,即所谓“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1]1071。所以,致知必在于格物。阳明还将“格”解释为“正”,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1]1071所以,正心也就是从事“为善去恶”的格物工夫。在阳明心学中,“盖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功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1]1069。
在阳明这里,不仅“身、心、意、知、物”只是“一物”,而且“善恶”亦只是“一物”。《传习录下·门人黄直录》中记载: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直因闻先生之说,则知程子所谓“善固性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又曰:“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本非恶,但于本性上过与不及之间耳。”其说皆无可疑。[1]110
据此,阳明以“过”来理解“恶”正与程颢相同,其所谓“善恶只是一物”与程颢的“善恶皆天理”亦有相通之处。只是程颢讲“善恶皆天理”,还有从先验的角度来理解善恶的倾向。阳明则将“心之体”理解为无善无恶,亦即“至善”,如前所谓“至善者,心之本体”,并将具体的善恶归之于“意”,说:“有善有恶又在物感上看,便有个物在外,却做两边看了,便会差。无善无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时,只此一句便尽了,更无有内外之间。”[1]122由此,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1]109-110在阳明这里,不仅“意”是“应物起念处”,而且“一念发动处,便是知,亦便是行”[1]1293。所以,阳明主张知行亦只是一件事,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1]47,“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1]15。阳明因而批评朱熹“知先行后”的说法,强调“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1]15。
阳明不仅以知行合一来诠释圣学工夫,还进一步以“致良知”来概括圣人之学,说: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1]312
阳明从“致良知”的视域出发,将人区分为圣人、贤人与愚不肖者三个层次,认为圣人是“自然而致之者”,贤人是“勉然而致之者”,愚不肖者是“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阳明一方面从“致良知”这一工夫视域强调人有圣人、贤人和愚不肖者的差别,但另一方面又从良知本体的视域肯定“良知所以为圣愚同具”,“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人心有仲尼”。在阳明这里,良知虽是人人皆有,但有能致和不能致的差别。
孰无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谓“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1]211
可见,阳明讲“致良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知至”,这是知;二是“至之”,这是行。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所言“致字即是行字”[2]178,在阳明这里,“致良知”正是知行合一并进的工夫。
阳明讲“致良知”还强调“不假外求”,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1]7“致良知”不仅是“不假外求”的自然过程,也是自知与独知的过程。阳明说:“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1]81“所谓‘人虽不知,而己所独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处。”[1]135
阳明还从良知的自知、独知出发,将理想人格与自我的观念相联系,说:“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1]66另外,阳明还以“真己”为理想人格,说:
这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汝若真为那个躯壳的己,必须用着这个真己,便须常常保守着这个真己的本体。[1]41
阳明这里以“心之本体”诠释“真己”,赋予了精神自我以本体论的意义。如果说,阳明将“心之本体”与“天理”相联系,是对传统伦理价值普遍性的肯定,那么,将“心之本体”与“真己”相联系,则是对自我精神个体性的发现。阳明所谓“真己”是指精神自我,不同于“躯壳的己”。“躯壳的己”在阳明这里是指耳、目、口、鼻、四肢等,亦即现今所谓的生命自我。阳明在区分“真己”与“躯壳的己”的同时,亦强调“真己何曾离着躯壳”[1]40。也就是说,精神自我与生命自我在阳明这里是相统一的。总之,阳明“真己”这一概念的提出,赋予了传统身心之辨以新的意义,将身心修养向自我哲学这一领域进行了拓展。
结语
阳明借助“良知”这一概念,建立起了新的心学概念结构。阳明心学概念结构之新:一是相对于朱熹的理学而言,以“良知”替代“天理”;二是相对于陆九渊的心学而言,以“良知”为“心之本体”。所以,除了“心”这一代表阳明学说的概念外,阳明心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良知”。阳明将传统的性、理、天、道等概念归为本体(即“体”)的范畴,将意、知、行、事等概念归为工夫(即“用”)的范畴。需要注意的是,传统的气、精、神、物等本体论概念在阳明心学中是被归为“用”的范畴。另外,阳明对本体与工夫的区分有时也是相对而言的。比如,阳明就曾说:“本体原是‘不睹不闻’的,亦原是‘戒慎恐惧’的。……见得真时,便谓‘戒慎恐惧’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功夫亦得。”[1]120阳明对本体与工夫关系的理解,源于其对程颐“体用一源”学说的一元论诠释。与此相应,阳明心学概念结构亦呈现出鲜明的还原论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