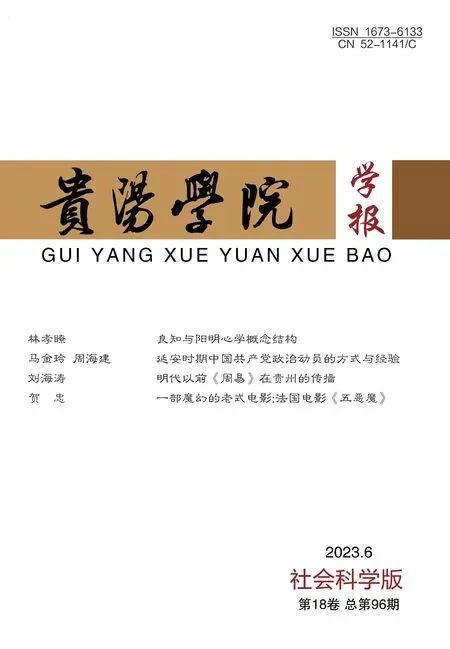论先秦道家思想对心灵归属感建立的启示
武静文,周 玲
(贵阳学院 阳明学与黔学研究院,贵州 贵阳 550005)
心灵归属感是一种从恐惧和焦虑中脱离出来的信心、安全和稳定的感觉,表现在个体在应对外部环境时表现出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对于个体生命具有稳定价值作用。道家,又称“道德家”,司马迁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膳足万物……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可见,道家对于与外部世界产生摩擦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重大。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交活动频率不断增加,现代人面临高度的工作压力、生活压力以及人际关系交往压力。在外部选择增多、信息繁杂的当下,人们如何从容应对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获得心灵归属感,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先秦道家主张对个体生命的重视,倡导以顺应自然的“无为”反哺自身的“有为”;倡导通过不加妄为,放下我执从而顺应自然,打破压力给与自我的囹圄,面对拼搏人生,如何减轻外之负荷,让自己在急匆匆的步伐中也能轻畅呼吸?道家给出的答案是:要贵虚守静,轻名重实才能不为外物所累;要扬弃我执,天人合一才能超脱俗世,以恬养智。先秦道家希望在个体生命和群体生活之间营造出和谐融洽的氛围,这对当前生活节奏加快下的个体增加心灵归属感,增强自我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不加妄为,放下我执——顺应自然
老子认为“道”是万物所产生的本原,生生不息的万物有其自然之序,而“道”作为推动自然之序流转的“序”本身给予万物发展内在的力量,人的发展也应该顺应“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超出生命本身的“益”会反噬自然之德、伤害人自身,所以老子认为要损伤外性而益于内,去矫饰而润自然。且事物有其本身的潜在性和可能性,如果勉强参与、不顺应其原本规律的意志、限制其发展,是非常危险的,轻则“尤”,重则失去本我,在世俗浪涛中浮沉。“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1]4老子认为圣人,即得“道”之人,处理世事是以不加干涉、不恃己能的无为态度,不囿于言语教导的行为方式和不居功自傲的行为准则,以此呼吁人们回归本然自我。
杨朱的“贵己”“重生”被部分学者认为是自私主义,“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好像是不愿为公贡献,只是求“私”己。《列子·杨朱篇》中禽子问杨朱:“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为之乎?”杨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济。”禽子曰:“假济,为之乎?”杨子弗应。禽子出语孟孙阳。孟孙阳曰:“子不达夫子之心,吾请言之。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为之乎?”曰:“为之。”孟孙阳曰:“有断若一节得一国。子为之乎?”禽子默然有间。孟孙阳曰:“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省矣。然则积一毛以成肌肤,积肌肤以成一节。一毛固一体万分中之一物,奈何轻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则以子之言问老聃、关尹,则子言当矣;以吾言问大禹、墨翟,则吾言当矣。”[2]可见,杨朱所提倡的轻物重生,是反对儒家倡导的“名教”。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1]78。正因为人们所追逐的都是不合于“道”的东西,所以才会为此所困,只有放弃追求这些外物,发扬本心,方是顺“道”而为,才能爱护本然自我,增加心灵安全感。杨朱强调对生命个体的关注,他对生命个体在“养生”“贵生”“全生”“存我”“全性”“保真”等方面的重视,不仅是对老子思想的传承,更对民众建立心灵安全感有较大的引导意义。
“度在身,稽在人”[3]240。“人不尊己,则危辱及之矣”[3]241。在列子看来,做到什么程度在于自己,如何评价交给他人,无论世间的嘈杂如何染我,我也只是将期待归于自身。“色盛者骄,力盛者奋,未可以语道也”[3]242,人际交往中并不是努力就有回报。面对环境,并不是自己努力就能跟上时代脚步,就能应对社会变革的林林总总,但也不必因为跟不上就对自己失望。列子也认为与因气色强盛而骄傲的人,力量强盛而奋勇的人不可谈论道的真谛。对当下的我们来说,选择的扩大强化了人们对于“外”的重视,从而忽视了对自身“内”的关切,“自我”在选择面前越来越被忽视。重而稳,轻而浮。增加对“我”的关注和涵养,增加心灵的归属,可以增加我们做人之稳、行事之稳。老子不加妄为,放下我执,不仅是对“我”的回头,更是归于“我”的第一步。
二、轻物重生,舍末求本——回归本然
“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观念,老子从天道出发,认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1]11。降至人道以“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11。从“自然”推至社会,要顺其自然,保持虚静。“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1]34。老子强调以致虚守静来消解心智,认为运用心机的人会闭塞原本明澈的心灵,固执成见的人会妨碍原本可以获得的明晰认识。只有顺应自然,不加妄为才可以生“静”,透过“静”的功夫才能不加妄念,回归本我。
《列子·杨朱》中的第一则故事就以杨朱与孟氏对话的方式引出了“若实名贫,伪名富”[3]217的结论,认为“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3]218。真名声可能会贫穷,虚假的名声也可能会富贵。做实事的人可能没有名声,有名声的人却不做实事,由此观之,名声实际上是虚伪的,不应该为了名而“苦身燋心”,失去本然自我,最终导致惨淡收场。杨朱说“遑遑尔竞一时之虚誉,规死后之馀荣;偊偊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3]219惶恐不安地去竞争一时的虚伪声誉,以图死后所留下的荣耀,生活在层层束缚的藩篱之中。这与生活在一层又一层牢笼中、罪恶深重的囚犯又有什么区别呢?当前社会环境下,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时间也在碎片化地被利用。人们忽视对自己心灵的照拂,忘记本然自我也需要被关怀,逐渐成为了社会生活附属物。不断追求华服豪宅等奢侈外物,使得自己疲惫不堪却不舍停止,最终被欲望操纵。
《列子·天瑞》中记载,或谓子列子曰:“子奚贵虚?”列子曰:“虚者无贵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静,莫如虚。静也虚也,得其居矣;取也与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碣而后有舞仁义者,弗能复也。”[3]29列子认为,虚即是无所依凭,不要只注重事物的名,要以虚静之理探寻名背后之实。在列子看来,为人处世的最好办法是由静而致虚,这与老子思想一脉相承。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1]34万物生生不息,最终都要归于灭亡,老子称之为“归复”,意即静。虚,即看透万物本不恒常的本性,静的目的即是明白这一恒常不变的规律,摆脱物我的束缚,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列子继承老子修真养性的实质,以绝对的精神安宁为追求。精神安宁在人的生命中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心灵安宁才能有良好的心灵归属感,才能徜徉于本我,不为外物所累。就当下来看,轻重之分就像是个别与群体的博弈,但是少数在“重”上下注,多数人在“轻”中沉浮。为了钱而剥削生命,为了名而哗众取宠,为了利而丧尽天良,在这世界上多享一天乐就多忘记原本的自己一分,追逐的一生里无“我”,方向尽是“他”或“他们”。而虚中生静,静中生明,回归本然是我们当下分清孰轻孰重,在本末倒置的迷途里返程不可缺少的一步。
三、贵虚守静,轻名重实——不为外物所累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46老子认为求全之道莫过于“不争”。“不争”之道在于“不自见(现)”“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多少人在琐碎的“面子”征伐战中迷失自我,因为所谓的争口气伤害了自己最亲近的人。追逐事物的显相,强于求“金”求“盈”,或急于彰扬显溢引起无数纷争。老子看到芸芸众生处于失去本然、追名逐利的纷争中,提出只有回归自然的本我才能让灵魂安定,获得心灵归属感。
“且趣当生,奚遑死后”,在杨朱看来,在死亡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要说生前的贤愚之分和高下之别,更何况生前之事,我们又能决定几分呢?死后同为“臭腐、消灭”,却为求一时的名而使身心陷于焦灼苦楚,有什么乐趣可言?用一生去追逐虚浮,疲抑身心却不可得,实为不值,更是不堪,不如好好地享受当下的生命,“从心而动”[3]220“从性而游”[3]220,不为外物所累,增加心灵归属感。可见杨朱与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老子强调“见素抱朴”“少思寡欲”,杨朱强调“贵己”,都是从涵养自身出发,而这在春秋战国时为民众休息精神,增加心灵安全感做出指引。在子产相郑的故事中,杨朱进一步否定礼义和名位,认为正是因为人们执着追求名位,才身心憔悴,不能得其本然性情,应该顺应自然。“既生,则废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于死。将死,则废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于尽。无不废,无不任,何遽迟速于其间乎?”[3]230轻物重生,但不应为“生”所累,重的是自然的本性,重的是生命自身,而不是求外物享受之“生”。
“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常不胜之道曰强。”[3]82柔软则有韧性,不轻易大喜大悲。在应对社会变革的冲击时,因为柔而没有过强的反应,因而更容易适应。老子曾举例,小草柔软的时候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它可以在复杂的环境下存活,面对巨石,它可以弯曲生长寻找阳光雨露;面对踩踏,它也会先弯曲再重振旗鼓。在抑郁症患者数量急剧增多,心理问题越来越应该被关注的当下,压力是造成心理疾病的罪魁祸首。而贵虚守静,轻名重实是对生命的重视,更是对压力的释怀。当代人心灵的广度可以很大,心灵的韧性却不够强,我们需要站在高处看自己、观人生,增强心灵的韧劲儿,通过增加心灵归属感稳定自己的心性。
四、扬弃我执,天人合一——超脱俗世,以恬养智
《老子》第十九章中有“见素抱朴,少思寡欲”[1]40,第二十章中有“唯之与阿,相去几何?美之与恶,相去若何?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1]41在老子看来,善恶美丑贵贱是非,都是相对的,人不能在价值判断浪潮中追捧世俗却迷失本我。最可贵的“本”与“真”是我们的财富,更是心灵稳定的源泉。老子坚守自我,坚守“道”,不反自然也免被侵蚀,众人之声鼎沸嘈杂,因我愚之,从而不为所动。人之“真”在何处?愈真愈假,以假乱真。真假之间的错乱是当下人迷了眼的原因,更是当下人不能逃避的选择。
《庄子·逍遥游》中写道:“蜩与学鸠笑之曰:‘我決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飡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4]13庄子在广袤无垠的北冥看到一飞冲天的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它从世俗的限制中脱离出来,悠游自在、无牵无挂,没有被功、名、利、禄、权、势、尊、位所捆绑。明道者只有胸怀着“大”而冲破自我狭窄又可怜的认知才能超脱俗世,获得灵魂的安慰。王仲庸说“逍遥游,是指的明道者——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以后所具有的最高精神境界。”[4]13世人总是徜徉于俗世的琐碎,醉心于追求消极的现实,没有了本我,没有了灵魂,循环往复到不了彼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4]20陈鼓应在注释“无己”时认为其意指没有偏执的我见,即去除自我中心,亦指扬弃功名束缚的小我,而真至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只有脱离尘海浪浪,来到彼岸的本我面前,专注自我的灵魂,因虚而静,由静养虚,才能促进心灵归属感的建设,让自己畅游,甚至“御风而行”。“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4]43“大知闲闲,小知閒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4]52“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4]67“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4]67“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4]67庄子从“丧我”的精神境界出发,提出“莫若以明”的结论似乎是想要平息世间被扰乱的灵魂,成心作祟而起意气之见,争执不断却不是为了自我的安逸和舒心,为的是名利场上的一席之地,庄子大批“非也!非也!”“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4]46庄子认为,穷尽一生去追寻的东西不是灵魂的救赎而是使自己更加疲惫的东西实属遗憾,身心俱疲的人生并不值得追求。在瞿鹊子与长梧子的对话中,有“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置其滑涽,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芚,参万岁而一成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4]101-102从预言中庄子批评了意见与限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4]71的精神境界。世界的纷纷扰扰,我们如何逃离呢,如果不能逃离我们,又能如何呢?用自己去改变世间或是自身吗?怕是不足取的。庄子在《人间世》篇中告诉世人,人间种种纷争,追根究底也不过是在求明用智罢了,不如“心斋”,不如“坐忘”,以灵魂历历万乡。庄子用涵养空明的心境来保存、涵养我们对所处世界最后一点稳定和可控制的踏实。“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4]108
从老子建立自然本体论倡导修道、体道,到杨朱、列子转向养生养性之学,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开启心性说,先秦道家塑造了一条层层递进的修养路径。庄子不愿意处乱,坚守“道”,走向“真”,以自然为始为终,以旷阔之心灵培育“我”,以舍而得,舍的是世间的束缚,得的是心灵的广袤无垠。庄子之逍遥,得之于忘,处之于生;得之于丧我,处之于得我;得之于不拘,处之于自由;得之于生死齐一,处之于惬意自适。当下的社会中,人们都太过于“急”,有限的机遇,无限的焦虑,有限的时间,无限的需求。人们忘记了身处自然界的我们本就是自然的一分子,忘记了人的精力有生理的限制,忘记了“上升”的快乐比“下降”的快乐更加丰富持久。超脱俗世不仅仅是对我们心灵的关切,更是我们安抚灵魂的技巧,不拘于当下之小,永远保持旷阔的向往是庄子的以恬养志,更是我们加强自我稳定,从容应对人生的法宝。
五、结语
总而言之,先秦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基调,以“致虚守静”来消解心智,不加妄念;用“涤除玄览”来濯其心性,不以世俗烦扰,回归本我;用“俭以养德”来减少外物追求,减少妄念;用“为道日损”少思寡欲,进而无为自然,不在世俗的价值判断中迷失自身。杨朱提出“轻物重生”,认为“实无名,名无实。名者,伪而已矣。”在杨朱看来,人生的最高追求在于让生命体验到快乐,让身心体验到安逸,持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而不是为了外物而损害自己。在庄子看来,人类的困境在于并没有将自身视为大自然的一分子,也不愿遵从天地运行的规律。他反对背离自然规律的社会规范,追求人的绝对自由,呼唤万物依照天性进入大自然的流转,以实现天人和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以儒学为主流,至宋明发展至鼎盛时期,儒家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举足轻重。儒家士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理想,强调“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强调有为、力行,强调积极进取的人生选择,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出卓越贡献。但是儒家对人类为文明和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的曲折性估计不足,对人类在不断进取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问题以及对人性本身的扭曲与伤害缺乏思想准备或不予重视,没有留下足够而必要的回旋余地。而以先秦道家为基础的哲学观察到社会发展中人类因为竞争而产生人性异化的现象,力图用回归自然,“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观来矫治人性的异化,倡导净化、稳定心灵,返璞归真,使社会和谐宁静。而且,不同于儒家倡导的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为代表刚性有余而韧性不足的民族性格,道家提倡柔弱、无为、知足、谦下、知止、淡薄、居下、处顺、静观,崇尚“不争之德”。先秦道家关注个体生命价值,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调和中增加个体生命的弹性,引导人们养成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无为而无不为”“夫唯不争,故无尤”,这些人生智慧为现代人心灵归属感的建立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