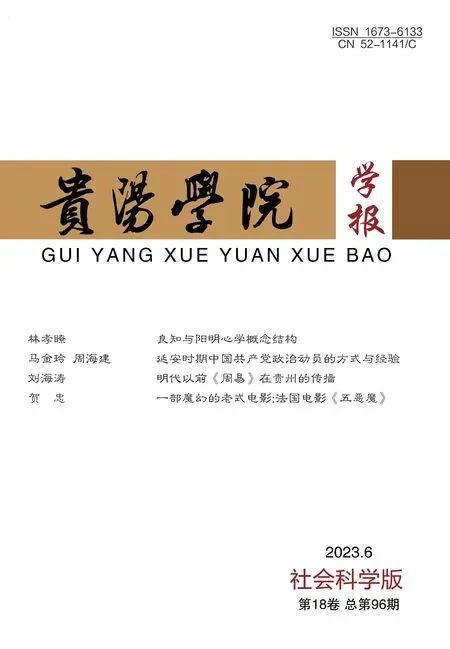明代嘉靖张氏家塾刻本《李诗选》选源考
雷 磊,陈君忆
(1.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32)
明代题“张含精选、杨慎批点”的《李诗选》十卷,最早的版本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杨慎序张氏家塾刻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杨序云:
吾友禺山张子愈光,自童习至白纷,与走共为诗者。尝谓余曰:“李杜齐名,杜公全集外,节抄选本凡数十家,而李何独无之?”乃取公集中脍炙人口者一百六十余首,刻之明诗亭,属慎题辞其端云[1]卷首。
由此可知此选刊刻之大概。需特别提出的是,其刊刻动因之一乃在于此选之前杜诗选本已多至数十家,而迄无选李诗者。事实大致如此①(1)①就李诗而论,元有选本,《千顷堂书目》及《补元史艺文志》著录元范德机批选《李翰林诗》四卷元刻本。明代李诗选本较复杂,在嘉靖二十四年杨慎序刻《李诗选》之前,仅有二种:一是明宣德赖进德刻《李杜诗解》三卷本(《千顷堂书目》著录),是李杜合选本,且未见传本。二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李杜律诗》四卷本,亦为李杜合选,且仅选律诗。杨慎似未将此二种算在独立的李诗通选之列。嘉靖二十四年刻成二种李诗选(一是王寅编闵朝山刻《李翰林诗选》五卷,系与《杜工部诗选》六卷合刻;二是朱谏辑注朱守宣刻《李诗选注》十三卷《辨疑》二卷),虽曰选注,然仅删除疑伪之诗,实同全选。以上二种,张、杨恐均未阅及。总之,张含、杨慎李诗选本“独无”之说,似可成立。。动因之二则是杨慎一派持李优于杜论,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李杜光焰千古,人人知之,沧浪并极推尊,而不能致辨。元微之独重子美,宋人以为谈柄。近时杨用修为李左袒,轻俊之士往往傅耳。”[2]王氏是以批判的态度来评论杨慎李杜论的,但显然可见杨慎持李优于杜论。而张含实为杨慎弟子,属杨慎一派之核心人物——“杨门六子”之首。有上述动因,则张、杨选评李诗乃在情理之中。张、杨《李诗选》是明代第一部有明确文学宗旨的李诗通选选本,具有相当的文学和文献价值,而杨慎实为张、杨《李诗选》编刻的核心人物。
杨慎颇为重视李白诗集的版本和李白诗歌的校勘问题,杨慎《李诗选》批注26条,有8条论及上述问题,杨慎《升庵诗话》也有多条诗话论及于此。对于《李诗选》的选源问题,张含并无言说,杨慎又语焉未详,本文即对此问题加以探讨。
一、“古本”为选源之校本
关于李诗集版本,杨慎有“古本”“今本”“俗本”等提法。欲明确《李诗选》的选源,则需先厘清“古本”“今本”“俗本”等的含义或指称。通常的“古本”,则当指明本以前之唐本、宋本、元本,但杨慎所谓的“古本”则仅指其家所藏的宋代乐史刻本,这一结论可由以下三言参证得出:
升庵曰:今本无此四句,以慎家藏本补之[1]卷二《长干行》。
升庵曰: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1]卷十《哭宣城善酿纪叟》。
此诗余家藏乐史本最善,今本无“怜肠愁欲断”四句,他句亦不同数字,故备录之[3]361。
乐史本即《李翰林集》二十卷,由乐史于宋咸平元年(998年)编刻,今佚。乐史又编刻《李翰林别集》十卷,今有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重刻宋淳熙本,载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有云:“李翰林歌诗,李阳冰纂为《草堂集》十卷,史又别收歌诗十卷,与《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为二十卷,号曰《李翰林集》。”则可知《李翰林集》二十卷所收均为歌诗,凡七百七十六篇②(2)②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缪曰芑重刻宋元丰三年(1080年)晏知止刻《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中有宋敏求《李太白文集序》,言及凡七百七十六篇。。詹锳先生据上述三条引文,认为“乐史本在明中叶尚存”[4],则乐史本之亡佚在杨慎身后。由杨慎所谓的“古本”仅指乐史本这一事实大概可推知,宋本之最早者乐史本为张含选刻、杨慎批点《李诗选》时所见唯一之元以前李白诗集,其先之唐本③(3)③如魏颢刻《李翰林集》、《李白集》稿本、李阳冰刻《草堂集》十卷、范传正刻《李白文集》二十卷、《李白歌行集》三卷等。似均已亡佚,其后之宋本亦在若存若亡之间。唐本和乐史本今均不存,即以杨慎用乐史本校勘和评点《李诗选》此点而论,可证张、杨《李诗选》具相当之文献和文学价值。“古本”亦不指元本,因元本在明代多有翻刻,而成了“今本”。因此,杨慎所谓的“古本”就成了乐史本之专名了。
那么,乐史本是张、杨《李诗选》之选源吗?我们认为,选本之选源有底本和校本之分,而乐史本仅为选源之校本。上引三条文献,杨慎均提出了校勘意见,仅有一条被《李诗选》所采纳,另二条未被采纳。采纳的是上引第一条,《李诗选》卷二收《长干行》二首,其二中“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薄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四句,“今本”未收,而据乐史本补入。因此,“今本”和“古本”(即乐史本)均为《李诗选》之选源,但有先后主次之关系,大概张含系先据“今本”选入《长干行》二首,其第二首并无“北客”四句,稿本交由杨慎批点后,刻本则据杨慎意见补入了今本无而乐史本有的此四句诗。那么,所谓“今本”即为《李诗选》之编选底本,而“古本”即乐史本为编选之校本。由此又可知,杨慎不仅参与了《李诗选》的批点、作序工作,而且还参与了《李诗选》的编选和校勘工作。
校勘意见未被采纳是上引后二条。先看第二条,《李诗选》卷十《哭宣城善酿纪叟》有“夜台无晓日”句,并未据乐史本改为“夜台无李白”。上引第三条也是如此,杨慎《升庵诗话》“李太白相逢行”条引其家藏乐史本《相逢行》全诗中“今本”所无之“怜肠愁欲断,斜日复相催。下车何轻盈,飘飘似落梅”四句,张含《李诗选》卷三收入此诗,但并未补入此四句,而且杨慎所云“他句亦不同数字”也未被《李诗选》采用。
总之,“古本”仅指宋乐史本。《李诗选》选诗者和刊刻者为杨慎弟子张含,张含大概系据“今本”而选李诗,杨慎则予以批点,其部分批点为校勘内容,系以“古本”即乐史本校“今本”,且仅有一条校勘结论被采纳,则“今本”为选源的底本,而“古本”为校本。
二、宋乐史本之优
宋乐史本后之宋本,宋敏求分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曾巩考次本《李白诗集》二十卷、南宋当涂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杨齐贤注本《李翰林集》二十五卷均已亡佚,无从详考。现存宋本或翻刻宋本尚有三种: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缪曰芑重刻宋元丰三年(1080年)晏知止刻《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世称缪本,可视同为宋元丰本),北宋蜀刻《李太白文集》三十卷本(世称蜀本),明初重刻南宋咸淳(1265—1274年)刻《李翰林集》三十卷本(可视同为宋咸淳本,简称咸淳本)。蜀本系据元丰本翻刻,与缪本属同一系统(即元丰本系统),文字并无大异,二本讹脱、漫漶处可互校。因此,本文即以元丰本统称缪本和蜀本。下文将上引三条文献所提及的乐史本文字与元丰本、咸淳本进行比较,以考察三者之差异或关系。
《李诗选》卷十《哭宣城善酿纪叟》云:
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1]卷十《哭宣城善酿纪叟》。
“夜台无晓日”句下,杨慎批云:“予家古本作‘夜台无李白’,此句绝妙,不但齐一死生,又且雄视幽明矣。昧者改为‘夜台无晓日’,夜台自无晓日,又与下句‘何人’字不相干。甚矣,士俗不可医也。”[1]卷十《哭宣城善酿纪叟》就文义而言,“夜台无李白”确优于“夜台无晓日”。但各本均作“夜台无晓日”,咸淳本即如此,唯元丰本此首有校语云:
一作《题戴老酒店》,云:戴老黄泉下,还应酿大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何人[5]卷二十四。
但已改题,恐非乐史本之原文。则宋三本颇有差异,且宋乐史本似优于元丰本。因有校语,元丰本又优于咸淳本。另二条文献亦可佐证此一推论。
《李诗选》卷二《长干行》二首其二中八句云:
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薄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好乘浮云骢,佳期兰渚东。鸳鸯绿蒲上,翡翠锦屏中[1]卷二《长干行》。
前四句杨慎批云:“今本无此四句,以慎家藏本补之。”[1]卷二《长干行》不仅“今本无此四句”,咸淳本亦无此四句。元丰本有此四句,但文字略有差异:
北客至一作真王公,朱衣满汀一作江中。一作“比①(4)① 笔者按:当作“北”。客浮云骢,经过新市中”。日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5]卷四。
“至”“汀”“日”三字与乐史本不同,但其有校语:“至,一作真”,“汀,一作江”。似可推知“一作”之本即为乐史本。宋本往往有后本出而前本隐(佚)之情形,元丰本出,则乐史本隐;蜀本出,则元丰本隐;咸淳本出,则蜀本隐。乐史本明中期以后亡佚,元丰本至清康熙才得以重刻,而咸淳本有明初重刻本,显隐渐变,当为上述规律之旁证。乐史本虽佚,其文字往往通过元丰本之校语得以流传。可以想见,元丰本校语中所谓“一作”“一云”之类尚存大量乐史本文字,但很难确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乐史本虽亡而略存。另外,元丰本有上“北客”四句,但无下“好乘”四句;而咸淳本无上“北客”四句,却有下“好乘”四句。可见乐史本、元丰本、咸淳本并非一个系统而分属三个系统。有学者认为咸淳本源于乐史本,恐非是。因乐史本不存,则宋本三个系统就只剩下元丰本和咸淳本两个系统。
杨慎《升庵诗话》全引乐史本《相逢行》如下:
朝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中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乍迟回。夹毂相借问,知从天上来。怜肠愁欲断,斜日复相催。下车何轻盈,飘飘似落梅。娇羞初解佩,语笑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相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言三青鸟,却寄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壮年不行乐,老大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无令旷佳期[3]361。
因文字差异颇大,亦全引《李诗选》卷三《相逢行诗》,以作比较:
胡骑五花马,谒帝出银台。秀色谁家子,云车珠箔开。金鞭遥指点,玉勒近迟回。夹毂相借问,疑从天上来。蹙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衔杯映歌扇,似月云中见。相见不得亲,不如不相见。相见情已深,未语可知心。胡为守空闺,孤眠愁锦衾。锦衾与罗帏,缠绵会有时。春风正澹荡,暮雨来何迟。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光景不待人,须臾发成丝。当年失行乐,老去徒伤悲。持此道密意,毋令旷佳期[1]卷三《相逢行诗》。
更可证《李诗选》其选源底本非为乐史本,而是更接近元丰本或咸淳本,原因如下:一是元丰本、咸淳本、《李诗选》三本均无“怜肠”四句。但元丰本有校语:“一本更添‘怜肠愁欲断,斜日复相催。下车何轻盈,飘飘似落梅’。”实际上将乐史本逸句揽存,更胜于咸淳本及此后之元本和明本。二是乐史本“娇羞初解珮,语笑共衔杯”二句,三本均作“蹙(或邀)①(5)①《李诗选》作“蹙”,元丰本和咸淳本均作“邀”。入青绮门,当歌共衔杯”。“娇羞”语正承前言“轻盈”“飘飘”之意,似符杨慎“太白号斗酒百篇,而其诗精炼若此,所以不可及也”[3]361之评,亦当以乐史本为胜。“娇羞”二句,元丰本亦有校语录存。三是乐史本作“朝骑”,而三本均作“胡骑”。“胡骑”与下句不侔,实不可解。而“朝骑”之“朝”与下文“斜日”相对,又与“春风”“暮雨”“壮年”“老大”相应,共同表达相见相亲、及时行乐之主题。后清代王琦注本采“朝”为正文,且校云:“世本作‘胡’,误。”[6]其他还有多处文字差异,不详论。以上三例似已可证实杨慎“此诗余家藏乐史本最善”[3]361之论。同上,因元丰本多有校语,在文献上实优于咸淳本。
总之,乐史本有优于其他元丰本、蜀本和咸淳本之处,杨慎据此校勘和评点李诗,是《李诗选》文学和文献价值的重要体现。
三、元本为选源的底本
上文已言,“今本”可能是《李诗选》选源的底本。但是,“今本”究指何本呢?我们认为,“今本”应属元本系统。所谓的元本系统是指元本和明翻刻元本。而元刻本并无多本,特指元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初刻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重刻于元至大三年(1310年),即余氏勤有堂刻本,今存元至大本。而明翻刻元本则有重刻本和删节本之分,在张、杨《李诗选》之前,重刻元本可以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刘宗器安正书堂刻本(简称安正堂本)为代表,而删节元本就是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郭云鹏宝善堂刻本(简称宝善堂本)。本文主要考察元至大本、明安正堂本、明宝善堂本,此三本属同一系统,即元本系统(既有元刻本,又有明翻刻本),我们统称为元本。
宋本、元本均为分类本,《李诗选》亦如此,可列其歌诗类目,以作比较。元丰本歌诗二十三卷(卷二至二十四),类目如下:
古风(卷二)、乐府(卷三至卷六)、歌吟(卷六、七)、赠(卷八至十一)、寄(卷十一、十二)、别(卷十三)、送(卷十四至十六)、酬答(卷十六、十七)、游宴(卷十七、十八)、登览(卷十九)、行役(卷二十)、怀古(同上)、闲适(卷二十一)、怀思(同上)、感遇(卷二十二)、写怀(同上)、咏物(卷二十三)、题咏(同上)、杂咏(同上)、闺情(卷二十四)、哀伤(同上)。
乐府有四卷(卷三至六),分别称为“乐府一”“乐府二”“乐府三”“乐府四”,他类或称上下、或称上中下者,为便省览,均合并一处,下同。咸淳本歌诗二十卷,类目如下:
古风(卷一、二)、乐府(卷三至五)、赠(卷六至八)、寄赠(卷九)、饯送(卷十、十一)、酬答(卷十二)、留别(卷十三)、杂拟(卷十四)、怀(卷十五)、登览(卷十六)、歌吟(卷十七)、游宴(卷十八)、杂咏(卷十九)、闺情(卷二十)。
某类多卷,亦称上下或上中下者,均已合并。咸淳本歌诗类目同元丰本比,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咸淳本歌诗分14类,而多三卷歌诗的元丰本有21类,前者少7类。减少的是行役、怀古等3类(怀古、怀思、写怀)中的2类、闲适、感遇、咏物、题咏、哀伤等8类。咸淳本有杂拟,而元丰本无此类,则实际少7类。二是类目顺序不同。如“歌吟”,缪本在第三,咸淳本在第十一。又如元丰本“别”在“送”之前,而咸淳本“留别”在“饯送”(和“酬答”)之后。其他类目顺序不同处甚多。
元本二十五卷,除“古赋”类外,歌诗二十四卷,类目及其顺序全同元丰本,差异有三:一是分卷有异,二是元本一类多卷者,未标序号(上、下,或上、中、下,或一、二、三、四),三是诗歌排序大同而小异。总体而言,差异并不大,可证元本或据元丰本编刻而成。《李诗选》之类目及其顺序亦同于元本和宋元丰本,仅诗歌排序略有差异而已。
经过上述考察,仅排除了咸淳本为《李诗选》选源之底本的可能性,但并不能确定其选源底本是元本还是宋元丰本。这可从文字差异的方面进一步加以考察。
元丰本卷二类目为“古风上”,标题为“古风五十九首”,但检其文本,并无“古风下”类目,且古风也仅57首,少2首。元本59首古风全,同元丰本相较,顺序大致相同,但元本第20首(“昔我游齐都”)实合元丰本第18(“昔我游齐都”)、第19(“泣与亲友别”)二首为一首。则元丰本与元本相比,少3首,即元本之第8(“咸阳二三月”)、第16(“宝剑双蛟龙”)、第22(“秦水别陇首”)。我们再看《李诗选》古风共选5首,而第2首(“咸阳二三月”)正为元丰本所缺者,且第20(“昔我游齐都”)亦为合元丰本第18(“昔我游齐都”)、第19(“泣与亲友别友别”)二首为一首者。可见,《李诗选》当以元本系统为选源底本而非宋元丰本。
杨慎《李诗选》和《升庵诗话》中校勘性批语和诗话提及6题11首诗:《长干行》二首其一、《长干行》二首其二、《相逢行》、《横江词》六首、《赠郭将军》、《哭宣城善酿纪叟》。元本系统之元至大本、明安正堂本、明宝善堂本等,于上述六首李诗,文字大同小异①(6)① 惟《横江词》六首其一“一风三日吹倒山”句,二明翻刻元本皆作“一风二日吹倒山”,恐为翻刻之误,“三日”当是。,亦可合并一处讨论。此六首诗,《李诗选》同元本只有4处差异,而其中2处差异显然系因杨慎校勘而改:一是《长干行》二首其二“北客”四句,杨慎批语已明言“今本无此四句,以慎家藏本补之”。二是《长干行》二首其二“八月胡蝶黄”,亦明言“今俗本作‘来’,非也”,“今本”和“俗本”均误,张含当据杨慎意见而改。再分析另2处差异,都在《赠郭将军》诗中:一是元本“薄暮垂鞭醉酒归”句,《李诗选》作“薄暮垂鞭信马归”。二是元本“畴昔雄豪如梦里”,而《李诗选》作“畴昔豪雄如梦里”。但是,《李诗选》之前的宋本(元丰本、咸淳本)和明本均同于元本系统,作“醉酒”和“雄豪”,则此二处差异,实为张含所改,“醉酒”似有意改之,“雄豪”似刊刻倒乙。因此,4处差异,虽原因不同或不明,但均为《李诗选》编者所改,不能据此而否定元本为《李诗选》选源底本的事实。
总之,《李诗选》选源底本属元本系统,但究竟是哪一本,因各本间差异不大,一时难以断定,需待细心校勘后,或能得出答案。
四、明本系“俗本”
“俗本”又指何本呢?还是要回到杨慎校勘性批语中去考察。杨慎批点提及“俗本”者亦有三条,第一条云:
《唐文粹》作“黄”,今俗本作“来”,非也。胡蝶以春时来,八月作来时也。秋蝶多黄,感金气也。白乐天诗:“秋花紫蒙蒙,秋蝶黄茸茸”,此可证也[1]卷二《长干行》。
“今”“俗”并称,但元本和明本均作“来”,则无法判定。所谓明本系指张、杨《李诗选》之前刊刻的非元本系统(题名为萧士赟注《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二十五卷者)之李诗集,主要有三种:一是明成化刻《唐翰林李白诗类编》十二卷本,二是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李濂刻《李白诗集》十二卷本,三是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万虞恺刻《唐李白诗集》八卷本。因未见李濂刻本,今以上述成化本(简称明十二卷本)和嘉靖本(简称明八卷本)为考察对象,此二本最大的特点在于将李白诗先分体再分类编排,且二本体目类目完全相同。其文本的来源大概也是元本系统。杨慎第二条校勘性批语云:
杨慎曰:太白《横江词》六首,章虽分局,意如贯珠。俗本以第一首编入长短句,后五首编入七言绝句,首尾衡决,殊失作者之意[1]卷四《横江词》。
此批语即单言“俗本”。而分编者正是明十二卷本和明八卷本,前者卷十“长短句”体“歌吟”类只收各本《横江词》六首之第一首,而于卷十二“七言绝句”体“歌吟”类中收《横江词》六首之后五首。后者分法完全相同,可见八卷本系源于十二卷本①(7)① 明八卷本有李濂序,可推知源于李刻《唐李白诗》十二卷。八卷本又与《唐翰林李白诗集类编》十二卷体类全同,文字大同,则八卷本和二种十二卷属同一系统。。宋本、元本都是合收六首,仅明本(十二卷本和八卷本)分收,即此而论,杨慎所谓“俗本”当指明本。第三条云:
俗本首句作“将军豪荡有英威”,乃妄人乱改者,当以古本为正[1]卷五《赠郭将军》。
宋本、元本、《李诗选》均作“将军少年出英威”,亦唯明本作此,则俗本亦指明十二卷本或明八卷本。总之,由上二例显证杨慎所谓“俗本”即指明本(明十二卷本或明八卷本)。
综上所述,杨慎所谓的“古本”是指宋乐史本,“今本”属元本系统,“俗本”指明本(明十二卷本或明八卷本)。《李诗选》选源底本为属元本系统之“今本”,而选源校本则有“古本”乐史本等。通过考察,我们还可知道,宋三本中,乐史本优于元丰本,元丰本优于咸淳本。但是,乐史本已佚,幸赖杨慎校语略存一二,弥足珍贵。元丰本系统(缪本和蜀本)亦多有校语,其中应有乐史本文,惜多数难以确指,乐史本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元本系主要依据元丰本编成,明本又系主要依据元本编成,可见元本在明代前中期颇为盛行。总之,张、杨《李诗选》有相当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