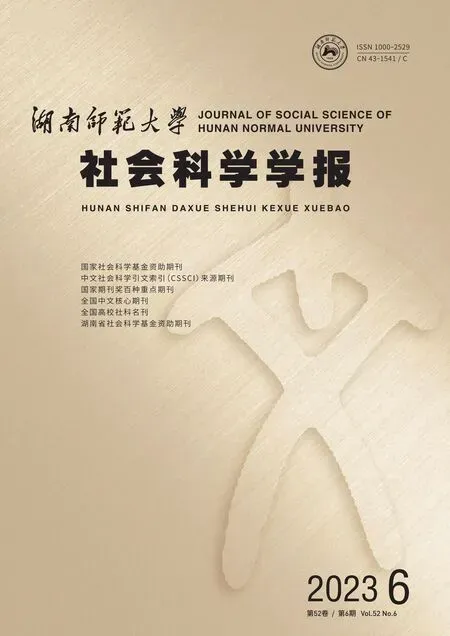孙吴国史修撰的正统新塑和文学新变
徐昌盛
孙吴官修的国史仅有韦昭《吴书》,西晋私撰吴国史蔚然兴起,可知者有陈寿《吴书》、周处《吴书》、张勃《吴录》、胡冲《吴历》、环济《吴纪》、顾荣《吴事》①、“二陆”《吴书》(未成)和虞溥《江表传》等八部著作。陈寿《吴书》尚存,韦昭、张勃、胡冲和虞溥的吴史著作亦有丰富的遗文传世,这已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也产生了一系列辑佚和考证的成果②。那么,在吴国史从官修向私撰的转变过程中,史家如何调整叙述立场来应对正统观念的变革?与中原文化暌违近百年的吴国史家在文学实绩和著述观念上又有哪些独特的成就呢?
一、从官修到私撰:吴晋之际的吴国史书写
韦昭的《吴书》是吴国的官修史书,是孙吴史官三次编纂的成果。
孙吴第一次官修《吴书》,是在孙权太元元年(251)。华覈上疏请求召回流放的薛莹说“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1]1256,可知早在孙权晚年的时候,已经组织丁孚、项峻等编撰《吴书》,然而两人“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纪录”[1]1256。《志林》载“项竣、丁孚时已有注记”[1]1132,“注记”是古史的体裁,亦称“记注”,属帝王起居注、实录一类的史料,则丁孚、项峻在编撰《吴书》时已有可供参考的史料。同时,中书机构也保存了大量的档案。《吴历》记载说孙亮“数出中书视孙权旧事”[1]1154,孙亮看到的孙权旧事,即由中书机构保存。另外,当时也有记载和赞美吴主功绩的文献,如张纮《孙破虏将军纪颂》《孙讨逆将军纪颂》,韦昭《吴书》说:“纮以破虏有破走董卓,扶持汉室之勋;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义。既成,呈权,权省读悲感,曰:‘君真识孤家门阀阅也。’”[1]1244张纮卒于建安十七年(212),说明孙吴政权早期已有孙坚、孙策的史料。
孙吴第二次官修《吴书》,是在孙亮建兴元年(252)。《三国志》韦昭本传载孙亮即位后诸葛恪奉命辅政,于是命韦昭为太史令,开始撰写《吴书》,华覈、薛莹等都参与了编撰工作[1]1461-1462。另有周昭,“与韦曜、薛莹、华覈并述《吴书》”[1]1242(《三国志·吴书·步骘传》)。又有梁广,《史通·古今正史》载孙亮命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人“访求往事,相与记述”[2]322,而众人之中,以韦昭、薛莹的史才最为突出,故刘知几说“并作之中,曜、莹为首”[2]322。由此可知,第二次修《吴书》,明确参与者有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及华覈等人。韦昭为太史令,既说“韦氏作史”,则韦昭是主要负责人。《中兴书录》载“项峻撰《吴书》,韦昭续成之,五十五卷”[3],知韦昭是在项峻等人的《吴书》基础上编撰。薛莹有《条例吴事》,“条例”即作者在撰写史书之前预设的关于史书书法和结构的规定,可知薛莹做了很多纲领性工作。此时撰写的《吴书》“备有本末”[1]1256,则孙亮之前的吴史很有可能基本完成。
孙吴第三次官修《吴书》,似在孙皓凤凰二年(273)以后。韦昭仍是主事者,薛莹是完成者。韦昭因获罪远徙,华覈上疏救理说“《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1]1464。孙皓外放薛莹领兵,华覈上疏说周昭、梁广早已去世,韦昭已获罪,薛莹又从戎远徙,导致《吴书》编纂“委滞,迄今未撰奏”[1]1256,因此华覈请求孙皓召回薛莹“使卒垂成之功,编于前史之末”[1]1256,获得了准许。《史通·古今正史》亦记载:“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2]322事实上,《吴书》并未在韦昭生前竟功,他死后由华覈、薛莹最终完成,但韦昭贡献最大,故仍署名韦昭。因此《隋书·经籍志》载韦昭撰《吴书》二十五卷,梁时有五十五卷[4]1083。沈家本说:“韦在时书尚未成,华、薛续成之也。”又说:“《史通》云曜终其书,殊非事实。惟书非成于韦之手,而仍属之于韦者,大约此书体例皆韦手定。不为孙和作纪,乃其一端。韦在时稿本已具,特未裁定奏上耳,故书之成也,华、薛皆不敢居以为功,华、薛二传亦不言作《吴书》也。”[5]
及至西晋,私撰吴国史盛行,现知的陈寿、周处、张勃、胡冲、环济、顾荣、“二陆”、虞溥等所撰的八部吴国史,极大地丰富了吴国历史的文本景观。
陈寿《吴书》由私撰而入正史,影响最大。常璩《华阳国志·后贤志·陈寿传》载晋平吴后,陈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6],《隋书·经籍志》增加“《叙录》一卷”和“宋太中大夫裴松之注”[4]1083,并说西晋时,“陈寿删集三国之事,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仍各依其国,部类相从,谓之《三国志》”[4]1085。又说陈寿去世之后“梁州大中正范頵表奏其事,帝诏河南尹、洛阳令,就寿家写之”[4]1085。梁州大中正上表尚存,说陈寿《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7]2138陈寿死后,朝廷派人就其家抄写《三国志》,于是私撰史得到了官方的承认。
私撰吴国史中,有五部出于吴人之手,即周处、张勃、胡冲、顾荣、“二陆”等人的吴史。另有环济《吴纪》属于编年史,《隋书·经籍志》载九卷,但存世材料较少。周处《吴书》,《晋书》本传说他“著《默语》三十篇及《风土记》,并撰集《吴书》”[7]1571,但早已不流传。张勃《吴录》,《隋书·经籍志》载三十卷,尚有遗文传世。“二陆”的《吴书》,见于兄弟之间的通信,陆云《与兄平原书》二十七说“《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国事遂亦失”[8]1122,本来计划写五十卷,惜乎未能完成,故不见著录。胡冲的《吴历》在诸家私撰吴史中最具价值。胡冲是侍中胡综之子。胡综不仅负责“军国密事”,而且擅长文章写作。《三国志》本传记载说孙权统事以来:“诸文诰策命,邻国书符,略皆综之所造也。”[1]1418胡冲曾任中书令,前揭孙亮“数出中书视孙权旧事”,说明中书机构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又薛莹《条例吴事》记载“胡冲意性调美,心趣解畅,有刀笔,闲于时事。为中书令,……亦自守不苟求容媚”[9]。胡冲既有家学渊源,又担任要职,且为人耿介,其《吴历》具有重要的史学和文学价值。
二、“三方之王”:孙吴国史的正统观念新塑
孙吴国史的官修私撰,最关键的是正统塑造。王夫之慧眼独具地指出“蜀汉之义正,魏之势强,吴介其间,皆不敌也”[10](《读通鉴论》)。蜀汉是帝室胄胤而有血统优势,曹魏是仿尧舜禅代嗣位且定都洛阳。孙吴依靠东汉兴起的谶纬符瑞神秘学说塑造正统,吴人史家在晋撰写吴史无法使用,但陆机独辟蹊径,提出了“吴亦龙飞”“三方之王”“三主鼎足”的说法,即三国俱是正统的观念,这是当时的新型正统观。
韦昭《吴书》已注重塑造吴国正统,正统问题始终是孙吴君臣的关注重点。祭天是昭示正统的仪式。孙权的南郊,第一次是黄龙元年(222)在武昌南郊祭天,第二次是太元元年(251)在建康秣陵县南十余里郊中。孙皓塑造正统意识强烈,对符瑞和谶语深信不疑,故有华里之行、封禅国山碑和改土德为金德的举措③。韦昭《洞纪》尤能说明吴人的正统诉求。《洞纪》的“纪”本有正统之意,韦昭说“告于百神,与天下更始,著纪于是”[11](《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三·引裴骃案)。《史通·本纪》说:“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2]34《资治通鉴·晋纪》记载:“吴主欲为其父作纪,(张)昭曰:‘文皇不登极位,当为传,不当为纪。’”[12]韦昭《洞纪》“记庖犠已来,至汉建安二十七年”[4]1089(《隋书·经籍志》),韦昭因见古历注的记载“既多虚无”“亦复错谬”,甚不满意,于是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1]1462-1463(《三国志·吴书·韦昭传》)。《洞纪》记载了孙权称吴王以前的历史,黄武以来的部分计划一卷,但未及完成而韦昭被杀。有学者指出:“韦昭将《洞纪》上限定在庖犧氏时代的这种编排,其实也是对孙吴官方自称正统所在的自觉回应,隐含着对孙吴政统与上古三代秦汉一脉相承的自我标榜,亦即为吴与魏、蜀争正统。”[13]28又建安实有二十五年,韦昭记为二十七年,显然拒绝认可曹魏的黄初年号,意谓曹魏是伪政权,吴国直接承继的是汉代正统。韦昭《国语解叙》说虞翻、唐固于“建安、黄武之间”[14]661开始为《国语》作注,即以黄武接续建安,与《洞纪》的正朔观念一致。《建康实录》卷一载曹丕代汉改年号为黄初元年,“而权江东犹称建安”[15]20。《建康实录》有建安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年的纪年,而新出土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也有“建安二十六年”“建安二十七年”的纪年,但罗新指出这些纪年系追改,其实220—222年,孙吴“亦步亦趋地遵奉了北方的延康和黄初年号,直到黄初三年(222)十月”[16],罗新又指出“走马楼吴简中的建安纪年简,都是黄武以后追述前事时所写的,用延长建安年号的方法来遮掩孙吴遵奉曹魏法统的历史”[16]。《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中的吴人铜镜,为当时所铸,其中并无建安二十五至二十七年的纪年,而是沿用延康、黄初的年号。据此可知,建安二十六、二十七年的纪年,完全是吴人对历史的追认,属于孙吴塑造正统观念的产物。韦昭的《吴书》虽遭后人删改(如韦昭《吴鼓吹曲十二篇》称“武烈皇帝”“大皇帝”,而裴注引韦昭《吴书》却称坚、权),但仍能看到塑造正统的努力。兹以吴人最为重视的瑞应图谶问题为例。韦昭《吴书》载富春孙氏发迹前的祥瑞说孙坚葬于家乡吴郡富春县的东面:“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及母怀妊坚,梦肠出绕吴昌门,寤而惧之,以告邻母。邻母曰:‘安知非吉征也。’”[1]1093又载孙坚攻入洛阳得传国玺似有神助,他们发现城南甄官井上早晨有五色气,于是孙坚令人下井探个究竟,发现了汉代的传国玉玺,上面书写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形制是“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1]1099。又载赵咨劝孙权说“朝廷承汉四百之际,应东南之运,宜改年号,正服色,以应天顺民”[1]1124,这与孙权《告天文》强调“权生于东南”意思相同,也受当时流行的“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1]1168的谶语影响。
陈寿《吴书》虽系因袭韦昭《吴书》而成,但以“正魏伪吴”的立场对韦书正统观进行了改造。陈寿于西晋时撰《三国志》,自然以魏为正统。陈寿正统观念最明显的表现是纪魏而传吴蜀,即“唯魏帝为纪,其功臣及吴、蜀之主,并皆为传”。因此《史通·列传》说陈寿《三国志》所载的吴蜀两国的皇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2]42。陈寿的正统意识还体现在故意隐匿史实和曲意为魏晋回护。刘知幾已经注意到陈寿等人不敢直书司马懿之败和司马昭弑君。《史通·直书》记载司马懿、司马昭执掌魏柄时期,曹氏和司马氏斗争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2]180,然而史臣却曲意隐讳不书,“陈寿、王隐咸杜口而无言,陆机、虞预各栖毫而靡述”[2]180。赵翼亦指出陈寿在西晋修撰前史“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17](《廿二史札记》)。陈寿的正统观念也体现在各国史书卷帙规模的安排。陈寿《三国志》所依据的王沈《魏书》有48卷,韦昭《吴书》有55卷,但《三国志》中《魏书》有30卷,《吴书》仅20卷,可见陈寿删减《吴书》最多。陈寿不仅删除了公孙渊对孙权称臣的上表(“《吴书》载渊表权曰”突出了吴国正统),还删除了吴国的谶纬符瑞,因此学者说陈寿“刻意压抑吴国称霸的天命依据”[18]。陈寿当然也有所增补,比如《魏赐九锡文》属于曹丕对孙权的封赐文,体现了尊魏的正统观。
吴人私撰吴国史的动机,应是对陈寿《吴书》“正魏伪吴”的不满。陈寿《三国志》本是私撰,他死后惠帝命人就其家抄写得以流传。《三国志》获得了中朝士人的美誉,正魏伪吴蜀的立场也得到官方的认可。陈寿卒于297年,《三国志》不久流传于世。张勃《吴录》成书一般认为不早于晋惠帝永宁年间(301-302)[19],又陆云多次写信与陆机讨论《吴书》的修撰,时间大约在永宁二年(302)夏之后。吴人入晋后一直遭遇中朝士人的歧视,吴人注重私撰吴国史,应是由陈寿《吴书》流传而激发,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争取故国的正统地位,这可从吴史文献中得到验证。
张勃《吴录》坚持吴国正统的立场。《吴录》说:“大皇帝大会饮宴,下马迎鲁肃,……帝拊掌欢笑。”[20]1652又说孙皓“大皇帝孙也”[21]。张勃不仅称孙权为“大皇帝”,而且称孙休为“景帝”,还称孙坚为“武烈皇帝”、孙策为“长沙桓王”,跟陈寿《吴书》的孙破虏、孙讨逆、吴主、“三嗣主”不同。《吴录》还记载了孙权的《告天文》,这是孙吴标榜正统的重要文献。有学者指出《吴录》的笔法和框架与陈寿《吴书》截然不同,《吴录》不仅为孙吴诸帝设置“纪”,而且调整了传主的取舍标准和列传的内部构造。具体来说,《吴录》增加了不少人物的传记,并且形成了合传、类传的方式,又扩充了卷帙规模,30卷的篇数与魏国史的规模等同。为了尊崇故国,《吴录》收录了陈寿不录的孙策、孙权、孙休的文诰,并且记录瑞应,说明孙氏称帝乃天命所归[19]。
“二陆”讨论《吴书》编纂时明确表达了对韦昭《吴书》和陈寿《吴书》的不满。陆云《与兄平原书》二十五说陈寿《吴书》收录有《魏赐九锡文》和《分天下文》两篇文章,接着又说“《吴书》不载”[8]1117。陈寿《吴书》确实收录有曹丕《策孙权九锡文》和胡综《中分天下盟文》,则陆云所谓的“《吴书》不载”指的是韦昭《吴书》。陆云又说“同是出千载事,兄作必自与昔人相去”[8]1117,还说“《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国事遂亦失”。陆云赞美陆机述《吴书》是保留吴国史实的功臣,勉励陆机的《吴书》应不同于昔人,显然是对既有的吴国史不甚满意。“二陆”准备重写一部《吴书》,主要工作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补作志、表。所谓“百官次第、公卿名伯”[8]1117,当指《百官志》《公卿表》,这是陈寿《吴书》所无的志、表。二是重作人物传记。如陆云说陆逊的传记“诸人所作,多不尽理”[8]1117,则对现有的《陆逊传》不满意,故拟重作。三是增补人物传记和调整传主设置。姚信,陈寿《吴书》无传,陆云认为应有传,宜入《儒林传》;唐固,陈寿《吴书》将之与张纮、严畯、程秉、阚泽、薛综同列,陈寿评又说“严、程、阚生,一时儒林也”[1]1257,可知入《儒林传》,陆云认为宜入《尚书传》。
陆机提出了魏、蜀、吴俱属正统的新型正统观。韦昭《洞纪》以吴接汉,不承认黄初年号,陆机身仕晋朝,提出“三方之王”来塑造吴国正统,这无疑属于明智之举。陆机始任著作郎即撰《顾谭传》,顾谭是吴郡顾氏才俊,则表明陆机对吴国的历史人物已经有过深入的思考。陆机《顾谭传》记载:“宣太子正位东宫,天子方隆训导之义,妙简俊彦,讲学左右。时四方之杰毕集,太傅诸葛恪等雄奇盖众,而谭以清识绝伦,独见推重。自太尉范慎、谢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称其名,而悉在谭下。”[1]1231陆机为谋晋官而撰文称孙权为天子,尊吴之心昭然。惠帝元康六年(296),潘岳替贾谧写诗赠予陆机说:“三雄鼎足,孙启南吴。南吴伊何,僭号称王。大晋统天,仁风遐扬。伪孙衔璧,奉土归疆。”[22]629(《为贾谧作赠陆机诗》)潘岳、贾谧等人称吴国为“僭号”和“伪孙”。陆机回应说“爰兹有魏,即宫天邑。吴实龙飞,刘亦岳立”[22]673(《答贾谧诗》其四),认为魏、蜀、吴三足鼎立,意思说三国都是正统,很显然是对贾谧等人“伪吴”立场的不满。随后的元康七八年间,贾谧以秘书监身份主持《晋书》限断议,当时正统问题的舆论环境可想而知。陆机《辩亡论》强调:“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按,即蜀国)有岷、益,吴制荆、杨而奄交、广。”[23]739北齐的李德林看得非常准确,说:“士衡自尊本国,……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正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征?”[4]1355
陆机提出“三方之王”,原因是魏吴蜀都是汉族政权,三国互不统属,都有争夺正统的资格,只是塑造正统的方式有所差别。东晋习凿齿《晋承汉统论》认为“孙、刘鼎立……魏未曾为天下之主”[24]2230,接受了陆机的三国政权对等地位的说法。东晋开始,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少数民族政权也在寻找合法性,如前赵匈奴刘渊在血统上自称刘邦之后,前燕鲜卑慕容儁选择制造天命,北方政权往往以中原为天下中心自诩正统,进而指责东晋南朝为“僭晋”“东夷”“岛夷”等。刘琨《与石勒书》说“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7]2715,后来宋孝武帝进行礼制改革,建立了以建康为中心的天下观,汉族政权正统的地位得到了普遍承认,文化认同成为正统的核心已深入人心。没有势均力敌的汉族分裂政权,陆机的“三方之王”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了。
三、事异文详:孙吴国史的文学新貌及其本土资源
诸家吴史多出于私撰,它们提供了历史事件的不同侧面,增添了丰富的情节和细节,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充当了后世小说的渊薮,塑造了史家文学的新貌。究其原因,吴地丰富的本土史学资源是取之不竭的宝库,而吴人强烈的正统观念是导致异闻纷纭的心理动机。
诸家吴史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记载,是文学书写的宝贵资源。如诸葛恪被杀,属于孙吴政治的大事,史书记载颇有异同,能够充分揭示诸家吴史的不同面貌。陈寿《吴书》说孙峻已布置好伏兵,散骑常侍张约、朱恩察觉到异常,秘密报告给诸葛恪,诸葛恪正准备返回时,遇到滕胤,称“卒腹痛,不任入”,滕胤并不知晓孙峻的阴谋,勉励诸葛恪“宜当力进”,诸葛恪“踌躇而还”,席间饮酒十分警惕,孙峻建议他可喝自带药酒,方使诸葛恪宽心,然而突起剧变:
胡冲《吴历》载:
张约、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药酒入。[1]1439
滕胤到底是劝勉还是阻止诸葛恪呢?陈寿、胡冲记载完全不同。孙盛《三国异同评》认为《吴历》记载更加准确:“恪与胤亲厚,约等疏,非常大事,势应示胤,共谋安危。然恪性强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岂胤微劝,便为之冒祸乎?《吴历》为长。”[1]1439-1440
又孙峻杀诸葛恪时孙亮的表现,诸家吴史的记载情况如次。前引陈寿《吴书》说“酒数行,亮还内。峻起如厕”。张勃《吴录》说孙峻提刀称有诏收诸葛恪,孙亮起立说:“非我所为!非我所为!”[1]1440然后被乳母引入内室。胡冲《吴历》说:“峻先引亮入,然后出称诏。”[1]1440陈寿与胡冲都说孙亮不在场,而张勃认为孙亮在场,裴松之据此评论道:“峻欲称诏,宜如本传及《吴历》,不得如《吴录》所言。”[1]1440诸葛恪是一代权臣,竟被诛戮,实乃大事,参与者众多,而被杀的过程传闻不同若此,虽然增加了还原历史的难度,但丰富了文学的多样性书写。
又如孙登次子孙英之死,陈寿《吴书》说“五凤元年,英以大将军孙峻擅权,谋诛峻,事觉自杀,国除”[1]1366,然而胡冲《吴历》称“孙和以无罪见杀,众庶皆怀愤叹,前司马桓虑因此招合将吏,欲共杀峻立英,事觉,皆见杀,英实不知”[1]1366,胡冲提供的细节应属客观事实。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David Mitchell文学成就上能算个什么玩意?撑死畅销作家而已。”这让我精神为之一振。我在人群里搜索声音的主人,然后我看到一个高个子的青年人双手插兜离开了咖啡馆。
据此可知,诸家吴史为历史事件保存了不同的说法,陈寿《吴书》尽管因行文简略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但有时不免有“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1]1471(裴松之《上〈三国志〉表》)的弊病。诸家吴史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的缺陷,能够促使读者最大程度地认识历史真实。四库馆臣在《三国志》提要中说裴松之受诏作注的功绩有“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25]等。是非之异、委曲之详、阙佚之事,俱是文学书写的丰富宝库,充分说明诸家吴史的文学意义。
诸家吴史记载的历史详细情节,丰富了文学的情节描写。如孙坚杀南阳太守张咨本末,陈寿《吴书》说张咨自以为与孙坚无甚过节,于是赶赴孙坚营中饮宴:
酒酣,长沙主簿入白坚:“前移南阳,而道路不治,军资不具,请收主簿推问意故。”咨大惧欲去,兵陈四周不得出。有顷,主簿复入白坚:“南阳太守稽停义兵,使贼不时讨,请收出案军法从事。”便牵咨于军门斩之。郡中震栗,无求不获。[1]1096
胡冲《吴历》说:
初,坚至南阳,咨既不给军粮,又不肯见坚。坚欲进兵,恐有后患,乃诈得急疾,举军震惶,迎呼巫医,祷祀山川。遣所亲人说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闻之,心利其兵,即将步骑五六百人诣营省坚。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1]1098
胡冲《吴历》补充了孙坚对张咨不满的原因,提供了孙坚杀张咨的不同说法,从而丰富了历史情节。陈寿隐匿了孙坚杀张咨的原因,实际上加强了孙坚诛杀江东英豪的原罪,而胡冲增补的材料,客观上维护了吴国创业的名声。两人的材料选择实际上体现了不同正统观念的影响。
又王叡被孙坚诛杀,陈寿《吴书》记载简略,说:“荆州刺史王叡素遇坚无礼,坚过杀之。”但张勃《吴录》进行了详细的补充,说王叡曾与孙坚共同讨击零陵、桂阳的地方势力,王叡“以坚武官,言颇轻之”,这是对孙坚的无礼之举。后来王叡准备讨伐董卓,扬言先杀关系向来不好的武陵太守曹寅,曹寅向孙坚陈说王叡罪过,孙坚于是率兵攻袭王叡。王叡听闻兵至,在楼上发问缘由,孙坚前锋回答说:“兵久战劳苦,所得赏,不足以为衣服,诣使君更乞资直耳。”王叡说我无所吝惜,便打开库藏,允许军队进去察看实际情况。等到军队来到楼下,王叡看到孙坚亦在军中,十分吃惊地问道:“兵自求赏,孙府君何以在其中?”孙坚说:“被使者檄诛君。”王叡问:“我何罪?”孙坚曰:“坐无所知。”王叡穷迫,“刮金饮之而死”[1]1097。张勃的记载,使孙坚杀王叡的经过纤毫毕现。
诸家吴史的细节描写,以《江表传》最为精彩,极富文学意味。如孙坚攻入洛阳城,“旧京空虚,数百里中无烟火。坚前入城,惆怅流涕”[1]1099。孙权对周泰满身创痕的动情:“权把其臂,因流涕交连,字之曰:‘幼平,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卿吴之功臣,孤当与卿同荣辱,等休戚。幼平意快为之,勿以寒门自退也。’即敕以己常所用御帻青缣盖赐之。坐罢,住驾,使泰以兵马导从出,鸣鼓角作鼓吹。”[1]1288又如公孙渊斩杀吴使并献首于魏明帝,孙权怒不可遏地说:“朕年六十,世事难易,靡所不尝,近为鼠子所前却,令人气涌如山。不自截鼠子头以掷于海,无颜复临万国。就令颠沛,不以为恨。”[1]1139再如逍遥津孙权遇险归来后君臣一席对话如在眼前,《江表传》载:“权征合肥还,为张辽所掩袭于津北,几至危殆。齐时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权。权既入大船,会诸将饮宴,齐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当持重。今日之事,几至祸败,群下震怖,若无天地,愿以此为终身诫。’权自前收其泪曰:‘大惭!谨以克心,非但书诸绅也。’”[1]1380孙权即位后,对赤壁之战主降的张昭等人的奚落也跃然纸上,《江表传》载孙权即尊位后,归功于当年的周瑜,张昭举起笏板准备褒赞功德,还未及发言,孙权说:“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1]1222张昭闻言十分惭愧,伏地流汗。如是种种,《江表传》的记载仿佛重现了历史现场,使人物栩栩如生、恍然眼前,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当然,《江表传》来源于地方史料,采纳了很多民间传说,因此有颇多不准确的地方。裴占荣《虞仲翔先生年谱》指出:“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书五六十部,惟《江表传》为多谬误,诸如:(一)《孙策传》注载张津死于孙策之前。(二)孙策尽识韩当宾客。(三)《孙匡传》误引孙朗为孙匡。此等过失,悉由松之自举出者,则《江表传》之纪录群言,并不精核,于以可见。”[26]虽然《江表传》史料不够准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史学价值,但其客观上塑造了史家文学的新貌。
诸家吴史也构成了后世小说的创造资源。如孙策杀于吉之事,《江表传》载道士琅邪于吉受到了吴郡和会稽郡民众和宾客的欢迎,引起了孙策的警惕,于是拘系于吉。信徒们请求孙策母亲救助,孙母对孙策说:“于先生亦助军作福,医护将士,不可杀之。”孙策回答道:“此子妖妄,能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尽委策下楼拜之,不可不除也。”将领们联名上书请求孙策宽宥于吉,孙策说:“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1]1110遂急忙斩杀于吉。而孙策之死,陈寿《吴书》说:“会为故吴郡太守许贡客所杀。先是,策杀贡,贡小子与客亡匿江边。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1]1109胡冲《吴历》记载孙策受伤后,医者叮嘱“好自将护,百日勿动”[1]1112,好好将养百日可得康复,然而孙策在“引镜自照”后十分悲怆:“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椎几大奋,创皆分裂,其夜卒。”[1]1112孙策竟因毁容愤慨而死。《搜神记》糅合了《江表传》和《吴历》的记载而加以发挥道:“策既杀于吉,每独坐,仿佛见吉在左右,意深恶之,颇有失常。后治创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1]1112陈寿记载的应该是历史事实,胡冲说是不满毁容而死,而干宝进而说是因杀于吉而遭遇鬼祟,充满了神秘色彩,从而增加了事件的文学性。
私撰吴国史展现了独特的文学面貌,这得益于丰富的吴国地方史料来源。吴国地方史料最多的是郡书和地志,它们记载了吴国地方的人物和风貌。在郡书上,谢承是会稽人,故有《会稽先贤传》;陆凯是吴郡人,故有《吴先贤传》;徐整是豫章人,故有《豫章列士传》;士燮久居交州,又任交州刺史,故有《交州人物志》;陆胤曾任广州刺史,因有《广州先贤传》。孙吴的地志有朱育《会稽土地记》、顾启期《娄地记》、韦昭《三吴郡国志》、徐整《豫章旧志》、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等。察其成书,有的是为家乡所作,有的是为任职之地而作。《江表传》也是汲取吴国地方史料而成,但作者虞溥是中朝人士,曾在鄱阳内史任上大修学校,还给《春秋》经传作注,又撰《江表传》和文章诗赋数十篇[7]2141,兼通经学、史学和文学。他的儿子虞勃“过江上《江表传》于元帝,诏藏于秘书”[7]2141。虞溥所撰《江表传》是其西晋时在江南任职时所撰,有学者据《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十年十一月,“改诸王国相为内史”,指出虞溥任职江南不早于太康十年[27],又有学者据《晋书·虞溥传》的“有白乌集于郡庭”,结合《宋书·符瑞志》的“元康四年十月,白乌见鄱阳”[13]58,认为《江表传》“大抵始作于晋惠帝元康四年(294)前后”[13]59。根据史书的记载,早在西汉武帝的时候,“计书既上太史,郡国地志,固亦在焉”[4]1116(《隋书·经籍志》),汉代以来地方官有每年上“郡国地志”的制度,这是虞溥编撰《江表传》的前提[28]。虞溥是鄱阳内史,当然能接触到“郡国地志”,吴国地方上确实保存了大量的史料,为史家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资源。
这些地方史料中蕴含了吴人的立场和感情。前揭胡冲《吴历》对孙坚杀张咨进行了回护。东晋孙盛敏锐地指出:“《江表传》之言,当是吴人欲专美之辞。”[1]879,更有学者指出《江表传》的“东吴立场”,表现在:美化孙坚的创霸江东,在赤壁之战中强调孙吴统帅的骁勇和谋略,在孙刘荆州之夺中,刻画刘备的无能与贪婪等[27]。虞溥本无赞美吴国的必要,《江表传》所载的情况,当是吴国史料的本来面貌,故学者说,虽由晋吏虞溥所编,藉以蒐集当地民情,故表面上看似由北方立场来定位南方江表偏夷之视野,实际上其内容却保存着江东地区人士话语之原貌[27]。
私撰吴国史在民间生长,不受官方意志和规范的约束,能够自由表达立场、尽情镕铸史料,又适逢江南地方史书的蓬勃兴盛,更加注重异说、情节、细节等,从而形成了与东汉魏晋官方史家迥然不同的新貌。
四、“不朽之书”:吴国史修撰与著述观念更新
凤凰二年(272),华覈上疏救理韦昭说:“今《吴书》当垂千载,……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华覈指出《吴书》是垂名千载的“不朽之书”。无独有偶,大约太安元年(302),陆云与陆机讨论《吴书》说“诲欲定《吴书》,云昔尝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8]1117(《与兄平原书》二十五),又说“出千载事”“《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陆云也将《吴书》的编纂当作流誉千载、垂名不朽的事业。通过对汉晋学术的考察,我们发现吴人史家通过著史来追求不朽是当时的新创。
私撰史书传之不朽的观念早已有之,但在史学独立之前,史学是经学的附庸,史家重在攀附儒家经典,并非关注史书本身。司马迁《报任安书》说所纂《史记》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29]2735,其目的自然是传之后世,但《太史公自叙》明说《史记》是模仿《春秋》而作。班固自叙道:“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29]4235(《汉书·叙传下》)班固将《汉书》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意在“扬名于后世”,其妹班昭最终完成《汉书》,但《东征赋》仍说“唯令德为不朽兮,身既没而名存”[24]987,仍然关心儒家的“立德”不朽。迁、固的著史主要是追摹儒家经典,而非依靠史著本身扬名传世。胡宝国《文史之学》说:“固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自己写《史记》是‘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但他主要的目的还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东汉末年,荀悦在《汉纪》中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他所说的著史的目的全在政治方面,没有掺杂个人因素。这种认识至少在魏晋以后不具有普遍意义。魏晋以后私人撰史风起云涌,当与时人著史以求不朽的认识有很大关系。”[30]胡宝国从著史目的来讨论,亦从另一角度说明汉与魏晋之史书意识不同。随着魏晋史学的独立,史部著作骤增,史书不朽才进入文人学者的视野。
曹丕谓之不朽的文章主要指属辞、著论,后由刘劭加入史著而延伸至属辞、著述,从而贯穿了集部、子部和史部。王充《论衡·对作》对作、述、论辨析道:“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31]1180-1181“五经”称为“作”,出于圣人之手。司马迁、刘向、班彪(即《史记后传》,后班固续成《汉书》)的史书称为 “述”。王充说“论者,述之次也”[31]1180,“论”主要是子书。曹丕《典论论文》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桓范是曹丕的亲近之臣,所作《世要论·序作》强调“著作书论”的“不朽”和“流誉于千载”[24]1263。曹丕《典论论文》突出强调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文体的文学价值,又说“唯幹著论,成一家言”,其《与吴质书》称徐幹所著的《中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23]591,可知曹丕的文章范围既有诗赋铭诔,又有奏议书论,另有子书《中论》,前者为狭义的“文”,后两者是广义的“论”。曹丕的创作重点亦在诗赋和子书《典论》。胡冲《吴历》记载说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1]89,曹丕将自己的诗赋和《典论》赠给孙权,可知诗赋和子书属于曹丕的得意之作,也是曹丕文章观念的显证。徐幹重视著论,而不重视诗赋,因此他“废诗赋颂铭赞之文,著《中论》之书二十篇”[32]。夏侯惠推荐刘劭时说“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1]619,刘劭本人的文章确有子书《人物志》的著论之作和《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等属辞之作,与曹丕同辙,这并不意外,因为刘劭是太子曹丕的舍人。但刘劭进一步突出了史著的地位,其《人物志·流业》说“文章之材,国史之任也”[33]40,又具体说“能属文著述,是谓文章,司马迁、班固是也”[33]37-38。刘劭认为文章包括了属文和著述,而著述包括了《史记》《汉书》等史书。刘劭以《史记》《汉书》为“述”的思想渊源于王充《论衡》。刘劭的著述比曹丕的著论多了史著,但刘劭突出的史著尚不在曹丕文章不朽之列。实际上,曹丕标举文章的“立言”不朽,虽属于孤明先发,但亦是空谷足音,久无嗣响。笔者遍检《三国志》和严可均《全三国文》等存世文献,曹魏士人的不朽观念仍然集中在“立功”领域。即使是曹丕,即位后三次举兵伐吴,虽然无功而返,但“立功”之意判然,而“立言”之论靡闻。《搜神记》载魏明帝曾下诏三公说:“先帝昔著《典论》,不朽之格言。其刊石于庙门之外及太学,与石经并,以永示来世。”[1]118《搜神记》的记载是否可信暂且不论,但魏明帝的“不朽之格言”不过是祖述曹丕的主张而已。
吴国史家最早明确提出了史著不朽的观念。华覈上疏孙皓请求召回薛莹续成《吴书》时说薛莹不仅学术广博,而且文章更妙,“同竂之中,莹为冠首”[1]1256,如今懂经学的多,但“记述之才,如莹者少”[1]1256,又前揭华覈上疏挽救韦昭说:“今《吴书》当垂千载,……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薛莹和韦昭俱是文学家,都有别集传世,但华覈说薛莹的“文章尤妙”突出了“记述之才”,主要指《吴书》的写作才能。西晋的“二陆”称编《吴书》是“真不朽事”“出千载事”“可垂不朽”,这既是对华覈观点的呼应,又是对史著地位的确认。我们可以用曹魏国史编纂的事情与之相对比。曹魏应当进行了三段过程的国史编纂,《史通·古今正史》有载:“魏史,黄初、太和中始命尚书卫顗、缪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又命侍中韦诞、应璩、秘书监王沈,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司徒右长史孙该,司隶校尉傅玄等,复共撰定。其后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2]321又《晋书》王沈本传载其“好书,善属文。……后起为治书侍御史,转秘书监。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与荀顗、阮籍共撰《魏书》,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7]1143。据此可知,第一次是曹丕、曹睿时期,参与者有卫顗、缪袭等,但只是粗略写成纪传,未能竟功;第二次是曹髦时期,参预者有韦诞、阮籍、孙该、应璩、王沈、傅玄、荀顗等,开始于正元二年(255);第三次是王沈“独就其业”,在曹奂景元二年(261)后、咸熙二年(265)前[34]。《魏书》编纂的史臣基本是文学家,但未见其有讨论史著不朽的记载。
经过吴人史家的努力,史著不朽的观念很快被广泛接受。“二陆”与曹丕一样也关注诗赋与子书,如陆云《与兄平原书》其三说“诲颂,兄意乃以为佳,甚以自慰……佳文章已足垂不朽”[8]1142-1143,又葛洪《抱朴子》载陆机作子书未成,临死前还念念不忘说:“古人贵立言,以为不朽。吾所作子书未成,以此为恨耳。”[20]2709但“二陆”在编纂《吴书》时突出了史著不朽观念,这是前所未有的,属于当时的独造。从此之后,史著不朽成为文人关注的重点。东晋王隐勉励祖纳编纂晋史说:“当晋未有书,而天下大乱,旧事荡灭,君少长五都,游宦四方,华裔成败,皆当闻见,何不记述而有裁成?”[7]1698又说应劭《风俗通》、崔寔《政论》、蔡邕《劝学篇》、史游《急就章》等“行于世”的著作可以“没而不朽”,又强调自己“疾没世而无闻焉,所以自强不息也。况国史明乎得失之迹……”[7]1698,察其语气,王隐似乎视国史的价值超过了子书。宋文帝令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于是“鸠集传记,增广异闻”[35],宋文帝看到书后十分满意,赞叹道:“此为不朽矣!”[35]刘宋何法盛看到郗绍《晋中兴书》说“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36],何法盛将郗绍与袁宏、干宝等史家并列,说明经过魏晋学者的努力,史著不朽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何以史著不朽由吴地史家提出?这与吴国史学的发达有关。孙吴的史学成就在三国之中最为杰出。蜀汉不置史官,导致史学不甚发达,但也有谯周《古史考》《蜀本纪》、陈术《益部耆旧传》及《志》、王崇《蜀书》等史学著作,并孕育了陈寿这样的著名史学家[37],但《隋书·经籍志》所载蜀国史著仅有谯周《古史考》。魏国虽然有专门的史学机构秘书监和著作省,并且进行了三次国史编纂,但魏国史学著作并不多见。检核《隋书·经籍志》,明确为魏人编纂的有7部④,明确为吴人编纂的有12部⑤之多。《隋书·经籍志》所载史书当然不能完全反映三国时期的史著面貌,但吴国史书能保存至唐初,历经三百年汰洗后仍然传世,说明质量比较可靠。正是史学发达的传统,入晋吴人才会自然而然地萌发私撰吴国史的意愿。
综上所述,孙吴国史的官修私撰,竟是如此的意蕴丰富,不仅促进了史家文学的发展,而且推动了著述观念的更新。孙吴的史学著作在当时最为发达,最突出的表现是郡书和地志的繁多,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丰富的典藏。孙吴国史的生命力旺盛,直到唐初编《隋书·经籍志》,尚颇多存于天壤之间。孙吴国史蕴含的种种特点,倘若没有深入切实的细致研究,则很难得到准确的揭示,既有的曹魏学术中心的观念也就无法得到破除,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重新厘清文史发展的脉络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 陆云《与兄平原书》二十六说:“义高家事正当付令文耳。弟彦长昔作《吴事》,云三十卷,可令钦求。谨启。”刘运好《陆士龙文集校注》认为“彦长”当为“彦先”(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1121页)。
② 类似的成果有陈博《韦昭〈吴书〉考》(《文献》1996年第3期),唐燮军《韦昭〈吴书〉三题》(《书目季刊》第43卷第3期,2009年12月),唐燮军《张勃〈吴录〉对孙吴国史的重构及其边缘化》(《史林》2015年第4期),熊明《汉魏六朝杂传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陈娅妮《晋代非吴地著史者的孙吴历史书写——以〈吴纪〉〈江表传〉为中心》(《东吴学术》2019年第3期)等,中国台湾学者王文进《论〈江表传〉中的南方立场与东吴意象》(《成大中文学报》第46期,2014年9月)、王文进《论裴松之〈三国志注〉中的“三吴之书”》(《东华汉学》第22期,2015年12月)和陈俊伟《韦昭〈吴书〉之国族本位与人物书写》(《东华汉学》第25期,2017年6月)等,日本学者满田刚《关于韦昭〈吴书〉》(《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6期,第2004年)、《胡冲〈吴历〉辑本》(《创价大学人文论集》24期,2012年)、《环济〈吴纪〉辑本》(《东洋哲学研究所纪要》第29号,2014年)、《关于虞溥〈江表传〉》(《创价大学人文论集》30期,第2018年)等。
③ 参见宫宅洁《魏蜀吴的正统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汉字情报研究所编《三国从鼎立到统一——史书碑文的阅读》,京都:研文出版,2008年)和渡边义浩《孙吴的正统性与国山碑》(载《三国志研究》第2号,2007年)。
④ 即王沈《魏书》、鱼豢《典略》、无名氏《海内先贤传》、周斐《汝南先贤传》、苏林《陈留耆旧传》、魏文帝《列异传》、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等。
⑤ 即韦昭《吴书》、谢承《后汉书》、薛莹《后汉记》、韦昭《洞记》、谢承《会稽先贤传》、陆凯《吴先贤传》、徐整《豫章列士传》、张胜《桂阳先贤画赞》、朱育《会稽土地记》、顾启期《娄地记》、朱应《扶南异物志》、万震《南州异物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