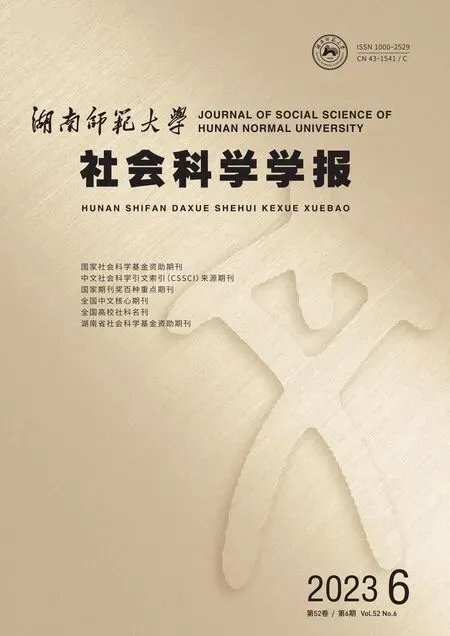跨媒介的故事讲述及其相关叙事学命题
尚必武
一、问题的提出:媒介盲视与跨媒介叙事研究的障碍
美国叙事学家西摩·查特曼在《故事与话语》(1978)一书中引用了法国叙事学家克劳德·布雷蒙的如下论述:
独立的意义层次,它被赋予一个可以从信息整体中分离出来的结构:故事(story,récit)。这样,任何一种叙事信息(不仅仅是民间故事),不管它运用什么表达过程,都以同样的方式显示出这一层次。它只是独立于其所伴生的技术。它可以从一种媒介转换到另一种媒介,而不失落其基本特质:一个故事的主题可以成为一部芭蕾剧的情节,一部长篇小说的主题可以转换到舞台或者银幕上去,我们可以用文字向没有看过影片的人讲述影片。我们所读到的是文字,看到的是画面,辨识出的是形体姿态。但通过文字、画面和姿态,我们追踪的却是故事,而且这可以是同一个故事。而被叙述(narrated,raconté)的对象则有其自身的意指因素,即故事因素(racotants):既不是文字,也不是画面,又不是姿态,而是由文字、画面与姿态所指示的事件、状态或行动。[1]7
众所周知,布雷蒙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人物。在上述文字中,布雷蒙重点论述了故事如何被不同的媒介所讲述而不改变其本质,故事的内容与意义不会受到诸如芭蕾舞、小说、电影、文字、画面、手势等媒介的影响。在认同和承袭布雷蒙关于故事可以独立于媒介这一论点的基础上,查特曼指出:“故事的这种可转换性,为声称故事确实是独立于任何媒介的结构,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由。”[1]7在查特曼看来,布雷蒙所论述的故事可转换性这一特点充分说明故事可以独立于媒介。彼时,以布雷蒙和查特曼为代表的叙事学家无视媒介的作用,纷纷走向对叙事普遍结构的探寻,结果导致了叙事学研究中长期存在“媒介盲视”(media blindness)的问题。
实际上,在叙事学研究阵营,布雷蒙、查特曼所表现出的媒介盲视问题并非个案。我们可以从叙事的定义、叙事对象的划分以及叙事学的定义三个方面来考察叙事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媒介盲视现象。首先,在关于叙事的定义中,很少发现有媒介的存在。比如,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说:叙事是“一个或一序列事件的再现”[2]127;以色列叙事学家施劳米什·里蒙-凯南把叙事虚构作品界定为对“虚构事件的连续性叙述”[3]2;美国叙事学家波特·阿博特认为叙事是“对一个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再现”[4]13;《叙事学词典》把叙事界定为“一个或多个虚构或真实事件(作为产品、过程、对象和行动、结构与结构化)的再现,这些事件由一个、两个(明显的)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多个(明显的)受述者来传达”[5]58。其次,就叙事对象的划分而言,无论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法布拉,休热特和查特曼提出的故事与话语的二分法,还是热奈特提出的故事、叙述话语、叙述行为,里蒙-凯南提出的故事、文本、叙述行为,以及米克·巴尔提出的叙述、叙述技巧、叙述文本的三分法,均难以发现媒介的存在。最后,在叙事学的定义中,我们也同样找不到媒介的影子。《叙事学词典》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界定叙事学:
1.受结构主义启发而发展的叙事理论。叙事学研究叙事的本质形式和功能(不包括其表述媒介)并试图描述叙事能力的特征。尤其是,它检验一切叙事所共有的(在故事、叙述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层面上)和能够使一切叙事互不相同的东西并且试图解释生产和理解这些叙事的能力。
2.作为一种对有时序的情境与事件进行表述的语词模式的叙述研究。在这一限定意义上,叙事学忽视本身的故事层面(例如,它并不企图系统地阐述故事或情节的语法),而专注故事与叙述文本,叙述行为与叙述文本以及故事与叙述行为之间的可能关系,具体地说,它考察语式、语态和声音等相关问题。
3.从叙事学模式和类别的角度,对特定(组合)的叙事进行研究。[5]66
就上述叙事学定义而言,无论是在关于叙事研究方法的理论来源(结构主义)还是在研究对象层面(事件与叙事类别),均没有提及媒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事学词典》在强调叙事学的研究重点是叙事的“本质形式和功能”的时候,还专门有意地以括号形式把表述媒介排除在外。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导致布雷蒙、查特曼、普林斯等叙事学家对媒介采取了盲视的态度,即媒介盲视的原因何在?
在《故事的变身》一书中,美国著名叙事学家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除了像查特曼一样引用布雷蒙关于故事可以独立于媒介的论断外,还引用了罗兰·巴特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那段广为人知的话:
世界上叙事作品之多,不计其数;种类浩繁,题材各异。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的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奇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色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绘画。而且,以这些几乎无限的形式出现的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6]
在上文中,巴特提到了承载叙事的各类媒介,如语言、画面、手势、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彩色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等,瑞安根据巴特关于叙事媒介的描述,认为叙事学先驱者们在建构叙事学这门学科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构想“一个超越学科与媒介的研究领域”[7]4。令人遗憾的是,叙事学后来发展成了一门主要研究文学叙事的学科。瑞安将造成此局面的主要原因归咎为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的影响。瑞安认为,在热奈特的影响下,叙事学从原本关注各种媒介的叙事最终演化成了主要关注文学叙事。众所周知,热奈特在《修辞格三》《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等系列论著中,提出了耳熟能详的时长、时距、频率、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等众多叙事学术语,建构了较为丰富的叙事学批评体系,但他的研究确实只聚集于文学叙事作品。譬如,热奈特最负盛名的《叙事话语》就完全是围绕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而作。瑞安号召将叙事研究重新拉至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轴线,她指出:“跨媒介的叙事研究使得媒介研究和叙事学均受益匪浅。”[7]4
既然跨媒介叙事学研究原本就是叙事学先驱者们在建构这门学科时所包含的一个项目,同时跨媒介叙事研究对叙事学和媒介研究都有裨益,那为什么跨媒介叙事研究迟迟没有展开?在瑞安看来,有两个原因使得跨媒介叙事研究遭遇障碍。第一个原因来自叙事学内部的立场,瑞安称之为“基于语言的叙事研究进路或曰言语行为进路”[7]5。普林斯、热奈特、查特曼是这一立场的代表人物,他们重点强调叙事是叙述者向受述者讲述故事的一种行为,因此把叙事作为一种语言行为或现象,进而把其他非语言媒介的叙述行为排除在研究范畴之外。在这一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列入修辞叙事学代表人物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费伦关于叙事的修辞定义(“某人在某个场合下为了某个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重点强调了叙事的言语行为,同样不涉及其他非语言媒介的叙事[8]5。跨媒介叙事研究遭遇障碍的第二个原因则来自媒介研究阵营,突出表现为“激进的媒介相对主义教条”[7]5。瑞安举了意大利符号学家兼文学家翁贝托·艾柯谈论文学作品与电影改编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艾柯宣称他的小说《玫瑰之名》与让-雅克·阿诺对该作品的电影改编之间毫无关系,二者只是名字相同而已。信奉“激进的媒介相对主义教条”的媒介理论家把“将媒介看作自足的符号体系,其资源同其他媒介资源是不可通约的”[7]5-6一说奉为圭臬, 认为不同媒介无法表达相同或相近的意义。总的来说,来自叙事学内部和媒介研究内部的两股保守力量使得跨媒介叙事研究遭遇阻碍。挪威奥斯陆大学的丽芙·豪斯肯(Liv Hausken)与瑞安持有相似观点。豪斯肯把媒介盲视划分为“总体的媒介盲视” (total medium blindness)和“冷漠的媒介盲视”(nonchalant medium blindness)两种类型。二者的区别在于,“总体的媒介盲视”主要表现为无视媒介的重要性,而“冷漠的媒介盲视”主要表现为无视具体媒介的特殊性,试图以一种媒介的理论去研究另一种媒介[9]。
无论是布雷蒙、查特曼等叙事学家们所表现出的媒介盲视问题,还是瑞安与豪斯肯关于媒介盲视原因的解释,都让我们愈加明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叙事信息的传递与媒介使用密不可分。在媒介文化得到充分彰显的当下,叙事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已然成为叙事学研究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环。尽管就叙事能力而言,“媒介的资质是不一样的,有些媒介是天生的故事家,有些则具有严重的残疾”[7]4,但走向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研究无疑是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
二、走向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研究
在《跨媒介叙事》一书的“导论”中,瑞安对跨媒介叙事学迟迟未被建构起来的现状表示极大的惋惜,同时呼吁在“进入对比较媒介研究和叙事兴趣骤增的时期(后者为人文科学中所谓的叙事转向所证明),人们再也不能对媒介的内在属性如何塑造叙事形式并影响叙事体验这一问题熟视无睹了”[10]1。在笔者看来,叙事理论家们若要正视叙事媒介影响叙事体验的问题,就意味着要建构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学,而首当其冲就是需要应对和解决叙事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媒介盲视问题。
为了应对媒介盲视问题,建构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学,瑞安提出了两条解决路径。
第一条解决路径是重访叙事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尝试在此基础上研究超越语言的叙事。瑞安指出,叙事在理论上是一种超越特定媒介的意义类型,但在实践上语言成为叙事可选的最佳媒介。瑞安考察了关于叙事和语言之间的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叙事是言语专属的现象,即离开了语言就没有叙事,这一观点与跨媒介的叙事研究不相容。第二种观点认为所有叙事的集合是一种模糊的集合,叙事性的最充分实施见于语言支撑的形式,只有将言语叙述的参数迁移到其他媒介,跨媒介叙事研究才有可行性。第三种观点认为叙事是独立于媒介的现象,虽然没有任何媒介比语言更适合让叙事的逻辑结构一目了然,但叙事学家们依然重点研究叙事的非言语显现[10]13。除了第一种观点之外,第二种观点和第三种观点基本认同叙事之于媒介的运用以及跨媒介叙事的可能性。此外,瑞安还指出:“倘若叙事学要拓展成一个无涉媒介的模型,第一步就是要承认其他的叙事模式,也就是说,唤起叙事脚本的其他方式。”[10]11瑞安具体论述了五种无涉媒介的叙述模式:第一,讲述式/模仿式(diegetic/mimetic)。讲述式叙述是叙述者以言语讲故事的行为;模仿式叙述是一种展示行为,模仿式叙述的范例是所有的戏剧艺术,包括电影、戏剧、舞蹈、歌剧等。第二,自主式/说明式(或辅助式)[autonomous/illustrative(or ancillary)]。在自主式模式中,接收者可以从文本摄取故事的逻辑构架;在说明式模式里,文本依靠接收者对情节的先前知识,重述并完成故事。第三,接受式/参与式(receptive/participatory)。在接受式模式里,接受者不在被呈现的事件里起积极作用,而把自己想象成事件的目击者;在参与式模式中,接受者可以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通过其能动性促成情节的发展。第四,确定式/不确定式(determinate/indeterminate)或称现实式/虚拟式(actual/virtual)。在确定式模式中,文本在叙事轨迹上规定足够数量的点来投射一个较为确定的脚本。不确定式模式只规定一两个点,由阐释者来想象一个(或多个)虚拟曲线穿过这些坐标。第五,字面式/隐喻式 (literal/metaphorical)。字面式叙述完全符合叙事定义,而隐喻式叙述则仅仅使用叙事的某些特征[10]12-13。
瑞安提出的第二条解决路径是重新定义叙事。在瑞安看来,“跨媒介叙事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为经典叙事学中的基于语言的正常定义寻找替代”[7]7。笔者曾指出,关于叙事的定义有“事件再现”“文本类型”“跨学科视角”三种基本类型,但这三种类型的叙事定义均把媒介排斥在外[11]65-73。为了建构有媒介意识的叙事学,瑞安提出关于叙事的模糊子集式定义:
空间维度
1.叙事必须是关于一个世界,栖居着个性化的存在物。
时间维度
2. 该世界必须处于时间中并历经显著改变。
3. 改变必须是由非习惯性物理事件所引起。
心理维度
4. 事件的某些参与者必须是智能行动者,具有心理生活,并对世界的状态具有情感反应。
5. 某些事件必须是这些行动者的有目的的行动,由可识别的目标和计划所驱使。
形式与语用维度
6. 事件序列必须形成一个统一的因果链并导向封闭。
7. 至少某些事件的发生必须被断言为故事世界的事实。
8. 故事必须向接收者表达某种意义。[7]8
必须指出的是,瑞安从空间、时间、心理、形式与语用维度来界定叙事,但实际上并没有明显地将媒介纳入叙事的范畴。笔者之前将叙事界定为“以某种媒介为基础、具有某种意义的某种序列”[11]71。在笔者看来,叙事具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基本要件: 序列(sequence)、意义(meaning)、媒介(media)。具体说来,首先,叙事必须是关于“什么”的序列;其次,序列的特定效果在于产生某种意义,实现或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最后,序列的存在需要特定的载体,这个载体就是媒介。离开了媒介,序列就无法实现[11]71。
在重新界定叙事之后,我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媒介?如何把媒介纳入叙事研究的范畴?约书亚·迈耶罗维茨说:“媒介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我们对该领域的主题内容是什么并没有共同的理解。”[12]55换言之,媒介概念具有很大的含混性。瑞安曾这样描述媒介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社会学家或文化批评家的回答可能是电视、电台、电影、互联网;艺术批评家可能列举音乐、绘画、雕塑、文学、戏剧、歌剧、摄影、建筑;艺术家的清单会以黏土、铜、油彩、水彩、织物开始,以所谓混合媒介作品的奇特物品结束,如草、羽毛、啤酒罐拉环;信息理论家或文字历史学家会想到声波、古本手卷、抄本古籍、浮凸表面(盲文文本)、硅片;现象学派的哲学家会把媒介分成视觉、听觉、言语,抑或是触觉、味觉、嗅觉。媒介理论和其他领域一样,研究对象的构成取决于研究者的目的。”[7]16-17在《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一书中,克劳斯·布鲁恩·延森把媒介界定为“物质的载体、表达的话语或情态形式(modal forms)以及全社会对于交互活动的形式与限制加以规范的制度”[13]61。延森把媒介细化为三种类型:物质、形式与制度。第一,作为一种物质,媒介具有“特殊的、可控制的以及历史的形态”,进而使得“表达与交互成为可能”[13]61。第二,作为物质载体的媒介可以通过形式来实现人类的交流与传播,譬如言语、歌曲、静止与活动的图像等,“这些形式一方面基于生物和人类的感觉;另一方面,形式深受历史悠久的差异和教化的影响”[13]62。第三,媒介也是一种制度的存在,是“社会中特殊的、随历史而变动的制度——可控制的、启发思维的制度”[13]62。在延森看来,诸如书写、印刷和电子媒介等不仅延伸了文化在空间的发展,而且也延续了民族、国家等。
与延森不同的是,胡易容、赵毅衡从符号学视角来界定媒介,认为“符号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载体的物质类别称为媒介(medium,又译‘中介’),媒介是存储与发送符号的工具。媒介与符号载体的区别在于符号载体属于个别符号,而媒介是一种类别:例如一封信的符号载体是信纸上的字句;而媒介是书写,是一个文化类别”[14]143。他们根据媒介的功能,把媒介划分为三种类型:记录性媒介、呈现性媒介、心灵媒介。记录性媒介指的是能保存的符号文本,比如岩画、文字书写与印刷等。呈现性媒介指的是用于表演的符号,如身体姿势、言语、音乐、电子技术等。心灵媒介是构成幻想、梦境、白日梦等的符号载体,它们往往被认为是符号表意的草案[14]143。如果我们可以通过扩大叙事概念的范畴来将媒介包含在内,那么是否也可以从叙事角度来界定媒介?
从叙事角度出发,瑞安提出了审视媒介的三种可能路径,即作为符号的媒介(media as semiotic phenomena)、作为技术的媒介(media as technologies)与作为文化实践的媒介(media as cultural practices)。瑞安的吁求是将叙事学研究的关注点从文字叙事转向非文字叙事,从语言形式的叙事转向非语言形式的叙事,并在《跨媒介叙事》一书中重点考察了面对面叙述、静态图片、动态图片、音乐、数字媒介等。然而,跨媒介叙事是否就等同于非文字叙事或非语言形式的叙事?该问题涉及跨媒介叙事研究可能存在的误区。在瑞安看来,当下的跨媒介叙事研究大致存在三种可能的偏误性认识:第一,将个体文本的特质视为媒介特征,但问题在于个体文本的特征是否必然为媒介所体现?第二,媒介盲视,即忽略不同媒介的具体特性,直接把某一种媒介研究中的概念移植或搬用到另一种媒介的研究。第三,激进相对主义,即过于强调媒介的独特性,认为每种媒介都要有自己完全不同于其他媒介的叙事学体系与研究工具[10]28-29。可见,就三种潜在的问题而言,媒介盲视与激进相对主义截然对立,前者无视媒介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后者则过于强调具体媒介的独立性与特殊性。在媒介盲视和激进相对主义之间,瑞安提出了8种相应的解决方案:(1)批判为文学而提出的叙事学模型;评价其范畴在书面语言之外的媒介的适用性;若有必要,改编这些工具或提出新的工具。(2)界定非言语媒介讲故事的条件。(3)对“叙事性的模式”进行划分。(4)辨别并描述某一媒介所独有的叙事文类、手法、问题。(5)探讨再媒介化现象,尤其从一个媒介到另一媒介的叙事转移问题。(6)探讨“媒介X能做而媒介Y不能做的”,并追问媒介如何突破局限。(7)研究“多媒体”媒介中各个轨道对叙事意义的贡献。(8)追问特定媒介的属性是否会促进或妨碍叙事性[10]29。
在笔者看来,瑞安所列上述8种解决方案重点涉及叙事学家们把媒介引入叙事研究后的两个维度:一是调整与更新现有的叙事理论体系和概念以更好地描述不同媒介所承载的叙事;二是聚焦和探讨不同媒介的特殊性及其之于叙事再现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建构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学不仅要把媒介纳入叙事研究的范畴,调整或更新现有的叙事理论体系和概念,而且还要关注媒介尤其是跨媒介之于叙事研究提出的新命题,尤其是在宏观层面涉及叙事本质的叙事性以及在微观层面涉及诸如叙事时间、空间、人物等要素的叙事学命题。
三、跨媒介的故事讲述及其叙事性问题
在《媒介间性与故事讲述》一书的“编者前言”中,主编玛丽娜·格里沙科瓦(Marina Grishakova)与玛丽-劳尔·瑞安说:“尽管媒介的概念在叙事学中已变得非常重要,然而,可以用来指涉叙事与媒介之间关系的表述有很多,术语由此已成为一个真正的噩梦:跨媒介性、媒介间性、复媒介性、多媒介性,更别说多模态性了。这些术语之间到底有何区别?这种术语的模糊性延伸到了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一研究:应该将其称为多媒介、跨媒介、媒介间、还是简单的‘以媒介为中心’的叙事学?”[15]事实确实如此。如果说叙事学本来就是术语和概念扎堆的地方,而将叙事与媒介进行关联之后,关于媒介与叙事的相关表述简直成了术语的狂欢,从媒介到媒介间,从多媒介到跨媒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难怪格里沙科瓦和瑞安用术语的噩梦来形容当下有关叙事与媒介描述的乱象,比如跨媒介性(transmediality)、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复媒介性(plurimediality)、多媒介性(multi-mediality)、多模态性(multi-modality)等。那么上述这些关于媒介的诸多概念之间存在什么区别呢?
2005年,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了备受学界期待和关注的叙事学研究大型工具书《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该书收入了题为“媒介间性”的词条,撰写者是跨媒介叙事学的权威人物沃纳·沃尔夫(Werner Wolf)。沃尔夫对当下叙事学研究中与媒介相关联的术语做了区分与阐释。在沃尔夫看来,“媒介间性”在广义上来说是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的媒介等效物,涵盖不同媒介之间的所有关系,在狭义上指的是一部特定作品对多种媒介(或感观通道)的运用,例如,歌剧采用了手势、语言、音乐和视觉舞台设置,由此导致了歌剧的媒介间性。“复媒介性”指的是包括多种符号系统的艺术品。“媒介间转换”(intermedial transposition)指的是从一种介质到另一种介质的改编。“媒介间参照”(intermedial reference)指的是一个文本涉及其他媒介的现象,如以“其他媒介”为主题(如讲述画家或作曲家职业生涯的小说)、对其他媒介进行引用(将文本插入绘画中)、描述(以艺格敷词手法在小说中再现某幅画作),或从形式上对其进行模仿(借用赋格曲结构的小说)等。“跨媒介性”指的是一个文本的表现形式不受特定媒介束缚的现象[16]252-256。同年,伊莉娜·拉耶夫斯基(Irina O. Rajewsky)对内媒介性(intramediality)、媒介间性、跨媒介性也做了区分。在拉耶夫斯基看来,所谓的内媒介性指的是叙事作品只涉及一种媒介的现象;媒介间性指的是涉及超越媒介界限的多种媒介现象,至少会涉及两种媒介;而跨媒介性指的是叙事作品并不指定某一具体媒介来再现的现象,其媒介性可以由多种不同的媒介来实现[17]43。
倘若参照叙事的故事/话语二分法,话语在本质上就是故事讲述,我们可以据此认为跨媒介叙事的本质就是“跨媒介的故事讲述”(transmedia storytelling)。这也是当今国际媒介研究的权威学者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持有的观点。在詹金斯看来,跨媒介的故事讲述指的是对跨越诸如小说、绘本、电影、电视连续剧、电子游戏等媒介对人物、故事以及世界的再现。具体说来,跨媒介的故事讲述“代表了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一部虚构作品内在元素为了创造一个统一而协调的娱乐体验,系统性分布在多个传递渠道上。理想状态是,每个媒介都为故事的展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8]。詹金斯的这一观点在德国跨媒介叙事理论家扬-诺尔·托恩(Jan-No⊇l Thon)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托恩把跨媒介叙事视作“叙事再现的跨媒介策略”(transmedial strategies of narrative representation)[19]31,并且以电影、绘本、电子游戏为对象,重点讨论了跨越多种媒介的叙事再现与故事世界之间的关系,不同叙述者所使用的叙述再现策略,以及对人物意识加以再现的主体策略。与托恩类似,瑞安也受到了詹金斯的启发,讨论了跨媒介的故事讲述,并列出若干个不是跨媒介故事讲述的反例,譬如改编(adaptation)或插图(illustration)、跨虚构性(transfictionality)、多个媒介平台为某个叙事产品所做的广告、多模态叙述(multi-modal narration)等。与之相反,真正的跨媒介故事讲述指的是叙事内容形成“一个统一的故事”(a unified story),它是一种自足的意义类型,遵循着一条从故事的初始状态到复杂化再到冲突和释然的时间弧线[20]4。瑞安调侃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叙事文本的接受者如果要通过读一本小说来了解一个故事的开端,然后去电影院了解下一段故事,又购买绘本去读下一段故事,最后又去玩电子游戏来发现故事的结尾,该有多么恼火。这显然不是真正的跨媒介故事讲述。瑞安指出:“跨媒介故事讲述不是连续剧,它不是单一的故事,而是各种文件中所包含的各种独立的故事或事件。这些故事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发生在同一个故事世界。人们愿意在许多文件和多个平台上寻找信息,因为他们非常喜欢故事世界,以至于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关于它的信息。”[20]4如果跨媒介故事讲述不是一般所理解的改编、插图、跨虚构性、多个媒介平台为某个叙事产品所做的广告、多模态叙述等,而是指通过不同的媒介平台来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再现一个整体的故事世界,那么这些不同媒介又如何影响故事世界的建构?这个问题涉及叙事性,即叙事何以成为叙事,以及为什么有的叙事会比其他叙事更像叙事的问题。
沃纳·沃尔夫在《跨媒介叙事学:理论基础与部分应用(小说、单幅图画、器乐)》一文中,将媒介看作一种交流手段,认为这种手段可以被看作一种文化实践,不仅受到文化规约的影响,也受到技术渠道和制度渠道以及符号系统的影响,媒介的符号要素、技术要素和历史文化要素影响了其对信息的传递[21]263。这种可变性也会影响作品的叙事性。在这个意义上,沃尔夫说:“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学表明,有的媒介比其他媒介更好地支持接受者的叙事化倾向。这种可变性的结果之一就是对表达出来的故事的结果、实现以及人际可辨识性也存有差异性。”[21]277沃尔夫根据媒介对叙事性程度的影响性,将媒介划分为四种类型:强叙事媒介(strongly narrative media),如小说、戏剧剧本及其相关的表演、电影等;产生叙事性的强媒介(strongly narrativity-inducing media),如某些系列图画或单个图画;产生叙事性的弱媒介(weakly narrativity-inducing),如贝多芬的器乐作品;以及非叙事媒介(non-narrative media),如抽象的油画、电话黄页等[21]278。我们知道,在叙事学那里,几乎所有的叙事研究都绕不开叙事性。《叙事分析手册》的两位主编吕克·赫尔曼与巴特·凡瓦克说:叙事性是当下“叙事学研究的一个中心概念”[22]172。阿博特认为叙事性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4]25。梅尔·斯滕伯格曾这样解释“叙事性”的重要地位:“只有通过叙事性来界定叙事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过于限定叙事的主题,也不会错过叙事的文类特征,叙事学家也才有可能不受约束地研究叙事学。”[23]115约翰·彼尔、加西尔·兰德强调说:“叙事性成为叙事学研究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话题”[24]7,“正如早期的文学理论或诗学对‘文学性’的探讨一样,当代叙事学研究的一些重要论题都是围绕叙事性展开的”[24]8。进入21世纪,叙事性得到了叙事学家们前所未有的关注,比如,在《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第二版的“后记”中,里蒙-凯南坦言:“现在,同‘文学叙事学’相比,我更加关注‘叙事性’。”[3]151笔者曾指出,“叙事性”是指“叙事的特性”(the quality of being narrative),它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叙事性”指涉一种“属性”,即叙事之所以成为叙事的品质,凡具有“叙事性”的就是“叙事”,否则就是“非叙事”。第二,“叙事性”指涉一种“程度”,即不同的叙事具有程度不等的“特性”,涉及为什么有的叙事比其他的叙事更像叙事。如果说“叙事性”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存在于“叙事”与“非叙事”之间,那么“叙事性”第二个方面的含义则存在于“叙事”与“叙事”之间[25]99-109。
在后经典语境下,修辞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为叙事性研究的主导方法。随着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兴起,我们还需要考察承载叙事讯息的媒介如何对叙事性产生影响,一方面弥补叙事学对媒介与叙事之间关系关注不足的缺憾,另一方面也丰富现有叙事学方法对叙事性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推动叙事学的发展。目前不少西方学者从跨媒介叙事角度对“叙事性”展开研究,其核心目的在于呼吁关注文学叙事(尤其是小说)之外的其他媒介的叙事,扩大叙事研究的范畴。瑞安曾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跨媒介叙事研究重点会聚焦“叙事性”,并认为“媒介研究可由此得到一个比较点,揭示个体媒介的特异资源和局限,这比单个媒介研究更有效率,而叙事学作为迄今主要关注文学虚构的事业,也可以通过思考非语言形式的叙事,得到反思其对象并焕发新生的机遇”[10]30。问题在于媒介究竟何以影响叙事性?我们不妨从麦克卢汉关于媒介的论述出发去探寻答案。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一书中,麦克卢汉说:“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讯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26]1媒介就是讯息,媒介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实际上就是因为受到媒介所传递出的讯息的影响。媒介对叙事性的影响可以主要归因为讯息对叙事性的影响。
问题在于,讯息究竟何以影响叙事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特拉维夫叙事学派的代表人物梅尔·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那里得到启发。按照斯腾伯格的理解,叙事性就是时间轴线上的故事讲述行为与阅读行为的互动,而连接二者的就是叙事讯息,即读者根据叙述者提供的叙事讯息量来产生三种普适性阅读兴趣。如果读者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那么就会在阅读轴线上产生关于过去发生了什么的“好奇”(curiosity),以及对将要发生什么的悬念(suspense);如果读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那么当他们突然接收到自己先前不知道的信息时,就会产生发生了什么的惊讶(surprise)[23]115-122。与三种阅读兴趣相关的是读者所发生的回顾(retrospection)、前瞻(prospection)和认知(recognition)三种阅读行为。笔者曾提出,关于跨媒介叙事研究视域下的叙事性研究,我们需要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1)文学叙事的“叙事性”与其他媒介的“叙事性”有何异同?(2)在利用文学叙事的“叙事性”研究方法考察跨媒介叙事的“叙事性”的同时,如何利用后者为研究前者的“叙事性”服务?(3)如何实现后经典方法(修辞、认知、女性主义等)与跨媒介的“叙事性”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4)如何研究“混合型媒介”(mixed-media)的“叙事性”?[25]99-109实际上,无论是文学叙事与其他媒介叙事之间的“叙事性”比较研究,还是其他叙事学方法和跨媒介叙事方法关于叙事性研究之间的互通与借鉴,都涉及具体媒介之于叙事讯息的传递与交流。因此,从叙事讯息传递这个角度来考察不同媒介之于叙事性的贡献和影响,应该是未来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四、从跨媒介叙事到跨媒介人物
传统的叙事学术语体系中,关于人物的界定几乎从来不涉及媒介。对此,我们不妨以几部叙事学权威参考书为例来说明。《叙事学词典》从三个方面来界定人物:(1)被赋予人的特性并从事人的行动的存在体,具有人的属性的参与者。(2)参与者,从事某种行动的存在体。(3)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体系中,它是动原(或动因)的两种特质之一,动原的另一种特质是思想(推理思维能力)[5]12-13。《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把人物界定为“故事世界的参与者,即在戏剧或叙事虚构作品中出现的任何个人或统一群体。在狭义上,该术语仅限于被叙述领域的参与者,不包括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同时,在日常使用中,‘人物’一词通常指某人的个性,即个人的持久特质和性格”[27]52-53。《剑桥叙事指南》把人物定义为“任何一个被引入在叙事虚构作品中的实体、个人或集体——正常情况下是人或类似于人”[28]。在论及人物研究的方法时,尤里·马戈林(Uri Margolin)认为所有的人物理论模式可以分为模仿型和非模仿型两大类。模仿型的人物理论将人物视为人类或类人实体,而非模仿型的人物理论将人物简化为文本语法、词汇、主题或组成单位。西方学界关于模仿型人物研究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语义研究、认知研究和交际研究[27]52-53。无论是《叙事学词典》与《剑桥叙事指南》,还是《劳特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它们关于人物的定义都没有提及叙事媒介,而它们在关于人物研究的模式与方法上,也同样没有提及叙事媒介。
是否叙事媒介对人物以及人物的塑造就毫无影响呢?答案显然不是如此。2009年首次出版的《叙事学手册》对人物的界定是“故事世界中基于文本或媒介的角色,通常是人或类似于人”[29]30。该定义第一次提到了人物也可以是“基于媒介的”(media-based)。叙事媒介何以会影响人物塑造,或更具体地说,叙事媒介如何影响读者对人物的想象与认知重构?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势必要求我们将宏观层面上对跨媒介叙事的研究转向微观层面上对跨媒介人物的研究。福尔蒂斯·雅尼迪斯(Fotis Jannidis)指出,读者在想象跨媒介人物时会依靠三种形式的知识:(1)给被视作有情众生的实体提供非常基本的结构的基本形式;(2)诸如蛇蝎美人或冷酷侦探的人物模型或类型;(3)关于人类的百科知识的基本推断,这些推断有助于了解人物塑造的过程[29]30。 实际上,从认知角度来说,这三种知识并不专属于跨媒介人物,对于文学叙事中人物也同样适用。换言之,雅尼迪斯所列的三种知识并不完全关乎媒介或跨媒介人物。
问题在于,什么是跨媒介人物?保罗·贝尔特蒂(Paolo Bertetti)认为,跨媒介人物是一个虚构的英雄,其冒险故事在不同媒介平台上被讲述,每个平台都提供了更多关于这个人物生活的细节。在一个共享的叙事世界中,不同的人物可以生活和行动,每个故事都可以聚焦于不同的人物。尽管同一人物会出现在不同文本和媒介平台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文本或平台共享同一个世界。一般来说,跨文本性和跨媒介性都对人物的地位提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对人物的身份提出了问题,因为人物身份并不总是有明确的界定[30]。贝尔特蒂特别强调的是,“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人物之间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30]。如果真像贝尔特蒂所说的,跨媒介叙事与跨媒介人物之间没有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那么跨媒介人物是如何被建构的?贝尔特蒂将目光转向了符号学,他认为,从符号学角度来看,跨媒介人物的构建有三种基本方式:(1)同一个媒介对某一个人物改造、重写、修改和转译的所有文本。(2)不同媒介对某一个人物改造、重写、修改和转译的文本。(3)与人物相关的所有文本和解释性话语(如新闻、评论、批判性研究)的副文本[30]。在笔者看来,上述三种方式与跨媒介人物最为密切相关的是第二种,该方式涉及跨越不同媒介形式的人物塑造。
近年来,国际叙事学界对跨媒介人物的关注日渐升温,成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焦点话题。其中,扬-诺尔·托恩关于跨媒介人物的研究最值得关注。托恩指出,在跨媒介叙事研究领域,人物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表现为人物是什么、人物有什么形式和人物有何功能的跨媒介视角与具体媒介视角之间的张力。无论是对人物如何在一种媒介形式中再现到人物如何在任何或所有其他媒介形式中再现的“过度概括”(overgeneralize),还是过于强调不同媒介形式和/或它们所再现的人物之间的差异而“概括不足”(undergeneralize),都是不足取的。二是许多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使用“人物”一词来指代截然不同的叙事现象,引发了一定的概念混乱[31]。托恩举例说,很多文学和电影研究领域的人物研究学者把人物界定为故事世界中基于文本或基于媒介的人;与此同时,“人物”这个术语以及诸如“詹姆斯·邦德”“蝙蝠侠”“劳拉·克劳馥”或“蜘蛛侠”等人物名字通常也用来指代更全球化的、更包容的、更异质的各类建构物,而这些建构物通常不能被理解为是在一个“逻辑上一致”的故事世界中具有意图式内在生活的单个的被再现实体[31]。为了解决概念混乱的问题,托恩提出了局部性的具体作品人物(local work-specific character)、跨媒介人物(transmedia character)、整体局部性的跨媒介人物(glocal transmedia character)以及整体跨媒介人物网络(global transmedia character network)等概念。所谓的局部性的具体作品人物指的是某个具体作品中出现的具体人物;跨媒介人物指的是通过一种以上媒介形式的不同文本得到再现的人物;整体局部性的跨媒介人物指的是通过一种媒介形式的不同文本得到再现的人物;整体跨媒介人物网络指的是通过不同媒介再现的人物融入某个统一的故事世界。比如具体作品中的人物劳拉·克劳馥不仅在电子游戏中得以再现,也在多个小说、绘本、电影和一系列粉丝小说、粉丝艺术与角色扮演等粉丝行为中得到再现。这样具体作品中的人物,尽管被不同的媒介所再现,最后都融汇成跨文本或跨媒介人物,而每个人物也随之被想象成一个处于某类故事世界中的具有意图式的内在生命的单个被再现实体。再如,蜘蛛侠原先是美国漫威公司旗下漫画中的超级英雄,后来从漫画走向电影,从最早的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到后来的彼得·帕克,到女蜘蛛侠格温·斯黛西,再到蜘猪侠彼得·波克,以及到后来的潘妮·帕克,除了最早的蜘蛛侠迈尔斯·莫拉莱斯之外,后面的蜘蛛侠都知道彼此的存在,都可以进入漫威公司所涉及的多重宇宙世界。在《蜘蛛侠:平行宇宙》(Spider-Man:IntotheSpider-Verse,2018)中,来自其他宇宙、不同版本的蜘蛛侠们纷纷来到了迈尔斯所在的世界,蜘蛛侠们集结成队,共同对抗蜘蛛侠宇宙最强反派魔伦,而这些不同的蜘蛛侠实际上也构成了整体跨媒介人物网络。托恩关于跨媒介人物研究的重点是考察那些尽管在不同媒介平台上出现,但共享同一个故事世界的人物,随着再现人物的媒介平台不断增加,最终会呈现一个跨媒介人物网络的状态。
跨媒介人物打破了经典叙事学体系中的人物塑造固化手法,聚焦不同的媒介平台如何再现同一个故事世界中的流动人物。在论及人物及其塑造方式时,施劳米什·里蒙-凯南以小说文本为基础,归纳了人物塑造的三种基本方式,即直接定义法、间接呈现法以及人物类比法[3]62-72,但是没有提及其他不同媒介平台的使用对人物塑造的影响。就媒介平台之于人物的塑造以及受众对跨媒介人物的认知与体验,我们不妨以美国小说家唐·德里罗的小说《欧米茄点》(PointOmega)为例作进一步阐释。2010年,德里罗出版了小说《欧米茄点》,作品以一位不知名的男性观众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观看苏格兰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的艺术片《24小时惊魂记》(24HourPsycho, 1993)为开端。戈登将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经典电影《惊魂记》(Psycho, 1960)以极为缓慢的速度播放,使得原本不到2个小时的电影拉长为24个小时的艺术片。小说同时讲述了电影制作人吉姆·芬利试图以美国政府对伊作战前顾问、退休学者里查德·埃尔斯特的政治经历为中心,拍摄一部电影纪录片,但拍摄因埃尔斯特女儿杰西的突然造访和离奇失踪而终止。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呈现了一个“消失女性的故事”。在《惊魂记》和《24小时惊魂记》中,消失的女性是上班女郎玛莉莲。在卷款逃跑途中,玛莉莲在贝茨旅馆被患有精神病的诺曼·贝茨杀害。如果以电影《惊魂记》的时间为切割线,在此之前,《惊魂记》中所上演的消失女性的故事以及人物玛莉莲、贝茨出现在罗伯特·阿博特·布洛赫(Robert Albert Bloch)的小说《惊魂记》(Psycho,1959)中,而布洛赫小说《惊魂记》中关于“消失女性的故事”则可以直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震惊美国的“平原镇屠夫”艾德·盖恩。盖恩承认自己在1954 年 12 月 8 日至 1957 年 11 月 16 日期间杀了2人,但实际估计有20人。1958年1月6日,盖恩被判终身囚禁于国家精神病院。在电影《惊魂记》之后,又陆续有《惊魂记2》(1983)、《惊魂记3》(1986)、《惊魂记4》(1990)拍摄上演。1990年,美国加州的好莱坞环球影城主题乐园设置了景点贝茨旅馆、贝茨大楼, 为游客提供互动式游览,后又于1995年和1998年分别被拆除。1993年,戈登推出《24小时惊魂记》,2010年,小说家德里罗将之写进小说《欧米茄点》。可以说,从平原镇屠夫的犯罪事实到虚构的“消失女性的故事”,从犯罪卷宗到新闻报道和小说,再到电影、电影续集、主题乐园的娱乐设施,在同一个故事世界(消失的女性)中,人物玛莉莲、贝茨被不同的媒介平台呈现和塑造,读者也对之有不同的体验,甚至在《欧米茄点》中不知名的男性观众在恍惚间有要和贝茨一样体验与死去的玛莉莲躯体同处一室的冲动。通常,一个媒介平台的受众并不需要了解讲述“消失女性的故事”的其他媒介平台,依然可以解读这个故事、解读人物玛莉莲与贝茨。当然,因为通过接触不同的媒介平台或接触媒介平台数量的不同,读者对人物玛莉莲与贝茨有不同的认识与体验,甚至有的体验是不可重复的。譬如,游客之前在好莱坞环球影城主题乐园可以体验贝茨旅馆、贝茨大楼,但在它们被拆除后,失去了对故事世界与人物的体验,就是一例。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瓦尔特·本雅明说:“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总是可复制的,人所制作的东西总是可被仿造的。学生们在艺术实践中进行仿制,大师们为传播他们的作品而从事复制,最终甚至还由追求赢利的第三种人造出复制品来。然而,对艺术品的机械复制较之于原来的作品还表现出一些创新。这种创新在历史进程中断断续续地被接受,且要相隔一段时间才有一些创新,但却一次比一次强烈。”[32]5在本雅明看来,尽管艺术作品在原则上是可以复制的,但绝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本雅明的这一观点在跨媒介叙事中也同样适用。在涉及多个媒介的跨媒介叙事中,一种媒介形式并不是对另一种媒介形式的简单重复,而是不同媒介形式创新了故事讲述的方式,并最终共同建构了一个整体的故事世界,形成可能的跨媒介人物网络。
结语
沃纳·沃尔夫曾论述了开展跨媒介叙事研究的诸种裨益,譬如,跨媒介方法使我们能够描述许多媒介和文类所共有的重要潜力,有助于提升我们对媒介特性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突出智人(homo sapiens)是讲故事的动物,是叙述人(a homo narran),从而带来人类学上、认知上,或许还有进化论上的新见解”[21]。在沃尔夫看来,这些裨益说明“跨媒介叙事学是一种真正有意义和有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对人文学科做出最主要贡献的方法之一,探究了什么使得我们在本质上是人类这个问题”[21]。换言之,按照沃尔夫的解释,跨媒介叙事研究能够进一步凸显人类是“讲故事的动物”,而且有助于回答人类在本质上何以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当下,跨媒介叙事研究迎来了较为蓬勃的发展势头,各种关于跨媒介叙事研究的会议、论文、专著和课题大幅增加。本文在辨析媒介盲视与跨媒介叙事研究遭遇障碍的基础上,呼吁走向具有媒介意识的叙事研究,并由此探讨了跨媒介的故事讲述以及与其相关叙事性和跨媒介人物等问题。关于未来的跨媒介叙事研究,笔者认为,还需要在跨媒介叙事进程、跨媒介聚焦、跨媒介时间、跨媒介空间等方面做更多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