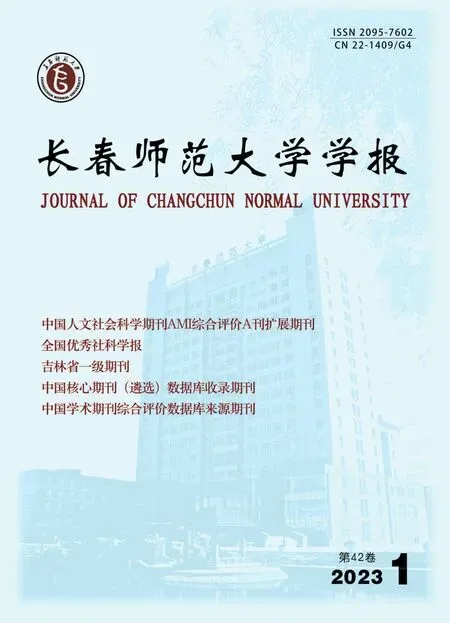《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年版)》教材图像叙事变化的意蕴
聂广壮,王立仁,2
(1.喀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喀什 844006;2.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吉林 长春 130024)
相比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8年版)教材中无图像呈现,2021年版的《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有56处图像叙事,其中“结构”图像8处、“人物”图像18处、“事物”图像30处,主要设置在“图说”和“拓展”栏目中,部分以插图形式设置在正文中。图像在章节中分配的比例较为合理,能较好地融入教材主旨,鲜明地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价值。
一、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应用趋势
(一)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现实依据
1.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图像泛化的挑战
虽然“图像时代”[1]和“图像转向”[2]被作为理论基点的社会事实还未被国内学界完全认可,但是随着科学技术解决了图片传输的速度问题、存储问题以及移动终端的便携性问题,信息图像化趋势加速发展。形象、生动、丰富的图像抓住了广大受众的眼球,瞬间将其带入叙事情节和叙事逻辑中,使图像成为人们在互联网中语言表达、信息传递、意义建构的主要方式,也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多媒体教学的重要呈现形式。与此同时,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得不面临图像泛化的应用挑战,如浏览式感官体验带来的认知零碎化问题、图像狂欢遮蔽内在理论与思想的问题以及图像中心主义视觉先行、图像至上问题等。
2.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图像叙事的经验
心理学实验发现,受教育者使用有图像的教材时接受知识更快,这为教材的图像叙事设置提供了实证支撑。对比小学至大学的思政课教材,图像叙事存在直观的变化趋势:图像在数量上由多至少;在类型上由以卡通连环画为主至以实际场景照片为主;在图文关系上由整体图文同构至模块图文同构;在意象关系上由寓意于景至寓意于形;在图问设计上由图外设问至空图设问;在图像组合类型上由教材一体式图景组合至单问题多图像类比式组合;在图像内容上由个人生活的描绘至社会生活的显现;在图像功能上从以情感、知识为重点至以价值、理论为重点。但也可以发现部分图像叙事过度重复,图像堆砌,甚至有的图像的叙事基础与受教育者的认知层次不契合。因此,图像叙事应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材一体化设计进一步联系起来。
3.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自2013年以来经常强调,要“创新对外宣传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提升思政课教材的政治性、时代性、科学性、可读性……编制中华民族古代和革命建设改革时期英雄人物、先进模范进课程教材图谱”[4]。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强调,要持续开展“教材文献资料、学术话语、表述方式、呈现形式研究,以及思政课课程与教材、教学评价之间的互动研究等,促进思政课教材的科学性、权威性与针对性、生动性有机结合。”[5]
(二)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理论依据
1.古代传统图像叙事的起源与发展
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用图像记载、表达和传播信息。图像叙事在古代以不同形态、形式存在于雕刻、绘画等载体和介质中,成为在广泛文盲与文化贫困的情况下统治者掌握的区别于口头叙事和文字叙事的传达和记录信息的手段。由于文字取代了图像的信息功能,图像的功能回归原始,即表现人“对象性本质力量的主体性”。与西方注重写实的发展进路不同,中国传统图像叙事认为“立象尽意”[6]不佳,更追求“得意忘象”。不以“穷意之象”为目的,而由“言外之象”达“象外之意”。在意象关系中,中国传统图像以“意超象外”“意余于象”为审美标准和精神诉求。中国传统的图像叙事理念不仅涉及绘画艺术领域,还在史学领域、中医学领域有所立意。
2.中国共产党图像叙事的历史实践
近代以来,图像叙事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在识字率不高的“旧中国”,为满足向工人、农民等阶层灌输无产阶级思想的需要,陈独秀等人创办的《劳动界》周刊运用生动鲜活的图画揭露了资产阶级的罪行,对启发工人奋起抗争起到了实际效果;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沪、赣、湘、粤等省总工会、农会创办的《工人画报》《农民画报》《镰刀画报》等,为革命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积累了丰富经验;延安时期,木刻版画成为当时绝佳的叙事载体,对革命斗争宣传、革命精神教育和民众启蒙起到了巨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图像叙事在重大历史事件的政治动员、群众组织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广泛运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载体进一步丰富。
3.外国图像叙事相关理论的积极借鉴
图像在西方哲学领域一直受到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埃德蒙德·胡塞尔等思想家的关注。20世纪末,W.J.T.米切尔提出“图像转向”,标志着图像研究成为当代学术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图像由西方哲学联系到心理学、文学、造型艺术以及当代的数字影像、媒体技术等,以图像为核心的理论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巨大范围。[7]242-243目前,国内图像研究现状的整体面貌可以归纳为四个基本范畴,即横向共时性比照关系的文学和艺术以及横向共时性比照关系的哲学和视觉文化。[7]262-263国外研究中较受关注的是柏拉图的模仿论和洞穴隐喻、海德格尔的“世界图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像说和胡塞尔的图像意识。
二、《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图像叙事变化
(一)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就是以传导国家意志为赋意目的,以受教育者的认识时空为领域,以视觉图形为主要载体,满足受教育者直观阅读需要的叙事方式。《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图像叙事遵循了这一内涵。
1.图像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重要载体
图像的本质是在特定的空间内凝固时间。照片中的情景单元被凝固了,即它以空间的形式保存了时间。事物在特殊时间的截取,要能体现过去的回溯和未来的延续,以构成一个能够被观者联想或想象的叙事。除了遵循客观事实的截取,人们还可以通过绘画编写事物在凝固时间内重组的单元获得叙事效果。要使图像叙事的终点达到叙事者的目的,需要对其进行提前赋意。如果一个简单的线条、图形或不存在于现实中的符号被提前赋意,在得到共识基础后,它们在凝固时间内的组合就会形成一幅抽象的画作,同样可以在共识者的脑海中形成一个叙事。依照以上逻辑,录像、电影、游戏等表现为一定时间内的图像空间延续或一定图像空间内的时间延续,是以空间形态展现情节潜势的极致情形。
2.传导国家意志是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的目的
《思想道德与法治》依照国家教育部规定编写,体现了国家对教材编写的需要,把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作为目的,分布在图像叙事的根本规定上。在这样的方向下,赋意就有了意识形态性要求,就是依据图像所含的元素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教育者作为主体,通过赋意掌握图像叙事的话语权,使图像能够持续到达叙事的预设终点。图像具有不可言说性,图像叙事可能会在其他认识下构建错误的叙事过程而适得其反。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不仅要选择赋意稳定的事物瞬间,还要通过不断阐发和诠释达到对赋意的稳定追加,使受教育者默认图像叙事的自叙路径,达到图像叙事的教育目的。
3.受教育者的认识时空是图像叙事的领域
如果受教育者对图像元素的正确赋意不明晰,或缺乏认识的知识基础,那么在其认识时空中就只能把图像作为一个短暂的截片看待。受教育者认识的构建来源于对真实历史的总体反映,因此教育者对图像的赋意应穿插图像中元素所处的历史背景。叙事者的成功在于对历史的把握和诉说的艺术。因此,帮助受教育者梳理历史是使其形成认识时空的前提。另外,受教育者认识的构建来源于模型化思维。一般来说,并列关系表达为平行线,相互作用表达为双箭头线条,集合间的关系表现为几何图形在同一平面内的透明叠加。图像叙事能够满足对文本描绘事物的抽象化或具象化,需要受教育者利用一般的赋意规则使图像叙事与文本叙事相互转化。因此,教育者需要在受教育者的认识时空中构建出历史与逻辑、联想与推理的综合能力。
(二)《思想道德与法治》图像叙事的特点
1.“二维码”链接文本信息
受限于教材的载体是纸张印刷本,图像叙事的类型主要是二维图像,然而《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设置的“二维码”打破了这种绝对体量的限制。受教育者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实现超级链接的跳转,开辟了虚拟的“第二课堂”窗口,达到了教材结构主次分明和补充重点内容的效果,顺应了“图像世界”的信息化趋势,这是功能图像作为认识工具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中运用的一次飞跃性尝试。虽然教材中“二维码”的设置不多,链接的内容多为文献资料,但是这一尝试为未来丰富应用“二维码”提供了丰富图像维度的设想空间。
2.多种图像叙事方式相结合
单一图像叙事以最富孕育性的顷刻为内容,是在动作完成前最耐人寻味的定格。例如第121页,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陪住院老人欣赏美丽的夕阳。综合图像叙事是把不同时间点的单一场景或其中的图像元素并列或并置于同一逻辑下,形成超越时空的串联,起到对比或类比效果。例如第104页,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和第一辆火星车祝融号在毛泽东“更富更强”“共富共强”的回音中得到串联与对话。另外,图形元素组合成的结构系统,其图像叙事的功能随着系统的复杂而减弱,在功能上趋向于思维导图,例如第6页“速览‘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3.图文并茂的图像叙事关系
“置图于左、置书于右”[8]讲求“索像于图”“索理于书”。图文并茂不仅表现为平行式设置,还在于综合图像叙事中内部系统的图文并茂。图文并茂实际上是由“图”出发至“像”与在文本叙事中由“书”出发至“像”的结果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下把“书”抽象出的“理”对应“像”的复合过程。图文关系中的“文”是关联结构、赋意目的和唤醒社会记忆的关键,使叙事的“图像”和图像的“叙事”在两个维度上相得益彰。
4.以“见证者”的实际叙事
教材中的图像叙事多包含鲜明而真实的人或事物,而非意识流的纯思展现,使得赋意空间具有明确的指向。观者以“见证者”[9]的视角向内将自我代入为叙事主体,向外联通社会记忆,在联想、想象和情感中构建出“叙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10]可见图像叙事的前提和基础都是从实际出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以实践为基础,突出图像叙事的真实性、准确性,鲜明脱离虚构性,趋向历史性。叙事以连接叙事世界和读者所处真实世界为意义。
三、《思想道德与法治》图像叙事的功能意蕴
(一)思想性与趣味性相结合的阅读功能
图像叙事作为教材结构内容的一部分,具有知识性的基本属性。但在《思想道德与法治》教材中,有些图像已在较低层次的教材中重复出现,知识性这一功能意蕴便退为次要,而思想性成为图像的灵魂。另外,图像作为一种活泼的可以创造的表现艺术,具有趣味性。图像叙事的趣味性就如钻石的切面一样,使其自身材质的精纯得以引人注意。趣味性体现在卡通人物的呈现中,如《思想道德与法治》中关于“路怒症”的叙事,使用了两个拟人化汽车表达出司机的愤怒表现,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再如“疫情常态化防控”的叙事中,“就地过年”和“保持距离”的卡通人物生动地表现了这些内容。
思想性和趣味性综合表现为阅读功能。教材中图像叙事的首要功能在于满足受教育者阅读的需要,而受教育者认识理论,需要形象化的思想性表达和有益于理解其思想性的趣味设计。得益于图像引人注意的设计,图像作为教材中被首先记忆的内容,发挥着坐标定位的作用,有利于快速检索以再次阅读。因此,图像叙事有利于满足受教育者对教材工具性检索和持续性阅读的需要。
(二)具象性与抽象性相结合的认识功能
图像叙事的具象性和抽象性是相对于不同对象而言的认识方向。图像之于具体事物,是对事物单方面的静态描摹并在思维层面约等于事物的过程,是对事物外现形态的二维“撵平”;图像之于理论文本,则是在文字略简处的具体描绘,是以文本内容为“点”连接成形的过程。一方面,认识主体运用各角度图像叙事的描摹,获得复印事物的二维“撵平”,为指导实践做准备;另一方面,通过图像的推演,获得事物的物理运动规律,最终抽象为理论文本。例如第96页,通过“奋进者”号潜水艇的图像叙事,可以具象化认识“支撑创新战略”。图像是事物抽象化为理论和理论具象化为事物的中介。
具象性与抽象性综合表现为认识功能,即教学中的中介作用。图像叙事的抽象性和具象性缓解了具体事物与理论文本在表达中的功能断层,能够迎合受教育者学习理论“展维”的需要,也能满足其“坍维”的需要。“展维”是通过展现直观的图形组合展开理论原点包含的核心逻辑关系的表达倾向;“坍维”是对具体事物仅从所要研究的维度入手加以认识,是利用直观的图形组合表达本质、规律等范畴的倾向。教材图像叙事的两个表达倾向有利于教材内容被有效吸收。
(三)典型性与暗喻性相结合的教化功能
图像既具有能够引起强烈注意的典型形象,又具有潜移默化的暗喻作用,即显性与隐性在工具目的性上的统一。恩格斯指出:“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11]塑造典型形象就是依托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实践,将突出的精神品质凝结在先进人物上。接着将典型形象延展于受教育者的生活实践中,拉近叙事内容与受教育者的距离,使其在自省中自觉。教材注重人物和事件的历史印记,以小见大地运用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例如第155页,以1943年周恩来过生日的事情突出周恩来在革命年代修身自律、保持节操的形象,暗喻受教育者要在生活中自律自省的现实要求。
典型性与暗喻性综合表现为教化功能。教化功能即教人“党性”,化人“遮蔽”。“党性”是思想政治教育中阶级性、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统一。[12]通过典型的图像叙事,回归“政治人”的要求,培养受教育者的“党性”自觉。教材的图像叙事中,人物、事物多与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不谋而合,蕴含了“党性”的价值规定性。“遮蔽”是经验感知中无法抗拒的限制思想的“知识”,教材注重对此解蔽。如第124页,图像叙事解蔽了美国种族问题下“普世价值”的虚伪性。
(四)价值性与引导性相结合的传导功能
图像叙事作为认识具体事物和理论文本的中介,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价值,同时这种价值规定于图像,表现为“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的教育价值。价值性不仅体现在受教育者的自身需要方面,还体现在教材建设目标规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在实践中,价值性表现为一种引导力,即引导教育者朝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应然方向发展,引导“思想道德与法治”课朝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应然方向发展。图像叙事具有突出的引导性,例如教材第27页,时传祥以身为掏粪工为荣,以苦为乐,任劳任怨,蕴含“爱国”“敬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受教育者具有引导作用,也引导了“思想道德与法治”课在此要注重对奉献精神的阐释。
价值性与引导性综合表现为传导功能,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强调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道德与法治》的图像叙事传导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等内容,不仅强调意识形态性内容,还强调属于从属地位的道德规范等,从而达到全面提高受教育者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
四、应用《思想道德与法治》图像叙事的路径
(一)教育者结合教材主导图像叙事的赋意空间
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体现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这门课的图像叙事中,就是要把握图像赋意过程中的话语权,即主导图像叙事的赋意空间。在不同的解读视角下,图像所表达的内容会有不同的结果;同时,对图像的过分关注会削弱教育的目的性。要使受教育者固化对图像的认识,需要教育者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保证赋意空间在可控范围内。可控来源于教育者对历史背景的提前铺垫和图像信息的深度挖掘,教育者对图像的充分认识是应用图像叙事的前提。教育者对图像的赋意过程也是对受教育者先在结构的唤起过程,这种唤起依托事实和实践。
主导赋意空间并不意味着死守教材,但也不意味着可以违背国家意志,而是发挥好故事旁白及时出现的重要作用和放风筝者及时松线和紧线的掌控艺术。首先,可以围绕教材中的人物图像选择利于对其补充叙事的图像,这有利于受教育者通过自主联想和想象构建起故事的样貌。其次,围绕人物的生活环境、历史环境、政治环境等完成对人物的叙事。既要满足受教育者“成为人”的需要,又要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的需要,所以最终落脚点是人。例如教材中“中国天眼”的图像是一个全景的鸟瞰图,教育者可以对文本叙事中的“总工程师南仁东”进行额外的图像叙事补充。再次,主导赋意空间不意味着只补充当前时代的图像。正如教材第104页,通过党带领国家发展进步的前后对比,获得事实上的直观。最后,可以与国际对比。例如第121页揭示了“生命至上”主题,而第124页揭示了美国黑人白人谁的命才是命的种族冲突,中国制度的优势不言而喻。
(二)教育者结合教材传导图像叙事的精神实质
“叙事艺术的实质既存在于讲述者与故事的关系之中,也存在于讲述者与读者之间的那种关系当中。”[9]240首先,受教育者具有基本趋利避害的生物倾向,这被德国动物学家和哲学家恩斯特·海克尔称为“向性”(Tropism),强调了人的认识在感性认识阶段的最初反应,并且表现为喜与厌的基本情感倾向,由此作为文明发展的动力和精神生产的源泉。情感是受教育者自觉进入图像叙事的起因,教育者运用图像叙事时需要注意对这种“向性”的把握。其次,图像叙事本身是无声的、静默的,需要教育者通过言语、表情、动作等传达更丰富的情感,点燃自己的激情,照亮图像叙事的内容。这样,图像叙事中的情、教育者的情和受教育者的情在感染的讲解中达到统一。最后,情感的互联并不是最终的目的,教育者还需要在此氛围下传导出精神实质,使受教育者的情感与图像叙事的精神内容进行串联,帮助受教育者建立共鸣的基础。
实现共鸣还只是传导精神实质的一种准备,当受教育者的感性认识充盈时,便会扩大对理性认识的需要,为产生认识过程的飞跃做准备。理性认识的对象是图像叙事的内容主旨,图像叙事所指的主旨与其所在章节的主题扣合,与其所在的临近文本的主旨契合。“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目的,主要是讲授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治观,帮助学生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弘扬中国精神,尊重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5]教育者需要对图像中的国家意志加以准确点明。
(三)教育者结合教材引导图像叙事的创造方向
从教材的图像叙事可以看出,图像的审美反应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教育者在进行图像叙事的过程中,应注意把握图像艺术审美的美学解读,消解、扭正受教育者由于片面认同、虚无认同而产生的审美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图像叙事是“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审美教育的衔接契机。这要求教育者必须提升自身的审美素养,更好地通过图像叙事的美育过程渗透人格教育、情感教育等内容。教育者应该注意到受教育者具有自觉赋意的主观能动性,受教育者有一种表达的需求,即受教育者具有对图像叙事二次创造的需求,表现为娱乐化、情感化、生活化。受教育者通过想象、记忆、抽象、联想等步骤,赋予被改造的图像叙述其自身主体性的片段,以获得某种关注。教育者可以利用这种需求,调整教学过程中对图像赋意的重点,引导其创造的方向与教育目标相适应,将一般兴趣引起的涂鸦创作引向感人心魄的艺术创作。
正向的创造来源于对图像叙事内容的认同,即自觉将图像叙事设置在国家意志的方向上。如网名为“乌合麒麟”的付昱,他创作的《致莫里森》、Blood Cotton Initiative、《披甲》等具有多层解读的深意,表达了最直接的态度和思想。这引起了青年人对国外污蔑者反击过程中图像叙事的表达自觉,这是与以往朴素的爱国行为所不同的方式。他的图像创作为教育者在“思想道德与法治”课程中引导受教育者创作图像叙事提供了现实的经验。
五、结语
《思想道德与法治》图形叙事的变化,体现了守正创新的现实意蕴,既有利于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也有利于表述方式和呈现形式的创新,实现了科学性、权威性与针对性、生动性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