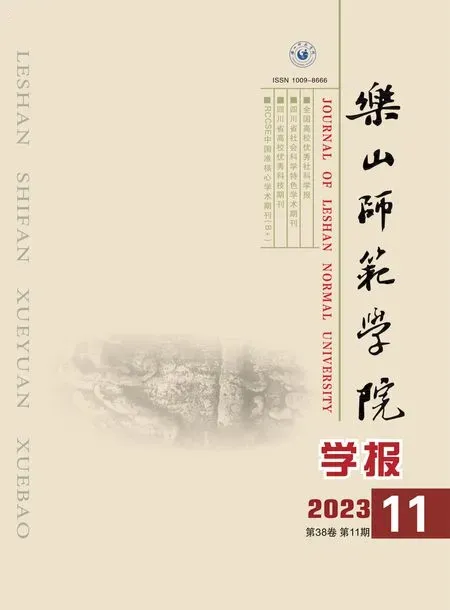僧人·诗人·山水:论帛道猷的山水诗
李 杰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徐汇 200234)
中国诗歌中的山水描写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但是“《诗经》中的溱洧……都是用自然山水景物作为其他题旨(历史事件、人类活动行为)的背景;山水景物在这些诗中只居次要的位置,是一种衬托作用”[1]84,因此有山水描写并不代表就是山水诗。刘勰《文心雕龙》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2]61即认为山水诗兴起于刘宋时期,今人亦常将谢灵运视作山水诗的“鼻祖”[3]。其实不然,钱锺书指出山水诗“则附庸蔚为大国,殆在东晋乎”[4]1036-1037,东晋时期庾阐、李颙、湛方生等人已经在纪行诗中有意识地进行山水描写[5]302-304。在众多写山水的诗人中,诗僧帛道猷的一枝独秀,创作出了纯粹以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诗歌,这在山水诗发展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当今文学史著作鲜有提及帛道猷其人其诗,究其原因有二:第一,东晋高僧辈出且诗才横溢,帛道猷的光芒被支遁、慧远等名僧所遮盖;第二,我们对僧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没有足够重视,如高华平在《论两晋佛教僧侣的文学创作》所言“佛教僧侣创作在中国山水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有所忽视”[6]54,人们习惯性把东晋时期的僧人之作归结为玄言诗或佛理诗,较少关注到僧人的山水诗创作。目前只有少数研究六朝佛教文学或山水文学的学者注意到了帛道猷在山水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如:钟涛在《名僧与东晋文学》中认为,帛道猷的山水诗“为玄言诗向山水诗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7]171;袁济喜等认为帛道猷“体味山水田园完全取代了体味仙心玄理”[8]155。而王伟萍甚至觉得“后人把改变山水在诗中的地位、创作真正意义山水诗的第一人归于谢灵运,其实这个第一人当属帛道猷”[9]50-55。但他们未深入分析道猷能够创作成功的原因以及在诗学发展史上具体的贡献。鉴于此,故笔者不揣谫陋,就其诗歌的相关问题展开论述,以就教于博雅之家。
一、玄言笼罩下山水诗的雏形
帛道猷是会稽山阴人,本姓冯,“学于帛尸黎密”[10]73,所以改姓“帛”,今人考证其约329—399 年在世[11]38。他“少以篇牍著称”[12]207擅长写作,并且“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12]207情逸高雅。《高僧传》载帛道猷欲邀请好友竺道壹从虎丘山来若耶山游玩,于是写信称:“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痾,乐有余也。但不与足下同日,以此为恨耳。”[12]207并于信中附诗一首:
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榛。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步践其径,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12]207
竺道壹收到帛道猷的信后“有契心抱,乃东适耶溪,与道猷相会,定于林下。”[12]207当时竺道壹是“闲居幽阜,晦影穷谷”[12]207,在虎丘山过着隐居生活,之所以能够把他吸引出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帛道猷抓住了竺道壹热爱山水的性格,其信中之诗把若耶山之美给描绘出来了。
该诗分为三部分。前四句写景:山峰起伏,连绵数千里;山下溪流,缓缓从茂林修竹中流出;云朵飘过,远处一篇朦胧;清风穿林,榛树簌簌作响。将远景(峰)、近景(榛)、高景(云)、低景(津)立体式地展现出来,塑造出清幽空僻的环境,给人一种“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13]172之感。紧接着作者后四句由景转向写人,沿着小路悠悠前行,虽然一个人也没有,但是通过几声鸡鸣以及路边被遗漏的柴草,故而知道深山密林中有人居住。其中“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写得极有趣味,一声鸡鸣让诗人恍然大悟,原来丛林深处有人家!从“隐不见”到“知有人”,画面由静而动,由寂静而有声,蕴含着作者从未知到惊喜的心理变化,一抑一扬,耐人咀嚼,陈祚明赞此二句“境地佳”[14]448。处在此山此景中,作者不由感慨,这就是上古先民的生活方式啊!其悠闲、淡泊、与世无争的心境呼之欲出。该诗在流传过程中似有损益,后世方志中还有“开此无事迹,以待疎俗宾。长啸自林际,归此保天真”[15]194四句,但依旧是承接前文而抒情之句。全诗结构凝练,从景到人最后抒情,一气呵成。写景细致,远景(峰)、近景(榛)、高景(云)、低景(津)兼容并包;写人手法高超,通过鸡鸣、遗薪间接点明深山有人家;抒情得当,末尾虽有议论但只是情感、思想的升华,并未深入探讨哲理,令人回味无穷。全诗语言简洁而清秀,如钟嵘所言“有清句”[16]560。
檀道鸾《续晋阳秋》载东晋诗坛“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13]310。文坛在孙绰、许询的影响下,在诗作中写符合道家哲理的内容,诗坛处在玄风笼罩之下,虽然有人想改变这种局面,但是“彼众我寡,未能动俗”[16]34。而帛道猷在这样氛围下,创作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诗歌,实属可贵,并且这是比较纯粹的山水诗,对比同时代诗人作品,我们就能更真切认识到帛道猷这首诗在山水诗发展史上的意义。
清代沈德潜多次言及支遁对山水诗的开创之功,“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17]3212,“支公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18]261-262。但其实支遁山水诗“往往铺排玄佛,枯燥无味,写景也多堆砌雕饰之语”[19]66,以其山水代表作《咏怀诗五首》中第三首为例:
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髣髴岩阶仰。泠风洒兰林,管濑奏清响。霄崖育灵蔼,神疎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隗隗形崖颓,冏冏神宇敞。宛转元造化,缥瞥邻人象。愿投若人踪,高步振策杖。[20]74
该诗前六句以景起兴,春天清晨的阳光洒落在园圃中,引发了诗人对岁月流逝的感叹,于是激发了作者登山咏怀的冲动。中间八句写山中景象,有泠风、兰林、悬崖、溪流、兰芝、石室高人等。末八句则叙述石室高人通过修炼摆脱尘世羁绊,并且诗人也愿意像他一样归隐石洞领悟真理。全诗虽然有山林景色,但是作者的立意并非为了欣赏美景,而是要引出山林中居住着的道高人,从而表达寻化出世的佛教思想。诗中夹杂着诸多佛教、玄学语如“寻化”“外身”“无想”“抱朴”等,大段大段地阐发玄理,描写景物的笔调也显得玄涩呆滞而看不出生机,因此这首诗依旧是体悟哲理的玄言诗。
另一位被范文澜先生称作山水诗先驱的庾阐[21]92,其存世的山水作品存在虚构山川景色的情况,如其代表作之一《三月三日诗》:“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悠想盻长川,轻澜渺如带。“[22]873从“心结川流”“目散霄外”“悠想长川”中“结”“散”“散”等词可见作者是在“寄意无极,游心太玄”,是在玄思而并非身临其境;诗中的清泉、素濑、轻澜等景物也只是想象中的情境,作者没有前往实地查看,并且“写景概括、含蓄、不尚刻画,不加藻饰,几乎只是平面的略加点染”[23]141。和帛道猷同时或稍后,被称作“始革孙、许之风”[24]1778、谢灵运先导的殷仲文,他的山水诗《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也用绝大部分篇幅讨论玄理,诗中仅有的“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夹籁惊幽律,哀壑叩虚牝。”[22]933-934就显得无关紧要,其诗歌“玄气犹不尽除”[25]908,依旧只是借景物来表达哲理。
帛道猷去世后不久,谢灵运便以“景情理”模式[26]53大规模地创作山水诗歌,从此山水诗“开辟了体物的新时代”[27]233,也奠定了山水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帛道猷脱离玄言气息“景情”结合的山水诗可以说已经是走在时代前列,是山水诗的雏形之作。
二、帛道猷创作山水诗成功的原因
帛道猷作为僧人而创作出以山水作为独立审美对象的作品,这和东晋时期般若学的兴盛以及他超脱尘俗态度有关。
两晋时期《般若经》大行于世。“般若”意译为“智慧”,是大乘“六度”之一,可通过修得智慧抵达涅槃彼岸,而这一“智慧”的内容就是对世界本质“空”的认识,因此吕澂先生认为般若“就其客观方面说是性空,就其主观方面说是大智(能洞照性空之理的智慧),把主观客观两方面联系起来构成一种看法,谓之‘空观’”[28]46。僧人作为方外之士“摆脱世俗的烦恼、捆绑而实践空观最好的途径和环境就是置身山水胜景中”[29]51,因此当时治般若学的僧人“对自然山水情有独钟”[30]131。《世说新语》载竺道壹有一次在雪天回东山,他人问及路上见闻,竺道壹说:“风霜固所不论,乃先集其惨淡。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13]173他不顾旅途疲劳、风雪寒冷也要欣赏沿途“林岫皓然”之景色,可见对山水美景之钟爱。
帛道猷处在般若学盛行的年代,他的好友竺道壹即般若学“六家七宗”之幻化宗的代表人物,在大时代背景熏陶以及周边好友的感染下,他自当受到般若学的影响,会通过山水来体悟佛家真理,《高僧传》即载帛道猷“好丘壑”[12]207。般若学主张“诸法性空”“无我”,即世界上一切事物现象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因缘而生,没有独立的自性,在这样的观念下,僧人能够平等对待世间一切,因此在欣赏山水时不会把自我因素强加于外物,而是能够把山水当作纯粹的个体看待。帛道猷长期在山林中畅游,对一草一木有着独特的情感。为了成功把好友邀请来同游山水,他创作出纯粹以山水为欣赏对象的作品也并不奇怪。而他能够迥异于其他诗人,在诗中不谈佛理、玄言而纯粹写山水,则和其超脱尘俗的生活态度有关。
经过汉、魏、西晋三代的发展,佛教逐渐壮大,但是这个时候的佛教往往附庸于中国传统文化如道家、阴阳家等以求生存。到了东晋后,佛教已经逐渐摆脱附庸地位,开始走向回归本教教义,佛教徒往往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弘扬佛教扩大本教的影响力,故而写诗往往带有功利性,这样在写山水作品时便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宣扬、体悟佛理之路;并且与帛道猷同时代的玄学家、佛教徒所讨论的问题“仍然落实在现实人生的道德准则上”[29]51,因此他们并未真正进入山水的世界。
帛道猷则不然。他给竺道壹的信中称自己“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药,服饵蠲痾,乐有余也”。可知他喜爱在山林中优游度日,与山水亲近而非世俗世界;虽然是僧人,但是也爱读儒家经典,说明他思想豁达,并未受缚于自己的身份。在山林之中攀岩采药养生,意味着他如隐士般生活,未被世俗所羁绊。在这种生活下,他触兴为诗,是以随心随性地态度创作,并无功利性,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审美层面,才能把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从而创作出纯粹的山水诗。
三、帛道猷山水诗的意义
(一)从“体道”走向“体物”的先驱
东晋时期文坛主流倾向是以“体道”为美,刘宋之后南朝诗歌以“体物”为美[27]8-14,而帛道猷则是文坛审美从体道转向体物的先驱人物。
西晋太康时期把诗歌推向了缘情绮靡的高峰[23]103,诗歌片面追求语言、形式的华美而内容苍白之弊端日益明显,这就促使人们转变审美观,重新为诗歌发展寻找出路。两晋之交玄学、佛学兴盛,东晋时期诗人们便以体悟玄理为要务,文人们“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单乎此”[24]1778,当时诗人们的兴趣是创作“体道”的玄言诗。但是玄言诗把诗歌引入了另一个极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16]28,诗歌纯粹说理显得干巴巴而毫无韵味。东晋诗坛已经有诗人逐渐把笔端转向大自然,如前文所说支遁、殷仲文等诗人,不过他们对自然的描写仍然受制于时代,诗句中的山水景色很大程度还是为了体悟玄理。直到刘宋以后,谢灵运开始大规模地创作山水诗,虽然袁行霈称谢灵运山水诗“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31]107,但是这个时候玄言已经是服务于山水,属于情感的升华,诗歌中山水是主要部分,玄言属于次要部分,自此扭转了人们以哲理为题材的审美,诗人的目光转向世俗世界,此后山水、器物、亭台楼阁、美女等成为了诗歌的题材,南朝诗坛主流以“体物”为主。
帛道猷处在东晋后期,虽然也受玄学、佛学影响,但他能够创作出不含玄言、佛理气息的山水诗,可谓是诗风从“体道”转向“体物”的先驱。之后谢灵运大规模创作山水诗,奠定了山水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帛道猷当是山水诗发展链上重要的一环。
(二)“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的典范意义
帛道猷诗中“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两句尤为人称颂,陈祚明称“境地佳”,王澧华教授赞其“神来之笔”[32]。唐朝人甚至因此直接将帛道猷诗截取四句“连峰数千里,修林带平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33]1863重新组成一首诗,明代杨慎称:“此四句古今绝唱也。”[34]90
诗人这种由声音推知本体的写作方法被后人广泛借鉴,甚至还引发一出争论。陈岩肖《庚溪诗话》云:
秦少游诗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僧道潜号参寥,有云:“隔林髣髴闻机杼,知有人家在翠微。”其源乃出于道猷,而更加锻炼,亦可谓善夺胎者也。[35]176
认为秦观、道潜诗句都是学于帛道猷,并且觉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代诗评家亦赞同秦观、道潜此二句源自道猷,但不认可陈岩肖的鉴赏水平。杨慎说:“庚溪作诗话,谓少游、道潜比道猷尤为精练。所谓‘苏粪壤以充帏,谓申椒其不芳’也。”[35]90“苏粪壤以充帏,谓申椒其不芳”出自《离骚》,意为“把大粪装入香囊中佩戴,还说大椒这种香木不香”,用来比喻是非颠倒、善恶不分,很显然是尖锐地否定陈岩肖的鉴赏水准,觉得秦观、道潜的模拟句比不上道猷原句。之后焦竑也认为读了秦少游和参寥的诗句“益见道猷之工,学者知二诗不如道猷,可与言诗矣”[36]161。
我们暂且不讨论帛道猷原玉好,还是秦观、道潜拟作好,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帛道猷这种写作方式引起了其他作家的模仿,具有一种典范意义,如沈佺期《入少密溪》“树密不言通鸟道,鸡鸣始觉有人家”[37]1027,刘威《游东湖黄处士园林》“遥知杨柳是门处,似隔芙蓉无路通”[37]6525,朱湾《隐者韦九山人于东溪草堂》“初行竹里唯通马,直到花间始见人”[37]3478等都可以看到帛道猷的影子。
四、余论
帛道猷在玄言笼罩下的东晋诗坛创作出了纯粹以山水为审美对象的山水诗,在山水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创作的成功和般若学以及自身超脱尘俗的态度有关。其诗歌体现了诗学从“体道”向“体物”的转变,其诗句“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成为后世模仿的典范。
帛道猷其诗其人得到后人认可。梁代钟嵘《诗品》将帛道猷列入下品,明代王士祯则认为“下品之……帛道猷……宜在中品”[38]4800。其实无论是在下品还是中品,都体现出帛道猷诗歌被后人赞赏。《诗品》共品评了自汉代至梁代123位优秀诗人[39]99,帛道猷能赫然在列,其才华可见一斑;《诗品》共品评了3 位僧人——汤惠休、帛道猷、释宝月,六朝有诗才的僧人很多,如支遁、释慧远、释宝志、释法云等,但是这些僧人都未能被钟嵘赏识,可见帛道猷的才华在僧人当中为出类拔萃者。后世不断有人情系道猷,宋代释德洪《追和帛道猷一首》言:“永怀山阴老,漱流味馀津。幽寻见兰丛,苍然出荆榛。”[40]82清代屈大均《代同公答蒲公》称:“采药凌峰不觉遥,耶溪频负道猷招。”[41]246其悠游山林、陵峰采药成为后代佳话,帛道猷可谓历千古而闻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