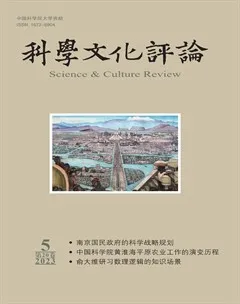从自然静观到技艺操控炼金术汞硫理论对矿物观念的重塑
严弼宸
一 从散发物理论到汞硫理论
亚里士多德在《气象学》(Meteorologica)第三卷末尾,用干湿两种散发物(exhalation)解释了地下矿石与金属的成因[1]。这两种散发物产自太阳对地表的热作用,它们在《气象学》前三卷中被用于解释流星、彗星、银河、雨雪霜露、风云雷电、地震彩虹等月下界诸气象现象的成因[2]。通过统一融贯的散发物理论,矿物的生成与月下界其他诸多气象现象一起被编织进通天彻地的自然阶梯之中,成为亚氏自然哲学的一部分[3]。这种自然哲学式的矿物成因理论,在后世却演化出另一种对矿物的理解。它被称为“汞硫理论”(Mercury-Sulfur Theory),在千余年里始终被视为炼金术的理论基础。
汞硫理论的基本主张很容易和亚氏的散发物成矿理论建立起关联。在亚氏的理论中,干性与湿性两种散发物在地下封闭的环境中混合形成金属。亚氏还通过表明金因不含干性散发物从而不受火的影响,暗示了两种散发物的比例决定不同金属的性质。因而一种流行观点就将亚氏的散发物理论视为汞硫理论的源头,汞本原被视为类似于亚氏的湿性散发物,硫本原则对应于干性散发物([4],页49;[5],页24;[6])。
但这种简单类比忽略了两种理论之间的差异。一个明显区别在于,汞硫理论中的二本原,通常作为金属的质料被理解,而散发物既是矿石和金属的质料因,同时也是成矿过程的效力因[1]。约翰·诺里斯(John Norris)注意到这一区别,修正了散发物理论是汞硫理论直接基础这一传统观点。他认为汞硫理论旨在建立一种使汞和硫在不同条件下达到质料平衡的理论机制,以解释不同金属的具体成分;而散发物理论仅仅提出了一种对矿物自然生成的一般性设想,实际上未能对不同金属的成分差异做出任何具体解释[6]。
但除此之外,这两种理解矿物成因的不同方式背后还存在着更根本的差异。汞硫理论之所以要建立质料平衡的理论机制,是因为它预设金属种类取决于形成过程中的成分。因此通过改变成分就有可能实现金属种类的嬗变,这一步不仅发生在自然中,也应能被人工技艺所完成。这样一来,汞硫理论不仅解释了矿物的自然生成,还支持了人工嬗变这一炼金术的基本理想。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散发物理论仅仅提供了一种解释月下界自然现象发生原因的架构,亚氏并未做出技艺能够依照自然原因复制自然的承诺,它始终处于自然哲学静观的位置上。技艺与自然的张力,是理解汞硫理论与散发物理论之根本差异的关键。
本文考察了阿拉伯炼金术传统如何利用汞硫理论来超越自然哲学静观,从而为炼金术实践提供支持;伊本·西那(Ibn-Sinā,约980—1037)又如何通过强调矿物成因中不可被技艺模仿的自然原则,否认了炼金术的可能性。伊本·西那的诘难在13世纪引发了一场关于炼金术的辩论,科学史家纽曼(William Newman)的研究表明这场辩论为弥合自然与技艺的鸿沟提供了可能[7,8]。以此为背景,本文考察辩论各方如何通过阐发以汞硫理论为基础的矿物成因理论,对炼金术进行批判或辩护。这些考察表明,经由汞硫理论这样一种对矿物生成的理解框架,矿物成因与人工技艺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矿物最终从亚氏自然哲学传统中的自然自在之物,转变为可被人工技艺操控的物质对象。
二 阿拉伯炼金术中的技艺操控
在阿拉伯炼金术传统中,贾比尔最先给出了一套对汞硫理论的完整表述,它能够解释金属的生成过程并指导炼金术的具体实践([4],页50)。他认为金属的自然生成就是硫作为主动本原与预先存在的汞的结合。硫本原具有灵活的运动能力,能够解释金属在地下的广泛分布;又具有物质成分的可变性,能够解释地下金属成分的多样性。金属的区别仅在于偶然性质,而后者最终仅仅取决于硫的形态及其受热程度。这意味着金属间的转化,在理论上并不存在什么人力难以跨越的阻碍,通过人工技艺调节硫的形态及其受热程度就有可能实现金属嬗变。
为了在炼金术实践中实现这一可能性,贾比尔又提出一种炼金药理论([4],页52—57)。他改造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将原本仅仅是抽象本原的火、气、水、土四元素,乃至无法脱离实体单独存在的冷、热、干、湿四性质,全部看成可以单独分离并具体存在的物质。通过反复加热、蒸馏等人工技艺,贾比尔认为能够从任何物质中分离出单纯的四元素,并进一步获得单纯拥有某一种性质的质料。按比例重新调配这些单性质的质料,就能获得具有任意性质的炼金药。既然金属的种类取决于硫的形态,而硫被视为干、热性质的结合,那么从根本上而言,向任意金属中添加比例适当的炼金药,便能调整金属的性质比例从而实现嬗变。
在炼金药理论的配合之下,贾比尔使汞硫理论从一种为金属自然生成过程提供解释的矿物成因理论,转变为炼金术实践所能依据的技艺操作原则。这种在自然哲学中植入技艺操控理想的思想倾向,对整个阿拉伯炼金术传统产生了巨大影响。10世纪的波斯医生、炼金术士拉齐(Abu Bakr Muhammad ibn Zakariya al-Razi,约865—923)所代表的实验炼金术便是这一影响下应运而生的高峰。
拉齐的炼金术作品直到17世纪都属权威教科书之列([4],页65)。他的代表作《秘密之书》(Kitabal-Asrar)被视为现存最早的实验室手册,介绍了自然物的分类、各类操作所需设备以及一系列炼金术操作程序和规范[9,10]。《秘密之书》对矿物的分类以及一些具体的工艺操作表明,汞硫理论是实验炼金术的基础。拉齐分类中最基本的矿物是汞、卤砂、硫、硫化砷这四种精气(Spirits),汞与卤砂代表不可燃的本原,硫与硫化砷代表可燃的本原。提纯四种精气的操作是各类工艺操作的基础,因为纯净的精气是后续各种制金工艺所必需的物质[10]。由此可见,汞和硫被视为构成其他矿物的本原。他的另一作品《论矾与盐》(Dealuminibusetsalibus)更确切地表明,矿物是蒸气在自然长时间的运作下被浓缩和凝结而成的,汞和硫是这些蒸气中首先被凝结的物质,二者就是矿物的起源[11]。
拉齐的汞硫理论与贾比尔有诸多不同。贾比尔认为,只有硫是决定金属性质的主动性本原,而拉齐却使硫和汞在形成矿物的过程中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它们从蒸气凝结成液态的水性物质和油性物质,并在尚未凝固时发生混合,然后固化成原始矿物。此外,在贾比尔的理论中,金属的转变是通过预先调节硫的形态、比例以及受热程度而实现的。但拉齐却将调节的过程放置在汞和硫结合形成原始矿物以后——汞和硫在适度混合并凝结成矿物后,在漫长的时间中受自然的逐渐调节,最终转变为贵金属[11]。
这些区别决定了拉齐炼金术实践的特点:炼金术士必须通过人工技艺缩短金银自然形成所需的时间,并且这种技艺必须对汞和硫都施加影响。纽曼的一项研究指出,拉齐在这里所说的“汞”和“硫”,并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本原,也不是贾比尔所寻找的纯粹属性的承担者,而是现实存在的含有杂质的矿物,是有待被炼金术士提纯的普通材料[11]。正因成矿过程中的汞和硫并不纯净,自然才需耗费漫长的时间,将含有杂质的原始矿物孕育成完美的金。拉齐认为自然状态下带有金属光泽的液态汞含有过多水性,而真正纯净的“最好的汞一定是白色且柔软的”([12],section1,part2,1.8);同样,自然状态下粘腻且可燃的硫磺,也被视为含有过多的油性,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净化。《论矾与盐》介绍了一系列净化普通汞的方法,《秘密之书》总结了净化的原则:提纯汞所要做的是祛除其水性,提纯硫所要做的则是祛除其油性和可燃性([12],section3,part1,A.3)。只有经过人工技艺的净化,自然的汞和硫才能转变成炼金术士期待的纯净质料,使用这些原料就能大大缩短制备银和金的时间,实现人工制金。
贾比尔和拉齐对汞硫理论的不同理解,导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炼金实践。但无论在实践方式上有多大区别,有一种信念是他们共同持有的,那就是技艺能够在人工环境中重现甚至加快自然进程,从而快速制得金银,这种信念为他们的矿物成因理论所支持。然而,同样接受汞硫理论的伊本·西那,却通过强调金属自然形成过程的某些原则,根本上否认了这一信念,从而对嬗变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诘难。
三 伊本·西那对炼金术的诘难
在《治疗之书》(Kitābal-Shifā)中,伊本·西那采用汞硫理论的基本主张,精确地描述了不同金属的不同组成([13],页39—40)。然而他却紧接着强调,这仅仅是金属自然形成的发生方式,由于人的力量不可与自然相比,炼金术并不能像自然那样生成新的金属:
尽管如此,炼金术意义上的性质,在本原或其完美程度上与自然的性质有所不同,它只是与自然有相似关系而已。因此人们相信,它们的自然形成以这种方式或以某种类似的方式发生,而炼金术在这方面无法与自然比拟,尽管他们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却也无法超越自然。至于炼金术士的主张,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没有能力实现物种的任何真正变化。([13],页40—41)
此前的炼金术士似乎理所当然地以为,只要足够理解矿物的自然形成过程,就有可能通过技艺重现甚至改进自然。伊本·西那却明确指出自然与技艺的对立。在他看来,一种矿物成因理论本身(如汞硫理论)并未承诺技艺的任何可能性。恰恰相反,真正理解矿物自然生成的人就会承认人工制金和嬗变的不可能,因为矿物成因中蕴含一些人工终究无法模仿的因素。他接着就表述了这些未被炼金术士真正认识的内容:
我认为,不可能通过某种技艺抹去“种差”,因为这些[偶性]的变更并不等于复合物被转变为另一个。这些可感之物不能让种发生变化,变化的只是偶然性质。由于金属的种是不被认识的,只要种差不被认识,何以能够知道是否它被移除或是它是如何能够被移除?……此外,一个复合物不能嬗变为另一个,因为实体复合的比例不尽相同,除非它被还原为原初质料,即它成为某物之前之所是。然而,仅凭熔炼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它只是为该事物添加了某些外在的东西。([13],页41—42)
贾比尔曾经认为,生成不同的金属意味着生成不同的偶然性质,伊本·西那显然纠正了这种对矿物成因的理解。通过借用亚里士多德对实体和偶性的区分以及“属加种差”的事物认识方式,伊本·西那表明,自然发生的金属生成以及不同种金属之间的转变,在根本上不是金属被赋予了各种新的外在可感的偶性,而是金属获得了某种先在的、决定金属是其所是的种差[8]。人的感官只能认识味道、颜色、重量等外在偶性,真正决定金属本质的种差是人的理智无法企及的,因而这一过程也就无法通过人工技艺实现。仅凭熔炼、蒸馏等炼金术技艺,并不能改变金属的种差,只能做到给金属的表观染色而已。([13],页41)
纽曼的研究表明,伊本·西那坚持种差超越于人之理智的基础是亚里士多德在《论生灭》(Degenerationeetcorruption)中提及的混合物理论。该理论认为真正的混合物不是其微小组分单元的并列,而应是严格意义的同质——它的任一部分都与整体相同(GC,328a1-15)。伊本·西那相信,混合物之所以同质,是因为它舍弃其任一组分的形式而被形式赋予者(dator formarum)赋予了一种新的“混合物的形式”(forma mixti),这又被称为实体形式(forma substantialis)。这里的形式赋予者,只能是天界的灵智、星体的统治者、超越一切人类理智的神意的代理人。因此汞硫本原的混合,本身并不能使热、冷、湿、干四性质自发组合成一种拥有新性质的新金属,这只是准备好了前提条件,使得形式赋予者能够赋予它新的实体形式。只有在天界力量的作用下,新的金属才能生成。其中本原的性质依然保留,它们体现为金属的偶性;而被赋予的实体形式,就是决定金属根本性质的种差([14],页38—40)。
伊本·西那将汞硫理论视作对矿物生成过程的解释,但又通过在其中引入无法被人类理智企及的天界力量,证明了技艺弱于自然,人工无法模仿自然中的金属生成,从而深刻否认了炼金术的信念。12世纪晚期,英格兰学者阿尔弗雷德(Alfred of Sareshel)将《治疗之书》论及矿物的部分单独译成拉丁文,并赋予它《论石头的凝结和粘合》(Decongelationeetconglutinationelapidum,以下简称《论凝结》)的标题。《论凝结》被附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第四册一个译本的结尾流传,并日渐被许多学者误以为是亚氏文本的一部分。由于亚氏在13世纪的拉丁欧洲备受推崇,这使得《论凝结》具有相当大的声望。这一方面有助于汞硫理论在拉丁欧洲的牢固确立,另一方面又仿佛亚氏本人宣布炼金术的嬗变理想是不可实现的。《论凝结》的巨大影响引发了13世纪拉丁欧洲的炼金术之辩,一场表面上争论嬗变是否可行,实质却事关人工与自然地位的全面辩论([4], 页84;[14],页37—38)。
四 炼金术之辩中的矿物成因理论
纽曼近三十年来的系统研究与大量出版物,是讨论中世纪炼金术史无法忽视的可靠文献来源,他将中世纪炼金术理论的许多片段融合成一种协调的、令人信服的叙事(1)关于对纽曼中世纪炼金术史研究的评价,可参见林德伯格的说法([15],页321 注释1)。。13世纪的炼金术之辩是纽曼炼金术史叙事中的重要事件,他调用详实的一手文献从各个方面勾勒了这场辩论中各方阵营的基本立场和辩论策略([7];[16],页1—57;[14],页34—36)。本节以此为背景,重点关注矿物成因理论在炼金术之辩中扮演的角色,考察辩论各方如何通过改造以汞硫理论为基础的矿物成因理论,对炼金术进行批判或辩护。
一种反对炼金术的策略,是延续伊本·西那突显自然与技艺之鸿沟的思路,通过强调人力无法企及的矿物成因,否决人工嬗变的可能性。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对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1100—1160)《四部语录》的评注(Commentuminquatuorlibrossententiarum),包含了他对炼金术的否定性意见。他发展了伊本·西那提出的实体形式只能由自然赋予的学说,进一步表明自然通过太阳的热量以及特定地点的力量为金属赋予实体形式,这两种自然成因无法被炼金术模仿。因为炉火的热量不同于太阳,炼金术实验室也不同于产生金属的特定地下环境[7]。将天界的星体力量视为矿物成因并非阿奎那的首创,他的老师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2)在纽曼关于13世纪炼金术之辩的叙事中,大阿尔伯特基本被视为支持炼金术的一方,他弥合自然与技艺鸿沟的方式被认为启发了13世纪晚期保罗的微粒炼金术([14],页34—54)。但需注意的是,阿尔伯特对炼金术的态度十分复杂,他如何调和亚氏自然哲学中的矿物理论与炼金术矿物理论这两种大异其趣的观念,并形成自己对矿物成因的独特理解,需要单独撰文讨论。就曾在《论矿物》(Demineralibus)中将之阐发为矿物形成的重要因素,他甚至试图论证炼金术士可以在特定天象时进行嬗变实验以“借取”星体的力量[17]。
阿奎那所说的“特定地点的力量”,则被他的学生罗马的吉莱斯(Gils of Rome,约1243—1316)理解为一种正式的矿物成因。吉莱斯指出金属的产生需要一种特定的“处所性”(virtusloci),这代表一种只存在于地球深处的矿化力。他认为一些生物的生成不需要特定的处所,只需有充足的物质本原,如从死牛中自发生成的蜜蜂。但有一些事物则既需物质本原,也需特定的处所,如用葡萄酿造的葡萄酒,因为酒只能产生于葡萄内部。金属的生成类似于葡萄酒,仅凭汞和硫那样的质料不足以形成金属,它还必须接受地下的矿化力,因而真正的金属只能在地球深处产生[7]。
面对反对者的诘难,13世纪初的《赫尔墨斯之书》(BookofHermes)和13世纪晚期被托名于罗吉尔·培根的《短篇祈祷书》(Brevebreviarium),发展出一种对金属生成和转化过程的再阐释策略,来为炼金术提供辩护。针对伊本·西那关于种差不被人所认识、物种不能被技艺转化的断言,《赫尔墨斯之书》回避了各种金属之间的种差问题。它提出各种金属同属一个物种,有着单一的定义:任何金属都是复合的、可熔化的、不可燃的、具有可塑性的实体。因此金属间的生成与转变就不再涉及任何物种转变,只是在种的具体偶性上发生变化而已[7]。
《短篇祈祷书》则进一步弱化种差与形式的作用,将金属仅仅视为具有具体偶性的物质:所有金属都由汞和硫这两种物质成分组成,它们在地下受烹煮和净化的程度成为不同金属的成因([14],页67)。因此金属生成过程中受到转化的并非物种,而只是由物质决定的具体金属的外在偶性。事实上,《短篇祈祷书》已将金属的偶性与其物种分离开来,物种被当作一种先验给定的形式,不再具有转变的可能性。而具体金属的偶性被视为物质的性质,由于物质可感知、可分割、可朽坏,因而具有被技艺转化的可能:
物种并没有被转化,被转化的只是个体……银的物种,即银之银性(argenteity),并没有被转化为金的物种,即金之金性(aureity)。银不会变成金,因为物种不能被转化,这是因为它们本身(物种)并不受制于感性的作用,既不可分割,也缺乏对立面的作用。具有可分割的部分或对立面的作用,才是导致转化的原因。它们是通过特定微粒和可分割的物质的变异,而被偶然地、并非真正和直接地转化的,这些特定微粒和可分割的物质是可腐烂的、复合的以及可感知的对象或主体。([14],页67—68)
这种对金属转化的物质主义理解方式暗示,无论是金属生成的自然过程还是炼金术的嬗变,都不涉及物种的转化,而只被视为一种偶性的变化,它源于环境对汞、硫这两种物质成分所施加的影响。伊本·西那声称的只能由自然赋予的实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被悬置起来不加讨论。金属的转化仅仅通过物质及其所受影响就能够加以解释,而在这一层面上,自然与技艺并无区别。
五 物质主义的微粒炼金术理论
13世纪晚期的方济各会修士塔兰托的保罗(Paul of Taranto),在《完满大全》(Summaperfectionis)中充分吸收了上述辩护思路。他提出一种彻底物质主义的微粒炼金术理论,将人类理智无法企及的实体形式请出了炼金术领域,完成了对炼金术技艺正当性的捍卫(3)纽曼为《完满大全》的作者考证、版本流传、后世影响,以及《完满大全》中的矿物观念和物质理论做了详尽充实的研究,并且提供了一个有详细评注的英译本(参见 [16])。J. Norris和晋世翔都对《完满大全》中的微粒理论进行过介绍(参见 [6]和[8])。。
在《完满大全》的序言中,保罗首先便明确了炼金术技艺的前提是了解矿物的自然哲学并加以模仿,这包括矿物的本原、原因与生成方式([16],页634)。而技艺能够模仿自然的信念,则来源于他对亚里士多德《气象学》第四卷中两段话的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为人工加热和自然热量的等同提供了担保([14],页73—74)。遵循技艺模仿自然的原则,炼金术士在转化金属时,就必须使用自然界形成金属的质料,即汞和硫。但保罗所秉承的汞硫理论可以说是一种“纯汞理论”,因为他将汞视为所有金属的主要成分,而将提供油性和可燃性的硫仅仅视为金属中的杂质([14],页74)。而他为整个炼金术技艺确立基础的关键则在于这句宣言:“技艺并不能模仿自然的全部运作,而是要以技艺所能的方式正确地模仿她。”([16],页634)保罗承认炼金术批判者的一些说法,即人确实无法认识自然生成金属的所有条件,这包括所谓的天界力量、种差和实体形式。但他却指出炼金术并不需要完全了解所有自然条件,技艺可以自己的方式重现自然的金属生成过程([16],页646—647)。
技艺之所以能操控矿物,首先是因为矿物没有灵魂,仅仅是单纯的物质。保罗认为,有灵魂的生物不能被技艺所完善,因为生物的缺陷来源于灵魂,而技艺只能改变物质,无法为之注入灵魂。但是矿物低于生物,矿物没有灵魂,只凭借其物质组成和比例而存在,因此就能够被人工技艺所完善([16],页647—648)。其次则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星体力量、实体形式等所有超出技艺范围的自然原则都不必被加以考虑,因为这些原则始终在自然地发挥着作用。而技艺是自然的帮手,它不必完全取代自然,技艺只需安排好自身能够考虑的物质原则,就足以产生自然的效果:
不是我们使金属发生转变,而是自然(使之发生)。我们只是按照人工的方式,为她准备好了物质。因为自然以她自己的方式运作,而我们是她的帮手……如果他们说金属的完善性来自于一颗或多颗星体的位置,而这种完美性我们并不知道,我们会说其实没有必要知道这个位置,因为任何种类的可生灭之物,其个体的生成与毁灭,每天都在发生着。因此很明显,对任何种类的个体而言,星体的位置每天都具有可完善性和可毁灭性。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等待星体的某个位置。只需为智慧的自然安排好物质,使她能让星体的适当位置与物质相协调,这就足够了。([16],页649)
通过以上的理论构建,保罗为炼金术清理出了一片稳固可靠的地基。在这片地基之上,无需再考虑任何超出人类理智的天界力量、种差、实体形式,技艺只需和经验能够完全把握的物质属性打交道。保罗因此才能够最终将金属完全视为统一的物质微粒,它们的具体特性只在微粒的大小和相对比例上有所不同,一种完全基于物质微粒聚合与分解的关于炼金术嬗变的微粒论解释才得以可能[6]。
六 余论:从自然哲学到现代矿物观念的曲折
不同于仅仅作为一种自然哲学静观的亚里士多德散发物理论,汞硫理论在阿拉伯炼金术士的阐发下,被植入了通过技艺重现乃至超越自然的理想,并成为炼金术实践传统的理论基础。伊本·西那充分阐明了这种炼金术传统中隐含着的自然与技艺的张力,并由此提出一种对炼金术的深刻批判,其关键就在于对矿物生成中无法被技艺所模仿的自然要素的强调。技艺与自然的绝对鸿沟导致保罗放弃认识自然的全部运作,不得不将人类理智无法企及的自然原则彻底悬置起来。正是这种放弃,使得对矿物生成的理解能够从自然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最终满足于一种符合经验事实并易于自身理解的物质主义的自然运作模型(4)13世纪晚期基督教思想家对上帝无限性的神学反思,强调了上帝意志的绝对超越以及有限的人类理性与无限的上帝之间的绝对鸿沟,同样导致了某种对认知的放弃(cognitive resignation)。这种放弃的一个后果是,将人的想象力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遗产中解放了出来,使人们不得不满足于人的心灵能够为自己提供的清晰可靠的数学/机械论模型,这被认为是使自然哲学朝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的必要一步([18],页136,148—150)。13世纪炼金术之辩所产生的结果与同一时期神学反思所引发的思想后果,二者具有显见的同构性,这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一系列观念演变的最后,保罗才能够给出一种对矿物生成的彻底物质主义的理解方式:矿物的形成仅由微粒、分散、聚合、热量等概念就足以机械地解释。矿物因此从技艺难以完全模仿的自然之物,转变为能够被人工技艺操控的物质对象。
纽曼注意到,《完美大全》对黄金的纯粹经验性和物质性定义,在17世纪获得了回响:弗朗西斯·培根和波义耳等新科学的代表对黄金的定义与之惊人地相似([14],页76)。因此从保罗彻底物质主义的微粒炼金术出发,一种机械论式的现代矿物观念似乎已经呼之欲出(5)纽曼和普林西比都尝试建立一种关于化学演进的历史连续性叙事,他们认为波义耳通过17世纪炼金术士斯塔基(George Starkey,1627—1665)和塞内特(Daniel Sennert,1572—1637)的工作,了解到了保罗的微粒炼金术思想,并深受其影响(参见 [19])。。然而在轻易地为微粒炼金术与现代矿物观念构建关联以前,还须注意一个历史事实——炼金术并未因为13世纪的炼金术之辩而在拉丁欧洲获得正当性,保罗的微粒炼金术理论也没有被当时大多数炼金术士所遵循,恰恰相反,世俗政权与教会对炼金术的谴责自13世纪晚期以来愈加频繁。普林西比认为,由于炼金术在公众心目中很少远离伪造货币等犯罪活动,对一种潜在的经济欺诈的防范,是欧洲各国的执政者纷纷颁布法令禁止炼金术活动的主要原因([4],页89—90)。纽曼则认为教会的谴责主要是因为将炼金术问题神学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基督教教义从原则上不能容许上帝以外的任何力量实现物种的改变,炼金术很容易被视为一种异端邪说[7]。面临神学和政治的多重压力,炼金术士不得不在14世纪增强其保密性,以免遭到当权者的严厉审判。直到16世纪欧洲出现大量矿冶技术文献,炼金术理论依然被比林古乔(Vannoccio Biringuccio,1480—1539)、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1494—1555)等矿冶作者视为重点批判对象[20]。
彻底物质主义的微粒炼金术理论在这样的背景下缺乏传播和发展的土壤,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中难以作为形成现代矿物观念所需的有效学术资源。炼金术汞硫理论的介入,使得亚氏自然哲学式的矿物成因理论发展为一种与技艺和经验紧密相关的矿物观念。但若仅凭炼金术自身演化而来的彻底物质主义的矿物理论,也无法面对基督教神学的压力。从自然哲学到现代矿物观念的曲折路径中,还需要一种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炼金术物质理论和基督教神学之间的折中与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