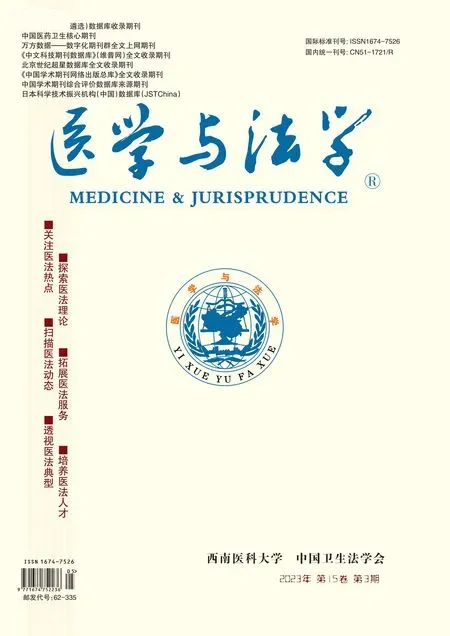医疗美容纠纷中诈骗罪的边界
仝潇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美容从明星专属到向普通大众普及,逐渐成为普通民众“二次变美”的一种选择。出现医疗机构不具备开展医疗美容服务的资质、主诊医师术中变更填充产品等因由,引发一系列医疗美容纠纷案件。自2017年至2023年4月,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公布的医疗美容纠纷判决书共计33例,其中以欺诈行为为案由提起诉讼的案件就有7例。可见欺诈行为在医疗美容行业中确有存在,并且给受害者及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界定,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司法实务中,消费者多是选择通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合同编”,或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民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医疗美容纠纷中的部分欺诈行为同时也符合诈骗罪的违法构成要件(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欺骗,受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遭到财产损失,欺骗行为与财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可能需要刑法来加以规制。在学术界,刘长秋教授也曾经指出,欺诈性美容整形给我国美容整形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对于社会影响极坏,且其中性质恶劣的行为应当予以刑罚处罚。[1]可见,对于医疗美容纠纷中的欺诈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具有探讨的必要性。
一、医疗美容纠纷中欺诈行为罪与非罪的认定
当前针对民事欺诈和刑事欺诈的关系,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首先,民事欺诈不排除刑事欺诈,不能通过主张行为构成民事欺诈,而得出否定刑事欺诈的结论。其次,刑事欺诈不等于民事欺诈,也不能认为只要行为符合民事欺诈的条件,就得出行为成立诈骗罪的结论。[2]张明楷教授也指出民事欺诈与刑事犯罪中的诈骗罪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即诈骗罪与民事欺诈的区分仅仅是诈骗罪与不构成诈骗罪的民事欺诈的界限。[3]
诈骗罪和民事欺诈的共同点是二者均具有欺诈行为,因此在医疗美容纠纷中辨别该欺诈行为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实务中,与民事欺诈相比,刑事欺诈往往会导致被害人陷入失去民事救济可能性的高度风险,其具体表现为两种情形:一种是民事救济无力——即使被害人能够发现真相也无法通过民事救济弥补其遭受的损失[4]。在医疗美容纠纷中不存在此种情形的诈骗罪。即使法院不支持患者所主张的医疗美容合同应当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还患者的医疗费并进行三倍惩罚性赔偿,也可以通过《民法典》“侵权责任编”或“合同编”的相关条款补偿患者所遭受的经济损失。法律适用结果的主要区别是患者能否获得三倍的惩罚性赔偿,而无论适用何种法律,患者所遭受的损失均可以通过民事救济得到补偿,因此不存在民事救济无力的说法。另一种是难以发现真相,即受骗人难以发现真相,因而从源头上阻断了其寻求民事救济的可能性;而这在医疗美容纠纷中,该种行为则可能构成诈骗罪。例如2019 年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曾审理一起案件,该案中原告在某医疗美容机构进行隆鼻手术,与主诊医生协商,要求采用进口膨体作为隆鼻假体,且术前多次与工作人员核对,并额外支付膨体差价2000 元,后因手术失败,原告经多方调查,发现术中植入的假体为国产膨体。①在该案中,原告在术前多次向工作人员核对拟植入的假体是否为进口膨体,均得到肯定答复,即工作人员明知该美容机构没有进口膨体,也不曾有购置进口膨体的计划,却欺骗原告,表明将为其使用进口膨体进行手术,原告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并选择在该美容机构进行手术,支付了进口膨体的价格;如果不是因为手术失败,原告不可能发现自己受到欺诈而被植入了国产膨体(正常诊疗过程中患者不会要求美容机构提供术中用品的商标、产地等)。笔者认为,此种行为即属于诈骗罪中难以发现真相的情形。
日本刑法将诈骗罪欺骗行为分为欺骗行为的内容(重要事项性)和欺骗行为的样态(举动欺骗);而“重要事项性”被理解为“对照该交易或者业务内容的性质、目的,被害人在交付财物或者利益之际有充分考虑之必要性的事项”;[5]而“举动欺骗”是指,举动这一作为本身能够被评价为显示了虚假的事实,属于作为方式的欺骗行为的一种类型[6]。医疗美容诈骗罪以此标准认定,具有一定科学性。
(一)医疗美容诈骗罪之“重要事项性”的认定
1.执业资格的具体认定。
原卫生部令19 号《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美容医疗机构必须获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后方可开展执业活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医疗机构必须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以下简作《许可证》)、诊疗科目等重要事项悬挂于明显处。②由于医疗美容机构的服务管理也同时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制约,因此,医疗美容机构也应当将《许可证》、诊疗科目、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悬挂于明显处。就诊者选择医疗美容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在原有的基础上变得更加美丽动人;而医疗美容手术也兼具手术失败的风险及潜在的术后并发症,因此就诊者在术前选择诊疗机构时必然十分小心,对于未出示相关证明材料的美容机构,就往往不会考虑。如果诊疗机构未悬挂相关材料或者悬挂不齐全,而就诊者选择其服务的,则诊疗机构不属于欺诈行为(没有相关证件,所以未悬挂),就诊者属于其自身的过失行为;但如果诊疗机构伪造或者篡改相关证明文件并悬挂于明显处,就诊者基于相信该美容机构具备从事相关医疗美容服务的资质而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自己的财产,选择在该美容机构从事医疗美容手术,则该美容机构的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医疗美容服务实行主诊医师负责制。从事医疗美容服务的主诊医师必须同时具有执业医师资格(经执业医师注册机关注册登记)和《医疗美容主诊医师资格证》。由于国内公立医院管理较为严格,任职的医疗美容医生一般都是在毕业后取得执业医师资格并经多年工作评上相关职称后,才有资格独立开展医疗美容手术;因此,如果就诊者选择在公立医院进行医疗美容手术,则默认就诊者是基于为其进行手术的医生具有医疗美容的资质的认识,而选择在该医院手术并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如果公立医院为其指派的手术医师不具备相应的资质,则属于利用就诊者的信任对其进行欺骗,使其陷入错误认识并处分财产,该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消协联合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共同发布的“2022年十大消费舆情维权热点”显示,全国消费者协会每年收到的医美行业投诉案件高达7233件,所投诉的主要问题包括部分医美机构证件不齐全、超范围经营、工作人员不具备执业资格等。③因此在非公立医院进行医疗美容手术则不能默认手术者均具有医美手术资质。如果美容机构所提供的宣传资料、手术者所提供的证明材料均使就诊者在审慎检查之后认为手术者具有医疗美容资质并基于该种信任处分财物、选择手术,则其同样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职称欺骗的认定。
医疗美容不同于常规的诊疗行为,更具有商业化的功利。普通的诊疗行为目的是治愈疾病,不论手术者是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还是主任医师,经过专业的训练,均能够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因此对于疾病的治疗,相同级别的医院,手术医师的职称、经验并不会影响手术的价格。但是医疗美容手术作为一种商业化服务项目,受到市场支配的调节作用,技术高超的医师诊疗位供不应求,收费价格自然也就偏高。由于在医疗系统中职称的评定需要结合工作年限、手术例数等综合评价,且医疗技术本就是一种熟能生巧的过程(操作的例数越多,经验越丰富,术后效果通常越完美),因此在医疗美容行业中,不同职称的手术者收费标准不同(例如南京某三甲医院整形科,同样进行双眼皮全切手术,副主任医师主刀是8500元,主任医师主刀是1.2万元)。如果主刀医师是副主任医师,但是医疗美容机构的工作人员称其是主任医师(通过宣传栏、公示栏、工作证等途径)而欺骗就诊者,就诊者因被骗而同意进行该项手术,并基于对主刀医师职称的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财产,则医疗美容机构工作人员的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二)医疗美容诈骗罪之“举动欺骗”的认定
1.手术方案的选择。
医疗美容手术之前,就诊者要进行面诊,主诊医师通过自己的审美以及现有的医疗技术手段向就诊者详细介绍手术方案,在取得就诊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方可进行后续手术。医疗美容手术的附加手术项目繁多,比如双眼皮手术有埋线、全切、全切+开眼角、全切+抽脂、全切+抽脂+脂肪填充、全切+开眼角+抽脂+脂肪填充等。如果术前工作人员仅打算对就诊者进行A 方案手术,但是为了赚取更多的费用,欺诈就诊者签署B 方案的《知情同意书》(B方案的费用〉A方案的费用)最终却按照A方案进行手术。由于工作人员的欺诈行为,就诊者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进行手术,且术后就诊者难以发现术中已经更改了手术方案,则工作人员的行为符合诈骗罪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如果手术者在术中发现B方案效果不好,临时改为A方案,但术中及术后均未告知就诊者,由于其行为前并没有欺诈的故意,因此该行为不属于欺诈行为。
2.医疗器械的选择。
在医疗耗材市场中,来自不同厂家的同种产品价格不一。同时,美国等欧美国家的医疗器械的价格要远高于国内品牌,其效果也较国内品牌为佳。因此很多爱美人士为了追求更好的医美效果,明确表示选择进口医疗器械。工作人员为了赚取非法利益,欺骗就诊者,声称将为其使用进口器械而实际却是非进口器械,就诊者基于错误认识支付了对价(进口产品价格),则此工作人员的该种行为属于欺诈行为。如上述浙江省的案例中,主诊医师明知其所在的医疗美容机构未配置进口膨体,也无进购进口膨体的打算,但是为了赚取非法利益,仍多次告知原告,为其隆鼻使用的是进口膨体,主诊医师的行为就应当认定为符合诈骗罪中的欺诈行为。
二、医疗美容欺诈中之法益侵害的具体认定
由于诈骗罪是财产性犯罪,其侵害的法益是公私财物,因此明确存在公私财物的减少是认定诈骗罪的关键。在理论界,财产损失共存在三种学说,即形式的个别财产损失、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整体财产的损失。[7]
(一)形式的个别财产损失
“形式的个别财产说”认为,只要被害人是由于受到欺骗而处分了财物,就认为其个别财产遭受了损失,不论其所获得是否超过了对价,均成立诈骗罪[8]。该学说的经典案件是日本的“捐款诈骗案”和“骗买肝炎药品案”。根据此种学说,在医疗美容案件中,只要就诊者因为受到欺骗(重要事项性或者举动欺骗)而处分了财产,不论其手术是否成功,欺诈人的行为均成立诈骗罪,诈骗金额为受害人所支付的所有对价。根据《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诈骗公私财务数额3000元以上的,即可满足诈骗罪中数额较大的规定④。在职称欺诈案件中,以副主任医师职称欺骗患者,声称是主任医师(以南京某三甲医院双眼皮全切手术为例,行为人的诈骗数额是支付的主任医师价格:12000元),符合诈骗罪数额的要求,诈骗金额为12000 元。但是根据我国刑法诈骗罪的定义,诈骗罪的认定既要有欺诈行为,又要有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手术成功的就诊者而言,尽管其支付了主任医师的价格却只享受到副主任医师的操作,但是无论手术者是谁,就诊者都达到了预期的目标,现实中未受到真正的财产损失,不符合我国诈骗罪有实际财产损失的要求。此时若要认定行为人诈骗12000元,显然不妥,因此形式的个别财产损失学说不适用于我国医疗美容纠纷案件。
(二)实质的个别财产损失
所谓“实质的个别财产说”,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即被害人处分财产的目的是否得以实现。在医疗美容案件中,就诊者选择医疗美容手术的唯一目的就是改变面部缺陷,重塑美好外形。因此对于手术成功的就诊者而言,由于其手术目的已经实现,即使受到了欺骗,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也不构成诈骗罪。但是对于手术失败的就诊者而言,由于其没能实现手术目的,因此行为人的欺骗行为构成诈骗罪。例如在上文提到的浙江省医疗美容纠纷案件中,原告因为手术失败(未实现手术目的),在调查取证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受到欺诈。如果手术成功,原告不会主动调查手术是否侵犯了自己的财产权。但是无论原告是否调查,被告的欺诈行为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为原告是否追究而改变。因此根据手术成功与否判断是否构成诈骗罪显然不妥。
(三)整体财产的损失
该种学说认为,是否侵害了财产法益,取决于被害人处分的财产价值是否大于行为人的对待给付。在“整体财产损失说”下,又有两个分支:其一即财产损失是客观的经济损失。[9]在医疗美容案件中,根据上文分析的诈骗行为,职称欺骗、手术方案欺骗、医疗器械的选择欺骗都具备欺诈行为,且均因欺诈行为获取了额外利润,诈骗金额为就诊者支付的金额与其获得的对待给付之间的差价。在职称欺骗的案例中,同样以南京某三甲医院双眼皮手术收费标准为例,如果就诊者被骗支付了主任医师手术费用12000元,实际是副主任医师主刀(标价8500元),那么就诊者被骗的金额为主任医师标价与副主任医师标价的差价(12000 元-8500 元=3500 元),达到诈骗罪数额较大的标准,成立诈骗罪,诈骗金额3500元。但是在上文浙江省医疗纠纷案例中,国产膨体和进口膨体的差价为2000元,不满足诈骗罪成立数额较大的要求,因此即便医美机构具备欺诈行为,并且因欺诈行为获取了额外利润,其行为也不能成立诈骗罪。其二是客观价值+财物的使用价值以外的经济损失。[10]财物的使用价值即被骗取购买某种用不着的物品,因为该物品也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认定诈骗罪时要将该物品的价值除去。根据此理论,日本的“骗买肝炎药品案”就不构成诈骗罪。但是在医疗美容手术中,由于就诊者并不存在额外购置商品的情形(术后欺骗就诊者购买产品的情形除外),因此该理论不适用于医疗美容手术案件。
作为财产性犯罪,诈骗罪的构成既需要有违法性行为,同时受害人还要基于行为人的欺诈存在财产损失。因此仅有违法性行为或者仅有财产损失均不能构成诈骗罪。针对诈骗罪法益侵害的三种学说,笔者认为“整体财产损失说”中的客观的经济损失学说较为适宜医美案件中的欺诈行为。首先在“形式的个别财产说”中,只要被害人由于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处分了财产均成立诈骗罪显然不妥;其次在“实质的个别财产说”中,是否构成诈骗罪取决于手术成功与否(逻辑上更为荒谬)。客观的经济损失学说则更为恰当,诈骗的金额为受害人实际支付与所获得服务之间的差价。
三、医美案中诈骗罪之“此罪与彼罪”的评判
虽然医疗美容纠纷中的诈骗罪主要区别于民事欺诈行为,但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认定时也要与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保险诈骗罪、医疗过失行为等相区别。
(一)与故意伤害罪区别
医疗美容作为一种非诊疗目的性手术,即并非以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为目的,它不会像普通的诊疗目的性手术那样给就诊者带来客观利益,具体而言,只能给就诊者带来主观利益(视觉感官上的利益),因此,实施医疗美容手术必须征得就诊者本人同意,如果医生在未征得就诊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医疗美容手术,则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11]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欺骗他人捐献器官的,构成故意伤害罪。面部组织、皮下脂肪等也属于广义的器官,因此如果医生以非法目的欺骗就诊者使其对自己的面部特征、结构陷入错误认识,从而同意医生摘除其面部组织的(承诺无效),医生的行为也可能构成故意伤害罪。诈骗罪与故意伤害罪的区别在于,故意伤害罪侵犯的客体是就诊者的身体健康,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由于医疗美容是一种付费同意伤害行为,因此不排除医生的行为可能同时构成诈骗罪和故意伤害罪。
(二)与非法行医罪区别
非法行医罪是指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非法行医,情节严重的行为。在医疗美容中取得医生职业资格是指既取得医师资格证,执业范围又注册为整形美容科的主诊医师。非法行医罪的认定不需要以取得财产为定罪标准,即情节严重的免费行医行为也可能构成非法行医罪,而医疗美容中的诈骗罪必须是以非法占有公私财产为目的,这是二者的本质区别。如果受害人被无执业资质的行为人欺骗而处分财物,无论手术成功与否,受害人是否有实质性的财产损失,情节严重的均可依照非法行医罪定罪处罚。
(三)与保险诈骗罪区别
保险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类型,二者是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当犯罪构成要件同时适用特别法和普通法时,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在医疗美容纠纷中保险诈骗罪的行为客体是保险公司(商业保险部分)和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险部分),而诈骗罪的行为客体是就诊者。在我国医疗美容行业中,绝大部分的医疗美容项目是自费项目,当医生为了拉拢客户等目的,将医疗美容项目变更为可以报销的其他诊疗项目时,其行为欺骗了医疗保障局或者/和保险公司;而医疗保障局或者/和保险公司由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受到损失,就诊者获得财产利益,《德国刑法典》将其归类为结算诈骗[12]。如果就诊者明知其不符合报销条件,而接受了医疗保险或者商业保险优惠,可能成为保险诈骗罪的共犯。在诈骗罪中,就诊者是受害者,而在保险诈骗罪中,就诊者可能不触犯法律,也可能成为犯罪主体。
(四)与医疗过失行为区别
由于医疗机构的过失行为导致就诊者遭受损害,可能构成医疗过失。在医疗美容领域,医疗过失主要分为诊断过失、注射过失和手术过失。诊断过失是指医生在面诊时错误的判断了就诊者的美容缺陷,注射过失常见于错误的选择了注射部位、注射技术、注射药物等,手术过失的类型与诊疗性手术一样,常见于手术时机和方法选择不当、手术过程中的技术操作失误[13]。此处因医疗过失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均指就诊者的身体健康遭受损害,而诈骗罪是财产犯罪,其指代的损害是就诊者的个人财产损失。
四、结语
在医疗美容案件中,受害人多以民事途径提起诉讼,但是不能排除某些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医疗美容基于其商业性特色以营利为目的,其欺诈行为要区别于民事欺诈,鉴于医疗美容与普通的医疗诊疗行为(非营利性)的差别,也要将其欺诈行为区别于故意伤害罪、非法行医罪、保险诈骗罪、医疗过失行为等。
注释
①(2019)浙0382 民初7684 号,干雨薇与乐清顾得美医疗美容诊所有限公司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
②参见《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必须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诊疗科目、诊疗时间和收费标准悬挂于明显处所,不得擅自修改。
③参见全国妇联女性之声,“价格刺客”“菜刀不能拍蒜”……新的一年,可别再踩这些“坑”!,2023-01-31。
④参见《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兼论“二维码偷换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