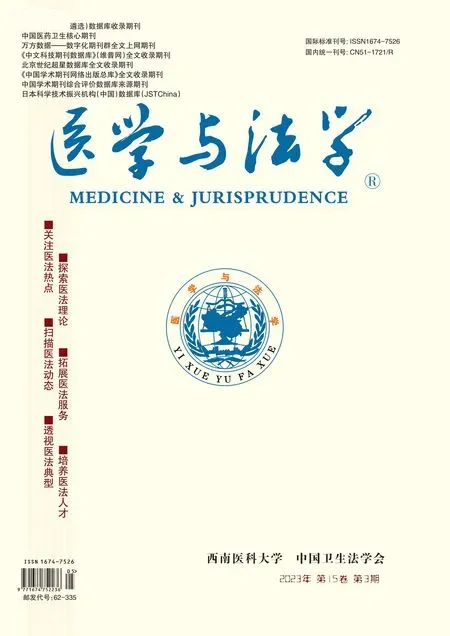俄罗斯代孕法律规制研究
杨振楠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发展及其趋势的演变,代孕作为辅助人类生殖生育的技术手段逐步被公众认识和接纳;而代孕技术在给诸多家庭带来生育希望的同时,也冲击着社会传统的伦理道德,并由此引发诸多法律问题。现代意义的“代孕”是指有生育能力的女性(即代孕母亲)借助现代医疗技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及其衍生技术),将受精卵植入子宫内,为他人(委托方)完成妊娠、分娩的行为。近年来,受环境污染、过早婚前性行为、性传播疾病感染、人流药流次数增加、工作压力大、生育年龄延迟等因素影响,不孕不育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据中国人口协会、国家卫健委于2018年发布的数据,中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从20 年前的2.5%~3%攀升到12%~15%左右,患者总数达5000万。[1]面对社会中由解决不孕不育问题而日益增加的客观需求,我国有关法律制度却并没有为代孕技术及其适用提供制度指引,而仅以部门规章的形式简单禁止,此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能遏制代孕行为的发生,反而更易诱发负向的社会激励[2],造成地下代孕产业发展猖獗。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每年通过代孕黑市诞生的婴儿超过1万名,且逐年增加。[3]以禁止为初衷的代孕制度预期却与社会的实际结果相抵牾,尤其在保护代孕子女的合法权利上表现乏力;而由代孕引发的抚养权争议、继承权争议、监护权争议等诸多问题,更是频频见诸媒体,甚至还出现代孕弃养行为等,都不断挑战着社会伦理道德与法律底线。正视人民群众对代孕的合理需求,了解需求背后的真实民意,有限开放代孕,应已是大势所趋。[4]从制度类属分析,代孕制度本质上仍属于生育制度范畴;而因代孕成功后所诞生的婴幼儿及其天然附随的民事法律后果具有不可逆性,故法律应为代孕子女的健康成长提供制度保障。[5]因此,构建以社会民众合理需求为导向、以代孕子女合法利益保护为核心的代孕制度,是我国当前代孕技术适用现状和法律制度模式下的较优选择。[6]
就此而可资参考的是俄罗斯的相关状况,其与我国面临着相似的人口结构问题,根据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Росстат)的数据,自2016 年以来,该国的出生率出现了大幅下降[7];2019年,人口自然减少达到31.7万人,出生率仅为10.1‰[8]。俄罗斯人类生殖协会(РАРЧ)认为,其国家出生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孕不育率的攀升。[9]俄罗斯不同地区的不孕不育率从17.2%到24%不等,总体人数也在持续增加[10];从2005年到2018年,18~49岁的妇女患不孕症的人数翻了一倍,从2005 年每10 万名妇女中有146.6例增加到2018年的273.8例[11]。基于人口问题解决的客观需求,俄罗斯通过代孕制度,在满足医学原因无法生育群体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实施人口政策的综合治理,在鼓励生育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概而言之,俄罗斯代孕法律制度所采取的是完全代孕模式,其核心在于限制代孕行为主体、保护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也是我国构建代孕制度的功能定位点与核心考量处,故系统阐述俄罗斯代孕制度模式及其发展趋势,可以为我国相关制度建构提供有益参照。
二、俄罗斯代孕制度的立法现状
俄罗斯在代孕法律规制方面采取了本体法与关联法并行的方式。本处所说的“本体法”是指用以规制代孕生殖技术及其应用的专门立法;而所谓的“关联法”则是指相对本体法而言,虽不是用来专门规制代孕生殖技术,但内容却有规范代孕之相关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则,其主要体现在传统法律制度中(详见下表)。

表 俄罗斯代孕关系的立法实践
(一)《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
2011 年11 月21 日,俄罗斯颁布了第三百二十三号联邦法《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12]。该法的监管对象为个人、国家权力机关、医疗组织和医务工作者;其第五十五条对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运用的相关问题,以及使用该技术的程序、禁忌和使用限制都应得到授权的联邦行政机关的批准等等,都作出了相关规定,同时指出细胞、生殖器官组织和人类胚胎不能用于工业目的,强调不允许选择孩子的性别,但有可能继承与性别有关疾病的情况除外;该法第五十五条第九款对代孕的概念首次做出规定:代孕是指根据代孕母亲(携带胚胎并生下胎儿)与因医学原因不能怀孕及生育的委托父母(提供卵子、精子)达成的代孕合同、或者代孕母亲与因医学原因不能怀孕及生育的单身女性达成的代孕合同,而由代孕母亲怀孕并生育子女(包括早产)。根据该法的“代孕”定义,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代孕是通过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至代孕母亲的子宫中进行的生理过程;孩子与委托方之间存在基因与遗传关系;代孕母亲和委托方之间的关系基于他们所缔结的代孕合同;委托方使用该技术需要有一定医学前提;委托方仅包括已婚父母及单身女性。[13]此外,该法第五十五条第十款规定,代孕母亲的年龄必须在20岁至35岁之间,至少已经生育过1个健康的孩子,且拥有健康状况良好的医学证明,并对将要采取的医疗措施自愿签署书面同意书;其中,已婚女性只有在得到其配偶出具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并按照俄罗斯联邦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登记,才能成为代孕母亲。该法还强调,代孕母亲不能同时作为卵子的捐献者。
(二)《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禁忌以及使用限制》
在代孕技术的适用层面上,俄罗斯联邦卫生部在2020年7月31日发布了第八百零三号令《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禁忌以及使用限制》[14],该法令清晰规定了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规则,其中第五部分规定了使用代孕辅助生殖技术的客观标准,且只有已婚夫妻或单身女性由于几种特定的医学原因导致无法生育的才可以使用代孕技术;而所谓“特定的医学原因”指没有子宫、宫腔或宫颈畸形且无法矫正或矫正无效、子宫内膜病变(宫腔粘连、宫腔闭塞、子宫内膜萎缩)且无法矫正或矫正无效、禁忌清单中的疾病(情况)、反复尝试胚胎移植后没有怀孕(3 次及以上高质量胚胎的移植尝试)、与遗传病学无关的习惯性流产等;还要求应对代孕母亲进行相应的医学检查、植入代孕服务提供者的胚胎数不得超过2个。
(三)《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15]对代孕的亲子关系认定作出了规定,其五十一条第四款要求,已婚夫妻以书面形式同意将他们的胚胎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的,只有在孕儿女性(代孕母亲)同意的情况下,该夫妻才能被登记为孩子的父母;其五十二条第三款对代孕中父亲身份及母亲身份的争议解决作了阐明,规定孩子出生且完成父母登记后,代孕母亲及该委托夫妻双方均无权再以代孕事实为由,对已有的父母身份和亲属关系提出争议。
(四)《关于公民民事行为》
1997年颁布的《关于公民民事行为》[16]之第十六条第五款对以代孕技术出生的婴儿登记问题作出规定:以生育为目的,同意将其胚胎植入另一位女性体内的夫妻,请求对孩子进行出生登记时,应向登记机关提交由医疗机构签发的出生证明,以及代孕母亲同意上述夫妻登记为孩子父母的书面证明。即申请人若想将自己登记为孩子的法定父母,须同时向登记机关提交两份证明文件,一份是证明孩子出生事实的文件;另一份是代孕母亲自愿放弃亲子登记,同意将他人登记为孩子法定父母的文件。[17]
近期,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针对出生登记的程序性事项作出说明:出生登记须在孩子分娩后的一个月内申请,由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孩子出生地或居住地向民事登记处或提供国家市政服务的多功能中心提交;申请时应提交申请人的护照、由医疗机构出具的孩子的出生证明、由医疗机构出具的确认代孕事实的文件,其中应包含代孕母亲同意将他人登记为孩子父母的同意书、父母的结婚证明或亲子关系的证明[18]。
三、俄罗斯代孕亲子关系的认定
《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与《关于公民民事行为》对俄罗斯亲子关系的认定作出规定:由代孕技术出生的婴儿,原则上由代孕母亲作为其法定母亲,除非其放弃亲子登记,同意将他人登记为该婴儿的法定父母;在出生登记完成后,代孕母亲无法撤销其同意;一旦发生亲权纠纷,无论是委托人抑或是代孕母亲,都无法以代孕事实为由对身份关系提出质疑。在俄罗斯,非遗传并非系否认亲子关系的必要条件。由于代孕问题的复杂性,实践中出现诸多亲子关系认定上的难题。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民事与行政诉讼法系副教授邦纳(Боннер А.Т.)在其《人工授精:现代医学和人类社会的碰撞》中,对涉及代孕的父子(母子)法律关系争端的诉讼案件结构进行了大量分析,他指出这类诉讼的数量有增加的趋势,争讼类型也变得更加多样化。[19]
(一)代孕母亲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优先权
根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已婚女性只有基于生育目的、书面同意将胚胎植入另一妇女(代孕母亲),且分娩妇女(代孕母亲)同意的情况下,才能作为子女的父母进行登记。这意味着只有在代孕母亲同意的情况下,委托方才能获得作为法定父母的权利和义务;若代孕母亲拒绝,并将自己登记为监护人,那么委托方将仅被认为是基因捐献者。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法官克尼亚泽娃(Князева С.Д.)认为,此种代孕的法律规制模式破坏了公民利益的平衡,不仅侵犯了委托方的权利,也侵犯了代孕子女的权利。[20]同时,代孕子女的利益还可能受到严重损害,因为立法上对生育子女的代孕母亲的优先事项给予照顾,不仅剥夺了以代孕方式出生的子女在委托方家庭中优先成长的机会,而且客观上也可能造成孩子无父。[21]
俄罗斯将代孕母亲的同意作为确认基因父母亲子关系的前置条件,以平衡基因父母和代孕母亲的利益。将代孕母亲的权利优先于基因父母的权利,承认代孕母亲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优先权,是以“分娩者为母”理论为基础,体现了罗马法之“mater est quam gestation demonstrate”(母亲由怀孕决定)原则。俄罗斯学者指出,确立代孕母亲在亲子关系认定中的优先权,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国家保护妇女、儿童和家庭原则,应予以立法修改。
2017 年5 月16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全体会议通过了第十六号决议《关于法院在审查涉及儿童身份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22]。该决议确认了司法实践中代孕母亲与委托方亲权纠纷的处理方式;决议指出代孕母亲的拒绝,并不是法院拒绝确认委托方父母地位的无条件理由;规定对于由代孕技术产生的亲子关系纠纷,应由法院审查:双方是否签订了代孕合同、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原告是否是孩子的遗传学父母、代孕母亲基于何种理由不同意将原告登记为孩子的父母等,且法院应依据上述审查事实,以孩子的最大利益作为首要考虑进行裁决。[23]托科拉斯基(Антокольская М.В.)在由其主编的家庭法教科书中称,这一立法应被视为《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的成就之一,它成功解决了一个道德上的复杂问题,避免了遗传学父母被迫将其子女交给他人。[24]
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给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俄罗斯在司法实践中对儿童权益的保障。根据《关于法院在审查涉及儿童身份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的规定,每个儿童都有尽可能在家庭中生活和成长的权利,有权了解自己的父母,有权照顾他们,有权与他们一起生活,除非有悖于他的利益。与确定儿童身份有关的案件,将按照《俄罗斯联邦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由申请人居住地的区法院审理。[25]在法院审理涉及确定儿童身份的案件中,法院应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二条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五十七条的规定,给予儿童对影响其利益的所有事项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以及在任何司法或行政程序中发表意见的权利,如在确认亲子关系的案件中,法院可就与依法审查案件有关的情况询问儿童的相关意见。上述规定为寻求保护儿童权利和合法利益的主体以及儿童本人创造了更为有利的司法条件,有利于切实保障孩子的权益。
(二)单身男性在亲子关系认定中存有争议
根据《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五十五条第九款的规定,接受代孕服务的主体应为已婚夫妻或单身女性,即单身男性无法利用代孕技术成为孩子的父亲。在俄罗斯,代孕是一种公认的治疗不孕症的方法。由于医学上的原因无法生育的女性有权使用代孕服务,但不能生育的单身男性却被不合理地剥夺了这一权利。莫斯科国立法律大学民事与行政诉讼法系副教授邦纳(Боннер А.Т.)指出,拒绝单身男子申请代孕子女登记违反了《俄罗斯联邦宪法》的规定,因为对单身男子权利的保障不仅源于《俄罗斯联邦宪法》第七条所规定的国家对父亲身份的支持,也源于第十九条第二款所规定的对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平等保障,同时第十九条第三款特别强调了男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平等地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的机会。[26]
针对拒绝为单身男性登记为孩子父亲的争议,俄罗斯的司法实践值得考究。2010 年8 月,莫斯科巴布什金斯基区法院发布了俄罗斯第一个有关单身男子利用生殖辅助技术后进行亲子登记的判决,这项判决业已成为其整个国家关于男性代孕登记案件的里程碑。[27]法院裁定,在俄罗斯法律中,没有任何禁止或限制未婚男性通过辅助生殖技术实现自己成为父亲的可能性,拒绝对孩子的出生进行登记并不符合法律的要求,这不仅侵犯了男性的合法权益,也侵犯了案中代孕婴儿的利益。考虑到现行立法并未规定对仅有父亲的孩子建立亲子关系和登记监护的问题,法院认为有必要参照使用现行《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的规范,并特别指出“缺乏法律规范不能成为减损或侵犯儿童及其父亲的合法权益的理由”[28],故确认公民身份登记部门因孩子的出生父母仅为单身父亲一方而拒绝登记的做法是非法的;随后,俄罗斯法院在涉及单身父亲的类似案件中都作了几乎相同的判决,如2011 年3 月4 日圣彼得堡斯莫尔宁斯基区法院法院在第2-1601/11号案件中的裁决,2011年3 月25 日莫斯科特维尔区法院在第2-1894/2011号案件中的裁决等等[29]。
四、俄罗斯代孕合同的规定
(一)有关合同主体的法律规定
根据《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规定,代孕合同是特殊的合同,具有财产与身份的二重性。俄罗斯有关法律对使用代孕服务的各主体规定了明确的限制条件,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能签订代孕合同。
首先对代孕服务接受方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应当指出,在俄罗斯只有具备俄罗斯联邦卫生部2020年7 月31 日发布的第八百零三号令《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禁忌以及使用限制》中所列出的原因时,才有可能使用代孕技术,明确排除了非不孕不育患者适用代孕合同的可能性。也即排除了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因缺乏生育意愿而寄希望于使用代孕方法的可能性。目前,俄罗斯也在进一步限制可以在俄罗斯接受代孕服务的主体范畴。2022 年5 月24日俄罗斯国家杜马一读通过了一项法案,该法案旨在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使用代孕服务。[30]根据该法案,只有拥有俄罗斯国籍的已婚夫妻或单身女性,由于医学确诊欠健康而致不孕不育,才可以使用代孕服务;只有俄罗斯公民才能成为代孕母亲,且由代孕技术出生的孩子必须加入俄罗斯国籍[31],该法案的出台,也与新型冠状病毒大肆蔓延而俄罗斯的边界关闭、进而导致不少在俄代孕出生的婴儿不能离境有关,如人权理事会副主席伊琳娜·科考拉(Irina Kirkora)就表示,由于代孕母亲和外国委托方无法见面以证明遗传关系,大约有1000名婴儿因此无法离开俄罗斯。[32]
其次对代孕母亲进行了必要的限制。依据《俄罗斯联邦健康保护法》规定,代孕母亲的年龄必须在20岁至35岁之间,且至少已经生育过1个健康的孩子,拥有健康状况良好的医学证明,对将要采取的医疗措施自愿签署书面同意书。已婚女性只有在其丈夫出具书面同意的情况下,才具备提供代孕服务的资格。该法强调,代孕服务提供者不能同时作为卵子的捐献者。[33]在实际操作中,准代孕服务提供者还需进行全面的健康检查。只有在满足了上述条件后,代孕机构才可以安排代孕服务提供者与服务接受者见面,并最终在律师的帮助下签订合同,列清孩子归属、代孕母亲权益保障等条款,以保护各方利益。
(二)有关合同性质的学术讨论
代孕合同可以是商业性的,也可以是非商业性的(利他主义)。商业性的代孕合同规定了代孕服务的物质报酬,且通常有医疗机构和医疗人员介入,而非商业性的代孕合同除怀孕期间的合理费用外,不得规定其他任何报酬,此类合同通常在亲属之间签订,提供代孕服务方可能不符合代孕立法的一般要求。
俄罗斯相关法律对于代孕合同的性质并未作出明确规定,法学界正在讨论代孕合同的性质,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观点。一是认为代孕合同属于受民法管辖的民法合同体系,应参照《俄罗斯联邦民法典》中关于有偿提供服务合同的规定予以适用。米莲可娃(Митрякова Е.С.)指出,代孕合同与有偿提供服务合同具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应将代孕合同列入《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三十九条有关有偿提供服务合同管辖的合同清单。[34]根据《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有偿提供服务合同的定作人应为向其提供的服务给付报酬,这与有偿代孕合同的行为范式一致:委托人向为其提供代孕服务的代孕母亲付费。但实践中的代孕合同既可以是商业性的有偿模式,也可以是利他主义的无偿模式,无偿性的代孕合同将无法适用有偿提供服务合同的规定。在这点上,鲍里索沃伊(Борисова Т.Е.)指出,将代孕合同的有偿部分归类为民法上的有偿提供服务合同,而把无偿部分置之不理是不正确的。[35]第二种观点认为代孕合同具有家庭法性质,不能归于民事合同体系。列别杰娃(Лебедева О.Ю.)认为,代孕合同的基础在于代孕母亲向基因父母转移个人非财产权利,不能仅根据有偿性特点,将其归入民法中有偿提供服务合同的范围。[36]斯捷列娃(Стеблева.Е.В.)认为,代孕合同应该被归入家庭法领域,因为其基础不是商品或金钱交易,而是实现由于生理原因无法拥有自己孩子的妇女的生殖功能。[37]第三种观点是将代孕合同视为一种混合的无名合同。佩斯特里科娃(Пестрикова А.А.)认为,尽管在家庭法与民法领域都没有对代孕合同的明确规定,但代孕合同本身并不违反现行立法规定,可以将代孕合同认为是根据《俄罗斯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一条合同自由原则缔结的跨领域的民事家庭混合合同。[38]基于此观点,贝吉亚(Бегзиa А.М.)指出,规范代孕合同关系,应根据《俄罗斯民法典》第六条规定的民事立法类推适用原则,对其类推适用合同法与家庭法的一般规则。[39]
五、俄罗斯代孕法律制度的评述及启示
(一)俄罗斯代孕制度的特点
通过了解俄罗斯有关代孕制度的立法,不难发现俄罗斯的立法者将代孕更多地看作是一种健康保障措施,将代孕制度规定在卫生法中,旨在于符合医学的条件下开展代孕。俄罗斯的例证也进一步表明,当代孕政策符合一国的国家战略意志时,可以有效获得社会民众的支持,代孕和传统伦理观念间的冲突和矛盾也将被淡化,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一种实用主义立法态度的体现。[40]俄罗斯针对代孕问题的立法及司法实践有诸多有益经验参考。
首先,俄罗斯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亲子关系认定中的儿童权益。包括《俄罗斯联邦宪法》《儿童权利公约》《关于法院在审查涉及儿童身份案件时适用法律的问题》等法律规定,都对儿童利益进行了全面保护。同时俄罗斯司法实践不以代孕母亲的优先权固化亲子关系,而是对代孕合同、基因父母及代孕母亲三者的法益进行综合考量,最终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首要依据对亲子关系进行判定,体现了对儿童权益的尊重与保护。另外,目前俄罗斯正积极打击以代孕服务为名进行以人口贩卖犯罪的行为,将以《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一百二十七点一条第二款对贩卖新生儿的犯罪行为提起刑事诉讼,最高可判处10年有期徒刑。[41]
其次,俄罗斯对代孕合同主体进行了明确限定。《俄罗斯联邦公民健康保护法》与《关于使用辅助生殖技术的程序、禁忌以及使用限制》对代孕合同双方主体的资格进行了明确限定,要求使用代孕服务的接受方与提供方都需满足一定的资格条件;对于代孕服务接受者,需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特定医学条件;且对性别、婚姻状态有额外要求。对于代孕服务提供者,则需满足要求的年龄、生育情况、健康状况,已婚者还需取得丈夫的同意。对代孕合同主体的明确限定一方面有助于规范代孕合同的订立,另一方面有助于遏制违反法律规定的非法代孕行为。
如今俄罗斯代孕法律制度有收紧趋势,除禁止外国人在俄罗斯使用代孕服务的草案正处于国家杜马审议阶段外,也有相关人士主张进一步对商业代孕作出限制。俄参议员叶琳娜(Елена Мизулина)主张禁止代孕的商业性,强调商业代孕等同于人口贩运;同时不能完全禁止代孕,因为“在有些情况下,这种方法是已婚夫妻拥有自己亲生孩子的唯一途径”。[42]莫斯科地区儿童监察员克谢尼娅·米绍诺娃(Ксения Мишонова)则表示,俄罗斯的代孕应该退出商业领域,转到国家层面,由国家医院统一提供服务。[43]
俄罗斯代孕法律规制也存在一定不足,例如:尚未制定统一的代孕制度,司法实践均处于简单框架内执行;俄罗斯法律仅对代孕的某些方面作出规定,且其中大多数只涉及医疗方面,而法律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相关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代孕技术应用程序,未制定代孕母亲与基因父母之间合同的实质内容、合同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合同的性质,更没有为委托方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在此情况下代孕母亲可以保留孩子,也可以敲诈基因父母终止妊娠;更为重要的是,在代孕问题的卫生行政管理方面,俄罗斯并没有设置一个专门管理代孕问题的机构,代孕问题仍主要由医院处理。
(二)俄罗斯代孕规制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目前,我国部门规章对代孕虽持禁止态度,但依旧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违法代孕行为的发生,以致存在大量涉及代孕的纠纷。截至2022 年12 月27 日,笔者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相关民事案由的案件数量为348篇,从裁判年份来看,自2012年起首次出现代孕相关的裁判文书至今,代孕案件呈逐年递增趋势,至2020 年仅一年即高达134篇。①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裁判此类纠纷时往往存在定性模糊、法律适用不当、判决理由不清等问题。究其根源,是我国法律制度缺失所导致的无法可依。[44]面对我国代孕的强大需求,逃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而面对代孕技术应用已大势所趋的现实,我国可以采取有限开放代孕的制度,完善相关法律规范,做到有法可依。
俄罗斯的代孕制度对于我国代孕制度的构建有借鉴意义,但不能采用简单的“拿来主义”。面对我国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现实背景,我们应明确代孕制度构建的本土功能定位,对俄罗斯的代孕制度进行细化,在排除不适移植的部分外,借鉴其正面经验并予以完善。不适移植的部分主要是指现有社会秩序下,我国没有商业代孕的文化和制度土壤,对于俄罗斯的商业代孕模式我们应予以排除;在此基础上,俄罗斯的代孕制度核心在于限制代孕行为主体及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运行,这也是我国代孕制度构建的主要考量,有助于实现保护代孕子女合法利益的功能定位。具体而言,俄罗斯代孕制度经验对我国有如下启示:
一是合理选择代孕模式。在对中国的代孕制度进行立法构建之前,应首先明确代孕模式的选择。在俄罗斯,代孕母亲不能同时作为卵子的捐献者,这意味着代孕仅包括完全代孕这一种形式。完全代孕模式下,由委托方提供精子或卵子,之后将胚胎移植入代孕妈妈腹中,这种模式保证了子女与委托方的遗传联系,同时由于代孕母亲仅是胚胎的载体,不会产生复杂的伦理道德问题,可以说完全代孕模式是我国的最佳模式选择。
二是限定接受代孕服务的主体范围。对于接受代孕服务的主体资格,应进行合理限缩。在俄罗斯,只有特定几种医学原因造成不孕的已婚夫妻及单身女性可以接受代孕服务,这不仅可以满足社会的正当需求,也符合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我国应积极借鉴俄罗斯的经验,对不孕者合理开放代孕服务,同时也应考虑提供代孕服务主体的婚姻状态。限制代孕服务的主体范围对于保障社会稳定至关重要,若每个人都可以基于各种原因而自由自在地购买代孕服务,那么子宫就会沦为工具,儿童成为被买卖的“物”,这与代孕技术适用制度化的初衷相悖。
三是限定提供代孕服务主体的资格范围。对代孕母亲进行一定的资格限制,既是对代孕母亲的健康负责,也是对新生命负责。在俄罗斯,代孕妈妈只有符合一定的年龄、生育情况、健康情况,才可以作为提供代孕服务的服务方,已婚者还需取得丈夫同意。需要注意的是,其他无关的干扰因素,对于代孕服务的开展没有帮助,不应作为提供代孕服务主体资格的考量因素,例如提供代孕服务者的外貌、身高、性格、学历等非母婴健康关涉因素。
四是严格规范代孕合同。以往中国的司法实践对代孕合同的处理方式一般是以违背公序良俗为依据裁判代孕合同无效,这不仅忽视了委托方的生育权和代孕母亲的利益,也为代孕技术实践中亲子关系、监护权及抚养权的认定等带来了不便。尽管俄罗斯立法实践未对代孕合同进行规范,但其司法实践中将代孕合同条款作为认定亲子关系的重要考量因素,表明了代孕合同的关键作用。我国可以吸取俄罗斯的相关司法实践经验,加快提请有关代孕合同的法律法规的制定筹备工作,严格界定代孕合同的类型,同时明确双方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填补我国现行立法中有关代孕合同私法规范的空白。[45]
五是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对亲子关系的认定遵循着“分娩者为母”原则,但其中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因素,因为实践中许多代孕母亲只是履行合同义务进行代孕,目的是获得合同报酬,不能因此对其赋予更多的法律义务。[46]俄罗斯司法实践在处理亲子关系认定中,将儿童利益最大化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并充分尊重儿童的想法与意见,该做法值得借鉴。同时也应加大对非法组织代孕、贩卖儿童行为的惩治力度。
注释
①参见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217BMTKHNT2W0/index.html?pageId=ae3b3-d01ae7733efd5587d940e4d93eb&s21=%E4%BB%A3%E5%AD%95&cprqEnd=2022-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