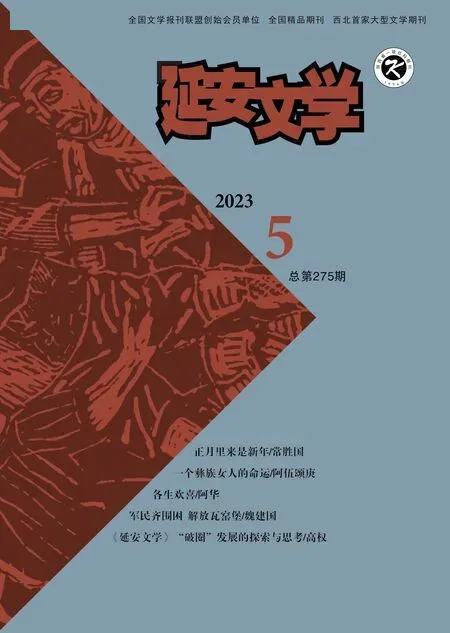星星点灯
张建华
一
这是一个从未有过的静谧的夜晚。窗外万籁俱寂,偶尔有一辆晚归的车子轻轻划过,一种细密的声音穿过重重叠叠的墙壁,悠悠流淌进来。
豆娘拥着一床柔软的鹅绒毯斜靠在床头,闭上眼,微笑了很久很久,倏然有一滴眼泪缓缓滑向鬓角,她没有伸手擦掉,任由它在鬓角安营扎寨。黑暗的屋子里回荡着郑智化的歌:“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这套音响足够完美,把郑智化的情绪渲染得恰到好处,郑智化又把豆娘的心唱得无比温柔。
她的心情太好了,这一刻,数小时之前那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五彩纷呈的舞台、令人陶醉的歌儿,所有的东西,都被短信里那五个闪闪发光的字屏蔽了:豆儿,我娶你!
短信是军哥发来的,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她的人生,自从《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以后,就像坐上宇宙飞船一样开挂了,鲜花、荣誉、笑脸,想得到想不到的都纷至沓来,最令她开心的莫过于军哥,和今夜军哥的那一条彩虹般的短信。但她绝不能表现出来,前夫狗蛋带给她的伤痕过于深刻,许多年了,她可以遇山开路逢水架桥,但感情是她的禁区或曰软肋,她压抑住内心的狂喜,生生拖了约莫一个小时才缓缓划开手机回复道:“好!”然后生怕美梦飞了,马上关了手机,像婴儿那样蜷缩起来,困倦袭来,瞬间入梦:
在豪华的酒店里,她披着婚纱,款款走向红毯尽头。舞台上,军哥和天元穿着笔挺的西服,含笑看着愈来愈近的新娘,眼里洋溢着幸福的泪花。
葱花和张吉祥、桂桂盛装出席,现场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满场的鲜花突然化作漫天的花幕,以绝美的姿态缓缓飘落,伴随着汩汩的流水声,她仿佛看见三十年前的那些时光,最痛苦的,最幸福的,一幕一幕逶迤而来……
二
“咔嗒!咔嗒!……咔嗒!”第一声响,豆娘没有在意。第二声响,豆娘的心莫名地颤了一下。她支棱起耳朵,夜是那样寂静,打火机在夜里的声音也格外清晰,她带着一些不明晰的预想,光着脚丫子懵懵懂懂地走到客厅。
丈夫狗蛋裹着被子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一张锡纸,第三声打火机显然发挥了作用,他表情迷醉地深吸一口,再吸一口。忙了一整天,没有哪个人的意志会如此坚定……傻子也懂得狗蛋在干什么了,况且豆娘跟着师父张吉祥和其他师兄弟走乡串巷,什么没听过?
她惊呆了片刻,疯了一样扑过去,拼尽全身气力一巴掌扇在狗蛋迷醉的脸上,嘴里发出喑哑的带着哭腔的嘶吼:“你干啥哩?”眼泪在她清秀的脸上喷涌而出。那一瞬间,所有的疑问都有了答案,怪不得置办婚礼用品时他动不动呵欠连天,怪不得有日子了他常常说着话就躲出去不见人影了。怪不得新婚之夜,宾客散尽,本是春宵一刻值千金的时候,他并未猴急着洗漱进洞房。明明是初夏,他却说冷要找床厚被子盖。原来,答案在这里等着她。
狗蛋缓缓睁开眼,看见豆娘那张满溢着愤怒、绝望、恐惧和悲伤的脸,慌乱地一把卷掉被子,连拖鞋都顾不上踩,光脚站在地中央,冰冷的地板照着狗蛋高大的身子和惊慌乞求的眼睛,锡纸掉在地上,一些白色的细碎的粉末和着特殊的香味飘散在空气中。豆娘不假思索,啪啪扔出去两巴掌,转身就走。
狗蛋跑过来想要拉着妻子,只是徒然伸了下手,又颓然垂下去。豆娘踉踉跄跄地进了卧室,咔嗒一声锁住了门,任凭狗蛋噗通一声跪在门外痛哭流涕。他想解释,但屋子里的灯已经灭了。
豆娘躺在床上,虚脱了一般,仿佛那三巴掌耗尽了她平生的力气。她却感到无比冰冷,无比绝望——这就是我曾经魂牵梦萦的打算作为余生依靠的那个男人吗?我怎么那么傻啊?为什么是我!
她捂着被子,哭得声嘶力竭,她心里的天漏了,女娲也补不住了。
她和狗蛋,都是张吉祥门下的弟子。豆娘学戏,虽是迫不得已,但她灵醒,一点就通,别的徒儿觉得学戏苦,会偷懒,豆娘不,豆娘自己下工夫,背本子,练嗓子,学什么都比一起去的小娃强、快。师父张吉祥对媳妇桂桂说:“这个小豆娘是个机灵娃娃,又能吃苦,嗓子又脆,只怕这一茬娃娃里头就这个将来有点出息。”
桂桂说:“嗯,我也看着行了,好好培养去,就当行善积德了。”
一年以后,父亲去世的阴影逐步散去,豆娘天性恢复,淘气十足。练功之余,爬树上房,无所不为。
这一天,豆娘和一群小伙伴在一棵树底下玩。
豆娘和一个叫红旗的小伙伴打赌比爬树。豆娘往手心里吐了一口,挽起袖子,指着一棵歪脖子树说:“就这颗树,谁爬得高算谁赢?我先上。”说着蹭蹭蹭猴子似地爬到树影里去了。小伙伴们高声叫好,狗蛋眼巴巴地看着:“豆娘,小心点,咱不比了行不行?”
豆娘:“那不行,比就要比个输赢。”一边说,一边继续往高爬。爬着爬着回头一看,太高了,脚下的树枝又太细了,嘎巴嘎巴直响,要折了,豆娘吓得目瞪口呆。这时,不知哪个孩子喊了一声:“快,师父来了!”
众孩子们一哄而散,只有狗蛋还眼泪汪汪地看着树上。
张吉祥站在树下抬头看,急得大喊:“小豆子,你这个娃娃咋不长记性呢?要摔下来可咋给你妈交待啊?”
这时狗蛋跑到树跟前,二话不说,手脚并用往上爬起来,张吉祥更加着急:“狗蛋,你个坏小子你可不敢爬哦,掉下来两个咋整!”
狗蛋一边爬一边喊:“师父,快去二牛家找梯子,我去救小豆子。”
是夜,孩子们站成一排,低着头大气也不敢出。
豆娘跪在堂屋中间,头顶着一块雕花方砖,张吉祥脸色铁青坐在太师椅上,拿着三泡台杯子一口一口抿茶,半晌,轻轻放下茶杯,冷着脸开腔。
“说,以后还爬不爬树了?一个女娃娃家,爬高上低,像个啥样子啊?”
豆娘瘦小的身子颤抖着说:“师父,我错了,饶了我吧。”
师娘桂桂走进来,端了一盘水萝卜放在八仙桌上,瞥了一眼豆娘,对张吉祥说:“军他爸,罚也罚了一个时辰了,让娃起来吧?”
狗蛋噗通跪下来,“师父,饶了小豆子吧,她小,不懂事,我这个大师哥也没有管好他。”
桂桂说:“豆娘,你可要记住啊,以后可不敢上树了,看看多危险。咱唱戏的,身子骨多金贵,师父是为了你好。懂不?”
张吉祥夹了一块水萝卜在嘴里咂摸半天,慢悠悠地喝了一口茶,低着眼皮说:“收了你,是看在你爸的份上。你妈寡妇失业的,我不忍心跟她要束脩,你再不学好,我给你妈交代不下去。下次再这么个,你回家去,我当不起你师父。”
桂桂赶紧给豆娘眼色:“快给师父磕头,说以后不了。”说着双手费力地搬着豆娘头上的青砖往门外走,狗蛋眼疾手快抢了过来:“师娘,我来。”
年轻人,难免因为一件事情就暗动了春心。况且这些常年唱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说书人,更况且男帅女美的这一对,学戏练功,眉眼往来,情愫暗生,大家都看在眼里,都觉得般配。
第一次公开表演,在东坪村,孩子们对着镜子化妆,豆娘已经十六七岁的样子,乌溜溜的眼睛充满灵气,她端详着自己的模样,抿抿嘴,又补了补眉毛。
狗蛋站在一旁,笑吟吟地盯着豆娘,小声说:“小豆子,你真好看。”
豆娘嗔怪:“哎呀师兄,这么多人,说啥呢?再说,马上出去了,还有心情说笑?我都紧张死了。”
狗蛋小声说:“放心,有我呢。”
豆娘和狗蛋款款上台,鞠了一躬,站在台中央。狗蛋拉起三弦试了试音,二人目光交汇,豆娘唱了起来。
豆娘一举一动颇有风范,赢得台下连声叫好。周围是白茫茫的雪野,戏台前面的人们都裹着厚厚的大棉袄。
演过几场,眼看过年,张吉祥给徒弟们派发了年钱,一一送走。豆娘和狗蛋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这一段分别,二人书信往来,好不柔情蜜意。
年关将近,狗蛋骑着自行车,车篮子里放着二斤猪肉,车后座上绑着一捆子粉条进了村。
一个流里流气烫着卷发穿着喇叭裤的青年拉住他。
狗蛋停下脚步:“六十,你干啥去?”
“嘿嘿嘿,大演员回家了?几时回来的?”
“回来好几天了。快过年了,这不?办点年货。”
“哦哟,好后生么。好不容易休息了,过几天哥带你去见世面去。”
“干啥去?”
六十诡秘地一笑:“嘿嘿嘿,好地方。”
狗蛋好奇:“什么世面啊这么神秘?”
六十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保证你喜得不得了。”
六十带着狗蛋去了“红又红”歌舞厅,那是一个难为人道的地方,狗蛋很快就沉迷其中了,六十和舞厅内的光头相视一笑,“干杯,这条鱼还是肥着哩!”
很快,狗蛋从一个初进舞厅怯懦懵懂的土老帽化身时髦青年,他在堂屋里摇摇晃晃抱着一只枕头跳舞,录音机的声音刺耳而尖利。
狗蛋姐姐走进来,拧着眉毛关了录音机,狗蛋从迷幻中醒过来说:“姐你干啥?”
狗蛋姐姐:“你最近着了什么疯魔了,天天打扮得跟个小流氓似的,一到黑就不见人,告诉你,少跟六十混,我可听人说那货抽大烟着哩。”
狗蛋说:“不是吧?再说了,他抽大烟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抽。”
狗蛋姐姐:“跟好人学好人,跟上师公子跳家神,反正我不许你跟他来往。”
狗蛋刚刚尝到了灯红酒绿的味道,哪能片刻就醒来?他狠狠地摔门而出:“烦死了!一天唠叨。”
新婚之夜,却成了豆娘和狗蛋婚姻的忌日。狗蛋在门外跪了一夜,他知道自己已经陷入死地。
天亮了,豆娘和狗蛋的婚房门被三个戴着大盖帽的人敲响,狗蛋蓬头垢面地跟着警察离开了那个他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梦。豆娘始终没有开门,她的心在昨夜死去,无法复原。
母亲葱花不是没劝:“死女子啊,让你小心挑选你就是不听,好看顶啥用啊?你看你现在死不死活不活叫庄里人不笑话死了?”
豆娘也不是没反抗,家门口有座刚修的大桥,七米,她毫不犹豫地跳下去了,大腿粉碎性骨折,在床上躺了三个月,不容易恢复。趁家人不注意,她悄悄来到桥下,眼看着水快没过头顶了,一个钓鱼的大叔发现了她,连吼带喊,一群人跳下水把她劫持上岸。
既然死不成,那就只有好好活下去一途了。村子里是流言集散地,豆娘的故事不胫而走,豆娘憋住一口气想要活出个人样来,给那些目光和声音看看。她快刀斩乱麻,坚决和狗蛋离了婚。从此,戏台成了她的家。
三
豆娘怎么就学了戏呢?这就说来话长了。几乎所有生在陕北的女娃,都有一间回忆中的窑洞,豆娘也不例外。
一个简陋但特别洁净的窑洞里,一盏油灯闪烁着,火苗映在一个怀孕的女人脸上,显得特别祥和。女人面前放着一张炕桌,桌子上放着剪好的窗花和一沓红纸。炕的另一边,一个男人打着呼噜睡得正香。女人偶尔抬头看一眼男人,抿嘴笑笑,偶尔低头看看自己的肚子,一双粗糙的手摩挲着。窗外,天空幽蓝,明月慈祥……
鸡鸣三更,女人悄悄爬起身,轻轻点亮油灯,披衣翻身下炕,捅开煤炉,又费力地提出一壶水坐上去,蓝色的火苗很快冒起来了,透过炉圈缝隙呼呼地闪烁着。男人来成被吵醒,翻身爬起,揉着惺忪的睡眼看着媳妇:“葱花,不再睡一阵了?你别动,我来弄。”
葱花莞尔一笑:“不了,鸡打鸣了,我给咱冲个鸡蛋花吃。炕热乎乎的,你再睡会儿,做好我叫你。”
来成要下炕,女人歪着头嗔怪地盯着他看,男人只好重新钻进被窝:“好,好,你都快生了,还这样操心,快把我惯坏了。”葱花一边麻利地拿出两个馍,一黑,一白。女人拿出一张报纸铺在炉子边上,把馍烤上去:“你多歇歇还要去下井,我在家又没啥事。吃了再睡阵子。窑下太苦了。”
来成去了矿上一个月,把准日子头又请假回了家。
农村女人怀着娃劳作不停,豆娘出生就比较顺利。葱花仅费了一身臭汗,豆娘就痛痛快快呼哧一下来到了人间。村西的麻婶站在炕沿边,剪断脐带,倒提着婴儿拍打两下,一声响亮悦耳的婴啼惊醒了早晨的村庄,门前的枣树上,一层雪被豆娘的第一声歌谣惊得扑簌簌摇落一地,一只早起的麻雀翅膀一划险些掉下树枝去。
麻婶在屋里喊:“来成啊,是个女女,看这声嗓。”
来成有些失望地撩开厚厚的拼花门帘走进了,接过麻婶手里刚刚包好的孩子,心疼地看了看媳妇。葱花欢喜又歉疚地看了一眼男人,慢慢垂下眼帘。来成见状赶紧说:“女女好,女女俊,像她娘。”吧唧一口亲了上去。
麻婶笑眯眯地看着夫妻俩,揭开产妇的被子看了看又掖好被角:“来成子,要勤着些给换炉灰啊,不要叫湿着凉着,月子病遭下了可麻烦得很。我走了,对了,看这娃娃俊眉修眼的,就叫个豆娘吧,名字贱好养。”一边说一边往外走。
来成赶紧给娘俩熬小米粥。陕北的新小米,熬了粥是最有营养的,喝了粥,再吃了大公鸡,葱花的奶水就像储量丰富的油井采也采不完,把个豆娘养得白白胖胖,人见人爱。出了月子,葱花忙忙催着来成回矿上,怕请假时间太长丢了差事。她一个人洗洗涮涮,把家里家外搞得井井有条,日子真是有声有色。
来成下了矿,难免有些脏猫烂狗瞄上葱花这棵鲜嫩嫩的身子。比如,夜里葱花坐在炕上,怀里抱着胖乎乎的豆娘,豆娘抓住自己灵巧的小脚丫,欢欢实实吃着奶。冷不防村里田二就推开门进来了,也不说话,眼睛贪婪地看着葱花白格森森的胸脯子,葱花厌恶地皱眉往后挪。
见葱花不言语,田二涎着脸说:“豆花娘的,我来成哥下窑也有日子了,你不想他吗,嗯?”
葱花白了一眼,壮着胆子说:“驴槽里伸出个马嘴,关你屁事,滚出去。”
田二凑进一步:“嘿嘿嘿,豆花娘的,其实我也不比来成哥差,不信你试试?”
葱花一把抓起炕角的笤帚,指着田二说:“我忍你不是一天两天了,再骚情我告诉我家来成,狗腿子给你砸折。滚蛋!”
田二讪讪地缩着脖子出去了,嘴里说:“这婆娘,急啥呢,谁用还不是个用?拔了萝卜坑坑在呢。嘿嘿,好白净的奶子啊。”
葱花红着眼放下孩子,一脚跳下去扣上门栓,再把顶门杠顶着门扉,眼泪哗地淌下来。好在有邻家大妈经常支起耳朵护持着,且来成囫囫囵囵在人世间,这种桥段顶多恶心人一下,在农村也不算大事,谁也不敢欺人太甚。
老百姓的光景,大多这样,谁家的炕头没有三寸灰呢?苦日子甜日子,都难起什么波澜。就在这一平如镜的岁月中,豆娘四岁了,水格灵灵的大眼睛,一笑起来弯弯的。
秋收毕,村里请了大戏,台上演员们披挂上阵。豆娘睁着滴溜溜的眼睛好奇地掀起后台的帘子,看里头的演员们来往穿梭、化妆打闹,眼神充满了羡慕。
台下村民们有纳鞋底的,有缝衣服的,有织毛衣的,有嗑瓜子喝烧酒的,不时一叠连声地叫好。小豆娘被一阵叫好声吸引到台前,眼神大胆地盯着俊俏的男演员看半天,又趴在戏台边沿盯着女演员的一举一动,一时入了迷。来成嗑着瓜子,笑盈盈地看着女儿。
有村民支着耳朵听戏,嘴里不闲着:“来成,你狗的枪法太准了,听说咱葱花嫂又怀上了?啥时候生?”
来成笑:“快了,个把月就生了。”
六花嫂子呲着牙,手下的麻绳拉得呲呲响:“人家娃都快生了问这话?正月十五贴门神呢——迟了半年。不过来成子,我看你婆姨腰细肚子尖,恐怕这胎是个儿。”
来成低头笑:“休管儿了女了,健康就行。我们老人都殁得早,家里人少,太孤了。”
又一个人接话:“不过在咱农村里,还是得有个儿,顶门立户看家护院的,你长年在窑下,葱花还得有帮手。”
村东头的秃头老汉远远丢过来一句:“对啊,要不然有些猫啊狗啊的容易上房。”
村民们哄堂大笑。来成有点恼:“闭上你的狗嘴,你家婆姨房顶上才有猫狗。”
豆娘依然入迷地趴在台沿看着演员们唱念做打,在那一刻,周围的世界在她小小的眼睛里隐身了。
豆娘的弟弟天元在一个枣子压弯树枝的清晨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啼来到人间。来成喜得眉开眼笑:“哈哈哈,我有儿子了!老子有儿子了!”
有苗不愁长,眨眼工夫,天元也呼啦啦满地跑起来,一儿一女赛神仙,来成和葱花两口子的人生巅峰如此简单,外人羡慕得直咂嘴。
这个春天,山凹凹的杏花开得格外好,一嘟噜一嘟噜地把整个山都染成了粉色,香气在空气中飘来荡去,这样的日子自然能使所有的人都很愉快。豆娘和天元在院子里追来追去,一条黄狗卧在门边,几只鸡咕咕咕咕在院子里觅食。天元大鼻涕淌在下巴上,嬉皮笑脸看着姐姐。春种已经结束,没有什么活路,葱花坐在院子里纳鞋底,慈爱地看着孩子们玩闹,一切都那么美好。
美好的东西总是难以长久,就在这时光静好,他们那破烂溜丢的大门突然哐嘡一声响,队长的儿子长生急急慌慌闯进来了大喊:“葱花——葱花,快收拾东西,赶紧去矿上。”
葱花的心别地一跳,每一个矿工家属都有着故意忽略但不得不面对的恐惧,她故作镇静地说:“狗撵上来了?咋了么长生?”
长生说:“来成子可能出了点事,具体还不知道。我在小卖部刚接的电话,矿上派来个车,正在村口等着呢。”豆娘和天元闻言停了下来,葱花愣怔片刻说:“好好好,走,走。”拉着一双儿女就往外跑。
葱花眼睛浮着泪花,焦急地看着远处。路边是已经收割过的庄稼地,不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几只乌鸦呱呱地叫着飞过田野。
到了矿上,车还没有停稳,葱花已经跳下车,抱起天元,跌跌撞撞往窑口跑过去,豆娘懵懵懂懂跟着娘跑,鞋子跑掉了一只,也顾不上捡。
葱花一边跑一边哭:“来成,来成啊!来成我来了。”她的脚步踉踉跄跄,头发被山风吹得凌乱不堪,活像一只骤然失水的葫芦。矿井周围乱成一锅粥,哭的、喊的、闹的仿佛戏台开了锣,医生和救护人员来往穿梭,五花八门,一个穿着齐整、干部模样的人看见葱花,伸手拦住她说:“别往前凑,耽误救人。”
葱花哭着问:“我家王来成还活着不?”在等待宣判的那一刻,她的喉管是痉挛的,捏着嗓子不敢呼吸,仿佛一动喉结,王来成就被自己判了死刑。
干部面无表情地打开一本册子说:“死了十个,张大毛,周红旗,钱三蛋……没有王来成,那就好,没死,暂时活着,送医院了。”
葱花瞬间长出一口气,被自己的骤然而至的口水呛着了,她闭了闭眼睛,喘微微地问:“去哪个医院了?严重不?”
干部又看了看花名册说:“现在还不清楚。”
葱花扭头就走。豆娘跟在后面跑:“娘——娘——”葱花伸手拦住一辆三轮车,一把将女儿捞上来。
医院不大,很快就找到来成的病房。病房里住着十几号人,靠窗一张小床上,来成浑身裹着绷带,昏昏沉沉躺着,一条腿被锯掉了,包着厚厚的纱布。葱花远远看着来成的断腿,一时不知道作何反应,两行眼泪呼啦啦碾过她失去水分的脸庞,怎么擦也擦不干。豆娘惊恐而无助地看看床上的爹,再看看娘一行一行落下的眼泪,忍不住哇地哭了。
葱花被女儿的哭声惊醒,一手抱着天元,一手揽住女儿的小脑袋,哑着声音叫,“羔羔啊,咱娘儿们以后可咋办啊?”
豆娘哭着抬起头:“娘你别哭了,豆娘以后都听娘的,豆娘帮娘干活,帮娘带弟弟。”
四
来成躺在炕上,两眼无神地看向窗外,那些火红的大枣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抬了抬手臂想揉揉眼睛,可手臂无法动弹,他无声地啜泣起来。
葱花挑着一担水走进屋子,提起桶子哗哗地把水倒进水缸,拿手抹了抹额角。
来成假装睡着了,睫毛颤巍巍地抖动着,眼泪无声无息流着。葱花爬上炕看看丈夫,泪花泛上来,她强忍着拿起毛巾,轻轻地擦去丈夫的眼泪。
来成闭着眼睛说:“葱花,对不起,我成了废人了,成累赘了。”
葱花摸摸男人的头:“会好起来的,有你在,我就能撑住。”
来成哭:“不如让我死了算了,我活着有什么意思?”
葱花泣不成声:“来成,来成,不敢这么想。你要往宽处看,前十年你养活我和娃娃,后十年我来养活你。你一定好好活下去,只要你活着,我们什么都不怕,你放心,我一定把娃娃们好好拉扯大。”
葱花要强,缝补浆洗、上山下田,样样不肯落于人后,村上的人没有不敬佩的。
再一晃豆娘十岁了,她和八岁的弟弟抬着硕大的水桶从河边走回家,一桶水晃到家已经把大半桶洒在路上,豆娘暗暗咬着牙不吭声,转身挑起空桶出门了。
看看水缸满了,豆娘擦了一把汗,快手快脚地喂了猪和鸡,踩着小凳子和好了面,面粉洒了一案板。她嘘了一口气,搬过小凳子放在门外,又搬出一把靠背椅子当桌子,又把炕桌拿院子里,拉过弟弟天元,姐弟俩认真写作业。
来成靠着被子斜躺在窗前,失神地看着门外的天空。屋子里干干净净,安安静静,昏暗的光线斜照在屋子里的地上。
葱花进了院子,已经晒黑的脸上充满疲惫。豆娘看见娘,赶紧站起来端出一杯水说:“娘你回来了,快喝口水。”
葱花倦倦地说:“写作业吧,玉米总算是点完了。娘歇口气再做饭。”
豆娘递上板凳:“娘您歇会,我和了面,咱们吃面条吧。”
葱花坐在门口喝完水,站起来进屋看看来成,出来去了厨房。看见矮小的女儿踩着小板凳费劲地擀面条,热气充满了屋子,也盖上了葱花的眼帘。
她拿掌心抹了一把眼,快手快脚剥了两三根小葱,舀水冲洗切好,端掉滚水锅放到角落盖好,拿出小铁锅坐上,把小葱扔锅里。油太少,锅里很快有些焦味飘出来,呛得她咳嗽起来,她赶紧掂起水壶倒下去,呲啦一声,锅里浮起一些油花花。她盖上锅,豆娘的面已经擀得又薄又圆,她的眼泪瞬间又冒出来,她赶紧抹掉,伸手摸摸女儿的头,“羔羔去院子里写作业,我下面,做好了先给你爸晾上。”
饭很快熟了,豆娘搬出小桌子,摆好凳子,舀出一碗拿到窗下,拿一只网罩扣下晾着,然后依次给母亲、弟弟和自己盛了饭。农家饭的香味和袅袅飘散的炊烟注定成为豆娘余生最幸福的回忆之一。
来成已经可以自己拿筷子吃饭了,他斜靠在被子上,艰难地慢慢把面条送到嘴边。葱花和孩子们也呼啦呼啦扒饭。葱花看了看发黑的墙壁和墙上的裂缝,若有所思。
吃毕饭,她放下碗筷,豆娘麻利地开始洗碗。葱花说:“豆儿,妈去找找你长生叔,让他找人给咱修修屋子吧,太破了。去年夏天就漏得厉害,眼看马上又到雨天了。”
豆娘:“嗯,娘你去吧,家有我呢。”
五
地震在这个山圪崂里是并不常见的事情,所以谁也没想到这个午后,来成会永远告别这个世界。
早晨上学的时候,天元看见天上鱼鳞一样的云彩莫名觉得害怕,他一边追着姐姐小跑,一边气喘吁吁地问:“姐姐姐姐,这都好几天了,为什么天上的云彩看上去怪兮兮的?还有,咱家大黄这些日子也怪,动不动就大声汪汪。”豆娘一边急急慌慌走路,一边说:“云彩嘛,啥样的都有,问那么多干啥?狗就是叫的,不叫还叫个狗吗?快走,迟到了。”
教室坐落在半山坡上,只是一个小小的院落,没有院墙,早操的钟声悠悠飘来,远远传来羊叫声,和钟声构成奇妙的和谐。卷毛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春天来了。
他扫视一圈教室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吗?春天来临的时候,桃花、杏花、梨花都会相继开放,可好看了。”
豆娘认真地听着,眼神热切而机灵。
教室里,前面坐着豆娘班上的十几个孩子。后面坐着低一级的天元和十几个孩子。天元班上的同学在悄悄写作业,等豆娘班级下课以后,再给他们上课……
放学的钟声一响,豆娘姐弟俩蹦蹦跳跳走出教室往家赶。山路弯弯,河水清清,小草刚刚萌发,茫茫的田野上,一群小学生就像洒落在塬上的豆子。孩子们互相打闹着,就像麻雀窝里被捣了一杆子。毕竟是孩子,豆娘一边倒退一边笑嘻嘻地看热闹。突然,有一个孩子捡起一块石子,嗖地一声向对手袭去,不料准头不对,石子照着豆娘的面门飞来。豆娘连忙闪身一躲,刚下过第一场春雨,山路湿滑,她毫无征兆地滚下坡去。
天元惊恐的哭声引来了周围的村民,葱花赶到医院的时候,只见豆娘头上裹着厚厚的纱布,昏迷不醒。葱花欲哭无泪地说:“大夫,我娃咋样?”
大夫说:“从片子上看,伤着丘脑了,长不高了。而且,后脑勺部位伤口太深,娃娃小,愈合快,但伤了脑子,以后恐怕念不成书了。”
葱花无声饮泣:“老天爷啊,瘸腿上拿着棍敲,这可咋办呢么!”
来成斜靠在被子上,脸上干干净净,眼神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突然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呛得他脸都紫了。门外的黄狗汪汪汪狂叫起来,引得村里的狗叫成一片,来成艰难地朝窗外看去,只看见天上又有大片大片像鱼鳞一样的云彩,看上去有些吓人,他心里莫名跳了几下。
来成自语:“狗日的,好几天了,这鱼鳞云都不散,怪道了。”
路两旁,农人们正在忙着春种,山桃花这里一丛,那里一棵,布谷鸟叫得人们心烦意乱。突然,大地一阵晃动,田里有人大叫:“天啊,快了不得,地震了!”
天空瞬间布满阴云,炸雷接二连三,雨点哗啦啦打了下来。葱花,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她也顾不上自己,爬起来跌跌撞撞往家的方向跑。
葱花没有飞毛腿,她赶到的时候,房子已经坍塌成一堆废墟,天元浑身灰土,惊恐地扑进母亲的怀里,葱花瞬间天旋地转晕倒在地。
缘分这东西,端的是奇妙。来成和葱花,就这样天人永隔。
一座新坟立在桥下,桥头的杏花在晴空下轻轻发抖。豆娘头上还缠着纱布,目光忧伤地跪在坟头,葱花麻木跪在一旁,左手一个右手一个搂着自己的儿女,没有眼泪,也没有语言。
政府行动很快,屋子是立刻建起来了,但人没了。葱花在新建的瓦房面前恍惚了许久,突然放声大哭,这辈子她哭了许多次,只有这一次的眼泪令她永世不忘——这一次大哭,是一个女人对过去苦难的哀悼和对未来苦难的决心。
一对儿女嗷嗷待哺,她是母亲,和所有的母亲一样,除了坚强,她别无选择。
豆娘伤了脑子没法读书,葱花就带着她投奔张吉祥。张吉祥是远近闻名的说书人,手下弟子三十,各个身怀绝技,十里八乡无人不知。
张吉祥坐在一把旧太师椅上,打量着葱花和豆娘。葱花把一小袋黄米放在八仙桌上。豆娘睁着滴溜溜的眼睛四处打量。
葱花说:“张师傅,我寡妇失业的,这个娃娃命也不好,前阵子把脑子摔坏了,大夫说念不成书了。求您收下她,给条活路。”
张吉祥长叹一声:“唉。”
葱花拉过女儿:“豆娘来,给师父磕头。”
豆娘跪倒在地磕三个响头。
张吉祥说:“起来吧,学戏的规矩你们得守。”
葱花说:“那是,我们豆娘肯定听话。”
张吉祥说:“可苦哩,能受?”
豆娘说:“师父,我能行。”
张吉祥拉过桌上红印泥,用食指沾了一下,轻轻在豆娘额头按了一个印,对葱花说:“回去吧,来成家的,娃娃放我这,放心。”
豆娘的人生,就是从这个戏台衍生的。
离婚后,她比以前更刻苦,很快成了名家,一群师兄弟和师父吉祥一起,心甘情愿做了她的配角。陕北这个地方,别的没有,天然气和石油就像是自家的后花园埋着的金锞子,一旦被发现,所有人的命运都变了。2005 年,张吉祥的儿子军哥开了煤矿,赚了个盆满钵满。
狗蛋失去的,军哥悄悄地看上了,张吉祥和桂桂自然乐意。
又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将在这个春天的夜里悄悄启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