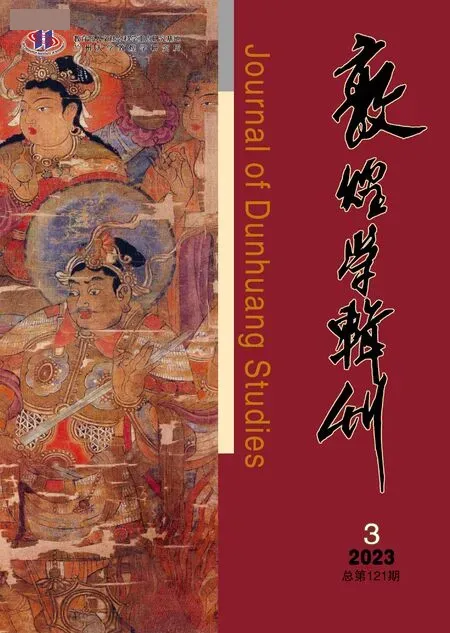汪宗翰与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早期流散
陈双印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清末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随着被誉为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四大发现之一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偶然被发现,藏经洞文物外流也随之开始。
《重修敦煌县志》载,藏经洞发现后:“中藏经卷累累垛积,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亦有不携回者。”(1)吕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0页。总之,藏经洞文物被发现后的情形,正如王冀青所言:“实际上,自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初起,藏经洞文物便已经进入了四处流散的进程。”(2)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0页。是不争的事实。
“敦煌卷子最初的流传,一般都以为是由于斯坦因的搜购,其实在他未到敦煌以前,这些卷子已经零星地传布于世了。最初得到这些经卷和画旌的,有叶昌炽、汪栗庵、恒介眉、张又履、张筱珊等人。”(3)苏莹辉《敦煌石室和敦煌千佛洞》,中国台湾《“中央”日报》1965年3月31日(5)。以上苏莹辉所举最早得到藏经洞经卷和画旌的叶昌炽诸人,都是敦煌藏经洞文物发现之初,在甘肃任职的地方官员。这几人当中,尤其是曾任敦煌知县近四年之久的汪栗庵暨汪宗翰,因为近水楼台的缘故,无疑是在斯坦因、伯希和等欧洲探险者成功盗买藏经洞文物,捆载西去之前,在甘肃地方官员当中,得到藏经洞文物数量最多的人物之一,并且因为藏经洞发现之初,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为和敷衍的封存,造成了洞内大量文物流散海外,汪宗翰应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受叶昌炽之托搜集敦煌县内碑拓简牍等古物
汪宗翰,原名汪耀祖,“翰”一作“瀚”,字栗庵,湖北武昌府通山县人。光绪己卯(1879)科举人,庚寅(1890)恩科会试二甲第一百二十四名进士(4)朱鳌、宋苓珠《清代进士传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第3册,第1889页。。中进士后先是被钦点主事签分吏部,1893年授侍中,1896年调任甘肃镇原知县。此后便一直在甘肃做官,先后任镇原县令、华亭县令、主管甘肃行省乡试内帘考官,光绪二十八年(1902)农历3月改任敦煌县令。
1902年4月28日,汪宗翰从邬绪棣手中接过知县大印,成为新的敦煌县令,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九日卸任。汪宗翰担任敦煌县令近四年,不论是与其之前几任陈问淦、严泽、吴绪棣,还是后来的黄万春、王家彦相比,汪宗翰是任敦煌知县时间最久的。
进士出身的汪宗翰,其文化水平自是不用怀疑的,关键是他还善诗文、懂金石、精通书法。汪宗翰曾为莫高窟千佛洞撰写的楹帖:夏无酷暑冬不奇寒四季得中和景象,南倚雪山西连星海九州寻岳渎根源,受到了曾担任甘肃学政的著名金石学家、学者、藏书家,同样是进士出身的叶昌炽“非俗吏之吐属”(5)[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7册,第4286页。的较高评价。斯坦因“在著作中提到汪氏时,总是冠以‘有学者之风的’或‘博学的’一类形容词”(6)金荣华著《敦煌文物外流关键人物探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66页。,可见其学识确实不赖。文人出身的汪宗翰,与一般俗吏不同之处,也从另一件事上表现出来,就是他更懂得历史文化遗存对于彰显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刊立古阳关石碑,以志遗迹”(7)[清]佚名撰《敦煌县乡土志》卷2《历代沿革·疆域》,甘肃省图书馆藏手抄本。,这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行为。
早在京城之时就曾得到过敦煌县内石碑拓片的甘肃学政叶昌炽,托汪宗翰替其搜求敦煌辖境内的各类碑拓。叶氏不但是比汪宗翰早一年的进士,更是时任主管甘肃一省文教的学政,何况所请托搜集的碑拓,就在汪宗翰的辖境之内,汪知县岂有不答应之理。汪知县上任不久,就对叶氏的请托有了回报。叶昌炽在其所著《语石》里记载:“敦煌县千佛洞,即古之莫高窟也。洞扉封以一丸泥,十余年前,土壁倾堕,豁然开朗,始显于世。中藏碑版经象甚夥。楚北汪栗庵大令宗翰以名进士作宰此邦,助余搜讨,先后寄贻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画象》,写经卷子本、梵叶本各二,笔画古拙,确为唐经生体,与东瀛海舶本无异。又诸墨拓中有断碑仅存两角。”(8)[清]叶昌炽著,姚文昌点校《语石》,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0页。
据《清史稿·职官志三·县》载:“县,知县一人。正七品。……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猾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都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9)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357页。可见,作为一县百姓父母官,知县的权力是很大的,阖县官民谁不巴结逢迎。
有文化修养,有收藏古物的喜好,又受人之托搜求碑拓之物,加之手中有权,汪知县在敦煌县境内搜求碑铭古物,可谓是如鱼得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之便。
二、汪宗翰敦煌文物收藏品来源
早在汪宗翰出任敦煌县令一年多以前的“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0)陈双印《莫高窟王道士〈催募经款草丹〉再考》,《档案》2022第9期,第32页。有关藏经洞发现的时间,有1885年、1886年、1899年、1900年几种说法,见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25-29页。,藏经洞文物就已被偶然发现并开始外流(11)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25-29页。。传言王道士就曾送给时任敦煌县令严泽一批藏经洞经卷,1900年12月7日卒于任上的严县令,生前只“手存二卷”。由此看来王道士所赠经卷,严县令“竟然没看出手中经卷的历史分量,根本没当回事”(12)张翠萍《敦煌悲天》,《山西档案》2001第6期,第33页。,笑纳的不是很多。继任敦煌知县的邬绪棣,“似乎没有收藏藏经洞文物的记录”(13)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31页。,但这并不能证明他手中没有藏经洞文物,只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线索而已。
与前两位不同的是,汪宗翰文学底子很好,懂得欣赏,自己收藏简牍书画等古物,又受叶氏请托搜求敦煌境内碑拓等。王道士结交这位同乡知县的得力之物,自然是藏经洞出土的佛经和绢画等古物了。正如王冀青指出的,“汪宗翰和王圆禄是湖北同乡,两人多了一层关系,比较容易沟通。所以,王圆禄很快就将藏经洞发现之事告诉了汪宗翰,并不断给汪宗翰选送藏经洞文物”(14)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32页。。荣新江也指出:“他是王道士同乡,所以王道士把一些很好的经卷和绢画送给了他。”(15)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第2期,第25页。因此,汪宗翰手中的藏品来源之一,来自于王道士的多次馈赠。在汪宗翰长达近四年的任职时间里,王道士究竟赠送了多少藏经洞文物,已成为永远无法搞清的谜,但是数量一定不少,这是毫无疑问的。
汪宗翰手中藏经洞藏品的另一来源,主要来自于敦煌地方官绅的馈赠。“王道士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面对这么多古代的经本和画卷,当然也知道它们的‘价值’。他不断拿出一些书法精美的佛经写卷和漂亮的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过往的官僚士大夫们,以换取一些功德钱”(16)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第25页。。因此,敦煌当地很多官绅手中或多或少都收藏有藏经洞文物。正如施萍婷所言:“自从藏经洞文物出土以后,至斯坦因、伯希和东来之前,王道士又是送给官府又是送给财主,‘自有不少流入达官贵人以及当地人士之手’(向达先生语)”(17)施萍婷《敦煌研究院藏土地庙写本源自藏经洞》,《敦煌研究》1999第2期,第41页。。而敦煌知县汪宗翰,好古,又搜集碑拓简牍绘画等,“上好是物,下必有胜者矣”(18)[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疏《礼记正义》卷55《缁衣第三十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576页。,这就难免有人会投其所好。所以,汪宗翰的收藏,不排除其中的一部分来自于敦煌当地官绅的馈赠。
汪宗翰手中藏经洞藏品的第三个来源,应来自两次莫高窟之行的拿取。第一次,徐珂《清稗类钞》记载,壬寅(1902)许伯阮游敦煌,见“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19)[清]徐珂撰《清稗类钞》第9册《鉴赏类·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197页。。王冀青指出许伯阮“提到的‘某县令’,应指汪宗翰”(20)王冀青《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文史知识》2016第16期,第16页。。《重修敦煌县志》收录的《千佛洞古佛经发现记》一文记载,藏经洞发现后,王道士“即时报知地方官,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当时人亦不之重也。有携回一、二卷,也有不携回者,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21)吕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第40页。。王冀青对此提出质疑并指出:若在藏经洞甫一发现的1900年即时报官,当时的敦煌知县应是严泽,“汪宗翰是1902年四月才上任的,他第一次检查藏经洞文物的时间,只能是上任后不久。但不管怎么说,这段记录暗示,王圆禄在1902年肯定向汪宗翰报告过藏经洞之事。而第一个关注藏经洞发现之事,并对藏经洞文物进行全面检查的敦煌县知县,还应该是汪宗翰”(22)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32页。。另一次是光绪三十年(1904)汪宗翰负责检点藏经洞时的顺手牵羊(23)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5页。。早期流散在外,后归江西蔡氏收藏的一件藏经洞出土的《唐画大士像》上,汪宗翰的亲笔题识:“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翰谨记”(24)汪宗翰的题识,系本文作者根据邹安主编《艺术丛编1》第1至4期,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345页插图上的文字释读。(图1),证明卫聚贤因从王道士处取去若干写经及画像此说不诬,因此,借着检点藏经洞文物的机会,以“迎归署中供养”的名义,顺手牵羊,汪宗翰又得了数量不少的藏经洞藏品。

图1 汪宗翰藏《唐画大士像》(采自邹安主编《艺术丛编1》第1至4期,第345页图)
三、汪宗翰手中藏经洞文物知多少
汪宗翰在担任敦煌知县的近四年时间里,通过不断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地方官绅的馈赠,以及两次检点藏经洞文物时的肆意拿取,手中集聚了数量不少的藏经洞文物。
徐珂《清稗类钞》一书中记录:“壬寅,许伯阮游敦煌,得唐人手书藏经五卷,出而语人曰:‘石屋分内外,内屋因山而筑,有六十六穴,穴藏经四五卷,别无他物。外屋石床一,左铺羊毛毡,尚完好,右铺线毡,已成灰。床下僧履一双,色深黄,白口,如新造者。中一几甚大,金佛一尊,重约三百两。金香炉大小各一,大者重百余两,小者二三十两。大石椅一,铺极厚棕垫。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后为大吏所知,遣员至敦煌,再启石壁,尽取经卷而去。闻县令取佛炉,悉熔为金条,以致唐代造像美术,未得流行于世,惜哉!’”(25)[清]徐珂撰《清稗类钞》第9册《鉴赏类·伯希和得敦煌石室古物》,第4198页。
《清稗类钞》中提到的许宝荃,字伯阮,为时任陕甘总督崧蕃幕僚。他在壬寅年(1902)游敦煌,亲眼目睹“县令某携佛炉而去,又取经二百余卷”,许伯阮所说某县令就是汪宗翰,他也得到了唐人手书藏经五卷。说明这次许伯阮游览莫高窟千佛洞时有汪县令陪同,仅汪宗翰一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从藏经洞拿走了数目惊人的200余卷经卷和佛炉等物。
《重修敦煌县志》中“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的记载,与《唐画大士像》绢画上汪宗翰的题识“甘肃敦煌县千佛洞宋初石室所匿唐画大士像光绪卅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毕迎归署中供养信士敦煌知县汪宗翰谨记”,所述内容十分接近,故两者所记应该指的是同一件事。依据《唐画大士像》上的题识,汪宗翰检点藏经洞的时间是光绪卅年四月朔日暨公历1904年5月15日。汪宗翰此次莫高窟之行,究竟拿走了多少经卷和佛画,我们已经没法搞清。不过,《唐画大士像》上的题识表明,汪知县以“迎归署中供养”的幌子,顺手拿了一部分藏经洞文物却是事实。
叶昌炽在壬寅年(1902)七月初二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得敦煌令汪君宗翰第二函,颖芝莲溪之友,以吏部改官作令,签掣镇原,调补边缺,颇悒悒不得志。”(26)[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14年,第6册,第3763页。心情抑郁的汪宗翰到敦煌上任后,“欲通过叶昌炽改善自己‘悒悒不得志’的处境——‘调省’任事”(27)蔡副全《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敦煌研究》2011第2期,第98页。。卫聚贤指出:“叶昌炽(苏州人,于民国二十五年左右病故)于光绪二十八年为甘肃学台,对于古物亦好,托汪宗翰搜讨。汪宗翰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观音象,写经卷子本、梵页本各二’送给叶昌炽了(见叶著语石卷一第二十九页)。”(28)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7页。从1902至1906年叶昌炽任甘肃学政期间,恰好也是汪宗翰任敦煌知县的时间。汪宗翰除了数次寄信给叶昌炽外,还多次寄赠大量唐元石刻碑拓和敦煌经卷、佛画。据蔡副全最新统计,汪宗翰只送给叶昌炽千佛洞藏经洞出土文物,就包括绢画《水陆道场图》《水月观音象》各1副,《大般涅槃经》4卷,梵文写经31叶等(29)汪宗翰所赠叶昌炽敦煌文物种类和数量,依据蔡副全发表在2011年第2期《敦煌研究》上的论文《叶昌炽与敦煌文物补说》中的数据统计得出,特此说明。。
罗振玉在《沙州石室文字记》里披露了一件汪宗翰送给同年陆季良的绢画,“光绪戊申,同年陆季良示余甘肃敦煌县令汪宗翰所遗后唐天成四年已丑岁五月廿九日樊宜信造《药师琉璃光如来象》,绢本,长三尺许。笔意古拙,彩色鲜明。其所题记文皆右行,盖千佛岩莫高窟物也”(30)罗振玉《沙州石室文字记》,罗振玉编纂《敦煌丛刊初集六·敦煌石室遗书百廿种》,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41页。。这件《药师琉璃光如来像》绢画,经荣新江考证,就是王惠民发表在《敦煌研究》1999年第2期《日本白鹤美术馆藏两件敦煌绢画》一文里介绍的第一件《药师说法图》(31)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8页。。
在陕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考察中,发现了文物单位收藏的属于藏经洞早期流散部分的21种敦煌写经,根据题识可以辨认出其中的多数,是徐锡祺在1905年7月至1906年5月署任安肃道道台时,为时任敦煌知县汪宗翰赠送的精美长卷佛经。据王庆卫推测,汪宗翰任敦煌县令时的送礼对象,除了叶昌炽、徐锡祺以外,应该还有在徐锡祺之前任安肃道道台的和尔赓额、崇俊两人。但他又引用王冀青的观点,认为1904年在汪宗翰检点藏经洞文物后,命令王道士将藏经洞文物封存并负责看守。王道士便在藏经洞门口安装了一扇木门,加装了锁具,直至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一直如此。因此,从这种状况来看,在1906年5月后署任安肃道道台的崇俊基本没有机会再从汪宗翰处得到敦煌写卷(32)王庆卫《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以西安地区藏品为中心》,《敦煌研究》2019年第5期,第134-142页。。其实汪宗翰早已通过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官绅的馈赠以及检点藏经洞文物时的恣意拿取,手中拥有了数量不少的藏经洞文物。藏经洞文物封不封存,都不会影响到汪宗翰用手中的藏品送礼。之所以没有给崇俊赠送藏经洞文物的原因,是依据《重修敦煌县志》记载,早在崇俊接任安肃道道台的1906年5月之前的3月份(33)吕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第40-42页。,汪宗翰就已离开敦煌,调往省城兰州任事了。
王冀青先生经过研究,认为:“可以推断,汪宗翰为了同样的目的,也应给其他‘大吏’或上级官员送过藏经洞文物。”(34)王冀青《藏经洞文物的发现与流散》,《文史知识》2016第16期,第17页。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可以确定汪宗翰仅在敦煌知县任上,至少曾经给叶昌炽、陆季良、许宝荃、和尔赓额、徐锡祺等人赠送过藏经洞文物。不过,汪宗翰极有可能给何衍庆、侯葆文也有赠送。因为前者不但是1904年汪宗翰任敦煌知县时的顶头上司——安西直隶州知州,更是安肃道道台和尔赓额派来敦煌复查采买粮事件(35)有关“敦煌采买粮事件”详细情形,请参阅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3期,第60-76页;郭胜利《敦煌抗粮事件与清末西北边政之探讨》,《中国边疆学》2020年第2期,第163-186页。的主官,而后者侯葆文是1905年10月至11月代表甘肃省府,被派往敦煌县实地调查采买粮事件的主官。
邰惠莉转引范耕球介绍自己收藏敦煌遗书的经过说:1947年春,在兰州城隍庙附近范先生见一售卖敦煌写经的人,“问是真的吗?那人说:其祖父干过敦煌县长,说这是宝物,叫子孙珍藏。……共购卅多卷。那人现才说,姓汪,祖上湖北人。其它不说”。后来,范耕球所购敦煌写经,经冯国瑞、慕寿祺鉴定,确定为敦煌写经,“出售经卷的汪姓年青人,自称是1904年任敦煌知县的汪宗翰的后人”(36)邰惠莉、范军澍《兰山范氏藏敦煌写经目录》,《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80页。。在藏经洞开启四十多年后,范先生一人竟然就从那位自称是汪宗翰后人的年青人手中,前后购得“卅多卷”,证明汪宗翰手中藏经洞藏品确实不少。
总之,汪宗翰手中究竟有多少藏经洞文物,具体数目已无从知晓。不过,从多次接受王道士和敦煌地方官绅馈赠,两次从藏经洞拿取经卷,一次竟取走二百余卷经卷,一次不知具体数目,以及利用藏经洞文物馈赠多位上司和同年,其后人出卖藏经洞经卷数量十分庞大的事实判断,汪宗翰手中拥有的藏经洞文物数量,一定不会少于数百卷!
四、误报隐瞒,疏于管理,必须对早期藏经洞文物的大量外流负责
1.汪宗翰误报瞒报藏经洞文物信息
王道士在藏经洞发现后,很快报知了时任敦煌县令严泽,后来也应该报告了接任的吴绪棣,却都没有引起重视。传言心有不甘的王道士,“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37)谢稚柳《敦煌石室记》,收入氏著《鉴余杂稿》,上海:上海美术出版社,1996年,第3页;又收入氏著《中国古代书画研究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4页。。而据王冀青考证,如果这件民间流传的有关王道士赴肃州献经一事属实,“那这位道台必定是和尔赓额,而不是廷栋”(38)王冀青《廷栋旧藏敦煌写经入藏时间辨正》,《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第213页;王冀青《关于敦煌写本廷栋收藏品》,《敦煌学辑刊》2008第2期,第1-9页。。不管如何,王道士辛苦奔波,其目的有邀功请赏之嫌外,无非就是希望官府知晓藏经洞藏品的事并接手管理。
1902年汪宗翰接任敦煌知县,因为是湖北同乡的缘故,易于交流,王道士也一定将藏经洞的消息报告了汪宗翰。也是在这一年,许伯阮游敦煌,亲眼见汪宗翰从藏经洞拿走经卷二百余卷。不知为何,却迟至癸卯(1903)十一月十二日,叶昌炽才收到汪宗翰赠送的唐元拓本和藏经洞出土的“绢色黯黕,丹黄陊剥,惟笔果出于俗工,尚不甚古,极早为明人之笔”,所绘系水陆道场图的旧佛像一副,和“笔法遒古,确为唐经生派,纸色界画与日本估舶者无毫厘之异”的《大般涅槃经》写经四卷等(39)[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6285页。。
有汪宗翰赠送的出自藏经洞的经卷画像等实物,加上汪宗翰书信中对藏经洞以及洞内藏品的描述,叶昌炽“乃知唐人纸卷中,东同一流传特以震旦重遭劫火,消磨殆尽。敦煌僻在西荒,深山古刹,宜其尚有孑遗。闻此经出千佛洞石室中,室门镕铁灌之,终古不开。前数年,始发键而入,中有石几石榻,榻上供藏经数百卷,即是物也”(40)[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6285页。,可能才有了“建议藩台衙门(甘肃省政府)将此古物运于省垣保存”(41)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89页。的动议。事实绝非像任光宇引用《重修敦煌县志》中“即时报知地方官,……汪令即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的记载,并说“这说明汪宗翰相当重视这个发现,在1902年内对藏经洞文物进行过初步核查。而且,其上司甘肃学政叶昌炽有日记证明,他很快就得到了汪氏的报告,并多次得到汪氏赠送的藏经洞珍贵文物”(42)任光宇《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的起始》,《唐都学刊》2021年第4期,第8页。。不过叶昌炽可能因从汪宗翰的书信中得知,藏经洞内仅仅“榻上供藏经数百卷”,且石室打开之时,“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又见同僚“恒介眉都统,张又履、张筱珊所得皆不少”(43)[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第7册,第2484-2485页。,错误地估计可能藏经洞内所余经卷已不多,加之“估计运费要五六千两,以运费无着,乃于光绪三十年三月下令敦煌县长汪宗翰‘检点经卷画像’(原文云‘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见艺术丛编第三册’)乃为封存”(44)卫聚贤《敦煌石室》,《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第66页。,使得藏经洞文物失去了一次运往省城兰州保存的绝佳机会。
如果说汪宗翰之前对藏经洞经卷数量的了解,只是出自王道士的一面之词,尚好理解。可问题的关键是,壬寅年他陪许伯阮游敦煌,携佛炉并取佛经二百余卷而去,肯定对洞内所藏经卷数量有了大概了解,为什么却在给叶昌炽信中,依旧撒谎说藏经洞内仅有“藏经数百卷”,这就很有些令人费解了。
在甘肃省府要求检点藏经洞经卷的檄文下至敦煌后,“时县令汪宗翰率同文武官绅,大致翻阅一过,约数佛经二万余卷”(45)吕钟修纂《重修敦煌县志》,第40页。。二万余卷佛经,应是汪宗翰检点藏经洞经卷后所得之数。但是,通检从汪宗翰检点藏经洞文物后的1904年农历4月1日直至离任敦煌知县的1906年农历2月9日的近两年时间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里的相关内容,反映出虽然其间两人一直书信往来不断,并且,为能尽快调离敦煌,汪宗翰不仅托人替自己在叶昌炽处说项,还数次附赠敦煌各地所出碑拓,其中有两次附赠了藏经洞出土文物,但却没有只字片言谈及二万余卷经卷数量之事(46)通检叶昌炽《缘督庐日记》第6、7、8、9、10、11、12册中,凡涉及敦煌藏经洞文物的内容,却没有只字提及藏经洞有二万余卷经卷。。这说明汪宗翰根本没有将这一信息写信告诉过叶昌炽,叶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不知究竟。
1906年清政府废黜科举,学政改称提学使,叶昌炽被免职,不久便离开甘肃,回了苏州老家。被蒙在鼓里的叶昌炽,直至己酉年(1909)十月十六日才从张訚如口中获知伯希和将石室大量写经画像捆载西去的消息,起初误以为是敦煌莫高窟新开一石室中之物,表示惋惜的同时,还谴责了不知爱古的敦煌地方的俗吏边甿和对汪宗翰“保护”石室所出之物的肯定。他在当天的日记里是如此描述的:“午后张訚如来言,敦煌又新开一石室,唐宋写经画象甚多,为一法人以二百元捆载去,可惜也。俗吏边甿,安知爱古,令人思汪栗庵。”(47)[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第10册,第6284-6285页。叶昌炽既说新开一石室,更证明其自始至终对藏经洞文物数量的不甚了了。
叶昌炽在其己酉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记里又写道:“午后张訚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氏经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虽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石室发见事,亦得画象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鞧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48)[清]叶昌炽著《缘督庐日记》,第10册,第6326-6327页。这段日记中的感慨之言,无疑是针对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一书中“(伯希和)亟往购得十巨箧,约居石室中全书三分之一,然所有四部各书及经卷之精好者,亦略尽矣”(49)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宣统二年(1910)国粹学报社印,第1页。的描述所发。只是不知道幡然梦醒,得知了藏经洞文物流散部分实情的叶昌炽,在自责“愧疚不暇”的同时,笔下对熟视无睹的“中国守土之吏”的谴责,是否也包含了汪宗翰在内?
华振之指出,在叶昌炽第一次收到汪宗翰寄来的出自藏经洞的写经和画像时,“叶氏为对考古素有研究学者,不知何以当时竟未深入查究,否则,这些艺术珍宝,也许可以幸免流徙异邦的劫运”(50)华振之《敦煌石室,国之瑰宝(下)》,《东方杂志》1976第8期,第42页。。黄征也在《敦煌文献的发现》一文中说:“在1902年3月的时候,汪宗翰当上了敦煌县令,王道士不失时机地又送上一些样品。汪宗翰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很好,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当上敦煌县令后曾在当地收集到一些汉简。当王道士送来敦煌卷子时,他打开一看,十分称赏,于是马上就写了报告交到甘肃学政叶昌炽那里,接到批复后又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和文献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他是在1904年亲自奉甘肃藩台之命检点封存藏经洞的。可是不幸得很,汪宗翰在1906年2月就被调离敦煌县,以致未能将移送敦煌文物、文献到公府之事办妥。”(51)黄征《敦煌文献的发现》,《嘉兴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第8页。
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事件发生了就是发生了。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并最终导致大部分藏经洞文献“流徙异邦”的结果来看,我们认为叶昌炽之所以没有“深入查究”的原因,除了与其在官场上谨小慎微,抱着绝不越权的信条,在建议将藏经洞之物运到兰州保存,遭到藩台“运费无着”的婉拒后,便不再极力争取,只是檄文汪宗翰“乃为封存”有关外,可能还因为相信了汪宗翰洞内仅“藏经数百卷”,初开之时众人分取的谎言,又眼见同僚几人手中也有不少藏经洞经卷,可能误判藏经洞内文物已所剩无多,不值得再去争取也有很大关系。
如果早在1902年汪宗翰陪同许伯阮游览莫高窟,拿走二百余卷经卷和佛炉后,又或是在1904年检点完藏经洞之后,将内藏“二万余卷”经卷的消息,第一时间就毫无隐瞒地报告了叶昌炽。叶昌炽会不会再次积极运作,争取甘肃藩台采取措施,将藏经洞之物运往兰州保存,我们不得而知。“过去学术界都传说叶昌炽曾建议甘肃藩台把所有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但因运费没有着落,没有成功。细检近年广陵古籍刻印刊行的《缘督庐日记》全本,没有找到相关的记载,从叶昌炽当时不知有数万本不被发现的情形来推测,这个传说大概也是难以成立的”(52)荣新江《王道士——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敦煌研究》2000第2期,第25页。。叶昌炽之前应该有过向甘肃藩台建议把藏经洞古物运到省垣兰州保存的建议,否则,可能就不会有汪宗翰1904年奉檄检点藏经洞之物的事。同样的,如果叶昌炽得知依然有数万卷的经卷躺在藏经洞内,是不是会如其日记中所言“鞧轩奉使”,“罄其宝藏”,运往兰州保存也未可知!不过,汪宗翰几年间刻意隐瞒藏经洞文物信息的行径,是造成藏经洞文物没有被运往兰州保存的一个主要因素。
2.随意拿取和馈赠,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
上文所揭,汪宗翰1902年陪同许伯阮游敦煌莫高窟,一次就拿走了多达二百余卷的藏经洞文物。1904年汪宗翰虽奉檄前往检点藏经洞文物,但却只是草草地“大致翻阅一过”,在其眼皮底下,随从的文武官绅当场“有携回一、二卷者”,汪县令不但不予阻止,自己也以“迎归署中供养”的名义,不知道私拿了多少经卷。依据第一次汪宗翰陪同许伯阮游莫高窟,拿走二百余卷藏经洞文物的行为推测,估计这次所拿经卷数量也一定不少。汪宗翰通过两次莫高窟之行的随意拿取和文武官绅的分取,无疑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
为了搞好与上司的关系,同时为达到尽早调离敦煌的目的,汪宗翰不断利用手中的藏经洞文物,给能够替自己说项的同年及上司送礼。目前所知曾接受过汪宗翰赠送的至少一卷至数卷不等藏经洞文物的有叶昌炽、陆季良、许宝荃、和尔赓额、徐锡祺、何衍庆、侯葆文等数人。这样,一批藏经洞文物经由汪宗翰之手,开始流向甘肃任职的一众官员手中。正如王冀青所指出的,“1902年汪宗翰被任命为敦煌知县后,加速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汪宗翰任敦煌知县期间(1902-1906),许多藏经洞写本和绘画品被送给了在兰州的甘肃学政叶昌炽(1849-1917,1902-1906任职)和其他官员”(53)王冀青《1907年斯坦因与王圆禄及敦煌官员之间的交往》,《敦煌学辑刊》2007第3期,第66-67页。。因此,汪宗翰就任敦煌知县后,不但没能阻止藏经洞文物的外流,相反,其随意拿取、赠送藏经洞文物的行为,在客观上加速了早期藏经洞文物的外流。
3.敷衍的“封存”,造成了藏经洞文物被斯坦因、伯希和盗买的结果
汪宗翰在奉檄检点完藏经洞文物之后,没有采取任何行之有效的保护措施,只是轻描淡写地“吩示王道人善为保存”,便不再过问,正如《敦煌学大辞典》中“汪宗翰”的词条所描写,“光绪三十年三月改命敦煌县检点封存,汪氏实主其事,但未严加保护,而是交由王道士就地保管”(54)季羡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888页。。检点后藏经洞文物保管的情形,也依然如同后来斯坦因和王道士谈判时,王道士抱怨的那样没有丝毫改观:“官府甚至没有对这批卷子如何处置作出任何安排”(55)[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姜波、秦立彦译《发现藏经洞》,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页。。藏经洞门口粗糙的木门和铜锁,还是王道士事后自己安装的,并且,“锁的钥匙由王圆禄亲自保管。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访时,情况一直如此”(56)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38页。。
汪宗翰不负责任的检点,名义上的封存,与掩耳盗铃无异!后来的事实证明,王道士依然如故,不断地从已“封存”的藏经洞内拿出一些精美的经卷和佛画,送给敦煌当地的官绅和香客。小小的敦煌县城,汪县令不可能不有所耳闻,但对此却充耳不闻,听任王道士偷拿藏经洞文物赠送敦煌地方官绅,无疑助长了藏经洞文物的外流之风。
1907年斯坦因成功骗买走了大批藏经洞文物后不久,王道士担心藏经洞内文物被官府收走,自己手中没有了可以赠送和出卖以赚取香火钱的经卷,便和上寺、中寺的喇嘛一起,以转经为名迷惑信众,在莫高窟第351窟(伯希和编第160窟,张大千编第146窟)内建造了两个封钉坚固,外表漆画一新,实际上里面塞满了大量从藏经洞内偷拿出来的大批经卷的所谓的转经桶。
1909年10月,敦煌县令陈泽藩奉命查验藏经洞文物时,发现了转经桶,但他并没有将转经桶内经卷收走,只在转经桶上加贴了盖官府印信的封条予以封存,并口头“严谕”王道士将经桶严密看守,以免遗失,同时给继任的知县写了一份有关转经桶的移文。1910年10月20日又写了第二封移文,交代了转经桶之事,“嗣后,奉学部搜买。敝县会同学厅,传集绅民,尽其洞中所存者,一律搜罗,护解省垣,其经桶原封未动”(57)卫聚贤《敦煌石室》,第89页。。其后,继任敦煌知县申瑞元也有给民国第一任敦煌县长黄金绶的移文。移文证明,“一直到清朝灭亡,转经桶一直在王圆禄的看管之下”(58)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第106页。,未被拆封。
这说明,王道士还是很怕官的。在官府严令下,时间虽然过去了几年,但转经桶在王道士看管下依然完好如初。反过来说,假如当初汪宗翰稍稍用些心思,在检点完藏经洞文物后的第一时间,命人在藏经洞门口安装上木门并上锁,再加贴上县府的朱标印封,将钥匙拿回县衙保管,并且像申瑞元一样,严谕“妥为保守毋再遗失私买,致干咎,切切”(59)卫聚贤《敦煌石室》,第89页。,即使王道士胆大包天,也不敢私揭了县府印封,破门撬锁,偷拿藏经洞文物。因此,汪宗翰对藏经洞文物检点后不负责任的敷衍封存,直接造成了日后王道士依然不断拿取私卖赠送当地官绅,并最终将大批藏经洞文物盗卖给斯坦因、伯希和,流向欧洲的可悲结局。
五、结论
以前因为受资料限制,学界较少关注汪宗翰收藏藏经洞文物的情况,也很少注意到藏经洞文物流散之初,大量藏经洞文物的流散跟汪宗翰的关系。随着更多与汪宗翰曾经有过交往官员的信件、日记以及收藏的藏经洞文物上的题识,汪宗翰曾经收藏的藏经洞文物上的钤印、题识等信息的披露,我们对汪宗翰在藏经洞文物流散之初的所作所为,基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担任了敦煌知县近四年时间的汪宗翰,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便利条件,即便不是藏经洞文物流散之初,攫取藏经洞文物最多的甘肃官员,但无疑是在清廷学部将藏经洞文物运往北京前,至少也能算得上是获得藏经洞文物数量最多的人物之一。
2.汪宗翰随意拿取藏经洞文物的行径,一定程度上纵容了随同文武官绅“各人分取”的行为,致使很多藏经洞文物流入敦煌官绅手中。同时,汪宗翰为了讨得上司欢心和达到尽快调离敦煌的目的,不断用手中的藏经洞文物,给叶昌炽等一众官员送礼,导致在他任敦煌知县期间,藏经洞文物流散数量增多,流散步伐加快。
3.汪宗翰刻意隐瞒藏经洞文物数量信息,致使叶昌炽没有再尽力向甘肃官府争取,从而错失了将藏经洞文物运往省垣兰州妥善保存的机会。
4.汪宗翰检点完藏经洞文物后,单纯为了应付上级官府,极不负责,徒具形式的“封存”,不仅没能阻止王道士继续偷拿藏经洞内文物赠送、私卖地方官绅的行为,并最终造成其将大批藏经洞文物盗卖给西方探险家,流失到欧洲的悲惨结局。
美籍独立学者任光宇集各家之说,通过排比汪宗翰在藏经洞文物发现后的所作所为,做出刍议:“虽然有记载显示汪氏频频向上级赠送遗书的目的,在于运动自己升迁和调回关内,但客观上做到了及时上报、调查藏经洞发现,并协助叶昌炽正确鉴定了敦煌遗书。总的来说,汪宗翰在其任内有小功无大过,表现好于一般‘俗吏’”(60)任光宇《敦煌学术史所涉早期人物整理与评议——兼论敦煌遗书发现人暨敦煌学的起始》,第8页。。
纵观汪宗翰在藏经洞文物早期流散过程中所扮演的各种角色,实在配不上任光宇对他这样的谬评!
王庆卫指出:“在早期藏经洞文物的流散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和一个关键人物即汪宗翰有所关联。”(61)王庆卫《徐锡祺旧藏敦煌写经简述——以西安地区藏品为中心》,第139页。现在看来,不是或多或少的问题,而是直接和汪宗翰有很大关联。如果汪宗翰在获知藏经洞文物信息的第一时间,不隐匿,及时上报,又或者在“封存”藏经洞文物之时能尽职尽责,或许现在藏经洞文物的收藏会是另外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