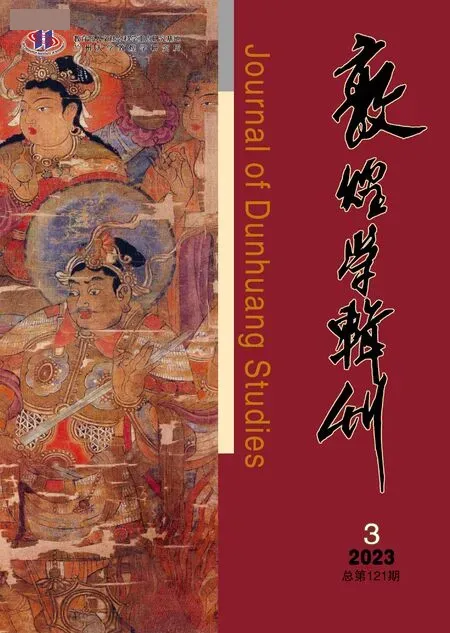甘肃省博物馆藏大统十二年权旱郎造像碑研究
张兆莉 马 德、2
(1.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2.敦煌研究院 文献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30)
西魏大统十二年(546)权旱郎造像碑于1999年在秦安县出土,现收藏于甘肃省博物馆。权旱郎造像碑供养人的姓氏构成表明该碑是以家族为单位开凿的发愿功德碑。(1)罗宏才等《西部美术考古丛书——宗教艺术与民众信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0页。学界在该碑题记的校录、该碑所涉及的宗教信仰、族属姻亲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2)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如下方面:1.造像题记校录:张宝玺《甘肃佛教石刻造像》,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1年,第213-214页;魏宏利《北朝关中地区造像记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84-185页;唐晓军《甘肃古代石刻艺术》,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79-283;汪明校注《麦积区金石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5年;刘雁翔校注《天水金石文献辑录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7年,第363页。2.该碑体现的宗教信仰及宗教特征的研究:俄玉楠《秦安西魏石塔诠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87-96页;魏文斌、陈月莹《帛法祖兄弟与3-4世纪初的北方佛教》,《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50-60页。造像碑题记体现的族属与姻亲关系的研究:文静、魏文斌《甘肃馆藏佛教造像调查与研究(之一)》,《敦煌研究》2012年第4期,第35-36页;张铭、魏文斌《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甘肃馆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敦煌研究》2016年第5期,第52-56页;赵世金、马振颖《甘肃武山水帘洞石窟群北朝供养画像浅析》,《西夏研究》年2018年第2期,第104-105页;罗宏才编著《宗教艺术与民众信仰》,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88-190页;安俊维《中古时期略阳权氏家族相关佛教石刻研究》,《丝绸之路》2020年第3期,第72-76页;王怀宥《甘肃华亭县出土北朝佛教石刻造像供养人族属考》,《敦煌学辑刊》2016年第2期,第133-145页;王怀宥《甘肃天水地区出土北朝权氏佛教石刻造像研究》,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2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5-33页。,但该碑独特的碑额样式、产生的根源等问题未见专门研究。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碑额样式、产生的根源做进一步探讨。
一、大统十二年权旱郎造像碑概况
权旱郎造像碑的碑身高181厘米,宽67.5厘米,为扁体蟠螭顶圆首千佛造像碑,碑额被四条躯体相交的蟠螭环绕,几乎占据碑体的三分之一。阳面碑额的中心位置雕刻一巨大兽面,巨目阔口,两条龙首向下的蟠龙从兽面阔口向左右伸出。蟠龙躯体呈“S”型,前爪靠近浅龛垂下,后爪伸向碑额顶部。兽面下方开一外方内圆的圆拱浅龛,龛楣为火焰形,龛内雕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圆拱龛左侧有供养人2身,右侧有供养人3身。圆拱龛下方并开七个小型圆拱形浅龛,龛内均雕坐佛一身,组成七佛。七佛龛下方雕刻10排千佛立像,每排30身,共计300身,铺满碑身。千佛下方雕刻内容呈四层排列:第一层雕刻8身供养人立像,每身旁刻姓名,第一位手执鹊尾炉者是比丘僧朗昌。第二层、第三层为车马出行图,雕刻牛车2辆,马5匹,骑马供养人6身,为首者身后出现手持华盖仆从,并有题刻“弟子权旱郎供养佛时”;牛车中载有数人,题记表明是权氏家族的女性供养人。第四层雕刻10身供养人,身旁同样刻有姓名,均为权氏家族成员。
碑身正面刊刻内容如下:
第一排供养人姓名:
比丘僧郎昌忘父权遝白供养佛时忘母文陵供养佛时□□权□郎供养时忘弟权□郎供养佛时忘姊□□□供养佛时忘嫂吕妙香供养佛时忘女云妃供养佛时
第二、三排车马出行图中供养人题名:
弟子权旱郎供养佛时弟子权愿息弟子权愿□弟子子愿弟子子和弟子法□清信□王□□清信姊王□□弟子□□弟子□□息女淑妃息女南妃
碑左侧为千佛,并有题记,内容如下:
亡兄权敬郎小忘兄权□仁权养具权六特
碑右侧上部雕刻千佛,下部雕刻供养人。
碑阴形制与碑阳基本类似,碑额正中为兽面,下方开尖拱龛,龛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及二力士二狮子,碑身上部雕18排千佛,每排30身,共计540身。碑身下方为发愿文,位于界格内,共计24行,每行11字。内容如下:

发愿文提到的“清信士权旱郎”位于碑阳第二排的骑马供养人队伍中,唯其身后出现持华盖仆从,昭示权旱郎在权氏家族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其也是该碑的主要施主。该碑题记中出现“大魏大统十二年”纪年,是甘肃留存的北朝后期石刻造像中唯一的一例,这为研究甘肃北朝后期石刻造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权旱郎造像碑的形制、题材、装饰图像内容和表现手法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又体现了北朝晚期甘肃石刻造像的新面貌。该碑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图1 权旱郎造像碑

图2 权旱郎造像碑碑额(图1、2均由兰州大学魏文斌教授拍摄并提供)
二、碑额兽面分析
北朝佛教兽面包括石窟兽面、造像碑兽面和单体造像兽面,其共同特征是有首无身,巨目阔口,两角两耳耸立,口中露出巨齿,嘴角有对称獠牙。兽面纹的“母题”原型最早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兽面纹饰、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兽面石雕、龙山文化玉器上兽面纹样等都具备上述结构特征。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饕餮纹和铺首延续了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兽面纹的基本特征,表明“这不仅是延用了一种术传统,而且是传承了信仰和神话”(3)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第48页。。宋代《宣和博古图》认为此类兽面纹图像就是《吕氏春秋》中的饕餮,故而兽面纹以饕餮之名一直沿用。梅原末治将具有饕餮外观形象的图像归为兽面范畴,这一观点得到高本汉、夏鼐、马承源、李济、张光直、刘敦愿、陈公柔、张长寿、段勇等学者认同(4)青铜器兽面纹定名研究如下:[日]梅原末治著,胡厚宣译《中国青铜器时代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9-30页;Bemhard Karlgren(高本汉),Yin and Zhou in China,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BMFEA),No.8,1936;Bemhard Karlgren,New Stuidies o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9.1937;李济、万家保《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2本):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8年,第69-70页;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纹饰综述》,收入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纹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1-34页;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第137页;刘敦愿《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第111-148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323页。,现在学者大多采用“兽面纹”这一说法;“饕餮纹”虽有使用,但范围较小。按照图像所属关系,兽面纹图像体系可分为礼器兽面纹、墓葬兽面纹、佛教兽面纹。5世纪中期,佛教石窟中首先出现兽面纹;6世纪初,佛教造像碑出现兽面纹;6世纪末,单体圆雕菩萨像出现兽面纹。
权旱郎造像碑的碑额兽面样式在甘肃出土的北朝千佛造像碑中极为罕见:碑额与碑身的比接近1∶2,阳面碑额处口衔二蟠龙的兽面图像处于碑额的中心位置,占据了碑额面积的二分之一,同时也成为碑额的视觉中心。北朝时期的千佛造像碑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北魏太和末年至景明元年(493-500)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千佛造像碑大多以扁平方形平顶碑为主,碑身为梯形或长碑体;甘肃地区千佛造像碑形制基本沿袭了中原扁平平顶碑的样式,扁平圆拱顶碑亦在此阶段出现。北魏熙平至永熙年间(516-534)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扁平方形平顶千佛造像碑依旧流行,但碑身上部样式略有变化;扁平圆拱顶碑出现。这一时期天水地区的千佛碑的主龛形制多为圆拱形龛或尖拱形龛,龛楣处出现交缠二龙或者一身双首龙的装饰,尖拱形龛出现火焰纹装饰,如麦积山133窟北魏晚期的7号碑、北魏永熙二年(533)张家川武威王千佛碑等。北朝晚期(534-572)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千佛造像碑样式多样,除了扁体圆拱顶碑、扁体平顶长方形碑外,碑身矮且宽的蟠螭顶圆首碑增多。此类蟠螭顶圆首碑的碑身高和宽的比例接近1.5∶1,甚至有些接近2∶1;碑额为蟠螭顶,龙爪向下或者做对举状。碑额处或者碑身上方开龛。西魏权旱郎造像碑正是第三阶段蟠螭相交环绕碑额边缘的圆首碑。碑额正中出现面积较大的兽面,(5)俄玉楠和张铭将兽面称为饕餮:俄玉楠《甘肃省博物馆藏北朝造像研究》,兰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张铭《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甘肃馆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第55页。王敏庆认为是荣耀之面:王敏庆《荣耀之面:南北朝晚期的兽面图像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3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99-523页。兽面和蟠龙下方开龛像。该碑的规制、造像风格和图像组合表明西魏时期天水造像碑艺术在中原石刻造像模式(尤其是长安石刻艺术)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成熟的造像模式。
(一)碑额兽面的位置分布
北魏时期造像碑兽面,主要位于碑身或碑额小龛的龛楣中心位置。如景明二年(501)徐安洛四面造像碑(图3)兽面均出现在圆拱尖楣龛的龛檐正中。此兽面圆额头,无冠,额头上方阴线刻竖条纹,眉和角成一体,内卷呈马面纹状,上有阴线刻花文。臣字形眼眶,卵圆形眼珠,圆形鼻,阔口露6齿2獠牙,口衔龛檐,龛檐已经残破。永安三年(530)薛凤规造像碑的佛教兽面的分布位置受景明二年徐安洛四面造像碑的兽面影响,该碑的碑额占据碑体的三分之一,正面碑额为二蟠龙,龙身下方开尖拱龛,龛楣处出现兽面。北魏永熙二年(533)武威王千佛碑(图4)、大统六年(540)巨始光造像碑的碑额样式和佛教兽面的分布与薛凤规造像碑的碑额类似:蟠龙环碑额,下方开小龛,龛楣正中出现佛教兽面。永熙二年武威王千佛碑为圆首蟠龙千佛碑,兽面出现在阴面碑额的蟠龙正中,兽面所占比例较小但处于视觉中心。两条蟠龙的龙身位于碑额边缘左右两边,俯首向下。兽面下方为圆拱尖楣龛,龛内雕刻一佛二菩萨;龛额左右各雕刻凤鸟一只。大统六年巨始光造像碑的碑额出现的兽面及组合样式同样受到永安三年薛凤规造像碑的碑额样式影响,在碑额的蟠龙下方开凿带有兽面的小龛。永熙二年武威王千佛碑出现的兽面位于小龛上方的蟠龙相握前爪的正中处,与薛凤规造像碑、巨始光造像碑所出现的兽面的外观造型类似,但所处的具体位置不同。这一位置的变化表明,在北魏晚期,秦安地区的造像碑已经从细节上探索期独立的样式。张铭认为权旱郎造像碑碑额正中出现兽面口衔蟠龙的样式延续了北魏永熙二年武威王千佛碑的碑额样式。(6)张铭《甘肃秦安“诸邑子石铭”考析—甘肃馆藏佛教造像研究之三》,第55页。权旱郎造像碑碑额兽面的分布位置、图像组合与北魏永熙二年武威王千佛造像碑相似;碑额兽面样式更加富有装饰效果,表现手法更接近中原石刻造像技法。
苗圃地的选择通常应优先选择靠近水源但是没有积水的区域,土地应保证基本平整,且能保证灌溉的便捷性。同时,选择的位置应保证充足的光照条件,通风性好,并且方便田间管理。土壤方面需要尽量保证土质优良,砂之壤土或者壤土是优先选择的播种区域,如果土质条件较差,在育苗前需要对土质进行改良,如果是盐碱质,则含盐量不能超过百分之零点二,并且应建立相应的防返盐措施。

图3

图4(图3 景明二年徐安洛四面造像碑局部,采自赵力光编《长安佛韵——西安碑林佛教造像艺术》,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9页;图4 北魏永熙二年武威王千佛造像碑,采自李宁民、王来全主编《甘肃散见佛教石刻造像调查与研究·天水卷》,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88页)
(二)碑额兽面的类型样式
北朝造像碑兽面遵循了石窟兽面的造型要素,在双目、口部、鼻子等造型相对固定的基础上,兽面的头冠、双角、面部装饰等元素存在一定差异。按照造型差异,将其分为五种样式:A型(7)按照头冠、角、眼部、口部造型的差异,A型造像碑兽面分为AⅠ式、AⅡ式、AⅢ式、AⅣ式、AⅤ式五种型别。:额头有冠有双角,面部有装饰,巨目阔口,口中有衔物,露巨齿獠牙;B型:额头有冠,有双角粗眉,臣字目,面部无装饰,口中有衔物;C型:无冠无角面部无装饰,阔口张开,口有衔物,不见下颌,粗眉,卵形目尖耳耸立;D型:无冠无角面部有装饰,尖叶状双耳耸立,卵型臣字目,不见下颌;E型:无冠无角,面部无装饰,阔口张开露巨齿獠牙,口中有衔物。权旱郎造像碑兽面的额头上鬃毛根根竖起,两个对称且内弯的双角,角上有三道阴线刻的“∽”形花纹作为装饰。双角下方毛冠之上为粗眉,眉尾上扬且卷起,眉毛上同样有阴线刻的装饰花纹。粗眉下方是巨大双目,“臣”式眼眶,眼角向面部卷起,眼珠采用阴线刻,滚圆且凸出。尖叶状双耳带有花纹,分别从眼角处伸出紧贴眉尾。双目之间有四层阴线装饰花纹构成的圆形宝珠,宝珠上方为桃型毛冠。宝珠正下方为三角形鼻子,鼻子两侧各有一排胡髭,阴线刻出的蛇形花纹作为装饰。紧贴胡髭下方的是阔口,露出上下两排整齐的牙齿(上牙为7颗巨齿,下牙为6颗巨齿),嘴角露出上下四颗獠牙,两条蟠龙从阔口中垂首向下。权旱郎造像碑兽面的造型为典型的A型造像碑兽面样式,其外观造型受到了中原造像碑兽面尤其是北朝长安地区造像碑兽面样式的影响。
(三)兽面样式来源
权旱郎造像碑兽面的造型结构与中原石窟兽面的造型结构相似,表明该造像碑兽面受到中原石窟兽面造型的影响。北朝造像碑兽面造型在石窟兽面双目、口部、鼻子等造型要素的基础上,围绕头冠、双角、面部装饰等造型元素进行变化。北魏时期的石窟兽面,按照角的造型、额头造型、额头是否有冠、两目之间是否有宝珠装饰、口中是否有衔物等造型元素,分为八种类型:A型:额头有冠,有双角,面部有装饰,口部有衔物或者露出口部露半圆形舌;B型:额头无冠,有双角,面部有宝珠,口部张开,或有衔物或露出巨齿;C型:额头有冠,有双角,两目之间无装饰,口有衔物;D型:额头有冠,无双角,面部有装饰,口部有衔物,或露舌;E型:额头无冠,有双角,面部无装饰,口部有衔物,或者露出半圆形舌;F型:额头无冠,无双角,面部无宝珠,口部有衔物;G型:石窟兽面额头无冠,无双角,面部有装饰,口中有衔物;H型:圆额头,无冠,面部有装饰,阔口紧闭。其中,H型仅出现1例,分布在庆阳楼底村1号窟,龙门石窟古阳洞集中出现了H型之外的其它7种类型。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古阳洞,正是孝文帝之缘,众多皇亲国戚、文武百官、知名高僧聚集古阳洞开龛造像。(8)窟内造像题记也表明龛主多以皇室宗亲、功臣及眷属为主,地方大族官员及高级僧侣也占较大比重。古阳洞上层南北两壁的八大龛及列龛的造像记表明各龛竣工年代多在太和二十二年(498)至景明四年(503)之间;中层龛造像记表明竣工的年代多为正始至延昌年间(507-515);最下层列龛的造像记表明竣工年代多在熙平至正光年间(516-520)。古阳洞石窟兽面集中分布在太和末年至孝昌年开凿的石窟,这一阶段恰好历经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三朝。太和末年古阳洞出现的石窟兽面为A型(具体为AcⅡ式);景明年间至延昌年间出现的石窟兽面为出现A型(具体为AaⅡ式、AaⅢ式、AaⅣ式、AaⅤ式)、B型(具体为BbⅠ式、Da式)、E型(具体为EⅠ式);熙平年间至孝昌年间出现A型(具体为AaⅢ式、AaⅣ式、AaⅤ式、AbⅡ式、AbⅢ式、AcⅢ式、Ad式)、B型(具体为Bb式、Bc式)、C型、D型(具体为Db式、DcⅠ式)、F型(具体为Fa式、Fb式、Fd式)、G型。古阳洞石窟兽面的类型样式表明,宣武帝、孝明帝两朝造像龛出现的石窟兽面样式最为丰富。古阳洞北壁第N94龛太和十九年(495)尉迟造像碑下方最早出现AcⅡ式石窟兽面。景明年间古阳洞窟顶第D87、D88龛(图5)为AaⅢ式石窟兽面。宣武帝时期,古阳洞南北壁两壁自上而下持续在中层开龛,其中八大列龛中,北壁第N152龛、N178龛、N246龛(图6)、N258龛、N317和南壁第S67龛(图7)、S71龛均出现石窟兽面,对应出现样式为:北壁第N152龛为EⅠ式、第N178龛为AaⅢ式、第N246龛为Da型、第N258龛为AaⅤ式、第N317为AaⅡ式;南壁第S67龛为AaⅣ式、第S71龛为AaⅡ式、第S130龛为BbⅠ式。可见,北魏宣武帝时期,古阳洞石窟兽面已经出现6种样式。(9)根据上述造像龛明确题记年代以及分布情况,可分为两组:第一组为AaⅡ式(S71龛、N258龛)、第二组为AaⅢ式、AaⅣ式、AaⅤ式、BbⅠ式EⅠ式、Da型。可分为两个时期,早期佛教兽面为AaⅡ式;晚期为AaⅢ式、AaⅣ式、AaⅤ式、BbⅠ式EⅠ式、Da型。熙平年间开始古阳洞在最下层开龛造像,除了南北两壁最下层的大龛外,围绕第二层和最下层之间的部分小龛也出现了石窟兽面。古阳洞下层大龛如第N246龛、S174龛(图8)、N289龛出现AaⅤ式石窟兽面;第N178龛、N283龛出现AbⅡ式石窟兽面。古阳洞石窟兽面在这一时期形成典型样式,对龙门石窟火烧洞、魏字洞、药方洞、普泰洞出现的石窟兽面产生重要影响。洛阳周边石窟及长安地带的造像碑开始大量出现兽面,其造型样式遵循古阳洞A型兽面的基本造型元素(巨目、粗眉、大鼻、阔口、巨齿、对称獠牙)的基础上,衍变出新的类型样式。

图5 古阳洞D88龛(采自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0页)

图6 古阳洞N246龛(采自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第1册,第89页)

图7

图8(图7 古阳洞S67龛,作者拍摄;图8 古阳洞S174龛,采自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第1册,第174页)
北魏中后期以后,甘肃石刻造像艺术在摄取长安风格的基础上,在材质、技法等领域已经逐渐形成带有地域风格的雕凿体系,以浮雕或圆雕为主要表现手法,使造像碑具有拙朴厚重地域风格。同时该碑浅浮雕和阴线刻等技法结合来表现该图像,明显受到中原石刻技法的影响。以浅浮雕的方式来塑造碑额兽面的整体外观造型,兽面的双目、头冠、双角等细节以较为细致的阴线刻画,尤其是粗眉之间鼻梁处三层圆线和毛冠出现的毛发等,线条流畅且细密,具有典型的中原石刻传统技法特征。大统十二年权旱郎造像碑的兽面图像样式充分说明西魏时期,佛教兽面图像在融合长安石刻造像技法和样式的基础上,已经形成新的图像样式。结合该碑的雕凿背景,可知古阳洞北魏时期出现的佛教兽面成为具有崇高意义的图像,在装饰和护法等功能之外,该图像不仅成为权氏家族煊赫地位的象征,还是权氏家族政治诉求的体现。
三、权旱郎造像碑出现缘由
北魏末年政治动荡,先是北镇镇兵与关陇城民暴动,尔后有“北边酋庶”尔朱氏擅权,至532年,北魏经历了三任皇帝的更换;自534年起,宇文泰集团与高欢集团开始东、西魏的对峙。宇文泰为维系政局的安定,一直以拥护魏室的旗号为立国之基;为排挤魏室而集权于宇文氏又实行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和平衡各方势力,在此过程中,关陇豪族成为宇文泰的拉拢对象之一。宇文泰为实现专权,通过“当州首望”和“作牧本州”两项政策拉拢关陇本地土豪,这两项举措与权氏家族由地方豪族向军政望族的转变有着重要关系。权氏作为地方豪强,虽然与当时门第显赫的士族大姓不可同日而语,但因其家族在秦州地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依旧属秦州地区上层人士。因此,大统十二年权氏造千佛碑除了祈福等家族信仰之外,更深层的原因是强调其家族声望和对当时政治动向的准确把握与回应。
(一)营造家族声誉以图“首望”
据权旱郎造像碑的造像内容和供养人题名可知,该碑是家族成员联合供养造像活动的产物,表明权氏家族在秦州地区根基深厚且姻亲遍布,已具备举行世族宗族型佛教供养活动的能力。僧人朗昌的参与表明权氏家族在宗教活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权氏作为北朝时期秦州土豪,虽为小姓但是却因军事实力和家族庞大而盘踞一方已久。(10)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一文中认为略阳权氏为氐族,参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77页。王怀宥认为略阳休官权氏为兴国氐人,“休官”一词本是由“兴国”演变而成,参见王怀宥《甘肃天水地区出土北朝权氏佛教石刻造像研究》,第24-27页。与权氏家族相关的造像碑出土地表明,权氏家族在当时的活动区域为秦州略阳郡、天水郡(今秦安县、张家川县、庄浪县),这一区域恰好是两汉至十六国北朝时期秦州胡人(尤其是氐与羌)部族分布的区域,他们对这一时期河陇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过重大影响,《三国志》《晋书》《魏书》中均有记载。《晋书》中记载了略阳豪族休官首领权干成先后任前秦、后秦高官,(11)[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卷117《姚兴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77页。这也表明略阳氐族在十六国时期已经成为能够左右当地政局的地方豪族。然而,在整个北魏门阀士族体系中,类似权氏这种小姓在当时可谓籍籍无名。以韦、杜、杨、苏等为代表的关西高门的家族地位并不及中原高门士族,次一级的关陇地方豪族更是声明不显。以唐人柳冲对门第评论标准来看,权氏甚至是在当时难以入丁姓之流(12)柳冲将门阀做了评定和分类,即“郡姓”者,以中国士人差第间阅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胰”,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抑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见[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199《柳冲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675页。。北魏末六镇起义时,关陇地区亦有两支以胡族城民为主的反魏势力使朝廷甚忧之(13)一支活动于陇山以东的泾水流域,先后由胡深及其部将万侯丑奴领导;另一支活动于陇山以西的秦州地区,先后由莫折大提、念生父子率领。,“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逋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14)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99-105页。正光五年九月(524)萧宝黄为西道行台、大都督,与崔延伯一起入关平叛莫折大提、念生父子所建的反魏势力时,权景宣被举荐为轻车将军。由此可见,权氏这种次一级的家族凭借其军事实力或地方影响力,借机具备了一定的话语权。
宇文泰在大统十二年推行“选当州首望”之策来笼络关陇地区豪族势力而获取其拥护,此举将地方武装势力转化为中央政府支配的军事力量,不仅方便调动各地兵员军资,还实现了对地方军事力量的有效吸收和控制。因此,出于个人利益和家族长远发展,入选“首望”对权氏家族来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以军功进入宇文泰集团的权氏,营造家族名门郡望的意识增强。权旱郎造像碑在此背景下诞生,在宗教诉求之外,其本质是强调其家族声望,营造家族声誉以图“首望”。
宇文泰置大统十四年(548)以当州乡帅统领乡兵之策,一方面来扩充军队,一方面可以更好地控制地方势力。权氏一旦入选“首望”,在已有军功的情况下,可以由盘踞乡里的地方豪强摇身一变成为朝廷认可的官员。权氏不仅可以将私人武装合法化,还可以凭借在乡里社会与统治集团所获得的双重身份,在地方权力团体中更具优势,这对权氏家族具有强大吸引力。在这一时期,权氏家族重要成员权景宣官至高位,大统十五年(549)任大都督、豫州刺史,镇守乐口。权景宣以少胜多击败东魏刘贵平后,西魏朝廷加封其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权氏家族众多子弟担任州主簿、主簿都督等官职,石佛镇权氏石造像题记中也有所记载。(17)石佛镇权氏石造像题记内容如下“岁次丙子九月癸酉朔廿日使持节、抚军将军、大都督权庆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都督(豫)州刺史、秦州大中正权州主簿、州权仰世父母子道工菩萨藉斯微诚,赖复国柞永护利法界普达州主簿都督子景,侄荡寇将军武子通,侄略、侄岳”题记相关的研究,见汪明《石佛镇权氏石造像题记简考》,第75页。
(二)响应“法统”以求“作牧本州”
权旱郎造像碑的产生也是对宇文泰周礼复古这一政治举措的积极回应。在当时复杂诡谲的政治环境下,个人仕途与家族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权氏家族因军功而荣显,作为受益者对宇文泰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是拥护的态度。
北魏末年帝位频繁更替,(18)532年高欢占领洛阳后,将尔朱氏拥立的皇帝元恭(北魏前废帝)废黜,又废黜与尔朱氏抗衡的皇帝元朗(北魏后废帝),改立元脩(《魏书》又称“出帝”)为帝。处于弱势的北魏王朝在动荡中并未被取代,而是被权臣拥立出现东、西魏对峙的局面,原因在于当时北方尤其是中原黄河流域“人心向魏”,尤其是对孝文帝极为尊崇。北魏后期世人将孝文帝所创汉制视为完美典范,“处于动乱中的人们并没有将动乱的根源归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反而将确立孝文帝的法统,肯定孝文帝的地位,视为恢复秩序的法宝”。(19)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8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5页。东、西魏建立后,双方为谁代表北魏正统争持不下,均以正统自居。尊崇孝文帝、延续孝文帝政治举措是当时东、西魏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20)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第57页。既有利于政局的稳定也有利于粉饰宇文泰、高欢等人专权的真相。东魏、北齐几乎全部继承了孝文帝所创官制;西魏虽延续了前朝旧制,宇文泰为削弱魏皇室的政治势力实现集权,借恢复周代礼制之举进行中央官制改革。(21)宇文泰作为西魏政权的实际掌权者,想要削弱魏室朝廷的实权实现军政大权集权于宇文氏,通过武力消灭具有一定军事实力和民望的魏室要付出的政治风险过于沉重,为防止受人攻讦,孝文帝礼制改革中的周礼成为宇文泰根据政局来推行官制改革的幌子。
大统十二年玉璧大战后,东魏再无力对西魏发动大规模攻势。外部强敌消灭后,宇文泰于大统十二年将六尚书三十六曹制改为六尚书十二部制,其幕府亲信出任六尚书。大统十三至十四年间(547-548),宇文泰参照周礼对中央官僚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变成虚职;三公和六卿之间设三孤,品秩上降低了六卿的政治地位,同时,六卿成为虚职。(22)六卿所涉及的邦治、教、礼、政、刑、事等各类事务通过各府所属职官(六属)完成。大统十七年(551)宇文泰官至冢宰,魏室权力被架空成为彻底的傀儡。然而,宇文泰依旧尊奉魏室并未取而代之,可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魏室“法统”的支持者已经成为不可对抗的政治力量,“孝文帝已成为一种不容怀疑的象征,他所制定的政策方针成为人们批评现实政治与制度的参照物”。(23)何德章《北魏末帝位异动与东西魏的政治走向》,第55页。
政治生态环境制约佛教信仰的社会表达,宇文泰复兴周礼的政治行为,同样会影响到佛教。权氏作为秦州的当地豪族,其宗教信仰会与当时的主流信仰保持一致。因此权旱郎造像碑的规制、图像样式和内容选择上,会选择北魏时期的流行图像。该碑出现的兽面,一方面沿袭了北魏造像碑兽面图像的余韵;另一方面,此兽面图像从商周青铜器兽面图像发展演化而来,同时,该碑兽面图像与青铜器兽面的平面图像造型上的高度一致性,除却装饰和护法等功能外,兽面图像具备的崇高意义不言而喻。古阳洞北壁正始二年(505)开凿的宣武八大龛之一的N152龛,盝形龛楣下方出现石窟兽面。该龛西侧造像记(24)刘景龙《古阳洞:龙门石窟第1443窟》第3册,第26页。(第1852号)记载,像主为王史平、吴共合、曹人兴、权六烦,其中权六烦为横野将军钩楯署洪池丞,这表明,自北魏时期,权氏族亲的宗教行为与时局紧密联系。同时,也表明权氏族亲已经较早接触古阳洞石窟佛教兽面图像。大统十二年权氏家族刊碑造像祈福以求功德的行为,依旧是将家族的宗教行为与时局政治紧密联系。营造家族声誉的同时又积极响应了宇文泰周礼复古之举。这一举动体现了权氏家族的政治诉求——凭借已有的军功和一州首望而有资格“作牧本州”实现“世以为荣”。
“作牧本州”则是宇文泰笼络关陇及其周边地区地方豪族的另一重要举措,主要针对的是那些世居乡里,在地方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关陇豪族,这对以军功而显荣的权氏家族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对权氏家族而言,无论是出于个人政治前途还是为门户计,“选当州首望”是实现“作牧本州”的重要一环。《周书》记载了出身当地的关陇豪族出任本州、郡的刺史郡守的记录。西魏大统十二年之前出身当地的豪族出任本州、郡的刺史有骠骑大将军杨宽(大统五年授东雍州刺史、大统十年授河州刺史)(25)[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2《杨宽传》,第367页。、李贤(大统八年授原州刺史)(26)[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5《李贤传》,第413页。、蔡祐(大统九年授青州刺史转原州刺史加帅都督)(27)[唐]令狐德棻《周书》卷27《蔡祐传》,第444页。、王羆(大统五年时为雍州刺史)(28)[唐]令狐德棻《周书》卷35《郑孝穆传》,第610页。等。大统十六年(550)府兵制的实行,使秦安、陇右等地的地方豪族(29)陇右地区的地方豪族主要有:陇西乞伏氏、辛氏,略阳苻氏、吕氏、杨氏、权氏,天水杨氏,南安姚氏,安定皇甫氏等等。从地方领兵乡帅摇身一变成为朝廷命官,在兵府中担任各级要职,其社会政治地位再次获得提升。
权氏家族与宇文氏政权的结合实现了关陇地方豪族的崛起,成为宇文泰西魏北周政权的统治核心,实现了由略阳地方小姓土豪向军政望姓的跨越,至唐代,权氏家族更加庞大兴旺并且成为高门望第。敦煌文书S.2052《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一卷并序》中所记载(30)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23-328页。,秦州天水郡权氏已经成为唐十道诸郡姓望氏族,唐代的权氏家族成员的墓志铭涉及的官职以及姻亲关系可以作为佐证。《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君墓表》(31)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321《著作郎赠秘书少监权君墓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3637页。《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并序》(32)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501《唐故东京安国寺契微和尚塔铭并序》,第5901页。《唐故左监门卫将军华定遂三州刺史千金县开国伯权府君墓志铭并序》(33)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56页。《唐故袁州刺史右监门将军驸马都尉天水权君墓志铭并序》(34)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205《唐故袁州刺史右监门将军驸马都尉天水权君墓志铭并序》,第6460页。《唐故相权公墓碑》(35)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卷562《唐故相权公墓碑》,第2352页。《故左卫高思府果毅都尉权府君墓志》(36)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第78页。所涉及的权氏族人有权皋、权文诞、权万春、权毅、权得舆、权文异等人,墓志中均被称为天水略阳权翼之后。《唐睦州桐庐县丞柳君故夫人天水权氏墓志铭》《唐故灵武节度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京兆韦府君墓志铭》《鄜坊节度使推官大理评事唐君(款)墓志铭》《再从叔故京兆府咸阳县丞府君墓志铭(并序)》四篇墓志铭中,出现较多权氏家族的姻亲。从中可以看出,成为名门望族的天水权氏家族在唐代已经在长安跻身显贵,且姻亲更是遍布高门官宦之家。唐代与郡望有关的记载中,权氏祖先成为了商武丁之后。敦煌文献S.2052《新集天下望姓氏族谱一卷并序》《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通志·氏族略》的记载可以看出,关于权氏的记载都涉及封地与大姓氏。权氏的祖先在春秋时期居住在汉水流域,子孙以封地权城为姓氏,作为大姓豪族被秦朝迁置到了略阳,从此定居下来,居住了上千年,至北朝时,显亲权氏人丁兴旺,己发展为大姓望族。《元和姓纂》也称权氏:“秦灭楚,迁大姓于陇西,因居天水。”(37)[唐]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定《元和姓纂(附四校记)》卷5,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549页。可以看出,权氏家族经过各方面的努力,最终实现了家族身份的成功转变,由地方酋豪到军功显贵,最后成为科举显贵。
在诡谲的政治环境下,个人仕途与家族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政治立场,权氏家族因军功而荣显,作为受益者对宇文泰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是积极响应的态度。出土的权氏家族造像碑题记表明,西魏、北周时期,秦州权氏家族在地方军政机构中担任要职,如权景晖为陇右府参军、权道奴任渭州南安郡守。(38)北周保定三年(563)权道奴造像碑题记出现“荡难殿中二将军都督渭州南安郡守阳县开国伯权道奴供养佛时”;供养人中出现其中的“权帛郎”应与“权旱郎”为同一家族。结合史料可知,权氏家族成员基本上沿着“地方酋豪—当州首望—地方领兵乡帅—朝廷命官”这一轨迹走上晋升之路,实现了家族社会政治地位的提升,作为宇文泰的拥护者,权氏家族成员的筹谋极为成功,家族门庭得以改换,最终成为望族。
四、结论
权旱郎造像碑的规制和雕刻内容反映出北朝末期天水一带千佛造像碑的演化过程。该碑与同时期圆首蟠螭碑的不同之处在于,该碑的碑首正中出现巨大兽面:此兽面不仅处于视觉中心,并占据碑额较大面积,是北朝末期所出现的造像碑兽面中较为罕见的一例。碑额兽面的造型元素和出现位置,可见该碑受到中原造像碑尤其是北朝长安地区造像碑上所出现的兽面样式影响,是西魏时期天水地区石刻造像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新样式。碑额兽面与俯首蟠龙组合出现在造像碑的尖拱龛龛楣上方,是关中地区和中原地区造像碑出现的碑额兽面组合和位置的延续。该碑对兽面图像着重表现,既有对北魏石刻造像的借鉴、吸收和融合,又在雕凿过程凸显本土石刻传统,表明北朝末期甘肃石刻造像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造像模式。同时,该碑题记中出现“大魏大统十二年”纪年,是甘肃留存的北朝后期石刻造像中唯一的一例,这为研究甘肃北朝后期石刻造像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权旱郎造像碑及其他权氏家族所雕凿造像碑表明,西魏——北周时期秦安(天水)已经成为西北地区石刻艺术的中心区域,也逐渐开始影响到周边地区。碑额兽面形象、规制、表现手法、造像风格可以看出,该碑不仅继承了北魏石窟佛教兽面图像样式和石刻技术,也体现了西魏时期甘肃石刻艺术的变革与创新。
借助“选当州首望”统领乡兵和“作牧本州”两项政策,权氏家族由地方酋豪小姓家族,成为当地具有话语权的首望家族,并凭借军功成为宇文氏集团的重要力量。家族利益决定了权氏家族成员的政治立场,其宗教行为也与宇文氏权力集团保持一致。大统十二年权旱郎造像碑兽面采用北魏古阳洞石窟中佛教兽面的样式,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是权氏家族在宗教上对宇文泰恢复“法统”之举的响应,体现了自北魏以来佛教艺术与政权之间的依附和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