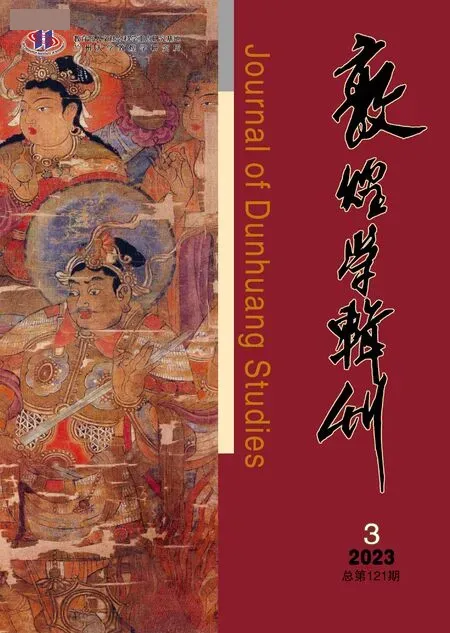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冲突探析
——以德藏档案书信为中心
闫 丽
(浙江大学 1.文学院、2.中亚与丝路文明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28)
二十世纪初,德国先后四次派遣吐鲁番考察队,由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和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相继领导前往新疆进行探险发掘。其中格伦威德尔是著名的印度学家、藏学家和考古学家。勒柯克是有名的宗教学家、语言学家,在回鹘语摩尼教文献、吐鲁番学研究等方面有突出成就。吐鲁番考察活动和对所获文物的研究成为二位先生交流的纽带,也使他们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是柏林民族博物馆的同事。1883年格伦威德尔成为印度艺术部代理主任,1902年勒柯克转入印度部工作,使他们有了交流机会,也使格伦威德尔对勒柯克有初步的良好印象。考察期间,勒柯克细心照料生病的格伦威德尔,让他们有了进一步交流。然而除考察期间在异国他乡的互相关照外,更多的是他们对考察活动细节及所获文物处理方式等问题的摩擦。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吐鲁番探险队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四次探险队所获文物的整理与研究,相比之下,对探险队史事及成员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很少提及第五次考察。(1)王冀青《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载陆庆夫、郭锋、王冀青编《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3-246页;张广达《吐鲁番绿洲及其探险简史》,见氏著《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1-105页;陈海涛《德国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综述》,《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第67-74页;刘进宝《丝路文物被盗的历史背景》,《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第106-114页;郭金荣《德国的四次“吐鲁番”探险》,《德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35-40页;张重洲《德国探险队与清末吐鲁番社会——以第二次、第三次考察为中心》,《丝绸之路》2016年第16期,第18-20页;吐送江·依明《德国西域探险团与德藏回鹘语文献》,《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2期,第159-171页;居政骥、许建英《关于20世纪初德国到中国新疆考察旅行的若干问题——以德国档案文献为中心》,《中国地方志》2022年第1期,第107-115页。然而,近年来随着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相关信件公布,(2)关于格伦威德尔的信件有两部分。其一是2001年公布慕尼黑大学图书馆手稿部收藏的227封信,包括112封他写给自己导师库恩(Ernst Kuhn)的信,6封致汉学家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的信,37封致人类学家卢尚(Felix von Luschan)的信,24封致地理学家安德里(Richard Andree)的信,12封致哥根廷大学的信,30余封致Carl Bezold、Schlagintweit等学者的信(参见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01)。其二,2012年公布的5封格伦威德尔给东方学家安德烈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的信(参见Aloïs van Tongerloo and Michael Knüppel,Fünf Briefe A. Grünwedels an F. C. Andreas aus den Jahren 1904-1916,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ï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62,2012(1))。勒柯克的信件公布时间较晚,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勒柯克给隆德大学拉奎特(Gustaf Richard Raquette)的23封信,现存于隆德大学图书馆(参见Aloïs van Tongerloo (Geel)und Michael Knüppel (Kassel):Briefe von Albert v. Le Coq an Gustaf Richard Raquette aus den Jahren 1907-1927,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Vol. 43,2014);第二部分是勒柯克给德国语言学家裴鹏团 (Willi Bang Kaup)的104封信、勒柯克妻子Elinor von Le Coq给裴鹏团的3封信以及裴鹏团与其他汉学家来往信函涉及勒柯克的3封信(参见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Der Erwecker Manis Im Spiegel seiner Briefe an Willi Bang Kaup aus den Jahren 1909-1914, Berlin/Boston:Walter de Gruyter GmbH,2014);第三部分是勒柯克给俄国考察家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的4封信(参见Mikhail Bukharin,Albert von Le Coq and the Russian Explorers of Eastern Turkestan,Berliner Indologische Studien,Vol. 23,2016)。另外,1962年发表了勒柯克妻子的两封信(参见James Kritzeck and Elinor von Le Coq,Albert von Le Coq,Spring, 23,No. 3,1962),其内容与勒柯克相关;2015年公布了哥根廷州立大学图书馆手稿部藏语言学家缪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üller)致东方学家安德烈亚斯(Friedrich Carl Andreas)的11封信(参见Aloïs van Tongerloo and Michael Knüppel,Einige Briefe F. W. K. Müllers an F. C. Andreas aus den Jahren 1904-1910,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 Vol. 165,2015(2)),其中涉及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交往,因此也纳入本文中。他们间的交流也逐渐清晰。本文即以这些书信为主要材料,探讨他们的交流与冲突,继而明晰吐鲁番探险队对我国新疆文物的掠夺情况。
一、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前四次考察活动
1902年至1914年,德国先后四次派出吐鲁番考察队沿中国新疆丝绸之路北线进行探查,此次活动最早由格伦威德尔发起。1899年在罗马召开了东方学代表大会后,格伦威德尔得出结论,德国有必要对中国西部进行考察。在同事胡特(Georg Huth)以及与胡特熟悉的柏林药理学家勒温(Louis Lewin)的帮助下,他们筹集到军火商克虏勃(Friedrich Krupp)、企业家西蒙(James Simon)等的经济赞助,外加来自民族博物馆的公共资金和“柏林民族学协会”的捐款,组成德国首次吐鲁番考察队的经费。发起者格伦威德尔任此次考察的领队,胡特作为推动者也参与其中,此外还有博物馆技术员巴图斯(Theodo Bartus)。此次考察从1902年8月至1903年4月,带回文物46箱(每箱重约37.5公斤)(3)Albert von Le Coq, 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2. und 3.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 Leipzig: J. C. Hinrichs’sche Buchhandlung, 1926, p. 8.,其中包括梵文、回鹘文、蒙古文、古突厥文、汉文、古藏文等写本,还有泥塑、壁画、木雕等文物。
这次考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进而使各国探险家展开竞争,也推动了后续新疆考察活动的开展。1902年秋在德国汉堡举行的国际东方大会上斯坦因(Aurel Stein)分享了他在于阗发掘的文物,各国认为新疆文物丰富,考古潜力巨大。因此大会决定响应由俄国人提出成立“国际中亚研究会”的建议,在圣彼得堡设总部,欧洲各国和美国设立分会,各分会独立展开工作,与总会保持联系(4)Herbert Härtel,Marianne Yaldiz,Die Seidenstraße-Malereien und Plastiken aus buddhistischen Höhlentempeln, Berlin:Reimer,1987,p. 13. 又见陆庆夫、郭锋、王冀青编《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238页。。德国随即成立“德国中亚研究会”,由印度学家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和皮谢尔(Richard Pischel)主持工作,第二次考察活动随之被提上日程。此次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德皇威廉二世的赞助,因此又被称为“第一次普鲁士皇家吐鲁番考察队”。然而因格伦威德尔的身体原因不允许远赴中国,第二次考察队成员有待确定。
经过遴选,勒柯克最终被任命为考察队领队,这与他自己的实地考察、文物收集与整理经验以及多语种基础有关,当然也离不开格伦威德尔的推荐。首先他于1900年进入柏林民族博物馆工作,起初他跟随人类学家卢尚(Felix von Luschan)在非洲海洋部任志愿者,在随卢尚赴土耳其的萨姆遗址(Zenjirli)实地考察期间,收集了库尔德文的样本并于1903年自费出版。基于此项研究,1909年他被基尔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这为他前往新疆考察积累了实地经验。同时,他在萨姆遗址收集库尔德文样本时,还以库尔德人为例进行了人类学研究,这项工作为他在新疆的人类学研究奠定基础。其次,在语言方面,他经商期间已经熟练掌握了德语、英语、法语。进入博物馆后,开始在东方语言研讨会学习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梵语。第三,1902年勒柯克转入格伦威德尔的印度部工作。期间格伦威德尔将他介绍于柏林机械库(现德国历史博物馆)负责人乌比施(Edgar von Ubisch),帮助整理编目馆藏的武器和战利品,其中包括普鲁士腓特烈·卡尔亲王捐献的亚洲武器藏品,这使勒柯克对亚洲武器文物有了初步了解。这项工作取得出色的成绩,这种编目方法也为他之后对新疆文物的整理奠定了基础。基于上述因素,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派出时,格伦威德尔向普鲁士政府建议将勒柯克任命为领队(5)James Kritzeck and Elinor von Le Coq,Albert von Le Coq,p. 119.。
第二次考察时间自1904年9月至1905年12月,考察重点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所获文物103箱(每箱重约100-106公斤)(6)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p. 8.,这次考察期间巴图斯首次从佛教石窟墙壁剥离完整的壁画。考察结束后勒柯克并未返回德国,因为他于1905年8月18日在哈密前往敦煌途中收到格伦威德尔将于10月份赴喀什汇合的信,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前往敦煌的计划转向喀什,等待格伦威德尔到来后开始第三次考察。
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在喀什汇合,第三次考察正式开始,他们彼此间的照顾保证了考察活动的顺利进行。1905年8月18日,勒柯克在哈密前往敦煌的途中收到格伦威德尔将于10月份赴喀什汇合的信,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前往敦煌的计划,转向喀什。9月,格伦威德尔与会说一点中文的波尔特从柏林出发前往新疆,然而此次行程并没有预想的那么顺利。首先,1905年勒柯克发表关于俄国影响吐鲁番考察的报告之后,俄德展开论战,双方关系冷却(7)Ingo Strauch,Priority and Exclusiveness :Russians and Germans at the Northern Silk Road (Materials from the Turfan-Akten),L'orientalisme des marges:Eclairages à partir de l'Inde et de la Russie, Vol. 2-3,2014,p.161.。格伦威德尔原本打算途经印度到达新疆,然而因为第三次考察经费很难支撑到1905年5月底,且还需要解决第一次考察的经费问题,最终他不得不选择经俄国前往新疆。在刚开始过境时,因为过境文件不符合圣彼得堡的规定,他们在探险家格鲁杰(Григрий Гржимйло)的帮助下,获得了新文件,这使计划的行程有所延误。其次,他们在行程中寻找丢失的行李又耽误了不少时间。第三,格伦威德尔在穿越帕米尔高原时又身患重病。这些都耽搁了他们的行程。最终,格伦威德尔与波尔特于12月6日到达喀什,与10月5日已经到达的勒柯克会合,这已经比原计划晚了两个月。
然而,因格伦威德尔的身体原因,他们只好在喀什停留三周后才前往库车。考察伊始,格伦威德尔还未痊愈,不能骑马。所以勒柯克“找到一辆马车,车上铺满草再铺上垫子,车顶架起遮阳棚”(8)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102.供生病的格伦威德尔使用。为了不延缓考察进程,骑马的勒柯克与巴图斯通常先于格伦威德尔和波尔特到达目的地,他们先寻找食宿处,待“格伦威德尔到来之前,已经准备好了馕、茶水等”(9)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102.。这些细节的照料是考察顺利推进的保障。1906年6月底,勒柯克因痢疾愈发严重,不得不提前离开考察队,途经印度返回柏林。1907年4月其他成员离开新疆,在新疆的活动正式结束。此次考察以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为中心,盗走文物128箱(每箱约70-80公斤)(10)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9.。
二、考察期间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的矛盾及成因
前期互相关照且欣赏的两位先生在第二次考察时产生误解,勒柯克不满于俄德中亚委员会关于两国考察队在新疆探险范围的划分,并将原因归咎于格伦威德尔,导致双方产生误会。第三次考察期间因为剥离石窟壁画,双方产生正面冲突,经过格伦威德尔的警告后,勒柯克并未大量切割壁画,而是在之后的第四次考察中“满载而归”,双方也就此渐生嫌隙(11)陆庆夫、郭锋、王冀青编《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244页。。然而通过分析,格伦威德尔对于切割壁画的阻止并非单纯地出于保护我国新疆文物,而是出于考古学研究角度考虑,反对不加筛选的堆积文物。基于双方考察目的、学术背景、学术阵营倾向的差异分析,发现他们的矛盾实有根源。
(一)考察期间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矛盾
第二次考察之前,俄国、德国委员会协定对两国在新疆的考察范围进行划分,其中吐鲁番至哈密地区属于德国,俄国人主要在库车地区。(12)刘进宝《丝路文物被盗的历史背景》,第109-110页。格伦威德尔作为领队自然也是与俄国中亚委员会的交涉者。第二次考察时勒柯克与巴图斯先行出发,勒柯克到达乌鲁木齐后,“发现俄国人去了吐鲁番,所以他觉得协议被破坏,就去了库车勘察”(13)Ingo Strauch,Priority and Exclusiveness,p. 158.。这引起了俄国方面的不满。1906年5月,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ский)给奥登堡的信中说:
我很惊讶在库车不仅有格伦威德尔,还有吐鲁番考察队……从我到库车开始,就对吐鲁番考察队的行动表示极度担忧,我听说勒柯克到处探查,他去了阿克苏地区的沙雅县、通古孜巴什遗址而且还派人去其他地方,似乎是在寻找发掘点……我决定对考察范围予以澄清,所以与勒柯克谈话。他感到很惊讶,他告诉我他以为俄罗斯委员会已经允许格伦威德尔在库车的所有地区工作,俄罗斯委员会没有办法派出自己的探险队,他对我的到来也感到很困惑,并要求我将此次谈话转达给格伦威德尔。(14)Mikhail Bukharin,Albert von Le Coq and the Russian Explorers of Eastern Turkestan,p. 21.
可见,此时他们对于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的活动范围有所误解。格伦威德尔提及他在第三次考察前与俄国中亚委员会负责人拉德洛夫(Васлий Рдлов)达成口头协议,允许德国将考察范围扩大到整个库车地区(15)Ingo Strauch,Priority and Exclusiveness,p. 158.。因此,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等赴库车、焉耆发掘。1905年俄国中亚研究委员会派遣别列佐夫斯基兄弟前往库车考察,此时同在库车活动的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引起了别列佐夫斯基兄弟的强烈反对,他们被迫停止在森木塞姆石窟的发掘。基于之前的误会,勒柯克将他在库车考察受限的原因归咎于格伦威德尔与俄国商定考察范围时的退让。他在1909年6月4日致信裴鹏团(Willi Bang Kaup)时抱怨道:“很难理解格伦威德尔竟然将库车留给了俄国人,在那里我被严格禁止做任何工作”(16)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34.。勒柯克对格伦威德尔产生成见,继而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产生裂痕,也为他们之后的冲突埋下伏笔。
其次,在考察期间勒柯克与巴图斯剥离了柏孜克里克、克孜尔、七个星佛寺等石窟的大量壁画,这个行为引起格伦威德尔的强烈反对。1906年,他们在克孜尔活动期间,格伦威德尔负责临摹壁画、科学测量,勒柯克负责组织工作,巴图斯主要拆除壁画、包装物品,而波尔特则拍摄大量的图片。他们在一个石窟中发现大量壁画,对此格伦威德尔并不感兴趣,而勒柯克坚持要将他们全部剥离带走。经过商讨格伦威德尔在临摹后极不高兴地同意了(17)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129.。除了剥离壁画,勒柯克甚至想将“孔雀窟”窟顶分段锯开后运到柏林拼接。这个行为受到格伦威德尔的严格反对,他表示如果勒柯克坚持如此,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此破裂(18)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122.。最终,勒柯克不得不适可而止,仅在此剥离了两组装饰画。这种“斗争”情况在二人都参与的第三次考察中比比皆是。虽然此次考察勒柯克并未如愿带走所有他想收集的壁画,但他认为格伦威德尔阻止他切割壁画的原因是为之后的俄国探险队保留文物。1913年3月德国派出第四次吐鲁番探险队,此次只有勒柯克和巴图斯参加,他们肆无忌惮地揭取壁画,虽然考察时间不到一年,但所劫获文物的数量是四次考察中之最。7月13日还在新疆的勒柯克向裴鹏团写信分享他们在库车的考察时说:“我们在库车三周,巴图斯在石窟中气势汹汹地解救了格伦威德尔为他的俄国朋友留下的所有物品”(19)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128.。
(二)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矛盾根源
首先,考察目的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他们在剥离壁画时的冲突。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探险机会和对各种文物的收集导致了德国以及其他国家民族博物馆的建立”(20)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Eine neue Quelle zur Vor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Jahrbuch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Band XXV, Berlin:Gebr. Mann Verlag,1988,p. 126.。基于欧洲殖民国家关于国际认可的竞争,他们在考古研究发掘方面展开角逐,希沙利克黄金文物(21)希沙利克黄金文物(Treasure of Priam)是古典考古学家弗兰克·卡尔弗特(Frank Calvert)和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在土耳其西北海岸希沙利克发现的黄金和其他文物的宝库。目前,大多数文物收藏在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伊什塔门(Ištar Gate)、帕加马祭坛(Pergamon Altar)等都被送到柏林以充实博物馆。新疆文物的发现使其无疑成为另一个欧洲各国在考古方面竞争的场地。别列佐夫斯基(Михал Михйло вич Березóвский)给奥登堡的信中评价德国考察队时说:“这是一次补充其博物馆的远征,是为了使其辉煌程度超过其他国家博物馆”(22)Mikhail Bukharin,Albert von Le Coq and the Russian Explorers of Eastern Turkestan,p. 23.,很明显,德国四次探险队的派遣目的之一,即为拓展博物馆的藏品。勒柯克成为第二次考察的领队,还有个原因,就是他在1904年1月为民族博物馆组织购买并运输莱特纳(Gottlieb Leitner)的雕塑收藏品(23)Ernst Waldschmidt,Albert von Le Coq,Berliner Museen, 1930(3),p. 52.,民族博物馆关于印度和犍陀罗的雕塑最早来源于此。所以勒柯克在考察期间更是大肆掠夺文物。早在第一次探险队结束后,格伦威德尔意识到柏孜克里克石窟的重要性,但由于时间紧张并未发掘。第二次考察开始前,他特意叮嘱勒柯克将此地留待他到达后再发掘,但因为格伦威德尔的身体情况,他的行程再三改动,甚至在其中一封信中告诉勒柯克他将取消考察(24)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p. 71.,所以“为了给博物馆搜集一些有独特价值的藏品”(25)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 Facsimile- 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gl. Preuß.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 Turkistan, Berlin:Dietrich Reimer,1913,p. 14.勒柯克决定改变计划,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展开发掘,最终他与巴图斯在此地剥离壁画几十幅。在第四次考察中他更是无所顾忌地切割壁画。1913年7月5日他给博德(Wilhelm von Bode)的信中表示:“虽然过去了七年,我最想带回的那些壁画保存得都还不错,足以成为我们吐鲁番藏品中的精品”(26)[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54页。。足见他在四次考察中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博物馆搜集藏品。
当然格伦威德尔的考察也以此为目的。第一次考察期间,他切割了高昌T遗址的魔鬼像、东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部分(27)Albert Grünwedel,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 München:Verlag der K. B.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1906,pp. 39-40.。考察期间在给妻子的信中也透露“我们从木头沟带回了四块壁画”(28)[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79页。。虽然考察后他患严重肝硬化,但仍然说:“我得去旅行,否则博物馆可能会缺少文物”(29)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p. 62.。相比之下,格伦威德尔更关注如何能将所获文物物尽其用。第一次考察后他对如何处理这些文物提出疑问,在给库恩的信中,他表示:“把壁画整理复原将是非常困难的,我对考察结果表示满意,但我无法摆脱一种糟糕的情绪,因为我们现在所知甚少,能依赖的来源也很少,而且生产出有意义的东西又很少。”(30)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p. 42.所以他主张以考古学方法对遗址进行科学发掘。当得知柏孜克里克壁画被大量损毁后,格伦威德尔说:“如果我在1902-1903年冬天多一万马克,我就可以在那里多待一年,这样结果就会大不一样”(31)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p. 65.。可见相比短期盗挖,他更主张进行长期考古发掘。
格伦威德尔始终批评博物馆大量未经筛选的堆积物,认为“除非经考古认证并整理”(32)Caren Dreyer,Albert Grünwedel ein Leben für die Wissenschaft,In:Toralf Gabsch,Auf Grünwedels Spuren, Leipzig:Koehler&Amelang,2012,p. 28.才可展览收藏。对此,在与库恩谈论慕尼黑博物馆分布意见时,他说:“民族博物馆堆积如山的文物并未被妥善确定,继而形成可怕的压舱石占用空间,消耗劳动力……而慕尼黑应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化中,遵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以印度古物为出发点,为原始民族建立典型群体文化”(33)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p. 80.,这也是他对博物馆运作的设想。可见他并非绝对地反对切割壁画,而是反对饥不择食的掠夺。他主张从考古学视角出发对文物进行研究并构建文化环境、还原历史原貌。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藏吐鲁番考察档案中记载,第二次考察在柏孜克里克期间,勒柯克写信给柏林表示“我有些无法控制自己要将这些东西带走——不带走才是真的不负责任”“格伦威德尔如何看待此事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后来的任何报告或者信件中,都没有出现过对勒柯克的谴责”(34)[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135页。。格伦威德尔不在场时对于剥离壁画的态度不明确,但一起考察时却强烈反对。结合他考察目的之一也是为博物馆收集文物考虑,他是否从根本上反对剥离壁画值得怀疑。而从他第一次考察在新疆的行为可见他也会剥离有重要历史、艺术价值的壁画,因此其“反对意见可能主要是能否在不损坏壁画的情况下将其拆除”(35)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17.。

勒柯克参加了后三次考察队,关于第二、三次的考察过程,他先后发表了《中国新疆旅行工作报告》(46)Albert von Le Coq,Bericht über Reisen und Arbei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Ethnologie Vol. 39,1907.《吐鲁番考察记》(47)Albert von Le Coq,Exploration archéologique à Tourfan,Journal Asiatique,1909(10).《普鲁士皇家第一次新疆吐鲁番考察队的缘起、行程和收获》(48)Albert von Le Coq,A short Account of the Origin,Journey,and Results of the First Royal Prussian (Second German)Expedition to Turfan in Chinese Turki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09(2).《第二次吐鲁番探险队在木头沟附近亦都护城、胜金口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发现》(49)Albert von Le Coq,Einige Fundstücke der zweiten Turfan- Expedition aus Idiqut- Schähri,Sängim Aghiz und Bäzāklik bei Murtuq(Oase von Turfan,Chinesisch- Turkistan),Amtliche Berichte aus den Königlichen Kunstsammlungen 30,1909.《第二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经过和收获》(50)Albert von Le Coq,Reise und Ergebnisse der zweiten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Mitteilungen der Geographischen Gesellschaft in München 5,1910.《吐鲁番考古调查》(51)Albert von Le Coq,Exploration archéologique à Tourfan,Annales du Musée Guimet;Bibliothèque de Vulgarisation 35,1910.《高昌——第一次皇家普鲁士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的重要发现》(52)Albert von Le Coq,Chotscho. Facsimile- Wiedergaben der wichtigeren Funde der ersten Kgl. Preuß. Expedition nach Turfan in Ost- Turkistan,1913.《新疆的古希腊痕迹》(53)Albert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 1926.《吐鲁番探险队在新疆》(54)Albert von Le Coq,The Turfan Expedi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Art and Archaeology 22,1926.以及《德国吐鲁番考察队的行径与收获》(55)Choros Zaturpanskij,Reisewege und Ergebnisse der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n,Oriental Archiv 1912(3).(以笔名Choros Zaturpanskij发表)。第四次考察后他撰写了《第四次德国吐鲁番探险》(56)Albert von Le Coq,Die 4. deutsche Turfan Expedition,Túrán:Zeitschrift für osteuropäische,vorder und innerasiatische Studien, 1918(1).《新疆的土地和人民》(57)Albert 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 Leipzig:Hinrichs,1928.。在内容上主要以人文环境、民俗文化、行程记录为主。另外,勒柯克根据途中调查的当地民歌、谚语记录形成《吐鲁番地区的谚语和民歌》(58)Albert von Le Coq,Sprichwörter und Lied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Berlin:Teubner,1911.,这本书源于第二次考察结束后勒柯克与他的维族同伴马姆斯特(Mirab Mamasit)前往喀什途中,马姆斯特告诉勒柯克大量的当地谚语与民歌,这引起了勒柯克极大的兴趣,当他到达喀什后,格伦威德尔因行程耽搁,所以勒柯克在这段等待的时间内汇总了这部分材料并将“其中一些歌曲用留声机录制”(59)Friedrich Krälitz, Review:Sprichwörter und Lieder aus der Gegend von Turfan. Mit einer dort aufgenommenen Wörterliste, Anthropos. International Zeitschrift für Völker und Sprachenkunde, 1911(5), p. 1052.,最终整理出三百多条谚语(60)Aloïs van Tongerloo (Geel)und Michael Knüppel (Kassel):Briefe von Albert v. Le Coq an Gustaf Richard Raquette aus den Jahren 1907-1927,p. 279.。在此基础上,他还整理出词汇列表作为附录,并注明进入吐鲁番方言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外来词,以及他们在吐鲁番的变化和当地语言的融合情况。从勒柯克对于民俗、谚语的兴趣可知,他主要以人类学调查、民族学分析为主,这成为他们关系裂痕的根源之一。
最后,双方倾向的学术阵营不同也间接导致了他们的冲突。吐鲁番考察队最初由格伦威德尔发起,这源于俄国探险家克莱门茨(Дмтрий Клéменц)从吐鲁番所获文物。1898年,克莱门茨前往吐鲁番考察,并带回手稿和壁画残片。1899年末,他在前往罗马参加东方学大会途经柏林时,与格伦威德尔进行会谈,并把即将在会议上展览的文物让格伦威德尔先睹为快,这次会晤在德国掀起研究中亚的热潮,也激起格伦威德尔去新疆考察的想法。俄国学者也有去新疆考察的愿望,但并未得到财政支持,所以“他们只能通过直接或间接参与外国人的活动来实现他们的学术目标”(61)Ingo Strauch,Priority and Exclusiveness,p. 157.。1903年6月考察队经过俄国时,格伦威德尔拜访了俄国在喀什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还通过奥登堡熟悉了俄藏中亚文物(62)Caren Dreyer,Albert Grünwedel ein Leben für die Wissenschaft,p. 17.。考察队在俄国期间以及考察结束后运输物品时都受到俄国学者的大力帮助。第一次考察后,格伦威德尔给库恩的信中提及:“如果没有他们,整个事情就不可能完成”(63)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Eine neue Quelle zur Vor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p. 137.。第三次考察开始,他们在俄国期间护照遇到问题、行李丢失时,格伦威德尔立即向俄国学者格鲁杰、奥登堡等寻求帮助。考察结束回程途经圣彼得堡时,格伦威德尔在奥登堡的邀请下,与俄国学者在克莱门茨的公寓分享考察收获并展示了随身携带的文物(64)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ewechsel und Dokumente, p. 73.,可见他与俄国学者关系密切。
而勒柯克因为在库车的考察活动受到限制,外加他在新疆时被俄国领事们独断专行的态度所惊讶,结识领事后他曾委婉劝诫,但得到模棱两可的回答(65)[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116页。。这些都使勒柯克对俄国不屑一顾。但他与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George Macartney)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考察期间马继业向勒柯克提供了很多帮助。第二次考察结束后,勒柯克在喀什等待格伦威德尔期间留宿于马继业处,受到马继业夫妇的热情款待(66)Lady Macartney,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 London:Ernest Benn limited,1931,pp. 209,221.。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动荡。此时德国准备派遣第四次考察队,但刚开始就遇到问题,中国政府拒绝签发旅行许可证。这个问题立即得到解决,因为马继业承诺为他们办理自己辖区内的有效旅行证件,据勒柯克说其中还包括考古发掘许可(67)[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252页。。考察期间喀什发生动乱,马继业立即发电报告知勒柯克(68)Albert 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 p. 83.。为了感谢马继业的帮助,勒柯克两次致信外交部建议为马继业颁发普鲁士勋章(69)居政骥、许建英《关于20世纪初德国到中国新疆考察旅行的若干问题》,第113-114页。。可见,由于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感情倾向不同,导致他们关系的紧张。由此产生的影响甚至贯穿他们交流始终。
三、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矛盾的尖锐化
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在考察期间产生矛盾并出现正面冲突,然而他们的争执并不止于此,还涉及到关于考察团所获文物研究及后续考察队的派遣方面。1909年,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的矛盾,在对于摩尼教文物最初发现者的争论中变得尖锐,勒柯克甚至担心自己因此受到意外伤害。在第五次考察派出前双方再次在中亚委员会发生争论。
(一)摩尼教文物最初识别者之争
20世纪初,有关摩尼教的著作都是在宗教层面的反摩尼教论著。直到西方探险家在新疆考察后,回鹘语摩尼教文献首次曝光,使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正是这些发现构成了摩尼教研究的实际起点。而关于摩尼教文物的最早发现者,在格伦威德尔与语言学家缪勒(Friedrich Müller)之间展开了激烈争论。在这场斗争中勒柯克的态度及行动直接加剧了他与格伦威德尔的矛盾。
第一次考察期间,格伦威德尔和巴图斯发现了一批摩尼教的手稿文献。但当时他们并不清楚这批文献的来源。格伦威德尔在第二次考察前完成关于第一次考察《1902-1903年考古工作报告》的排版,在库恩的支持下由巴伐利亚学院接受出版,并请缪勒的助手烈辛(Ferdinand Lessing)校对。当他在新疆第二次考察时,缪勒已经释读出第一次考察带回的手稿(70)张广达《文书典籍与西域史地》,第104页。,确认它们是摩尼教文献。而在格伦威德尔的报告中说他在看到石窟壁画时立即想到了摩尼教(71)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Eine neue Quelle zur Vorgeschichte des Museums für Indische Kunst,p. 139.。缪勒认为格伦威德尔有抄袭行为,并动员博物馆反对抄袭。格伦威德尔同意为和平起见从印刷品中删除这段话,但坚持自己的立场(72)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187.。之后,二人关于盗窃知识产权出现了强烈的争论。格伦威德尔要求缪勒出示如何怀疑并认定此批手稿为摩尼教的过程(73)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 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83.,缪勒拒绝讨论并将此事提交博物馆法务顾问(74)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83.。
俄国学者与勒柯克分别就此事发表自己的证词或见解。由于格伦威德尔提及第一次考察结束回程中,他在圣彼得堡克莱门茨公寓向俄国学者展示了随身携带的丝绸残片和微型壁画。他们“一致认为这些物品可能与摩尼教相关”(75)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unwedel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 p. 73.。所以格伦威德尔请求俄国学者为他出具书面证词,证明在第一次考察回程经过圣彼得堡时,他已经告诉俄国学者在遗址中识别出这些物品为摩尼教(76)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34.。俄国学者为格伦威德尔出具了相关证词,此处足见格伦威德尔与俄国学术界的亲密关系。(77)格伦威德尔组建第一次吐鲁番探险队即受俄国学者影响,详见陆庆夫、郭锋、王冀青编《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第235-237页。
勒柯克起初认为俄国学者的证词挽救了格伦威德尔,但作为这件事情的亲历者,他也向律师表明了此事的过程,他说:“我们知道格伦威德尔考察回来后,如何绞尽脑汁地和我们每个人讨论微型画的内容,他认为这些画是景教的,之后又认为是拜占庭的过程,直到有一天穆勒进来说它们属于摩尼教,格伦威德尔跳起来说‘我早该知道’”(78)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34.。很明显勒柯克认为格伦威德尔抄袭成立。但俄国学者的证词明显有利于格伦威德尔。
此事在之后又有反转,勒柯克在给裴鹏团的信中说:“在缪勒的发现之后,格伦威德尔又在圣彼得堡停留了大约4个月,我不知道他对俄国人说了什么。现在克莱门茨的唯一借口是他们记错了时间”(79)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35.。同时他也表明作为第一次考察队的队员巴图斯也认为“如果有人发现摩尼教,那一定是缪勒博士”(80)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35.。相比于格伦威德尔,巴图斯在此事的态度也倾向于缪勒。而在这场争论中俄国学者又表示自己在时间记忆上有偏差,所以勒柯克更加笃定格伦威德尔抄袭之实。同封信中他甚至叮嘱裴鹏团“请您保留这封信,以防我出什么事”(81)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35.。可见此事进入白热化阶段。
经过论战,皇家博物馆总署于1909年1月2日致信格伦威德尔告知“行政总局在彻底审查了提交的所有争议材料后,无法确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上级当局进行干预”(82)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p. 189.。最终,格伦威德尔在给库恩的信中承认了缪勒在摩尼教研究的成就,他说“缪勒的研究解决了摩尼教的问题”(83)Hartmut Walravens,Albert Grünwedel Briefwechsel und Dokumente,p. 73.。
当然勒柯克倾向于缪勒的原因除了他是事情的经历者外,也与缪勒与他的友谊以及他与格伦威德尔日益积攒的矛盾有关。一方面,1909年勒柯克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之初遇到困难,最终经缪勒帮助联络专家意见,此事才得以解决(84)Aloïs van Tongerloo and Michael Knüppel,Einige Briefe F. W. K. Müllers an F. C. Andreas aus den Jahren 1904-1910,p. 433.,而且缪勒与勒柯克都参与摩尼教文献的释读整理,双方是亲密的朋友。另一方面,第一次考察结束后,缪勒对所获文物进行研究,识别出埃斯特朗格洛文字的手稿遗迹(85)Friedrich Müller,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 Schrift aus Turfan,Chinesisch Turkestan,Sitzungsbericht König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XI,1904.,而格伦威德尔在第一次考察后并未对中亚书写系统进行深入研究。当然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的关系原本就有很多问题,只是在此时尤为突显。在1909年10月给裴鹏团的信中抱怨道:“该死的格伦威德尔再次伤害了我,所有压力都再次压在我身上,使我毛骨悚然”(86)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46.。
此事使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矛盾升级,并在之后交恶。1911年5月31日勒柯克在给裴鹏团的信中直接以“偷盗的喜鹊”指代格伦威德尔,值得提及的是,喜鹊在德国文化中并非报喜鸟,而是让人联想到偷窃、厄运等不祥之事。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缪勒的矛盾使他身心俱疲,外加博物馆搬迁等行政事务阻碍了他的学术工作,因此第二次考察的调查成果《新疆古佛寺》直到1912年才得以发表,1910年他完成《新疆古佛寺》手稿之后,研究重点又回到了藏学领域,1913年10月格伦威德尔前往圣彼得堡学习藏学。关于摩尼教最初发现者之争的余波在博物馆渐渐淡化,然而他与勒柯克的矛盾却依旧明显,并在第五次吐鲁番考察队派出时再次发起争执。
(二)第五次吐鲁番考察团派出前的争论
四次吐鲁番考察结束后,德国打算派遣第五次吐鲁番考察队,此次计划最先由勒柯克提议,但在商议过程中遭到格伦威德尔的反对。此次勒柯克与格伦威德尔的冲突还要归咎于他们倾向于不同的学术阵营。第四次考察期间,因为“驻乌鲁木齐的新疆最高官员将在中国土地上发掘的外国人视为敌人”(87)[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第263页。。外加新疆物价上涨,考察团的经费并不能支持他们继续考察,所以勒柯克与巴图斯不得不返回德国。但此时勒柯克已经有再次赴新疆考察的想法及详细计划,并在回国后不久举行的吐鲁番委员会会议上提出。由于此前吐鲁番探险队考察范围在喀什到哈密,所以勒柯克将此次考察范围设定在他们从未去过的新疆南部。此时勒柯克的身体已经不能支撑他进行远程考察,因此他推荐曾在西藏完成五年考察的地理学家塔菲尔(Albert Tafel)担任领队,作为他的继承者。
但是派出计划在实施开始并不顺利,主要阻力来源于格伦威德尔。1914年5月27日勒柯克向裴鹏团致信说明了详细情况,他表明:
起初,吕德斯并不感兴趣,但博德很热情,并承诺给予经济支持。吕德斯也被鼓励向部长申请另一半必要的经费,他立即申请了。
几天后,博德突然变的畏首畏尾,不想再继续下去了。当我向他询问时,他说:“格伦威德尔教授向我报告了对拟定地区非常不利的情况”,所以他改变了主意。
幸好我知道1911年10月,格伦威德尔曾送来一份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称新疆南部地区非常重要,也很有希望。因此,我让吕德斯宣布召开新的会议,并敦促格伦威德尔出席。(88)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p. 138.
由此可知,在勒柯克提出第五次考察计划时,格伦威德尔以新疆南部并不重要为由影响博德支持考察的热情,然而他却忘记自己在1911年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疆南部对于考古工作而言很有希望。因此,始终想推进考察的勒柯克以此为由要求召开新的委员会重新商定考察计划。最终,通过勒柯克的据理力争,“博德被要求履行最初的承诺”(89)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139.,第五次考察计划继续推行。7月7日,柏林外交部致函德国驻英大使馆,希望通过其与英国政府交涉,关于塔菲尔由英国政府向马继业或者他的助手发送一封推荐信。同函还透露“这次行动已有一个来自国家资金的更大的费用补贴支持……塔菲尔博士已经打算在这个月的后半月踏上他的这次经过俄罗斯的出国旅行”(90)居政骥、许建英《关于20世纪初德国到中国新疆考察旅行的若干问题》,第114页。。可见此时考察已经势在必行。然而,战争期间俄德关系恶化,再次影响了考察队的进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次计划完整且有资金保障的考察不得不被取消。但勒柯克将此次考察计划未实施的责任归咎于格伦威德尔与俄国的关系。7月23日他给裴鹏团的信中表示“由于我们对俄国人的依赖,塔菲尔是否能去似乎又成问题,对此格伦威德尔难辞其咎”(91)Michael Knüppel,Aloïs van Tongerloo,Albert von Le Coq (1860-1930), p. 141.。基于前四次考察期间格伦威德尔与俄国学者的关系,勒柯克自然而然将此次考察未成行的原因归结于格伦威德尔,反之以勒柯克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前四次考察团对俄国的依赖,或许第五次考察队也可能选择其他路线前往新疆。
总之,格伦威德尔是勒柯克在柏林民族博物馆工作期间的上司,他们在博物馆及吐鲁番考察期间建立了友谊。然而,考察伊始,因为对所属势力范围划分问题上存在误解,他们关系产生裂痕。基于双方考察目的侧重、学术背景、学术阵营的差异,他们在对考察范围划分、新疆石窟壁画处理方面产生矛盾。这种冲突越演越烈,在摩尼教文物最初发现者的争斗中矛盾升级。1910年格伦威德尔完成关于新疆考察的著作后,中止有关新疆考察的研究,回归藏学研究。但双方的矛盾依旧存在并在关于第五次吐鲁番考察队派出时出现争执。虽然考察团最终并未成行,但基于双方日益积累的矛盾,勒柯克将此原因部分归咎于格伦威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