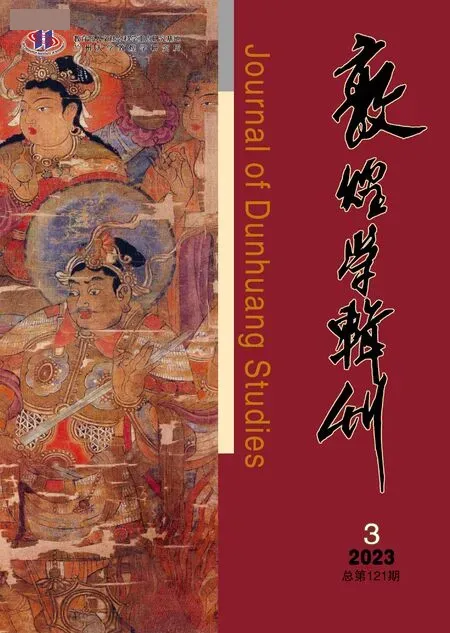新疆档案所见德国吐鲁番考察队与中国官府的交涉
蒋小莉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20世纪初,远在欧洲中部的德国加入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西北地区探险劫掠的热潮,在1902-1914年间曾先后派出四次考察队共5名成员进入新疆考察,他们是: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格里格·胡特(Georg Huth,1867-1906)、瑟奥多·巴图斯(Theodor Bartus,1858-1941)、阿尔伯特·冯·勒柯克(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和赫尔曼·波尔特(Hermann Pohrt,1877-1950),其中格伦威德尔领导了第一、第三次考察,勒柯克领导了第二、第四次考察,巴图斯作为随队技工是唯一参加了四次考察的成员。他们重点考察的地区在丝路北道沿线,除发现大量古代多语种文书,还对丝路北道的主要石窟寺群及地面寺院遗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美术考古调察。同时,为将珍贵文物据为己有,他们大规模切割石窟壁画,将大量出土文物携归,对原址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大清会典》规定:“凡洋人持照过境,归地方官照约保护,按入境出境日期咨报总署。”(1)光绪《大清会典》(1899年),中华书局,1991年重印本,第910页上栏左幅。1911年进入民国后,各地对入境外籍人士的查报制度依旧。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在新疆境内的行止,当地官员均有接待查验,并将他们出入辖境的具体日期、事由及动向等行文汇报上级,再统报外务部。这些保存至今的中国官方档案,既是考证德国考察队行程的依据,也反应出当时德人与新疆地方政府的交涉状况。
一、入境旅行许可的办理
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最早由印度学家格伦威德尔倡导建立。他当时是德国皇家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ür Völkerkunde)印度部负责人,其所著犍陀罗佛教艺术研究的开山之作《印度佛教美术》(BuddhistischeKunstinIndien)奠定了他在佛教艺术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2)Albert Grünwedel,Buddhistische Kunst in Indien, Berlin,1893;1900. 该书英译本据1900年格氏的修订版翻译:Buddhist Art in India,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Miss. Agnes C. Gibson,revised and enlarged by Jas. Burgess,London,1901,(reprint:Varanasi 1974)。。1899年10月,他在看过俄国科学院教授拉德罗夫(Wilhelm Friedrich Radloff,1837-1998)、塞尔曼(Carl Germanovich Salemamm,1849-1916)及人种学家克莱门兹(D. A. Klementz,1848-1914)等带到柏林的吐鲁番出土的数件古代艺术品后(3)这些文物得自1898年克莱门兹率队在吐鲁番绿洲的考古调查,克莱门兹以德文发表了考察报告:D. Klementz und W. Radleff,Nachrichten über die von Kaiserli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St. Petersburg im Jahre 1898 Ausgeruestete Expedition nach Turfan,St. Petersburge:Tip. Imperatorskoij Akademij Nauk,1899.,当即向普鲁士科学院提议组成德国自己的考察队前往新疆。他强调“任何耽搁都会加速这批无价的中亚史料的永久丢失”,并相信在学界关注的写本文书方面“可以期待更多的发现”(4)Along the Acient Silk Routes:Central Asian Art from the West Berlin State Museums,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New York,1982,pp. 25-27;王冀青《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收入陆庆夫等《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35-237页。。
《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公布了15件有关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的外交档案(5)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编《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1年,第155-161页。。其中第一件新疆巡府饶应祺给镇迪道按察使庆秀的札饬中,抄录了大清外务部1902年4月1日下发的公文: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1902年4月1日)承准外务部咨开: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1902年3月27日)准德穆使函称:有德国士人二名,一名旅威力,一名忽特,由德国往新疆、外蒙古等处游历,请发给护照二张,等因。除由本部分缮护照二张,札行顺天府盖印送交德穆使转给收执外,相应咨行查照,饬属于该士人旅威力、忽特持照到境时,照约妥为保护,并将入境、出境日期声复本部可也。等因,到本部院……(6)《饶应祺就格伦威德尔、胡特来新疆游历事给庆秀的札文(1902年5月15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55页。
旅威力即格伦威德尔,忽特即胡特,公文中转述德国驻京大使穆默(Mumm von Schwarzenstein)函,仅称二人为“士人”,而此次考察各地的公文呈报中亦随称二人为“德国游历士人”,并无其他头衔。此类“护照”是外籍人员入境“游历”的范围规定和通行许可。大清外务部在为进疆考察的外国人签发入境护照后,便向新疆巡抚下文申明沿途查验护照与照约保护事宜,再由地方政府逐级下达备案。待外国人入境,沿途官府需查验旅行者所持护照原件与下发复件是否吻合(7)[德]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6页。。
据高杏佛对德方档案的研究,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直至1902年1月方正式成立,格伦威德尔于当月致函德国皇家博物馆行政总监处,请求为他本人和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家胡特申请“政府公务护照”。穆默于3月27日向大清外务部申请发放两份“旅行护照”,3月30日即得到肯定答复。穆默以电报向柏林通报了结果,后将两份“大清护照”寄回德国(8)[德]高杏佛撰,陆平、王丁译《德国吐鲁番探险队持有的中国旅行许可文书原件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第102-112页。。对照中方档案日期,格伦威德尔与胡特在启程前数月即已获得正式旅行护照,且大清外务部亦早有备案。随队的巴图斯,据吐鲁番厅同知文立山所报,持有的是镇迪中俄通商总局办理的地方通行执照。
……兹查德国士人旅威力、忽特二名,执持外务部护照,于十月二十四日(1902年11月23日)抵吐,并另有德国游士巴他士一名,执镇迪通商总局执照同日到吐。又有俄属澳木省安回库达依别尔林、科帕里省商民五德尔巴耶甫二名,执持通商总局执照,注明跟随德国士人旅威力、忽特前赴吐鲁番、库车、喀什噶尔等处游历,亦同日到吐。敝厅遵即一体保护,并派妥役随德国士人旅威力等前往厅属二堡、三堡、鲁克沁、辟展等处游历,分饬各乡头目妥为照料。(9)《文立山为报格伦威德尔、胡特入出吐鲁番日期事给李滋森等的申文、焉耆府的牒文及给差役的护票(1902年12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57页。
由此可知,巴图斯的旅行许可是在考察队到达乌鲁木齐后,向中俄通商总局申请办理的。新疆建省后,俄将新疆视为其商战之场,借贸易之名扩张势力,大批俄商进入新疆。为解决日益增多的通商交涉事件,新疆地方政府于1896年4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专门机构,即新疆中俄通商总局(10)厉声《新疆对苏(俄)贸易史1600-1900》,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06页。。巴图斯所持执照多为进入新疆省游历经商的俄籍商人颁发,对持照人的活动范围有具体的规定与许可,同样需要接受沿途官府的查验。除巴图斯外,格氏与胡特也同时获得了这样的当地执照(11)参高杏佛上文中所附许可证原件照片及录文。,显然是得益于俄国领事的协助。
外国人获准持护照进入中国游历,始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定。据1861年签属的《中德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德人须持有领事馆所颁且有中国当局印信的护照方可入境游历。《大清会典》(1899)相关条款则申明:“凡洋人游历,请照则给,有照者则盖印。游历护照有各国使臣自备请总署盖印者,有由总署劄顺天府盖印者,有请出使大臣给发者,有请各直省督抚给发者,有专请南北洋大臣给发者”。德国首次派遣的吐鲁番考察队基本遵循了中德之间的条约获取入境旅行许可,而之后三次考察人员入境许可的办理则采取了诸多“便利”之举。
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的考古收获震惊了德国各界,为在掠夺中国新疆文物宝藏的国际竞争中抢得先机,德国决定尽快派遣新的考察队再赴新疆,负责筹备此次考察的是刚成立不久的“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德国委员会”(12)斯坦因(M. Aurel Stein,1862-1943)在新疆考古收获的公布促成了“国际中亚探险协会”在1902年汉堡国际东方学家会议上的正式成立,这一协会负责组织管理各国前往中亚地区的考察,总部设在圣彼得堡。随后该协会之“德国委员会”也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德国中亚考察的开展无需再靠学者个人的倡议和努力促成,该团体将负责筹措资金,落实考察并与“国际中亚探险协会”进行协调。。由于格伦威德尔坚持先完成田野材料的整理再赴考察地(13)该次考察报告最早发表在德国皇家巴伐利亚科学院年鉴第1卷第14分卷第1册中,后于1906年出版单行本:A. Grünwedel,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in Idikutschari und Umgebung im Winter 1902-1903,Abh.d. Kgl. Bay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München 1906;[德]阿尔伯特·格伦威德尔著,管平译《高昌故城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1902-1903年冬季)》,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年。,委员会委派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的义工勒柯克带领巴图斯提前出发,进行预备阶段的考察。此次考察得到了德皇威廉二世的出资支持,故又称“德国皇家普鲁士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14)自此以后的三次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德皇均有出资。。1904年9月12日考察队正式启程,在1905年12月初格氏抵达喀什之前一直由勒柯克领导。与格伦威德尔选择在一定范围内开展集中考古研究不同,勒柯克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为博物馆获取文物,此次考察他们不但割取了柏孜克里克的壁画,还获取了包括摩尼教文书在内的大量写本。正是由于勒柯克的巨大“收获”,原本是一次预备性质的考察被视为以他为领队的一次正式考察。
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两名成员于1904年10月8日经俄道入境中国时,持有的是大清驻德国钦差大臣荫昌(1859-1928)填发的护照。荫昌年少时入北京同文馆学习德文,后留学德国,恰与德国王子即后来的威廉二世同班,二人因此相熟。为使第二次吐鲁番考察尽早开展,德皇不仅在资金上给予支持,而且在外交手续上利用了驻德钦差大臣的特权。据新疆公文档案抄录,荫昌所写内容如下:
……案准大德国外部文称,本国博物院院长封礼格、副工程师巴图司现奉本国政府谕前往中国吐鲁番、喀(哈)密、喀喇沙尔城、乌鲁木齐、玛纳斯、拜城、伊犁府、喀尔喀城(即叶城)、玛纳巴什、叶尔羌(即莎车)、喀什噶尔城等处游历,应请给发护照等因前来。本大臣查与约章相符,为此填给护照,仰以上各处关、卡、津隘地方官于德员封礼格、副工程师巴图司到时,务宜遵约妥为保护,毋得留难阻滞,是所厚望。须至护照者。(15)《庆秀就是否批准勒柯克、巴图司入塔城游历事给李滋森的咨文(1904年10月31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62-163页。
公文中“封礼格”即勒柯克,将当时还是人种学博物馆义工的他称为“博物院院长”,勤杂工巴图斯称为“副工程师”。采用这样夸大的头衔,目的只有一个,使二人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为他们在新疆的活动提供方便。这与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亚考察时,在大清护照上虚称印度政府“总理教育大臣”的官衔手法一致(16)王冀青《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所持中国护照简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4期,第69-76页。。
荫昌填发的“护照”并非外务部所颁,故新疆地方官府未提前得到公文札饬。接到勒柯克一行入境塔城的报告后,当地官员“当即检查游历案卷,并无德国封礼格、巴图司其人,是否未经咨明外务部转咨来新,抑因道路窎远,文牍尚未递到,均未可知”。即便如此,新疆镇迪道按察司还是批准了勒柯克一行入境游历,并要求沿途地方官“照约保护”。据1904年11月12日时任巡抚潘效苏就发给勒柯克、巴图司护照事给李滋森的札文可知,大清外务部1904年9月28日方得到穆默为勒柯克、巴图斯办理护照的正式申请,而二人已于9月12日自柏林出发,故德使除提出“请发给护照二张”,还要求“将护照转送乌鲁木齐提督交给二人收执”。后因乌鲁木齐提督改为喀什噶尔提督并移驻喀什,且外务部护照中二人姓名音译与荫昌填发不同,导致了寄送的延误。当勒柯克、巴图斯到达乌鲁木齐并持片拜会巡府时,“询据面称,系因考查古迹而来,所经之路亦与外务部文内所指各处相符,现寓俄领事馆中。似丰礼格即雷科克、巴图司即巴都司之转音,合将护照二纸札发”(17)《潘效苏就发给勒柯克、巴图司护照事给李滋森的札文(1904年11月12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64页。。为落实护照发放一事,新疆省政府逐级下文,后由吐鲁番厅将护照转交至二人手中(18)《方鋆就已将护照、公文送交勒柯克、巴图司事给李滋森的申文(1904年12月19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68页。。
1905年12月4日格伦威德尔带领摄影师兼翻译波尔特由明约路卡入境,到达喀什后与在英国驻喀什外交代表马继业(George Halliday MaCrtney,1867-1945)处等候的勒柯克、巴图斯会合(19)马继业原名乔治·马嘎特尼,他于1890-1908年任英国驻克什米尔公使的中国事务特别助理,是英国驻新疆喀什噶尔的外交代表,1908年成为英国驻喀什噶尔领事馆首任领事,1909年升任总领事,1915年离职回国。参[英]C. P. 斯克莱因、P. 南丁格尔著,贾秀慧译《马继业在喀什噶尔:1890-1918年间英国、中国和俄国在新疆活动真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12月30日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正式启动。他们在库车、拜城境内发掘数月后再次前往吐鲁番地区,中途在焉耆锡克沁遗址的考察结束后(20)焉耆锡克沁遗址即勒柯克所称硕尔楚克。,勒柯克于1906年6月29日因健康原因离队返回喀什,后越过喀喇昆仑山口进入印度,再由印度乘船回国(21)勒柯克后将他的这次考察历程写成探险游记发表,书名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ürkistan直译为《新疆古希腊化遗迹考察记》;A. von Le Coq,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istan:Berihte und Abenteuer der II. und III. deutschen Turfan Expeditionem,Leipzig 1926. 1928年该书的英译本由巴威尔(A. Barwell)翻译出版,英文书名为Be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中译本有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考察队余下的三人在完成了在吐鲁番等地的发掘后,于1907年4月5日踏上归途,经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再经俄境于当年6月9日回到柏林。这是德国考察队在大清王朝统治下的新疆进行的最后一次探险。有关第三次考察队成员护照的问题,俄国驻乌鲁木齐领事科罗特科福(Krotkoff)1906年12月24日给时任镇迪道按察使荣霈所发照会有涉。
为照会事。兹据侨寓吐鲁番德国游历士旅威力函称,于五个月前经喀什英员马继业由德京伯林寄来本游历士等护照三张,不知此照现在何处等语,函询前来。相应照请贵道代为查询此项护照是否递到贵衙门或递到抚台衙门,如已递到,务请速交本领事转寄该游历查收可也。(22)《科罗特科福就查询由柏林寄来的格伦威德尔等人护照事给荣霈的照会(1906年12月24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3页。
由上述内容可推知,德国外交部门在勒柯克离开考察队提前返德后为留下的三人申请了正式的大清旅行护照,并自柏林寄出,然三份护照“或寄由喀什道转递,抑或径递吐鲁番厅,均未声明”。科罗特科福于1907年2月20日再向荣霈发照会,敦促其电询各方,查找德人护照下落(23)《科罗特科福为再次查询格伦威德尔等三人护照事给荣霈的照会(1907年2月20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4页。。护照是否最终送至考察队手中,档案中未有明示,然由照会可知,格氏等确实办理了外务部下发的正式入境许可,虽未持证在手,也一样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接待与保护。
1911年8月德国民族学博物馆“吐鲁番展厅”开展,前三次考察收获的重要文物经过整理,终于作为常设展品陈列展出,获得了极大的关注。德国委员会计划派遣勒柯克与巴图斯再次前往中国新疆,以期更多的“收获”。1912年初,民国政府拒绝了德国外交部为第四次吐鲁番考察队成员办理入境签证的申请,理由是无法在西北动荡的局势之下确保外国人的人身安全。当时,作为民族学博物馆正式策展人的勒柯克并未就此放弃,他与马继业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2年底,马继业致函勒柯克表示新疆局势已趋稳定,并承诺可帮助他们获得当地的旅行证件。1913年5月勒柯克与巴图斯抵达喀什,喀什提督杨缵绪在马继业的游说之下为他们发放了地区性的通行证(24)杨缵绪,系1912年1月“伊犁起义”的领导人。1912年7月与杨增新和谈并签订和议,任喀什提督兼观察使,统管天山南路。1913年1月底,杨缵绪带领部队到达喀什,不久与英国领事马继业建立了良好关系,希望与之联手制衡俄国势力在新疆的渗透与扩张。由于受到各方势力的反对,杨缵绪于1913年8月辞职离任。。《民国二年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简况》对此有记录:
德国状元修撰封礼格,随带绅士巴德司二人于民国二年五月十三日由喀什明约路卡入境,托驻喀英领事马转请喀什观察使发给护照,往南路一带游历。……现据各知事呈报前来,均经接洽保护,并称该游历寻觅山水,考查古迹,并无拍照、测绘要地情事,亦无交涉事宜。理合登明。(25)《民国二年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简况(1913年)》,《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299-300页。
勒柯克后来声称所办证件中还“包括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的许可证”试图使自己的盗掘合法化(26)[德]勒柯克著,齐树仁译《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6页;[德]勒柯克著,管平、巫新华译《新疆佛教艺术》,乌鲁木齐:新疆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18页。。而据中方档案可知,他们在新疆境内活动既未获得民国政府外交部许可,也未经位于乌鲁木齐的新疆省交涉署提前批准,所持仅是喀什观察使所发地方性旅行许可。当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动荡,新疆省也面临着内乱与边患的压力,喀什地方官员欲借英国之力制衡俄国在新疆的势力扩张,马继业乘此之机为德国考察队入境获取文物谋取便利。杨缵绪离任后,为确保通行的顺畅,德人又获取了德国驻沪领事签发的所谓“护照”,即《民国三年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简况》中所记“德国状元封礼格带绅士巴德司持该国驻沪领事护照”(27)《民国三年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简况(1914年)》,《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300-301页。。实则德国驻沪领事并无此权限,这是他们利用新疆政权尚不稳定,行政职责未及明晰的状况而采取的投机手段。马继业还为同年9月进疆的斯坦因如法炮制了获得旅行许可的流程(28)王冀青《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持中国护照评析》,《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第21-30页。。德人的此次考察开始不久,恰逢国际局势风云变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在即,勒柯克、巴图斯不得不提前返回德国。此次考察德人没能前往吐鲁番,他们采取了野蛮劫掠的方式对龟兹石窟壁画大规模割取并盗运回国,远非科学意义上的考察。
德国四次吐鲁番考察队建立的背景不同,办理进入中国新疆的“护照”即“旅行许可”的外交程序也各异。他们借游历或寻访古迹为名,破坏遗址、挖掘获取文物,然官方所发护照内容更强调“照约保护”,“毋得留难阻滞”,是晚清及民国初年因国家贫弱造成的不平等外交状况的具体写照。
二、新疆官府对德国考察队的“照约保护”
有清一代,中央王朝完全控制着新疆,并在新疆建立了行省制度,与内地各省有着统一的行政流程。辛亥革命后,杨增新被任命为新疆都督,然“其政治设施无非满清遗制”(29)黄建华《国民党政府的新疆政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82页。。遵照《辛丑各国和约》中责成各省官员“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的条款,外国人一旦获得外务部颁发的“护照”,申请所到之处的地方政府便须履行保护之责(30)《辛丑各国和约》(1901年9月7日)之附件十六:“远人来华,或通商以懋迁有无,或游历以增长学识,即传教之士,亦以劝人为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艰辛……责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饬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行,不即立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惩办,各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见王铁崖《中外旧约章》第1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19页。。德国吐鲁番考察队四次进入新疆活动期间,晚清新疆巡抚更迭三任(31)德人考察期间,清末新疆巡抚有三任:饶应祺(1895-1902年10月在任);潘效苏(1902-1905年在任);联魁(1905-1910在任)。参钱实甫编《清季重要职官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222页。,又历民国初年设交涉署处理涉外事件,有关德国考察队的中方档案体现了这些历史背景的变化,也反映了沿途地方官府对德人“照约保护”的具体内容。
1902年9月格伦威德尔带领德国第一次吐鲁番考察队进入中国境内的固勒扎,即宁远,当地俄领事安排德人住进塔塔尔人所开客栈内。宁远知县李方学接到乡约报告后前往查验,同时“传该各乡约照约妥为保护,并送给蒸盆、点心、洋酒等物,用副我宪台厚待远人之意……”(32)《李方学为报格伦威德尔、胡特到宁远县日期及活动情况给庆秀的申文(1902年9月21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55-156页。外国人在新疆境内旅行,需向沿途各地方官府报告行踪,官府则需提供沿途的安全保障。德国第一次考察队结束考察返回柏林,自吐鲁番哈拉和卓启程。吐鲁番厅同知文立山于1903年3月11日,发给差役护票如下:
为饬差护送事。照得德国游士旅威力、忽特、巴他士随带跟役二名,取道焉耆前赴库车、喀什噶尔等处游历。除牒知外,合行派差护送。为此,仰役即将该游士旅威力等五名所带行李、箱包等件,沿途小心护送至焉耆府正堂刘衙门投交,仍候印收,携回备案。去役毋得违误,致干重咎。切切。须票,右票差长福。准此。(33)《文立山就护送格伦威德尔、胡特、巴图司前往焉耆事发给差役的护票(1903年3月11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58页。
时任焉耆府知府刘嘉德在德人入境后,“当即验明,派役保护”,并继续派役护送至下一站,“移请库车厅札饬新平县一体照约妥为保护”(34)《刘嘉德为报格伦威德尔等人入出焉耆日期事给庆秀的申文(1903年4月9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58-159页。。同样的文件在有关德国第二、第三次考察队的留存档案中均有体现。各地官员对进入辖境的德国考察队成员例行护照查验、申报其出入境日期,并派役护送以保障其人身安全。
此外,新疆地方官府还承担着给外国旅行者传递信件、药品以及沿途预办粮草等事项,并办理完毕后行文报送。公布的德国考察队相关公文有《沈永清为转递格伦威德尔致科罗特科福信件事给荣霈的申文》《袁鸿祐就已将格伦威德尔信件交予马继业事给钱宗彝的移文》《李滋森为转交勒柯克、巴图司信件、药品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文》《李滋森为具领勒柯克、巴图司过境时垫付养料、柴草、价银事给乌苏厅、绥来县的札文》等多件,可见地方政府对有涉外交的公务往来相当慎重。
德国第一次考察结束后,德方为后续的考察进行铺垫,对中国地方政府的保护与接待表示了感谢,并列出致谢名单,请大清外务部进行查找(35)高杏佛《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感谢信》,罗丰主编《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320-329页。。穆默函称“中国各官在路途实力相助,惜有时无从查明是何许人,请设法俾文内所挂之人尽知该二人感谢之忱,想须究一答报之责”。奇台知县罗正湘、孚远知县王懋勋就此查找事宜,给时任镇迪道按察使李滋森报送了申文。文中抄录了外务部对新疆地方官“游历保护认真,致令外人欣感,深得交邻之道”的褒扬之言(36)《罗正湘就奉令查报曾帮助格伦威德尔等的前任官员事给李滋森的申文》《王懋勋就奉令查报曾帮助格伦威德尔等的前任官员事给李滋森的申文》,《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60~161页。。然由于格氏在清单中未给出官员的中文姓名,查找似无结果。第三次考察队,格伦威德尔曾在考古报告中提及,为了考察的方便他们尽量选择住在遗址里,“饮食等方面,由于中国官员的细心照料,安排得令人完全满意”(37)A. Grünwedel,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bericht über archäologische Arbeiten von 1906 bis 1907 Kuca,Qarasahr und in der Oase Turfan, Berlin 1912. [德]A. 格伦威德尔著,赵崇民、巫新华译《新疆古佛寺:1905-1907年考察成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考察队回德后,德方再次列出答谢人员名单请外务部查找,其中身份清楚的有鲁克沁王等。荣霈要求地方对名单上的人员“转饬查明现在住址,飞速具复,以凭核咨”(38)《荣霈就查明曾帮助勒柯克、格伦威德尔的中国官员、士民事给吐鲁番厅的札文(1908年5月25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6页。。
清末新疆地方官员逢有外国人持合法手续入境游历,以礼相待、沿途护送等均属照章办事。在清末官修《新疆图志》之《民政志》所收设立巡警的章程中,特列出专条,要求礼遇外国人并对其“竭力保护”(39)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附索引)》卷40“民政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768页。。对于外国人的探险考察,只要不涉外交纠纷,新疆官员则视其为增长见闻学识的行为,赞许其“不惮万里裹粮,探讨名物,以扩其见闻,助其学识”,并将“当时来游历者,皆萃集喀什噶尔城中”视为文化交流的雅事(40)王树枏等纂修,朱玉麒等整理《新疆图志(附索引)》卷57“交涉五”,第990页。。官员们对外国探险家不畏艰险的“格物精神”表示钦佩,而对这种“探险考察”给当地文物古迹造成的掠夺与破坏似乎并无认知。自上而下对所谓“厚待远人”的重视,反映出贫弱外交下的执政当局对外交涉只求息事宁人,而任由国宝丧失的痛心历史。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晚清、民国两个时代对监督保护游历新疆的外国人员政策上的差异,从1913年新疆外交公署《为呈赍各国游历人员报告事卷》的说明中可见一斑:
查前清军咨处文开:外人游历各处,实地调查,极有关系。嗣后凡各国人员持有外部护照赴该省及各口岸游历者,希将一切情形详报,以备查考等因。当经前交涉总局通行在案。查民国二年本署成立后,迭经令行各属:凡外国人员游历到境,照约保护并侦察有无参观何项要所,及拍照、测绘要地,及有无交涉事宜去后,据各属呈报各国游历人员入境、出境并一切情形前来。(41)《民国二年各国来新疆游历人员简况》,《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299页。
从行文中可见对外国人入境监管力度的加强。1914年6月14日袁世凯还颁布了《限制古物出口令》,可惜为时过晚且并未令行禁止。
持喀什观察使护票的勒柯克自1913年6月24日到达库车拜会官府之后,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内,再未向中国官方申报行踪。外交部新疆特派员张绍伯发文库车县,要求就德人“究竟住在该县境内作何事干,仰该县知事迅速查明具复,以凭传报”(42)《谭长谷为报勒柯克、巴图司出库车县日期及在该县活动情况给张绍件的呈文(1914年1月1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7页。。据库车县知县谭长谷申报:
查封礼格、巴德士等于本年六月游历到库,适天气炎热,不便遄行,拟休息月余,再行东下。旋因抱病调养,延缓多时,迨病全愈,始游历县境渭干河千佛洞,及往来沙雅、拜城附近一带,约近三月之久……据称,封礼格、巴德士二人所到之处,大都查访古迹,寻览山水,尚无明背约法行为。(43)《谭长谷为报勒柯克、巴图司出库车县日期及在该县活动情况给张绍件的呈文(1914年1月1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7页。
勒柯克与巴图斯于1914年2月19日由疏附县明约路卡出境回国。此事疏附县、交涉署、新疆行政公署均有呈报、备案及批文。新疆交涉署也于1914年3月30日就勒柯克、巴图斯在新疆境内考察情况向外交部提交呈文。从这一系列的公文流程可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对入境的德国考察队的活动察报在案,且“派役常随保护并防察一切违章情事”,结果是“大都查访古迹,寻览山水,尚无明背约法行为”。而此次考察,勒柯克、巴图斯活动的主要范围在库车及周边地区,在为时几个月的实地挖掘中,勒柯克采取了全然不顾及田野考古规范的“疯狂劫掠”模式。他在1913年7月5日看过克孜尔石窟后写信给博物馆:“虽然过去了七年,我最想带回的那些壁画保存得都还不错,足以成为我们吐鲁番藏品中的精品。”(44)[德]卡恩·德雷尔著,陈婷婷译《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254页。而在后来出版的《中国新疆的土地和人民——德国第四次吐鲁番考察记》中(45)A. von Le Coq,Von Land und leuten in Ostturkistan:Berichte und Abenteuer der 4. deutschen Turfanexpedition, Leipzig 1928.,他却将对古迹原址的破坏与盗割美化为对文物的“抢救”和“保护”。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劫掠,各地上报到地方交涉署给外交部的呈文中,都一致地表达了下引同样的口径:“复查该德人封礼格、巴德司二人自入境游历各属系为考查古迹、寻览山水,并无拍照测绘要地情事,亦无交涉各项事宜,已经各属保护出境”(46)《交涉署为报勒柯克、巴图司在新疆境内考察情况给外交部的呈文(1914年3月30日)》,《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第188页。。
由上可知,地方官府在德人入境辖区时都有查验护照,派役保护,并为德人在境内活动提供后勤协助,对德人出境时间及动向,也都有明确的记录,同时派出专人护送,因此,对他们在遗址的挖掘,并将大批文物运送出境的行为不可能不知。但由于当时官员对新疆古代文物的价值缺乏认知,且普遍都有惧怕列强的心理,英、俄两个帝国的驻新疆领事又充当了德国考察队的外交代言人,因此照章办事的地方官并没有记录,也绝少干涉德人的盗掘与盗运。然德人对新疆古迹破坏式的考察,并非从来没有受到阻止。德国第二次吐鲁番考察队试图在“阿图什附近靠乌什木尔干古城的三处石窟挖掘”时,据勒柯克所记:“由于道台对我们挖掘不表同意,我们只好放弃在这个遗址区里的挖掘行动。” “没有获得当地清朝官吏(道台)的批准之前,我们被禁止在任何地方进行挖掘,即使他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兴趣。”(47)[德]勒柯克著,陈海涛译《新疆的地下文化宝藏》,第110页。
历次的交涉文件中,德国考察队成员旅行目的申报批准的内容均为游历、瞻望古迹、考查古迹、寻览山水,并未有发掘古迹、收集古物以及将文物运出中国的允许。德国考察队的盗掘、盗运,均是损害中方利益的擅自行动。
三、结论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中国处于国力衰微、外交贫弱之境,上自官员士大夫,下至平民百姓,国人对西域古迹与文物的价值缺乏认知。政府官员逢外国人持证入境,一概“照约保护”,虽履行查验护照之责,但对盗掘、掠夺文物的行径不知其害,而绝少干涉。德国吐鲁番考察队活动的档案反映出的状况,是这一时期列强在中国边疆探险活动的一个缩影。德国考察队借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以本国文化官员的身份向中国官方申请入境游历考察,获得官方的照顾与保护,实则在新疆境内开挖古迹并将大量珍贵文物运输出境(48)据勒柯克公布,第一次带回古物46箱,每箱约37.5公斤;第二次带回古物103箱,每箱100-160公斤不等;第三次带回古物128箱,每箱70-80公斤;第四次带回古物150箱,每箱70-80公斤。,是对我国文物主权的侵犯,而驻疆的俄国领事及英国代表,也为这种文化掠夺提供了各种便利。这一时期纷至沓来的西方探险队造成了中国西北地区文物的大量损毁与流失,是“中国科学、文化史上的巨大损失”(49)王冀青《刘半农与美国自然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交涉始末》,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1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319页。。五四运动以后,这一局面终于改观,随着不平等条约的逐渐废除,文物主权意识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觉醒,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文物维护会等组织先后成立,外国人在华无视中国主权的考察,开始受到中国政府及广大民众的坚决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