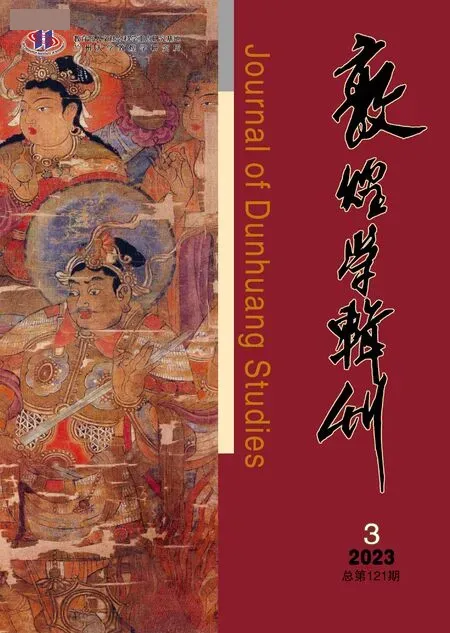王梵志诗的文学史意义
戴莹莹 邹 知
(1.四川大学 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0;2.浙江大学 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00)
1925年,刘复先生的《敦煌掇琐》出版,其中有三个从巴黎抄回的王梵志诗写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至此,学界开始了漫漫百年的王梵志诗研究之路,研究主要集中在诗集的辑录、校注、考订和诗歌的语言、思想、艺术特征等方面。学界一般认为王梵志诗的文学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诗歌内部而言,王梵志诗主要用白描、叙述和议论方法再现和评价生活,弥补了文人诗的弱点(1)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29页。;从诗歌外部而言,王梵志诗直接开创了唐代白话诗派(2)项楚等《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对唐代的通俗诗派产生了重要影响(3)张锡厚《论唐代通俗诗的兴起及其历史地位》,景生泽主编《唐代文学论丛》第9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4页。。然而,作为文学作品的王梵志诗,在诗歌史、文学史上,是否有特殊的意义?它是如何一步步推动学界“构建”唐代诗歌流派、“重写”文学史的?本文拟立足中国诗歌中“前人没有注意的传统”(4)陈致主编《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序言》第1页。下同,不再出注。,探讨王梵志诗的诗歌史、文学史意义,考察其对文学史、学术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中国诗歌具有悠久的创作传统——叙事传统和抒情传统。陈致在《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中指出:
目前海内外关于诗歌抒情传统的研究已形成一股热潮,最近又有学者提出中国诗歌还有叙事传统。这两种传统包含的范围很广,其概念也能为海内外学界普遍理解。但是我们认为创作传统的内涵其实是多方面的,可以不限于这两种思路。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中,在审美观照、体式格律、艺术表现、取题选材等许多方面都包含着对于前人创作传统的许多思考和总结。同时,古代诗学的这类理论思考本身也形成了其特有的传统。我们除了用现代学术思辨来阐释和总结这些传统以外,还可以从多种角度在古人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发现前人没有注意的传统。(5)陈致主编《中国诗歌传统及文本研究》,《序言》第1页。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今,敦煌学界都在持续挖掘这种“前人没有注意的传统”,遗憾的是尚未引起诗歌史、文学史及诗学批评领域学者足够的重视。而王梵志诗的创作实践正具备这种未被发现的传统的特征——它在取材选题、艺术表现、体式格律、审美观照等各方面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王梵志诗正好是在文人诗歌最薄弱的环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6)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前言》第29页。
一、底层暴露:取材选题、诗歌语言
(一)取材选题:“零距离”的唐代农村
王梵志诗以唐代民间生活为背景,着重描绘山野乡间的村夫村妇及其琐细日常、喜怒哀乐。不同于陶、谢、王、孟等文人笔下清静幽美的田园风光、恬静淡雅的隐居生活、自得其乐的农耕体验,王梵志诗创造了一个迥然不同的唐代农村世界。王诗中的农村田园,丑恶、贫穷、肮脏、混乱,偏重展示中国封建农村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没有半点温情,互相倾轧,充满了恶毒和怨恨。
家庭内部,父母、子女各为己利。父母抱怨儿女:“长大毛衣好,各自觅高飞。”(《人间养男女》)(7)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493页。;甚至狠毒地咒骂亲生骨肉:“腹中怀恶来,自生煞人子。”(《父母是怨家》)(8)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92页。;兄弟聚族而居,却勾心斗角、私聚家产:“当房作私产,共语觅嗔处。”“一日三场斗,自分不由父。”(《兄弟义居活》)(9)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15页。。王诗常通过前后强烈的反差对比表现各种社会关系唯利是图的本质,如:
父子相怜爱,千金不肯博。忽死贱如泥,遥看畏近著。(《父子相怜爱》)(10)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351页。
前人敬吾重,吾敬前人深。……君看我莫落,还同陌路人。(《前人敬吾重》)(11)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17页。
吾富有钱时,妇儿看我好。……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哨。(《吾富有钱时》)(12)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2页。
上述三首分别揭露父母子女、朋友、夫妇间人际交往的共性:趋炎附势,虚与委蛇。富贵时相亲相爱,没落时恩断义绝。
社会内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大多即可怜又可恨。如一些乡村、州县小吏,当其作为统治者时,他们以收受贿赂为生;当其作为被统治者时,又面临重重压力。如《村头语户主》:“在县用纸多,从吾便相贷。”(13)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13页。《佐史非台补》:“钱多早发遣,物少被颉颃。”(14)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00页。这些小官小吏往往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经济压力,有的甚至要向更贫穷的农民借贷;作为被统治者的农民间则贫富悬殊,《贫穷田舍汉》《富饶田舍儿》二诗以强烈的对比鲜明地揭露了这一巨大差异:
贫穷田舍汉,菴子极孤凄。……黄昏到家里,无米复无柴。男女空饿肚,状似一食斋。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幞头巾子露,衫破肚皮开。体上无裈袴,足下复无鞋。……门前见债主,入户见贫妻。舍漏儿啼哭,重重逢苦灾。(《贫穷田舍汉》)(15)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58页。
富饶田舍儿,论情实好事。广种如屯田,宅舍青烟起。槽上饲肥马,仍更买奴婢。牛羊共成群,满圈养肫子。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里政追役来,坐著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遣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马。(《富饶田舍儿》)(16)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53页。
穷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负债累累,承担着繁重的租税;富者却坐拥广田、牛羊成群,享受着荣华富贵。压在穷人身上沉重徭役负担,富人只在推杯换盏间解决。巨大的贫富差距令人骇然不已。
王梵志诗中的农村世界,家庭内外、社会各级的人物形成了一个“闭环”系统。无论是个人的夫妇、父子、兄弟、奴主、朋友关系,还是社会的官吏、吏民、民民关系,人们多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来交际。王梵志诗无限深入地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血缘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深刻展示人类精神的幽暗面。在现存的唐诗文献中,这是绝无仅有的。王诗突破了诗歌“言志”“缘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种种束缚,创造了新的叙事题材和叙事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唐代诗歌的总体面貌。王诗中也有少量描写闲适安逸的农村生活的诗歌,如《吾有十亩田》以农民的视角书写“遨游自取足”(17)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348页。的简单朴素的躬耕生活。但这些作品并不作为王诗的主体出现,在文学史上也不具有特异性。
陶渊明、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都写过农村生活,但他们在对客体世界观物取象时,所采取的身份、立场、审美,及对待现实的态度与王梵志诗不同。陶诗、杜诗“通常是自上而下地俯视劳动人民的生活,并给予深厚的同情”(18)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前言》第24页。,通过捕捉短暂的生活瞬间,艺术化地再现农村、表达情感。其诗歌既反映了部分现实,也变形了真实世界。而王梵志诗“则是从社会底层的内部观察人民的生活,并作为人民的一员来唱出自己的痛苦,因此它比文人诗歌更真实,更具体,更深刻。”(19)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前言》第24页。它即展现了封建农村世界,塑造了底层百姓人物群像,又展示了作者的精神和生活世界,折射出底层破落文人群体。两重世界相互交织、以诗证史,不仅反映了那个世界的历史真实和社会真实,更反映了“心灵真实”,展示了时人的内心世界(20)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前言》第26页。。这既是“史”笔,更是“小说”之笔。
(二)诗歌语言:下层社会的语言系统
中国古典诗歌强调语言的简约性、艺术性、象征性、音乐性等,但王梵志诗却以口语、俗语、方言、“脏”语等白话语言为主,采用了俗字、俗音和口语语法,通俗直白、粗鄙丑陋。不同于文人的诗歌语言,王梵志诗还原了唐代下层社会的语言系统,展现了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
王梵志诗中保存了大量的口语、俗语,包括当时人们常说的土语、流行语,如“方孔兄”“眼赫赤”“常展脚”“饭盖”“兀硉”“土角”“肥没忽”“遮莫”(21)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67、264、25、330、287、42、88、294页。等;方言如“山鄣买物来,巧语能相和”(22)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64页。的“和”,意为哄骗。“中心禳破毡,还将布作里”(23)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90页。的“禳”,为“充填”之义,此二字至今都还存在于成都方言中;“脏”语,即不见容于文人诗的粗陋之语,如“粪尿”“老烂鬼”“臰秽”“粪塠”“脓血”(24)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08、496、499、519、52页。等。诗人毫不避言“死”“尸”“臰”“秽”等词,词语虽然刺眼,却极具冲击力;通过梵志诗的用韵还可考察当时唐代民间口语俗音的真实面貌。都兴宙以《王梵志诗校辑》收录的三百余首五言白话诗为依据,归纳整理出25个韵部(25)都兴宙《王梵志诗用韵考》,《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第121-126页。,妥佳宁、何宗英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27个韵部,较清晰地展现出当时中原真实的语音状况(26)妥佳宁、何宗英《从王梵志诗韵看唐初中原方音》,《古籍研究》2008年第2期,第105-110页。;语法上,王梵志诗大量采用口语语法,与文人诗的书面语法不同。比如“是谁……”“请看……”“饶你……”“得”“有”“不”(27)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73、275、279、283、318、279页。等均是口语中常见的句法和用字,一般不用于诗歌书面语。
这些口语、俗语、方言、“脏”语,一方面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丰富了汉语词汇库;另一方面表明了诗歌作者的社会身份和文化特质,展示了唐代下层文人诗歌的语词、语意、语句、语法等语言形式之间的差异性。当诗人的社会、语言背景越趋于一致,语句、语词的选择范围越相似,语意的表达、理解越接近,诗歌也越容易形成普遍性、关联性和规范性。然而,王梵志诗使用的是唐代下层社会的语言,它具有特殊性、孤立性和不规范性,更依赖诗歌场域的建构,需要特殊性解读。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唐代诗歌语言的另一维度。
二、丑态展现:描写技法、意象编联
(一)描写技法:重“形”不重“意”
不同于文人诗的重“神”取“意”,王梵志诗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以白描、写形为主,重“形”不重“意”,注重对人物、事件进行白描式地刻画叙写。其诗以真实而精准的白描手法,勾勒出唐代民间底层百姓的“人物绘”。
文人诗即使是描写社会底层平民,也仍然是以取“神”、取“意”为主。如白居易《新丰折臂翁》:“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28)[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9页。《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29)[唐]白居易撰,谢思炜校注《白居易诗集校注》第1册,第393页。诗人截取人物面容的几处典型细节,加以艺术化地描写,刻画了折臂翁、卖炭翁两个老人形象。以小见大,字句精炼而内涵丰富,通过最具特征的细节传神达意。同样是描写老人,王梵志诗则不同。如《心恒更愿取》描写一个想娶年轻女子的糟老头:“身体骨崖崖,面皮千道皱。行时头即低,策杖共人语。眼中双泪流,鼻涕垂入口。腰似就弦弓,引气急喘嗽。口里无牙齿,强嫌寡妇丑。”(30)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48页。诗人用白描手法,刻画了一个骨瘦嶙峋、皱纹横生、流泪垂涕、缺牙驼背的农村糟老头。该诗以细致的笔触摹写了老叟的体格、脸面、姿态,眼、鼻、腰、口、齿,不遗余力地展现老翁形象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写形,而不传言外之意。这是另一种叙事传统。
古典诗歌中也有重“形”不重“意”的作品。如晋宋之际“巧构形似”“贵尚巧似”的山水诗,擅长细致描摹女性容貌的宫体诗等。不同的是,文人诗以“形似”为手段,实际上仍然以“传神”为宗旨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表现“声情神韵”,如来裕恂《汉文典注释》所言:“文章之声情神韵,全赖描写摹拟以传之,故其功用,悉在形容。”(31)来裕恂撰,高维国、张格注释《汉文典注释》,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王梵志诗虽也有夸张、比喻之语,但用意仍在真实地描写、刻画人物、事件,而非为对象注入“神韵”“灵趣”。
(二)意象编联:审丑的逆光效应
中国传统诗歌重视“意”“象”“境”的关系。以“象”达“意”,表达诗人的主观情感和体验;“意”“象”交融,建构“意境”,创造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诗歌世界。因此,诗人选择意象,往往具有一定的目的——情景交融,以达审美愉悦;虚实相生,增强诗歌表现力;新颖独特,以悦人耳目等。但大部分王梵志诗取“象”、寓“意”、造“境”的美学基调是“审丑”而非“审美”,其叙事是“丑”的,语言是“丑”的,意象的选择和编联也是“丑”的。
首先,选择“丑”的意象。写女性,王梵志诗避开仙女、美女、少女,专意于懒妇、刁妇、妒妇、小家女、穷尼姑。如《谗臣乱人国》诗中,作者以刻薄的语言讥刺丑女:“丑皮不忧敌,面面却憎花”(32)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300页。,丑女若是簪花,则丑上加丑;写官员,王梵志诗少写清官、好官,却对那些“天下恶官职”用笔甚勤,如颠倒黑白的三司长官、凶恶的御史台、不知厌足的贪官等(33)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332、337、330页。;梵志诗中面丑、心丑的人物形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各个角落,除女性、官员外,还有心毒的浮逃人、不孝子、穷苦的农民、精明算计的奸商、贪婪自私的地绅等(34)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88、592、558、164、633页。。人物之外,梵志诗中还充斥着大量“丑”的事物,如“椀鸣声”“破毡”“黄檗皮”“积代骨”“白骨”“粪塠”“虫蛆”“尸”“臰秽”“脓”“坟墓”等(35)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22、367、493、514、536、519、499、508、512页。,几无任何美感可言,反而阴冷、龌龊。
其次,“丑”意象的编联。编联多个意象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王梵志诗通过大量的丑陋意象营造出荒芜、恐怖、阴森的环境。如:“命绝抛坑里,狐狼恣意飡”“门前夜狐哭,屋上鵄枭鸣”“新坟影旧塚,相继似鱼鳞”“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36)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21、321、514、536页。等,旧塚新坟,狐鬼夜鹰,怪异瘆人。此外,作者还通过意象编联构成简单的叙事情节,奠定故事的基本格调。如《怨家煞人贼》:“怨家煞人贼,即是短命子。生儿拟替翁,长大抛我死”(37)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10页。,子女长大不念养育恩情,却想霸占父辈资产,父母怨恨子女,咒其短命。诗人以“煞人贼”“短命子”等意象编联,揭露丑恶的人情和残酷的现实。又如《天子与你官》:“饮饗不知足,贪婪得动手。每怀劫贼心,恒张饿狼口”(38)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330页。,以“劫贼心”“饿狼口”等意象,夸张地表现官吏贪得无厌的丑相。
中国传统诗歌重视“审美”,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虽也有“审丑”现象,但其写作动机与范围都与王梵志诗明显不同。如杜甫《负薪行》描写了一群年近半百仍未出嫁的怪异、粗丑的“老姑娘”:“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嗟。……至老双鬟只垂颈,野花山叶银钗并。”(39)[清]浦起龙撰《读杜心解》,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95页。这些夔州处女已半边白发,却犹结双鬟,头戴山花银钗。但诗人没有调侃和贬低这些丑女,而是表达了极大的悲悯与同情,这与王梵志诗鉴赏、把玩丑女形象迥然不同。
十九世纪西方象征派、现代主义,二十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将描写和刻画“丑”作为一个重要的创作命题,直到二十世纪才在中国美学、艺术界产生影响,而这种“反其道而行”的创作手法早在唐代王梵志诗中就已大量运用了。“丑”充斥王梵志诗歌,颠覆了读者的阅读经验和期待视野,产生“审丑”的逆光效应。诗人对“丑”的对象进行审视、观照、书写和刻画,诗歌的意、象、境因而粗俗、丑陋和畸形。
此外,王梵志诗大量运用不见于文人诗的独特意象,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对后世诗歌(尤其是宋诗)产生了重要影响。王梵志诗中大致有三类最富个性和创造性的意象:俗世意象、佛教意象和隐喻意象。俗世意象,包括俗世中的人物和事物(40)参考高国藩《论王梵志诗的艺术性》,《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5期,第129-134页。该文第二节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王梵志诗中的俗世意象,但举例大多是人物形象。其实,王梵志诗中的俗世意象远远不止人物,还包括许多事物。。人物形象如村头、贫农、土豪、懒妇、懒汉、奸商、工匠、浮逃人、乡长、贪官、御史、守财奴、达官儿、府兵等(41)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13、367、553、132、126、167、172、588、109、330、337、170、161、158页。,物象如私产、元宝、四合舍、百人斋、资产、三台、故塚、破瓮、山门、街巷、鬼朴、土孔笼、棺木、衾被、饭瓮、食瓶、籍帐等(42)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15、207、201、199、193、191页。,都是唐代底层平民生活中常见的物象。佛教意象如:三恶道、天堂、地狱、恒沙劫、五戒身、无常、业道、冥空、一队风、菴罗、未来因、悉达、生路、四果等(43)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17、213、582页。。这些晦涩的宗教术语在中国古典诗歌中难以见得,即使是在擅长用典、说理,受佛禅影响较深的宋诗中也是不见的;隐喻意象,如“馒头”喻坟墓、“翻著袜”喻颠倒众生,“鬼见拍手笑”以比喻讽刺守财奴等(44)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649、651、644页。。隐喻意象多具讽刺性,想象大胆新奇,反映民间思维。
三、民间书写:体式韵律、唐代民歌
(一)体式韵律:民间书写的异质性
体式韵律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诗人的文化水平、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方式。文人诗是一种精致书写,其体式韵律具有规范性。王梵志诗则是一种异质书写,体式韵律具有不规范性。

用字方面,梵志诗毫不避讳使用重字。如“众生眼盼盼,心路甚堂堂”“死时天遣死,活时天遣活”“生时不须歌,死时不须哭”“请看汉武帝,请看秦始皇”(48)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83、262、267、275页。等,俯拾皆是。其诗常用叠词或上下句采用相同的句式,仅改动个别字。相同的字词在一首诗中可出现两次、三次甚至更多。节奏方面,文人诗要求诗歌的节奏韵律、词汇意象富于变化,有抑扬顿挫之感。而王梵志诗却不受此限,许多诗歌意象少、句式单一、用词重复、节奏平直。如《众生眼盼盼》:“一种怜男女,一种逐耶娘。一种惜身命,一种忧死亡。”(49)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283页。四句话首二字全同,且都是二、一、二式的结构,两句之间、两联之间缺乏起伏变化。
(二)王梵志诗与唐代民歌
王梵志诗写卷中还混杂着一些民间歌谣,包括歌诗和曲词。根据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的定义:“流传在平民口上的诗歌,纯是歌咏平民生活,没染著贵族的彩色;全是天籁,没经过雕琢的工夫,谓之民歌。”(50)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年,第2页。民歌是以平民生活为创作内容,以口耳相传为传播形式的诗歌,与文人诗和白话诗都有所区别。
民间歌诗,即下层民众用于咏唱的诗篇。王梵志诗中的哪些诗歌曾经过百姓歌唱,如今难以详考。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根据《敦煌掇琐》考定二十八首王梵志诗为民歌。一方面,作者考定这些诗篇出于民间,而非佛教劝善歌。这是由于诗歌的内容反映世俗生活而不是宗教情绪,并且有些作品公然反对佛教、辱骂和尚;另一方面,作者考证这部分诗歌原本是口头歌唱文学,而非最初就是书面文学。文章通过整理写卷中大量的“音近形远”的错别字证实了这一观点(51)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02-212页。。本文以这二十八首诗歌为对象,分析王梵志诗写卷中的歌诗对唐代民歌的贡献和意义。
第一,继承了民歌关注现实的传统。《诗经》中的“风诗”是现存最早的民歌,开辟了民歌现实主义的传统,区别于《九歌》等浪漫的楚地民歌。汉魏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关注现实的精神,其诗“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元稹《乐府古题序》)(52)[唐]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92页。北朝乐府民歌更以描写的社会面广泛著称。王梵志歌诗是这一悠久传统的延续,二十八首皆为现实主义佳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民生疾苦。如《二十充府兵》等六首(53)其余五首分别是:《生时同毡被》《患夜盲症的老病卒》《儿大作兵夫》《穷汉村》《男女有亦好》,参考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该六首在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中分别题为:《你道生胜死》(第533页)《知识相伴侣》(第613页)《父母生儿身》(第502页)《富儿少男女》(第566页)《男女有亦好》(第606页)《不见念佛声》(第499页)。揭露了唐代府兵制实行后期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富饶田舍儿》等七首(54)其余六首分别是:《贫穷田舍汉》《贫穷实可怜》《夫妇生五男》《人间养儿女》《父母是冤家》《门前见债主》,参考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该七首在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中分别题为:《富饶田舍儿》(第553页)《贫穷田舍汉》(第558页,前16句)《工匠莫学巧》(第172页)《夫妇生五男》(第539页)《人间养男女》(第493页)《父母是怨家》(第592页)《贫穷田舍汉》(第558页,后4句)。反映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土地兼并普遍、贫富分化加剧、农村经济凋敝的社会现实。
第二,扩大了民歌的题材范围。民歌的题材,以表现男女恋情最多,如《古诗十九首》《子夜歌》《凤归云》等。其次是反映风土人情、边塞征战、劳动生活等题材,如《竹枝词》《战城南》等。王梵志歌诗以广大民众为表现对象,深入细致地刻画他们艰辛悲苦的生活,以冷静的笔触控诉黑暗政治和荒诞现实,字里行间充溢着批判和讽刺。如《心恒更愿取》(55)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548页。尽情嘲讽“老夫少妻”,《世间慵懒人》《家中渐渐贫》(56)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第126、132页。批判了那些好吃懒做的男女。王梵志歌诗对社会阴暗面的关注之广、批判力度之大,都是那些仍受“温柔敦厚”“风雅比兴”影响的现实主义民歌无法相比的。
第三,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增强了民歌的叙事性。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将二十八首王梵志歌诗分为六类,分别是:“府兵、战争”“地主、雇农、逃户、贫农”“官与吏”“和尚、道士”“商人、工匠”“其他(包括‘男二流子’‘女二流子’‘老夫少妻’‘家庭’‘后娘’)”(57)杨公骥《唐代民歌考释及变文考论》,《目录》第1-2页。。这些作品绝大多数以人物为中心,按身份、职业属性展开叙事。我国古代的民歌缺乏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因而具有较强的抒情性,且多为短歌,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那样的长篇纪事民歌很少。王梵志歌诗恰好弥补了这一空白,二十八首诗均以纪事见长,篇制短小。这表明我国古代民歌中存在不少“叙事短歌”这种体裁模式,部分作品具有很强的叙事性。
再论曲词,王梵志诗写卷中发现了一首《回波乐》、两首《隐去来》词。《回波乐》早在北魏时期就已出现,现存四首,均为六言四句的定格(58)参考刘尊明《词起源于民间再阐释》,《中国韵文学刊》1995年第1期,第61页。四首《回波乐》分别为李景伯、沈佺期、杨廷玉及优人失名者所作。。王梵志诗写卷《回波尔时大贼》为六言十二句,说明《回波乐》“创调之初并不受六言四句的限制,其形式远为灵活”(59)张锡厚《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第128-129页。。《隐去来》是敦煌曲,为净土歌赞《归去来》衍生之曲,用以歌颂期盼归隐净土的心声(60)参考郑阿财《敦煌净土歌赞〈归去来〉探析》,《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4期,第24页。。《回波乐》《隐去来》曲词的发现“更有力地表明词的产生还可以上溯到唐代初年,它为词学史研究提供了生动而又难得的材料。”(61)张锡厚《整理〈王梵志诗集〉的新收获——敦煌写本L1456与S4277的重新缀合》,第129页。进一步为“词起源于民间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四、结语
诗歌的审美价值和美学范式是考察文人诗歌艺术价值的重要维度,而当我们用传统的诗歌审美范式去鉴赏王梵志诗时,得出的结论就是梵志诗没有多少价值:“这些作品在诗歌的艺术价值上,自然是不高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62)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00页。“诗歌的艺术水平很低”(草莽《王梵志的诗歌价值不高》)“其诗歌的价值不是太高”(胡适《白话文学史》)(63)草莽《王梵志的诗歌价值不高》,《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7页。。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评价,原因在于我们始终用既有的学术批评话语和限定的诗歌传统来阐释王梵志诗,没有从具体的诗歌创作实践中去发现“前人没有注意的传统”,或者忽略了这种传统的意义和价值。从具体的创作实践出发,王梵志诗至少有两大重要意义:
其一,文言之外,打开了诗歌史的多重维度。过去一百年的唐代诗歌研究,除辑佚、增补、证伪外,最重要的莫过于白话诗的提出和研究。从王梵志诗的研究,到敦煌诗歌、寒山诗、拾得诗、释道诗歌的研究,学界一步步拓宽了诗歌史的书写空间,为唐代诗歌文献的整理、研究打开了多重视野。
其二,雅俗之外,打开了文学史的多重维度。在校录、注释王梵志、寒山等诗歌的过程中,学界逐渐认识到民间诗歌、俗文学的题材、语言、韵律、审美特征,并通过文学、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的交叉综合研究,充分认识到俗文学的特点、性质与研究对象,及其与俗语言、俗信仰、俗文化的融合贯通,从宏观上建构唐代俗文学。此外,在研究王梵志诗和白话诗的基础上,学者尝试系统地将禅门僧人与僧人诗作纳入诗歌史研究范畴,将唐代白话诗置于佛教诗歌的系统之中,将文学史与禅宗史交错考察,凸显文学的宗教特征与宗教的文学特征,提出白话诗派和佛教文学的关系。文学史和宗教史是交错的,不能武断分割。在鉴赏、研究白话诗、俗文学、佛教文学、道教文学时,亟需抛弃固有的批评体系,建立全新的研究和阐释模式,拓宽文学史研究的领域,重写中国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