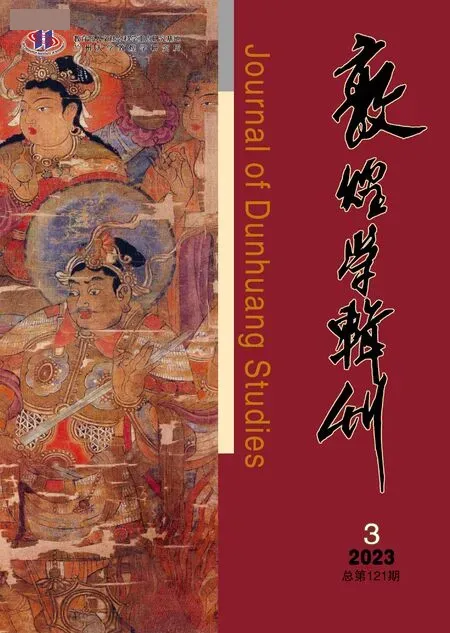S.389《肃州防戍都状》文本研究
敖特根 袁 嘉
(西北民族大学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甘肃 兰州 730030)
一、文书与研究信息
S.389《肃州防戍都状》(图1),敦煌写卷,现收藏于英国国家图书馆;黄褐色纸,首全尾残,长78cm,宽27cm;楷书,字迹工整,存42行592字。文书正背面都有文字,背面为《孝子传》(1)首尾俱残,存29行,行18-20字。所存为明达、郭臣、舜子、文让、向生等人孝顺故事。参阅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901-913页;L.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British Museum,1957,p. 254. [黄永武主编《敦煌丛刊初集》(一):《英伦博物馆汉文敦煌卷子收藏目录》,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1年,第3册,第303页;Victor H. Mair,“Lay Students and the Making of Written Vernacular Narrative:an Inventory of Tun-huang Manuscripts”,Chinoperl Papers [《中国演唱文艺研究会论集》],10 (1981),pp. 5-96;郑阿财《敦煌孝道文学研究》,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博士论文,1982年;王三庆《〈敦煌变文集〉中的〈孝子传〉新探》,《敦煌学》,第14辑,1989年,第189-220页;曲金良《变文的讲唱艺术——转变考略》,《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85-97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程毅中《敦煌本“孝子传”与睒子故事》,《中国文化》1991年第2期,第149-153页;谢明勋《敦煌本〈孝子传〉“睒子”故事考索》,《敦煌学》第17辑,1991年,第21-50页;潘重规《敦煌变文集新书》,北京:文津出版社,1994年,第1257-1275页;曲金良《敦煌写本〈孝子传〉及其相关问题》,《敦煌研究》1998年第2期,第156-164页;魏文斌、师彦灵、唐晓军《甘肃宋金墓“二十四孝”图与敦煌遗书〈孝子传〉》,《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75-90页;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253-256页;王昊《敦煌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32页;张鸿勋《从印度到中国——丝绸路上的睒子故事与艺术》,《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第51-58页;伏俊琏《敦煌小说叙录》,王萍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第9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7页;张婷、李晓明《试论敦煌变文孝道观的特点》,《孔子研究》2017年第6期,第113-120页;赵洋《中古时期孝子形象的历史书写与传播——从正史到敦煌写本》,《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4期,第25-34页;潘文竹《敦煌孝亲类说唱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第171-205页。。文书右下角盖有大英博物馆的红印(British Museum)。由于残缺,写成年份不明,荣新江先生认为唐中和四年(884)十二月中旬(2)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历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32-39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305页。。国内外很多学者先后对此残卷进行了研究,或在研究中利用了此残卷,其大体情况如下:(3)参看申国美、李德范编《英藏法藏敦煌遗书研究按号索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97-100页。

图1 S.389《肃州防戍都状》(采自IDP)
介绍:Stein,A.,1921年,第2卷,第918页:“Ch. 936. Rolled document containing official report from the frontier of Su-chou. Pl. CLXVII. [Ch. 936. 成卷的文书。含从边境城市肃州发来的官方报告。图版167。]”;(4)Sir Aurel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 II,Text.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1.斯坦因著(1921),巫新华等译(1998),第2卷,第509页;(5)[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2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向达,1939年,第397页;(6)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新第1卷第4期,1939年,第397-419页;收入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99页;郑学檬、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87-209页。Giles,L.,1957年,第254页。(7)L. Giles,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图版:Stein,A.,1921年,第4卷,图版CLXVII(Ch. 936);(8)Sir Aurel Stein,Serindia. 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Vol. IV,Plates. 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1.斯坦因著(1921),巫新华等译(1998),第4卷,图版CLXVII/167(Ch. 936);(9)[英]奥雷尔·斯坦因著,巫新华等译《西域考古图记》第4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黄永武,第3册,1981年,第302-303页;(10)黄永武主编《敦煌宝藏》,第3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第1卷,1990年,第179页;(11)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1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唐耕耦、陆宏基,第4辑,1990年,第487-489页;(12)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微缩复印中心,1990年。马托弟、韩树伟,2017年,第112页;(13)马托弟、韩树伟《三封〈肃州防戍都状〉相关问题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第111-116页。国际敦煌项目(IDP):Or. 8210/S.389。
录文:前田正名著(1964),陈俊谋译(1993),第204-205页;(14)[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唐耕耦、陆宏基,第4辑,1990年,第487-489页;王震亚、赵荧,1993年,第216-217页;(15)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荣新江,1993年,第36页;荣新江,1994年,第63-64页;(16)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所见归义军与东西回鹘的关系》,收入饶宗颐主编《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荣新江,1996年,第304-305页;郝春文,第2卷,2003年,第250-251页;(17)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2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马托弟、韩树伟,2017年,第112页。

译文:Rong Xinjiang荣新江(《通颊考》),trans. Wilhelm K. Müller,1990,pp. 283-284.
二、文书录文
从上面的文字中可以看出,前人对这件文书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然而,经过我们认真对照原始文本与有关研究成果之后发现各家录文及断句略有出入。现以国际敦煌项目(IDP)(53)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http://idp.bl.uk),简称IDP。中的文书原件图版为底本,并参照近人多种录文,将本件全文抄录、标点如下(录文中的数字表示行数):
[1]肃州防戍都 状上
[2]右当都两军军将及百姓并平善,堤[3]俻(备)一切仍旧。

又今月[15]七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充使到肃[16]州,称: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17]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十一月[18]一日并往归入本国。其退浑王拨乞[19]狸,妻则牵驮,夫则遮駈(驱),眷属细小[20]等廿已来随往,极甚苦切。余者百姓[21]、奴、客并不听去。
先送崔大夫回鹘九人内,[22]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迹)往向南,二人[23]牵龓嘉麟,报去甘州共回鹘和断事[24]由。其回鹘王称:“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25]只(质),便和为定。”其龙王弟不听充只:“若[26]发遣我回鹘内入只,奈可(何)自死!”缘[27]弟不听,龙王更发使一件,其弟推[28]患风疾,不堪充只。“更有迤次弟一人[29]及儿二人内,堪者发遣一人及十五家[30]只,得不得,取可汗处分。”其使今即未[31]回。
其龙王衷私发遣僧一人,于凉州嗢[32]末首令(领)边充使。将文书称:“我龙家[33]共回鹘和定,已(以)后恐被回鹘侵凌,甘州[34]事,须发遣嗢末三百家已来,同住甘[35]州,似将牢古(固)。如若不来,我甘州便共[36]回鹘为一家讨你嗢末,莫道不报。”
[37]其吐蕃入国去后,龙家三日众衙商[38]量,城内绝无粮用者,拣得龙家丁壮及[39]细小壹伯(百)玖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40]票阿吴等细小共柒拾贰人,旧通颊[41]肆拾人,羌大小叁拾柒人,共计贰伯伍[42]拾柒(捌)人,今月九日并入肃州,且令逐粮,居(后缺)
三、词语注释
文书中出现不少人名、职衔名、部族名、地名、机构名和日期等,现将其表列并试作解释如下(括号内数字表示出现次数):
A. 人名:崔大夫(5)、索仁安(3)、田特啰禄、泛建立、杨略奴、拨乞狸(2)
1. 崔大夫:唐政府派遣之官吏(54)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0-100页。。P. T. 1288吐蕃《大事纪年》中也出现一位“崔大夫”(730),称:“夏,赞普驻于巴局之丁丁塘。唐廷使者崔大夫前来致礼。”(55)王尧、陈践译注《敦煌古藏文文献探索集》,第14、96、159页。但二人生活的年代相差百余年。
2. 索仁安:敦煌大族,是归义军肃州防戍都的军将。索仁安之妹嫁凉州田特啰禄为妻,反映出敦煌民族间的通婚融合(56)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278页。。
3. 田特啰禄:杨富学先生认为汉姓蕃名(57)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278页。。吐蕃借用汉姓主要有郝、任、陈、田、董、申、郭、梁、张、杨、朱、杜、邓、王、彭、卢、阴等(58)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273页。。笔者认为在正确复原“田特啰禄”的藏语对音之前很难断定此人为吐蕃人。依据突厥语系部族名称qarluq(“葛逻禄”)推想,倒是像突厥人的名字。
4. 泛建立:归义军肃州防戍都的军将之一,又见于P. 2937号附断片一中第二件文书,称“肃州使泛建立”。军将索仁安出使回鹘时把肃州印交给他保管,可知他也是肃州的重要守将(59)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第32-39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07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0-100页。。
5. 杨略奴:甘州人,唐中和四年(884)12月7日出使肃州。
6. 拨乞狸:甘州吐谷浑人的首领,号称“退浑王”。
B. 职衔名:大夫(6)、军将(2)、防御使(2)、(防御)副使、回鹘王(3)、退浑王(2)、龙王(4)、可汗
7. 大夫:官名(60)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修订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2页;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第217页。。这件文书中的“大夫”指的皆为崔大夫,是御史大夫的省称。
8. 军将:状文中两处出现“军将”。第2行:“两军军将”;第4行:“军将索仁安”。郑炳林、冯培红在《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都头一职考辨》一文中提到“侍卫亲军马军‘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其职隶于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则‘每都有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承勾、押官,各以其职隶于步军司’”(61)郑炳林、冯培红《晚唐五代宋初归义军政权中都头一职考辨》,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第72页。。据此笔者推测,状文中的“两军”或许指马军和步军。
9. 防御使:官名。唐武则天圣历(698-700)年间开始设置的地方军事长官。安史之乱之后,唐于军事要地置防御使,以防御敌军入侵,一般由刺史兼之,不赐旌节。又“防御使、副使、判官、推官、巡官,各一人”(62)[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49下《百官志四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10页。参见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第218页;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第434页。。归义军在收复河西诸州后,在凉州、凉州西界、沙州、瓜州、肃州等地设立了防御使(63)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0-100页。。文书中两处出现“防御使”。第5-6行:“其大夫(崔大夫)称:‘授防御使讫,全不授其副使。’”第12行:“凉州防御使”。归义军在收复河西之后,在肃州、凉州等地设立了防御使。根据唐朝制度防御使“不赐旌节”,但是唐政府派遣崔大夫去河西,任命凉州、肃州等地防御使,说明这些地方的防御使是由朝廷任命的。值得注意的是,崔大夫没有前往归义军统治中心的瓜沙地区,肃州为其河西之行的最后一站。
10.(防御)副使:防御副使。“官名。唐玄宗天宝(742-756)后置,佐防御使掌本州岛军事防务。”(64)吕宗力主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第434页。参见前注9。
11. 回鹘王:文书中三处提到“回鹘王”。两处与索仁安有关,一处与回鹘和龙家之间的“和断事”有关。索仁安“于回鹘王边充使”,反映出归义军与回鹘间的暧昧关系。研究敦煌于阗文文书的学者认为,光启元年(885)九、十月回鹘可汗就在甘州城死亡(65)黄盛璋《敦煌于阗文P. 2741、Ch. 00296、P. 2790号文书疏证》,第41-71页。。
12. 退浑王:甘州吐谷浑部落首领,叫拨乞狸。状文中两次提到“退浑王拨乞狸”。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一月一日,此人率领吐谷浑部落大小20人,跟随吐蕃大小500余人退出甘州,一路向南,回归故土。P. 2962《张议潮变文》中记载了位于沙州西南方向一千多里的退浑国,文中亦有“吐浑王”。可见虽说公元663年吐谷浑被吐蕃征服,但亡国后的吐谷浑人“仍以部落为单位独立存在着”(66)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142页。,其世袭王室汗族仍继续保留。参见前注6。

14. 可汗(Qaγan):目前学术界关于首任甘州回鹘可汗的观点,主要有四种,其中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出现于我们所讨论的S.389号《肃州防戍都状》里的回鹘王(68)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第31-40页。。荣新江先生指出,这件文书中出现的回鹘王或可汗应当算作甘州回鹘的第一任可汗(69)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第32-39页。。文书中出现“回鹘王”和“可汗”两种称呼。我们认为“可汗”应该是龙王对“回鹘王”的称呼,这段文字应视为直接引语。
C. 部族名:回鹘(9)、吐蕃(3)、退浑(3)、嗢末(3)、龙家(3)、通颊、羌

16. 吐蕃:敦煌藏文文献Bod;突厥文《毗伽可汗碑》(735)东面第5行:Tüpüt(72)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蒙古秘史》(1240)§260:Töböd,汉语旁译作“西番”(73)[日]栗林均编《〈元朝秘史〉モンゴル语汉字音訳·傍訳汉语対照语汇》,仙台:东北大学东北アジア研究センター,2009年,第471页。。“吐蕃”是7世纪初到9世纪中叶(618 - 842)存在于青藏高原的古代藏族政权名,由松赞干布到朗达玛延续了两百多年。“吐蕃”也是古地名、古民族名。它不是汉语本有词,而是一个音译词。有学者认为该词来源于突厥语Tüpüt,是古突厥人对古藏人的称呼,由突厥语tüp和藏语bod形成tüp+bod的结构,义为“蕃部族”。藏族则自称“博巴”或“博”(bod)(74)朱宏一《再谈“吐蕃”的读音及其规范》,《辞书研究》2022年第6期,第104-116页。。
公元7世纪初,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了吐蕃王朝,定都逻些(今拉萨)。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西北地区的精锐部队被朝廷调动支援内地,导致西北边防空虚,给了蛰伏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帝国可乘之机,其逐步将势力扩大至陇右以及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地区。公元786年,最终攻占敦煌,一直延续了六十余年(75)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第1-7页。。吐蕃占领河陇之后,频频四处征战,东侵唐朝,北征回鹘,西抗大食。各族民众在吐蕃的统治下,备受压迫和奴役(76)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第24-44页。。随着日趋稳定的统治,该地区的民众进入了漫长的“吐蕃化”时期,直到吐蕃统治结束。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遇刺身亡,国内大乱,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吐蕃统治秩序迅速崩溃(77)荣新江《龙家考》,第144-160页。。
17.退浑:即吐谷浑。“吐谷浑”这个名字兼具“人名、姓氏、族号和国号等多重含义”(78)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136页。。《梁书》《南史》等南朝汉籍中又称“河南国”(79)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Wiesbaden:Harrassowitz Verlag,2017,p. 169.。“吐谷浑”的上古汉语拟音为:thɑ-jok-gun(80)Schuessler,Axel.,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7,pp. 502,259,290.。早在1921年伯希和就曾指出:“吐谷浑”之名,可追溯至最初的 *Tu’uγ-γun(*Tuyuγ-γun)或 *Tu’uγun(*Tuyuγun),唐末被简化成“退浑”和“吐浑”(81)Paul Pelliot,“Note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T’oung Pao. Second Series,Vol. 20,No. 5 (1921),pp. 323-331.杨富学等著《敦煌民族史》(第153-154页)称:吐谷浑灭国(663)后,遗民移居河东、河西诸地,被称作退浑、吐浑。。藏文文献载为’A-zha(82)Christopher I. 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 17.。斯坦因敦煌古藏文文书《吐谷浑纪年》中称作Thogon(83)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p. 169.。由南朝梁沈约(441-513)等人所撰《宋书》卷96《鲜卑吐谷浑传》开头第一句是:“阿柴虏吐谷浑,辽东鲜卑也。”同书又载:“西北诸杂种谓之为阿柴虏。”关于这一点,伯希和指出“阿柴虏”非吐谷浑人自称,而是“西北诸杂种”即西北少数民族用来称呼他们的名称。“阿柴”可以追溯到一个古老的*A-žai 或 *A-ai,传入藏语后便成了’A-ža(84)Paul Pelliot, “Note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p. 324.。有学者认为《蒙古秘史》(§256)中提到的唐兀惕人“阿沙敢不”(Aša Gambu),其名字前半部分“阿沙”(Aša)便是古藏文对吐谷浑人的称呼’A-zha的音写,说明吐谷浑人的民族身份至少在名义上在西夏帝国多元化的民族构成中得以保留(85)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p. 171-172.。青海都兰县吐谷浑人古墓的古代DNA数据显示,他们的基因是藏缅人群和阿尔泰人群的融合。此项研究第一次展示了古代吐谷浑(慕容鲜卑+古代羌人)的基因成分(86)Yu Xue-er,et al.,“Ancient DNA from Tubo Kingdom-related tombs in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revealed their genetic affinity to both Tibeto-Burman and Altaic populations”,Molecular Genetics and Genomics 297 (2022),pp. 1755-1765.。
关于吐谷浑语,伯希和、李盖提、卡拉等人进行过研究(87)Paul Pelliot, “Note sur les Tou-yu-houen et les Sou-p’i”, pp. 323-331; Louis Ligeti, “Le tabghach, un dialect de la langue sien-pi”, In: Mongolian Studies, L. Ligeti (ed.),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0, pp. 265-308; György Kara, translated by John R. Krueger, Books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More than Eight Centuries of Writing Mongolian, Bloomingto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05.,认为吐谷浑语属于古蒙古语(Ancient Mongol)东南语支(鲜卑语支)中的一个分支。2015年法国学者武阿勒撰文称:“吐谷浑语其实并不属于蒙古语族的主流,而是一种旁蒙古语(Para-Mongolic)。”(88)Alexander Vovin,“Some notes on the Tuyuhun (吐谷浑)language:in the footsteps of Paul Pelliot.”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7 (2015:2),pp. 157-166.关于“Para-Mongolic”一语,沈安筑博士指出:“The English prefix para- in the sense of ‘parallel to something’ is from Ancient Greek παρá ‘alongside,beside,by the side of’. [英语中表示“与某物平行”的前缀“para-”源自古希腊语“παρá”,意为“在旁边、旁边、靠近”。]”(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 14,n. 51);“The English construction ‘para-X’ implies a language family parallel to language family X,and not a language family which is divergently related to language family X. [英语中的“para-X”结构指的是一个平行于语系X的语系,而不是一个与语系X有分化关系的语系。]” (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 p. 14)。目前“Para-Mongolic”又被译为“准蒙古语”“类蒙古语”“蒙古语亲属语言”等等。美国青年学者沈安筑博士提出了鲜卑-蒙古语系(Serbi-Mongolic languages)的观点,并认为:“蒙古语分支(包括现代蒙古语族语、中古蒙古语及其直系祖先)和鲜卑语分支(包括契丹语、拓跋语、吐谷浑语和其他语言)是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即原始鲜卑-蒙古语的姊妹分支。”(89)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p. 13.
自六世纪末起,吐谷浑即越过南山山脉(祁连山),进入河西(90)[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22页。。七世纪末期因受唐蕃之争的余波,吐谷浑逐渐定居于从关陇大地经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广袤的土地。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吐谷浑被吐蕃所灭,诺曷钵(624-688)可汗奔凉州,率数千帐内附唐。咸亨三年(672),唐置安乐州(治今宁夏同心县东北),以诺曷钵为安乐州刺史,子孙仍世袭青海地号,直至贞元(785-805)时为止。由于吐谷浑部族逐渐与各族人民相融合,因而11世纪以后的文献中已不再有吐谷浑部落活动的记载。
对于吐谷浑人之前的辗转迁徙的历史,学界多有研究,兹不赘述。关于吐谷浑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资料包括:《周书》《南齐书》《晋书》《宋书》《北史》《资治通鉴》《魏书》《梁书》《通典》、吐蕃《大事纪年》(P. T. 1288,Or. 8212)、古藏文《礼仪问答》(P. T. 1283)等(91)Andrew Shimunek,Languages of Ancient Southern Mongolia and North China:a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rbi or Xianbei Branch of the Serbi-Mongolic Language Family,with an Analysis of Northeastern Frontier Chinese and Old Tibetan Phonology,p. 172.。

根据史籍记载,吐蕃在征服周边部落和民族的过程中,先后将苏毗改名为“孙波”(sum-pa),多弥改名为“难磨”(nam),白兰改名为“丁零”,党项改名为“弭药”(mi-nyag),吐谷浑改名为“阿柴”(’A-zha),这些民族虽然改了名字,但吐蕃并没有将他们彻底废弃,而是维持了其部落集团的存在,旧的族名仍然流传了下来。但是,史籍中没有出现吐蕃将某一民族改称为“嗢末”的情况(103)张青平《唐宋之际河西地区的嗢末考察》,兰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1页。,因此,正如陆庆夫先生所言,嗢末是一个包含多民族成分的混合体,以河陇地区吐蕃化的汉族为主体,同时也包含苏毗、羊同、白兰、党项、吐谷浑、吐蕃等部族(104)陆庆夫《敦煌民族文献论稿》,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9年,第237页。。《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862)”条载:
是岁,嗢末始入贡。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吐蕃每发兵,其富室多以奴从,往往一家至十数人,由是吐蕃之众多。及论恐热作乱,奴多无主,遂相纠合为部落,散在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宕之间,吐蕃微弱者反依附之。(105)[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0“咸通三年”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101-8102页。
嗢末最初就是以一个没有实际行政区划、没有实际部落组成的称呼,是吐蕃对其所征服的各民族的总称。但在吐蕃统治河西地区的后期,嗢末就逐渐向一个具有实力的部落集团演变。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洛门川(今甘肃武山县)讨击使论恐热(blon Khrom bzher,?- 866)举兵叛乱,和吐蕃鄯州(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尚婢婢争得你死我活,由于吐蕃高层间的内斗,对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势力有了致命的打击,而这恰好为嗢末提供了脱离吐蕃自立的机会。再加上张议潮收复河西的契机,长期受制于吐蕃的嗢末“揭竿而起”,发起“啸合”起义,自此,真正意义上的“嗢末部落”开始崛起。
势力逐渐壮大的嗢末部落,利用唐王朝和归义军的矛盾,占领了河西咽喉要地凉州。有学者认为归义军征服了嗢末,但公元848年沙州人张议潮聚众起义,于851年以沙、瓜、甘、肃、伊、西、鄯、河、兰、岷、廓等11州天宝旧图归唐(106)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49页。,此时并不包括凉州。归义军收复凉州是在861年(107)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75-298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50-152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2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第9-21页;李宗俊《晚唐张议潮入朝事暨归义军与嗢末的凉州之争再探——以新出李行素墓志及敦煌文书张议潮奏表为中心》,《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第89-97页。,而根据史料来看,在收复了凉州的第二年,嗢末便驱逐了驻守的唐军,开始向朝廷进贡,标志其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而归义军并未真正的控制也没有实力降伏“凉州嗢末”。凉州嗢末后发展为和肃州龙家、甘州回鹘等实力相当的河西少数民族部族。
五代时期,嗢末及其后裔的活动印迹还能依稀见于史料。后来逐渐融入到以潘罗支(北宋时吐蕃西凉府六谷部首领)为首的六谷蕃部,直到北宋大中祥符(1008-1016)年间,西夏占领凉州,六谷蕃部灭亡,嗢末部落也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吐蕃在河、陇很多地区均设有通颊部落,因此其民族构成较为复杂。通过敦煌文献和木简的记载显示,通颊部落的民族成分在不同的地区有所不同,如曾有吐蕃人、汉人、粟特人、突厥人,都出现在与通颊部落相关的记载中,且都是由各民族中地位较低的人组成了这一部落(128)杨铭《通颊考》,第113-117页。。而荣新江先生认为,通颊部落至少应有“羌、氐、汉、藏、粟特等系属的民众”,以及生活在西北地区的一些小部族(129)荣新江《通颊考》,傅杰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史考据文录》,第2119页。。通颊和嗢末具有一些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吐蕃在对外征战过程中,由被征服民族构成的部落或群体,其民族构成也是随着吐蕃的对外战争不断变化的。但通颊是以部落的实体形式存在,而嗢末没有部落存在,更多意义上是对一个群体的称呼。
21. 羌:《说文解字·羊部》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130)[东汉]许慎著,汤可敬译注《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38页。据陆庆夫先生介绍,羌族人有以羊角作首饰的习俗,考古工作者曾在疏勒河流域发现的火烧沟文化遗址中,在殉葬品中发现了较多的羊骨及成对的羊角,说明了该遗址就是古羌人的聚居地。又根据C14的测定,发现火烧沟先民生活的年代大约与夏朝相当,且河西地区很多地方分布有火烧沟文化类型,故说明河西地区早在夏商时期,就生活着大量羌人(131)陆庆夫《敦煌民族文献论稿》,第5页。。
陆庆夫先生指出,S. 389文书中出现的“羌”,应指党项部族(132)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敦煌研究》1998年第3期,第110-118页。。《旧唐书·西戎传》记载:“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13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8《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90页。党项本西羌之后,早先曾居住在东起今四川松潘,西至且末、鄯善,南连青海吐蕃,北与吐谷浑相属,绵亘数千里的山谷间(134)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第110页。。


岑仲勉先生对王静如的观点并不认同,他认为Tangut一名最早见于开元末突厥文《毗伽可汗碑》(138)《毗伽可汗碑》建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Tangut(“党项”)见于东面第24行。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第148、158页。,其名之存在,最少可上推于隋朝。党项与Tangut实为“同原异式之译法”。“党”对应Tang;蒙古语复数词缀为-ut,单数为-un;g-可变为h-,-n可延长为-ng,又a、o、u三元音可互相转换;“项”字在《切韵》中的读音为ghang,广州话hong,也就是说,正好Tangun变Tang-hung,便是“党项”音译。“党项”之“党”字不存在复辅音问题(139)岑仲勉《党项及于弥语原辨》,参见氏著《中外史地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8-281页。。
李志清先生认为,党项的“党”,为“大”的对音通假;“项”读“向”,和四季的“夏”读音相近。所以“党项”一词读音所对应的,应为“大夏”,中古读音之通假可为“都乡”或“党项”。史学家之所以在记录时没有写成“大夏”而是以“党项”或“大峡”代替,大概是为了避免与上古禹国“大夏”同号,故借以通假以音表名,以音明义(140)李志清《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载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宁夏文化厅文物处编《西夏文史论丛》第1辑,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0-222页。。
对于“党项”的构成,黄兆宏先生在总结周伟洲等学者的观点后,提出其是在“东起临洮、西平,西据叶护”这一范围之内所居住的鲜卑、羌、匈奴等多种族的部落集合体的总称(141)黄兆宏《“党项”涵义辨析》,《文史杂志》2013年第5期,第56-58页。。党项族在丝绸之路上不断壮大其势力,为了生存发展,逐渐开始把目标盯向了理想的生存之地——河西走廊。最终,在三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党项于景佑三年(1036)占领了河西地区,因此持续了190年的归义军政权至此画上了句号。景佑五年(1038),李元昊建国称帝,国号“大夏”(142)陆庆夫《党项的崛起与对河西的争夺》,第117页。。
D. 地名:肃州(5)、凉州(3)、甘州(6)、嘉麟
22. 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143)P. 3451《张淮深变文》记:“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文本中“肃州”凡五见,另外“城家”“本州”等指的也是“肃州”。肃州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唐大历元年(766)陷于吐蕃,大中三年(849),由张议潮收复(144)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第11-19页。。在张淮深统治(867-890)晚期,归义军设置了“肃州防戍都”的建制,以加强对河西东部地区的管理(145)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 294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2页。。在张淮深统治的末年,肃州脱离了归义军(146)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94页。。对其具体时间学界也曾进行过讨论。李军认为于中和四年(884)至光启三年(887)间,龙家等族建立了肃州政权,光启三年四月时,肃州政权已经建立,归义军也已经丧失了对肃州的控制权(147)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4页。。荣新江先生则认为光启三年十一月的文书(P. 2937号附断片一中第二件文书)表明,肃州此时尚在归义军手中。“P. 3569V《光启三年四月官酒户龙粉堆牒》和《押衙阴季丰牒》中与西州回鹘、凉州嗢末并列记录的肃州使,似也不能当作是肃州脱离了归义军之证。”(148)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第38页;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307页。根据S.0367《沙州伊州地志》,肃州地区本身就有龙家人的活动,而且肃州地区的龙家还有自己的首领。曹氏归义军晚期,统和二十八年(1010)之前,肃州政权为甘州回鹘吞并(149)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7-98页。。
23. 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地处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东端,由于其贸易、文化、交通等原因,历来是各方势力必争之地(150)参[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301-302页。。汉唐之际,凉州是中国西北地区仅次于长安的最大古城。唐前期一直是横断吐蕃和突厥的河西节度使所在地(15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49-150页。。唐中央政府多以凉州为重心对河西进行统治(152)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第77-89页。。吐蕃势力侵占河西,凉州首当其冲,广德二年(764)被吐蕃攻陷(153)前田正名认为吐蕃军最早侵入河西地区是在万岁通天元年(696)对凉州的攻击。见[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45页。。近百年之后,咸通二年(861)归义军将其从吐蕃手中夺回(154)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第77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第16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2页。。但是,在归义军攻取凉州以后,唐朝立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止张议潮势力的过分膨胀。从郓州(今山东)天平军调2500人镇守凉州,设立凉州节度使,拒绝将凉州划归归义军管辖。凉州节度使的主要作用实际上是防范归义军(155)参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第159页。。自此以后,唐政府、归义军和嗢末三股势力为凉州的控制权明争暗斗直至唐亡(156)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第77页。。但事实上,在中和四年(884)以前归义军已经失去了凉州的控制权(157)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一)》,第16页。。晚唐五代凉州地区居民主要是吐蕃、吐谷浑和嗢末,以嗢末为主(158)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第19页。。
24. 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地处河西走廊中部,历来为河西走廊重镇。“甘州”在状文中凡六见。由于回鹘步步侵扰甘州城,甘州自然也就成了肃州防戍都关注的重点。大历元年(766),甘州陷于吐蕃(159)赵晓星《敦煌落蕃旧事》,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65页。,大中三年(849)由张议潮收复。唐僖宗干符(874-879)年间,归义军和张淮深得不到唐朝的支持,势力遽衰。中和元年(881)以后,甘州被吐蕃、退浑及龙家占据。中和四年(884)以后,甘州渐渐成为回鹘可汗牙帐所在地。光启三年(887),“甘州回鹘”一名首次出现在敦煌文书中,说明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中间(160)以上见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第32、39页。陆庆夫先生认为:“此时甘州回鹘尚在草创时期,在甘州立脚未稳,……直到乾宁元年(894),甘州尚在归义军手中。”(陆庆夫《甘州回鹘可汗世次辨析》,第33页。)。唐长孺先生称:“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161)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93页。。张氏归义军时期,甘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城市,有吐蕃、吐谷浑、龙家、通颊、羌等(162)冯培红《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第22-30页。。
25. 嘉麟:唐代凉州的管辖县,敦煌文献有多处记载(163)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90页;王震亚、赵荧《敦煌残卷争讼文牒集释》,第215-216页;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归义军行政区划制度研究(之二)》,第68-73页。。
E. 机构名:防戍都
26. 防戍都:依照唐长孺、李军等人的观点,其设置年代似乎是张淮深统治(867-890)晚期(164)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94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0-100页。。张淮深统治晚期,由于归义军东部凉州、甘州地区逐渐失控,所以归义军在肃州设置防戍都,试图改变对肃州以及东部甘州、凉州的管理(165)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0-100页。。此处“都”应该是“唐末藩镇亲军的称号”(166)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6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3777页。,“一部之军谓之一都”(167)[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4“僖宗中和元年”条,第8254页。。
F. 其他词语
27. 状:书信(168)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2747页。参见吴丽娱《下情上达:两种“状”的应用与唐朝的信息传递》,杜文玉主编《唐史论丛》第11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9年,第65-70页。。 Wilhelm K. Müller译作“reports”(169)Rong Xinjiang荣新江(《通颊考》),trans. Wilhelm K. Müller,p. 283.。
28. 右:南开大学文学院刘艳红博士对敦煌文献表状笺启中“右”的含义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单独标注的‘右’表示‘如上,如前’的意思,它紧跟在官衔、姓名之后,指代写表状官员的官衔和姓名。”这跟古代的从右向左书写的格式有关(170)刘艳红《敦煌文献表状笺启中“右”的含义》,《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25-27页。。英国剑桥大学亚洲与中东研究系高奕睿(Imre Galambos)教授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认为“…在这个标题的右边是‘右’字,通常是[社司]转帖主文本的开头”;“转帖主文本的第一个字是‘右’,在这个语境中它是指‘上述的,前述的’,指的是出现在标题中的‘社司’。”(171)Imre Galambos,“Scribbles on the Verso of Manuscripts Written by Lay Students in Dunhuang”,[日]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10号,2016年,第497-522页。由此可见,S.389《肃州防戍都状》开头的“右”显然是指出现在标题中的“肃州防戍都”。
29. 将:(1)(jiàng)将帅,将领:军将;(2)(jiāng)进献:将本州岛印与崔大夫、不将与凉州防御使去不得;(3)将近:将廿人;(4)赠送:将赤騵父马一匹……上与回鹘王;(5)将要,快要:且称将去;(6)传达,表达:将文书称;(7)乃,这才,才能够:似将牢古(固)(172)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4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2375-2377页。。
30. 平善:平安,安康(173)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516页。。
31. 堤俻:同“堤备”,意为“防备”。“堤”为“隄”的换旁异体,“俻”同“備(备)”。(174)见黄征《敦煌俗字典》,第13页;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472页。
32. 家:本件中“家”字共出现10次,分别为:崔大夫到城家、肃州旧人户十家五家、十五家只(2)、龙家(3)、嗢末三百家、共回鹘为一家。
归纳起来,文书中的“家”字有四种含义:第一,用在住户的量词:肃州旧人户十家五家、十五家只、嗢末三百家。其中“十家五家”为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175)鲁西奇《中国古代乡里控制体系的基本结构》,《南国学术》2018年第4期,第562-574页。;第二,家庭也:共回鹘为一家;第三,此处的“城家”,当为“家”之字义的衍伸,指的应该是归义军在肃州设置的防戍都等衙门;第四,关于“龙家”,荣新江指出:“龙家的‘家’是一种人、一类人的意思,在此应是‘部落’的同义语。龙家应即龙部落,其确切的含义是以‘龙’为号的一种部落组织或其成员。”(176)荣新江《龙家考》,第144页。
33. 其:本件中“其”共出现14次,是一个十分活跃的词。文中主要用作代词,表示“(他、它、他们)的”或“这”、“那”等意思。

36. 联:量词,用以称量成对的事物。犹言“对”“双”(179)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244页。。
37. 取:(1)拿,特指借取:取前件妹,兼取肃州旧人户十家五家;(2)听取,采纳:取可汗处分(180)参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738-1739页。。
38. 前件:复指前文提及的人、物、事(181)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615页。。
39. 得:(1)行,可以:去不得、得不得;(2)令,使:须得龙王弟及十五家只(质);(3)了:拣得龙家丁壮及细小壹伯(百)玖人(182)参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461页;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2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829页。。
40. 本国:另有“入国”说。所述“七人便随后寻吐蕃踪亦(迹)往向南”等,是因为吐蕃、吐谷浑故地在祁连山以南之故(183)[日]前田正名著,陈俊谋译《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23页。。正如荣新江教授所言,“我们似乎不应把这里的‘国’解为具有‘独立王国’意义的国”(184)参荣新江荣新江《龙家考》,第150页。。
41. 遮:掩盖,掩蔽,掩护。
42. 细小:家眷、妻小(185)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2272页。。
43. 苦切:非常痛苦(186)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182页。。
44. 百姓、奴、客:从中可以窥见吐谷浑部落组织的人员构成。
45. 踪亦:踪迹。
46. 龓:唐长孺以下诸家的录文均检录为“拢”(唐长孺)、“拢”“栊”“胧”等,实为“龓”字。义为“马笼头”。“牵龓”即“牵马的笼头,牵马”之意。今据原文图版改正。早期研究者从缩微胶卷中抄录了敦煌文书,难免会出现一些错误。龓字的各种录文,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有胧、栊、栊、拢等几种。右偏旁“龙”或“龙”,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左偏旁。出现了“木”“月”“扌”等不同形式(187)参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1602页。。
47. 只:通“质(质)”。用作抵押的人或物(188)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2704页。。文书中有“充只”“入只”等词。
48. 可:通“何”。奈可:为何。
49. 缘:因为,由于(189)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5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8年,第3433页。。
50. 迤:“迤”字本义为斜行,地势曲折延伸(190)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6卷,第3817页。。此处可理解为“顺延”。“更有迤次弟”就是换成第二个弟弟。
51. 衷私:私下、背地(191)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2710页。。部分学者将“衷私”理解为龙王的名字,显然有误。
52. 首令:同“首领”。
53. 已后:同“以后”。
54. 已来:同“以来”。用在数量词后,表概数,犹“左右”“上下”(192)张涌泉等《敦煌文献语言大辞典》,第2481页。。
55. 丁壮:指能担任赋役的成年人,犹“壮丁”(193)参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1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86年,第3页。。
56. 逐:寻求,追求(194)徐中舒主编《汉语大字典》第6卷,第3839页。。逐粮:追逐粮食。让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去逃荒。
57. 状文中的“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语,不知是人名还是部落名,近人尚无定论,出现多种不同断句,甚至有些混乱。S.4276《管内三军百姓奏请表》记有“通颊退浑十部落”,据此,将“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或许可以理解为退浑部落之称,但是这种可能性极小。不少学者对S.389号文书进行转录时在“退浑”后面加了顿号,把这些名称与“退浑”并列,这显然是不妥当的(195)冯培红《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第25页;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3页;杨富学等《敦煌民族史》,第211页。。文中“达票”一语出现两次,似当系退浑官衔,估计与P. 2569中的“官酒户马三娘”(196)唐长孺《关于归义军节度使的几种资料跋》,第294页。等相同的结构,那么“拱榆昔”和“阿吴”应该是人名。笔者认为吐谷浑与吐蕃言语相通,“达票”似乎可以作为藏语解释。藏语中把掌马官叫做“达本”(rta-dpon),窃以为“达票”有可能是类似于“达本”的一种官衔。
四、文书内容解读
此件文书是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十二月中旬归义军在肃州设置的防戍都上给沙州归义军节度衙门的报告。它的出土地点也能证明当时这份报告应该已送到沙州,即敦煌。归义军在沙州和肃州之间设立了走马使,其主要职责就是传递信息(197)李军《晚唐五代肃州相关史实考述》,第92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此份报告应该是由走马使送到沙州的。报告中谈到了自中和四年10月30日至12月9日的大约40余天内发生在肃州、甘州、凉州等地的一些事情。主要记载了归义军与朝廷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在西迁回鹘部众的冲击下甘州部落联盟瓦解时的情况。从用词来看,这件状文具有明显的口头语体特点,并且基本按照唐代状文的行文格式书写。现将具体内容解读如下:
肃州防戍都状上:
统领两军之军将与百姓一同平安顺遂,守备一切如旧。
10月30日,朝廷派崔大夫到肃州,来任命肃州防御使一职。归义军肃州防戍都副使、军将索仁安等人便将州印交于崔大夫执掌。崔大夫说:“我来任命防御使官员一事现已完成,不再安排副使的职位。”12月6日,索仁安率随从近二十人,向东出发。此去一是出使回鹘,并向回鹘王贡送赤騵马一匹,白鹰一双;二是去接回之前嫁给凉州人田特啰禄的妹妹,其妹夫现已身亡,故前去将她和肃州的十多家旧户一同接回。在索仁安出发前,崔大夫命他将肃州印交于凉州防御使,否则不能离开。但索仁安在离开之际,嘴上答应会按照吩咐将印交于凉州防御使,但在离开时避开了崔大夫,私自将印留给了另一位将领泛建立。
12月7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出使肃州,说道:“甘州城内的三百个吐蕃人连同家眷共五百余人,以及退浑王拨乞狸等于11月1日回归故里。退浑王拨乞狸一家,妻子则牵着马,马上驮着东西,丈夫则掩护着家眷,共二十来人跟随着吐蕃人一同离去,其情景异常艰苦和凄凉。剩余的百姓、奴仆和门客等没有一同前往。
之前护送崔大夫前往肃州的九个回鹘人中,七人追随吐蕃的踪迹向南行去,另外二人则骑马前往嘉麟,前去凉州汇报甘州与回鹘的和断情况。回鹘王说:“龙王必须将自己的弟弟及十五户龙家百姓作为人质交给我们,以便决定讲和之事。”但是龙王的弟弟并不同意去当人质,说道:“把我送去回鹘作人质,岂不是自寻死路!”由于弟弟并不服从,龙王又换了一位使者[前去游说],但弟弟还是以风疾为由拒绝去当人质。于是龙王说:“我打算将我的第二个弟弟作为替代人选,从他和他的两个儿子中选出一个愿意担此重任的人,再加十五户百姓前去充当人质,这个方案是否可行,一切听可汗定夺。”前去沟通此事的使者目前还未归来。
甘州的龙王私下派遣一名僧人出使凉州(198)河西人口中僧尼占很大比例,尤其吐蕃统治时期僧尼人数剧增(参荣新江《归义军及其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初探》,第26页),说明僧尼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僧人充使现象不乏其例(冯培红、姚桂兰《归义军时期敦煌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僧使交往》,收入郑炳林主编《敦煌佛教艺术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0-466页。),前去向凉州的嗢末首领求援。信中写道:“龙家和回鹘即使议和成功,也担心日后回鹘再来侵扰。为了保障甘州的安全,你方务必要派遣约三百户嗢末人共同驻守甘州,这样城防才会牢固。如果不答应,龙家会联合回鹘一同讨伐你嗢末,届时不要说没有提前向你们通报。”
在吐蕃归故国之后,龙家部族的高层商量了三日,从城内彻底断粮的民户中挑选了年轻力壮的龙家男性和家眷109人,退浑达票拱榆昔、达票阿吴等的家眷72人,旧通颊40人,羌族老少37人,共计258人,于12月9日一同进入肃州乞讨食物,居住(后缺)。
根据事件的前后顺序,我们将本状内容大致梳理如下:
10月30日,朝廷派崔大夫到肃州,来任命肃州防御使一职。
12月6日,归义军肃州防戍都副使、军将索仁安率随从近二十人,向东出发,出使回鹘。此时崔大夫尚未离开肃州。
12月7日,甘州人杨略奴等五人出使肃州(他们很可能是龙王派来的)。他们向肃州方面转告了甘州城内发生的三件大事:(1)11月1日,甘州吐蕃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一家撤出甘州,回归故里;(2)甘州与回鹘的和断情况;(3)甘州的龙王私下派遣一名僧人出使凉州,前去向凉州的嗢末首领求援。
12月7日后不久,崔大夫命令之前护送他前往肃州的九个回鹘人中的七人追踪吐蕃的行踪,向南行进。另外二人被派往嘉麟,向凉州节度使衙门汇报甘州与回鹘的和断情况。
12月9日,从甘州来的258人一同进入肃州乞讨食物。肃州防戍都衙门估计从他们的口中得知当时甘州城内严重缺粮,也就是说,文书最后一段文字的消息来源不是杨略奴等人,而是这258人。
五、关于文书内容的几点思考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崔大夫被朝廷派往肃州任命肃州防御使。抵达肃州后,归义军肃州防戍都副使索仁安等立即将肃州印交给了他。然而,崔大夫却意外地宣布取消了防御副使的职务,导致索仁安对崔大夫的这个决定非常不满。虽然如此,索仁安不能公开对抗朝廷的官员,只能以出使回鹘为借口向崔大夫请示。这一计划一方面表明归义军不愿意放弃对肃州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有意拿回鹘来威胁崔大夫,以示朝廷不支持他们的后果。这与甘州龙家在请求凉州嗢末支援时用回鹘来威胁嗢末的情况相似。崔大夫自然也明白索仁安欲出使回鹘的用意,因此他采取了一种策略,决定将肃州印交给索仁安,并要求他在抵达凉州后将肃州印交给凉州防御使。换句话说,崔大夫并没有明确反对索仁安出使回鹘,但要以废除肃州防戍都的建制作为代价。令崔大夫意外的是,索仁安答应了这个要求,但他临行前却没有携带肃州印,而是将其留给了另一位将领泛建立。索仁安深知如果没有了印,肃州防戍都衙门就会失去其合法性。由此可见,当时朝廷和归义军的关系非常微妙且复杂,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和不信任。朝廷对藩镇势力过于担忧,这在安史之乱后尤为明显,正是这种担忧最终导致了河西地区的失控以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建立。在朝廷的眼里,归义军和回鹘等少数民族政权都是一回事。这种中央和地方相互不信任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并不罕见。
2.从杨略奴等人出使肃州,并向肃州方面汇报甘州城内发生的事情来看,甘州的龙家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依附于归义军。另外,虽然回鹘兵临城下,甘州局势异常动荡,但是回鹘人并非将甘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在甘州与肃州之间依然有人员往来。
3. 据《资治通鉴》记载,乾符元年(874),活动在甘、凉一带的退浑和嗢末似乎在额济纳河一带合力击败“进入走廊内部而立足未稳的回鹘”(199)荣新江《甘州回鹘成立史论》,第35页。。因此,在退浑撤出甘州的情况下,为了有效地抵御回鹘人的入侵,甘州的龙家向凉州的嗢末寻求救援,说明9世纪中后期的嗢末已经是相当强大的势力。
4. 在回鹘人围困甘州并归义军势力日渐衰微不能控制局势的情况下,本来依附于归义军的少数民族就开始纷纷脱离,自谋生路。甘州吐蕃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拨乞狸等在此紧要关头离开甘州回归故里。另外,当时甘州城正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搞得人心惶惶。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自然引起了当时与回鹘争夺甘州的主要部族龙家权贵阶层的高度重视。于是,龙家各衙门里的官员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此事。这个会议持续了三天,讨论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不管怎么样,他们做出了最后决议:从甘州城内彻底断粮的民户中挑选出258人,让他们“组团”到肃州有粮食的家中去乞讨食物。由于这件文书尾部残缺,这些人就食肃州的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断定这只是一次“令民逐粮”事件,不能视作甘州龙家及其他部落从此“退往肃州”“撤入肃州”“退出甘州”,甘州从此变成了一座空城。如果龙家退出了甘州,也就没必要向凉州的嗢末首领求援。另外,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状文中给出了此次外出逐食的具体人数,而且书写者此处特意采用了汉文的大写数字。很显然,用大写的数字不容易篡改,也能反映肃州防戍都衙门对此事件的重视程度。挑选的258人中,有龙家109人、退浑72人、通颊40人、羌37人;其中既有壮丁,又有儿童,说明当时甘州的龙家高层充分考虑了“逐粮团队”成员的民族、年龄和体力等诸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