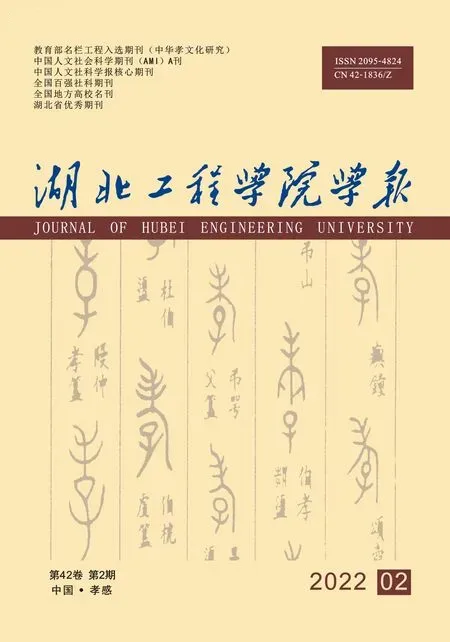天子之孝异于庶人
——论宋代士大夫对皇帝孝道的规范
李贺亮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
孝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价值体系中最重要的德目,《论语·学而》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儒家思想中,孝是人伦之本,是践行仁的出发点,同时也是政治教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的家庭、社会、国家深具影响。《孝经》一书的出现,标志着儒家孝治理论的系统化。汉代极为推崇《孝经》,提倡“以孝治天下”,并通过政令、法律、教育、人才铨选等系统将孝治理念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把尽孝与治国联系在一起,使得“孝”成为儒家政治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价值。由汉奠定的“以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在后世得到了延续,被奉为“金科玉律”[1]17。《孝经》对传播和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也为历代帝王、学者所推崇与重视。
在儒家传统“孝治天下”的意识形态下,孝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根本和家庭伦常的表现,更是构建社会整个秩序的重要基础,关乎国家大事。天子作为国家的道德典范及风化的最大关键,天子之孝更是整个政教系统的重心所在,具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汉晋隋唐时期,《孝经》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主要是统治者以此强调臣子在家尽孝,为国尽忠,通过“移孝为忠”的理念来规范臣子的忠心,以及对百姓通过孝的教化实现基层政治稳定,而天子之孝的政治作用在当时并未引起臣僚们的重视。到了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完善,人才铨选不再依靠举孝廉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有客观标准的科举制度来实现,而且三纲观念在宋代得到强化,并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因此,统治者不再需要依靠《孝经》“移忠为孝”的政治理念来规范臣子对朝廷的忠诚。吕妙芬通过整理大量的史料,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即“男女传记史料中明载妇女阅读《孝经》的例子从宋代以后逐渐增加,到了元明更加激增,但是男性的传记则不同,唐以前反而比元明以降有更多这类记载,显示《孝经》在近世逐渐淡出士人传记书写”[2]53。这也侧面反映出,孝或学习过《孝经》已经不再成为评价官员好坏的重要指标,孝逐渐从浓厚的政治价值转变为妇孺皆须具备的基本道德品质。
虽然《孝经》在宋代逐渐淡出政治舞台,转向庶民教化,扮演着启蒙读本的角色,但“天子之孝”的政治意义却得到了宋代士大夫的重视。通过检阅《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含《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补编》)发现,出现“天子之孝”的文章数分别为2篇和18篇,而《全宋文》中,出现“天子之孝”的篇目则有69篇。由此表明,“天子之孝”在唐以前的士人文章中甚少讨论,到了唐代才开始逐渐引起少数士大夫的关注,宋代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到了士大夫规范君德的视野之中。这一转变与宋代以文治国的背景下,士大夫格外强调君主道德修养的这一因素有很大关系。已有学者指出,“宋代以文治国方略的确定与经筵制度的定型,促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重权术与治术的儒家新帝学的兴起。……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正学,以《大学》为框架,以君德成就为根本,以尧舜圣王为榜样,指导帝王为学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与理论体系,以此确保儒家王道理想的实现与社会政治秩序的重建。”[3]正是在这种十分重视君主道德教育的政治背景之下,宋代士大夫格外重视“天子之孝”在孝治天下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由于目前学界尚缺乏对“天子之孝”的考察,本文以宋代士大夫有关“天子之孝”的论述作为讨论中心,来探讨士大夫视角中“天子之孝”的内涵及其在政治活动中的应用,并藉由此以思索“天子之孝”在古代政治文化中的作用。
一、宋代士大夫推崇“天子之孝”的动因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帝王术之一”[4],历代帝王都提倡“孝治”。正如日本学者桑原骘藏所说:“孝治主义的中国天子,在其谥号、陵号、庙号之中,完全缺少孝字,可说在中国国体上是绝无可能之事。”[1]22在宋代以前,《孝经》在政治文化与士人文化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在政治领域中作为执政纲领,要求官僚,乃至兵士都要学习《孝经》,而且还有着神秘灵验的功效,可以通过诵读《孝经》去邪、退兵、消灾、治病。[2]72-77但到了宋代,似乎统治阶层并不太重视《孝经》的政术价值,常常将其视为培养道德人格的基础教育读本,逐渐退出了中央政府的舞台。而相反的是,“天子之孝”却逐渐成为了宋代孝治观念中最为重视的一环。宋代统治阶层孝治观念的转变,可以从宋代经筵中皇帝的孝德教育这一方面来加以考察。
经筵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培养其道德及治国理政能力而特设的讲授制度,由博学儒者担任讲读官,负责讲经读史,并备皇帝顾问。经筵起源甚早,汉代已产生了后世经筵讲说形式,但“经筵”之名北宋才出现。宋代经筵制度初创于太宗、真宗时期。南宋吕中说:“自天平兴国开设经筵,而经筵之讲自太宗始。自咸平置侍讲学士,而经筵之官自真宗始。”[5]到仁宗时期经筵制度才成熟、定型,“开迩英、延义二阁,日以讲读为常”[6]80-81。而且规模扩大,欧阳修曾在上仁宗的奏疏中说:“侍读最为亲近,祖宗时不过一两人。今与经筵者十四人,而侍读十人,外议皆云经筵无坐处矣。”[7]4505经筵作为士大夫期待与塑造理想帝王形象的场所,受到士大夫的格外重视。如哲宗朝经筵官程颐便曾说:“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7]9031培养君德是宋代经筵的首要任务。
“孝”虽然是君主道德培养的重要德目,但在宋代经筵中《孝经》并不常讲。宋初经筵不讲《孝经》,最重视的是《周易》和《尚书》,偏重儒家政术的学习。从仁宗开始,经筵内容逐渐从主政术向主君德转变,《孝经》也始列经筵。仁宗是北宋最重视《孝经》的皇帝,“天圣二年(1024)二月乙丑,召辅臣于崇政殿西庑观讲《孝经》”[6]89,“庆历七年(1047)三月丙申,御迩英阁讲《孝经》”[6]105。这两次进讲《孝经》具有不同的意义。第一次是仁宗初即位,尚且年幼,进讲《孝经》为太后和经筵士大夫决定,表明当时士大夫确实将《孝经》作为启蒙性读物,启迪圣智,培养皇帝仁爱孝敬的道德人格。第二次讲《孝经》由仁宗自己决定,此时仁宗已经三十八岁,此次进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德性,而是仁宗欲以“天子之孝”的道德示范和风化的作用,来践行孝治天下的治理理念。仁宗一生积极地效法尧舜,为了时刻提醒自己行圣王之道,他还在坐席左右两侧置挂《无逸图》和《孝经图》,《孝经图》取《天子》、《孝治》、《圣治》、《广要道》四章,令蔡襄书之置于右侧。[7]4184由此可见,仁宗对《孝经》的重视与应用,主要是用来规范自己,效仿圣王践行“天子之孝”以实现孝治天下的理想。皇帝对《孝经》的重视也影响到了臣子,时为国子直讲的司马光于皇祐中撰《古文孝经指解》进献给仁宗以备阅览,并称“圣人之德,莫大于孝。……黎民乂安,四夷怀服,草木禽鱼,靡不茂豫,此诚孝德之极致也。”[8]很显然,这里指的不纯粹是道德伦理,而是强调《孝经》中“天子之孝”能够安定天下的政治作用。似乎在君臣之间这种默契的政治互动之中,逐渐形成了以“天子之孝”为核心的孝治理念。
英宗、神宗经筵均不讲《孝经》。值得一提的是,从宋太祖到英宗百余年间,《孝经》是科举中明经、学究等科的必试之书,但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将《孝经》移出了科举考试科目,一直到清初,《孝经》再没有被正式纳入科举考试科目中。[2]72这一举措,意味着《孝经》经学地位的下降,也标志着它丧失了在官僚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哲宗元丰八年(1085)即位,年仅十岁。元祐期间肩负起哲宗道德人格养成的经筵官主要是范祖禹。他不仅是司马光的高足,更是程颐之学的信奉者,在皇帝教育理念上与程颐基本一致,以培养君德为首务。他在入侍经筵期间十分重视皇帝的孝道教育,曾上《三经(尚书、孝经、论语)要言》、《孝经说》。范祖禹十分推崇仁宗,经常劝谏哲宗要效法仁宗,并直言“欲法尧舜,惟法仁宗而已”[6]132。他曾上奏乞哲宗如仁宗朝故事,复挂《无逸孝经图》,称“(哲宗)方以孝治天下,二书所宜朝夕观省,以益圣德”[9]。司马光、范祖禹以及仁宗朝宋绶所上的《孝经论语要言》便构成了北宋孝经学的主要著作,均是产生于皇帝教育的背景之下,可见北宋士大夫对《孝经》所倡孝治理念的重视,多在于“天子之孝”的政治作用。
哲宗元祐之后,《孝经》逐渐淡出了经筵舞台。尤其是南宋以后,《四书》地位抬升,以《大学》为框架的帝王教育体系也已成熟,皇帝孝德的教育多被纳入到修身、齐家的范畴之内,而《论语》、《大学》等书逐渐成了修身、齐家的重要教材。因此,义理浅白的《孝经》在成年皇帝的经筵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不再被士大夫视为重要的政术书,而多是作为童蒙读物。如宋高宗曾说:“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10]2086吕妙芬通过大量史料的分析表明,《孝经》在宋以后,“渐疏离于中央朝廷的政治舞台,转入地方庶民教化,剥落过去多元丰富的样貌,更多以蒙书的姿态出现”[2]10。但以“天子之孝”为核心的新孝治理念在南宋士大夫群体得到延续。如南宋高宗时,范祖禹之子范冲入侍经筵,继承父志,也曾进言高宗在讲殿置挂《无逸孝经图》,得到了高宗的采纳。[10]1466-1467即便南宋大儒朱熹怀疑《孝经》非圣人之言,不能欣赏《孝经》中孝治成效的论述,作《孝经刊误》质疑《孝经》,但他也不否认《孝经》所讲的孝道是极重要的人伦,并重视圣王孝道教化的作用。[11]朱熹在漳州任职时曾盛赞孝宗皇帝躬行孝道的榜样,认为天子之孝所以感神明而刑四海者如此之盛,并以此来教化漳州百姓。[12]由此可见,宋代“孝治天下”观念在士大夫对理想君主的期待与塑造中,逐渐缩小在皇帝践行“天子之孝”的范围之内,以“天子之孝”主导孝治。基于“天子之孝”在孝治中的重要性,一旦皇帝在孝道伦理或对“天子之孝”的认知上出现问题时,士大夫们便以“天子之孝”作为臣谏君的资藉予以规范。因此,宋代士大夫有关“天子之孝”的论述多见于他们进呈给皇帝的劝谏性奏疏之中。
二、宋代士大夫对“天子之孝”的诠释与政治运用
《孝经·天子章》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天子之孝德并不仅仅爱其亲,而要行博爱广敬之道于人民。它既有一般孝道所要求的尊亲、爱亲、养亲,又有天子特殊身份下所独有的政治层面的孝行,这两方面宋代士大夫都比较重视。但当两者存在冲突时,士大夫普遍认为天子之孝异于庶人,应以“安天下,固社稷”为主,格外重视天子之孝的政治属性。真德秀曾上奏言:“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陛下欲报先皇之大德,则继志述事所当先,衰麻之数、哭踊之节其次也;欲报慈闱之至恩,则先意承志者不可后,滫瀡之奉、跪拜之恭其末也。”[13]他对皇帝孝行的优先级排序,可以视为宋代士大夫的普遍态度。以下通过宋代士大夫有关“天子之孝”的几个主要论点,来了解“天子之孝”在宋代政治文化中的特殊意涵以及它在政治活动中的应用。
(一)遵循“以日易月”之丧制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语·阳货》)皇帝亦不例外,如《论语》中记载:“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论语·宪问》)为了不耽误皇帝处理国政,自汉文帝始,缩短皇帝服丧时间,行“以日易月”之制,一般缀朝三日后便要听政,二十七日除丧,此制为历代所沿袭。宋代皇帝为表哀思之情,彰显其孝德,多逾越此制,延长服丧时间。士大夫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多据易月之制对皇帝进行劝谏。
如景德元年(1004)三月,明德皇太后去世,真宗缀朝三日后仍未听政。宰相李沆等人上奏劝谏曰:“窃以机务至繁,不可暂旷;治命至重,不可辄违。……愿以宗社为念,少抑哀怀;望遵顾命之文,俯亲庶政。……则长乐如在之灵,实歆孝德。”[14]直到诸臣上第五表,言西北用兵,机务不能旷,真宗才不得已而从之。慈圣光献太后去世,神宗为其缀朝七日。王安礼等人为此连上七表,称“以日易月之礼、三日听政之权,非独遗诰之所贻,盖在昔至今,不易之道也”[15]91,“虽王者之有作,曷礼意之能踰?……伏望仰迪义训,思媚宗祊,俯就彝章,化形海宇,盖天子之孝也,非圣人孰与焉?”[15]93徽宗崩于异域,高宗号恸,终日不食,不理朝政。张浚上言:“臣窃惟天子之孝与士庶不同,必也仰思所以承宗庙,奉社稷;若规规然以坚守孝节为事,顾何以副委托之重哉?今日之事,厉害所系,则又大于此者。梓宫未返,天下涂炭,至雠深耻,亘古所无。陛下挥涕而起,敛发而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臣犹以为晚也。至若易月之制,听政之期,臣尝考之故事,揆以人情,皆为得中。”[16]诸如此类现象在宋代甚为常见。皇帝的这种行为,既是他奉先思孝的情感表达,也是经由此来表彰孝道的一种方式。士大夫屡加劝谏,表明他们普遍地认可“以日易月”之制,认为皇帝不能随意逾越礼制,置国政于不顾。尤其是常困于边事的两宋,久不听政对国家甚为不利。他们认为皇帝之孝的重心不在于拘拘然如庶人一般为亲服丧,而在于守宗庙、奉社稷,以安定天下为尽孝之首务。在服丧的这一问题上,易月之制成了士大夫劝谏皇帝的重要依据。
宋代真正践行三年之丧的皇帝只有孝宗。孝宗因其养子身份而入嗣大统,对孝道尤为尽心。高宗崩,孝宗表示“大恩难报,情所未忍”,不顾群臣反对,执意要按照儒家古礼为高宗服丧三年。为了安心守丧,他甚至内降手诏,令太子参决庶政,并在太子监国一年后,以“退就休养,以毕高宗三年之制”[17]694为由,内禅皇位于太子(宋光宗)。当然,也有少数理学士大夫从儒家礼制的角度出发,赞成皇帝行“三年之丧”。朱熹便十分推崇宋孝宗的孝行,认为易月之制废坏纲常伦理,曾向宁宗进言:“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余年,莫能厘正”,并劝宁宗效仿孝宗,“以日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用大布”[17]12766,以存孝思之情。但总体而言,古代皇帝行“三年之丧”者少之甚少,臣僚们也普遍赞同“以日易月”之制。即便是表面看来至仁至孝的宋孝宗,若以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考察其孝行,亦不能算是大孝。如王夫之评价孝宗的孝行说:“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视其败,孝宗之于孝也,抑末矣。”[18]所以,若皇帝以天子身份行“三年之丧”,反而被士大夫视为不孝。
(二)继父志与稽父政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又说:“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论语·子张》)。这是孔子提出考察人子孝与否的方法,但都没有谈及父道的价值问题。后世儒者的疏解多强调“不改父之志行乃是出于心有不忍,都侧重于血缘亲情的情感”[19],对于父道之是非则可暂且不论。在宋代士大夫看来,对于拥有特殊政治身份的天子来说,父政当改则改,当继则继,当改不改则为不孝。
仁宗时,宋庠有感于祖宗以来所编敕条繁长猥俗,曾上疏建议厘改旧章。他说:“(言者)必难臣曰:夫诏敕者多先帝所定,而不当改。臣对曰:凡诏敕之设,本臣庶上陈之见,宁一出先帝之口哉?况圣人以便利万物为至仁,不以因循陈迹为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敕,真宗皇帝革兴国之法,是皆不可乎?此守株之谈也。”[20]宋庠认为,皇帝不当以因循守旧为其孝行,而应以便利万物为其责任,对先帝已行制度进行革新。
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赵煦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宣仁太后)垂帘听政,以复祖宗法度为先务,重用反新法派大臣。司马光为反新法派的核心人物,他认为新法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天下人皆知、恶之,当务之急是全面废除新法。对于议者以孝子“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为由,阻止新法的废除,司马光对此给予了反驳。他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彼谓无害于民,无损于国者,不必以己意遽改之耳。必若病民伤国,岂可坐视而不改哉?《易》曰:‘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蛊者,事有蛊弊而治之也。干父之蛊,迹似相违,意则在于承继其业,成父之美也。”[21]202对于天子来说,父道的改与不改,关键在于其价值可否,若先父政令使百姓困苦、伤害国家,又岂能坐视不改。司马光通过对经典的灵活诠释,解“干父之蛊”为“改父之弊政”,借圣人之口肯定了改父之道的正当性。他认为,父子所行之政虽表面相违,但实质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国家的良好治理。为人子者,若能及时改父之弊政,成就父之美名,亦是大孝。为了进一步缓解哲宗的心理负担,司马光将新法弊政的罪责推给了王安石等变法派诸臣,认为“先帝之志,本欲求治,而群下干进者,竟以私意纷更祖宗旧法,致天下籍籍如此,皆群臣之罪,非先帝之过也”[21]203。所以,废新法不过是替父除害民之政而已。若废除新法,“使天下晓然,知朝廷子爱黎庶之心,吏之苛刻者,必变而为忠厚;民之离怨者,必变而为亲誉。德业光荣,福祚无穷,岂不盛哉!夫天子之孝,在于得万国欢心,以事其亲。”[21]203天子的孝德不在顺从父道,而在于抚四海,安万民,永保国祚。只要改父之道能顺应民心,变化风俗,使天下百姓皆拥戴朝廷,它就是合理的。在司马光看来,“得万国之欢心,以事其先王”(《孝经·孝治章》)才是“天子之孝”的真正内涵。后来罗从彦评价司马光此奏时曾言道:“当易危为安、易乱为治之时,速则济,缓则不及,改之,乃所以为孝也。天子之孝,在于保天下。”[22]他也认为哲宗改新法是符合天子孝道的。
哲、徽二朝都兴起过绍述之说,当时佞臣倡言以绍述神宗之政为天子之孝,鲠直大臣纷纷上疏反对绍述。陈瓘对以绍述为天子之孝的言论给予了极力反驳。他在《上哲宗论绍述劄子》中说:“尧、舜、禹皆以‘若稽古’为训。‘若’者顺而行之,‘稽’者考其当否。必使合于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不同。”[23]3陈瓘认为,“考其当否”是天子之孝与士大夫之孝的区别,而民情是衡量神宗之政当继与否的一项重要评判依据。他在《论善继善述奏》中说:“臣闻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天子之孝也,武王是矣。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者,卿大夫之孝也,孟庄子是矣。”[23]71-72此奏再次强调天子之孝与卿大夫之孝的区别,认为“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对卿大夫的孝行要求,而天子之孝当以继先王之志、发展先王未竟事业为主,而非战战兢兢,复行先王之政。他还指出,“神考之初,当百年宜改之运,改英祖者多矣,乃所以为善继善述也。《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23]72所以,改父之政并非独创,亦是祖宗故事。祖宗之间一继一述,皆是为了实现一人行善政,万民享其福的太平之世。陈瓘从区分“天子之孝”与“卿大夫之孝”以及天子之孝贵在继“志”不在继“政”两个方面,厘清了何为“天子之孝”。
在宋代政治活动中,蔡京是以孟庄子之孝来胁持君臣、排斥异己,以达到巩固自己势力的典型,陈瓘对他的大奸若忠的虚伪给予了揭露。他在《论蔡京交结外戚奏》中指出:“自蔡、卞发邪论,盗攘国柄,凡有所请,必以继述为说。稍改其意,则欲以不忠之名加于上下。假朝廷之诛赏,示私门之好恶,轻君误国,首尾八年。至于今日,狃于故态,又以此意胁持陛下,传会继述之论,假托报功之说,密持离间之谋,伺察陛下,包藏祸心,若有所侍。……陛下有庆,兆民赖之。天子之孝,孰大于此!今京所赖,非兆民之所同赖也。陛下一违京意,则京必以不孝之名责陛下矣。陛下徇一京胁持之私名,而不畏天下至公之大义乎?……盖公议若必以威势夺之,则人心离矣;人心既离,则主势孤若;主势孤弱,则外陵内侮,何所不至!非所以奉承宗庙,而慰安东朝也。然则蔡京之所谓孝者,果天子之孝乎?”[23]72这段文字表明,“天子之孝”不仅成为了蔡京在哲、徽两朝主张绍述神宗新政的工具,而且成为了他对付异己,窃取权柄的有力武器。蔡京假托“绍述”的名义,培植个人势力,凡有忤其意而改政者,均被冠之以不忠不孝之名。陈瓘向徽宗上此奏,欲要表明蔡京所持之论乃误国轻君之谬论,并非先贤所谓的“天子之孝”。他强调天子之孝在于行善政以惠万民,而蔡京所主张的“绍述”之政则违背民心,害至公大义,使天下离心离德。徽宗若继续受蔡京胁持,行误国之政,非但不能成其孝名,反而是对祖宗的大不孝。由此可见,在政治舆论场中,“天子之孝”似乎成为了北宋后期厘定国是的一个核心论点,陈瓘亦是以“天子之孝”作为去奸邪反新法的武器。
(三)抑私爱而徇公忧国
在宋代,皇帝的奉亲之孝与国家利益存在着强烈冲突的则是在高宗一朝。靖康之变,金朝攻陷北宋首都东京,掳走徽、钦二帝以及高宗亲母韦氏。在此后高宗绍兴年间,金庭屡屡以其父母为质,要求宋庭签订屈辱的和约。宋高宗为了尽其孝道,以证明其皇位的正统性,多屈从于金庭的要求。但士大夫十分反对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来成全皇帝奉养之孝,认为皇帝当以安宗庙、固社稷为孝。
面对金朝以高宗双亲来胁迫宋庭北面称臣的行为,魏矼反对屈辱议和,向高宗开陈了何为“天子之孝”。他说:“孔子称明王之孝治天下,则曰‘天下太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为天子之孝。方今宗庙社稷惟陛下是依,天下生灵惟陛下是赖。陛下既欲为亲少屈,更欲审思宗社安危之机与夫天下治乱之所系,考之古谊,酌之群情,择其经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从者,以国人之意拒之,庶几军民之心不至怀愤,且无噬脐之悔也。宗社安而国家可保,此非天子之孝乎?”[24]案孔子语出自《孝经·孝治章》,此言天子孝治的成效。“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则是强调天子之孝的内容所在。根据此二经义,魏矼认为高宗虽有爱亲之心,更应考虑天下苍生和祖宗社稷的安危,劝高宗割舍爱亲之情,成就天子之孝。赵雍对此亦有上言:“彼之绐我以渺茫之梓宫,劫我以难从之称号,母兄未见,乃先事仇,均之二策,孰为得失乎?天子之孝与臣庶不同,报难报之仇,雪难雪之耻,精变天地,诚动金石,震国威,立法制,为匹夫匹妇复仇,而朝四夷于明堂,此陛下之职,而群公所当尽心也。”[25]赵雍指出了金朝欲以孝亲之情来胁持高宗,事事牵制宋庭的诡诈。他认为,皇帝此时尽孝不应是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屈膝称臣以解救母兄,而应为父母、祖宗报仇雪耻,一怒而安天下,使蛮夷臣服。赵雍主张报仇、雪耻以尽孝道,亦是强调天子之孝在安社稷、奉宗庙。如王十朋言:“天子之孝莫大乎光祖宗而安社稷。……历代帝王虽守成、中兴、雪耻、复仇之迹不同,其功光祖宗、孝安社稷则一而已。”[26]
群臣虽对高宗多有劝谏,然高宗与秦桧执意求和。为了平息民心,秦桧借用当时李光的名望,张榜告示,倡议和议。同郡人杨炜上书李光,指责他依附权相,中了敌人奸议。他在《上李光书》中说:“帝王之孝唯安宗庙,固社稷,使祖宗之业万世不坠,其为孝固甚大而不可企及。其或不然,乃下同于匹夫,拘拘于礼之末节,事几一去,九庙四海且不可保,况其他乎?”[27]杨炜斥责李光不懂天子之孝,以匹夫之爱亲弃九庙四海,是陷皇帝于不孝。这说明杨炜在面对皇帝爱亲之情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时,亦主张割舍亲情之爱,以安宗庙、固社稷天子之孝。
以奉养父母为核心的孝行在《孝经》中对应的是庶人之孝。由于天子的特殊政治身份,常常以国家公器徇私人恩情,所以士大夫普遍反对天子不顾国家大义而践行庶人之孝,甚至有士大夫认为天子行庶人之孝必亡天下。如高登曾上奏言:“天子之孝与匹夫异,匹夫之孝独务全恩,天子之孝当先顾义。故匹夫之孝只施于其亲,而天子之孝心存乎天下。今有匹夫自讬于闾里,亲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承颜顺志,不敢以丝毫拂其意,世俗之所谓孝子。若使天子为之,则其亡天下也必矣。”[28]因此,在天下安危、国家利益面前,天子的亲情之爱则处于屈从地位。
三、结语:“天子之孝”的政治作用
综上所论,宋代士大夫欲通过在政治活动中对“天子之孝”的灵活诠释与应用,以达到匡正君主孝行的目的。他们对皇帝孝行的规范,实际上也是他们对理想君主的期待与塑造的一个过程。魏了翁说:“天子之孝以安国家、定社稷为先,故德为圣人,尊为天子。”[29]在宋代士大夫眼中,真正践行天子之孝的则是兼具道统(圣人)与治统(天子)于一身的圣王,而这正是儒家士大夫心目中的尧舜形象。因此,才有“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孟子·告子下》)之说。“天子之孝”作为儒家典籍中专为最高统治者所设定的孝行规范,“无论如何,皇帝按照礼法、伦理恭行孝道,毕竟意味着认同了一种臣子规范”[30],它对皇权有一定的限制作用。在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中,实际上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定措施可以限制皇权滥用,而“天子之孝”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可以起到调节皇帝政治行为的作用。宋代士大夫向皇帝灌输“天子之孝”理念,并不是向皇帝提供一种政治权术,而是培养皇帝的政治道德意识。按肖群忠的解释,“所谓的政治道德,则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政治秩序,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有关政治活动的合理、合宜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与政者道德品质的总和。”[31]这种政治层面的道德品质,它要求政治主体必须以公共利益为目的,以实现公共“善”为目标。所以,宋代士大夫对于天子孝行的要求都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方面的考虑。“天子之孝”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其功能就在于它能够促使王权沿着儒家政治价值理念的方向运行。本质上来说,这也是宋代士大夫践行儒家德治理念的一种表现。“天子之孝”作为宋代士大夫谏君的资藉,虽然在政治实践中并不一定能起到规范君主的效果,但作为一种道德价值,确实可以在精神层面对皇帝起到约束的效果。只有皇帝在政治道德的内在约束之下,才有可能施行合乎“以民为本”的王道政治。
——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