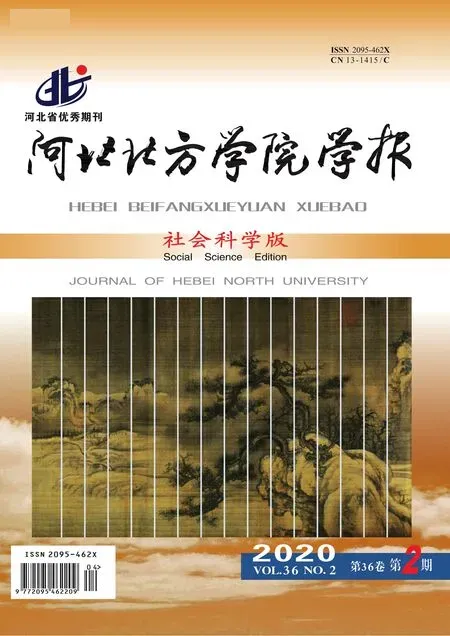《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异同考
——从明代朱鸿《孝经》类编著来看
李静雯,杨 亮
(1.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2.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朱鸿,明万历间杭州府仁和县(今杭州市仁和镇)人,字子渐。雅好《孝经》,考订古今《孝经》著述及诸家版本,“刻印过所撰辑《孝经汇辑》12种”[1]210,自成一家之言。张瀚所作《重刻序》中言:“余友朱君鸿生平纯孝,笃信是经,博求诸本,考订异同,详定释义,采辑经语,敷衍大义。”[2]2沈诏所作《经书孝语叙》道:“余朱友子渐氏,赋质纯,秉性孝。幼综文艺,长笃彝伦。每于明窗净几翻阅经书,凡涉奉亲系子道者,靡不殚思,或著简篇,或铭座右,沉潜玩味,务砥躬行。”朱鸿对《孝经》的解读视角独到,虽有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性,但他尝试突破前人的藩篱,反映了当时儒者对传统经学的努力和突破。
一、《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
朱鸿极其推崇《孝经》一书,以文章的形式将所思所得呈现出来,著有《孝经目录》《古文孝经直解》《孝经质疑》《孝经臆说》及《家塾孝经集解》等,并搜罗《孝经》的各种版本和重要著作,都保存在他编撰的《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中。《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是历代《孝经》著述版本的汇编本,集中保存了明代前中期对《孝经》一书的研究成果,包含了朱鸿关于《孝经》学术思想的基本思路和整体框架。其中所提到的文献资料,明代吕维祺著《孝经大全》和清代朱彝尊著《经义考》时都大量引用过。但两书因刊刻时间的先后、刊刻过程中产生的讹误及后世文本流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等原因,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孝经丛书》,14卷,明朱鸿编,明万历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3]293,“九行十八字白口,四周单边”[4]114。该书共分为8册。第一册为关西温纯和清源苏濬等为《孝经》一书所作的序言,以及朱鸿撰《孝经目录》与《孝经今文直解》;第二册为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以及宋朱申与周翰注《文公所定古文孝经》;第三册是元董鼎注《文公刊误古文孝经》;第四册为元吴澄撰《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以及明沈淮撰《孝经会通》;第五册是朱鸿撰《家塾孝经集解》;第六册为朱鸿撰《孝经臆说》与《孝经质疑》;第七册是朱鸿辑《五经孝语》;第八册为朱鸿辑《四书孝语》与《曾子孝实》。
《孝经总类》,20卷,明抄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十二册,八行或九行十六字至十八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该书按照天干地支分类,依次为:子集朱鸿撰《孝经目录》一卷以及唐玄宗李隆基注《孝经》一卷;丑集《孝经今文直解》一卷;寅集宋朱申和陈翰注《文公所定古文孝经》一卷;卯集元鄱阳董鼎注《文公刊误古文孝经》一卷;辰集元吴澄撰《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一卷;巳集朱鸿撰《家塾孝经集解》《孝经质疑》及《孝经臆说》各一卷;午集明孙本撰《古文孝经说》《古文孝经解意》和《孝经释疑》各一卷;未集朱鸿撰《古文孝经直解》一卷;申集明虞淳熙撰《孝经迩言》与《从今文孝经说》各一卷;酉集明沈淮撰《孝经会通》与《孝经杂钞》各一卷;戌集朱鸿辑《五经孝语》《四书孝语》及《曾子孝实》各一卷;亥集明虞淳熙撰《孝经集灵》一卷。
另有《孝经总函》12集20卷,明朱鸿编,明内府抄本,清丁丙跋,现藏于南京图书馆;明抄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但篇卷不全。《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为“《孝经总函》十二册,明写本”[5]440。
以《孝经丛书》和《孝经总类》为主,《孝经总函》等为参校本,综合运用校勘学的方法对其中差异进行分类,探讨出现差异的原因,并梳理《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的关系,以期更好地理解朱鸿《孝经》学著述与编选缘由。
二、文本对勘差异分析
对勘《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发现,《孝经总类》的卷数有所增加,还收录了虞淳熙等人的文章,且同篇文章在两书中并不完全一致。以下对两书中的差异进行对比与分析。
(一)段落内容不同
对勘《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发现,两书在段落内容上有所不同。《孝经目录》一卷记载了唐、宋、元以及明等各朝代《孝经》类著述的情况。如《孝经丛书》作:“汉《孝经》,附《今文直解》,刘向校定。”[6]8《孝经总类》对各朝代《孝经》著述都有详细介绍:“汉《孝经》。《今文直解》,列大夫中垒、校尉刘子政向所定,用颜芝本,一十八章,至今天下传诵。向以经文比古文,除其繁惑,而文势曾不若今日之顺。原有‘闺门’等句,唐司马贞削之。其题名皆后世所加,非向原本,《直解》则不知何世何人为之。”由此可知,《孝经丛书》较《孝经总类》更简明,仅列书名与作者,无内容的具体介绍。再结合相关文义可知,《孝经丛书》应是作者早期撰写并付诸刊刻的文本,与后期经过修订及增补的《孝经总类》多有不同。此外,《家塾孝经》一卷在朱鸿所编的两书中注文的内容有所变化,且《孝经总类》注文后还有总结性的议论文字。如《家塾孝经》:“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孝经丛书》注:“上言孝父母而天地明察,顺长幼而上下雍熙……此着明王事亲之孝而兼及弟道言之,非并举以相对也,读者不可不知。”《孝经总类》注:“此总赞孝道感通之大,复引《诗》以咏叹之也……明王之孝,果孰有大于此者乎。”《孝经总类》中关于《家塾孝经》一段的注文,以“此章统论”或“此章极言”为首,增加的文字为“孝通鬼神如此,由是观之,孝弟之至,可以通于天地鬼神,而况于人乎……亦言格神难、感人易也,深合此章之旨,明孝至此,无余惑矣”。结合上下文可知,《孝经总类》应作于《孝经丛书》刊刻后,朱鸿或后人于再修订的过程中增补了内容,使得整卷文章内容更加充实连贯,论述也更具义理性,使《孝经》理学化的特征也愈加明显。
(二)卷首与卷尾不同
《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在卷首与卷尾存在不同。如《孝经目录》卷首与卷尾,《孝经丛书》作:“明钱塘后学冯子京总校,仁和后学赵观参订”,“闽建阳宋儒后裔游英梓。《孝经目录》终”。《孝经总类》作:“明仁和后学朱鸿总辑,钱塘后学冯子京总阅”,卷尾无《孝经丛书》本15字。由此可见,《孝经总类》有总辑人朱鸿的名字但没有参订者赵观之名,且文卷的末尾不记刻作者游英的姓名。再如,《孝说》题目下有“三条孝本性生力,学更孝敬,身修德务,成其孝亲,汉求孝尤当严密”句,《孝经总类》卷首有此句,而《孝经丛书》缺失。此条内容也是朱鸿在编《孝经总类》时进行的再增添。又如,题目《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孝经丛书》作“《〈孝经〉四卷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总类》作“《〈孝经〉元本草庐校定古今文》”。文卷结尾,《孝经丛书》为“《孝经》四卷终”5字,《孝经总类》为“《孝经》”两字。通过《孝经总类》本的标题可知,《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卷数具体清晰,使人一目了然。
(三)语句字数不同
《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存在语句字数的增删与改变。如《孝经臆说》一文的句首章节内容,《孝经丛书》作:“唐虞之时,天真未鉴,去古未远,情窦未开,比屋可封,人人君子,三代之隆,直道而行。”《孝经总类》作:“唐虞之世,天真未鉴,比屋可封,三代之隆,直道而行。”“唐虞之世”的“世”,《丛书》本作“时”,属于单字的讹误,并对文意造成影响。“去古未远”“情窦未开”与“人人君子”3句,《孝经总类》本无而《孝经丛书》本有,应是作者为使语意更加完整后来增加的语句。又如《孝经臆说》“以下诸篇亦有次序,览者幸无忽焉”一段文字,《孝经丛书》作:“夫子赞舜之大孝而曰:‘德为圣人至。曰尊曰富,曰宗庙子孙,皆大德所得也。’”这句在《孝经总类》中有相关的变动,“德为圣人”后缺“至”字,“曰尊曰富”变为“曰尊富”,“皆大德所得也”变为“皆大德所致也”。《孝经丛书》中“德为圣人至”与《孝经总类》“德为圣人”相比,显然前者更符合文意,这应为《孝经总类》一书在流传或抄写中缺漏或讹脱所致。再如《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右经一章”结语中的文字:“古文‘居’上有‘闲’字,按许慎〈说文〉所引古文无之,‘侍’下有‘坐’字,按居即坐也,与上句义重。”《孝经丛书》中“闲”字,作“间”的繁体即“間”,易被当作是刊刻时出现的错误。然而,“閒”和“間”两字在古书中是通用的,不能把繁体的“間居”当作“閒居”之误,应综合考察多种版本来鉴定。因此,同一语句或字词在不同文本中出现的差异,如果对正确理解上下文意产生了影响,应摘要出来仔细鉴别。
(四)段落次序不同
《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在段落次序方面存在不同。如《孝经臆说》“以下诸篇亦有次序,览者幸无忽焉”句。《孝经总类》中这段内容下为“尝读《鲁论》一书,夫子论学以垂训万世”至“曷尝舍孝弟以立教哉?学者要须识得”一段。《孝经丛书》下则为“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长曰弟”至“亦维人子之自致焉尔”一段。实际上,《孝经总类》中这段内容在《孝说》篇“夫子首揭至德要道以授曾子”至“以告天下后世之为人子者”段之下。之所以出现段落文字顺序错乱的情况,可能是因版本在后世流传过程中,后人在重新整理或抄写时调整了位置。当然,这种调整并不是毫无依据,大多是为了使整体文意更加衔接,或者是顺应当时时代发展的主潮流。
(五)段落增减不同
《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段落内容的多少也存在不同。如《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中,“《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上有经文及注“《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孝经丛书》亦如此编排。《孝经总类》经文“《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以上则缺少《草庐校定古今文孝经》的经文及注文两段文字。再如,《孝经质疑》文末“自汉迄今传《孝经》者百有余家”至“后之学者须致思焉”一段文字后,《孝经总类》为“质疑总论“一段,《孝经丛书》也有“质疑总论”,但前面多出大段文字,简要摘录于下:“鸿尝谓孝子之事亲无间于生死存亡,观经首敷陈五等之孝……我成祖载于孝顺事实而亲名因以不朽。盖圣言广大精微,无所不贯。鸿复揭此以为亲没者之则”等。
通常情况下,较《孝经丛书》而言,《孝经总类》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但在这一节中,朱鸿关于《孝经》的两段议论性文字,《孝经丛书》有而《孝经总类》没有。原因或是朱鸿在编《孝经总类》时有意删去,或是后人在刊刻与抄写时遗漏。
(六)音注位置不同
《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两书的音注位置也有不同。如《家塾孝经》中,“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下的注文,其音注“长,上声”,在《孝经总类》中的位置是紧跟正文,《孝经丛书》中此音注的位置则放在正文的注文后。朱鸿编撰的这两部书,同一处注文的音义被分别放在一前一后的位置,应是书本在后世抄写与流传的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但并未对整体文意造成影响。因此,在阅读研究时只需要明了此为体例的问题,其他可忽略。
三、异同校勘的学术思想及意义
对勘发现,《孝经总类》的内容更加丰富完整,论证的方式更加严密,延伸拓展的范畴也更加广阔,且对《孝经丛书》中出现的错讹情况有一定的改正。因此,《孝经总类》一书应是在《孝经丛书》基础上所增加的订正本。两者虽为先后所呈现的文本,但不应以时间先后或简略繁复为标准来判定两书的优劣。黄永年曾言:“即使弄清了各个版本的先后和渊源递嬗关系,还不一定能立即判断其优劣。”[7]24《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虽有相异之处,但两者的整体框架和基本思想一致,都将朱鸿的基本观点一以贯之,没有相互抵牾之处。被选编在《孝经丛书》和《孝经总类》中的学者与文章也反映了朱鸿摒弃门户之见与融合不同派别的尝试和努力。唐玄宗在为《孝经》一书作注时道:“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8[12]古时圣人认为“孝”可作为育人的理念,由孝敬父母到教人知敬与爱,又推及以忠事上与立身扬名的道理中,一以贯之。由“孝”这一行为推至修身、齐家、治国乃至平天下,由孝顺父母辐射到忠君与爱国的理念中,与整个正统伦理中的政治理念紧密联系。
《孝经》一书发展至宋、元及明,显著特征有二:一是结合理学来解释《孝经》,提倡个人道德素养的提高;二是结合心学来理解《孝经》,使它呈现出民间宗教化的特点。朱熹关于《孝经》的论述仅见于《孝经刊误》一书及《朱子语类》中的若干文字,但它们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为当时及后世学者研究《孝经》提供了新方法和新思路,开启了一个以经学面对个体的时代,在提升个人道德的基础上去建构新的政治[9]54。朱鸿对于《孝经》发展至明代的一些现象也有过思考,他在《孝经质疑》中说道:“自汉迄今,传《孝经》者百有余家,各出己见,至文公出,独以修举遗经为己任,始定《古文孝经》,删去所引《诗》《书》并《左传》等语,故曰‘传文固多傅会,而经文亦不免有离析增加之失’,末又定《孝经刊误》。草庐吴氏又校古今文,定为一本,至本朝,传《孝经》者因乘其《刊误》,各列序次先后,咸用右第章数。”由此可知,明儒随意调整《孝经》一书经传的顺序在当时已经成为常态。《孝经丛书》与《孝经总类》中就包含朱鸿及其他人关于《孝经》一书经传离析与分章分句的内容。“孝“这一概念,辐射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孝顺父母,这不仅有助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且有利于营造和睦的家庭氛围,更有助于和谐的社会体系的建立。
朱鸿对朱熹《孝经刊误》中“分经传”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在持《孝经》原本之说的同时,也尝试对《孝经》进行分章分句。但他也是根据自己著述的需要进行分类,有时会有肆意删改《孝经》之嫌,且这种删改没有任何文献依据。朱鸿的这种肯定中有否定、继承中有发展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矛盾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明代学者研究儒家经典时遇到的困境与作出的尝试,并启发着后来学者在学术道路上的再探索与前进。
——以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讨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