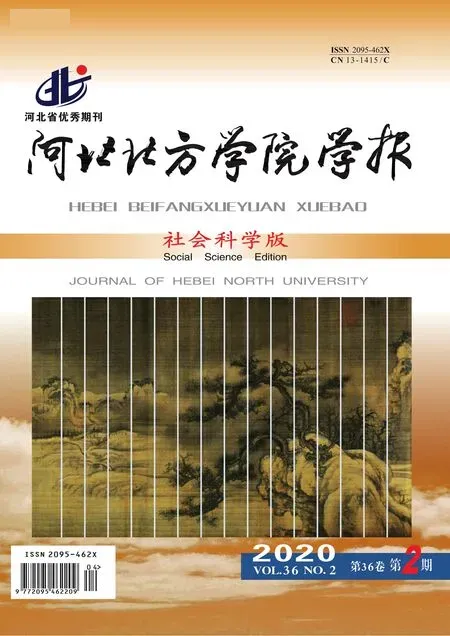《文心雕龙·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的比较研究
王 青 枝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文心雕龙·明诗》(以下简称“《明诗》”)是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第一篇,“根据政治社会的升沉,来解释各个时代的诗风”[1]210,通过“铺观列代”[1]210,以察情变之数;“撮举同异”[1]210,以明创作纲领,可被看作是一部浓缩的五言诗论。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并序对五言诗进行了一次探源和摹拟,他以为论诗应“通方广恕,好远兼爱”[2]136,且宜“合其美并善”[2]136。因此,有学者把《杂体诗三十首·序》看作齐梁时期第一篇五言诗的专论。将《明诗》篇中关于五言诗的部分与江氏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进行比较,探明在文学批评兴盛的齐梁时期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期为诗歌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
《明诗》是刘勰文体论的重要篇章,详细论述了诗的源流、作用、创作以及发展情况,可看作一部诗歌发展史。《杂体诗三十首》并序第一次完整地勾勒出齐梁以前五言诗歌发展的情况,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五言诗史。
(一)两者概况
《明诗》遵循“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1924的思路,阐明诗义,提出“持人性情”与“感物吟志”等重要理论,并描述上古至刘宋初年诗歌的发展变化,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陈述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趋势。关于《明诗》的创作时间,刘毓崧在《书〈文心雕龙〉后》写道:“此书之成则不在梁时而在南齐之末”[3],即齐和帝中兴元年(501)至中兴二年(502)。此观点后经范文澜进一步推定,并被学界普遍认同。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一经出现便被视为摹拟之作,他仅取汉初至齐梁众多诗人中的30位,却能完整地展现五言诗发展的历程,可谓“善于模拟”。且他眼光独到,不以耳代目,如对陶渊明及其诗歌的选取有力地证明了其精深的眼光与博大的胸怀。至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的创作时间,俞绍初认为应作于“建元之末、永明之初”[4],丁福林也以为其完成于齐建元四年(483)之前。《梁书·江淹传》载曰:“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5]251江淹《自序传》云:“故自少及长,未尝著书,惟集十卷,谓如此足矣。”[2]381据俞绍初考证,此序当作于建元四年(482)之后。丁福林在此基础上又将其规范于永明元年(483)之前,且认为其序中所言“集十卷”乃是前集。
(二)两者存在继承关系的可能性
刘勰早年“家贫不能婚娶”[5]710,遂“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5]710,且有“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1]1888的感叹,仕进之心十分强烈。他所依附的僧祐是当世名僧,深受竟陵王萧子良的器重。西邸盛会时期(487),“齐竟陵文宣王每请讲律,听众尝七八百人”[6]。《南史》记载:“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列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经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7]1102-1103江淹当时44岁,深受萧氏器重,亦在西邸士林之列。江淹“喜好文学,有才名……生平创作,数量不小,亦是诗文赋俱有名”[8]。其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杂体诗三十首》自南朝以来便引评论不断。钟嵘《诗品》称:“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模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9]施补华《岘佣说诗》曰:“江文通一代清才,神腴骨秀,其《杂拟三十首》,尤可为后人拟古之法。”严羽《沧浪诗话》云:“拟古惟江文通最长,拟渊明似渊明,拟康乐似康乐,拟左思似左思,拟郭璞似郭璞。”[10]此外,江淹入齐后仕途逐步通畅,曾官至御史中丞,《南史·齐本纪》亦曰:“(高帝)博学,善属文……所著文,诏中书侍郎江淹撰次之。”[7]113这对他的诗文传播也大有裨益。可见,江淹和僧祐彼此熟知。刘勰依附于僧祐并热衷仕途,而江淹身居高位,且已有文集10卷行世,刘勰拜读江淹的作品自在情理之中。刘勰《明诗》篇中对五言诗的探源与品评,显然是在《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楚谣汉风,既非一骨;魏制晋造,固亦二体”[2]136的基础上进行了取舍。
二、两者诗学观念的相同之处
《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同为齐梁时期的论诗名篇,都关注到五言诗发展史上一些重要的问题,如李陵与班婕妤诗歌的真伪以及东晋后的五言诗风等,这些对研究五言诗的起源与流变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对李陵与班婕妤诗歌的态度
李陵与班婕妤诗歌(以下简称“李、班诗”)的真伪直接关系五言诗的起源。李陵的作品集问世于魏晋,至刘宋时期广泛流传,“其中的五言赠答诗被钟嵘和任昉等人视为五言之祖”[11],《文选》中亦收录了署名为李陵的3首诗歌,南朝文士普遍把李陵视作西汉时期的文坛巨匠。但关于李陵作品的真伪问题,南朝文人并不完全肯定,早在刘宋时期就有人怀疑李诗的真实性。颜延之曾提出:“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12]而班婕妤“见疑于后世”正是肇自《明诗》,陈延杰在判定《怨歌行》并非班婕妤所作时就提到:“刘勰已疑之”,但应是出于对此句的误解。在对五言诗进行溯源时,江淹追至楚谣汉风,即《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13]。刘勰追至《诗经》,即《召南·行露》中的五言诗句“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14]。刘勰在江淹“楚谣汉风”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得出的“《召南·行露》”诗句比前者更早了一个时代。两人所持观点虽有分歧,但都认为五言诗发源于李、班之前,这一探源无疑暗示了李、班诗出现在汉代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刘勰所谓“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见疑于后代也”[1]185并非自己的观点,其陈述客观现象在前,“阅时取证”在后,得出的结论显然与“见疑于后世”相反。
江淹和刘勰都不怀疑李、班诗的真实性,这不仅是从时间上来判断,更是出于对其艺术价值的考虑。南北朝时期,模拟之风盛行,李陵的诗歌因其所蕴含的哀伤与无奈之痛成为文人争相模拟的对象。班婕妤和李陵同是先被帝王宠信,后又因误解被帝王舍弃。因此,李诗充满感时伤世的悲痛,班诗亦凄怆苍凉。六朝时,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文人处境艰难。他们的自我意识一旦觉醒,就急需宣泄内心的痛苦,在诗文中慷慨悲歌。再加上受楚辞悲痛哀婉与缠绵悱恻的基调影响,这一时期哀伤类作品盛行。《文选》不仅单列“哀伤”一类,在其他的文体中也大量收录了悲情主题的诗作,如“情”类中的《神女赋》和《洛神赋》,“志”类中的《幽通赋》《思玄赋》《归田赋》及《闲居赋》等,江淹的《恨赋》与《别赋》更是哀情赋的千古名篇。在此背景下,李、班诗作成为诗人竞相模拟的对象。有学者认为,对六朝文人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些诗的真伪问题,而是它本身所构建的伤别的情景……他们是真诚地和诗意中李陵凄凉的心境进行交流的”[15]。江、刘两人也正是从李、班诗歌本身的艺术特点去肯定其在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两人对李、班诗歌真实性的肯定。
(二)尊重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对于刘勰《明诗》篇中“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的观点,后世学者历来看法不一,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流调”两字。詹瑛将“流调”解释为“流行曲调”,周振甫以为“流调”是指“五言诗是四言诗的流变”,王宏林认为“五言是四言之后发展壮大的一种诗体,故释为流变或支流较为合理”[16]。刘勰评价《古诗十九首》“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1]193。可见在发展早期,五言诗风格质朴不粗鄙,比附事物婉转贴切,抒发情感惆怅动人,符合“清丽”的标准,称得上是一流的作品。但在后来的发展中,五言诗的风格发生了一些改变,尤其晋世以后,诗风偏向轻绮。刘勰所言“华实异用,惟才所安”[1]210,但近世诗人“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1]208,而“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轻靡者,浮文弱植,缥缈附俗者也”[1]1015。四言诗与五言诗属于两种不同的诗体,五言诗虽是四言诗的支流,但刘勰并没有因此重四言而轻五言。他以为四言诗是正规体制,应以雅正润泽为本;五言诗作为支流,应以清新华丽为主。但两者的体用各不相同,长于何种诗体应由诗人的才情而定。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序》是其文学观念的直接表达,30首拟作则是其文学观点的具体表现,他通过模拟原作诗人最典型的题材与风格来再现前代经典诗作的风采。江淹所摹拟的诗人中,汉代3人,曹魏6人,西晋7人,东晋6人,刘宋8人。从地域分布看,遍及“关西邺下”与“河外江南”。就艺术风格而言,从“《古别离》的古拙朴质,曹植诗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谢灵运诗的艳丽繁富,陶渊明诗的自然平淡,颜延之诗的雕琢绮密……”到“张华诗的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艳情诗的荡人心魄”[17],可谓风格众多,各具特色。就诗歌题材而言,更是涉及送别、游仙、离情、友情、艳情、悼亡、山水、田园与军旅等五言诗的各种题材。可见,江淹“以一个评论家的博大胸怀,对五言诗发展的各个时代和个人风格及各种体式均给予充分肯定,阐明了正是由于五言诗体的演变和多样的风格流派才使得汉魏晋宋五言诗得以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兴旺的局面”[18],充分体现了他“通方广恕,好远而兼爱”的论诗态度。
在刘勰看来,诗体和风格是两个不同维度的问题,四言诗与五言诗也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对后来轻靡的文风颇有微词。而江淹在《杂体诗三十首·序》中也已明确表示,五言诗应该“美并善”,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与辞藻声韵相和,不能单纯地追求声律与词采。在这一点上,刘勰与江淹的看法存在明显的继承性。
三、两者诗学观念的不同之处
齐梁时期是近体诗形成的准备阶段,诗人作诗追求对偶、声律与辞藻,一反魏晋时慷慨激昂的诗风,而儒、释、道及玄的多元发展也使文人的思想更加自由。再加上文学批评之风的盛行,文人各自阐释不同的文学观念已成风气。刘勰和江淹也不例外,这在《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中都有所体现。
首先,两者对东晋以后的诗歌态度不同。江淹选取的30人中,从汉代无名氏到东晋孙绰有18人,《明诗》除无名氏、卢谌及刘琨不取外,其余的15人全都出现。而江淹选取的后12人,即从东晋的许询到刘宋的汤惠休,《明诗》中未提一人。可以发现,刘勰在对五言诗选文定篇时,主要把目光聚集在东晋以前,对东晋以后的诗歌仅以“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1]208来概括,这与江淹“好远而兼爱”的态度有明显分歧。刘勰对近世绮靡浮弱的文风颇有微词,不仅在《明诗》中有所表现,在其他篇目中也屡屡提到。如《总术》篇:“凡精虑造文,各竞新丽,多欲练辞,莫肯研术。”[1]1633《风骨》篇:“文术多门,各适所好,明者弗授,学者弗师,习华随侈,流连忘返。”[1]1071《通变》篇:“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今附而远疏矣。”[1]1093面对齐梁时期卑弱华靡的文风,江淹也多有批评,他以为“世之诸贤,各滞所迷,莫不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重耳轻目,俗之恒弊”[2]136。但在实际论诗中,他并不拘泥于时代风气,也不以一己之好为标准,在时代、地域与风格上都呈现出“美并善”的态度。他所选的刘宋诗人占总人数的1/3,且对这8位诗人的拟作也多能拟出原作之神。如《鲍参军戎行》中的“孟冬郊四月,杀气起严霜……寒阴笼白日,太谷晦苍苍”[2]164,阴寒肃杀之气酷似鲍照原作,充分体现了其对不同时代风格的尊重与认同。
其次,两者对陶渊明诗歌的态度不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在南朝时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钟嵘的《诗品》仅将其列为“中品”,萧统的《文选》仅录其诗文9首,刘勰的《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及其诗作则只字未提。刘勰与陶渊明的思想存在冲突,如对佛教与政治的态度,刘勰是忠实的神不灭论者,且始终怀有积极的仕进态度,而陶渊明则是神灭论的隐逸者。此外,南朝文学偏向形式主义,注重声律和辞藻,陶渊明质朴自然的文风显然与时代格格不入。但江淹却首先发现陶诗的价值与意义,并将其归入大家之列。在用词上,江淹所用的“东皋”“苗”“阡陌”“浊酒”“锄”及“桑麻”等皆出自陶诗,高度还原了陶诗的意境。在语言风格上,江淹力求朴素无华,明白易了,高度还原了陶诗的古朴真淳。最重要的是,江淹准确地把握了陶诗中最具艺术价值的“田居诗”,“从文学史的角度把作为田园诗人与隐逸诗人的陶渊明暗示给后来的接受者”[19],并将陶诗放在五言诗史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在这一点上,江、刘两人的观点显然存在差异。
总之,《明诗》与《杂体诗三十首》并序存在继承关系,两者一致肯定东晋以前的五言诗,但在东晋以后的诗歌及陶渊明诗歌等问题上,态度明显不同。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之风甚盛,就以五言诗在齐梁时期的境遇而言,“有保守者大肆抨击,亦不乏开明者赞扬支持”[20]。可见,形成统一的批评标准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因此,在看待某一文学观念时亦不可过于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