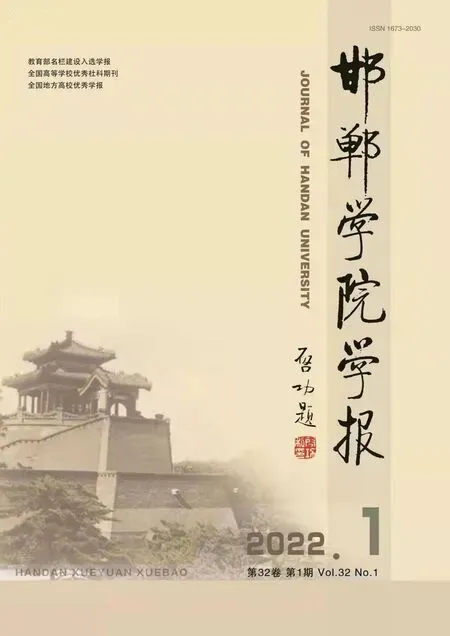西汉群臣上醻刻石解疑
秦进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朱山上的群臣上醻刻石,自清朝道光年间沈涛发现以来,引起了金石家、书法家、史学家等诸多学者的注意,撰文考证、探究其年代、介绍其特点者甚多。亦有人对于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实性心存怀疑,如光绪年间,《畿辅通志》分纂丁绍基认为:“其可疑者,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即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况此刻,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诸石纳在圹中,须待出土始见。临洺娄山亦非僻地,两《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均言,太宗征刘黑闼尝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岂不见此刻,而唐人亦无言及之者,何直迟至今日而人始见之耶?兹因近日考据家纷纷辨证,姑为之推阐时地,论说于左,而仍不能无疑也。《求是斋藏碑目》。”①同治《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略十一·广平府·永年县·群臣上寿刻石》,《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凤凰出版社2010 年,第10 册第297 页)。李鸿章修,黄彭年纂《畿辅通志》,清同治十年(1871 年)开始编纂,光绪十年(1884 年)以后刊刻面世。从开始修纂年代看,可称为同治《畿辅通志》。从面世年代看,可称为光绪《畿辅通志》,两者均有道理,按文献著录名从主人原则,此处称同治《畿辅通志》。丁绍基从三方面提出了质疑,这些怀疑之言,不见于丁绍基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保定古莲池煨芋室撰写的题跋②赵廿二年石刻拓本题跋载丁绍基撰跋文,无上述引文,虽然现在所见丁绍基跋文樊榕抄录于1936 年,但抄录的仍然是丁绍基撰写于光绪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的题跋草稿,故作光绪五年。详见秦进才《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两拓本价值初探》,《文物春秋》2008 年第1 期。,五年之后刊刻的《畿辅通志》丁绍基跋文结尾增加了上述几句话,光绪二十年刊刻的《广平府志》沿袭了光绪十年《畿辅通志》的这几句话[1]536,这几句话并被鲁迅所抄录①鲁迅所抄录的丁绍基跋文,见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群臣上醻刻石》,上海书画出版社1987 年,第1 册第9-10 页。又见李新宇、周海婴主编《鲁迅大全集·学术编·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群臣上醻刻石》,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22 册第9—10 页。。由上述可知,跋文结尾所增加的几句话,当是丁绍基在光绪五年后撰写的②缪荃孙著,张延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目录一·艺风藏书续集》卷五《求是斋碑跋》载:“丁酉冬日,偕金溎生谒丈于局前街故宅,犹为煮酒摘蔬,清谈竟日。后又相聚于天宁寺,别无几时,而丈归道山矣。”(凤凰出版社2013 年,第249 页)基本相同的表述,又见《缪荃孙全集·诗文一·艺风堂文续集》卷六《求是斋金石跋书后》(凤凰出版社2014 年,第388 页),再见《缪荃孙全集·诗文二·艺风堂集外诗文·仁民爱物斋手藏碑目并考证跋》(第215 页)。丁酉,指光绪丁酉,即光绪二十三年(1897 年),丁绍基在此年以后去世。光绪五年前后,丁绍基曾以故城县知县、分纂的身份,参与《畿辅通志》的编纂(同治《畿辅通志》卷首《畿辅通志纂修职名》,《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第3 册第5 页),因此撰写群臣上醻刻石题跋,据此可知光绪十年刊刻的《畿辅通志》所增加的文字,为丁绍基自己所增。。同治《畿辅通志》所注明来源的《求是斋藏碑目》,是稿本,而非刻本。所增加的话,不见于民国年间刊行的《求是斋碑跋》③丁绍基撰《求是斋碑跋》卷一《娄山石刻》(又作《求是斋金石跋(稿本)》、《求是斋金石跋》,正文卷首作《求是斋碑跋》,仅是摘录了稿本的一部分。刻本,张钧衡编《适园丛书》第十集,南林张氏刻本1916 年,第145册第1 页A—第3 页b;影印本,《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年,第19 册第14001—14002 页;《丛书集成续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年,第74 册第725-726 页)。此书没有丁绍基所增加的几句话。此书出版时,丁绍基已经去世,是稿本没有,或是丁绍基删去了稿本上的这几句话,还是后人删去了所增加的几句话,不见稿本无法判断,暂且书此待考。。从表面来看,丁绍基所言似乎也有些道理,前贤未见,是摩崖刻石而非墓志铭,地理位置又非偏僻,唐太宗曾登临此山,为何无人见到?光绪《广平府志》针对丁绍基的说法,指出:“又谓宋朝欧、赵、洪诸家曁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搜罗考证皆未及此,不能无疑,非也。汉封龙山碑至道光年间始见于世,能因欧、赵诸公未曾著录而见疑乎?”“或云唐太宗在此立营何以不言此刻,不知太宗立营在狗山,此刻在猪山,非一处也。”[1]536-537所言针锋相对,但还是以群臣上醻石刻“汉刻既有所疑,石赵决无此刻,故仍列之于赵,以俟考。”[1]537在认同群臣上醻刻石真实的前提下,在年代上留下了继续求索的余地。李葆恂亦因“以前人未见疑为赝作者”指出“其文词古质,篆势碓劲,定为西汉古刻无疑。”④王仁俊撰《金石三编·通考·汉·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石刻》引《匋斋臧石记》李葆恂《汉赵廿二年群臣上寿刻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19 册第40 页)。《匋斋臧石记》,又作《陶斋臧石记》。从文词、篆势两方面肯定了群臣上醻刻石之真。丁绍基怀疑似乎已经解释清楚,但仍有学者认为群臣上醻刻石的真伪是个大问题。既然如此,笔者就在前人基础上,对丁绍基怀疑进行辨析,做些解惑释疑的工作。
一、丁绍基怀疑貌似有理实则不可信
丁绍基怀疑群臣上醻刻石,主要理由是前贤未见、未有评论。其实,有些文物处于显著的位置,当时人了解其价值,十分珍惜,有实物,有记载,有图录,有注释,有评论等,可证其存在的真实性。后人记述其变迁,持续不断,证据链完整,可以证明其延续的真实性,如秦始皇刻石等举世著名的文物。有些文物,当时很普通,并不引人注目,随着时代的推移,数量减少,物以稀为贵,逐渐变得很珍贵,有所发现即被视为奇迹。
(一)不同时代的汉碑命运不同
器物的珍贵与否,不仅在于其本身,而且在于人们对于它的认识。汉代有些碑刻,汉朝人不以为是奇珍异宝,魏晋人也不注意保护,到现代仍然有些人不知道珍贵。
如三国魏都洛阳天渊池,“池中有魏文帝九华殿,殿基悉是洛中故碑累之,今造钓台于其上。”[2]1391曹魏时代的“故碑”,当是汉碑,有多少汉碑变成为九华殿的基础,需等到将来发掘出来才会清楚。
又如汉甘陵相尚府君残碑,“民国十一年阴历十一月十四日,洛阳城北张羊村北岭出土。地在元诲、元怀墓东一里。原石析为四,殆六朝时不知珍惜,裂为墓门。”[3]4这是甘陵相碑破析为六朝墓门,珍贵的汉碑,六朝人却如此糟践。
再如孙承泽言:“石刻在世,可以考证逸事,补史之讹缺,然所存者极鲜。旧记载:景祐时,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长安碑石为塔材;又雒阳天渊池中,有魏文帝九华楼殿基,悉是雒中故碑;金陵街衢,半是六朝旧碑。余向在汴梁,搜阅旧碑,止相国寺宋白一碑。张孝廉民表曰:国初欲建都于此,悉取烧灰筑城。燕京旧碑,多为中贵取置神道,或重修庙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慨也。”[4]1296-1297仅选取开封、洛阳、燕京等处地方,列举魏、宋、明等朝资料,毁碑行为使人吃惊,如果将全国资料收集齐全,破坏的情况会更严重。
还有现在洛阳白马寺山门东、中、西三门洞就有汉墓黄肠石53种,天王殿、大佛殿、清凉台天桥等处亦有[5]11-12。1973年,山东高密县田庄乡住王村建场院屋缺少砖石,打开古墓,取出汉画像石38块及孙仲隐墓志,做建场院屋之用,1983年,从墙上取下孙仲隐墓志,收藏于高密市博物馆[6]。诸如此类所在多有,恕不一一列举。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碑越来越稀少,变得越来越珍贵,也就越来越引人瞩目,在金石家眼中已属稀世珍宝。如今若访得汉碑,是文物界、史学界的重大发现、重要新闻,而一般人看来依然是很好的建筑材料,用来铺路修桥、砌墙盖屋等。
群臣上醻刻石的发现亦应当如此来看,对于其普通与珍贵,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认识,不同文化素质的人、不同行业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并不关系其真伪。
(二)丁绍基前贤未见之说不可信
丁绍基所言:“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即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学起于思,思源于疑,世界的进化,起源于怀疑,怀疑是科学、学术发展的动力,怀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真实性没有错,前贤欧阳修等未见、未评论群臣上醻刻石也是事实,从表面来看这是一句实话,但实话并不一定就真有道理。
首先,“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说不可靠。宋朝欧阳修,广泛收集金石资料,集著录与考证于一体,撰写《集古录》。因中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很多汉碑散布在荒郊野外,种类繁多,欲以一己之力,将汉碑搜罗殆遍,并不现实。欧阳修言:金石文物,因“风霜兵火,湮沦摩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为此收集了“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①(宋)欧阳修著《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2《集古录目序》(中华书局2001 年,第600 页)。(宋)洪适撰《隶释》卷2《东海庙碑》言:“欧阳公时,天下一家,汉碑虽在遐陬穷谷无胫而可至。《集古录》中已屡言难得为可宝,况今乎!”(中华书局1986 年,第31 页)感慨碑刻难得,是亲身体会之言。创立了金石学研究的范式。《集古录》十卷中有三卷涉及到汉碑,欧阳修为汉碑撰写了88 篇跋文,均是东汉碑刻跋文,而无一篇西汉碑刻跋文。曰:“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铭刻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7]2166可知,欧阳修未曾见到西汉石刻。赵明诚言:“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8]1所撰《金石录》继承了《集古录》的范式,订正欧阳修的讹误,补充其遗漏。“大略如欧阳子书,然诠序益条理,考证益精博。”[9]3608目录著录碑刻两千余种,其中汉碑221 种,撰写汉碑跋尾六卷136 篇,学如积薪,后来居上。著录“汉郑三益阙铭”,注言:“武帝建元二年。自刘聪后,屡以‘建元’纪年。此铭字画非晋已后人书。”[8]4此条所言不可信②对于汉武帝创建年号的时间,从宋代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现代学界虽仍然是诸说纷纭,但已认同建元年号出自于追记,而非当时就有。再则,汉武帝以来有五位皇帝用过建元年号,有建元年号的文物,需要从多方面考察才能确定。因此,《金石录》著录的建元二年《汉郑三益阙铭》,不可信。。著录“汉居摄坟坛刻石二”,注言“居摄二年”[8]4,是由王莽掌控的孺子婴在位期间,西汉虽已名存实亡,也可算是西汉碑刻。洪适撰《隶释》《隶续》,在欧阳修、赵明诚成就基础上,又有所发展①据《隶释目录》统计,19 卷中,注明“欧赵有”者72 篇,注明“欧有”者一篇,注明“赵有”者60 篇,不注者出处者44 篇,即洪适新增加者,由此可见,赵明诚对欧阳修的继承与发展,也可见洪适对于欧阳修、赵明诚的继承,自己的新发现。,收集了汉碑258 种,开创了著录碑刻原文的模式,保存了珍贵的资料。言:“自中原厄于兵,南北壤断,遗刻耗矣。予三十年访求,尚阙赵录四之一。而近岁新出者,亦三十余,赵盖未见也。”[10]1由上述可见,一方面金石资料收集之难,而且前人著录的碑刻也难搜集齐全,还有许多散落在山崖墟莽间、埋藏于地下者等待发现,也有些条件不具备者无法收集,同时,又有新的发现。《隶释》正文中无西汉碑刻,所收录的著述中,除有些“既无年月,竟不知何代所表也”“不知所立岁月”“并无年号,皆不知何代人也”[10]200、203、207等外,亦无西汉碑刻,因为,《隶释》主要收录隶书资料,“周秦先汉刻石皆用篆,故不录。”[10]210所以,也就删去了上述《金石录》所著录的《汉郑三益阙铭》与《汉居摄坟坛刻石二》等碑刻。其次,欧阳修言:“仅得其一二”,赵明诚言:欧阳修《集古录》有“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的弊端。洪适言:“亦三十余,赵盖未见也。”欧阳修、赵明诚不仅对于群臣上醻刻石未有评论,而且未曾著录过西汉末年之前的碑刻,洪适《隶释》《隶续》中也未著录过西汉碑刻。由上可见并非是“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丁绍基所言并不可信。
再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汉碑发现、研究也是后来居上,“特是古来金石虽日就毁佚,而其沦弃空山、沈埋地下、经搜求而得者,亦岁有增加。又旧拓石墨固少缺泐,亦有原石未经洗剔,而后来精拓转胜于前者。”[11]2147娄机撰《汉隶字源》著录碑刻309 种,其中汉碑280 种②(宋)娄机撰《汉隶字源》洪景卢《汉隶字源序》言:“凡见诸石刻,若壶、鼎、刀、镜、盆、槃、洗、甓著录者三百有九。起东京建武,讫鸿都建安,殆二百年。滥觞于魏者卅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第225 册第792 页);《汉隶字源》卷一《考碑》言:“汉碑三百有九。”(《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25 册第793 页)文中逐条排列了309 种,除去新莽候钲、耿氏镫、砖文及魏晋碑共29 种,汉碑实为280种,其中有些碑的碑阳与碑阴分为两种。。施蛰存《汉碑目录》载:到1980 年止,西汉22 种,东汉388 种,总计410 种[12]346。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编·秦汉刻石》卷二第一版附录胡海帆编《秦汉刻石文字要目》收录秦汉刻石文字412 种。娄机、施蛰存、胡海帆等所著录的均比欧、赵、洪三人数量为多,怎么会是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了呢?再则,这是后学根据保存原石与拓片者的汉碑数量的统计,如果加上亡佚者数量会更多,这些汉代碑刻在两宋时代肯定存在,而欧、赵、洪有的未曾发现,有的未曾著录,怎么说三人“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了呢?可知丁绍基所言与事实相差太远,并不确切。
其次,“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而于此刻曾不一及”,很正常。因为,群臣上醻刻石的发现是在清道光年间,群臣上醻刻石发现者沈涛的《交翠轩笔记》雕版印刷出来,已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丁绍基列举的清代六大金石学家,顾炎武、朱彝尊、钱大昕、王昶早已驾鹤西行,翁方纲、孙星衍也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与世长辞,他们“曾不一及”,既是事实,也合乎情理。
其中属于“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中的王昶,在清嘉庆十年(1805年)编成自三代至五代收录1500余通、160卷的《金石萃编》,博采前代金石诸家之长,将目录、录文、集解、考订等融合为一体,人称“实为宇宙之钜观,古今之杰构。”[13]6但也不是“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了。王昶自称:“余之为此,前后垂五十年矣,海内博学多闻之彦,相与摩挲参订者不下20余人,咸以为欲论金石取足于此,不烦他索也。然天下之宝日出不穷,其藏于嗜古博物之家,余固无由尽睹,而丛祠、破冢继自今为田父野老所获者又何限,是在同志之士为我续之已矣。”[14]2王昶头脑清醒,诚恳期待同行的续补。亦在清代六大金石学家之列的孙星衍编成《寰宇访碑录》后亦言:“若夫金石之录,日出不穷,非敢以此自足,亦愿来者之续成其志,以备石渠采择云耳。”[15]19851与王昶心情、态度相通,体现出金石大家的虚怀若谷、远见卓识。事情的确如此。同治年间,陆耀遹遵循《金石萃编》的体例,专收《金石萃编》所未收,撰成《金石续编》21卷。又先后出现了20余部续补《金石萃编》之作,或补其目录,或校其录本,或增录跋文,既延续《金石萃编》开创的金石著录体例,又拓宽了金石学研究领域,在研究方法上亦有进步①详见赵成杰《〈金石萃编〉之续补及其金石学意义》,《美术学报》2017 年第5 期;《〈金石萃编〉续补考》,《岭南学报》复刊第九辑,2018 年11 月。。有些人还用其书名,推出新的金石著述,如孙星衍《平津馆金石萃编》、刘承幹《希古楼金石萃编》、郭思恩《潮汕金石萃编》等。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亦是如此,罗振玉称:“孙季仇、邢雨民两先生《寰宇访碑录》,采取详备,为金石目录诸书之冠。”[16]20085评价准确,合乎实际。然而纰缪触目皆是,校勘刊谬者前后相继,有刘声木的《寰宇访碑录校勘记》《补寰宇访碑录校勘记》,罗振玉的《寰宇访碑录刊谬》,李宗灏的《寰宇访碑录校勘记》,杨宝墉的《孙赵寰宇访碑录刊误、补遗》等;遗漏自是难以避免,补充者接踵而至,不仅有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刘声木的《续补寰宇访碑录》,而且有罗振玉的《再续补寰宇访碑录》、杨守敬的《三续寰宇访碑录》等,形成了《寰宇访碑录》系列。难道后来诸书都是假冒伪劣之作?难道只有“国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于此刻一及”才是真的吗?王昶、孙星衍所言否定了这种说法,后人的刊误订谬、续修补编等,也证实了王昶、孙星衍言论的正确。
实际上,汉碑的收集整理,薪火相传,后来居上。孙星衍曾言:“国家统一车书,拓地万亿,山陬海澨,吉金贞石之出世,比之器车马图,表瑞清时,旷古所未闻,前哲所未纪矣。”[15]19851说明了新出土的文物,既是旷古所未闻,又是前哲所未纪,不曾看到,不曾评论,是很正常的。无论是郦道元记录的汉碑,还是赵明诚记载的汉碑,很多在后来遗失了②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缪荃孙校《金石录》后,编《今存碑目》,据此统计存汉碑刻55 种,其中存原石者35 种,存额者一种,存拓本者17 种,宋重刻本者一种,元重刻本者一种(《嘉业堂丛书》,吴兴刘氏嘉业堂1913—1930年,第106 册第1 页A—第3 页B)。相对于《金石录》著录的汉碑221 种来看,仅有24.8%左右的汉代碑刻凭原石与拓本流传到了清末。,现在存世的汉碑多数是清朝以来才发现的,宋朝人、清朝乾嘉时代的人没看到。清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收录了汉碑98通,日人永田英正编《汉代石刻集成》著录汉石刻176方,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全集·秦汉石刻》收录197种,徐玉立主编《汉碑全集》收集了两汉阙铭墓表、坟坛题记、摩崖题记、功德碑、祠庙碑等285种,合计360件,难道翁方纲、孙星衍没有看到、说到的都要怀疑吗?显然说不过去。
全集要全是编者追求的目标,全集不全是客观现实的存在。《汉碑全集》,下大功夫收集资料,依然有搜集不到而遗漏者,如1959年在河北定县北庄子中山简王刘焉墓发现有刻铭和墨书文字的石头174块[17],1984年江苏灌云县发现有题铭的画像石③陈龙山《补证灌云古代史的几件文物》,《灌云文史资料》 第5 辑,政协灌云县文史资料委员会1991 年,第88页。又见《灌云县首次发现的题铭画像石》,《灌云文史资料》第11 辑,灌云县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4 年,第34 页。④刘海宇著《山东汉代碑刻研究》(齐鲁书社2015 年,第129 页)。附录三《〈汉碑全集〉读后记·〈全集〉未收的山东现存汉代碑刻》列举了具体碑刻名称27 种(第476 页),占将近收录总数的1/10。,1987年甘肃张家川发现的东汉刻石《河峪颂》[18]等,均不见于《汉碑全集》的收录。又如“山东现存重要的汉代碑刻没有收录的有:《新富里刻石》《滕县西户口画像石题记》《枣庄王山头画像石题记》《泗水汉安元年画像石题记》《曲阜徐家村延熹元年画像石题记》等。”④《汉碑全集》主编亦言:“由于多种原因,现已发现、著录的汉碑本书未能收录”[19]2248。也就是说不是把已知的汉碑都收录到《汉碑全集》中。如永城保安山二号墓出土塞石近3000块,《汉碑全集》收录10块,仅占1/300左右。又如1987年江津县沙河发现崖墓题记,报道了三种[20],而《汉碑全集》仅收录了一种。在《汉碑全集》出版之后,有2011年,四川成都市出土的东汉太守李君碑、裴君碑[21]4-45,河南驻马店市驿城区胡庙乡发现的《东汉吴房长张汜请雨摩崖石刻》[22]1-2,2016年2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于世的汉安帝永初元年刻石与拓片[23]等。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现汉碑的几率越来越小,也就越来越珍贵,而历代积累起来的数量会越来越多,难道说现代收集的、出土的汉碑石刻,因为发现的晚,就都不可信吗?正是因为没有前人的著录,才是新发现,才增加了新资料,才能起到正经补史的作用。
《汉碑全集》著录的汉碑285种中,年代不清的有34种①《汉碑全集》有30%左右的没有具体年代,经过笔者依据其他资料补充之后,仍然有34 种年代不清楚。,年代可考的有251种。在年代可考的251种中:清代嘉庆及以前发现者有80种,道光至清末发现者有26种,民国年间发现者有53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2005年6月发现者有92种。嘉庆及以前发现者占31.87%,道光至2005年6月发现者占68.12%,绝大多数是“宋之欧、赵、洪诸家”所未见,“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曾不一及”,难道说这些都不可信?还一定让“欧、赵、洪诸家”“顾、朱、钱、王、翁、孙”再来做一次鉴定才能不怀疑?丁绍基所言,既不合乎情理,又不符合实际,以此怀疑群臣上醻刻石,能有说服力吗?
不仅仅是群臣上醻刻石及其汉代碑刻,20世纪以来,发现的甲骨文、敦煌文书、汉代简牍等文献,宋朝的欧、赵、洪诸位,清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他们见过吗?评论过吗?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现的诸多战国秦汉三国简牍、秦封泥等,宋、清两代金石大家既未见过也没发表过意见,难道就都不可信吗?前人的发现,公布于世,后人可以研究,可以发表意见。后人的发现,前人怎么研究,怎么发表意见。如果后人的发现以前人的看法为标准,前人未见、未评论就都要怀疑是假的,那不是否定一切新的发现吗?今天发现的文物要有前人的评论判断,否则就是假的,还会有新的发现吗?后人的一切要靠前人的评论定其真伪是非,文博事业等还会有发展,还会有进步吗?可见丁绍基的说法,难以成立,难以服人。应当看到,丁绍基所言是清末一部分人思想意识的真实反映,是“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24]324观念的延续,一切以前人见过、评论定真伪。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成就,也有每一代人的局限。欧阳修为金石著述开山奠基难以为工,赵明诚继承发展由粗转精,洪适另开蹊径推动向前发展,合乎金石学发展的常理,而丁绍基所言“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人生不满百,是多数人的情况。了却生前事,是每个人应当做的事情。清“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考证精博”,竖起了金石史上的里程碑,但要求他们对后来发现的群臣上醻刻石等,“于此刻一及”则是不可能的。汉碑继续出土,不能因为前贤未看到而否定其真实性,也不可能否定其真实性。
(三)唐太宗征刘黑闼未尝登猪山刻石
唐人李吉甫言:洺州永年县有“皇家平刘黑闼垒,在县西南十里,洺水南。贞观四年,于垒东置昭福寺,碑岑文本撰”[25]431;临洺县,“狗山,在县西十里。山顶石上有狗迹,因名。武德五年,太宗亲总戎讨刘黑闼,于此立营。”[25]433据此可知,唐太宗率兵征讨刘黑闼所立营垒,至少在永年县和临洺县各有一处。
《旧唐书》的《地理志》记载洺州、永年、临洺行政区划沿革,而不记载唐太宗征刘黑闼事[26]1498。《新唐书》载“永年、望。平恩、上。临洺、紧。……狗山有太宗故垒,讨刘黑闼于此。”[27]1014仅记临洺县有太宗故垒,而永年县无记载。
据上述可知,其一,《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三》记载有狗山、唐太宗征刘黑闼立营垒事,这是两书相同之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永年、临洺县有两处平刘黑闼所立营垒,《新唐书·地理三》未记载永年县营垒事。《旧唐书·地理二》并未记载狗山有唐太宗故垒。其二,《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三》记载的是狗山,又称娄山、驻跸山等,并非是群臣上醻刻石所在的猪山(朱山)。丁绍基撰《求是斋碑跋》卷一把位处猪山(朱山)的群臣上醻刻石写为《娄山石刻》,把娄山(狗山)当成了群臣上醻刻石所在地,无疑是把地理位置搞错了。其三,三书均未记载唐太宗征刘黑闼尝登猪山(朱山)刻石事。由上述来看,丁绍基所说的确如光绪《广平府志》所言“不知太宗立营在狗山,此刻在猪山,非一处也”[1]536,537,确实有误。
由上述可知,丁绍基所言把时间、地点、事件的关系弄混淆了,所说“两《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均言太宗征刘黑闼尝登此山刻石”,并不准确。光绪三年(1877年),丁绍基任广平府鸡泽县知县,与永年县相邻,不是登上猪山考察群臣上醻刻石,而是沿袭他人说法而作“娄山石刻”,不去核查《旧唐书·地理志》动辄说“两《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均言”,因此产生讹误是可以理解的,把娄山与猪山混淆,非丁绍基一人,而是一些人。[28]
(四)看见与发现文物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件事
对于群臣上醻刻石,丁绍基言:“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诸石纳在圹中,须待出土始见。临洺娄山亦非僻地,两《唐书·地理志》及《元和郡县志》均言,太宗征刘黑闼尝登此山刻石,既登此山岂不见此刻,而唐人亦无言及之者,何直迟至今日而人始见之耶?”我们知道唐太宗在永年县洺水南、狗山(娄山)等处立营扎寨,是否看到过北面猪山(朱山)的群臣上醻刻石,笔者尚未看到相关记录,丁绍基所言混淆了狗山(娄山)与猪山(朱山)的位置,所言唐太宗登上朱山看群臣上醻刻石是一厢情愿的想象,前面已经辨正过,不再赘言。
历代的确有人登上猪山(朱山),有的还留下了石刻文字。
如东汉石刻,在群臣上醻刻石之东21.01 米处,镌刻有“壬辰春后旬有三癸巳十九年书?日辰巳时??”九行20 个字[29]228-230。可知东汉有人登上猪山,应当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
又如唐代石刻载,“监军判官济阴郁久闾明达、侍御史鲁国郗士美、洺州刺史范阳卢顼、冀处士卢叶、监察御史刘荆海、邢州别驾杨审言、□□县尉李嘉同登。唐贞元(十四)年九月廿八日。”[30]据此可知,唐德宗贞元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798年11月10日),泽潞镇监军判官郁久闾明达等人,登上了猪山,并镌刻题名。他们应当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存在,但那是唐朝,汉代刻石还不那么珍贵。再则,他们是官僚,负责处理其辖区内的政治、军事等问题,群臣上醻刻石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只是留下了自己的纪念性石刻。
再如宋朝人题字“勾当虞候刘雾” ,同治《畿辅通志》已有著录①同治《畿辅通志》卷148《金石略·广平府·永年县·刘雾题名》(《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第10册第307 页)。王树楠又称为“宋时题名”( 《中国地方志集成·省志辑·河北》,第10 册第306 页)。,光绪《广平府志》亦有记载,认为“当为宋人刻石也。”[1]551后来失而不见。2016年1月7日,再现于世。有人认为是唐代摩崖刻石[31],有人认为是北宋石刻[32],有人认为究竟属于那个时代尚需研究,故称为古代刻石[33]。笔者认为无论属于何朝何代,都可证明“勾当虞候刘雾”登上了猪山(朱山)。
在东汉、唐宋人之前与其后,肯定还有人登临过猪山(朱山),只是没有留下登山石刻,没有留下相关记载,或者石刻、记载等已经散佚,我们不知道罢了。
文物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有在合适的社会条件下和合适的人在适当的时机才能发现。相对于发现者来说,熟视无睹者不少,视而不见者更多,不是说他们没有看到,不是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存在,而是说他们不知道那个存在的价值。梁启超说:“须将脑筋操练纯熟,使常有敏锐的感觉。每一事项至吾前,常能以奇异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别观察之兴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苹果落地?何以奈端独能因此而发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开水冲壶?何以瓦特独能因此而发明蒸汽?此皆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而已。”[34]83同样,无数登临猪山者,多数应当显而易见地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独是识真者寡,耳食者多。”[35]2413只有极少数人是发现者。
一般人的看见和学者的发现,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如群臣上醻刻石,一般人的看见,是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群臣上醻刻石;学者的发现,是不仅看到了群臣上醻刻石的存在,而且发现了年代、价值等问题。从西汉到清朝道光年间,近2000年的岁月中,有无数登上猪山看见过群臣上醻刻石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使他们看到了也是视而不见其价值的客观存在。直到道光年间,沈涛偶然地发现了群臣上醻刻石,提出了石虎建武六年说等,刊刻在《交翠轩笔记》中流传于世,引起世人注意,沈涛是发现者①张德容撰《二铭草堂金石聚》卷一《赵上醻刻石》目录称:“前人未有著录,惟见沈涛《交翠轩笔记》,刘喜海《金石苑》稿本载之未刊。”正文说:“向来未有著录,邵武杨兆璜守广平时访得之。”(《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3 册第1725、1748 页)“未有著录”,目录与正文说法是相同的,而最早著录、访得者,目录与正文分为两人,目录说是沈涛著录,正文说是杨兆璜访得。正文“邵武杨兆璜守广平时访得之”的说法,被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二《群臣上醻刻石》(第83 页)所引用转载,广为传播,很多著作都重复其说法,许多文章都转述其看法,数量不胜枚举。笔者认为发现者是沈涛,而非杨兆璜,参见拙文《燕赵历史文献研究•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探微》,中华书局2005 年,第83—86 页;《西汉群臣上醻刻石新探》,《中国历史文物》2008 年第3 期。。虽然,沈涛对于年代、字体的说法并不正确,但发现之功不可磨灭。在沈涛偶然性的发现中,体现着发现群臣上醻刻石需要基本的知识储备、金石学家的眼光、史学家的才、学、识等素养,再加上担任知府的机会,登狗山寻唐碑而无收获的情况,具“有锐敏的感觉,施特别的观察”等因素,正是诸多机缘凑集,才使得偶然地登上猪山(朱山)的沈涛成为群臣上醻刻石的发现者。在偶然之中也存在着必然,那就是发现群臣上醻刻石需要眼光,需要学识,需要机遇,以及社会需求等,没有这些眼光、学识和机遇等,你就是看过数十次,也不会发现其价值等。
发现的前提是看见,看见者并非都是发现者。有些文物,在内行眼里是瑰宝,在外行手里贱如草,这是内行与外行的区别,是专家学者与普通群众的区分,是收藏家捡漏的奥秘,也是古董商人发家致富的前提。
如现代人都知道甲骨文是国宝,“回忆光绪己亥、庚子间,潍县估人陈姓,闻河南汤阴县境小商屯地方(当为安阳小屯)出有大宗商代铜器,至则已为他估席载以去,仅获残鳞剩甲,为之嗒然!乃亲赴发掘处查看,见古代牛骨龟版,山积其间。询之土人,云牛骨椎以为肥田之用,龟版则药商购为药材耳。估取骨之稍大者,则文字行列整齐,非篆非籀,携归京师,为先公述之。先公索阅,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②王汉章《古董录》,《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50 期,1933 年。又称《殷墟甲骨纪略》,《王懿荣集》,齐鲁书社1999 年,第602 页。因此而发现了甲骨文,在此之前,甲骨是当做肥料来用、作为龙骨药材来卖的。
又如中山国“守丘刻石”,又称河光刻石等。1935年夏,被平山县南七汲村刘西梅不经意间挖出来,带回家当作石座用。1974年冬,考古队长陈应祺找到了刘西梅家中的刻石,向李学勤教授请教,才知道了是守丘刻石[36]346-347,确认附近大墓为王陵,为中山灵寿城的发现提供了线索等[37],成为打开中山国历史大门的钥匙。
再如作为镇国玉器之首的渎山大玉海,“盖金元旧物也。曾置万岁山广寒殿内,后在西华门外真武庙中,道人作菜瓮。”[38]360沈阳故宫博物馆的十大镇宫之宝之一的后金云板(又称努尔哈赤云板、大金天命云板等),曾经作为辽宁海城某小学的上课铃使用。在当时有多少人看见过,仍然充当菜瓮、上课铃,被人发现后,其命运也就改变了。
诸如此类,对于文物无知的例证难以枚举,导致文物毁灭者不知其数,致使国宝蒙难的事件罄竹难书③如有时间,既可以在网上搜索此类资料,不胜枚举,也可以翻阅流泉、王世建、黄沙主编的《尘埃历尽: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 年)和高学栋、夏风主编《邂逅太阳:中国珍贵文物蒙难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 年),两书也提供了一些例证,可供参考。。糟践文物,暴殄天物,这不是气话,而是对于文物无知者无可无奈何的说法。同样,群臣上醻刻石,“又系摩崖,非同墓志诸石纳在圹中,须待出土始见,临洺、娄山亦非僻地”。从山上有东汉、唐宋石刻,我们也可以推测登临猪山(朱山)者历代不断,无疑有些人看到了山顶之巅的群臣上醻刻石。但他们无相应的知识素养,无发现群臣上醻刻石的专业眼光,群臣上醻刻石在他们面前,仅是一块带字的石头而已,并没有发现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没有引起他们特别的关注,没有隆重地向社会推荐,没有深入、仔细的探讨,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能因为没有发现眼光的人,就质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真伪,那是没有道理的。
不仅文物珍宝,需要具有一定知识素养和眼光的人,才能发现其价值,自然景观也是如此。如河北赞皇县的嶂石岩地貌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丹霞地貌、张家界地貌)之一,多由红色石英岩构成。远远望去,赤壁丹崖,奇峰幽谷,如屏如画,千百年来就矗立在那里。1972年,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郭康发现气势壮阔的红崖长墙砂岩地貌,又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正式将该地貌命名为嶂石岩地貌,如今已成为国家四A级景区,闻名遐迩。
再则,即使是专家学者,对于文物真伪、价值的认识也不是一蹴即就,而要经历观察文物、粗浅看法、发现新证据、逐步深化的认识过程。
如王羲之《上虞帖》的唐摹本,文革中,被堆积在抄家物资之中。1972年,上海博物馆万育仁参加抄家物资书画等清理工作,发现《上虞帖》,带回博物馆,请专家鉴定,被视为赝品,打入仓库冷宫。三年后,万育仁又向博物馆馆长沈之瑜重提《上虞帖》。沈之瑜与马承源看后请谢稚柳鉴定。谢稚柳看到《上虞帖》,知道此帖刻于《淳化阁帖》诸帖中,多种著述都曾提到,但原本多少年来湮没不彰,不为人知。谢稚柳“把此帖又与《万岁通天进帖》《如何帖》相比较,于是,信定俱为唐人摹本。《上虞帖》以摹本的现象而论,逊于《万岁通天进帖》的王羲之书,但以《上虞帖》体势的灵动绰约、丰肌秀骨,却远较王羲之的《如何帖》为胜。这就已经看出《上虞帖》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了。”谢稚柳看到《上虞帖》还保留着北宋内府的原装,有月白绢签,宋徽宗瘦金体书“晋王羲之上虞帖”七字,隔水前押“御书”葫芦骑缝印,帖的前下角与后上角,与前后隔水相接处,均押“政和”“宣和”骑缝印,后隔水与拖尾相接处押“政和”骑缝印,拖尾中间押“内府图书之印”朱文大印。谢稚柳又看出了南唐“集贤院御书”和“内合同印”,“用同位素钴60的照射,果然描绘出‘内合同印’和‘集贤院御书’印,再后来,裱画师严桂荣在重新装裱时,经他的技术处理,这两方印又清晰地再现出来。此二印在宋代就被称之为两方金印,在并世流传的古书画上,有此两印的也仅见于《上虞帖》。发现这一历史流传的印记,对《上虞帖》是唐摹本,提出了有力的证据。”仍有人不相信,谢稚柳撰《晋王羲之〈上虞帖〉》一文,回应人们的质疑[39]227-230。几经观察鉴定,证实了的确是王羲之《上虞帖》的唐摹本。
又如1975年,陕西省西安市郊区山门口公社北沈家桥村杨东锋平整土地时,发现锈迹斑斑的铜老虎,随着锈迹褪去,露出了金字。1978年11月30日,杨东锋送交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经手者认为是杜虎符①黑光《西安市郊发现秦国杜虎符》(《文物》1979 年第9 期)报道杜虎符发现。,罗福颐认为是据传世秦新郪符而造伪[40]205-206,经反复考究确定为秦国杜虎符②戴应新《秦杜虎符的真伪及其有关问题》(《考古》1983 年第11 期),陈尊祥《杜虎符真伪考辨》(《文博》1985年第6 期)考辨杜虎符的真伪。晏新志《“杜虎符”的发现与研究述论》(《文博》2018 年第6 期)系统梳理杜虎符相关问题。。
再如1981年11月9日,陕西省旬阳县旬阳中学学生宋清捡到了一块多面球体的石头,上面刻有文字,认为是“骰子”,郑重其事地交给了旬阳县文化馆。文化馆工作人员不知是何物,放到了仓库中,尘封十年,1990年,专家看出了是北周贵族独狐信的26面球体印,镌刻有70余字,是目前所知面数最多的印章,是最早以楷书入印者,堪称国宝,价值连城,随之被收藏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不仅出土文物、传世文物、书画等有看见与发现的区别,而且传世文献也有看见与发现的区别。潞州长子县(治今山西长治市长子县丹朱镇)崔法珍断臂设誓,募刻大藏经,得山西、陕西善男信女捐助,从金熙宗天眷二年(1139年),到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年),在解州天宁寺等处刻成682帙、1379部、6980卷的大藏经。大定十八年,进献给朝廷印经一藏。二十年,进献经板于朝廷,金世宗命选导遵等人校正,遂印刷流传于世。元世祖中统(1260-1264年)初年,广胜寺印藏经会遣僧人入京用元初补雕版自印藏经,每卷前加印释迦说法图一帧,运回赵城,供养在寺中。700年来,多少僧人、住持、护法居士等看见过此书,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有僧人等修补此书,清雍正年间曾钞补残缺,无人发现此书的价值。附近村民进寺,取走经卷,用来覆瓿、糊窗、补壁,或拿去卖钱,或用以辟邪祈福,无人知道是佛教瑰宝。广胜寺大藏经亦未见诸于公私著录,不为世人所知。
1933年夏①《宋藏遗珍·宋藏遗珍叙目》范成《序二》载:民国“二十一年夏,有老头陀性空者,朝拜五台,转向终南山潜修,途经予西安庽所,承告赵城县广胜寺存古本藏经四橱,闻讯殊喜,雇车买骡,跋山涉水,行抵霍山。”(1936年,第1 页A)范成《历代刻印大藏经略史》作:民国“二十二年春”。《山西发见最古佛藏》载:“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前派范成法师,赴陕晋一带访经,刻在山西赵城广胜寺,发见古藏经五千余卷。”(《申报》1933 年8 月31 日,第14 版)。此文又见《正信》第2 卷第16 期,1933 年9 月15 日,可知当以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为是。,为影印宋碛砂藏经配补缺佚经卷的法师范成,来到赵城广胜寺,发现了大藏经,调查经藏的装帧、版式、行款、概况等,认为“若按《至元法宝录》所编,此经应有七千余卷,现仅存四千九百七十五卷,尚缺十分之三。”②《宋藏遗珍·宋藏遗珍叙目》范成《序二》(1936 年,第2 页A)。蒋维乔《影印宋碛砂藏经始末记》载:“照千字文计之,有七千余卷,现存五千零十七卷。”(《影印宋碛砂藏经》首册之二,上海影印宋版藏经会1935 年,第38 页A)两人说法不同,当是在不同时间而言,故有不同。访求零散经卷,查找影印宋碛砂藏经所需要的经卷,协助徐森玉选编珍稀藏经为《宋藏遗珍》,并函告各处,为报刊所报道③笔者目前所看到的,如山西通信《山西发见最古佛藏》,《申报》1933 年8 月31 日,第14 版,此文又见《正信》第2 卷第16 期,1933 年9 月15 日。《山西广胜寺发现宋藏经》,《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2 卷第5 期,1933 年10 月;《山西广胜寺收藏有金刻藏经》,《海潮音》第14 卷第11 期,1933 年11 月15 日,上述两刊均转载《申报》、《大公报》等消息。无畏居士(周肇祥)《广胜寺发见北宋錾经卷纪略》,《艺林月刊》第47 期,1933 年11 月等。笔者未看到的报道还会有。,成为现代佛教文献史的一大发现,改变了广胜寺大藏经不为人知的状况。
开创者难为工,后来者易为精。范成发现了广胜寺大藏经,有些问题仍未解决。1934年秋,蒋唯心到赵城检校广胜寺大藏经,归纳有关问题,撰写《金藏雕印始末考》,言:“今检各帙完整者极少,有全帙俱缺者,综计原藏应有七千卷,今才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盖已残十分之三矣。经皆卷子式,黄表赤轴,长短大小略有参差。卷首附装释迦说法图一幅,状如上寺后殿造像,右端题‘赵城县广胜寺’六字”④蒋唯心撰《金藏雕印始末考》(支那内学院1935 年,第6 页)。数量比范成所言少了18 册。。说明数量、形制、特点。明确广胜寺大藏经,“今正其名为金藏可也。”[41]9指出金藏由原刻与补刻两部分组成。说明原版雕刻最早与最迟年代,原版为私人募刻,大藏经板会设于天宁寺。补刻占全藏四分之一,采取了官私合作的形式。倡导刻藏者是断臂募刻的崔法珍,施主始终以村民为主体等。前面刊载12张金藏图片,后面附录《广胜寺大藏经简目》。《金藏雕印始末考》,系统梳理了金藏雕印的始末,深化了金藏发现的内涵,成为赵城金藏研究的奠基之作。随着实地考察、学术研究、影印出版、商业运作,书籍广告等多种形式接踵而至,默默无闻的广胜寺大藏经,广为世人所知,现在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国宝之一——《赵城金藏》。
发现是多层次的,不仅上述出土文物、地上文物与传世文献等,有人慧眼识宝是发现,而且前人有著录而失传不知其所在,后人再次发现其存在,阐释其价值,研究其内容,亦属于重新发现。
如元氏封龙山碑,宋洪迈《隶释》卷27引《天下碑录》载:“汉封龙山碑二。在获鹿县南四十五里山上,延熹七年立。”郑樵撰《通志》卷七十三《金石略一》载:“封龙山碑,镇州。”元纳新言:天台三公庙,“庙有封龙山颂碑一通,汉三公山碑一通。”[42]154明杨士奇曰:“右封龙山碑,在元氏县。汉延熹七年,至今千二百余年,石刻虽颇剥蚀而文字尚可寻究。碑首云:‘封龙山者,北岳之英也。’此本得之刘智安主事。”[43]635杨士奇,江西吉安府泰和人,官至首辅。刘智安(改名冯敏),江西吉安府永丰人,永乐十三年进士,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以封龙山碑拓本给同乡杨士奇,可见永乐年间仍有人在椎搨封龙山碑拓片,在社会上流传。自此之后,即使有记录封龙山碑者,也是简单而不准确。如明王应遴言:“封龙山碑,在元氏。”[44]4297很简单。清倪涛言:“封龙山神碑,在元氏县西五十里,光和四年立。”[45]318光和四年立,当是三公碑,碑名误。又作:“封龙山碑,延熹七年。”[45]403两者年代相矛盾,当是抄录前人著述以讹传讹而然。清代金石名著,如王昶《金石萃编》,翁方纲《两汉金石记》,孙星衍《京畿金石考》①(清)孙星衍撰《京畿金石考》卷下《正定府·元氏县》载:“唐封龙山碑”下有䕃按曰:“汉封龙山颂,道光间出,今在元氏文清书院。”(清同治光绪间吴县潘氏刊《滂喜斋丛书》批注本,第8 页A)可见原文无汉封龙山碑的著录,是后人用毛笔添加的批注,它本所无。《寰宇访碑录》,沈涛《常山贞石志》等均未著录,可知封龙山碑已经不为金石家所见,不为世人所知。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十一月,元氏县知县刘宝楠(号念楼)在王村访得封龙山碑,其子刘恭冕记载其事,曰:“家君宰元氏之明年,岁在丁未冬十有一月,访得此碑。在今县治西北四十五里王村,其地有三公废祠,元米惠迪撰此祠碑云:魏孙该《神祠赋》:‘元氏西界有六神祠,吾观其一,然皆以三公题额焉。’是也。元碑亦家君所得。既命工人舁至城庋置薛文淸祠之东箱,碑石故厚,工人恶其重,乃剥其碑阴中分之,碑上截断裂为三段,家君为之恨惜累日,爰命嵌合增置石座,而命冕考释其文。”[46]342元纳新记封龙山碑在天台三公庙,清朝发现在王村三公废祠,地理位置变了,也就使得学者不知其踪。张穆跋亦言:“又越十余年至道光二十七年封龙山碑岀,皆欧、赵、洪、陈诸人所未见也。封龙碑,宋人《天下碑录》有其目云:‘在获鹿县南四十五里山上。’丁未冬十一月,宝应刘君念楼宰元氏,始访得之于县西北四十五里之王邨,命工舁至城内文淸书院,而首以搨本见诒。”②(清)张穆撰《斋文集》卷四《延熹封龙山碑跋》(《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616册第372 页)。《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 册《商周至秦汉书法》八三《封龙山碑》上载张穆题记曰:道光“丁未冬,刘君念楼初访得此碑,手拓二纸,一以寄穆,一以寄梅郎中伯言。伯言将南归,用以裹书赠鲁川比部,于是鲁川伸熨装潢之。亦自诧有此碑初拓本矣。已酉十月。”(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年,第136 页)伯言,是江苏上元人梅曾亮表字,时任户部郎中。鲁川,是山西代州人冯志沂表字,时任刑部主事。张穆两则题跋,可与刘恭冕《汉延熹封龙山碑考》互证。以当时人记当时事,可靠可信。刘宝楠再次发现封龙山碑后,集中于元氏城内文清书院保存,椎搨拓片赠送学者、同好题跋、研究,有些学者挥笔题写碑跋,研究文字,求索人物踪迹,追求历史背景③如(清)许翰撰《攀古小庐杂著》卷十《金石说·汉封龙山碑》载:“道光廿七八年间,余同年宝应刘楚桢宝楠官元氏令访得之,平定张石州穆以拓本寄余。”释文并撰跋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160 册第764—766 页)。(清)张德容撰《二铭草堂金石聚》卷六《汉元氏封龙山颂》双钩碑文,并撰跋文(《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3册第1941—1946 页)(清)方朔撰《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卷二《汉封龙山碑跋》有题跋,有释文(《石刻史料新编》第二辑,第19 册第14258 页)等。等。自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之后封龙山碑销声匿迹四百余年,因刘宝楠再次发现,而被《补寰宇访碑录》《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著述收录,拓片刊载于《中国书法全集》《中国美术全集》《汉碑全集》等书中,《元氏封龙山汉碑群体研究》等论著相继问世,封龙山碑因再次发现而闻名于世。
又如汉司徒袁安碑,郦道元曰:彭城“城内有汉司徒袁安、魏中郎将徐庶等数碑,并列植于街右,咸曾为楚相也。”[2]1990此言又见于洪适《隶释》卷20收录的《郦道元水经注·袁安碑》,可见袁安碑早已有名于世。清代杨守敬认为,“此数碑,欧、赵皆不著录,洪但载郦说,盖已佚。”[2]1990但想不到,洪适去世七百余年后,袁安碑,“民国十八年发现于偃师城西南廿余里辛村东牛王庙中,地在洛阳故城东南。背面有万历某年刻字。初置神像前为供案,字在下面,无人知为古石。十七年七月以庙为小学校校舍,乡人夏日午憩,仰视有字,传知为汉石,次年村人任继斌初以拓本传世。”[3]31931年6月,周肇祥发布以画梅易来的袁安碑初拓拓片,发表袁安碑跋,使袁安碑传播的更广泛[47]。袁安碑何时从安徽徐州流落到河南偃师城,笔者不清楚,但袁安碑做了300余年的供案,会有多少人看见,无人知道是汉碑。1929年,任继斌初以拓本传世,1931年,周肇祥发表汉袁安碑跋文,亦属于再次发现。袁安碑传世后,又被章太炎视为伪作[48]。后闻名全国,成为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
诸如此类的事例,屈指难数。可知文物的发现,有看见与发现的异同。既有有意的寻找发现,也有无意的偶然发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需要发现者具有眼光和知识素养等,否则,就是看了几十年、见了无数次,也不能发现文物珍宝。而文物的真伪,国宝的价值,不是由发现时间的早晚决定的,反而是发现的越晚价值越高,因为物以稀为贵;不是因前贤未见就是假的,因为前贤也有生命的局限性,不可能万寿无疆,发现所有文物;也不是由最先看到者所决定的,而是由其本身蕴藏的价值所决定的,只有具有一定知识素养、眼光和机会的人,才能发现其价值。即使有素质有眼光有机会者,不下功夫也难以发现其奥妙。即便是专家,也未必一眼就能看明白,需要历经逐渐深化的认识过程,新资料、新思路,新方法等,推动着发现向前发展。文物等待了数千年而被知音发现是幸运的,文物发现者也是幸运的,但这种发现又仅仅是开始,因为文物珍宝内涵、价值、意义、影响等方面的发现,是永无止境的,社会的进步,学术的发展,使得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发现,在发现中提升着文物的价值,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
二、群臣上醻刻石真实的证据在本身
从清道光年间沈涛发现群臣上醻刻石以来,学者们聚焦于群臣上醻刻石的年代问题,先后提出了六种主张[49],前提是多数学者认为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实可信的,否则探讨假冒伪劣的群臣上醻刻石年代,岂不是白白耗费精力,正常人不为。
有些学者相信群臣上醻刻石为真。如称群臣上醻刻石为“汉祖刻”[50]3的赵之谦,多次撰写序跋,认为是“自瑯邪片石入海后,除鼓存疑外,此为传世第一古石矣”51]5258的梁启超,说明群臣上醻刻石真实性的徐森玉①上海博物馆编《徐森玉文集·西汉石刻文字初探》载:“目前所能收集到的西汉石刻文字拓本,而可以确认为是真的,有以下各种:一、霍去病墓石刻字:‘左司空’‘平原乐陵宿伯牙霍巨孟’二石。二、群臣上寿刻石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年,第134-135 页)等10 件,没有争论者,群臣上醻刻石包括在其中。,称为群臣上醻题记的商承祚[52]2,称之为西汉第一石的陈振濂②陈振濂著《陈振濂谈中国书法史殷商-魏晋》以《西汉第一石——群臣上寿刻石》命名,畅谈群臣上酬刻石所反映的山野气息与潇洒自若的仙家气派。(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 年,第57-58 页。)等,这些学者都相信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实的。
有些著述收录、记述、评论群臣上醻刻石。有些金石著述收录群臣上醻刻石。如张德容的《二铭草堂金石聚》,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杨铎的《函青阁金石记》,王仁俊的《金石三编》等,均收录群臣上醻刻石于书中。有些碑帖书目著录群臣上醻刻石,如张彦生的《善本碑帖录》,杨震方的《碑帖叙录》,袁维春的《秦汉碑述》,王壮弘的《增补校碑随笔》,彭兴林的《中国历代名碑释要》等,都将群臣上醻刻石著录在书中。至于中国书法史、两汉书法史、地方史志等著述中,记述、评论群臣上醻刻石者,大有其人,多有其书。由上述可知,众多学者、大量书籍,从积极方面认同群臣上醻刻石为真实。
在专门的金石辨伪著述中,如清陆增祥撰《八琼室金石补正》附录《八琼室金石袪伪》[11]2205-2219,马子云、施安昌著《碑帖鉴定》有《新旧伪造各代石刻》③马子云、安昌著《碑帖鉴定》下篇第二章《碑帖鉴定》附一《新旧伪造各代石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470-476 页)。又见马子云著《碑帖鉴定浅说》四《如何鉴定碑帖·新旧伪造各代石刻》(紫禁城出版社1986 年,第93-99 页),江岚《历代碑刻辨伪研究综述》,不仅参考上述陆增祥、马子云、施安昌等著述,而且还收录了方若原著王壮弘增补的《增补校碑随笔》、顾燮光著《古志新目初编》附《伪作各目》、赵超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附《伪志(包括疑伪)目录》等著述,附录《伪刻目录》,整理成《各家所列伪刻目录汇总表》[53],总计涉及到汉代伪刻90 余件,上述著述中均无群臣上醻刻石的名称,从消极方面证明群臣上醻刻石不在伪造、袪伪的范围之内。
不仅众多学者、著述认同群臣上醻刻石为真,而且2013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朱山石刻中,群臣上醻刻石是其重要的因素。
上述列举诸例对群臣上醻刻石为真的看法,得到了学者与官方两方面的认同。
学者与官方肯定群臣上醻刻石真实的看法,与丁绍基怀疑态度不同,已成为主流看法而为社会所认同。严格说来,上述看法是学者与官方对于群臣上醻刻石真伪的认识,这些认识来源于对于群臣上醻刻石本身的观察分析与思辨,也会随着思想、方法、史料等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作为理论根据,不是原始性的依据,诸看法的原始性依据,在于群臣上醻刻石本身。从群臣上醻刻石本身看,也可以自证其真。
(一)刻石的形制
群臣上醻刻石位于邯郸市永年区永合会镇吴庄村正北约二里的猪山(朱山)顶上,与山体连在一起,石刻高150厘米,宽52厘米。刻石字面依山斜面西向,高120厘米,宽8厘米,符合“古者方曰碑,员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54]917的定义,是不规则的长条状天然红砂岩摩崖石刻。表面比较粗糙,是未经过细致研磨处理的岩石,这是西汉石刻的特点之一。与其之前的中山河光石刻一脉相承,与其之后的霍去病墓石刻异曲同工。东汉时代的碑刻或摩崖刻石,有的经过了研磨处理,表面光滑、美观,形制的时代特征明显。
有些学者对于群臣上醻刻石形制有不同的看法,如马衡认为:“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厓。”“摩厓者,刻于厓壁者也,故曰天然之石。”定义与《金石索》一脉相承。“至西汉之《赵群臣上寿》刻石(赵二十二年,当汉文帝后六年),麃孝禹刻石(河平三年),东汉之宋伯望刻石(汉安三年),虽未详其形制,殆亦此类。李贤所谓‘方者谓之碑,员者为之碣’(《后汉书·窦宪传》注),是也。”[55]67、68也就是群臣上醻刻石属于碣类。有学者亦认为,群臣上醻刻石,“其形制基本上是一块椭圆形的碣石,介于方圆之间,和秦始皇刻石相同。”[56]191这种看法虽然持之有故,但并未看到群臣上醻刻石实际状况,带有主观想象之嫌。
群臣上醻刻石的形制,既有天然之石为载体的一般性,又有由猪山(朱山)地处太行山东麓低山丘陵地带来的特殊性。这里没有层峦叠嶂的高山,没有壁立千仞的岩峰,猪山(朱山)孤峰突起,仅海拔239米,群臣上醻刻石不是镌刻在陡立的峭壁上,而是雕刻在朱山之巅的红砂岩石上,面向苍天,身观群山,在摩崖刻石中是比较独特的。
(二)铭文的内容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15字铭文,着眼于纪事,包含了国号、时间、人物、事件、地点等历史构成要素,记述了西汉赵国历史上一件纪传体史书没有记载的历史事实。虽然字数不多,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体现着西汉初年诸侯王国的特色。
“赵”字起首,表示以国号为首,有众多资料可与群臣上醻刻石相互证明。如赵国,有“赵国易阳南界”石刻[57],“赵相刘衡碑”[10]171-172,“赵内者,容二升,重二斤二两”[58]铭文的铜豆器,“戍卒赵国邯郸邑中阳陵里士伍赵安世,年五十五”[59]161等类型相同的诸多居延汉简,“赵太子丞”[60]41、“赵内史印章” “赵相之印章”[61]1238等封泥。其他诸侯王国亦如此,有“昌邑食官鼎容二斗,第五”[62]287-290铭文的铜鼎,“常山食官钟,容十斗,重□钧□斤”[63]33、34铭文的铜锺,“江都宦者,容一升,重三斤”[64]铭文的铜行灯,“广陵王玺”[65]铭文的金印,“长沙丞相”铭文的铜印[66]24,彩版三1、2,“临菑丞相”[61]666、“齐御史大夫”[61]763字样的封泥,“广陵宦谒”铭文的印章[67],“齐内官丞”“齐铁官印”“齐乐府印”[68]52-57、“楚宦者印”“楚太仆印”“楚中谒长”[61]534、536、538等字样的封泥,朱书“长沙王后家杯”[69]字样的漆耳杯,“常山长贵”“常山长昌”[70]字样的瓦当等,多种多样的器物铭文,都以诸侯王国号为首。诸侯王以国号为首,把本国与汉朝和他诸侯国区别开来,凸显出诸侯国的地位。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国号与年月日因素俱全,不仅便于核查记述的准确与否,而且反映着西汉诸侯王自有纪年的事实。
“群臣上醻”,体现着诸侯王国拥有相对独立的“群臣”官制系统,上述所列举的诸侯国金玺、铜印、封泥等均可为证,但那只不过是诸侯国官制体系中的几个代表而已,汉初诸侯王,“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71]741“宫室百官,同制京师”[71]394,写出了其地位与权势,而“淮南王群臣”“长沙王群臣”[71]1747、1750、“昌邑群臣”[71]2946、“胶西群臣”[72]3401等,则体现出其声势,可见赵国群臣不是孤证。“群臣上醻”是典型的汉代语言等,不仅可以自证其真,而且还具有“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73]619的学术价值。
上述众多与群臣上醻刻石铭文相呼应的简牍、铜器铭文、封泥印章等资料,既可以与群臣上醻刻石互证,证实群臣上醻刻石并非是孤立存在,是诸侯王权势地位的真实体现,而群臣上醻刻石又可为新史料提供证据,相互证明,相得益彰。
(三)铭文的款式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国号在前、年月日因素俱全,是典型的西汉王国刻石的款式。
与此类似铭文款式的出土文物,有山东曲阜周公庙东高地出土的“鲁六年九月所造北陛”的题字[74]2、图版二,传世有“长沙元年造”铭文的剌庙鼎[75]45,湖南长沙风篷岭汉墓出土有“长沙元年造”铭文的铜灯[72],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带有“昌邑九年”“昌邑十年”铭文的漆器[77]183,虽然有石刻、漆器、青铜器等器物类别不同,但上述诸例都有国号与年代的因素,排列方式国号在前,年代在后。这是西汉诸侯王纪年款式的一种,还有其他的纪年款式[78]174-182。
此类型的纪年格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有。如《淮南子·天文训》记述的“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记载的异姓王纪年,如长沙国王的纪年,有“长沙文王吴芮元年”等,记载了吴氏长沙国诸王的纪年情况,还记载了同姓王纪年,如“淮南厉王长元年”“吴王濞元年”等,反映了纪传体史书中记述诸侯王纪年的款式,与群臣上醻刻石顺序一样,国号、谥号在前,年代序数在后。
群臣上醻刻石铭文的款式,与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互证,体现了西汉初年的时代特征,反映了诸侯王高贵的地位,明确地区分了赵国与汉朝和其他诸侯王国的异同,证实了群臣上醻刻石的确为真。
(四)铭文的字体、书法
群臣上醻刻石的字体,铭文中的“醻”“年”等字很明显地带有篆书风格,“丙” “臣”“石”等字带有隶书因素,标志着群臣上醻刻石体现出正处于篆隶变化时期,由秦篆的长形演为方形,转笔方折,带有隶书笔意,既有旧的痕迹,又有新的因素。群臣上醻刻石的篆书字体,与先秦、秦朝和东汉时代石刻篆书字体相比,有明显区别,体现了西汉石刻隶变特点,并且是现存汉篆中最早的刻石。
群臣上醻刻石的书法,书写自然随意,用笔结字,无拘无束,大小不一,布行紧凑,书风古劲朴雅,仪态朴茂雄浑,丰满有神,另具一格,继往开来。
无论是群臣上醻刻石的字体,还是其书法,都带着承前启后的西汉时代特点,由此可见,群臣上醻刻石是真实可靠的。
(五)铭文的历日
“赵廿二年八月丙寅群臣上醻此石北”,与《二十史朔闰表》《中国先秦史历表》《春秋战国秦汉朔闰表》等历表核对,赵二十二年八月的确有丙寅日,并且有两个先秦赵国君主——赵肃侯、赵武灵王,四个汉代赵王——赵王遂、赵共王充、赵节王栩、赵顷王商,六位赵国君、王纪年中均有“廿二年八月丙寅”,可知此历日不是向虚而造,而是在历史上的确存在过。由此亦知,“赵廿二年八月丙寅”不具有历日的唯一性,而是综合考量真伪的一个因素。
(六)刻石的位置
秦汉时代制作摩崖刻石,镌刻铭文,是很郑重其事的,多讲究位置,先刻者具有更多选择余地,后刻者选择余地相对变小。群臣上醻刻石,镌刻在猪山(朱山)之巅的岩石上,位置优越,显而易见是最早的镌刻者。
在群臣上醻刻石之东21.4 米处,有东汉壬辰春后旬刻石。刻石就在与山体相连的岩石上,刻石字面呈不规则四边形。刻石字面大致平整,依山势倾斜,与水平面约呈60 度角,石刻面向南[29]。东汉壬辰春后旬刻石没有刻在山顶最高处,当是群臣上醻刻石已经刻在了猪山(朱山)之巅,只好刻在稍微低些的位置上。可以推知群臣上醻刻石镌刻在东汉壬辰春后旬刻石之前。
还有唐代石刻、宋人题字等,其位置也均不如群臣上醻刻石优越,也可以证明群臣上醻刻石形成在前。
西汉群臣上醻刻石之真,不仅诸多学者、著述认同其真的看法可以参考,更重要的在其自身,而且综合考察群臣上醻刻石的形制、内容、字体、书法、款式、历日、位置等因素,无疑可证实群臣上醻刻石之真。
学术是天下公器,人有南北、中外之分,道无东西、古今之别,以求真求实求是为宗旨,以事实为依据,以实践为标准。参与者无身份高低贵贱之分,是非判断无人数多少之别,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认识无须区分对错,都是学术成果的组成部分,从不同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人名、地名、官名、年代等,是持之有故的“故”,这些具体的“故”看错了,说错了,言之成理也就失去了基础,认识也就站不住脚了。怀疑一切是学术的信条,丁绍基怀疑群臣上醻刻石的精神值得称道,但所主张的宋之欧、赵、洪诸家于金石之学“搜罗殆徧”,不仅欧、赵、洪自己不承认,清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达不到,而且现代学者也做不到,实属一厢情愿的想象。清朝顾、朱、钱、王以及乾嘉之翁、孙对于群臣上醻刻石“曾不一及”,的确是事实,实际上,前贤的寿命有限,后世的发现无穷,前贤对于众多文物珍宝“曾不一及”,实属正常,因此,以前贤未见、评论与否作为真伪的论定的依据,实属刻舟求剑,既不合情,更不合理,理当否定其说法。至于丁绍基所言是摩崖刻石而非墓志铭,地理位置又非偏僻,唐太宗曾登临此山,为何无人见到?丁绍基不仅把狗山与猪山混淆了,而且混淆了看见与发现的不同含义,看见群臣上醻刻石的人无疑不少,发现者只有沈涛。因为一般人的看见,是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群臣上醻刻石;学者沈涛的发现,是发现了群臣上醻刻石产生的年代、价值等,由此开始使群臣上醻刻石名扬天下,成为汉石之祖。群臣上醻刻石,不仅有诸多学者论证了其真,而且自身的形制、内容、款式、字体、历日等也可自证其真,丁绍基怀疑的看法站不住脚。我们不能像丁绍基那样以前贤未见,禁锢自己的头脑,遮蔽自己的眼光,应当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与时俱进的态度,开阔视野,前辈未看到的史料,我们发现了是贡献;前人未运用的史料,我们运用了是幸运。打开眼界发现新史料,动手收集新资料,积极推动群臣上醻刻石研究向着深化、细化方向发展,取得新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