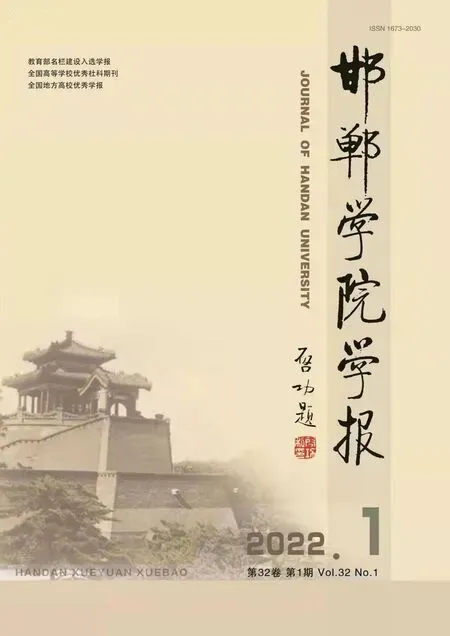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政策调整述评
吴洪成,闫 倩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在日本侵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下,大片国土沦陷,日寇残暴强盗行径使沦陷区教育难以维系。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国民政府对教育政策加以调整,并形成许多具体措施,包括与日伪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组织高校内迁、协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加强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等诸多方面。这些教育政策及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族教育在艰难中得以延续,减轻了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教育资源和办学活动的冲击,为全民抗战下的教育持续和保存人才力量发挥了一定作用,构成国共统一战线联合抗战背景下教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争取沦陷区教育权
1938 年10 月,武汉会战粉粹了日寇企图快速灭亡中国的既定战略,面对日军在中国战场进退维谷的局面,日本军政当局被迫调整对华战争策略。为此,日本制定《对华长期战争施策要领》,从单纯军事路线转变为“以华治华”和控制民众思想的“软”侵略。在此背景下,日本控制下的汪伪、华北、蒙疆以及冀东伪政权实行一系列亲日措施,包括破坏原有的教育机构、建立新民小学、调整小学课程、大力倡导日语教育、组织反共和粉饰中日关系、促进留日教育等诸多方面,企图以教育为媒介实现加强对华殖民统治的意图。为反抗教育侵略,遏制日伪奴化思想渗透,国民政府注重建立战时教育体制,维持正常教学秩序。
(一)设立战时教育机构
1938 年,民国政府行政院制定并通过了《沦陷区教育实施方案》,明确提出:“由教育部选择意志坚强、富有牺牲精神及教学经验之教育工作人员,为沦陷区教育督导员”,具体负责各该区内教育工作。[1]291战教人员应采取灵活方式设法维持战区失学青年教育,联络、救济战区教育界人士,宣传民族意识,避免被敌人利用,使之团结一致,服务于抗战教育事业。又由于侵华日军对中国教育机构的肆意轰炸及破坏,各级各类学校遭受严重损失。一时间,沦陷区高校师生纷纷南下,国民政府遂在教育部内设立“平津国立院校通讯处”。随着中国沦陷区范围扩大,又将该机构改组为“战区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通讯处”,专门办理战区教职员战时服务事宜。对于战区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部又专设“战区来京学生登记处”,根据学生意愿帮助其返家、借读于他校或参加战时服务。
1939 年5 月,教育部战区教育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指导战区失学青年继续教育工作。沦陷区被划分为70 个区,每区设督导员、干事、书记等职。督导员的工作内容有:组织各校教育人员和爱国青年联络当地抗战团体,按其特长秘密分派、开展工作,协助组织破坏、打击汉奸工作,搜集抗战情报。并具体规定督导员的任务要求:进入乡村,根据各地教育资源和实际需要设立私塾;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改革课程体系,宣传抗战爱国教育,使民众坚定抗战必胜决心;设法安置沦陷区流亡学生,使他们能继续接受教育。为掩护督导员工作,国民政府教育部鼓励民间发展和创立任何有利于抗战的组织,以广泛组织战区青年投身教育活动。1940 年3 月1 日,教育部在重庆成立“战地失学失业青年招致训练委员会”,该组织承担谋划并指导战区各项教育工作的职责。
战时教育的各组织机构和人员,具有隐蔽性、多元性的特点。他们利用各自身份开展教育工作,拓宽生存空间,壮大局部力量,为抗战时期维持各级各类教育,宣传抗战御侮思想,抵制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文化侵略做出应有贡献。
(二)改良私塾教育
抗战时期,尽管国民政府制定各种政策、建立各种组织机构维持教育正常运转,但迫于战争压力,沦陷区各级学校遭受敌军烧杀抢掠,教育场所、设施、师资、经费无法满足沦陷区师生教育需要。而私塾办学较少受时间、地点、场所限制,学额不定,受众较广。为提高教育普及效率,国民政府采取借助改良后私塾力量作为基础教育补充的策略。为此,1937 年6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出台《改良私塾办法》,对私塾设学的质量、环境、条件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由于提高私塾教育质量的关键在于塾师,因此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加强私塾师资力量。1938 年5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确定师范教育设施方案》,对师资标准、师范学校建设、小学教员任用等做出工作部署,那些经考核或鉴别不合格的私塾教师须经严格培训考试,才能续聘上岗任教。旨在藉此提高塾师专业素质,提升教学水平。1939 年3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审议教育家王星拱《酌用改良私塾制以增进教育普及效率案》,准予酌情采用实施。上述政策的施行,使得各地私塾教育得以发展,并根据形势变化在学校管理、课程设置及教学方式等方面做出适当调整。
为了保障私塾办学的开展及提升改良水平,教育部明确由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主管私塾改良,分级设计督促管理以及负责各项具体改良事宜。各地纷纷响应,将所在县市划分为若干学区,各学区成立管理私塾的基层组织机构,负责制定计划、组织辅助、审查塾师资格、议定私塾教科书以及根据私塾办学情况进行奖惩及取缔。在此基础上,又选定巡回私塾辅导员对各地私塾教育设施、教学工作等进行指导。各省市对私塾的管理亦十分严格,教育部奖励私塾办学较优者可酌情改为短期小学、简易小学或初级小学。那些不遵守规制,办学不力,塾师品行不正,塾舍不达标的私塾,将受到警告、处分,甚至依法加以取缔。
国民政府教育部参照小学课程标准和课时安排对私塾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也有诸多改良,力图改变传统私塾以“四书”“五经”为主体的课程体系。教学方法方面更注重启发诱导,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不允许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上述《改良私塾办法》规定,私塾课程分为基本课程和补充课程两种,基本课程为:一、国语(包括读文、作文、写字);二、常识(包括社会、自然、卫生);三、算术(包括珠算与笔算);四、体育。补充课程,得依地方需要,由塾师自定之。[2]679
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按照规定,结合各地实际需要,制定带有各地特色的教学要求、计划,尤其是课程表,交由私塾具体实施,各项基本课程应使用教育部审定或编辑教材。如《江苏省管理私塾实施办法》规定:私塾考虑自身状况,相当于初级小学、简易小学和短期小学的学阶和程度,应对应国家办学制度设置课程。如“相当于简易小学者,须依照本省《简易初级小学课程暂行标准》之规定——为党义、国语、算术、常识四科。相当于短期小学者,须依照部颁《短期义务教育实施办法大纲》之规定——为国语一科,其内容须包含史地、公民、算术、自然等常识。”[3]129
上述可见,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良私塾的初衷和目标都是通过改良使其与学制中小学阶段教育章程相一致,或朝此目标前行及过渡,以实现私塾这种传统教育类型被国家所实行的新教育体制所容纳。
中国近现代教育历史表明:改良后的私塾教育组织方式更加多样化,注重丰富学生认知,采用多元化方式教学,带领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如江苏省上述办法规定:城镇私塾应筹设儿童游乐场、劳作所、公共理科教室及艺术教室,或充分利用民众教育馆、图书馆、体育场、公园、农事试验场、商品陈列所、消费合作社等为辅助之教育机关。乡村私塾须筹设自然、体育、音乐等科之巡回教师。[3]129-130从中,可大略窥知私塾办学已具有现代新教育组织、方法的意味。
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私塾的积极政策使私塾教育的改良及转型成为潮流,促成战时教育出现短暂繁荣。应该说,此举为收容战区学生,抵制奴化教育,及维系后方的正常教育教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历史地分析,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良私塾的政策成效虽然因战乱纷扰、各地面临的现实矛盾以及守旧势力的排斥心理而大打折扣,但对旧私塾采取非禁止而加以改良提高的举措,对于抗战时期教育的延续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
(三)推行战时学校贷金制及公费制
国民政府推行的战时学校贷金制及公费制主要是为了保障大后方新建或组建中等及以上学校的学生求学条件而设立的。这就有必要先追述相关的学校设立状况。
为收容沦陷区流亡后方的学校师生,国民政府在后方的安全地区建立了国立学校,将厦门大学、东北大学等部分私立大学改为国立。到1945 年9 月,抗日战争胜利时,共创建国立中学34 所,国立大专院校附中16 所,国立师范院校和职业学校14 所。[4]471国立学校的创建,满足了流亡青年的求学愿望,也在战争中延续了中国教育的生命。
随着来自战区学生的不断增加,国立中学的数量也逐年递增。为解决国立中学生的经济困难,1940 年1 月,国民政府颁布《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国立中学学生贷金分为膳食贷金、特别贷金、零用贷金三种。贷金制推行后,无论是中学还是大学,凡是战区家庭经济来源断绝者,皆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政府补助的数目是自费生缴纳数目的数倍以上。此举使得沦陷区青年继续求学的困难得以缓解,越来越多的青年基于爱国热情和后方求学的安稳,纷纷冲破敌人封锁,辗转到后方来求学。
随着战事扩大,流亡学生也日益增多,大多数流落后方学生都等待着政府救济,原有贷金制办法不尽适用,给管理带来诸多问题。为了便于经费管理和提高救济效率,国民政府把贷金制改为公费制。1943 年8 月,行政院颁布《非常时期国立中等以上学校及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规定公费生办法》,规定分甲、乙两种公费,前者学膳费全免,后者仅免膳费。为鼓励学生从事抗战形势下急迫工作的人才需要,根据抗战实际状况与专业特点分配公费生名额。其中师范、医、药科系学生均为甲种公费生,其他院系酌情分配乙种公费生名额。各院系除公费名额外,若有来自沦陷区,家境贫寒而成绩、操行皆为优良者,按规定给予奖学金。而对于操行不良、成绩不合格者,停止其公费待遇。
公费生虽受国家救济,但国家各项事业需要专业人才支持时,亦可予以征调。抗战期间,不少具有一腔热血、视死如归的青年学子参军或进入军校学习,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战时服务。公费制的施行具有扩大学生规模、调节毕业生专业结构、保障教育公平、增进战争人才供给的重要意义。
二、实施高校内迁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侵略扩张加剧,高校所在地相继沦陷。国民政府为统筹、规划高校内迁相关工作,1937 年8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检发《战区内学校处置办法》的密令,要求各省市教育厅局如其主管区域辖有战区,应斟酌情形分别为下列之措置:1.于其辖境内或辖境外比较安全之地区,择定若干原有学校,即速尽量扩充或布置简单临时校舍,以为必要时收容战区学生授课之用,不得延误。2.受外敌轻微袭击时仍应力持镇定,维持课务,必要时得为短期休课。3.于战事发生或迫近事,量予迁移。其方式得以各校为单位,或混合各校各年级学生统筹支配暂时归并,或暂时附设于他校。4.暂时停闭。[5]2-31938 年2 月,国民政府还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具体负责高校迁建工作。
(一)高校内迁的背景
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军的炮火和铁蹄之下,战区和沦陷区教育组织机构遍体鳞伤。据记载,1937年7 月30 日,日军将南开大学图书馆炸毁,数百名日军侵略者进入大学校园横行,烧毁学生和教职工宿舍及主要标志性建筑,大量宝贵文献也未能幸免,被日军抢掠一空;1937 年8 月25 日,日本宪兵强行进驻北京大学,并进行搜查。此外,对其他各地方高校的侵略和破坏也是不胜枚举。据统计,到1939 年4 月,日本侵华战争已对我国92 所公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造成巨大损失:死伤108人,财产损失65367409 元法币。[6]371可以说,侵略战争对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打击甚为惨烈。为保留高等教育的火种,国民政府把高等学校内迁作为一项重振教育的应对举措。
1937 年9 月29 日,教育部颁发《战事发生前后教育部对各级学校之措置总说明》,规定战时安全地区各校预定收容沦陷区学生措施、沦陷区各校防御措施、订购与运输教科书计划等。这些规程为高等院校内迁提供了政策依据和社会保障。
(二)高校内迁的状况
平津各高校首先拉开了高校内迁的序幕。高校内迁的方向可以分为以下几种:首先,华北地区高校主要向西、向南两个方向迁移。典型的如北大、清华及南开三校合并成西南联大,经湖南衡阳,最后迁往云南昆明办学,创造战时高等教育的辉煌。其次,长江下游地区的高校主要向西南方向迁移。如浙江大学先迁江南北泰和县,最后迁至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办学,被誉为“东方的剑桥”。再次,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地区的高校迁移较为分散,主要分布在香港,广东北部和广西山区县市。最后,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高校主要向西迁至鄂西、川东山区以及重庆、四川内陆腹地。一些高校在仓促组织迁移中,因校舍遭日军占领或轰炸,许多师生遭到迫害或解散。
在持续进行大规模的高校内迁中,部分受损严重、师生大量流失、经费严重短缺的高校被迫停办或重组。如国立山东大学,青岛沦陷时日寇将山东大学校舍据为己有,设为兵营。学校先迁往川东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后又溯长江而至重庆,因迁徙过程中师生大量流失、图书设备损坏严重,遂被教育部下令停办。山西省立川至医学专科学校因日寇侵犯山西,由太原南迁至临汾,后临汾失陷,学校遭受严重损失,难以为继,遂并入山西大学医学院。
抗战之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平衡,专科以上高等院校大多设在东部沿江沿海等经济文化相对繁荣地区,而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缓慢。藉此高校内迁,既是高等教育劫难下的自救又是教育地理图谱的重新描绘。国民政府对于高等教育布局作适当调整,弥补西北、西南地区高等教育短板。因高校大量迁移至西部云南、贵州、陕西、甘肃、四川等地,西部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大为改观,较之战前有明显改善。据统计,作为大后方中心地带的西南地区,抗战时期一共接待了内迁院校61 所,其中有大学22 所,独立学院17 所,专科学校22 所。后方广袤的西北地区,先后有11 所内迁院校在此落脚或安家,含大学5 所,独立学院5 所,专科学校1 所。[7]71-72高校内迁在弘扬民族团结和共同御侮精神的同时,也为西部各地带去丰富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促成了战时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
(三)高校内迁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内迁院校在人才培养、专业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方面独具特色。内迁高校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学科建设以抗战救国和满足抗战时期生产生活实际需要为宗旨。各校在教学中秉承通才教育理念,文理并重,基础理论与应用开发相辅相成,学术思想和专业知识融会贯通。这种设计方案下培养出来的学生能很快适应抗战时期社会的不同需要,在战时环境下也能弹性就业,很快找到就业出路。1940 年,同济大学工学院出于抗战育人的需要,成立机械系和机电系,将原来的机电系一分为二,还在机械系内设立了造船组。内迁院校师生将学科专业知识运用于开发西南、西北后方省份资源。如浙江大学在遵义期间,史地系师生在野外考察时发现了团溪锰矿,工学院化验标本后认为等次很高,便由土木系测定矿区地形图,向资源委员会报告。农学院卢守耕对水稻育种和胡麻杂交进行实验探索,蔡邦华对西南地区马铃薯蛀虫、蝗虫开展研究等等,都是将学科发展与战时工农业建设紧密结合的典范。[8]32-40内迁院校在西部民族问题、社会学问题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内迁云南大理的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进行西南边疆文献的搜索和整理,对少数民族的社会和语言进行调查,经济商业系还对大理喜洲的物价指数、家庭消费、土地问题等进行了调研。
高校内迁是在抗战时期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抗战斗志,大大激发了内迁院校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坚定了他们同仇敌忾、与敌人抗争到底的决心。高校内迁保存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根脉和精华,给后方带来了一批新教育资源,使得中西部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得以改善。可以说,高校内迁具有深刻的拯救民族危亡,延续民族教育命脉的伟大意义。
三、设计各级各类学校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迫于各种压力对战时教育体系进行了必要调整。由于种种举措均是在战争条件下发生的,故而有针对日伪殖民主义教育侵略而采取应对性变动的一面。
(一)初等教育
日本侵华期间,中国的初等教育受到严重破坏。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37 年抗战爆发后,小学减少9 万多所,学生减少550 多万人。[9]135基于此种局面,国民政府对初等教育采取了相应的战时教育政策应对。
为维系初等教育,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各地广泛设立小学,普及国民教育,推进义务教育实施。1938 年5 月,颁发《各级学校兼办社会教育办法》,同年8 月又训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大量添设民众学校,发动知识分子充任教师,对失学民众需要时可实行强迫教育。学习可缩短为两个月,集中施行识字教育及公民教育,加授自卫训练、防空防毒常识,妇女加授看护及急救常识。学校一切设施应注意发扬民族意识及培养爱国思想”。[10]391之后,又向云南、贵州、四川、甘肃、江西、陕西、浙江、广东、武汉、重庆等省市陆续发出《战时民众补习教育实施要点》,具体落实各地区民众补习教育实施的各项事宜。上述教育规程受到所在省市的地方响应。1940 年12 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通过了《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规定:“8 至16 岁儿童,不分男女,均须受小学教育。每村建小学一所(不满50 户的村庄可与邻村合建),每乡建中心小学一处,每区建完小一处。小学修业期限,为适应战争环境暂定为二、三、二制,即分为初、中、高3 级,每级修业2 年。”[10]456同时,将义务教育与民众教育合流,推进战时失学民众补习教育。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添设小学,扩充学额和师资,改进学校教育设施和课程设置的同时,又要求各小学均应增设儿童义务随习班,以帮助无力入学儿童之教育。甚至设计小学在校生带邻里失学儿童在一星期规定时间上学,由在校生作导生,协调辅导。1938 年12 月10 日,教育部公布《小学增设儿童义务随习班办法》规定:“学校应督导在校学生各率邻里儿童入班授课,每星期三、六下午或星期日上午到校学习,其余时间在家自习,每日以二小时为度。原校学生作导生,指导作业,既改善邻里关系,又收教学相长之功。”[9]404
在实施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国民政府重视对儿童的训育工作。1938 年3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训育委员会”,旨在“培养公民道德,指导和考核训育实施,厘定礼制,培养训导人员,督导军事管理及童子军管理,指导学生自治团体”[5]75。该委员会设参事、秘书及督学等职,具体负责各项工作。1941 年10 月,教育部又公布《小学训育标准》,根据抗战建国需要,试图发扬中华民族的固有道德及民族精神,以培养尊崇三民主义的“健全”公民。[6]219国民政府对小学儿童训育格外关注,试图造就顺从现任政府和循规蹈矩性格的国民。但同时,确也多少反映了抗战教育的部分内容。
(二)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是培养具有较高知识能力水平的国民、小学师资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关键教育阶段。在各级教育中,中等教育组织结构及功能类型均最为复杂,主要包括普通中学、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三类。
1.普通中学
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学校师生风涌而至大后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为缓解教育困境,在大后方设立国立中学。国立中学创办之缘由在于收容来自沦陷区的失学学生,并使教师组织教学,培养造就他们。1937 年12 月起,教育部先后在河南淅川、贵州铜仁、重庆北碚嘉陵江三峡峡防局(今重庆市北碚区)等地设立河南、贵州及四川临时中学,均以“国立”命名,促成华中和华南各地部分流亡师生入校开展教育活动,“弦歌之音”不绝。1938 年4 月,学校易名,取消“临时”一词,改为国立中学。1939 年2 月27 日,《国立中学暂行规程》出台,规定国立中学名称按成立时间次序编排,即国立第一中学、国立第二中学,等等。为了考虑学生毕业后出路问题,学校内设师范部与职业部,让一部分内迁学生肄业师范教育或职业教育。[6]940国立中学的创办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抗战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来自沦陷区的失学青年提供了更多就学机会,也使后方中等教育呈现出新气象。
为了调整中学课程,以适应抗战特殊形势,1938 年2 月25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国立中学课程纲要》,规定国立中学训练学生精神、体格、学科、生产劳动及特殊教学与战时后方服务。这些课程的设计安排,注重训练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同时也兼顾了抗战时期社会部门的应急需要。精神训练在日常教育中让学生认识与学习抗战建国的重任;体格训练用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初中实施童子军训练,高中实施军事训练,注重学生目力、足力、臂力之锻炼,强化学生体格;学科训练,为适应战时需要,教学科目与时数应作适当调整。初中教学课程包括公民、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英文、音乐、图画。高中教学科目包括公民、国文、算术、英文、历史、地理及地质、物理、化学、生物。除了这些规定的课程外,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尽量补充与国防生产有关的教材”,各科教学的重点均需“极合乎中国的社会需要和战时需要”;生产劳动训练,各中学各科各年级学生都应接受生产劳动训练,平均每日劳动时间不少于1 小时;特殊教育与战时后方服务训练,依照教育部先前制定的《中等学校特种教育纲要》训练学生的特殊能力。[10]384-385
此外,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对完成中等学校学业,但未能报考或未被高校录取的毕业生实施教育过渡及救济,设立免费专修科和先修班,并为经济困难者提供食宿。专修科修业两年,先修班修业半年,授以大学预备教育,成绩优良者,可免试统一安排或选入大学一年级。国民政府教育部为中学及大学教育过渡而采取的应急措施为战地失学青年提供了延续教育求学的机会。
上述关于中学阶段的教育政策方略是有积极意义的。国立中学的创办以及其他教育组织方式的设计,收容和救济了大批流亡学生。其间相关课程调整凸显了培养抗战人才和满足生产生活需要的特点,以爱国教育为主线,宣传民族意识,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抗战力量,为抗战胜利输送了文化教育或专业技术的有生力量。
2.中等师范学校
早在1932 年2 月17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就制定《师范学校法》明确中等师范学校要独立办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又颁布一系列条例谋求推进师范教育发展。1938 年4 月,《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提出要注重师资培养,拟定方案,保证能壮大师资力量。
出于战时初等教育办学对师资力量要求加大,需要加强中等师范教育。从1940 年开始,国民政府教育部比照国立中学模式,陆续在后方设立了14 所国立师范学校。为减少设中学教育经费的大量投入,提高办学效率,设计国立师范学校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原国立中学的师范部独立而成或国立中学整体改为师范学校;二、收编地方省立或私立师范学校;三、增设新学校。与此同时,为扩大师范教育培养规模,还规定在师范学校或公立中学及公立初级中学内附设特别师范科和简易师范科,两科修业均为一年,所用教材重新组织编写修订,以缩短学校休假期限,毕业学生应补充为国民学校教员,以增强后方中小学的教师队伍。
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对师范学校课程进行了改革,师范学校学科建设体现了普通师范教育向乡村的延伸以及适应抗战需要的特点。1940 年3 月,教育部对原《师范学校法》中计划的课程进行修订,规定在原来基础师范教育课程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经济及合作、社会教育、地方行政及地方建设等科目。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为毕业生服务乡村建设、普及乡村义务教育打下基础。同时,为服务抗战需求,还对童子军、音乐、美术等课程进行调整。如培养童子军师资的课程有教育法、童子军教育概论、童子军行政及组织、童子军三级训练、童子军专科、童子军野外生活、实习。[11]140以增强学生身体素质,锻炼强健体魄,培养爱国情感。1941 年12 月,教育部训令应尽先扩充,积极改进师范教育。随后,组织、召集教育专家陆续制订《推进师范教育原则》《推进师范教育工作要项》等规程,要求各省拟定推进师范教育的方案,拓展师范教育区域分布,提高教师素质,注意专业技能训练,并设法充实设备等。
通过上述措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师范学校快速发展。据统计,1936 年全国共有师范生人数76445 人,1937 年因战事影响,降为48793 人,在国民政府积极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师范生数量自1938 年以后已逐年增加,1938 年增加至56679 人,1939 年59431 人,1940 年67551 人,1941 年约85000 人,1942 年约100000 人,到1945 年已经达到202163 人。[5]644-646抗战后方师范学校数量的骤增以及上述课程设置改革,既扩大了师范教育规模,同时又提高了师范生素质。这都十分有利于抗战时期初等义务教育的部分普及以及国民教育的推广,为抗战提供师资支持。
3.职业学校
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传授必要的职业知识及技能,使学生通过学习与锻炼获得从事该职业所需的能力及素质,从而为社会培养实际的专业技术人才。职业教育的核心办学机构及制度主体就是职业学校。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0 年4 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上提出:在加强普通中学的思想教育及技能培训外,还应当重视职业教育;在合理调整普通中学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同时,优先发展职业教育;在促进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行政干预。[6]10241932 年12 月7日,《职业学校法》出台,规定各职业学校应当分初等、中等和高等不同类型独立设立,中等职业教育及职业学校数量最多,中等职业学校与中等师范学校平级,课程除了国家统一外,学校也有开发及调整的余地。
抗战爆发后,为培养职业技术人员,满足民众生产与生活需要,受黄炎培大职业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国民政府教育部将职业教育重心转向乡村。1938 年7 月,颁布《创设县市初级实用职业学校实施办法》规定:各地应根据实际需要酌情办理职业学校,学校设置农艺科、生产制造科、蓄殖科、纺织科、应用化学科、木工科、机工科、土木科、印刷科等。这些分科专业先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陕西、甘肃等省市择县试行。1938 年12 月,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增设职业科办法》,提出“增设国立中学职业科,用于培养国立中学生的一技之长,使其毕业后能够更快从事生产活动和国防建设,各校收容之职业科学生,应与本校学生实行职业指导。”[1]652国立中学附设职业科是中学教育改革试验的有益尝试,不仅具有学制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教育资源的有效挖掘,培养战时急需的地方初中级实用技术人才。
为了满足偏远地区生产和物质供给,国民政府教育部先后在边疆创办了国立宁夏、青海、拉卜楞、松潘、西康、金江、清溪7 所职业学校。并在办理各类职业学校时,注重将师范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如教育部于1941 年6 月颁发《边远区域师范学校暂行办法》规定,边疆师范学校的中心工作包括:“1.提倡合作事业;2.改良农业、兴修水利、提倡造林与垦荒;3.指导农林产品的加工与副产品的利用;4.改良畜牧及其产品的利用。”[12]411在此“暂行办法”的导向下,各师范学校积极发展生产,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职业教育与师范教育的界限,带有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融合、流动的特色,从而产生更好的教育服务社会成效。此外,教育部曾多次督促大后方,通过举办技术人员训练班的方式加强初、中等职业教育的力量。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发展中等职业教育政策的有效制定和推行,使全国职业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1937年全国职业学校为292 所,到1945 年,全国职业学校数量增加至576 所。[13]562职业教育的增长有利于战时大后方恢复生产和社会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满足民众生产生活现实需要。
(三)高等教育
1912 年1 月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至1937 年7 月7 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逐渐形成,各类大学、独立学院的设立、建设及运行步入正轨。截至1937 年7 月,共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 所,大学42 所,独立学院34 所,专科学校32 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将战区高校迁往内地,进行改组和扩充,以减少敌伪对高等教育的破坏,保存高等教育实力。
面对学校内迁中师资大量流失,中等学校师资严重匮乏的困境,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一系列方案,推进高等师范教育发展。1938 年7 月,国民参政会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各级教育实施方案》,规定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学区,设师范学院培养教员,以满足中学教育师资要求。1938 年8 月10 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师范学院规程》。1942 年8 月,又公布了《修正师范学院规程》,规定师范学院以“养成中等学校之健全师资”为目的,由国家根据各地情形单独设置或附设于大学内。师范学院学生修业年限为5 年,专修科3 年,一律免收学膳费。[10]397另外,还对师范学院组织及课程、学生训导、学生毕业服务、师资审查和导师制等提出要求,大学各级教员任职资格和薪资待遇等作详细规定。
为规范大学招考办法,调节招生计划,改变各高校招生各自为政的状况,国民政府决定实行统一招生制度。1939 年6 月,统一招生委员会正式成立,管理相关招生事宜。考试科目、时间、试题发放全部由教育部统一规定,学生录取及通知书分发按照教育部的规定办理。高校统一招生以及相对统一的测试标准提升了考试的公平性和平等性,对同等学力报考者的严加限制提高了新生的生源质量。统考还可以大大减少招生院校在财力、物力及应考考生在时间和精力上的损耗。1940 年全国高校招考区总计16 大区及18 分区,考生18151 人,录取7204 人,录取率为38.7%,比以往的比例有所上升。高考中所招收的理、工、医、农类学生,在大学深造培养以后,成长为专业人才,大大缓解了战时科技和工程技术人才短缺的状况,有利于大后方经济的开发和坚持抗战的胜利。
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公布了一系列调整高等教育的规程,如1939 年5 月16 日,颁布《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独立学院及专科学校行政组织补充要点》,6 月21 日公布《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办法大纲》,6 月23 日订定《专科以上学校实施战时教程》《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1941年9 月29 日,颁发《政府机关委托大学教授从事研究办法大纲》。1943 年10 月30 日,颁布《国立专科以上学校教员支给学术研究补助费暂行办法》。上述规程内容包括:整顿、裁并内迁高校,调整大学办学目标,课程教学向战时服务靠拢,强化大学组织机构建设,鼓励高校学术研究和提高研究人员待遇等诸多方面。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高教政策战时调整,有助于恢复或稳定大学办学效益,使高等教育在战时得以延续,而且高校数量亦有所扩充。据统计,至1946 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82 所,其中大学53 所,独立学院62 所,专科学校67 所,总计较战前增加70%。虽然这些举措不乏刺激应对的滞后及被动,其实施效果也不尽如人意,但对抗战时期我国高等教育的拓展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四、加强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
边疆教育属区域教育专门领域,华侨教育更是国内教育与海外侨民教育的交错与过渡形态。这在历史常态下不属教育热点问题,但在抗战背景下,却有特定的抗战教育意义,因此受到格外注重。
(一)边疆教育
抗战前,国民政府对边疆教育已有关注和涉及。1928 年7 月11 日,国民政府设立中央治边部门——蒙藏委员会,主要掌管蒙藏行政事务与各种兴革事项。1930 年2 月,教育部设蒙藏教育司,负责蒙藏和其他边疆地区兴办教育的各项事宜。1934 年,教育部划拨教育经费以资助建立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教育机构,并电令各省根据各地教育实况草拟发展计划,以核准经费划拨。1936 年7 月,教育部颁布的《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教育计划指令》中指明,优先培养绥远、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康、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区的师资力量,对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与留学生教育等方面均有涉及。具体而言,初等教育方面,在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甘肃省等12 个地区增设小学,由地方政府进行统筹、拨金补助。中等教育方面,补助归化土默特特别旗旗立中学经常费,使其扩充;补助青海回教促进会附设中学经常费,使其扩充,改为省立。社会教育方面,由本部出资在各地装设无线电收音机11 架;各喇嘛寺庙筹设民众学校6 所;补助蒙古文化馆1 所。国内留学补助费方面,设置蒙藏回苗留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公费名额15 名。[2]883-888上述表明,抗战前在国民政府的关注和经费支持下边疆教育已有初步发展,但国民政府本身重视程度不够、经费补助不足以及边疆地区自然环境恶劣、教育基础差、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使得抗战前边疆教育发展十分缓慢。
抗战爆发后,为加强国防,维护边地安定,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倡导下,国民政府开展一系列边疆教育的实际工作。包括政策组织、经费补助、师范教育、职业教育等方面。
1939 年5 月,教育部颁布《蒙旗教育暂行实施办法》,提出要加强沦陷区师生的登记、救济和安置工作;战区之各级各类学校,应采用灵活办法维持教学,以满足抗战人才需求;后方应积极发展师范教育,培养中小学教员。1940 年5 月8 日,教育部组织设立边疆教育委员会,统筹规划边教工作,调整教育设施,促进边地青年升学及就业。1943 年,又根据边疆各省区教育实况,颁布《各边省办理边教三年计划》(1944-1946 年),酌令绥远、宁夏、青海、甘肃、西康、四川、云南七省按计划实施。此外,教育部也仿效内地在边疆划分督导区,设立督导员和通讯员,以便加强教育督导考核和联络通讯之便。1944 年6 月2 日,教育部公布《边疆学生待遇办法》规定:“家住蒙古、西藏及其他语言文化具有特殊性质地方的学生,均得享受保送升学、申请公费及常年补助等优待”。[10]531
教育经费是办学的重要支撑,1935 年起边疆教育经费即被列为专款,抗战以后逐年增加。包括以下四类:1.边远省份教育文化补助费。1935 至1945 年间,共拨款112795788;2.边疆教育事业费,包括边疆教育行政,建筑设备、研究考察、奖励、救济、编印课本等。1935 至1945 年期间,共拨事业费303643429 元;3.教育部办边疆学校经费,包括学校经常费、学生补助费、学生公费、临时费等。1935 至1945 年期间,共拨3602106841 元;4.特拨经费及其他补助费,包括西北建设专款、改善员生生活专款、复员费、冬季煤炭费、蒙藏青年训练费等。1935 至1945 年期间,共拨18050692元。[1]217-218上述经费补助涉及办学、教学及管理的各个方面,成为推进边疆教育的物质基础,在抗战时期边疆教育事业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
自清末民初以来,边疆教育起步晚、发展缓慢。限制因素很多,除了经费短缺之外,师资也是一大难题。为培养边疆学校中小学教师,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边疆创办了国立西南、贵州、西宁、康定、西北、大理、肃州、绥宁、丽江、巴安、成达、陇东12 所师范学校。同时,为了吸引青年入边从教,教育部十分重视提高教师待遇。1944 年7 月3 日,教育部颁布《边地国立各级学校教员奖助金办法》要求提高教师薪金,按照级别划分申领奖助金,服务期限满4 年者可享受公费进修。国民政府提高教师待遇和培养师资的一系列举措,大大提高了边教人员的物质生活水平,使他们安心从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矛盾。
边疆教育在社会各界热心教育人士的积极推动下,战时取得了巨大进步。据1944 年统计数据,新疆有公立会立民众学校1006 所,学生154396 名,专科以上学校2 所,中学6 所,职业学校9 所。西藏有小学3 所,另有拉萨仲科子弟学校1 所。西康省边民分康族和夷族两大部分。康族分布在康属各县局,夷族分布在宁属各县局及雅属各县局。西康省境内由地方办理的学校分康属、宁属、雅属。西康省境有小学3 所,实验中心学校1 所,由地方办理的康宁两属学校、省县立总共约有70 所。青海省有小学57 所。安远现有蒙旗小学38 所。宁夏现有简易师范附小1 所,小学11 所。战时边疆教育的发展不仅使祖国边陲地区的儿童和青少年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使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边疆各民族文化水平,而且有利于全民抗战,加强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
(二)华侨教育
1941 年12 月7 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反日战区范围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华侨学校被迫停办或关闭,华侨学生流离失所,亟待救济。
面对从沦陷区回国的大量侨生,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9 年7 月成立回国升学侨生接待所,具体负责回国侨生的复学教育工作。随着归国侨生队伍的扩大,1943 年接待所更名为回国升学华侨学生管理委员会。国民政府教育部十分重视华侨教育,曾发布相关规程支持其发展并取得一定成效。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凡在国内学校就学的回国侨生,因资金问题生活困难者,可申领救济金和膳食贷金,救济金共分为四类:特种救济金、寒衣补助费、医药救济金和临时救济费。自1942 年至1945 年秋,共发8 次特种救济金68347000 元,领得特种救济金的各级各类华侨学生14286 人;自1943 年冬至1944年冬,共发寒衣补助费128000 元,领得寒衣补助的侨生256 人;1945 年改为发贷金与实物两种,计领得贷金和实物的侨生119 人;1942 至1945 年,共发医药救济金481142 元;1945 年前计发临时救济金130 余万元。[6]1269此外,对于沦陷区因经费问题无力回国的流亡师生,国民政府还向他们拨发专款资助其回国返乡,1942 至1943 年,此项救济金共核发50 多万元。
除组织华侨教育专门管理机构及实施教育经济救助之外,国民政府教育部专设华侨中学,并在部分高校和中学中设先修班和侨生班,便于回国侨生升学和继续接受教育,并给予侨生以升学和就业优惠政策。1940 年,颁布《推进侨民教育方案》,决定增设华侨学校。从1940 年起,先后在云南保山、四川綦江和广东乐昌设立3 所华侨中学,收容侨生1000 多人。这些学校的设立既是政府在抗战期间变革中等教育体制的必然结果,也是重视华侨教育的体现,同时还为抗日战争增加了有生力量。此外,国民政府教育部还在国立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等高校设立先修班,便于回国侨生就学。凡成绩优异,品行良好,有志于学的侨生可申请保送名额到相关高等院校学习。仅1942和1943 年两个学年度,经侨务委员会保送由教育部分配到各高等学校入学的学生达1300 多人。[6]1270侨生就业亦有相关优惠政策的保障,如1940 年制定《考选清贫华侨回国升学规程》规定,每年从海外侨生中选取清贫者数人,公费资助其归国进入高校就学,毕业后安排从事侨务工作。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注意华侨教育,给予侨生升学、就业方面诸多便利,也照顾资助其生活,促进了战时华侨教育的发展,从而增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提高广大侨民对祖国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许多华侨在国外创业谋生的同时,还心系祖国抗日御侮,创办华侨学校,传播民族观念与文化,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综上所述,在社会各方政治势力及抗战民众力量的压力下,国民政府教育部组织教育部门及学校师生根据战时教育特殊形势及问题,调整及制定教育政策或规程,应对教育上的新挑战及问题。与敌伪展开争夺沦陷区教育权的斗争,抵制日伪的奴化教育,增强了师生民族认同感;组织高校内迁,保留了高等教育的元气,也促进了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协调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构建战时教育体系,适应国家“抗战”与“建国”的双重需要;重视边疆教育与华侨教育,加强民族团结,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事业。国民政府的一系列战时教育政策不仅严重打击了日伪奴化教育,为抗战胜利提供部分有效人力资源,而且有助于在民族矛盾上升、亡国灭种危机逼近的历史背景下,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延续教育生命,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事业的秩序稳定和教育活动“弦歌之音”不绝,为战后教育复原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