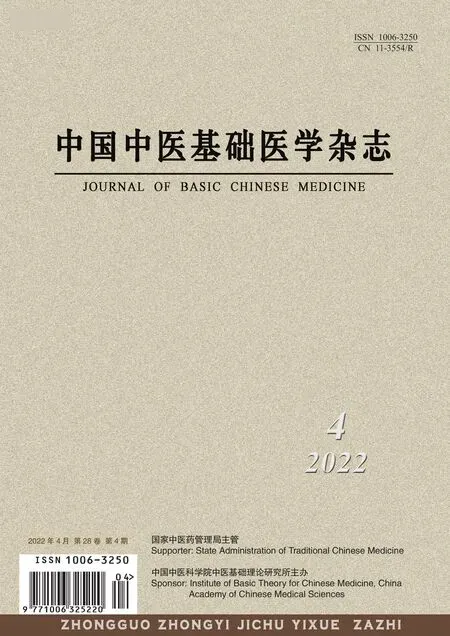湿疫治则治法探析*
吴佳琳,许华冲,陈孝银
(暨南大学中医学院,广州 510632)
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的变革、朝代的更迭,常常伴随着疫病的流行,中医药在抗疫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说文解字》:“疫,民皆疾也。[1]”《中医疫病学》将疫病定义为一类传染性极强、可造成大面积流行、起病急、危害大,无论性别和年龄其临床表现相似疾病的总称[2]。疫病属于中医学“温病”范畴,相当于西医的急性传染病。
1 湿疫考辨
湿疫是由感受湿性疫邪而引起的一类疫病,在中医文献中多以“湿温”称,历代医家对于湿疫有一定的认识。
战国时期的《难经·五十八难》中便有“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3],此为湿温病名的最早记载,即感受湿热病邪引起的温病,因疫病归属于温病,所以湿温应是涵盖“湿疫”在内。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南越列传》中提到“隆虑离湿疫,佗得以益骄”[4],这是湿疫病名的最早记载。宋·陈言首次论述湿疫的病因,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料简诸疫证治》中写道:“秋合清,而反淫雨,冬必病湿疫”[5],其指出气候异常是导致湿疫发生的原因。元·危亦林在《世医得效方·卷一》中对湿疫的症状进行描述提到“乍寒乍热,损肺伤气,暴嗽呕逆,或体热发斑,喘咳引气,名曰湿疫”[6]。明代医家吴又可所著《温疫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温疫病专著,也是我国第一部论述湿邪致疫的专著。书中认为温疫可夹杂其他邪气而为病,如“又有风温、湿温,即温病挟外感之兼证,名各不同,究其病则一”[7]242,提及湿温即湿疫。清代医家姚球在《伤寒经解》中记载:“感湿而病,名湿温。温,同瘟,以湿症传染,有似瘟疫也。[8]”可知湿疫是感受湿邪而发,湿中蕴热,湿遏热伏,其临床特点不能脱离湿热范畴[9,10]。
疫毒是四时气候失常所产生的邪气,而湿即为疫毒滋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清代医家林珮琴在《类证治裁》中言:“疠邪之来,皆从湿土郁蒸而发”[11],张石顽亦有相同的论述[12]。湿邪乃六淫之一,致使机体感染病毒等微生物后,不能及时有效地识别而进一步启动机体的免疫应答机制,从而不能将病原微生物驱逐出体外,这是直接的病因所在[13]。湿不仅能为疫毒提供存活和滋生的环境,还能阻滞气机,致使脾胃气机升降功能失调,继而导致机体免疫失衡,清除疫毒的能力下降而促进其传播,加重症状,延长病程[14,15]。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上焦篇》提到:“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16]”温疫多夹湿,若湿秽浊之邪积重则成戾气,又极具传染性,从而形成疫病流行。湿为浊之渐,浊为湿之极。湿浊久积必成秽浊,形成时疫[17,18]。
由此可知,湿邪过盛则化为六淫,又恰逢时行戾气,二者合而为患侵害人体,疫病乃起。湿与疫毒互结是湿疫发病的中心环节,因湿致疫故名湿疫。
2 湿疫的病因病机
2.1 湿疫的病因
湿疫属于中医学“疫病”范畴,其病因乃“以湿为基本属性的疫疠之气”。湿疫的发生与时间、空间和人密不可分。湿为六淫之一,有内湿和外湿之分。本非雨湿季节却偏逢阴雨连绵,非其时有其气;地处江河湖海纵横交错之区,水域面积大,气候潮湿,地湿上蒸,湿气重着,其境内之民易感外湿之邪;又因久居湿地,若平素饮食不节,恣食生冷肥腻之品,当人体正气不足以抵御外邪时,脾胃受损,气机升降失司,内湿停聚。如若恰逢外湿侵袭人体,内外湿邪相引合而致病。
2.2 湿疫的病机
湿疫的病机为湿疫毒邪侵袭人体,内外湿邪相互感召,疫毒内盛,阻滞气机,闭肺困脾,伤津耗液。在湿疫的病机演变过程中,大多为顺传,即由表入里、由浅及深,按卫、气、营、血依次传变。
薛雪在《湿热论》中提到:“湿热之邪,从表伤者十之一二,由口鼻入者,十之八九。阳明为水谷之海,太阴为湿土之脏,故多阳明太阴受病。[19]24”又因“温邪上受,首先犯肺”,由此可知湿疫之邪自口鼻、肌表而入,多以肺脾胃三脏为病变中心。湿性重浊黏滞,湿与热合如油入面,胶着难解,化热较慢,故湿疫起病较缓,传变较慢,病势缠绵,病邪流连气分时间较长,可分为初期、进展期、危重期和恢复期。
湿疫初期,以邪遏卫分、气分为主要病理变化,亦可邪阻膜原,枢机不利,病在上中二焦,湿重热轻。如《湿热论》中言:“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19]24”肺主一身之气,湿郁于上,壅遏阳气,致使肺失宣肃,升降失常,不能正常布散津液,导致湿聚在肺[20]。湿疫之邪由外入里引动内湿,表现出流连气分,稽留脾胃诸症,阻遏气机宣畅和脾胃升降。正如薛雪所言:“太阴内伤,湿饮停聚,客邪再至,内外相引,故病湿热”[19]25,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胃[21]。湿疫初期湿重于热,湿遏热伏,阻滞气机,蒙上流下,而后湿邪渐化可转变为湿热并重或热重于湿。
湿疫进展期,若中气实、阳气旺则湿从热化,热重于湿,湿疫毒邪顺传至中焦手足阳明经和足太阴经,以脾胃病变为主,邪气可在气分逐渐解除;若中气虚、阳气弱则湿从寒化,湿重于热,病在太阴脾。如薛生白所说:“中气实则病在阳明,中气虚则病在太阴。[19]23”湿热交合,其病重而速。疫毒之邪伤人最速,此期病情传变迅速,逆传手厥阴经深入营分而致重症,进入危重期易危及生命[21]。湿性趋下易伤阴位,湿为阴邪易伤阳气。阴阳两困,气钝血凝,湿热之邪不得外泄,传至下焦足厥阴经和足少阴经,若热重湿轻则邪气化燥伤阴,深入营血,损伤津液,出现气营两燔证;若湿困日久,在疫毒化热过程耗伤人体大量阳气,湿从寒化甚则耗伤肾阳,水湿内停,出现“湿盛阳微”的变证。
若能得到及时妥善的治疗,湿疫进入恢复期,此期邪去正虚,余邪未尽,伤津耗液。因湿邪困脾,致运化失司、化源不足而阴液亏虚;且湿热日久,湿从热化,热为阳邪,灼伤阴液;又因治疗时药物性偏温燥,致阴液亏损[22]。
总之,湿疫的发生发展取决于正气与疫毒之间的博弈结果,因个体禀赋体质而异。湿热相合,热得湿则郁遏不宣,热炽湿横,充斥肆逆,故多变局,一旦发展到逆传心包、横逆肝肾的阶段,则标志着病情进入危重期,预后不佳。
3 湿疫的治则治法
湿疫的治疗遵循“祛邪逐秽,养阴扶正,全程护阳”三大治则,其对应的具体治法主要有“透达膜原,疏利湿浊”“养阴扶正,涤除余湿”“温运脾阳,宣畅气机”。
3.1 首重祛湿,逐秽解毒
湿疫的治疗首重祛湿,因湿邪贯穿本病始终。湿疫是因感受湿性疫邪而引起的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流行性,毒邪伤人最速,因此在治疗上应尽早逐秽解毒,以防毒邪内传加重病情。
明·吴又可在《温疫论·上卷》中写道:“大凡客邪,贵乎早逐,乘人气血未乱,肌肉未消,津液未耗,病人不至危殆,投剂不至掣肘,预后亦易平复”[7]50,故祛邪要趁早。在《温疫论·下卷》中又言:“温疫之邪,伏于膜原……方其浸淫之际,邪毒尚在膜原,此时但可疏利,使伏邪易出。邪毒既离膜原,乃观其变,或出表,或入里,然后可导邪而出,邪尽方愈。[7]175”由此可知,湿疫初起不可汗不可下,因湿疫之邪客于膜原,邪不在经,汗之徒伤卫气,热亦不减;邪不在腑,下之徒伤胃气,口渴亦甚,解表和攻里都不行,只有通过疏利膜原才能够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邪去则正安。
清·叶天士生于江南一带,气候温暖潮湿,他在《温热论》中提到“且吾吴湿邪害人最广”[23]6。对于湿疫初起之时的治疗,其观点同吴又可,此期邪伏膜原,湿遏热伏,病位尚浅,病情尚轻,若迁延日久,湿毒化热内陷,必伤及营血分而难治。
清代医家史以甲在《伤寒正宗》言:“邪既入,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24]”他提出治疗疫病初起务必急急透邪外出,因势利导,通行三焦以解湿毒。秦之桢在《伤寒大白》中提到:“应燥而反湿,祛湿邪即是治疫”[25],即通过祛湿法治疗湿疫。
根据历代医家的经验,湿疫的治疗一般当急以祛邪为第一要义,祛邪的重点即是祛湿,湿去热孤,诸证自解。
3.2 养阴逐湿,清解余邪
在祛邪的同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用药,中病即止,须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虚邪侵是人体发病的根本原因。扶正祛邪的关键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提及疫病的发生与人体正气密切相关:“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入”[7]15。他重视疫病后期的调理,提倡养阴清余邪,而不宜温补,因热病容易耗伤阴液。
在温病四大家中,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提到治疗湿疫时强调祛湿的同时,不可过用寒凉之品以免伤及正气,亦不可妄投补药以免助湿助热。“如面色白者,须要顾其阳气,湿胜则阳微也,法应清凉,然到十分之六七,即不可过于寒凉……湿热一去,阳亦衰微也;面色苍者,须要顾其津液,清凉到十分之六七,往往热减身寒者,不可就云虚寒而投补剂,恐炉烟难息,灰中有火也”[23]6。
病久不解必伤及阴。在湿疫恢复期邪热渐退,此时救液则助湿,治湿则劫阴,不可再用苦寒之品。湿邪黏滞极易复聚,故余湿未尽不宜妄投补剂,以免闭门留寇,当养阴逐湿,清解余邪。
3.3 温阳祛湿,宣畅气机
湿与热犹形与影,形亡则影无法独存,所以秽浊去而热自清。湿为阴邪,易阻遏气机,损伤阳气,故治湿不远温,不可过用寒凉之品,以免冰伏邪气,伤及脾胃,致使气机升降失常,增加内外合邪的危险性,不利于祛除湿邪。
吴鞠通尝谓“湿为阴邪,非温不解”,张仲景曾提及相似的治则:“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因湿为水之渐,水为湿之积,湿聚而成饮,凝而为痰,故痰、湿、水异名同类。由此可知,湿为纯阴之邪,故治之之法当以温药和之,微温则阳气通,水液得阳则化气,气化则湿化,湿化则气通[26]。倘若误用或过用寒凉之品,更伤阳气,寒则涩而不流,气机闭阻,湿郁致热难以外透,使病情加重。
4 治疗湿疫的常用方
4.1 卫气同病,选用藿香正气方或藿朴夏苓汤
湿疫初起,湿重于热,既有湿郁卫分的表证,又有湿阻脾胃气机的里证,属于卫气同病。其中表证明显者用藿香正气方,里证甚者用藿朴夏苓汤。
藿香正气方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卷二》,原文曰:“治伤寒头疼,憎寒壮热,上喘咳嗽,五劳七伤,八般风痰,五般膈气,心腹冷痛,反胃呕恶,气泻霍乱,脏腑虚鸣,山岚瘴疟,遍身虚肿;妇人产前、产后,血气刺痛;小儿疳伤,并宜治之。[27]”雷丰在《时病论·卷四》中借用成方藿香正气散治疗时病兼秽浊之邪:“治外感风寒,内伤饮食,及伤冷、伤湿,疟疾中暑,霍乱吐泻,凡感岚瘴不正之气,并宜增减用之。[28]321-322”《温病条辨·卷二》中收录了由藿香正气散加减而成的5个加减正气散,用于治疗湿郁三焦、脾胃升降失司之湿疫。
藿朴夏苓汤开肺气以宣化内湿,醒脾气以运化水湿,通下焦以渗利小便乃治湿疫良方。藿朴夏苓汤首见于清末民初医家何廉臣的《湿温时疫治疗法》一书,而其方药组成早在清代医家石寿棠的《医原·湿气论》中便可见,主治湿疫初起邪在气分,湿重于热证[29]。何廉臣言:“湿多者,湿重于热也,其病多发于太阴肺脾。”肺主一身之气,肺气化则脾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全方由三仁汤、茯苓杏仁甘草汤、半夏厚朴汤和猪苓汤相合并化裁而来,集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于一体,以使表里、脏腑、三焦之湿内外上下分解,体现了治湿大法的配伍规律[30]。如叶天士所言:“彼则和解表里之半,此则分消上下之势,随证变法,如近时杏、朴、苓等类”[23]5,以杏仁开上、厚朴宣中、茯苓导下。全方虽未用清热药,但因其分消上下,使湿去而热无所依,符合叶天士所言“湿去热孤”的治则,属于八法中的“和法”[31]。
4.2 湿阻膜原,宜达原饮
湿热秽浊之邪郁伏膜原,阻遏气机,是湿疫初发的另一类型,可由湿遏卫气转化而来,常用方剂为达原饮。此期湿邪尚未蕴热,故重用辛以开之,使上焦得通、津液得下也。
达原饮首见于《温疫论》,用于温疫初起,疏利表气,直达病所,祛除伏邪。方中槟榔能消能磨除伏邪,为疏利之药,又除岭南瘴气;厚朴破戾气所结;草果辛烈气雄,涤痰湿、振脾阳,除伏邪盘踞,去恶气。三药协力直达其巢穴,宣透辟秽,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薛生白仿吴又可之达原饮,《湿热论》中载:“湿热证,寒热如疟,湿热阻遏膜原,宜柴胡、厚朴、槟榔、草果、藿香、苍术、半夏、干菖蒲、六一散等”[19]30,槟榔、厚朴、草果乃治疗湿疫之要药。
4.3 湿困中焦,用雷氏芳香化浊方
湿疫直犯中焦,或进展期膜原湿浊转归脾胃,致使湿邪蕴阻中焦,脾胃气机升降失常,枢机不利,湿重于热,可用雷氏芳香化浊方。
晚清医家雷少逸在《时病论》中拟法制方,以法代方。湿邪在里、阻于膜原者,拟宣透膜原法;霉湿壅遏、上冲气分者,用芳香化浊法。雷丰认为:“人感其气则病。以其气从口鼻而入,即犯上中二焦,以致胸痞腹闷,身热有汗,时欲恶心,右脉极钝之象,舌苔白滑。以上皆霉湿之浊气,壅遏上中气分之证,非香燥之剂,不能破也。拟以芳香化浊法,俾其气机开畅,则上中之邪,不散而自解也。[28]304”
湿为阴邪,其性重浊黏滞,用药最忌呆滞。雷少逸以“轻、清、灵、动”之品治之,即药味少、用量轻;其药味清淡,不滋不腻,用药灵活变通,生动活泼。在芳香化浊法中,君用藿佩之芳香以化其浊,臣以陈夏之温燥以化其湿,佐腹皮宽胸腹,厚朴畅脾胃,使上中气机宽畅则湿浊不克凝留,使以荷叶升清,令清升则浊自降,用药简洁,轻清流动[32]。
4.4 湿疫化热,宜甘露消毒丹
湿疫进展期若湿热俱盛,充斥气分,酿成热毒,以致津液被伤,可用甘露消毒丹。
甘露消毒丹出自《温热经纬》,又名普济消毒丹。关于其源流,一说最早出自《续名医类案》,后被收入《温热经纬》[33]。甘露消毒丹中诸药合用开上、畅中、渗下,即辛开肺气于上,启上闸以开水源;芳香化湿于中,醒脾气以复脾运;淡渗利湿于下,通水道以祛湿浊,湿化热清、气机畅利而愈疾[34]。如薛雪在《湿热论》中所言:“湿热俱盛之候,而去湿药多,清热药少者,以病邪初起即闭,不得不辛通开闭为急务,不欲以寒凉凝滞病机也。[19]35”王孟英认为本方为湿温时疫之主方也,治疗湿温时疫疗效显著,常作为湿疫化热的代表方。
徐鹤在《伤暑论·卷三》中曰:“阳明暑湿,流布三焦,发热倦怠,目黄咽痛,胸痞脘胀腹闷,泄泻溺涩,肌肤瘾疹,苔黄而腻,津不甚干,湿热犹在气分,甘露消毒丹主之。[35]184”徐鹤所言暑湿即湿温,同湿疫,因“暑兼于湿者,名曰暑湿,又曰湿热,又曰湿温”[35]26“凡瘟疫、温毒、温疟……内兼湿邪者,作暑湿治”[35]133,湿热流布三焦,通过辨舌确定湿疫仍在气分,故所用之药纯走气分。
4.5 气血两燔,用清瘟败毒饮
湿疫危重期疫毒充斥表里,郁伏深重,化燥伤阴,气钝血凝,形成气营血俱燔之证,可用清瘟败毒饮。
清代医家余师愚擅长辨证斑疹,并重用石膏治疗疫疹,其所创的清瘟败毒饮为后世治疗急性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徐鹤在《伤暑论·卷二》中提到:“若夫余师愚之清瘟败毒饮……乃治暑热之疫不夹秽浊而设。[35]135”清瘟败毒饮由白虎汤、黄连解毒汤和犀角地黄汤三方化裁而来,方中石膏配知母和甘草由白虎汤化裁而来,倾泻阳明气分之热以保津;连翘、竹叶轻清宣透,清透气分表里热毒,清心除烦以利尿下行,全方共奏气血两清、清瘟败毒之效[36]。清末民初医家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言:“热甚口燥无津,脉象洪数,唇焦大渴者,用清瘟败毒饮。[37]”
5 结语
湿疫是具有强烈致病性的毒邪,因湿致疫故名湿疫。湿疫的进展可分为初期、进展期、危重期和恢复期4个阶段,病机为湿疫毒邪侵袭人体,内外湿邪相互感召,疫毒内盛,阻滞气机,闭肺困脾,伤津耗液。治疗遵循“祛邪逐秽,养阴扶正,全程护阳”三大治则,首重祛邪,而祛邪的关键在于祛湿。湿为阴邪,得温则化,遇寒则凝,其性重浊黏滞,易阻滞气机,损伤阳气,故治湿多用辛温、苦温之品,宣肺气、运脾气、化膀胱之气以疏通三焦,复其运行水液之职而祛除湿邪[38]。温药多辛香温燥,易耗伤阴津,所以中病即止,不可过用,以免伤及正气[39]。在临床治疗过程中,湿疫复杂多变,不可拘泥于古方,当审证求因,辨证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