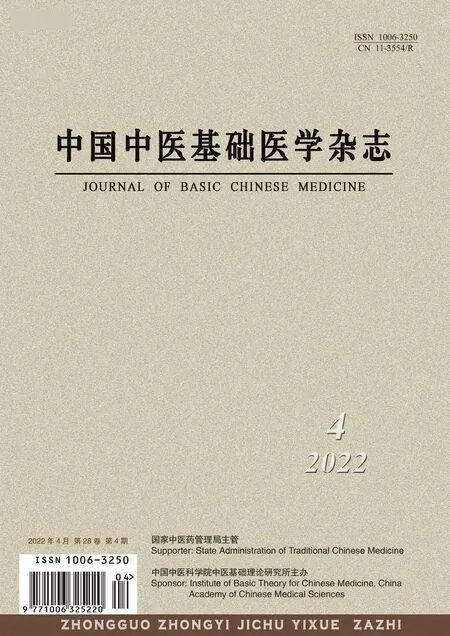《饮膳正要》养生思想的历史诠释*
安 宏,徐世杰,高 雅
(1.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北京 100700;2.中国中医科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北京 100700;3.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北京 100700)
《饮膳正要》是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为饮膳太医忽思慧编撰,成书于元朝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全书共三卷,包括诸般禁忌、聚珍品撰、诸般汤煎、食疗诸病及食物相反中毒等,还有米谷品、兽品、禽品、鱼品、果菜品和料物的详细说明。后世医家、学者多从学术价值、药物性状方面研究本书,未涉及本书的成书年代、历史背景及文化传承。笔者尝试从历史诠释学研究角度入手,挖掘元代饮膳养生思想,探讨《饮膳正要》的史料价值。
1 历史诠释学
1.1 理解的历史性
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已发生事实的理解,不同时代的人们可能对其意义做出不同的解释。历史意义在人们的理解中生成,人们理解的变化造成历史观念的流动[1]。人类是历史的存在,理解是在原有内容上加工而成,因此理解是具有历史性的,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理解的偏见,进一步决定了理解的创造性,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1.2 理解的偏见性
伽达默尔认为偏见是积极的,偏见构成了人们的最初体验。人们以自我思想去体验去诠释,从而赋予文本特殊性,这是对文本的感悟与再创造。伽达默尔以诠释学的方法探讨历史理解的意义,他认为历史理解的过程是主客体相互规定的过程,理解的对象也是主客体相互规定的统一体,解释者与解释对象之间通过“视域融合”形成历史认识[2]。
“视域”指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解释者在原有的文本即原作的视域下,加之现今的时代氛围,两种视域交织形成了“视域融合”,达到了全新的视域。事实上视域是随着时代需求不断更新的,是偏见的也是创造的。
1.3 历史的诠释性
诠释学(Hermeneutics)是意义宣告、译解、阐明和解释的技术,其基本功能在于把一种意义关系从另一个世界转换到我们自己的世界[1]3。不进行意义的转换就不可能有对历史的理解,历史必然存在诠释学的特性。历史诠释学就是发现、理解、阐明、解释历史意义的技术,就是历史事件转换到我们世界之中的技术。
伽达默尔明确提出“历史诠释学”概念并认为:“为了按照前有、前见和前把握来解释存在问题的诠释学境遇。[3]”“人类只能根据过去理解现在”[4],当人们认识历史时,不是仅仅依赖历史事实文本,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更多地思考过去的历史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思考“定在的未来出发的存在的真实历史化”[3]334,更好地理解与解释历史。
1.4 历史诠释的时代特征
历史是一个传统延续与变化革新的过程,历史的认识也是继承与不断创新的。历史诠释学就是在不断的重新规定与诠释历史文本中发展,反思历史,对原有历史文本进行新的诠释,将过去的视域地平线不断地向前推进,凸显原有文本作者没有发现的联系,重构历史认识或历史观念,形成全新的“视域融合”。
兰克指出:“历史瞬间给予历史联系以鲜明的节奏。我们把这样一些自由行动可以在其中起历史决定作用的瞬间称之为划时代的瞬间或转换期,而把那些其行动能起这种决定性作用的个人,用黑格尔的用语称之为‘历史性的个人’。[5]”历史的终极目的不是发现暗含在历史进程中等待展开的东西,而是发掘伴随着人类活动不断生成的事物[1]20。元代为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至忽必烈称帝,建元“中统”,改号“大元”,再至巩固政权,疆域超过历代,特殊的时期造就了繁荣的贸易,造就了物资交流,更造就了强大的统治者与独特的饮膳文化。“饮膳”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探究我国第一部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探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状况,探索历史进程中饮膳文化与人们生活的交互,也显得十分必要。
2 《饮膳正要》历史背景
2.1 游牧民族,养生需要
蒙古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逐水草而居。一方面特殊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蒙古人以肉奶为主、加工方式简单的饮食特点。另一方面随着王朝的建立,元朝活动中心由北方草原转移至中原及江南地区,新的生活环境与原有的饮食习俗叠加,产生了新的饮膳文化。加之饮酒纵欲、近亲结婚,导致当时的蒙古人寿命较短,急需具有针对性的养生方法改变这种状况,《饮膳正要》由此应运而生。
2.2 民族融合,交流频繁
元代是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一方面随着蒙古人与汉人通婚、杂居,民族间交流日益频繁,民族隔阂逐渐淡化,不同民族间的养生习俗相互渗透,大大加快了民族融合进程;另一方面中亚、西亚各族纷纷来华,中外交流加深,丰富了医药资源。具有代表性的如至元七年(1270年)宫廷下设广惠司,“秩正三品,掌修制御用回回药物及和剂,以疗诸宿卫士及在京孤寒者”[6]2221,促进了回回医药的传播。在《饮膳正要》中,可见许多回回药膳,如回回茶饭、畏兀儿茶饭、哈西泥等。
2.3 设饮膳医,调和五味
元朝建立后,统治者愈发重视学习汉族养生之道。忽必烈即位后戒骄纵,远游惰,克私欲,适游牧,节饮食,仿古制,设御医。《周礼·天官冢宰》言:“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7]”忽必烈亦设饮膳太医四人[6]5,主司补养调护及饮食宜忌,“于本草内。选无毒、无相反,可久食补益药味。与饮食相宜,调和五味,及每日所造,珍品御膳,必须精制。所职何人,所用何物……至于汤煎琼玉、黄精、天门冬、苍术等膏,牛髓、枸杞等煎。诸珍异馔,咸得其宜”[8]7。自设饮膳太医至撰写此书之时,已历经60余年,期间蒙汉饮食文化交融,太医们在饮膳方面积累了经验,这也是撰写《饮膳正要》的重要因素。
宋金元时期战火连绵,灾荒、动乱频发,医家多集思广益,推陈出新,分医学之门户。伴随统治疆域的扩大改变,蒙古人原有以肉类为主的粗加工饮食已无法满足需求,宫廷仿古制设饮膳医,建广惠司,广搜中外饮食疗法,调和五味,以“守中”为要。
3 《饮膳正要》养生思想
3.1 “守中”为要
《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9]”是故《饮膳正要》言:“保养之法,莫若守中,守中则无过与不及之病。调顺四时,节慎饮食,起居不妄,使以五味调和五脏。五脏和平则血气资荣,精神健爽,心志安定,诸邪自不能入,寒暑不能袭,人乃怡安。[8]11”忽思慧认为保养之法需以“守中”为要,无偏倚无不及,“药性有大毒……虽饮食百味,要其精粹,审其有补益助养之宜,新陈之异,温凉寒热之性,五味偏走之病”[8]11。若养生不忌、妊娠不忌、乳母不忌、幼儿不忌、饮酒不忌,贪爽口而妄避忌,则“疾病潜生而中不悟”[9]。因为忽思慧强调平日食疗养生,阴阳平和,切要“守中”,医者需先晓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疗,不愈再治以针。
3.2 保精养气
金元时期,全真教创建并迅速发展,道教养生迅速渗透到统治者阶级中,元代诸帝多效仿元世祖信奉神仙养生之术,饮膳太医也将道教思想融于药膳之中。忽思慧从历代神话及道家医籍中摘取25种方药,于《饮膳正要》中列“神仙服食”一节,选《抱朴子》《药经》《神仙传》《孙真人枕中记》《东华真人煮食法》等书,列地黄、天门冬、枸杞、黄精、苍术、茯苓、松子、栗子、五加皮等单药服食法,可填精补髓,返老还童。他还列《圣济总录》中所载地仙煎,将杏仁研碎加新牛奶、山药拌绞取汁,以温酒送服。方中“饮鲜奶,喝温酒”服药方式符合蒙古族习惯,忽思慧特地选用此方,并说明“治腰膝疼痛,一切腹内冷病。令人颜色悦泽,骨髓坚固,行及奔马”[8]166。《饮膳正要》中所载服食之法与道家不尽相同,并避开金石类丹药,而选择草木中平和补益之品,单药居多,酒膏较少,且书中并未提及“飞升成仙”之言,只涉及“行及奔马”“返老还童”“过目不忘”之词。这种选品偏好与功效描述特点,表明元代的宫廷饮膳有意识地绕开了自古与医学捆绑的神仙之学,以一种实用主义精神追求饮膳的安全有效。
3.3 养生食忌
忽思慧在《饮膳正要》开篇即言:“形受五味以成体,是以圣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后制药以防命……若贪爽口而忘避忌,则疾病潜生而仲不悟。百年之身而忘于一时之味,其可惜哉![8]6”养生需明确食物偏性及禁忌,不可贪一时之快,否则疾病丛生。书中列“养生避忌”“妊娠食忌”“乳母食忌”“初生儿时”“饮酒避忌”等节,指出常人摄生应薄滋味、省思虑、不劳神、不劳形,而对“孕育之人”“饮酒之人”“服药之人”等群体需区别对待,现简述如下。
3.3.1 孕育之人 《古列女传·母仪传》首次记录“胎教”:“太任之性,端一诚庄,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君子谓太任为能胎教……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人生而肖万物者,皆其母感于物,故形音肖之。[10]”妊娠期间应注意目、耳、口的感受,接触积极向上的事物,胎儿也会感同身受。《饮膳正要》也有提及:“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善恶犹相感,况饮食不知避忌乎?[8]29”小儿出生后,应选择健壮、慈善、温良的乳母,“子在于母资乳以养……若子有病无病,亦在乳母之慎口”[8]36。乳母不应过饱过饥,避免因脾胃虚弱或阳明热蕴导致乳汁难行。乳母也应随小儿疾病变换饮食,如小儿患积热、惊风、疮疡病症时,乳母应忌吃湿热、动风食物;若小儿患疥癣疮疾,乳母应忌食鱼虾、马肉等发物。
3.3.2 饮酒之人 蒙古人好饮酒,《饮膳正要》中酒的品种也多。值得一提的是,书中首次记载了蒸馏酒:“阿剌吉酒……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剌吉。[9]300”后世李时珍《本草纲目·穀四·烧酒》言:“火酒,阿剌吉酒。[11]”《证俗文·酒》也说:“火酒,秫酒也……火酒自元时始创其法,一名阿剌吉酒,见《饮膳正要》,李时珍《本草》详之。[12]”忽思慧认为酒可通血脉、厚肠胃、润肌肤、消忧愁,但饮酒不宜多,酒多则烂肠胃,熏蒸筋脉,“伤神损寿,易人本性”。饮酒后腠理疏松,外邪易入侵机体,不可当风卧,不可向阳卧,更不可冷水洗面,易发偏枯、疮疡。酒易生湿热,醉酒后不可食生冷油腻之物,如冷水、猪肉和甜食,使湿热加剧。
3.3.3 服药之人 服药期间,合理饮食可滋养脾胃,运化得当,化生精微,以行药力。《调疾饮食辨》中说:“病人饮食,借以滋养胃气,宣行药力。故饮食得宜,足为药饵之助;失宜则反与药饵之仇。[13]”病人若只贪口腹之欲,不知避忌,在服药之时食用不宜食物,往往拖延病情甚至恶化。忽思慧提出服药食忌:“但服药不可多食生芫荽及蒜,杂生茶、诸滑物,肥猪肉、犬肉、肥腻物、鱼脍腥膻等物,及忌见丧尸、产妇、腌秽之事。又不可食陈臭之物。[8]240”他认为辛膻等发物易致疾病反复,油腻之物易使疾病停留,也应避免不良环境对患者的精神刺激。
4 《饮膳正要》的历史诠释
《饮膳正要》的创作背景与学术特点凸显了环境迁移和文化融合对蒙古人食养食治方式的影响。尽管这一饮膳模式在当代已经失去了赖以有效存在与传播的土壤,但以当代视域审视这部宫廷饮膳专著时,先人的智慧仍然通过文字启发着当代饮膳实践与学术研究,令《饮膳正要》生发出新的价值。
4.1 饮食宜忌与环境迁移
辽金时代,蒙古各部分布于牧场地域,畜牧业在蒙古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蒙鞑备录》所述:“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彼国中有一马者,必有六七羊,谓如有百马者,必有六、七百羊群也。[14]”其中牧羊众多,人们也喜食羊肉,烤羊、蒸羊也成为蒙古族的传统。忽思慧认为:“羊肉,味甘,大热,无毒。主暖中,头风、大风,汗出,虚劳,寒冷,补中益气。[8]330”《饮膳正要·聚珍异撰》所列94种宫廷御膳中,有70余种以羊肉作主料,还以草果、良姜等辛温之品与羊肉搭配,以温阳补益之力更甚,如八儿不汤、糯米搊粉、大麦片粉等。
忽思慧将其他民族的中药材和蔬果融合与蒙古族“以肉类为养,以奶类为充”[15]的饮食习惯相结合,既可温中补益,也可帮助蒙古族人适应新环境的变化。《饮膳正要》的饮食思维也可给我们提供借鉴,当今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出差、游学变多,环境发生迁移,原有的饮食习惯很难与新环境协调,这时不妨根据当地风俗结合自身饮食习惯,调整饮食结构,加快与当代环境的融合。
4.2 饮膳文化的中西融合
元朝地域广阔,书中“聚珍异馔”更是“遐迩罔不宾贡,珍味奇品,咸萃内府”[8]50。书中除了蒙古族的“颇儿必汤”外,还有天竺的“八儿不汤”“撒速汤”、维吾尔族的“搠罗脱因”,食物中还包括新疆的“哈昔泥”,西番的“咱夫兰”,南国的“乞里麻鱼”,其中“回回豆子”“赤赤哈纳”等由本书首次记载。
《饮膳正要》不只是元代饮食生活的缩影,更是一本中外食物本草交流之书。如“马思答吉”为波斯语“mastaki”的汉字发音,即乳香[16],在元代宫廷备受青睐,做“马思答吉汤”有补益、温中、顺气之功。元代饮膳养生思想已经在与外界交流中碰撞,当代的饮食营养研究不仅需要扩大对外交流,也需下沉到民间打通壁垒,使“老树开出新枝”。
4.3 宫廷饮膳的民间推广
中国传统饮膳文化分为上下两层。身处上层的宫廷饮膳与基层的民间食养食治各有其生态位,因而传统上并没有频繁的交流。由于贫苦百姓经济差,以体力劳动为主,上层的饮膳文化在民间并没有生长壮大的土壤。但当代生活条件改善,劳动方式变化,精血亏虚也不少见,当代人的体质也转向“尊荣人”,宫廷饮膳平稳、调养为主的特点反而更适合当代人。《饮膳正要》也给当代的我们提供了膳食参考,我们也可调整饮食,使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结语
《饮膳正要》强调“守中”为要,保精养气,详列养生食忌,是对元代统治者宫廷养生的诠释。在当代的“视域”下,也可形成新的“视域融合”,可对环境迁移后的饮食提供指导,促进饮膳文化的中西融合,为宫廷饮膳的民间推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