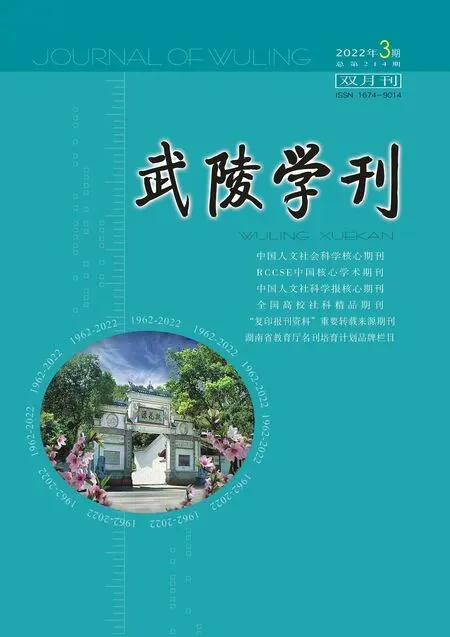明代讲会中的“教学设计”与课程思政的传统视角
阮春晖,周飞蓉
(1.邵阳学院 政法学院,湖南 邵阳 422000;2.邵阳学院 图书馆,湖南 邵阳 422000)
明代的讲会,就外在形式而言,是由教谕、师友、士子所组成的学术群体,有相对固定的教学场地,并通过个体与群体相互往来开展思想互动;就内在规定来看,有用以规范授受过程的讲会会约、学规、诫谕等。这种讲会实际上是明代非官方的重要教学模式,其构成具有现代教学所具备的核心要素,如教学目标的道德设定、教学环节的有序安排等。这就意味着明代讲会与现代教学有相通之处。此外,不论是明代讲会还是现代教学,其主要价值目标,是将受教者培养成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人。研究明代讲会不难发现,其有关德性科目的设置、德行内容的具体规定,对现代教育教学依然具有时代价值。当前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中,立德树人是首要目标,也是实践行为展开的伦理基础,因此,课程教学既要注意学科教学的道德立场,更要寻找与教学相关的优秀道德资源。毋庸讳言,明代讲会“教学设计”中所含有的道德性元素,是当前实施课程思政的重要内容来源,我们可以在古今相联的教学构成中寻找二者之间的共通点,为课程思政内涵层次的多样性布局提供有意义的思政素材。
一、“讲会”略说
学者吕妙芬认为,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就明代而言,其形式包括书院日常讲学,朋友们不定期的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1]。由此可知讲会是通过讲学聚会而形成,其形式也灵活自由。如果要追溯源头的话,讲会早在孔子时期就已有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讲学就是孔子所忧之事,因而孔子试图通过不断的讲学活动以解其忧,讲学的主要形式就是聚徒传播和交流思想,以此达到向执政者陈述自己思想主张的目的。孔子之后,孟子也有讲学,主要体现在对君王的政治谏说和师友、师徒之间的思想交流。不管是孔子、孟子,还是后来的“两程”(程颢、程颐),其思想的传播都有讲学的实质内容,但都还没有在一个有组织性、规模性的讲会中进行,也就是说“有讲而无会”。既有“讲”又有“会”,是从朱熹和陆九渊开始的。朱熹热衷传道讲学,曾大力振兴白鹿洞书院,招收生徒,制定《白鹿洞书院揭示》,使白鹿洞书院成为“前人教育之美”[2]的会讲之地。陆九渊除自己办私学外,还与朱熹开展讲学互动,他在白鹿洞书院所讲“义利之辨”以及与朱熹在江西上饶鹅湖寺的会讲,成为朱、陆二人相聚讲学的千古美谈,其讲学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通过制定教规并定期开展讲学活动,孔孟开创的讲会在朱、陆之时得到很好发展。
明代承继宋代讲会实践并有新的发展,形成了相当程度的规模效应。《明史》有“缙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3]之说,表明讲会在明代日趋兴盛,已超越前朝而成为当时一种普遍的教育教学形式。其中,王阳明及其后学的讲会活动尤为引人注目。王阳明军旅之余,时常与友人、门生往来讲会,相继不辍,在明代讲会史上留下许多佳话。他说“读书讲学,此最吾所宿好,今虽干戈扰攘中,四方有来学者,吾未尝拒之”[4]1088,可见其讲学之热情与执着。王阳明居绍兴时,时常与群弟子燕集于天泉桥,“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4]1424,学味盎然。中国哲学史上有名的“天泉证道”公案,就是王阳明与弟子在相聚讲会时思想交流的产物。王阳明的这种会讲之习,对其门下影响很大,从而在中晚明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讲会之潮。实际上,明代讲会就其文化使命而言,有传承儒家道统的一面,也有士子之间相互辩驳、以期学有所成的学术期待。因此,当一个讲会成立后,为防止学有停辍,常常需要“订会约以垂永久”[5]846,以之作为推动学子前行的“进修之要”,因而在明代中晚期讲会中出现了“在在有会,会会有约”[5]437的情形。在师友之间的思想交流中,与会者实录当时讲会内容,以“会语”或“讲语”的形式加以记载,既呈现当时讲会情形,也可为后学留下思想材料,成为研究前人教育教学的重要依据。
二、明代讲会“教学设计”中的核心教育要素
明代讲会很多,相关会约和会语也较为丰富,这里只择取晚明学者冯从吾(1557—1627,陕西西安人)的《关中会约》和《学会约》、杨东明(1548—1624,河南虞城人)创办兴学会时所拟定的《学问要义》和《兴学会条约》、吕维祺(1587—1641,河南新安人)的《芝泉会约》和《风芑学约》,作为凭藉材料来说明当时的教学情形。之所以选择这几则材料,一是因为这些会约或讲语中,有较丰富的“教学设计”值得我们重视,可为当前课程思政寻找到一个有益的传统视角;二是因为这些学者的学问之道和施教方法在当时具有典型性,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当时讲会式教学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一)“教学目标”的设定
《关中会约》是冯从吾讲学关中时于1597年订立的会约。在此之前,冯从吾与士子讲学于宝庆寺时,就写有《学会约》,并有《士戒》《谕俗》的教诫,作为与会者讲学交流的遵守之约[6]144-148。《关中会约》与《学会约》前后相联,可视作一整体加以看待。冯从吾举会的目的,在于“崇俭德以敦素风,酌往来以通交际,严称谓以尊古谊,绝告讦以警薄俗,周穷约以厚廉靖,恤后裔以慰先德”[6]143。这几条“教学目标”,涉及人的品德培养、交际往来、伦理秩序、正直言辞、慈善之心以及抚恤后裔等方面,从中可以看出立人之道德品性是《关中会约》《学会约》倡导的首要施教目标。
兴学会1596年由晚明学者杨东明创立,地点在虞城。讲会成立之初,杨东明便拟定了学问要义八款[5]847-855。这里的《学问要义》,实际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教学目标”。八款《学问要义》分指择术、立志、知性、虚心、真修、取友、脱俗、有恒,诸要义各有其作用,表现为:择术以审向往,立志以期成功,知性以示归宿,虚心以戒满假,真修以惩伪学,取友以广丽择,脱俗以澡雪习染,有恒以时保前功。在杨东明看来,这些“要义”是士子的“进修大要”,是从事学问的前提基础。如择术,杨东明认为天下有第一大事,“仰可参天,俯可法地,前可继往,后可开来”,这件事就是“学问之事”,故士子当以学问为重。又如立志,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以志立而成、志荒而废者”,只有立志,方能永不蹉跎,成就圣贤事业。
吕维祺是明末河洛地区大儒,以传道讲学为己任,创办了许多讲会、书院,芝泉讲会和风芑会就是其中之二。《芝泉会约》是吕维祺于1622年在新安创建芝泉讲会时所订立的会约。《芝泉会约》规定,立会的目的,“以立身修德为主,因以正人心、善风俗,非徒博名而已”[7]315-322,指出立身修德乃士子本分事。风芑会是1632年吕维祺在南京创办的讲会。当时士子中普遍存在着“取科第、做好官、多得钱”的思想倾向,有感于此,吕维祺发出了“我辈要寻真正受用安在”的呼吁,认为有必要成立讲会以正学风。《风芑学约》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针对这种现象,吕维祺从“定志向”“敦孝悌”“ 甘恬 静 ”“ 励潜 修 ”“ 慎 言论 ”“ 禁 奢靡”“简游宴”“勤实学”“精书理”[7]315-322等方面对此作了种种规劝。在他看来,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才能做到“热闹中别具冷眼,淡静处独有热肠”,学问的真谛才会由此呈现。因此,吕维祺认为,“是故学也者,以言乎其觉也”,指出学问的实质,其实就是对人生社会的觉悟,这是很有见地的。
(二)“教学过程”的安排
《兴学会条约》共十九条,对讲会的整个过程作了详细安排,置于现代教学中,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具体的“教学过程”。《兴学会条约》规定:讲会每月举行三次,非有不得已之事,不可不到;待士子到齐,需向先师像鞠躬行礼,朗诵经书中的警切之言;入座时当敛容默坐,定气澄心,进入学习状态;教学中,一主讲老师解读经书,另一老师诵读前贤语录;每次讲会的讲义由五人各作一篇,在讲会前交由会长加以择用;主讲老师讲毕,士子们用较多时间议论交流,交流时务要做到“平心和气,虚己受人,即言有不近理处,亦宜婉转开导”[5]856;讲习讨论中,特别要求与会者“各立言一条,或纪所可疑,或证所已信”[5]857,将平日学习的疑难或收获记录下来,先交由会长加以评定,再带至会所与众人一起交流。《兴学会条约》也强调,学问之事主要由自己完成,“自家病痛,须是自知自医,饰非文过,只徒自欺”[5]857,表明学习关键在于主体的自省自觉,以及真诚态度对于学习的重要意义。讲习毕,又向先师像鞠躬行礼,众人作揖相别,教学过程至此结束。可以看出,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与对教学纪律的谨严遵守是分不开的。
《学会约》在教学过程的安排上与《兴学会条约》有类似之处,如每月三会,安排在初一、十一、二十一,以中午为期。不过其中也有与之不同之处。如会约提出,坐久之后可以歌诗,“以畅涤襟怀”,在歌诗中反思自我,并指出这是与人为善的重要方式。冯从吾之学程朱色彩较浓,但在讲学中,他认为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也是圣学,讲会之中不可随便轻议,特别提醒学人“今日为学不在远求,只要各人默默点检自家心思,默默克治自家病痛,则识得本体,自然好做工夫”[6]145,强调自反自治对于为学的重要性。对于朋友偶有过失之举,亦在学约中提到“不惟不可背后讲说,即在公会中亦不可对众言之,令人有所不便”[6]145-146,注重顾及他人隐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在《士戒》中,冯从吾列所戒之事共二十款,以警示学子,其中“毋妄自尊大,侮慢宗党亲朋”“毋在稠众中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毋见人贫贱姗笑凌辱,见人富贵叹羡诋毁”[6]147等语,时至于今仍有很强的现实警醒意义。在《谕俗》中,冯从吾以一语点破讲学之道:“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之矣。”[6]148表明讲学不仅仅是求得学问的精深,更重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有善心、善行的人。提醒与会者在会讲过程中“自求其益”,包含着道德自律的要求,当然也是教学过程得以展开的首要心理基础。
与《学会约》相异,《芝泉会约》在讲会之初即有歌诗环节,且是士子一并进行,并伴有钟鼓之声,以节其韵,活跃气氛。继而主讲教师讲《四书》等儒学经典,强调讲说“务要明晰易晓”。士子将老师所讲内容熟念二三遍,掩卷沉思,之后进入“众相质问”环节,讲求对经典的反复参证,要求“务协中道,或相规劝”,做到“躬行为要,不可阔谈性命,使人无处捉摸”[7]316。除了研习经典,每次讲会都要讨论士子在学习过程中的“心得语”“疑书义”或“疑难事”。这项工作在开讲之前由士子拟好交由会长,在开讲时统一商证。需提到的是,讲会中还放置有迁善改过簿一册,将善言善行“以为众劝”,并“私相规正”有过者。迁善改过簿在讲会中的有效运用,对于扩展讲学内容、砥砺士子知行统一,具有很强的道德规范作用。教学过程中识与德相结合,是这一时期讲会的重要特色。
(三)“教学内容”的确立
明代讲会虽多,但讲会内容却相当集中,即通过研修儒家经典,体悟其中的思想智慧,在内圣外王的实践过程中实现自身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冯从吾在关中宝庆寺讲学的内容,后被编成《宝庆语录》刊行于世,所载内容大都与《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的讨论有关。对孔子之学,冯从吾尤为看重:“论学譬如为文,必融会贯通乎百家,然后能自成一家。若只守定一家,恐孤陋不能成家矣。学之道何以异此?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6]163将孔孟之学定为讲学的核心内容,既确定了讲学的重点,也保证了讲学的儒家伦理方向。由于儒家经典之学涉及学问、政治、教育、礼俗等多个方面,对《论语》等经典的强调,势必影响士子在日用常行中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为他们面对生活时提供价值指引,因此冯从吾讲学的内容在生活上总不出“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之义。除此,在教学内容上,冯从吾还特别提出会讲须树立“崇真尚简为主,务戒空谈,敦实行”[6]144的传授理念,反映出冯从吾在讲学时将儒家之道落实于会讲之中的殷切期望,希冀以此杜绝讲学中存在的虚浮空疏之风,振奋士人笃实潜行的心志,使其有益于社会人生。
杨东明与学友在讲会中的谈论内容,也被辑成《学会讲语》之语类流传下来。《学会讲语》内容列为《大学》答语、《中庸》答语、《论语》答语、《孟子》答语等四个部分,“教学内容”更加清晰可见。每部分都重点记载了当时讨论的主要内容,既可将之视为“教学实录”,也可将之看成是各自思想表达的一种方式。《学会讲语》具体内容关联“明德”“修身”“诚意”“立志”“性善”等多个知识要点。如有友问何谓“明德”,杨东明答之以“天有明命,赋于人为明德,人之本性也”[5]864,将人的本性与天道相联,挺立了人的自我存在,这对于传授《大学》经典要义,促发学子深度思考,自有言下跃然的效果。
明代讲会中的“教学内容”,以各时期儒家经典作为主要教材,在经典的解释和阐发上,突出老师的立场和士子的省思。就数量上看,儒家经典本极为丰富,在会讲中又鼓励各家之学相互贯通,因而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在传授过程中,主讲者又往往将儒家经典关联生活实践,因而会讲中的“教学内容”常能由此及彼,展开为对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现实的思想价值,对士子理想人格的形成有重要意义。
(四)“教学效果”的预期
《关中会约》施行有年,关中学者秦可贞感叹会约“行之十余年,弗替也”[6]143,并呼吁“斯会斯约永贞”,勿负会约所期。冯从吾在宝庆寺讲学期间,从游者日众,“一时缙绅学士多执经问难,而农商工贾亦环视窃听”[6]205。由于听讲人数日益增多,1609年,当地官员在宝庆寺周围创建关中书院,聚集生儒继续讲学。书院创建以后,“教泽洋溢,风韵四讫”[6]205,学风浓郁有嘉。冯从吾门人韩梅称冯从吾的讲学着意于事功、节义、文章与道德,“有功世教,媲美前贤”[6]206,韩氏自己身为教谕,当受冯从吾影响很深,也可预料他会把冯氏的讲学之风贯彻下去,并代代相传。
杨东明在虞城首创兴学会之后,出现了“相率秉承,会立而风动”[5]844的热闹讲学情形,门下弟子遍布虞城,并波及到邻县区域,士子中也不乏中进士、举人者。山西阳高县士子王下问,宦游虞城时听闻杨东明讲学之事,起先“心窃疑之”,在听了师友讲学之后,继而“洗心涤虑,求拜门墙”,感叹“往故未尝不诵诗书,何期圣贤旨趣乃至若此之妙也”。后王下问恪守官箴,相亲于民情,始知学与仕是合一的[5]862-863。由此可见当时讲学对一个士子求学和为官的双重影响。
吕维祺将讲学视为“法程”,注重德性教化,吸引了大批学者前来。以芝泉讲会而论,吕维祺家居八年,讲学芝泉书院,“直接濂洛之传,发明奥蕴,从游日重,士风化之”[8],对当地的文化宣教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624年的一次讲会中,名儒李缉敬等人讲学芝泉书院,“尔时远近之士皆来学,凡渑池诸生至者既新安士数十辈”[7]337,可看出当时吕维祺讲学效果对当地教育风化的影响。他在任职南京开讲风芑会期间,学者如影随形,身边有施化远、陈名夏、周景濂、张一儒等二百余人,影响甚大。
三、明代讲会中的教学元素与当代课程思政传统视角的开掘
课程思政是近些年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其基本涵义是:深入挖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德育元素,充分发挥课程立德树人的功能,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融为一体,推动学生德性涵养的有效形成,整体构建课程教学改革的大思政格局。课程思政的核心,在于将文化自信、家国情怀、科学态度、刚健有为的道德品性和实践精神融入学生的生命历程之中,让学生成为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时代人才。至于如何开展课程思政,则是仁智互见、各有所长。从明代讲会所显露出来的教学元素中,我们认为学与德、学与仕、学与行的关系问题,是当下开展课程思政教学时需思考的重要话题。
课程思政与德目教学的具体化。人才培养的首要目标是立德树人,立德究竟从哪些方面进行,则需要微观对待。在《论语》中,孔子有“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的话,认为仁、智、勇是君子之道的表现。至《中庸》,则将之称为“三达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谓“达德”,按照朱熹的解释,是“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9],表明仁、智、勇具有超越时空的道德意涵,不会因时代的变更而消失,只会因时代的前行而加注新的内容。上文所述明代讲会的“教学目标”中,《关中会约》提出的“崇俭德、酌往来”,《兴学会条约》设定的“择术、立志、知性、虚心”等学术要义,《芝泉会约》强调的“正人心、善风俗,非徒博名”,以及《风芑学约》中的“敦孝悌”“甘恬静”“励潜修”“禁奢靡”等道德要求,其实都是孔孟所提德目的具体化。以今天的眼光视之,明代讲会中的这些德目教学内容,仍然具有很强的教学参考意义。它让我们体会到,学习不仅表现为知识的累积,更是对多种德性的品味与践行。只有这样,人的德性发展才更全面。因此,在实施课程思政教学时,我们可以充分运用优秀传统经典,凝练其思想智慧,突出经典在课程思政中的作用,既将立德教学具体化,让学生体会到人的德性可以而且需要从多方面加以培育,同时又与古贤教学遥相对接,将优秀传统道德融会于课程教学之中,担当起承继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责任。这样,就会在古今文化之间通过教学架起思想的桥梁,既在课程教学中丰富道德教学的内涵和层次,也有益于树立起本民族的文化自信。
课程思政与“学—仕”问题的解答。课程思政还需面对学子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学—仕”关系。这一问题在就学期间尚不明显,但课程教学对于学子将来的“学仕观”则有很大影响。古往今来,学子们都面临着如何处理“学—仕”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孔子时,他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答案,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孔子的话表明,学与仕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实现互转,但两方互转各有一个前提,即做到“学优”和“仕优”,在此基础上方能向对方不断递进转换。《大学》强调“齐治平”之功,但突出“皆以修身为本”,表明外在事功的基础仍是内在的“修”,也就是人的道德修养和学问精进。明代讲会沿袭了儒家这种事业传统,并不反对学子追求功名,但功名需建立在“学”的基础上,因而“学”始终处于优先地位。在《士戒》中,冯从吾特别提到“毋假以送课,遍谒官长,以希进取”,反对在学问未精的情况下投官员所好,以达自己功名目的。在他看来,“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行其势也,非行其利也”[6]97,“义”排除了“势”和“利”的干扰而成为士子出仕的唯一目的。冯从吾也以自己的实际作为将这种理念贯穿其一生。他在举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仍始终不忘讲学,后诤言直谏,辞官回乡,归乡期间惟以读书遣怀为乐事,宝庆寺讲会就是在居乡期间进行的。此后他在官场上又起起落落,但对讲学一直未曾放下,真切诠释了“学—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得以在关学乃至儒学传承中留下应有的学术地位。杨东明、吕维祺二人也有相似经历,他们也深知“学—仕”关系对于士子成长的重要意义,因而在讲会中不断加以申诫。我们现在进行课程思政教学,不妨从传统文化的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中寻找事实依据,理性回应当代学子对于“学—仕”关系的疑问,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学—仕”观,以学促仕,以仕进学,这对于学子人生道路选择,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课程思政与实践精神的传承。课程思政的实质,是要在课程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一种伦理精神和道德情怀,使其在以后的人生事业中始终保持伦理的初衷、道德的初心。这就要求课程思政不能仅局限于道德观念的传递,更需要不断地开展道德实践。这种实践可分为两个层面,教师实践和学生实践。从教师实践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包含伦理的因素,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紧扣教学内容,以自己学识和教学方法,将教学内容中的伦理道德要素适时加以评说。此外,教师应当以身垂范,以行释言。冯从吾一生躬行实践,崇尚气节,他曾说:“为学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6]147又说:“学者须是有一介不苟的节操,才得有万仞壁立的气象。”[6]111因此他才能做到“终日讲学,而若未尝讲学;终日聚徒,而若未尝聚徒。”[6]25杨东明居乡间二十七载,以自身实践将讲学课堂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义学、社仓、助婚、平籴,以至修学、筑堤,无不曲为之所,而敬老、兴学为作人善俗计者,尤拳拳焉。”[5]801吕维祺为官几十年,所到之处,也是大力倡导讲学,并身体力行之。就学生实践而言,它不仅表现为道德感悟式的心理实践,也是将体悟运用于学习、生活、交往等方面的身体实践,并一以贯之地渗透于他的整个人生过程。冯从吾弟子遍天下,他们广为宣扬书院精神,对陕西关学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莫大作用。师生们的讲会实践,磨砺了书生意气,也推动了讲学事业的发展,成为明代教学时空中的闪亮点,由此亦可窥见晚明学术思潮的实学特征以及中国儒学的实践特质。吕维祺所办讲会以德业、举业并重,因此在他的门人中,多直节之士,弟子都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如被称为“咸以为师保父母”的梅长公就是其中突出之人。这些士人通过会讲实践而形成的精思力践、躬行不辍、崇尚气节的精神,实可以作为课程教学的有益思政元素,以此拓开课程教学的伦理丰度和思政广度。如此,方能将课程思政的教学时空展开为大课堂教学,并表现为一个连续性的道德体悟和伦理实践过程。
晚明学者萧良榦论及讲会在士人为学进德过程中的作用时曾说:“顾人心之良,不触则不发;良心之发,不聚则不凝。一番拈动,一番觉悟,一番聚会,一番警惕,此古人所以有取于会也。”[10]其意是指人的心灵只有通过相互激发,才能有所觉悟和提升,而激发的手段正在于当时进行的各种讲会活动。当代课程思政教学,也在于通过触发学子心灵,以点醒他们的内在良知,塑造出学子们成熟理性、具有道德情怀的人格面貌。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将学子培养成具有家国情怀、能放眼大局、具有崇高道德目标的人。陈来先生在谈及明代讲会的个人价值和社会意义时指出:“明代讲会的普遍流行,正表明儒者的心态根本上是超越州县地方的,而向往于伟大人格和文化理想。明代王学的理想、活动、心态都是超地域的,就社会关怀而言,所有儒者都一贯关切其原籍居住地的事务,但作为随时可能进入朝廷和外任要职的士大夫,他们从来没有在根本上放弃对中央政治的改革和全国社会风俗的改进。”[11]我们推行的课程思政教学,也应着意于学子高远人格和高尚文化的形成,着意于培养当代中国所需的“伦理型+”人才。明代讲会的“教学设计”,可以为此给我们提供有益的传统视角,我们应结合新时代要求,在古为今用的文化思路中更好地推动课程思政教学进程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