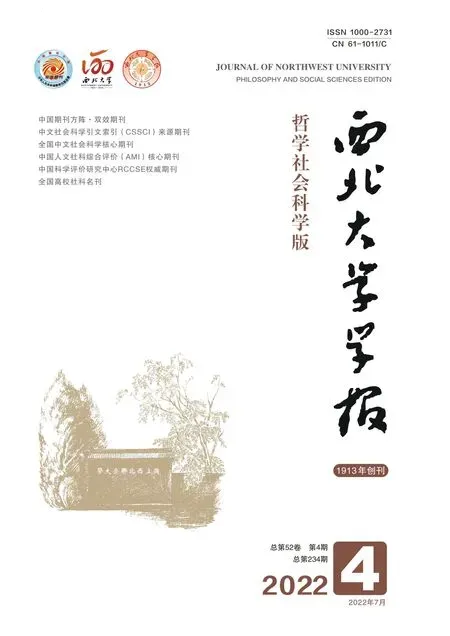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田立刚,樊鹏飞
(南开大学 哲学院, 天津 300350)
推类即“依类相推”,其基础在于对“类”的认识和把握。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推类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广泛应用并深入研究的一种推理”[1]136,是建构理论体系、表达和传播思想的重要方式。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推理本身的称呼”[2]127。推类原则即是作为一种推理类型或方法的推类所要遵循的原则,用以说明如何进行推类和确保推类的可靠性。先秦诸子对推类及推类原则有着丰富的讨论。以儒、墨两家为例:
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的“能近取譬”[3]65“告诸往而知来者”[3]9“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123等观点已经体现了推己及人的推类思想。孟子发展了孔子的相关思想,提出了诸如“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善推其所为而已矣”[4]16的观点。荀子受墨家影响,对“类”与“推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例如“类不悖,虽久同理”[5]97“推类而不悖”[5]501“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5]115不仅涉及了逻辑意义上的推类原则,也对推类提出了政治伦理层面的要求。
墨家基于“故”“理”“类”来立辞和辩说,提出了“以类取、以类予”[6]415的基本推类原则和“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6]328“异类不比”[6]320等具体的取类、推类原则,对辟、侔、援、推等论式也有描述性的规范。此外,墨家对论辩的研究颇为深入,还对“辩”中常见的谬误进行了讨论,其中也涉及了对正确推类的要求和原则。墨子及其后学在论辩等实践中发展了推类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上占据极高的地位,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推类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了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等著作继承且发展了前人的推类思想,并就推类的原则进行了论述。这些推类原则继承了先秦推类思想的特点,既注重思维形式本身的规律,也注重政治伦理和论辩等实践层面的原则。
一、《吕氏春秋》中的推类原则
在整合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吕氏春秋》进一步发展了推类理论,提出了“类同相召”“同构推类”和“类固不必可推知”的推类原则,前者体现了推类原则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征,后者体现了推类原则的实践性特征。针对推类中可能出现的错误,《吕氏春秋》提出了“察”的要求,来应对“推类之难”,提高推类的可靠性。
(一)“类同相召”与“同构推类”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所见知所不见。[7]391
这种由已知推及未知,由部分推出整体,由现象推知本质的实例,表明了《吕氏春秋》对推类重要作用的认识。
《吕氏春秋》认为,万物各不相同,是因为其结构和性质不同,而同类事物也可以因为其属性和结构相同而相互感召,故而可以事物的结构为依据来对万物进行认识和分类,即按照“类同相召”的原则,对同构的事物进行推类。
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7]558
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7]283
根据《吕氏春秋》的观点,天、地、人以及人类社会具有相同的抽象结构,并共同遵循四时变化的节律,故天地与人也可以称之为“同类”,可以相互推类。天地万物被比喻为一人之身,这种类同被称之为“大同”,而人体包含不同器官,天地具有五谷四季,这种内部差异被称为“众异”,圣人就是从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得知其类别,并以此认识世界。
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7]253
此例中,古、今、后世具有同样的结构和关系,因而从当下的状况可以推知古代与后世之事。这即是由同类事物所具有相同的结构或两组具有相同关系的事物遵循同样的规律,而能够进行推类。
“类同相召”与“同构相推”作为推类的依据与原则,具有一定的逻辑意义,是对推类可靠性的抽象要求。但需要注意的是,《吕氏春秋》中的“召”又包含了人为因素。《应同》中有“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7]288从这一角度来看,“类同相召”的原则就“陷于阴阳五行家的迷信,给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开了先河,这是应该批判的”[8]11。
(二)“类固不必可推知”
《吕氏春秋》不仅讨论了什么情况可以推类,还认识到推类并不是绝对可靠的,讨论了“类不可必推”的问题,并将其作为推类的又一原则。这一原则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作为推类对象的事物数量繁多且属性、关系复杂,另一方面是由于作为推类主体的人的认识水平存在相对性和局限性。
其一,“万物殊类殊形”[7]79,即万物类别繁多且各异,具有复杂性,这是从物类的量的角度来看的。同时“物多类然而不然”[7]661,即具体事物本身属性复杂,不能凭直观感觉简单判断其属性及类属关系。
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7]661
大小方形属同类,大小马匹也属同类,但小聪明与大智慧则不然,因为两者本质不同,不能简单类比。甚至原本具有相同属性的事物,在通过某种形式的结合之后,会产生不同的属性,影响人们的判断。例如:
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堇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7]661
莘和藟是两种植物,分别食用均会使人中毒毙命,但混合服用却能使人增寿;漆与水均为液体,但混合之后反而会变得坚硬异常。这种同类事物结合之后发生反常变化的情况表明不能随意依类相推。
其二,人的认识水平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并不能保证对事物的认识准确而全面,如果认知主体对事物的认识出现了偏差,那么就无法正确把握“类”,也无法正确地通过推类得出结论。例如:
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7]663-664
此例中,工匠认为木材尚未干燥,若此时抹上泥巴,随着木材和泥巴的干燥,房屋很快就会变形倒塌;而高阳则认为,木材逐渐干燥会愈发结实,泥巴干燥之后重量也会更轻,房屋一定不会倒塌。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工匠和高阳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体现了认识的相对性。同时,高阳“好小察而不通大理”,可见其认知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此基础上的推理论证自然无法满足可靠性要求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吕氏春秋》对推类的困难有了相对深入的认识,不仅考虑到了事物纷繁复杂这一客观因素,还考虑到了人的认识水平具有局限性这一主观因素。相对于《墨辩》中“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6]318从类的概念外延角度来考虑推类的困难,《吕氏春秋》注意到了物类的内部结构、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从这一角度来看,《吕氏春秋》中“类固不必可推知”的推类原则,是基于对认知活动主客体的深刻理解而对推类做出的规定,相对于“类同相召”“同构推类”原则对推理形式的抽象要求,这一原则强调了对认知实践的要求,体现出了明显的实践性特征。
(三)“察”——提高推类可靠性的方式
为了避免在推类中出现谬误,《吕氏春秋》对如何提高推类可靠性也做了探讨。《吕氏春秋》认为,“失察”是导致认知偏差和推类错误的原因,提高推类可靠性就要依靠“察”。
一方面,针对推类所依据的认识对象,要“察其所以然”。即认识事物不仅要知道其是什么,更要清楚其为何如此,了解事情发生或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7]208
如果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事物的认知就会流于表面,无法触及事物的本质及其因果关系,这样的“知”与“不知”并没有什么区别,迟早会遭遇困难。《吕氏春秋》中以列子学射说明了这一问题:
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于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7]208-209
在这个故事中,列子能射中标靶却不知为何能够射中,关尹子指出这样还不够,直到列子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关尹子才认可了其射术。《吕氏春秋》接着解释道,国之存亡,人之贤与否,都是有其“所以然”的。圣人不仅能够察知这些表象,更能够察知表象背后的原因。因此,必须真正理解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才能正确推理论证和理解社会运转机制。
另一方面,针对认识活动和推类过程,要“缘物之情及人之情”[7]619,充分考虑事物的实际情况和人的因素。具体来看,就是要“察传言”“察疑似”“察微始”“察不疑”[9]151。“察传言”,即经过传播或多次类比之后的言论往往失真,须仔细察验,辨别其真实性。“察疑似”,即仔细察验“类然而不然”的事物,避免直观感觉的偏差导致的将异类误当作同类来比较或推类。“察始微”,就是对推类的出发点,即前提进行辨别,排除错误的前提。“察不疑”,是指不能轻信固有经验或“常识”。
可见,“察”就是对“类固不必可推知”的一种应对手段,即仔细察验事物的类属性、类事理及推类过程,避免在“识类”“推类”等环节出现差错,从而提高推类的可靠性。
《吕氏春秋》中的推类原则,是建立在先秦“类同相推”观念基础上的。基于对类的属性、关系以及人类认知水平的进一步理解,《吕氏春秋》提出了“类同相召”和“类固不必可推知”两大原则,对推类进行了规范,并强调以“察”的方式来认清事物本质和规律,辨别虚假推类前提,保障推类的可靠性。《吕氏春秋》在推类理论上的进步是显著的,尤其是“类固不必可推知”的观点,对《淮南子》等著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受中国古代文化整体特点的影响,《吕氏春秋》对推类的探讨与先秦时期相关理论一样,重点仍在于认识和解决现实问题,因此作为一种推理理论的推类,其研究重点在于推理的内容,并没有从推理形式方面做进一步的探索。
二、《淮南子》中的推类原则
《淮南子》虽以道家思想为主旨,但并未像先秦道家一样陷入超脱尘世的“无为”,而是以一种顺应自然的“积极无为”的态度追求对现实社会具体问题的解决。正如《修务训》中所说:“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10]1322为了更好地认识规律、解决现实问题,《淮南子》十分重视推类的作用,依据“同类相动,异类不感”的观念,提出了“类可推而又不可必推”和“得事之所适,得事之所由”的推类原则。
(一)同类相动,异类不感
《淮南子》继承了前人关于推类的学说,对推类及其原则做了进一步的探讨,例如:
总形推类,而为之变象。[10]982
尝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抱壶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为不知类矣。[10]1215
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务通也,不明于类也。[10]1419
视书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类而取之。[10]1209
众人以为虚言,吾将举类而实之。[10]531
上述文本分别涉及了“推类”“知类”“明类”“类取”“举类”等说法,可见《淮南子》认为“类”是明理、推理的关键。
首先, 《淮南子》认为物类出自自然,并无优劣之分。 一方面, “名各自名, 类各自类。 事犹自然,莫出于己”[10]606, 即世间万物虽事殊类异, 但都依自然、 由阴阳而化生, 并不带有目的性。 另一方面, 万类皆有长短。 《说山训》中有: “桀有得事, 尧有遗道, 嫫母有所美, 西施有所丑。 故亡国之法有可随者, 治国之俗有可非者。”[10]1149即事物的善恶美丑不是绝对的, 不存在衡量物类优劣的绝对价值尺度。
其次,《淮南子》认为物类的同异源自其本质属性的同异,故本质属性相同的事物才可以相互感召。《览冥训》载:“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以其属骨,责其生肉,以其生肉,论其属骨,是犹王孙绰之欲倍偏枯之药,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谓失论矣。”[10]459地黄和甘草两种药物类属不同,分别“主属骨”和“主生肉”,若要令前者生肉而后者属骨,就好比王孙绰试图通过加倍用药来使人起死回生一样,是错误的想法,因为这两类事物原理不同,并不能简单类推之。
此外,《淮南子》还提出,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因客观条件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例如《说林训》载:“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犹客之乘舟,中流遗其剑,遽契其舟桅,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类亦甚矣。”[10]1169这里以“刻舟求剑”譬喻,说明物类是可以变化的,制度也应当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调整,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是“不知类”,会导致“刻舟求剑”式的荒谬结果。
基于上述对类的认识,《淮南子》对推类提出了“类可推而不可必推”的原则。
(二)类可推而不可必推
根据同类相动的观念,《淮南子》认为,类同联系的对象可以依类相推。例如《览冥训》中所举的例子:“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销金,则道行矣。”[10]460根据火能够烧焦木头这一事实,借助这一规律,推出利用火来销熔金属是可行的,即事物间的类同关系是类可推的根据。
类同关系,是基于类的外延关系来判断的。但仅从外延关系进行推类,又存在着困难。《墨辩》就提出过“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6]318,《吕氏春秋》也提出过“类固不必可推知”的观点。但是,《吕氏春秋》只是由一些具体事例得出了推类困难的结论,至于类如何可推,又如何不可必推,并没有明确的解释。在这一问题上,《淮南子》相对于前人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划分物类时,不仅依据类的外延, 还考虑到了类的内涵。 例如磁石可以吸引铁, 但却不能吸引铜, 如果仅从铜和铁同属金属之类而进行推类, 得出磁石可以吸引铜, 就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尽管就金属这一概念的外延来看, 由磁石可以吸引铁, 能够推出其可以吸引铜, 但是, 铁与铜虽然同属金属, 却又各自具有某些特有属性, 决定了其是否具有磁性。 将内涵纳入考量, 这是《淮南子》推类理论相对于《墨辩》和《吕氏春秋》中推类理论方面的一大进步。
具体来看,关于类不可必推的原因,《墨辩》中简要归结为“言多方,殊类异故”[6]417。《吕氏春秋》从对物类自身的复杂性和人类认识水平的局限性两方面进行了粗略说明。而《淮南子》在《吕氏春秋》相应观点的基础上,对类不可必推的原因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探讨。
首先,从物类划分的角度来看,物类表象复杂,难以确认和区分。《淮南子》提出“物类之相摩近而异门户者,众而难识也”[10]1304,因此类不可必推。具体困难包括四种,即“或类之而非,或不类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10]1304。即就分类来说,有些事物看起来类同,但实际上并非同类,有些事物看起来并不属同类,但实际上却是同类,就认识某一具体事物而言,某一事物的本质也可能与人们观察到的表象截然相反。
其次,就全面把握物类属性与关系而言,每一事物都具有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同类事物虽本质属性相同,但又具有不同的非本质属性,反之,异类事物虽本质属性各异,但可能具有相同的非本质属性;事物间的联系更是错综复杂,存在必然联系和偶然联系。因此不能仅凭对事物表象或部分的片面认识来随意推类。例如《说山训》:“膏之杀鳖,鹊矢中蝟,烂灰生蝇,漆见蟹而不干,此类之不推者也。”[10]1154-1155即由事物的表象而非本质推知的结论并不能成立。此外,仅从事物的部分出发,并不能必然推出关于整体的结论,这也是“类不可必推”的原因之一。
再次,在社会领域,由于人为因素的加入,物类“若是非是,若然非然”的情况就更难以捉摸了。
夫事之所以难知者,以其窜端匿迹。立私于公,倚邪于正,而以胜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怀于内者,与所见于外者,若合符节,则天下无亡国败家矣。[10]1308-1309
在现实社会,事情之所以难以捉摸,就是因为人们心口不一,处事常常夹杂了私心,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人为地为事物加上了与实际不符的表象,以此来蛊惑人心,实现其主观目的。这样一来,“若然而不然,不然而若然”的困难就愈发难以应付了。
总之,《淮南子》从思维形式的特点和人类实践的特点两个角度,解释了“类不可必推”的原因,即物类属性与彼此间的联系纷繁复杂,难以把握,且现实社会中人们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会隐瞒实情,导致察物辨类十分困难。相对于《吕氏春秋》的相关内容,《淮南子》不仅对事物的属性、联系的复杂性作了更为细致的分析,还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纳入考量,表明推类不仅是思维层面的推理活动,同时也是掺杂了实践因素的社会活动。
(三)得事之所适,得事之所由
为了提高推类的可靠性,《墨辩》主张辨类不可以片面,即“不可偏观”[6]417。《吕氏春秋》提出了“缘物之情及人之情”[7]619的要求。《淮南子》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针对“类不可必推”的原因,提出了“得事之所适”和“得事之所由”的原则。
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呙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适。[10]1144
第一,“得事之所由”就是要挖掘事物形成或发生的原因,探究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以此来准确把握类和类之间的关系。《人间训》中说:“圣人之举事,不加忧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万人调钟,不能比之律;诚得知者,一人而足矣。……夫车之所以能转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辖。”[10]1301圣人行事从容,是因为其能够明察事物之“所以然”。同理,不明白音律原理,纵使一万人也无法给钟调音,而懂得其中原理的话,只需一人便足以完成。可见,“事之所由”就是事物产生或形成的原因、根据或事物运行的原理,这是理解和把握事物及其类属的关键,好比车之所以能够行驶千里,其关键在车辖三寸之地。
第二,“得事之所适”就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根据时间、事态等条件的变化,灵活把握事物的类属和规律,对推类对象要“各用之于其所适,施之于其所宜”[10]768,才能保证推类的可靠。《说林训》中有:“爱熊而食之盐,爱獭而饮之酒,虽欲养之,非其道。”[10]1222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习性,不能因为爱熊而喂其吃盐,爱獭而使其饮酒,这都违背了其特定属性。又如《说山训》:“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10]1155要根据具体的用途来选择不同的工具,才能提高效率。
总的来说,“得事之所适,得事之所由”就是要准确把握不同对象的因果关系和变化规律,以此辨别物类,进而因类制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遵循这一原则,才能够为推类提供更准确、更全面的依据。
《淮南子》继承了以《墨辩》为代表的先秦逻辑传统和《吕氏春秋》的逻辑思想,在推类理论方面,对类的内涵、“推类之难”以及“类不可必推”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较前人更为细致和明确的推类理论。尤其是其对“类可推而又不可必推”“得事之所由”“得事之所适”等推类原则的讨论,对保证推类过程中思维的确定性与社会现实的吻合性都提出了要求,是对推类学说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淮南子》过于强调“类不可必推”,《览冥训》中谈及“类不可必推”时提出:“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以辩说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论,不足以定是非,……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应者为能有之。”[10]461这体现出其思想受道家影响颇深,带有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其对逻辑思想的消极态度。
三、《论衡》中的推类原则
随着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入了封建神学色彩的儒家学说成为“正统”思想。东汉时期,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11]84,“正统”思想又与谶纬之学结合,思想界出现了许多谬论。王充继承前人“重证验”的思想和科学批判的精神,著《论衡》以批判当时的虚妄谬论,正如《佚文篇》中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12]870“疾虚妄”,即辨别、批判、纠正不实和荒谬之言,为此,王充十分注重推理和论证,并将推类作为其论证理论的重要内容并广泛运用于论辩实践中。《论衡》中关于类和推类有许多讨论。
体同气均,禀性于天,共一类也。[12]328
凡变复之道,所以能相感动者,以物类也。[12]255
同气共类,动相招致。[12]627
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12]1072
先知之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12]1075
王充认为类和宇宙万物的基础都是“气”,同气则共类,可以相互感召,据此推彼,圣人可以凭借推类的方法,由细微推知全局,由开端推知结果,由已知推知未知。除了强调推类以小见大,由近知远的重要作用外,又与前人不同的是,王充在论证理论方面颇有建树,故其对推类的贡献,更多地是把推类灵活运用于包括演绎、归纳和类比在内的论证实践当中。
(一)演绎、归纳和类比推理中的推类应用
关于演绎法,王充在《论衡·自然篇》中论证“天是自然无为”的观点时,运用了带有鲜明演绎性质的推理方式:
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今无口目之欲,于物无所求索,夫何为乎?何以知天无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为体,土本无口目。天地,夫妇也,地体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也。使天体乎?宜与地同。使天气乎?气若云烟,云烟之属,安得口目?[12]775-776
在此例中,王充运用了类似直言三段论式的演绎推理,由“天无口目”推出“天之自然无为”。具体来看,又是多个三段论联锁构成的复合三段论:
先是从“地无口目”(大前提)和“天地对等”(小前提)推出“天无口目”(结论);然后继续从“凡无口目者是自然无为”(大前提)和“天无口目”(小前提)推出“天是自然无为的”(结论)在上述推理和论证过程中,王充的“云烟之属皆无口目”“地无口目亦知天无口目”等观点,实际上是基于其对类的认识而得出的,只有对自然事物的类属关系及物类的属性有所断定,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此例之外,《论衡》中还有许多演绎性质的推理论证案例,不再赘述。
关于归纳法,在《论衡·龙虚篇》中,王充通过枚举《左传》等文献中记载的案例,得出了龙并非天生神物,而是水生之类的结论:
叔向之母曰:“深山大泽,实生龙蛇。”
《传》曰:“山致其高,云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龙生焉。”
《传》又言:“禹渡于江,黄龙负船。”“荆次非渡淮,两龙绕舟。”
东海之上,有菑丘訢,勇而有力,出过神渊,使御者饮马,马饮因没。訢怒拔剑,入渊追马,见两蛟方食其马,手剑击杀两蛟。[12]282-283
在此例中,我们暂且不论王充对“龙”的认识是否准确,仅就其推理过程来看,王充采用枚举的方法,从四个有记载的事例中,得出龙是一种“鱼鳖之类”[12]283的结论。这一推类形式具有归纳推理的性质,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而根据水生这一属性划分类别,将龙归于“鱼鳖之类”,就是推类思想的体现。
关于类比法,在《感虚篇》中,王充对运用类比的方法,说明了“天雨谷”只是风将谷物吹起后落下,而非天自身降下谷物:
夫云出于丘山, 降散则为雨矣。 人见其从上而坠, 则谓之天雨水也。 ……夫谷之雨, 犹复云之亦从地起, 因与疾风俱飘, 参与天, 集于地。 人见其从天落也, 则谓之“天雨谷”。 ……生地之物, 更从天集, 生天之物, 可从地出乎? 地之有万物, 犹天之有列星也, 星不更生于地, 谷何生于天乎?[12]251-252
在此例中,王充以正常降雨做类比,指出“天雨谷”与之同理,是因大风将地面的谷物吹起卷至他处,风力减弱后谷物落下,人们便误认为是天降谷物。此外,他还补充说,地有地生之物,天有天生列星,谷不可能生于天,就如同星不可能生于地,这可以看作是归谬式的类比推理。即如果谷可以生于天,那么地上就可以有星星,但地上并没有星星,所以谷也并非生于天上。
综上可见,王充在其推理论证的实践中,已经能够综合运用具有类比、演绎、归纳性质的推类方法,表明其对推类的形式化认识比前人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王充在论证实践中对推类方法的灵活运用也体现了推类的实践性特征。
(二)“论贵是,事尚然”
相比前人“推类不悖”或“类不可必推”这样明确的推类原则,王充思想中的推类原则也是融合在其论证理论当中的,他对推类和论证提出了“论贵是,事尚然”的要求,这体现了一种“同一”的原则。
在形式逻辑中,“同一律”是基本规律之一,它是对思维形式确定性的要求,即在同一思维过程当中,同一个概念、判断和思维对象必须保持同一。这体现在论证或论辩中,就要求论证过程涉及的相同概念和判断必须前后一致,论辩双方所讨论的论题、双方所使用的相同概念或判断也要彼此一致,否则便会混淆概念或论题。
王充推类思想中的“同一”原则,既包含了类似“同一律”中对思维形式本身的同一要求,也包含了对思维形式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同一要求,即“夫比不应事,未可谓喻;文不称实,未可谓是也。”[12]145王充指出,作为思维过程的取类、推类应当符合实际情况,不能凭空捏造或主观臆断,不符合事实的类比和论证话语都是不成立的。这一观点的提出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直接关系,为了破除由于谶纬迷信的盛行带来的虚妄谬论,他特别强调推理论证中实事求是的重要性,明确提出了“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12]1197的主张。“论贵是”是说论证或论辩要追求论题的正确性,而非不知所云的华丽表述。“事尚然”是说论证或论辩要追求论据的真实性,即符合实际情况,而非凭空附和他人的观点。两者结合,就要求人们在论证过程中,要立足客观真实,实事求是,避免绮语妄言或人云亦云。
(三)“引效验,立证验”
为了使推类和论证达到“论贵是,事尚然”的目标,排除虚语空言,王充提出了“引效验”和“立证验”的具体要求。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12]1086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12]1183
“引效验”就是引用事实论据来验证论题。倘若论证时违背客观现实,不以事实论据来佐证论题,那么即使论题再有道理,论证过程再繁复,人们也不会信服。这是从事实和实践的角度对推类和论证的要求。“立证验”就是通过有效论证来证明论题成立。虚妄之言之所以能够混淆视听,一方面是人们没有明辨客观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不能通过正确的推理和论证过程来获得正确的结论。因此,要使论题的真实性得到证明,除了论据的支持,还要经过合乎逻辑的论证过程来完成。这是从形式和思维的角度对推类和论证的要求。
可见,王充提出的“引效验”和“立证验”的要求,从论据和论证过程两个角度,对提供论证有效性做出了规范,前者强调的是事实证明,后者强调的是逻辑证明。就这两者作为推类原则所反映出的特点而言,前者体现了现实和实践性,后者则体现了形式和思辨性。
王充逻辑思想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包括推理、证明与反驳等在内的丰富的论证理论。正如周文英所评价的那样:“在中国逻辑史上,王充的创新和贡献是把论证作为一种自觉的逻辑手段而加以运用。”[13]75同时,王充著《论衡》的目的,就在于针砭时弊,以逻辑的工具来破除妄言谬论,澄清社会风气。因此,王充融汇于论证理论中的推类思想及其提出的推类原则,不仅体现了高度的思辨性,还在继承先秦逻辑思想的基础上,发挥了逻辑的批判性作用,无论是目的还是实际效用都体现出了强烈的实践性特征。
四、秦汉时期推类原则的思辨性与实践性特征
推类是在中国古代特有的文化背景下,基于事物之间类同的关系所进行的推理方式,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世界整体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密切联系的感知和把握。通过对《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推类原则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推类以及推类原则思想总体上具有思辨性和实践性两大特征。
一方面,推类作为一种推理类型,其基础是对“类”的自觉认识。在这一点上,推类与西方传统逻辑类似,作为西方传统逻辑源流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就被认为是“类的逻辑”[14]34和“类与类之间的基本关系的理论”[15]81。推类理论中所体现的对物类外延的划分和对类之间关系的思考,表明了人们对不同事物及其联系的抽象认识,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对同一律、类比法等形式逻辑基本规律和推理方法的朴素认识。《吕氏春秋》中的“类同相召”“同构推类”原则,《淮南子》中的“同类相动,异类不感”原则,《论衡》中对演绎、归纳、类比等逻辑方法的朴素应用,都体现出了推类这一思维形式的抽象性和思辨性特征。
另一方面,推类与形式逻辑中的推理不同,并不注重对推理形式的严格规定,而是更关心推理的内容。例如《吕氏春秋》在讨论推类之难时,不仅认识到了事物纷繁复杂这一客观因素,还考虑到了人类认识水平具有局限性这一主观因素。相对于“类同相召”“同构推类”原则对推理形式的抽象要求,基于认知主体、认知能力而提出的“类不可必推”原则体现出了明显的实践性特征。《淮南子》指出现实社会中,人们心口不一,出于主观目的故意制造假象,带来了诸多“若然而不然,不然而若然”的问题,因此推类须“得事之所适,得事之所由”,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王充在《论衡》中也明确提出了“论贵是,事尚然”和“引效验,立证验”的主张,强调推理论证要符合客观事实。这些出于对现实因素的考量而提出的原则,体现了推类作为一种知识应用的现实性和实践性特征。
正如康德所说:“一切兴趣最后都是实践的,而且甚至思辨理性的兴趣也只是有条件的,唯有在实践的运用中才是完整的。”[16]167推类和推类原则同时体现了思辨性和实践性,这并不难理解。推类是中国古代特有的一种认知方式,同时也是这种认知方式的具体应用,本身就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紧密关联,并天然带有某种目的性。一方面,推类理论的形成离不开实践过程中的学习和积累,并为人们认识世界、宣扬主张等具体目的而服务;另一方面,具体应用让推类这一认知方式的合理性得以实现,人们还可以通过实践来反思和发展推类理论。因此,思辨性与实践性二者统一于作为认知和实践主体的人。
此外,推类和推类原则之所以具有思辨性和实践性的特征,离不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国古代逻辑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整体的一部分,作为中国古代逻辑的主导推理类型的推类,必然在某些方面体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特点。推类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而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化特别关注道德与政治这两方面问题,即“以人际原则为中心的伦理问题和以治乱为中心的政治问题”[17]113。具体来看,对道德问题的重视是为了让人们认识并明确个人在群体、社会当中所属的位置,并遵循相应的处世规则,代表了一种“求善”的需要和文化追求;对政治问题的重视是为了寻找最妥当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国家组织和社会运行能够有序、高效,体现了一种“求治”的现实追求。这一时期的文化特质,使人们形成了一种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应用为载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追求对新知识的探究或抽象理论的建构,而特别注重对自身思想主张的宣扬和对异见者的批驳。
因此,推类作为一种推理类型,其现实需求就是人们宣扬其思想道德和社会政治主张的论证实践,这就使得推类必须深度结合推理和辩说的具体内容,追求说理论辩的实际效果,以说明事理、晓谕他人为第一要务。从这一角度理解,推类及其原则所体现的实践性特征,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特征和现实需要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秦汉时期,思想界已经不再像百家争鸣时期一样活跃,但新的历史时期依然存在理论宣讲的需求,源自先秦的推类及推类原则思想,自然也继承了其思想源流的实践性特征。
五、结 语
“对‘类’概念的自觉认识是逻辑学赖以产生和建立的基础”[18]178。中国人对“类”的认识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在继承先秦时期推类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规范推类的原则。一方面,这些基于对“类”和类属关系抽象认识基础上的推类及推类原则思想,体现了其作为一种推理方式的思辨性特征。另一方面,受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这些推类原则也反映了强烈的针对道德与文化的“求善”追求和针对现实政治的“求治”需求,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从推类原则的角度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进行考察,并通过“思辨性”和“实践性”两大特征来审视这些推类原则,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推类这一中国古代主导推理类型。同时,对我们立足具体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之特殊性亦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