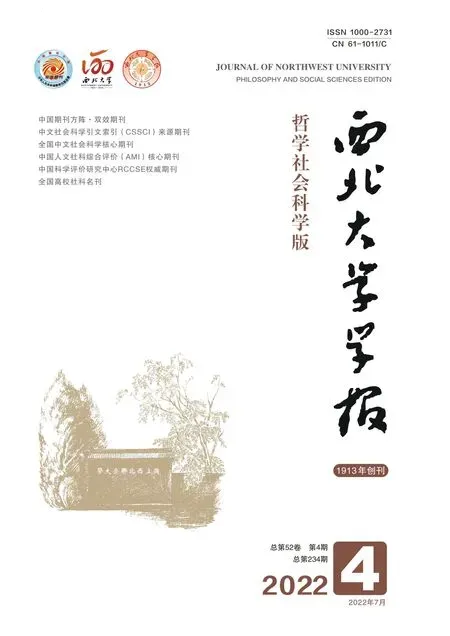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时空美学
——“场所”的相位与历史时间
霍士富,陈汝倩
(西安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大江健三郎从《饲育》(1958)获得芥川文学奖登上日本文坛,到《晚年样式集》(2013)作为“最后的小说”封笔,其间经历了几个转型期,但小说舞台始终围绕故乡的土地与“场所”(Topos)——四国森林“峡谷村庄”展开不断重构,最终建构了一系列凸显这一时空张力的、多重结构的神话世界。大江说:“小说是描写人物的艺术,但如何反映小说中人物与作者扎根的土地与场所,将决定其真实性(reality)。”[1]120也正是基于这一创作理念,建构在这片土地上的艺术作品,在承袭“既有的美学理念——形式(Forn)与内容(Inhalt);形态(Gestalt)与内包(Gehalt);现象(Erscheinung)与意味(Bedeutng);实在(Realitat)与理念(Idea)等二元对立、及其融合与统一”[2]之基础上,又融入多声部的叙事主题和多种音色交响的叙事要素,最终形成了凸显大江文学风格的时空美学。
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作为其故乡的土地与场所初次登场于《饲育》。大江曾说:“这一场所的地形学特征,实际上与我成长的森林中的峡谷村庄相似。……不过,通过该小说的书写,将位于四国山间的现实中的这一村庄‘化为无有’。同时,该小说中描写的想象宇宙,在鲜活而真实的神话与民间传说之构造上,奠定了此后作品的根基。”[3]30那么,大江为何在其创作生涯的一系列作品中执着地追求和反复建构故乡的土地与场所呢?在其之后的重要作品《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同时代的游戏》(1979)、《M/T与不可思议的森林物语》(1986)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1987)中,这一叙事空间又发生怎样的变奏?对此,川西政明认为:“从《饲育》到《拔芽杀仔》的‘峡谷村庄’,是在平面上建构多重化的虚构空间,而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此空间则演变为立体构图。因为单纯的平面构图,无法保障虚构的‘峡谷村庄’的实在性。在生的原理追求恢复秩序时,‘峡谷村庄’的虚构性必须在历史的虚构性中实现。”[4]此见解不仅洞察到叙事空间“峡谷村庄”的变奏——从平面构图演变为立体构图,而且指出此空间的意义必须在“历史的虚构性”中实现。在此,“历史的虚构性”的提出对大江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对大江文学而言,历史与神话作为拓展小说空间的两极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小说空间的地形学构造与历史时间之关系,大江告白道:“我是通过不同登场人物的想象力,对‘村庄’之‘场所’进行虚构和变形,同时特别重视地形学的构成要素。即我是通过历史时间或登场人物的不同视角,变革‘村庄’的地形,而非始终保持固定的地形构造。或者说在共同的无意识中有个原点,从外部看是歪曲的地形,而在内部人心中,这一变形的地形学构造是将过去与未来融为一个整体的、时间×空间的集合(unit)。”[5]6此告白披露了两个重要秘密:一是“峡谷村庄”的地形构造在其不同的作品中,不断发生演变;二是此空间是将“过去与未来”融为一个整体的“时间×空间的集合”,体现了大江文学的时空哲学。那么,大江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是如何建构其时空美学的呢?本文将运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美学和本雅明的历史时间哲学,首先从“峡谷村庄”的地形学构造切入,探讨其叙事空间的造型艺术,接着以小说脉络中的历史时间和圆环时间为线索,分析其时间哲学的深层内涵,最终透视大江文学的时空美学。
一、“缩减模型”的空间结构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在《野性的思考》(1962)中根据造型艺术明确表示:“作品在多重意义上表现为‘缩减模型’(modele reduit)。比如,宗教建筑中象征宇宙的绘画是缩减模型;即使是与‘实物等同’的艺术作品,如果是绘画则在体积的次元;如果是雕刻则在色彩、韵味和触感的次元。”[6]29因此,“缩减模型”是整体认知先于局部认知;是用知性次元的幻想补偿感性次元的断想,进而将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小宇宙”去构建。
大江在《饲育》中营造的小说舞台四国森林的“峡谷村庄”,虽仅初现神话空间的雏形,但足以体现“缩减模型”的空间结构。周围被灌木和森林环绕的“峡谷村庄”,因夏季以来持续的梅雨、进而发生“洪水”,冲断唯一与外界连接的“吊桥”。大人们不得已去村外时,只能沿着崎岖的山路绕道而行。“我”和弟弟就住在位于村庄中央公用仓库的二层;大人们在山里捕获的、从飞机上降落的“黑人士兵”就饲养在“我”家的地下仓库。由此形成内外空间的对峙——“峡谷村庄”与外部的战争空间,以及内部空间的三重结构:村庄、家和地下仓库。对此,大江率直地说:“这一短篇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首先它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少年在超国家主义的日本社会中体验的、我的主题系列之一。且最为根本的问题是该短篇描写了一个想象宇宙的‘结构’和‘场所’。”[3]14所谓“想象宇宙”就是“人们在生活和意识中,超越制度的规定和约束,动员感觉去理解某物,又称象征宇宙”[7]221。而植根于村庄的土地与“场所”,则与牛顿的物理学空间不同,其空间特质虽也向纵·横·高延伸,但它必须脱离抽象空间和均质空间而获得自由。其特点:“一是自然场所的性格。作为物必须各归其位,有上下、前后和左右之分;二是具有容器的性格。作为场所既有一定的空间延伸,也能容纳它物。”[8]142基于这一“场所”理念,小说中建构的叙事空间将呈现出:象征性场所——区别于世俗空间的、神圣空间和神话空间,诸如山顶、森林等;身体性场所——心与身体,或精神与身体相区分的实体存在。即人的意识或精神是身体的变形。《饲育》中建构的叙事空间“峡谷村庄”,首先是森林环绕的“自然场所”;而位于村庄中央的“家”和地下仓库,将作为“身体性场所”发挥作用,由此奠定了大江文学的神话空间。比如,饲养在地下仓库的“黑人士兵”之死,就是体现人的意识或精神在身体上的变形。当父亲挥舞的钁头砸下时,“我”的左手与“黑人士兵”的头颅顿时变得血肉模糊……从那一刻起,“我”不再是孩子了,童年时代的世界已与“我”无缘。由此实现了肉体死亡与精神成长的相互辉映,乃至其美学意识“死与再生”。
如果说《饲育》中建构的“峡谷村庄”孕育了神话空间的雏形,那么《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则在此叙事空间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和完善。前者通过从天而降的“黑人士兵”暗示外部空间与“峡谷村庄”的对峙、后者则将“二战”背景的外部空间演变为“安保斗争”(1960)的东京。“安保斗争”失败后,“根所”家族的“我”(蜜三郎)和弟弟(鹰四)、以及酒精中毒的妻子(菜採子)和智障儿子一同从东京返回故乡“峡谷村庄”,探寻人生意义。由此形成东京与“峡谷村庄”的对峙。首先,作为外部的象征性空间是“净化槽”。黎明前,蜜三郎和狗一起睡在院子施工挖下的“净化槽”里。他为何如此消沉呢?其原因有三点:一是不久前他的好友因参加“安保斗争”,头部被警棒打伤而精神失常,自杀前用涂料将头和脸涂成红色,肛门里插上黄瓜,赤身裸体地吊死在家中;二是妻子因儿子出生时头部长着大瘤子,手术后成为智障儿而酗酒中毒;第三,弟弟(鹰四)因“安保斗争”的失败,从美国巡回演出归来意志消沉。对于像洞穴式的空间“净化槽”,若桑绿指出:“小说开头,他自己下降到净化水用的人工地窖,这不是为了上升地上挖出的寻‘根’空间,而是暗示不毛之地,也是自闭症的象征。……自杀友人的头部染得像‘蔷薇花’,尸体上散发着‘百合味’,则洋溢着神话韵味。从古到今,英雄或美男子的尸体,都盛开美丽的鲜花。耶稣的血液盛开了红色的蔷薇花;圣母的尸体上盛开了象征纯洁的百合花。”[9]此见解从神话层面将“友人”之死定格为英雄的殉难,既肯定了“安保斗争”的价值和意义,又突显了此运动的失败对战后年轻一代的打击。也正是以“友人”之死为契机,“我”才带着弟弟和家人,为探寻人生的出路,返回祖先“根”之所在的“峡谷村庄”。
“我”和弟弟及家人坐着大巴,从暗黑的“峡谷”底部穿越森林时,车突然发生故障停下,四周的氛围令人窒息。对此,叙事者“我”叙述道:
尽管“我”在森林深处长大,但每当穿越森林回到峡谷时,总是无法从令人窒息的感觉中获得自由,窒息的感觉中枢充溢着死去的祖先们的感情之髓。他们在强大的长曾我部追击下,不断深入森林深处,发现一处仅能抵抗森林侵蚀的纺锤形洼地,便定居了下来。洼地里冒出优质的水,逃亡小组的统帅者、也就是我们家族的“第一男”,凭借想象力朝着洼地,莽撞地闯入幽暗的森林深处之时的感情之髓,与令我窒息的管道相通。[10]76
在此,“森林”与“水”首先以象征生命力的符号突显出来。因为植物周期性地呈现死与再生的现象,象征着人类死与再生的生命循环体系。就是在这块“纺锤形洼地”上,“根所家族”在院子中央建起了“老屋”,且在房屋下构筑了“地下仓库”。若桑绿认为:“这一古老建筑呈典型的‘曼陀罗’构图,平面图由同心圆构成,立体图则由位于‘中心’的一根重轴形成上下结构。即‘同心圆’的‘中心’是兄弟两祖先留下的‘老屋’,其周围是村人居住的峡谷,外围环绕着森林。从立体构图来看,‘老屋’就像一棵巨树的‘根’,直通隐蔽在下面的‘地下仓库’。或者说,仓库的上面居住着属于统治阶级的‘曾祖父’;下面居住着农民起义首领‘曾祖父的弟弟’。弟弟旨在破坏这一秩序,结果死去,留下这个‘地下仓库’。它就是这个家族的‘根’之所在。”[9]此见解非常形象地勾勒了“峡谷村庄”的地形学构图,对我们理解象征小说空间的“缩减模型”很有启发。位于“根所”家族中央的“老屋”的平面构图,是由“同心圆”构成,且以此圆为“中心”,周围是村人居住的峡谷,外围是环绕村庄的森林,由此完成了以“根所”家族为“中心”的村庄构图。再从此古老建筑的“立体构图”来看,位于院子中央的“老屋”就像一棵巨树,形成以树干为重轴的上下结构。此“树”上通“天”“根”入地,并直通隐蔽在下面的“地下仓库”。更为重要的是,“地下仓库”曾经是“万延元年”领导农民起义的叛逆者“曾祖父的弟弟”居住的地方,而且,最后死在这里。也就是说,居住在“地下仓库”上面的“曾祖父”,象征着秩序的统治阶级国家机构;而在其下面度过一生的“曾祖父的弟弟”,则象征着推翻秩序的、反国家机构的存在。由此完成了“峡谷村庄”的地形学构图。如今“我”的弟弟鹰四,决心效仿“曾祖父的弟弟”的行为,发动以“足球队”为组织的暴动,带领村民将“超市天皇”的货物洗劫一空。暴动失败后鹰四自杀,蜜三郎接纳妻子与弟弟怀孕的未出生的孩子,继弟弟之死后获得新生,进而完成系在祖先“根”上的“死与再生”的轮回。
“峡谷村庄”的地形学构图发展到《同时代的游戏》后,形成由“大岩块”部位的“颈”状地形结构,表现为内部空间“村庄·国家·小宇宙”与外部空间“大日本帝国”的对峙,在主题上实现了“边缘”(“峡谷村庄”)与“中心”对峙的突破。再到《M/T与不可思议的森林物语》后,将位于“边缘”的“峡谷村庄”形象化地称为“瓮村”。所谓“瓮”又称“瓮棺”,隐喻“死亡”之村,而“死亡”同时也孕育“诞生”。至此,“峡谷村庄”真正从土地与场所的层面,以“缩减模型”的多重结构完成了“村庄·国家·小宇宙”的神话构图。但此构图的实现还“需要在作品引入最为本质的时间性。将时间性纳入作品结构并加以无化,不仅可以确保结构的成立,而且能够克服时间与结构之间的裂痕”[6]157。下面我们就来看“缩减模型”的时间性。
二、“过去优先论”的历史时间
基于对通俗的时间论——过去的现在、当下的现在和未来的现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同一的同质时间——之批判,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首先明确提出:“时间来自未来”的时间论。他认为:“人的行为首先是明确目标,制定将来有可能实现的‘企划·构想’(project),然后据此否定所与(过去)、并加以变形。即在此否定行为中,边否定和边形自己的所与;边制作以前没有的‘新事物’。‘企划’是指未来性;所与是指过去性;行为是指现在性。在此三个时间相位(aspect)中,发端(initiative)始于未来行为是时间。因此,时间来自未来,同时将过去拉回到现在加以变形,制作新的事物。”[11]175本雅明(Walter Bendix Schoenflies Benjamin)虽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历史时间学理念,但又有所不同。对本雅明而言:“构想未来和成就自己的现存在,并不是主要问题。他认为希望存在于他者(过去的死者们),而非现在的我们。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回答以过去可能态存在的死者之‘希望’——倾听死者们的声音,努力实现其期待。”[11]177-178可见,与海德格尔“未来优先论”相比,本雅明的历史时间是“过去优先论”:追溯“过去”,并将其拉回到“现在”,用行为给予“过去”否定和变形,创造“新事物”。纵观大江文学的创作理念,其时间哲学显然是后者。大江说:“《万延元年的足球》的最初计划就是历史小说,以万延元年为起点追溯现代、特别是百年后安保年的历史时间。”[12]61在此,追溯“万延元年”是倾听“死者”的声音;由此推及“现代、特别是安保年”是行为;而完成“死者”的“希望”才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死者的奢华》(1957)开头就从描写二战末期“死者们”的心声切入,然后刻画生活于现在、特别是战后一代青年的现实世界。“浸泡在浓褐色液体中的死者们,用厚重的声音在窃窃私语,无数的声音在交头接耳很难听懂。”[13]7这些窃窃私语的“死者们”究竟在诉说什么呢?小说中写道:
关于战争,无论身怀多少观念的家伙也没有我有发言权。因为我自从被杀后一直浸泡在这里。
我看见士兵的腹部有枪伤,唯有那处似枯萎的花瓣,比周围的皮肤又黑又厚,颜色发生变化。
战争时你还是孩子吧?是,正在成长![13]24
平野荣久指出:“叙事者‘我’与既非人也非物的尸体,以内心对话的形式,深化了对问题的思考和印象,并将其升华至象征的高度。”[14]28此见解从叙事者“我”与“死者”的“内心对话”产生的艺术效果给予高度评价,无疑很有启发。但从这段对话中不难发现:死者还是孩子时就在战争中被枪击而死。即这个青年士兵的死,正如其腹部“似枯萎的花瓣”所象征的那样,在其人生的道路上尚在开花期就已“枯萎”,可见其内心的委屈和对战争的哀怨——“关于战争,无论身怀多少观念的家伙也没有我有发言权”。这就是叙事者“我”在搬运浸泡在医院地下室的“药水槽”里,供解剖用的尸体时,通过视觉、触觉和听觉领悟到的“死者”的心声。也就是说,隐含作者将叙事者“我”置于被战败和被美军占领的“现在”,去倾听二战中死去的“死者”的心声,进而实现让“死者”亲自控诉战争的罪恶;令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和思考何为战争的艺术效果,最终抵达作家和读者在“同时代性”的高度,共同投入反战运动,使“死者”的灵魂得以救赎。
《饲育》中叙事者“我”同样是立足“现在”,追溯二战末期(1944)发生在“峡谷村庄”的悲惨记忆,进一步深化大江文学的反战主题。太平洋战争末期,空袭日本的美军飞机被击落,村民们连夜在森林深处捕获了驾驶美军飞机的“黑人士兵”,像动物一样饲养在村里的地下仓库,并由“我”和弟弟、及其村里的其他孩子负责给他送饭。不久,“我们”就与“黑人士兵”建立其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并带他去河里洗澡。小说中写道:
我们突然发现,黑人士兵像英雄似的、堂堂正正地长着一个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殖器。我们绕在他的周围,用裸体的腰部互相磨蹭、嬉闹,不断地将水泼向他的生殖器。他用手握着生殖器,其英姿就像公山羊挑战时一样剽悍。我们笑到流着眼泪,还在用水泼他的生殖器。[13]148
可是,就在孩子们与“黑人士兵”建起童话般的世界时,大人们突然接到上面的通知,要将他送到“县上”去。当他意识到自己很快要被送走,进而被处死时,乘“我”给他送饭之际,将“我”作为人质控制在“地下仓库”。不久,父亲为了救“我”,将“我”的左手与“黑人士兵”的头颅一同砸碎。对此,川西政明认为:“《饲育》中存在美,但缺乏生的哲学。”[4]此见解显然是误读。因为“黑人士兵”的身体美,象征着其人性美,而且他身上这种美在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体现得淋漓尽致,由此与大人们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他那像英雄似的剽悍英姿,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殖器,不正是生命力的体现吗?然而,孩子们的美好童年;“黑人士兵”身上的人性美;一切都被大人们的所为——“父亲”的钁头击得粉碎,战争彻底地将人性异化。如果说《死者的奢华》重在倾听“死者”的声音,那么《饲育》则旨在通过追溯“我”的亲身体验,用血淋淋的史实控诉战争的罪恶。其共同指向是以“现在”的反战行动,将“过去”的历史加以变形,进而重构新的未来。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历史时间在叙事结构上表现得更加娴熟。万延元年(1860)和安保运动(1960)相隔100年,在小说中却遥相辉映,形成了“过去”的历史事件与“现在”的反美运动,在性质上重叠的二重结构。或者说,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陷入绝境的“我”、弟弟和妻子,穿越到100年前的“过去”,探寻“生”的意义和根据。蜜三郎“我”是因1960年秋天,友人突然用奇怪的粉装自缢而“死”深陷困境;弟弟鹰四是因“安保斗争”的失败而陷入绝境;“我”的妻子是因智障儿的诞生酗酒成瘾。那么,“过去”的历史事件又是如何呢?万延元年发生灾荒,曾祖父的弟弟带领民众暴动,强迫藩主废除了地租制。这次暴动虽取得了这方面的胜利,但不久该组织崩溃,许多参加暴动的年轻人被官府杀害。据说,此时曾祖父的弟弟独自逃出高知县,去东京的维新政府登上显赫官职度过了一生。对此传说,蜜三郎信以为真,认为曾祖父的弟弟背叛了暴动的宗旨,而鹰四却不以为然,认为革命家的自我同一(identity)不可能半途而废。不仅如此,对于1945年从海军复员回来的根所家族的次男S君,为了制止朝鲜部落长乘机牟取“大米”的暴利,带来村里的青年人袭击部落时,被对方杀害的事件,兄弟俩也持不同见解。即鹰四认为S君的死亡和曾祖父的弟弟的自我同一性质相同,并给予积极的、肯定的评价;而蜜三郎却始终持消极的、否定的评价。因此,鹰四决心效仿死者的行为,与祖先们获得灵魂上的统一。于是,在“峡谷村庄”将年轻人组合成“足球队”,以暴动的形式带领村民横抢朝鲜人经营的“天皇超市”。超市的货物洗劫一空,可是暴动最终失败。于是,鹰四便用火枪对准自己的脑袋自杀。不久,“超市”的老板收购蜜三郎家族的“老屋”,在将其拆毁时蜜三郎发现老屋下面有一个地下室,由此证明万延元年曾祖父的弟弟没有去东京,而是隐藏在地下室继续领导农民起义。至此,一直站在对立面的哥哥终于理解了弟弟的所为,并接纳了弟弟与妻子通奸怀着的孩子、以及智障儿,进而获得新生。即弟弟的“死”成为哥哥“生”的契机,由此完成“死与再生”的自我同一,以及历史时间1860年、1945年和1960年的重叠与重构。因此,“过去优先论”的历史时间旨在打破对空虚未来的期待,刷新“过去的印象”,实现“解放和救济死者的希望”。也正是在此理念的驱使下,大江文学继《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到《同时代的游戏》发生了“第三次转型”,从“过去优先论”的转向“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
三、“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
大江文学的创作理念为何如此执着于对“过去时间”的追溯,进而从“过去优先论”转向“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呢?他说:
如何记忆过去,如何选择和维持过去的记忆,以及如何有选择地建构过去记忆,将决定拥有该记忆者直面现实的态度。……或者说,歪曲过去的记忆,仅凭一己的记忆为现实中的自己辩护的人,对未来的也是牵强或敷衍地做出单项选择。像这种单项的未来选择,在过去、现在乃至未来惯性的延长线上,必将决定其人格。[15]35
可见,大江文学对“过去时间”的执着,是源于他对“过去记忆”的认知和世界观,也体现着其人格的发展和成熟。也正是基于这一对“过去记忆”的世界观,才由“过去优先论”发展为“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那么,何为“圆环时间”?在大江文学中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今村仁司指出:“圆环时间就是建构在自然循环根基上的、封闭的圆环反复,也是以过去为中心的时间意识。如果说由同一事物的反复形成的循环印象,是基于传统的价值规范为核心的生活方式,那么复归原状理念的时间表象就是圆环时间。”[16]43-44可见,这一时间理念有两个关键概念:①以自然循环为根基,是同一事物的反复形成的循环,如四季循环或历法。②此时间意识只有现在和过去,彻底将“未来”排斥在外。对现存在而言,假如有一个相当于“未来”的时间,那就是“死者的世界”。但它不是“未来”,而是“别的世界”,又称“永远的世界”,但“永远”在定义上已不是时间的世界。这一时间理念首先主要表现在《同时代的游戏》和《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
《同时代的游戏》以叙事者“我”寄给“妹妹”的六封信为结构,通过追溯过去“峡谷村庄”的神话和历史,书写在这片土地上绵延了几百年的“破坏者”的“死与再生”。据传说“破坏者”活了几百年,已成为巨人还不死,而且在村里经常发出刺耳的“怪音”。于是有个生活在村里最底层的人秘密将“破坏者”毒杀,并把其尸体肢解成碎片埋在遍布森林的各处。如今,叙事者“我”为了将“破坏者”的所有尸体碎片收集在一起,用了六天时间走遍森林,在“我”面前出现作为分子模型的硝子玉、蘑菇、洞穴和鞘等各种象征生命的东西。川西政明指出:《同时代的游戏》中“作为暗喻‘破坏者’的再生,与小说的文脉中许多符号融为一体,诸如蘑菇、洞穴、鞘、以及荚等。”[17]而对于“峡谷村庄”的创造者为何是“破坏者”的构想,大江告白道:“我曾幻想这个古老村庄的来源。起初是从外部村庄逃出的年轻人,来到这片森林建立属于自己的村庄。可是,不久这个村庄就会破坏掉,进入下一个世代。即这个破坏者实际上与最初在这片森林里建立村庄的人,属于同一存在,这就是贯穿小说的历史观。”[18]146从以上两点不难看出,该小说通过追溯过去“峡谷村庄”的神话和历史,表现作者的“历史观”,这是其一。其二是这一流传于“峡谷村庄”的“破坏者”的“死与再生”的神话,就像在大地上播种植物一样,只要有种子(“破坏者”的肢体碎片)播下,无论过去多少年,走进森林就会发现这一植物的后代,并随着四季的更替,在“死与再生”的圆环上延续着代代不息的生命。
这一时间哲学在《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得以继续发展,所不同的是前者从“破坏者”的“坏”字切入,而后者是从“怀”字着手。在《同时代的游戏》的第一封信中,叙事者“我”在墨西哥写给妹妹的信中写道:“妹妹啊!你曾这样问我:我一直没能记清‘破坏者’的名字,将‘坏’字和‘怀’字混为一体。于是经常把‘破坏者’的名字错记为‘怀念者’。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时,觉得‘破坏者’有种不可思议的魅力,为什么是‘破坏者’呢?”[19]85可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这两部作品在圆环时间的建构上究竟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致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对“怀念的年代”写道:“我看着‘光’的侧脸,脑海中浮现出‘怀念的年代’一词。义兄曾将从柳田国男那里引来的‘怀念’,与‘美丽的村庄’组合在一起使用。我在‘怀念’后面附加上‘年代’,组成‘怀念的年代’,就好像地图上的一个场所。”[20]121芳川泰久指出:“为何要将‘怀念的年代’作为地图上的一个场所去认知呢?……因为如果我回到那里,则会遇见:年轻时义兄所在的‘怀念的年代’;去都市生活后没有失去的、年轻时我所在的‘怀念的年代’;不是在鸟山福祉工厂作为智障工人,而是美丽、睿智的孩子光所在的‘怀念的年代’。就这样,‘怀念的年代’不是单纯的物理概念上的过去时间,而是‘另一个我’和‘另一个光’所在的时间。对此,我将会写出怎样的信呢?或者说,我又如何把这一不可能的时间,用怎样的语言将其唤回到‘现在·此处’呢?”[21]此见解提出的关键问题是,现在的“我”、义兄和光,回到“怀念的年代”去见过去的自己。此时,这一“怀念的年代”则是场所,而非时间,而用圆环时间中的概念理解,此时的“怀念的年代”则演变为“别的世界”或永远的世界,但这里的“永远”在定义上已不是时间。也许正是基于这一时间哲学的思考,小说中引出了“永远的‘梦’之时”。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信仰,或宇宙观·世界观。曾在远古时代的“永远的‘梦’之时”,曾经发生过非常重要的事情。其想法是在当下现在“时间”中的生死者们,只不过是重复着同一行为而已。不仅是澳大利亚的原住民有此想法,而且在世界各地都有。……那个重要的事情其实就是“永远”,它也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时间”之梦。如果要具体问在什么地方?那就是环绕“在”和峡谷的“森林”。这一源于死者的灵魂与森林纠结在一起,森林中的“永远的‘梦’之时”的规范,无疑也影响着当下尘世中的生死观[20]122-123。
津岛佑子认为:“著者基于‘永远的‘梦’之时’的联想,‘无论是我的生还是我的工作,都是为了实现这一梦幻,每天不停地做各种准备。’即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生,这样的工作,好似人人都知道这个终极的梦……”[22]此见解将“永远的‘梦’之时”与现代人“现在”的生和工作联想在一起,解读生和工作之意义,无疑很有启发。但是,笔者认为文脉中“永远的‘梦’之时”与西田几多郎的“永远的现在”之时间概念重叠,所不同的是“怀念的年代”具有两义性:既是时间,也是场所。具体地说,“怀念的年代”作为时间是“永远的‘梦’之时”,作为场所是环绕“在”和峡谷的“森林”。
小板国继对西田的“永远的现在”解释道:“过去虽如字义所示,指已经过去的时间。但其总是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着现在,同样,未来虽是指尚未到来的时间,而其总是在某种意义上蕴含现在。在现在中过去和未来同时并存,同时于现在的一瞬中,收敛无限的过去和未来。就这样,‘现在’在限定现在自身之时产生时间,并孕育着过去和未来。因此,时间是包容过去·现在·未来的‘绝对现在’或‘永远的现在’。或者说,从直线的限定来看,时间是‘非连续的连续’,而从循环的限定来看,时间是‘永远的现在’。”[23]165-166可见,从圆环时间而言,“怀念的年代”中的“永远的‘梦’之时”,等同于“永远的现在”,也是“包容过去·现在·未来的‘绝对现在’。”对此时间,义兄在其后加了“美丽的村庄”,由此组成“时间”与村庄的组合;而叙事者“我”在“怀念”之后加上“年代”,其实质与义兄的理念异曲同工。即无论是澳大利亚原住民,还是“峡谷村庄”共同体,其始终“怀念”的“永远之梦”就是回归过去祖先们的生活“场所”——“美丽的村庄”。而且,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祖先们就像义兄那样,无论犯下何种过错,都勇于承担主体责任,不惜代价地改变现实。
与那个令人“怀念的年代”相比,我们“现在”所处的年代又如何呢?大江说:“20世纪即将结束,这个世纪可谓是充满悲剧事故的世界。这一时代的根本问题是,作为主体如何担当责任,不惜一切地去努力改变现实。比如,对于核武器和核电站事故,我们作为个人应该如何承担起事故主体之责任?”[24]5这就是叙事者“我”通过自己的分身义兄,写给现代人的“信”。即直面核武器可以毁灭整个地球;核电站爆炸事件时有发生(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日本的福岛核电站)的现实,作为生活在这一场所的每个主体,我们应该如何承担起自己所犯的过错,努力去改变现实,进而将其建设为一个“美丽的村庄”。可见,“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绝非单纯的怀古情调,而是承袭澳大利亚原住民或“峡谷村庄”共同体的宇宙观·世界观,去构建一个“美丽的地球村”。
四、结 语
大江文学在时空美学上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叙事空间四国森林“峡谷村庄”的“场所”相位和历史时间的哲学思考。在《饲育》中,以“黑人士兵”从天而降,建构了内部空间四国森林“峡谷村庄”与外部空间“二战末期”背景的对峙,以及“峡谷村庄”的多重结构:四周环绕的“森林”;位于村庄中央的老屋“仓屋敷”和老屋下面的“地下仓库”。在叙事时间上,叙事者“我”立足于战后的“现在”时,叙述战时下的“过去”,从而使“过去”与“现在”重叠,真实地表现了战后美军占领下,日本国民的生存状态。这一现代神话的雏形,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进一步得以完善和深化,在空间上实现了现代都市东京与故乡场所“峡谷村庄”的对峙;在时间上完成了历史时间“万延元年”(1860)与现在时间“安保斗争”(1960)的重叠,乃至叙事主题上的突破:历史事件与现在事件在本质上的重现。100年前“根所”家族的祖先“曾祖父的弟弟”领导农民起义,反抗国家政权的“秩序”社会;跨越100年后的现在,“蜜三郎的弟弟”鹰四效仿祖先的行为,在同一空间的“峡谷村庄”煽动年轻人组织暴动,将“天皇超市”洗劫一空。最后“暴动”失败,鹰四自杀。这就是大江文学叙事技法的特质:将两个发生在不同时间轴上的事件,以悲剧的形式巧妙地重叠在一起,完成了历史事件与现在事件在本质上的循环。其表现原理是,通过对可以观察的历史现象,实现对不可观察的现实社会的反省与批判,进而从“死者”的呐喊中听出生者的希望。不仅如此,在此后的系列作品《同时代的游戏》和《寄给令人怀念年代的信》中,在叙事空间上,通过对“峡谷村庄”的重构,将其营造为“村庄·国家·小宇宙”的神话模型;在叙事时间上,由“过去优先论”的历史时间转向“回归过去”的圆环时间。大江文学就是这样,经过孜孜不倦的追求叙事形式与内容的有机融合,最终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关系的、人文主义的理念上,以“缩减模型”的多重结构重现了现代神话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