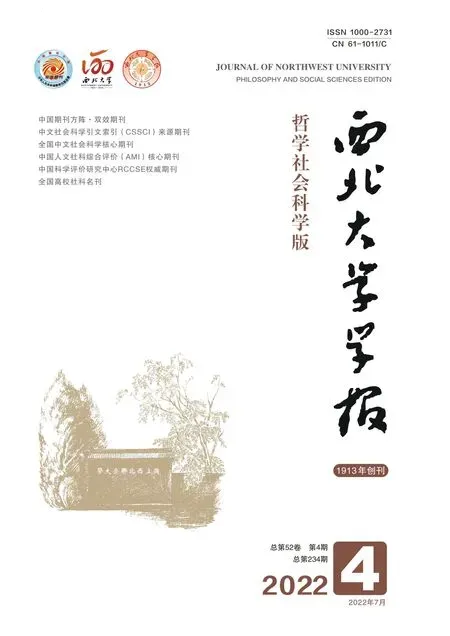中国古代整体性阐释的基础、边界及要件
韩 伟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文学阐释”是阐释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文学的阐释传统而言,虽然在不同时代呈现出的具体特征有所差异,但还是可以寻找到某些共性的宏观征象,这些征象明确了文学阐释的民族属性。自2014年开始,张江先生对中国阐释实践中的若干问题展开了持续探索,从“强制阐释论”的提出,到对“公共阐释”合理性的考察,再到关于“中国阐释学”的阐释特征、阐释逻辑的分析,这些都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1)相关论文如: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张江《强制阐释的独断论特征》,《文艺研究》2016年第8期;张江《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张江《“阐”“诠”辨——阐释的公共性讨论之一》2017年第12期;张江《论阐释的有限与无限——从π到正态分布的说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张江《阐释与自证——心理学视域下的阐释本质》,《哲学研究》2020年第10期,等等。。客观而言,对中国文学阐释实践中“强制阐释”现象的“破”较容易,但建构“中国阐释学”学术话语体系的“立”,则注定充满艰辛。笔者注意到,在其新作《再论强制阐释》(《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中提到了“整体性”问题,文中结合西方哲学、心理学以及艺术实践,讨论了“整体性的意义”。我们认为,不仅应该从特征论和价值论角度关注这一问题,更应该从本质论角度对之进行审视,并且认为应该从“整体性”特征最为明显的中国古代阐释传统中发掘有益资源,以此为基点思考中国阐释学建构问题。
一、整体性阐释的创构基础
整体性阐释能够形成的基础是对言、象、意的统合性感受。这种统合性感受往往是在我们刚刚接触到语言形式(语音、语法、字形等)时就同步发生了。为了论述方便,笔者将整体性阐释赖以形成的第一重关隘称作“语感想象”。我们认为,语感想象是一种偏重于由语言形式(语音、语法、字形等)引起的内在感受,其结果是“想象空间”及“文学意义”的形成。当人们接收到某个语音片段、语法表达、文字形象的时候,会调动起固有的审美经验,形成第一重语言感受。这种感受形成之后,会与词汇意义、文化传统等要素结合,形成真正的文学意象和意义。概而言之,“语言符号——语感想象——文学意象及意义”是一个有机思维链条。以诗歌为例,阐释层面的语感想象可以细化为语音想象、语法想象、字形想象三种类型。
首先,来看语音想象。中国古代诗歌尽管有时在意象运用上跳跃极大,语法结构上也不合常规,但只要文从字顺,符合听觉规律,接受者便会将上述问题人为过滤掉,在音响的整体效果中产生或流畅、或滞涩的审美感受。这种朦胧的感受就是最初的声音想象,也是诗歌欣赏的第一重“象”。构成音响效果的重要媒介是声调。诗歌中的声调实际上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元和韵谱》中有“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1]1281册,676的说法,朱光潜在《诗论》中借助实验心理学的成果,进行了更充分的延伸:“高而促的音易引起筋肉及相关器官的紧张激昂,低而缓的音易引起它们的弛懈安适。联想也有影响。有些声音是响亮清脆的,容易使人联想起快乐的情绪;有些声音是重浊阴暗的,容易使人联想起忧郁的情绪。”[2]171这些说法充分说明语音与情感、意义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无法孤立地进行所谓的形式阐释和内容阐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曾谈到诗人创作过程中感受、意义、语音之间的整体性关系。他说:“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日出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皎日’‘嚖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3]410这里涉及很多具有音响效果的叠音词,在刘勰眼中,它们是实现诗歌“情”“貌”统一的手段。很显然,声、情、貌在创作过程中是凝结在一起的。按此逻辑,阐释过程中将三者分开言说,实际上就是一种人为性肢解,遑论以某种所谓高大上理论的硬性言说了。
其次,来看语法想象。不妨以李商隐《锦瑟》中“庄周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句为分析对象进行初步探索。这首诗的第二句“望帝将春心托给杜鹃鸟”较通顺,“春心”为偏正结构,可解为“忧国之心”。但是与之构成对仗关系的“庄周晓梦迷蝴蝶”似乎颇令人费解,其中关键是“晓梦”当何解?若按照第二句的句式,它也应当为偏正结构,意为“白日之梦”,那么整句诗的意思就是“庄周将白日之梦赋予蝴蝶”或者“庄周在白日之梦中与蝴蝶相互迷失”,第一种解释很显然与庄周梦蝶的原意相悖,第二种解释可以说通,但却无法与“望帝春心”句形成互文。有的学者还将“晓梦迷蝴蝶”放在一起理解,“晓”取动词“通晓”之义,整句意为“庄周知道自己梦迷蝴蝶”。然而,此说同样无法与下一句形成互文。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从字面意义组合角度给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些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两句话的好感,更加不会影响它们成为千古名句。原因何在?恐怕与“语法惯性”有关。当人们已经初步具有了关于诗歌格式的前期积淀,往往会从惯性的角度审视句子。这种情况下,关注的焦点除了声律畅通之外,主要集中在语法格式是否整一上。一旦达到了这些标准,欣赏者就不会对个别词语(尤其是语序)是否恰当给予过多关注。
与“语法惯性”分列两极的是“语法形变”。所谓“语法形变”只不过是以现代语言学知识进行反观的结果,古代“汉语排斥所有的语法形式,把它们推委给精神劳动来完成”[4]314。抛开主谓宾定状补等固有的知识框架,中国古诗的“语法形变”实际上遵循着一种“主题优先”原则。在汉语诗歌中,很多诗句中修饰词与主词之间、主词与主词之间虽然在意义逻辑上可能存在从属关系,但在感受层面却是并置的,是现象学意义上的浑融整体。试看王维《春日上方即事》中“柳色春山映,梨花夕鸟藏”句,到底是“春山映柳色”还是“柳色映春山”已经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柳”“春”“山”被并置在一起,仅凭这些就可以形成一幅充满色彩的画卷。对于这种情况,叶维廉称“中国的旧诗所用的文言,由于超脱了呆板分析性的文法、语法而获得更完全的表达”[5]30。在多元主题模式下,现代语言学上的逻辑关系被削弱,代之以朦胧的内在感受逻辑。在此基础上,“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辽远想象得以驰骋。因此,很多时候我们读诗时会有“一知半解”或“云里雾里”的感觉,但并不会觉得这样不好,反而乐在其中,越是朦胧就越感到有滋有味,这一过程消解了一切现代阐释的优越性。
再次,是字形想象。承认字形的价值,而不是将字形看成“得鱼忘筌”意义上的无用工具,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有机性。实际上,从整句、整联、整诗的角度看,字形与字形组合往往会带来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并形成感受层面的格式塔。以《诗经·小雅·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为例。对于这两句,清人王夫之称“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6]10。将“杨柳”句视作乐景写哀,将“雨雪”句看成是哀景写乐,此说亦被周振甫、张少康等学者广泛征引。综观这四句,在字形层面出现最多的部首是“木”和“雨”。“木”旁与树木、森林有关,“从原型批评看来,森林已不仅仅是独立于人类之外的植物世界,而是富有文化意味的绿色家园,其中蕴藏着人类历经波折,走出漫漫长夜的动人故事”[7]104。再来看“雨”旁,“雨雪霏霏”四个字的连续排列,营造了一幅阴云笼罩、寒风瑟瑟的自然景象。与树木和森林相比,“雨雪”显然属于自然界的另一幅面孔,它们也就积淀成原始先民的另类情绪,“哀景”之“哀”由此生发出来。可以说,“字形想象”的存在为我们更立体地涵泳诗意以及判断诗句的文化意义提供了契机。我们认为,虽然王夫之对诗意的解读曾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2)比如赵立生的《诗经·小雅·采薇末章四句‘以乐景写哀’说质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4期;吴承学的《小雅·采薇“哀乐”辨》,《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姚爱斌的《王夫之诗·小雅·采薇评语的症候式解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等等。,但却与人的生命相合,为我们营构了更为完善的整体性想象空间。
汉语诗歌意义呈现方式的整体性是不争的事实,语音、语法、字形都是这种整体性的载体。实际上,我们对艺术之美的品读,无法决然区别出内容和形式,甚至在形式想象内部也不能让语音想象、语法想象、字形想象决然分裂,它们都是人主观世界的浑融性存在。现代脑科学认为,“虽然特殊的功能存在于特定的中心区域,但大脑的加工活动是由诸多区域的共时性加工完成的,它是一个有着大量并行关系的加工活动”[8]114,脑科学对大脑“共时性”加工行为的肯定,与阐释领域对艺术品“有机体”的认知正好形成呼应,进一步印证了艺术阐释的浑融性特征。本节为了论述方便,权将语音、语法、字形分开处理,实为无奈之举。
二、整体性阐释的边界
我们认为,文学阐释存在两个边界:能力边界和社会意识边界。能力边界受语言系统自身潜能以及语言运用者的个人能力影响。不同语言体系的符号数量有所不同,这就给符号与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带来难度。比如在某些原始语言中,词汇的数量非常有限,无法构成与现实世界的一一对应。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社会成员的艺术创造,也必然限制阐释的域界。除了语言系统的自身潜能之外,语言使用者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会对阐释的深度和广度产生影响。在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很多西方哲人看来,具有文学天赋且能驾驭语言的人是受诗神眷顾的佼佼者,同样,在中国古人眼中,能够“语天地大方”的人是洞悉世界“情伪”的圣贤。在中国文学的阐释实践中,高明的阐释者往往能达到“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效果,阐释本身就是一种诗性的再创造,这一过程实现了“诗”“诠”“阐”的水乳交融。因此,阐释之事虽难以决然摆脱“词场恩怨”“门户构争”的窠臼,但却是语言功底深厚之人“讨论瑕瑜,别裁真伪”[9]2736的生命呈现。
文学阐释的另一个边界是社会意识边界。这个边界较复杂,将重点讨论。从根本上讲,语言、文学都是依赖具体的族群而产生的,族群的发展、壮大逐渐衍生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形成与社会意识的出现往往互相倚重,并驾齐驱。社会意识边界具有时代性,中国古代文学阐释所遵循的社会意识边界沿着“礼边界”“德边界”“理边界”的路径向前推进。
商周至战国的文学阐释是在“礼边界”的框架下运行的。“礼”作为几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内在基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中国社会的运行方式。作为“元范畴”,它俨然成了艺术领域的“纠察官”[10]。“礼”的文化雏形是巫术信仰。在巫术仪式中,对天、地、四方的敬畏产生了最初的等级观念,这种观念逐渐从天与人之间的差异演化为君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秩序。殷商时期,一方面保持了巫文化的痕迹,另一面亦将等级秩序进一步人间化。《尚书》载商汤直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便是殷商时期巫、礼并存的基本写照。殷人崇鬼、尚酒的传统,建构了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文化模式,等级观念虽然初步形成,但尚未完全稳固。周人吸收殷商灭亡的历史教训,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一种自觉的理性意识,孔子言“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代社会尽管也曾“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但绝不是如殷人一样放纵不加约束,而是以“和谐”为施礼原则,所以周礼对商礼的“损益”,实则是对非理性礼仪精神的摒弃,易之以建基于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性追求。自此,礼从单纯祭祀、宴饮等日常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治理的层面,并逐渐完成了对社会文化的全方位影响,文学艺术自然在此之列。到了春秋时代,礼对社会的控制逐渐松动,但这种情况在文学领域却表现出相当的滞后性。甚至相反,出现了诉诸文学恢复礼乐传统的现象,文学与礼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密了。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孔子删诗,“删诗”实际上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阐诗”。“思无邪”是孔子对理想的诗歌主题的认知,也是他删诗的基本指导原则。文学作品思想主题的雅化追求实际上就是礼对阐释的干预,因此“礼边界”构成了这个时期的阐释意识。到了战国时期,《诗经》阐释与王道礼乐相统一,《孟子·离娄下》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11]192,《荀子·儒效》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12]133,等等。足见,儒者将《诗经》与其他教化性文本等而视之,文学阐释的坐标是政教和礼法。本质而言,周代以后中国文学的语言想象都没有挣脱“礼”的限制(3)张江先生在《“阐”“诠”辨》(《哲学研究》2017年第12期)一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存在两条差异深刻的阐释路线,“一条由孔孟始,重训诂之‘诠’;一条由老庄始,重意旨之‘阐’”。笔者也曾在拙作《儒家经学与浮屠译经:中国两种阐释传统及其关系》(《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0期)中提出过儒家经学阐释与佛教译经的两种阐释路线。上述观点的出发点不同,本质上并不矛盾。由于儒家文化对社会理性强大的统摄能力,所以实际上无论老庄式的阐释形式,还是佛教译经式的阐释形式,最终都难免受到儒家规范的“检阅”,儒家礼教及道德体系构成了显性的社会意识边界。。下文所述的其他时代的阐释边界,严格意义上都属于“礼边界”的时代变体,出于突出时代特殊性的考虑,权将各种“边界”进行细致化定位。
“德边界”是两汉、魏晋文学阐释的遵循标准。我们知道,儒家与道家在自己的体系内部都有大量关于道与德的言说,并且也建构了两者的联系。相较而言,儒家所言之德更重伦理,道家之德则倾向于自然而然。汉代是阴阳五行观念以及天人理论获得集中呈现的时期,“德”成了文艺领域新的遵循标准。汉代所尚之“德”,一方面具有儒家伦理的基本内涵,另一方面亦承袭了道家哲学的抽象性,遂使其成为代替“礼”而出现的具体思想标准,影响范围亦波及艺术领域。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思想家看来,“同类相动”是天地万物与人间社会相互勾连的基本思想基础,他承认“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13]445。以这种观念为指导,他将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五德(仁义礼智信)相互联系,并将前者视作后者的基础。这样,天地之美与社会之美、道德之美之间就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反观西汉大赋,它们实际上就是文人以辞采为载体,进行的道德性演讲,甚至有充当哲学和政治注脚的嫌疑。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文学阐释便无法超出“德”的边界,阐释成了抽象天地之德与现实社会之德的共同载体。按照清代四库馆臣的说法,“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9]2736。这段话重在说明体系性的“论文之说”的起点,与文学阐释的早期发生并不抵牾。《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诗品》作为体系化的阐释文本,表现出对魏晋新型之“德”的服膺。比如曹丕一方面承认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另一方面亦肯定“气”的价值。刘勰一方面以“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3]447-448体现出对儒家文统的遵行,另一方面还将“文德”中掺入了“自然之道”的因子。钟嵘也是将“气”与“动天地,感鬼神”糅和在一起。所以,两汉、魏晋时期文学阐释所依凭之“德”应该是传统儒家道德与道家自然观的融合,阐释的边界一方面不可凌越礼教规范,另一方面也不可违背阴阳之理、五行之序。
唐代以后,文学阐释的基本界域是“理”。通常情况,我们将“理”视作宋明时期的产物,似乎与唐代并不相关。实际上,唐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雅正的路子。出于对齐梁文风的拒斥,王勃表现出对“周孔之教”的向往,并对“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14]130忧心不已;杨炯对王勃的观点十分推崇,称赞王勃诗风“刚而能润,雕而不碎”[15]36。在理论倡导层面,陈子昂认为齐梁文学“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16]卷1 15,呼唤风雅之风的再度兴盛。创作与阐释实为一体之两面,上述文学观念,虽然囿于创作领域,却也灌注于阐释之中,“注释者不再是思想者,只是传统经义忠实的守护者和辩护者”[17]205-206。初唐基调既然已经形成,于是盛唐李白呼唤“大雅”古风的重振,中唐韩愈进一步号召“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柳宗元亦明确了“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理论旗帜,遂使“明道”观念确立起来。如果对唐代文学创作、文学阐释所尊奉之“道”和“理”加以概括,那么“雅正”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内核。沿着这个线索,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宋代理学家将文学家尊奉的“雅正”之“理”,与思想家钟情的“天地”之“理”进行了哲学性整合。于是天地、德行、文艺开始具有了更为完善的内在联系。理学之“理”本质上乃是儒家之“礼”的哲学升华,具体伦理道德演化成了形而上的意识性存在。这一过程,道德对社会、人生、文艺的控制力明显增强。在“理”的统御下,具有“静”和“净”特征的理想人性成为追求的目标,于是周敦颐《爱莲说》具有了理、性、人的多层涵咏空间,“理”亦成了灌注于艺术作品中的“天光云影”和“源头活水”。在牟宗三看来,宋明理学所尊奉的乃为“成德之教”,用现代术语亦可称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的形上学”[18]7。阐释层面,“按照伦理性、真实性的原则对原文作出诠释或评判……都不越过‘理义大本’的底线”[17]207。按照这个思路,可以说宋代实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宗教观念、民间意识的统一,理学遂具有了超强的社会统摄能力,“文皆从道中流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成了一种显性文学观念。至此,具有哲学根基的社会文化理性被建立起来,这种理性的内核是道德规范,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组织乃至社会成员的意识之中,“人欲”成了区隔这种理性的基本标志点。虽然明清时代,这种“社会文化理性”的统摄力在显性层面有所式微,但其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兴的集体无意识,并持久扎根于文化底层。
尽管礼边界、德边界、理边界在本质上存在明显的交叉关系,但三者毕竟不同,本文将它们看成是规约“整体性阐释”的三种文化原型。礼边界侧重硬性的制度性约束,“合礼”将文学阐释置于等级关系之下。德边界在人伦之德的基础上掺入了天地之德的因子,不违人伦,不抗自然成为衡量优秀作品的指标。理边界则受具有哲学根基的道德理性的支配,受其影响,分层性的社会意识开始走向了统一,并成为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理性。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起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学阐释具有边界,虽然这种边界具有流动性,但在同一文化体内部它更具有连续性。
三、整体性阐释的构成要件
按照张江先生的观点,海德格尔关于梵高《农鞋》的阐释带有强制阐释的味道。他认为农鞋仅仅是海德格尔借以阐发自己哲学思想的符号而已,如果换作其他画作,海德格尔仍然可以生发出大致相似的解读文字,“他的阐释脱离了对象,其阐释的不是鞋子,而是自我,是自我的意念与思想”[19]。显然,海氏貌似返回鞋子“存在”的所谓存在论阐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整体性阐释。我们认为,整体性阐释的前提一定是立足文本, 以解读文本思想内涵和审美内涵为旨归,而不是进行“没有艺术的艺术阐释”“没有文学的文学阐释”。 同时, 整体性阐释亦应重视作者与读者之间对话, 既要避免单纯以作者为核心的庸俗社会学阐释, 也要避免孤立强调读者感受的读者反应式批评。 在作者与读者的对话过程中展示作品的意义和温度,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阐释。 尽管我们已经接受了若干所谓西方“先进”的文学批评理念, 比如新批评、 后殖民批评、 女权主义批评、 身体批评甚至后人类批评等, 但我们认为文学传统具有民族性, 阐释传统也是如此。 就中国文学阐释而言, 中国古代的整体性阐释具有弘扬价值。 否则, 我们进行的永远是流派的贩卖、 概念的轰炸、 异质思想的演绎, 这一过程中文学作品鲜活的生命被肢解了。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整体性阐释”具有三个构成要件,即感性直观、诗性话语以及生命体验。首先来看感性直观。它是一种省略了逻辑推演过程的综合性认知,在固有感觉经验基础上完成对事物特征的整体把握。因此,感性直观又可称为经验直观,它以形象思维为基本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体系中,感性直观带有先验性,即经验源自先验。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曾描绘过这种状态:“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量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20]272柏拉图意在诠释本真之美的获得路径,在他的理论中,对美加以观照的能力是先验的。到了18世纪,康德的感性直观服务于“先天形式”,而黑格尔的感性直观是回归“绝对精神”的路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感性直观归入了“先验感性”的范畴。中国古代阐释学意义上的感性直观则来源于现实艺术经验,其原因有二:第一,感性直观的施用领域主要在文学、艺术领域,不侧重于哲学命题的发现,更加不会以之为工具探索先验本体。第二,中国文人将人生艺术化境界与最高的哲学境界相互统一,而且哲学境界的层次依靠个体的内心感受。于是感性直观的最理想情况是阐释者与接受者之间获得相同层次的感知,但感知出现衰减也无所谓,境界不具有唯一性。不妨以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对梅尧臣的评论来说明这一问题。欧阳修在这部“以资闲谈”的诗话中多次提到梅尧臣,核心评语分别为“闲远古淡”“深远闲淡”等,这些评价遂成为后世认知梅尧臣诗风、乃至北宋“平淡”诗学旨趣的钥匙。实际上,欧阳修下断语的过程中并未进行今天意义上的严密论证,甚至给人一种随意拈来的印象。但是,欧阳修的认知却准确而精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种“感性直观”性认知来自于他鲜活且深厚的文学经验。欧阳修与梅尧臣不仅是相交30余年的挚友,而且在自己早年的频繁贬谪过程中时常“行歌招野叟,共步青林间”(《游琅琊山》),受到民间歌谣的深入影响。有了这些经验储备,所以品读梅诗自然能一语中的,道他人所未道。
其次,是诗性话语。中国古人早就意识到语言的局限性,所以主张“立象以尽意”。在创作领域,遵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然后在言、象、意的动态流变中传达作者之情的逻辑。但在阐释领域,阐释的发生源则并非孤立之“情”,它更像是一种“情趣之理”。那么,阐释者所体会到的这个“理”是否能代表作者想表达,以及文本呈现出的复杂之“理”?事实上,“理”的变异(缩减或增容)始终贯穿于文学活动始终。单纯依靠逻辑性语言进行言说,很显然难以达到目的。此种背景下,诗性语言实现了令阐释者领会之理再度增容的效果。如果说逻辑语言的阐释完成了从阐释者的“情趣之理”到接受者的“明晰之理”的接受过程,那么诗性语言的使用则将削减了的明晰之理,接近乃至超越阐释者的“情趣之理”,进行二次发酵,最大限度地抵达创作者的原有境界。所以,诗性语言的使用将创作者、阐释者、(阐释)接受者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他们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诗境、诗意的完整性。朱光潜先生分析姜夔《点绛唇·丁未冬过吴松作》“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句时称“在读他的这句词而见到他所见到的境界时,我必须使用心灵综合作用,在欣赏也是在创造”[2]68-69。在他看来,“欣赏与创造并无分别”。朱光潜在这里并不是简单的接受者(欣赏者),而是扮演了阐释者角色。他要将诗句的美揭示出来,并传达给真正的接受者(读者),其对这句词的解读就是“创造”。这种创造性阐释在古代阐释实践中比比皆是,我们既可以看到以“花鸟缠绵,云雷分发”(《艺概》)揭示诗歌风格,以“鲸鱼碧海”(《戏为六绝句》)况喻诗人地位,以“良玉生烟”讨论境界之美的情况,更加可以看到“兴趣”“神韵”“性灵”“格调”之类的纲领性描述。中国文学阐释的这种方式一度被认为含混、低级,但这恰恰能保留作品的原始味道,较之援引某些西方方法、理论进行强制性的解读似乎还要高级一些。
再次,是生命体验。整体性阐释的关键在于对生命感受的完整还原。当然,生命体验是一个较抽象的说法,似乎难以定义。我们认为,其核心要件是对表现对象在特定历史时空中的鲜活存在的展现。本部分开头提到过海德格尔对梵高《农鞋》的阐释,虽然这个阐释赋予了鞋子“生命性”,但却不具备“体验性”,或者说海德格尔的现代的、哲学的体验并没有与农鞋主人、梵高的体验形成对话,两种体验还处在各自的时空之中。相比之下,笔者更欣赏闻一多先生对《诗经·周南·芣苢》的阐释,兹引述于下:
现在请你再把诗读一遍,抓紧那节奏,然后合上眼睛,揣摩那是一个夏天,芣苢都结子了,满山谷是采芣苢的妇女,满山谷响着歌声。这边人群中有一个新嫁的少妇,正捻那希望的珠玑出神,羞涩忽然潮上她的靥辅,一个巧笑,急忙的把它揣在怀里了,然后她的手只是机械似的替她摘,替她往怀里装,她的喉咙只随着大家的歌声啭着歌声——一片不知名的欣慰,没遮拦的狂欢。不过,那边山坳里,你瞧,还有一个佝偻的背影。她许是一个中年硗确的女性。她在寻求一粒真实的新生的种子,一个祯祥,她在给她的命运寻求救星,因为她急于要取得母的资格以稳固她的妻的地位。在那每一掇一捋之间,她用尽了全副的腕力和精诚,她的歌声也便在那“掇”“捋”两字上,用力的响应着两个顿挫,仿佛这样便可以帮助她摘来一颗真正灵验的种子……她听见山前那群少妇的歌声,像那回在梦中听到的天乐一般,美丽而辽远。[21]208
早于闻一多,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也进行了类似的解读:
读者试平心静气, 涵泳此诗, 恍听田家妇女, 三三五五, 于平原繍野、 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 余音袅袅, 若远若近, 忽断忽续, 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22]85
那么,方玉润、闻一多的阐释是否如海德格尔一样是在进行强制性阐释呢?我们认为,首先,两人阐释的对象是文本本身,并不存在先入为主的“前见”。而且他们只是加进了适当的时空元素,让诗歌变得鲜活,是所谓“同情之理解”。其次,两人都提到了歌声的审美效果,即“美丽而辽远”“余音袅袅”。《诗经·周南·芣苢》全诗分三章:“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每句中的叠音词“采采”起到了延长声音时值的作用,使歌声的绵延效果更为明显。在一般欣赏者眼中,几千年前歌者通过“采采”营造的审美效果可能未必被完全领会,但透过方、闻两人的阐释,这种如歌般的审美时空便得到了“敞开”,这恰恰是高明的阐释者应该做的。所以,方玉润、闻一多的阐释不属于强制阐释,而是加入了生命体验的整体性阐释。
当然,“整体性阐释”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阐释形式,其构成要件并非仅仅包括上述三个方面。作为一个开放性结构,它需要不断被充实、发掘。从历史的维度而言,不同时期的整体性阐释必然会体现出各自的独特性,其构成要件也必然有所差异。这些方面,都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断代性考察。只有这样,中国古代整体性阐释的哲学基础、发展线索,以及与创作实践的真实关系才能全面展示出来。限于个人能力和文章篇幅,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只能留待日后进行了。
综上所述,中国文学阐释是具有整体性传统的。这种整体性的获得源自表意文字的特殊属性,语音、语法、字形在感知层面是天然的统一体,以它们为基础构筑的形式系统又明显具有“意味”特征,这些都决定了整体阐释的合理性。因此,中国古代阐释很少见到孤立的语音、语法等方面的形式解读,也很少看到抛弃形式质素的内容解读。文学并非脱离社会理性的孤立存在物,社会意识因素也是构成阐释“整体”的基本内容。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整体性阐释的边界沿着礼、德、理的宏观脉络向前推进。在这个演化过程中,道德因子逐渐上升到哲学高度,并与意识形态相互结合,从而完成了道德礼法向政治意识形态,再到哲学意识形态的进阶。这就是宋代以后虽然表层社会观念不断变革,但基本的道德理性内核却没有发生彻底崩裂的原因。这种情况乃至在当代社会仍有余续,形成了带有集体无意识的持久性阐释边界。在这种隐性边界之内,感性直观、诗性话语、生命体验作为整体性阐释的构成要件得以具体显现,它们的存在使整体阐释的民族性特征更为鲜明。我们认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阐释标准和方法,先解决民族文学的问题,才有可能扩容、进化为世界范围的标准和方法。即便本文聚焦的论域是中国古代问题,但只要文化传统、文学传统没有断裂,这种阐释模式便具有可被继续挖掘的当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