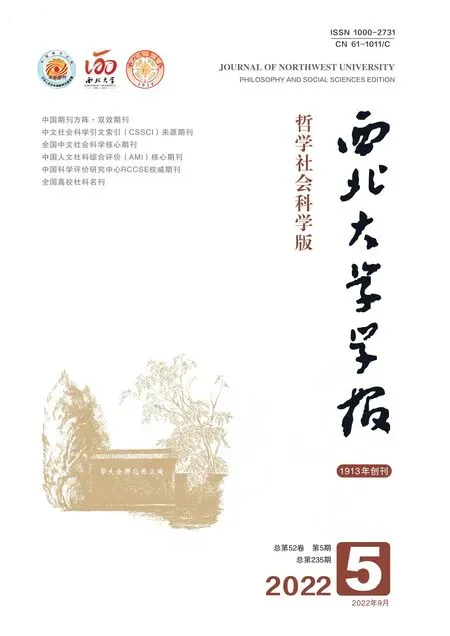“园林诗”范畴的史实与学理新说
李 浩
(西北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西安 710127)
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学者普遍认为山水诗与田园诗至唐初都是二水分流、两峰并峙,随着隐逸之风的盛行到盛唐时期始逐渐合流,形成了“山水田园诗”或“田园山水诗”的范畴,这种认知在20世纪以来海内外的中国古代文学叙述或唐诗书写中广为流行,通行的著述基本都是按照这样的概念梳理唐代自然诗的演进。笔者认为,这并不完全符合唐代诗歌发展的实际。
有唐一代,造园产业兴盛,名园遍布大江南北,与此相应的是,出现了大量专门书写园林景色、记录可游可居的园林生活、抒发园中闲适之情的作品,因此不能简单笼统地使用山水诗、田园诗或山水田园诗等旧有的概念来涵盖新的生活形态和情感内容,有必要引入“园林诗”和“园林文学” 等新范畴来记录新的文学现象。
园林诗作为一种独立于山水诗、田园诗之外的诗歌类型,大量出现于公私园林繁荣的唐代,与山水诗、田园诗有许多不同之处。随着唐代园林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必要从史实和学理上剖判辨析。
本文分别梳理了山水诗、田园诗和园林诗等概念的由来,并从史实上叙述山水诗、田园诗的缘起与嬗变,通过比较来彰显园林诗的突出特点,同时引入景观学上“四种自然说”的理论,以求从学理上界定荒野、田园和园林三类景观环境,试图为目前文学史和唐诗史书写提供一更科学明晰的话语系统和理论范畴。
一、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田园诗等概念的由来
中国文学中书写自然可以追溯到很早,如清人恽敬在《游罗浮山记》中所言:“《三百篇》言山水,古简无余辞。至屈左徒肆力写之,而后瑰怪之观、远淡之境、幽奥润朗之趣,不名一地,不守一意,如遇于心目之间。”[1]159一般认为,山水诗、田园诗的概念主要是指称东晋南朝诗歌书写自然的两个突出现象。
《文心雕龙·明诗》中谈到山水诗的形成问题:
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忘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雄,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2]65
在刘勰看来,山水诗到刘宋才开始出现,是文体因革、旧退新滋的产物。这种看法,对后代影响很大,如清王士禛言:“迨元嘉间,谢康乐出,始创为刻画山水之词。”[3]115清人沈德潜亦说:“游山水诗应以康乐为开先。”[4]7直至如今,谢灵运仍被视为中国山水诗的“鼻祖”。
当然也有学者不断修正完善前人的这些观点。一是对“玄言”“山水”关系的新认识。王瑶在《玄言·山水·田园——论东晋诗》一文中说:
由玄言诗到山水诗的变迁,所谓“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是诗人们底思想和对宇宙人生认识的变迁,而只是一种导体,一种题材的变迁。我们说山水诗是玄言诗的改变,毋宁说是玄言诗的继续。这不只是诗中所表现的主要思想与以前无异,而且即在山水诗中也还保留着一些单讲玄理的句子。谢诗中如“矜名道不足,适己物可忽。”(《游赤石进帆海》)“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斋中读书》)“怀抱既昭旷,外物徒龙蠖。”(《富春渚》)等,都是这种例子。[5]280-285
二是对山水诗产生时间的新认识。如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明诗》注中指出:“写山水之诗起自东晋初庾阐诸人。”[6]92钱锺书《管锥编·全后汉文卷八九》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诗文之及山水者,始则陈其形势产品,如《京》《都》之《赋》,或喻诸心性德行,如《山》《川》之《颂》,未尝玩物审美。继乃山水依傍田园,若茑萝之施松柏,其趣明而未融,谢灵运《山居赋》所谓‘仲长愿言’‘应璩作书’‘铜陵卓氏’‘金谷石子’,皆‘徒形域之荟蔚,惜事异于栖盘’,即指此也。终则附庸蔚成大国,殆在东晋乎。[7]1644
其实,钱锺书的看法也不是孤立的,早在清末“同光体”诗人沈曾植在《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中便言:“康乐总山水庄老之大成,开其先支道林。”[8]29在《王壬秋选八代诗选跋》中认为支遁的诗“模山范水,固已华妙绝伦”,“支、谢皆禅玄互证”,“谢固犹留意遣物,支公恢恢,与道大适矣”[9]366。马一浮《蠲戏斋诗话》中也说:“林公(即支遁)诗为玄言之宗。义从玄出而诗兼玄义,遂为理境极致。林公造语近朴而恬澹冲夷,非深于道者不能至,虽陶、谢何以过此!”[10]31-32
20世纪60年代,大陆学术界曾开展过山水诗的大讨论,主要集中在山水诗的阶级性问题上。1961年3月《文学评论》编辑部编印了《有关山水诗的材料》,将当时的文章分为七个方面的问题加以摘录,论者多对山水诗加以否定。20世纪80年代又出现了山水诗研究热潮,有论文400多篇,对山水诗的性质、自然美、共同美、代表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对山水诗的性质和范围做出了更明确的界定(1)关于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田园诗的缘起与演变,参见李浩《唐诗的文本阐释》第6章《唐诗的自然书写》,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本篇不再详细展开。。
山水诗、田园诗的概念作为常识和固定模式在文学史上已被普遍接受,然而无论从逻辑分类还是历史演变来看,园林与山水、田园都不能化为等同。山水指未经人化的广袤自然景物;田园与园林则是指经过人化的环境。其中田园是与人的物质功利有紧密联系的景物及产品,……而园林则是与人的精神功利有更多联系的景物及作品。山水、田园与园林不同,以三者为描写对象的山水诗、田园诗与园林诗亦存在似是而非的关系[11]。
二、唐园兴盛与唐代园林诗的出现
通过笔者的专题研究,发现唐代造园产业兴盛,公私园林以及寺观园林蔚然,楼台烟雨,泉石遍布,据北宋张舜民《画墁录》卷一记载:“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开印,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诸司农寺山池为最,船户部为最。”[12]502杜甫《丽人行》:“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13]336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游盖飘青云”条:“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闲地。”[14]56
沈青峰《(雍正)陕西通志》 卷九十八引《闲居笔记》:“骊山下逍遥别业, 盖韦嗣立所建, 赋诗勒石在焉。一夕忽失碑字,换墨题云:晓星明灭,白露点,秋风落叶,故址颓垣,冷烟衰草,前朝宫阙。长安道上行客,依旧,名利深切。改变容颜,消磨今古,陇头残月。”(2)按:此条材料“题云”以下引文,文字、题目、作者,学界有不同看法,也有许多讨论。此处不展开。[15]4431
以园林为描写对象的诗歌亦大量岀现。著名的如王维和裴迪均有《辋川集》二十首,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盆池五首》;卢鸿一《嵩山十志十首》;李德裕《思山居一十首》《春暮思平泉杂咏二十首》《思平泉树石杂咏一十首》《重忆山居六首》《忆平泉杂咏》等等。数量之多、范围之广,不得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然而如何对其进行归类?
显然,已有的山水诗、田园诗、山水田园诗概念已经不能涵盖这类新的文学现象,它应该属于独立于山水诗、田园诗之外但又与两者有交叉的另外一个诗歌类型,本文将其称为“园林诗”。
下面将用比较的方法对“园林诗”作一简单描述。
笔者认为,对合流形势下创作的诗歌似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山水诗、田园诗或山水田园诗,而应该有更细致合理的界定。下面以王维诗歌为例略作解说:
寂寞掩柴扉,苍茫对落晖。鹤巢松树遍,人访荜门稀。绿竹含新粉,红莲落故衣。渡头烟火起,处处采菱归。(《山居即事》[13]1277)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斤竹岭》[13]1300)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临湖亭》[13]1300)
《山居即事》中虽有“柴扉”“荜门”字眼,但整个田园环境却是由松鹤、莲竹构成,并非田园诗所能概括。再看《斤竹岭》和《临湖亭》,清人赵殿成考证“斤竹”即金竹,为竹之良种,产于雁荡山[16]243。雁荡山史称“东南第一山”,位于今浙江温州,可见“斤竹”或许是王维特意移植的。临湖亭是一座三重檐的水中亭台,由此可知,辋川非自然景观亦非田园风光,而是一座融自然与建筑、天然与人工的士人园林,王维经过多年的精心葺修,把辋川的自然景观的峰、峦、岗、宅、滩、湖、瀑、溪以及生长的花卉林木、珍禽异兽,巧妙地与人工加工后的竹洲花坞、亭台苑榭、馆阁柴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辋川这个大型自然风景区建筑成综合园林。故他和友人游览观赏的这些景观不再是简单的山水或田园,他们书写或咏叹的这些景色也不能再简单地称为山水诗、田园诗或山水田园诗,而应该循名责实,正名为园林诗。
三、从“四种自然说”等理论看山水、田园与园林的分野
按照生态学的观点,自然有不同的层面,每一个层面的自然都有自己的特征,只有当人们认识到每一层面的自然自身的价值,了解并尊重它原有的特征,才能真正做到与自然的协调。
西塞罗将自然分为原始的“第一自然”和经过人类耕作的“第二自然”。“第二自然”是人们在生活中最易接触的自然形象,因而能更好地体现在园林艺术中,西方人将源于各种生产性园圃的实用园,看作是西方园林真正的雏形。
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乡村环境,要成为以文化娱乐为主要功能的造园样板,就必须将乡村环境升华到艺术的高度。从古罗马时代起,西方人在乡村兴建别墅的风气就十分盛行,到文艺复兴时期更是长盛不衰。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西方人才真正认识到风景的艺术价值, 自然成为艺术创作的源泉, 并从此与园林艺术密不可分。 园林艺术被看作是利用大自然为人类游憩服务而创造的“第三自然”。[17]在越来越多的园林史家的笔下, 园林被定义为“第三自然”, 以区别于荒野的“第一自然”和田园风光的“第二自然”。
20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自然认识的发展,有些学者又提出了“第四自然”的概念作为补充,形成了更为完整的自然认识体系。
王向荣将自然划分为原始的自然、人们为了生产生活改变的自然、人们由于审美追求建立的自然以及恢复的自然等四种类型,他指出第一类属于原始的自然,后三类属于文化的自然[18]4-5。
第一类自然是原始自然,表现在景观方面是天然景观。
第二类自然是人类生产生活改造后的自然,表现在景观方面是文化景观。
第三类自然是美学的自然,这是人们按照美学目的而建造的自然,在历史上它往往是模仿第一或第二自然而建造,是对二者的再现或抽象,但选择原型的不同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东西方各种风格的园林都属于这一范畴。
第四类自然是被损害的自然在损害的因素消失后逐渐恢复的状态。自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但是修复的速度视破坏程度的高低和当地的自然条件状况会有不同,有时可以通过人工干预的手段来促进这一过程[18]4-5。
四类自然中,除第一自然是天然形成的以外,其余三类都是人类干预后的自然。
这种认识近年来在园林文化界较为流行,本研究吸收并采用其合理的成分,用于解释和说明东西方园林的差异,书写自然的三类诗体山水诗、田园诗和园林诗的异同。
但是,园林学界似乎没有关注到公木先生对“第三自然界”的探讨[19-20]。从时间上说,公木在1981年便提出“第三自然界”的假说[21]4-17,他认为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是以人类活动为核心的“第二自然界”的反映,是影子世界、精神世界,是浮现于人们大脑银屏上的光辉灿烂的创造物,它不存在于意识之外,它是生命的火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它是由艺术或诗所建立的形象王国。对此展开了充分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特的一家之言。简单地说,人类通过劳动从“第一自然界”中创造出“第二自然界”,人类本身便是这个“第二自然界”的主体并生活于“第二自然界”,而所谓“第三自然界”则是人类想象的产物[22-23]。
公木先生对他的这一理论颇为重视。1981年,《诗探索》上刊文介绍了他的“第三自然界”的假说,同时出版了专书讨论,文学界多人也参与了讨论,如赵敏俐、郭杰等都有专文阐发,从学理上来说也触及了诗学理论与艺术哲学的一些核心问题。可惜文学理论界的这些讨论与园林理论界的探索没有出现学术交集,也没有碰撞出学术的火花,两个本来创作相关、学理相邻的领域,本来应该共同从自然哲学和创造学的角度,推进这一有意义的讨论,目前看来,仍然任重道远。
对中国文学自然观进行深入阐释,并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还有顾彬提出的中国文学“自然观三阶段论”、唐代文学自然观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山水园林化”等思想[24]。
顾彬将中国文学自然观的三个发展阶段(周与汉、六朝和唐)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指出六朝的自然观到唐代才告完成,唐代是其发展的终点[24]4。
顾彬把第一个发展阶段的自然观说成是“自然当作标志”。之所以说周至汉代的文学中的自然是一种标志,是因为它“或为突出作者的主观世界服务(《诗经》),或作为象征(《楚辞》),或囿于统治者意识的范围之内(赋)”[24]63。第二个大阶段可划分为三个方面来讨论:建安、魏晋文学,向南朝文学的过渡和南朝文学。这个大阶段的自然观是把“自然当作外在世界”来描述,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文人们才特别发掘了真实的自然之美。关于“向南朝文学的过渡”时期,主要同两位人物有关:谢灵运和陶渊明。在谢灵运手里,山水诗达到了完美成熟的境地,而山水诗的创作始于谢万。诚如顾彬所言,“应把新的自然观、对自然的推崇及对自然的热爱这三点联系在一起看待”谢灵运的山水诗。与谢灵运相比,陶渊明并非不爱自然之美(在其诗中也有自然美的描写),只是他更乐意将自然(山和水)当作去官卸职后的安身立命之所。陶喜爱的是田园风光,在归隐田园的同时实现自我的完善(不进则退),“热爱大自然的标志是归隐至独居环境之中”,而“对山水自然的热爱,体现的主要是当时贵族们的趣味。”[24]148
唐代文学发展出的新自然观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这种自然观摆脱了豪门贵族趣味的影响,同时建立在中下层地主阶级的政治基础之上;二是“自然观成了新世界的一部分,并成为一种新情势的表露”[24]225。这个“新世界”指的当然是人的内心世界。顾彬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唐代文学中自然观的发展的:自然当作历史进程;自然当作农业和文明;自然当作危险;自然当作精神复归之所。“自谢灵运开始,大自然之美便已引起诗人的关注”[24]171。
唐代自然观主要观点“向内心世界转化”,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或称“三个世界理论”):第一阶段(第一世界),自然只具有象征性质;第二阶段(第二世界),自然是独立的,它变为可推断的现实性,主要指把自然当作客观的关联物,即眼前的景物可与诗人的情感世界画上等号;第三阶段(第三世界),对主观和客观的扬弃,外在世界同自我世界互相交错,几无区别。景和情已完全处于平等地位,主观性和客观性业已消解,难分彼此。
在该书引言的最后,顾彬总结了中国文学中“风景”一词的三个发展阶段:①当作个体和象征的自然领悟(周和汉)。②当作现实的客观部分的自然领悟、对其特点和美的理解(六朝)。③自然的深化(唐)。顾彬还比较了王维与白居易。王维笔下的农村显出质朴的形态,可作为排解个人愁闷之所又有些虚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白居易的诗歌和柳宗元的散文游记里,我们发现他们更加喜爱被改造过的文明形态(即便身处恶劣的自然环境当中),并且他们自己也参与这种改造活动,乐其所乐。或者可如是说,他们喜欢在作品中按自己的意图塑造山水(自然),因为只有经过改造后的自然方能显现其本性之美。
顾彬大概是1976年至1980年间完成《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1984年作者还做了修改。1990年推出了中译本,但该书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笔者虽然也是第一时间看到该书的中译本,但20世纪80年代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研究》,其中有《山水之变》一章,当时不知道顾彬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撰写《唐诗美学》,其中有《唐诗的自然表现》一章(后定名为《唐诗的自然书写》),也没有特别关注顾彬的成果。一直到最近,因为要将“园林诗”“园林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命题提出深入讨论,才注意到顾彬对此问题的系列成果。顾彬对中国文人自然观的概括,以山水园林化概括中古时期自然观的嬗变,应该说是敏锐的,也是独创的。但他将唐以后的发展视为“完成”,认为再较少变化,则有些简单化。按照笔者理解,整个前现代社会,自然观都在演变,前半段有山水园林化倾向,后半段则走向了园林境界化的路径。
今天看来,顾彬较系统全面论述中国文学的自然观,有自己的体系,也有支撑的材料。如果将顾彬的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与宇文所安《中唐文学论集》中的“微型自然”“私人天地”等论述联系起来[25],会发现不同领域不同课题的研究,会导向类似的目标(3)相关讨论参见李浩《微型自然 、私人天地与唐代文学诠释的空间》,《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本研究也有相关后续成果追踪并跟进此问题,可以参读。可惜的是,文学史界对王向荣的“四种自然”形态、公木的“第三自然”假说、顾彬及宇文所安对自然山水园林化的开拓性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也较少被商榷讨论。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提出园林诗的概念,并将其出现确定在唐代,应该有较充分的理论支撑和学理。
四、走在前列的园林文学研究实践
海内外学者很早就提出园林文学的概念,如台湾大学曹淑娟开设中国园林文学的课程,大陆多家园林学校和专业也开有园林文学的课程。由陈从周主编的《园综》,收录历代园记和园林散文200多篇。
陈从周敏锐地指出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游园》《拾画》诸折戏属于“园林文学”,他说:“汤显祖所为《牡丹亭》,而‘游园’‘拾画’诸折,不仅是戏曲,而且是园林文学,又是教人怎样领会中国园林的精神实质。‘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蘼外烟丝醉软’,‘朝日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其兴游移情之处真曲尽其妙。是情钟于园,而园必写情也,文以情生,园固相同也。”他还说:“白居易之筑堂庐山,名文传诵。李格非之记洛阳名园,华藻吐纳。故园之筑出于文思。园之存,赖文以传,相辅相成,互为促进,园实文,文实园,两者无二致也。”[26]14-15
据此可以看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作为工程技术依傍的园林史和古建的学人,这次远远走在了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之前,率先提出了“园林文学”“园林散文”“园林诗歌”的概念,并且已经从作品选辑、名作品鉴、课程教学几个方面展开,在这种背景下,古典文学研究界如仍不予以正视、关注和评论,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其实,无论哪个领域、哪个学科,率先突破都是好事。重要的是,相关学科要关注,要跟进,要做出学术评价,而不是漠视,或做鸵鸟状,以为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
唐代园林诗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且有助于学人深入了解文人生活与心态、唐代的园林文化,并对后代的园林理论、园林营造与园林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结 论
文学史研究中长期流行的山水诗与田园诗两分法及其至唐合流的说法使诗歌分类陷入困境,这种划分忽略了唐代造园产业兴盛的事实,遮蔽了以描写园林生活为内容的大量作品,因此有必要引入“园林诗”和“园林文学”的概念。园林诗作为一种独立于山水诗、田园诗又与其有交叉关系的诗歌类型,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唐代园林诗不仅拓宽了诗歌的创作题材,促进了唐诗的繁荣,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文人生活与心态、有助于认识唐代园林文化,并对后代园林建设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