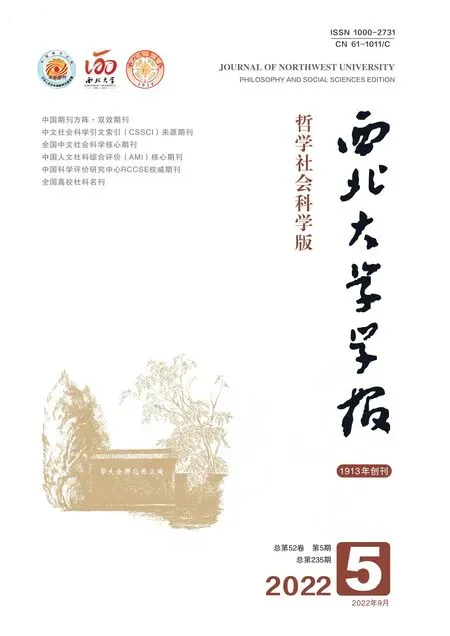“标准种类”: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的艺术本体论
章 辉
(三峡大学 影视文化与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 宜昌 443002)
本体论研究事物的存在方式。按照当代分析哲学家奎因的看法,本体论最终的限制,是奥卡姆的剃刀或本体论的节约:拒绝超出必要之外的多重实体。因此,最好的理论,是最简单的、最少本体论承诺的(ontological commitments)理论。艺术本体论讨论的是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问题是,美的艺术品是什么类型的物体或实体?是物质性的存在物,抑或是心理性的存在体,或者是两者之间的过渡类型?艺术品是独特的个体,还是普遍性的类型?作为艺术品,它们的存在模式是一样的吗?当代英语学界关于艺术本体论的讨论大体分为两种思路,一是持艺术本体的多元论,即艺术作品可分为两大类:类型(types)和个体,前者如音乐、戏剧和文学,这些艺术允许作品的多重性存在,后者如绘画和雕塑。二是艺术本体的一元论,即把所有的作品放置在一种范畴之中,通常是放置在类型之中。美国美学家尼尔森·古德曼(Nelson Goodman)是第一个试图解决这种复杂性的分析美学家,他区分了唯一性的艺术和多重性的艺术、签名的艺术和非签名的艺术。英国美学家理查德·沃尔海姆(Richard Wollheim)提出,音乐作品是类型,其演奏是象征(tokens),并非类型的所有特质都能够呈现在象征之中(1)艺术本体论是当代分析美学的重要问题,许多美学家都参与讨论,提出了具有创见的观点,相关文献和分析可参考笔者近年发表的文章:①《赝品: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问题》《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4期,又见《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4年第10期;②《“行动类型”:乔治·卡瑞的艺术本体论》《西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5年第7期;③《签名的与非签名的:古德曼的美学命题及其理论效应》《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又见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15年第8期。。沃尔海姆和美国美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托夫拒绝了古德曼的音乐作品是一种类型的演奏(a class of performances)的观点。古德曼的观点是反直觉的,因为它不允许没有被演奏的作品的存在。沃尔特斯托夫提出种类(kinds)概念,这就给不正确的演奏留下了存在空间。沃尔特斯托夫的《作品与艺术世界》(1980年)一书是当代分析美学的经典著作,其中第二章对艺术本体论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沃尔特斯托夫的思路是,首先从各门艺术的存在状况的分析中得出艺术本体论的结论,然后分析音乐艺术的本体论状况,最后又应用其理论分析各门艺术的本体论存在方式。本文拟细读沃尔特斯托夫的文本,详述其艺术本体论思想,以期深化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
一
在当代分析美学的艺术本体论问题的讨论中,术语“实例”(instance)被许多学者所使用,指的是多重艺术的单个表演或演奏,比如昨天晚上学校大礼堂演奏的一曲《茉莉花》就是音乐作品《茉莉花》的一个实例。这里“多重艺术”相对于“唯一艺术”,指的是如音乐、文学、戏剧这样的艺术,它们存在于许多“实例”比如音乐作品的多次演奏、文学作品的多次印刷、戏剧脚本的多次表演中,而绘画、素描等则是“唯一艺术”,某个艺术家在某个时空的唯一创作才是界定这个作品身份的根据,这种艺术的“实例”是唯一性的。但沃尔特斯托夫拒绝使用“实例”这一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含义混乱,其理由如下:首先,在所有艺术中,都存在着可感知的人工制品,这些都可以被视为那门艺术的实例。我们看到,这些可感知的人工制品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区分为“发生性作品(occurrence-works)”和“发生(occurrences)”。其次,当某个世界以可感知的人工制品被投射,就存在着那个人工制品和其世界,而这两个也都有理由被视为艺术的实例。第三,在诸如诗歌、小说和戏剧这样的艺术中,被投射的世界自身有理由被视为艺术品的实例[1]33。沃尔特斯托夫说,他使用的“实例”,指的是艺术品的所有这些不同的存在方式。当说到“艺术品(works of art)”的时候,也是如此意指。那么,艺术品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呢?是物质实体,是“事件(events)”,是心理状态,还是某种成员的集合?
沃尔特斯托夫指出,在很多艺术中,存在着表演和被表演的区别,比如音乐、舞蹈和戏剧,《天鹅湖》的表演和《天鹅湖》这个作品是有区别的,其特质是不同的。比如“为贝多芬所创作”是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特质,任何场合对它的演奏则缺乏这个特质。另一方面,“发生在某个具体时空”是它的演奏的特质,而非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的特质。一个作品的表演是它的一个“发生”,因此我们可以称一个能够被表演的作品为“发生性作品”。发生的本体论地位很清晰,但是发生性的作品的本体论地位很复杂。发生是“事件”,它们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开始和结束在特定的时间,持续一段时间。但发生性的作品不是事件。艺术的可感知的人工制品在其本体论地位上并非都是类似的。
在非表演性的艺术中,类似于发生和发生性作品的区别也是存在着的。比如图像性作品的印刷品和这个作品之间的关系,还有特殊的浇筑雕塑和作品之间的关系,如世界各地多所博物馆里的《思想者》和罗丹的作品《思想者》之间的关系,再如多个建筑物和其蓝图之间的关系。这三者之中的前者都是物质性的客体,它们可称为客体性的作品(object-works)。印刷品、浇筑、事例(建筑的 examples)都是客体性作品的客体。即是发生和发生性作品,然后我们有了客体和客体性作品,两两相对,其特质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同一个雕塑作品能够有两个不同的浇筑,既非这两个一起,也非其中的任何一个能够等同于那个作品。而且,一个客体性作品的两三个客体中的任何一个能够被毁坏但这个作品本身不会被毁坏[1]35-37。
文学、电影和绘画与前述艺术门类有所不同。文学作品能够被抄写下来,也可以发声朗读之,两者都有拷贝本,但其中之一是物质客体,另一个则是事件。而且抄写下来或复印下来这种拷贝行为类似于客体性作品中的事例、印刷品和浇筑的生成行为。沃尔特斯托夫认为,文学文本的复制品是它的一个客体,文学文本应该是客体性作品。但既然一个文学文本的朗读是一个事件,很类似于一个表演,文学文本也可纳入发生性作品之列。因此,文学作品和文学文本既是发生性作品,也是客体性作品。
那么音乐和戏剧也是发生性作品和客体性作品吗?对于戏剧回答是否定的。一曲戏剧的人工性组成部分是一系列行为,这些行为包括言语行为和其他行为,即角色扮演行为。因此,大声朗读一部戏剧的手稿不是戏剧的表演。一部戏剧的手稿的拷贝本也不是戏剧本身的拷贝本,而是正确表演的指南的拷贝本。手稿本身可以是一部文学作品,这个作品能够有大声朗读和拷贝本。但是戏剧作品的人工性组成部分不是其手稿,手稿的一个拷贝本不是其人工性组成部分的拷贝本。戏剧没有拷贝本,它能够有的是表演,因此戏剧只是发生性作品。
音乐的情形不是那么清晰。关键的问题是,乐谱的拷贝本之于一个音乐作品的关系类似于一个文学作品的拷贝本之于这个文学作品的关系,因而有理由称一个乐谱的拷贝本为这个音乐作品的客体吗?这一点难以明确。很显然,某个词汇能够书写也能够发声朗读,但一个声音不能书写只能发声。一个乐谱的拷贝本上面的符号不是声音的实例,而是生产声音的指南的实例。当然,某些词汇系列的书写也能够被视为那个系列的发声的指南,同时它也确实是那些词汇的一个实例。某些词汇,特别是在原始文化,从来没有被写下;某些词汇,特别是技术性的语言,从未被发声朗读出来。但大多数词汇具有两重展示即书写和朗读发声。但是假设有人认为音乐由音符(notes)而非声音(sounds)所组成,而且认为音符,类似词汇,能够写下和发声,这种想法值得考虑,但沃尔特斯托夫仍然认为音乐作品包括声音。
电影似乎类似词汇,具有双重地位。一部电影有许多印刷品(prints),一个印刷品就是一个物质客体,它也有许多放映,一个放映就是一个发生。因此电影就如文学作品,能够被视为客体性作品和发生性作品。但有个差异值得注意,即一部电影的一个放映总是需要那部电影的一个印刷品(即电影胶卷),但要朗读某部文学作品,无需阅读那个作品的某个拷贝本,我们可能凭借记忆朗诵它。
对于绘画,客体和客体性作品、发生和发生性作品的区别都不能应用其上,这里作品和作品的复制品之间当然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不同于印刷品之于原作的区别。一个印记(print)的所有印刷品(impressions)都是原作,没有一个是复制品,但对于绘画不能这么看。一幅画可界定为一个物质性客体。说绘画是一个物质客体不是否认绘画的复制品以及雕塑的复制品本身是艺术品。电影也是如此,虽然它是角色扮演、视觉性事件和物体的事变的(incidents)复制品。唱片也是如此,虽然大多数唱片都是声音的发生的复制品。值得注意的是,在视觉艺术复制品和雕塑复制品,有印记和印刷品的区别或者是作品(work)和浇筑(casting)的区别。在录音,则一方面是录音(recording)和这个录音的不同唱片的区别,以及某个既定的唱片(disc)和这个唱片的不同的播放(playings)的区别[1]38-40。绘画的原作和复制品的区别,就是当前分析美学讨论的艺术赝品问题。沃尔特斯托夫提出绘画的蓝本和复制品有区别,但没有讲这种区别在何处,这种区别对于绘画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影响何在,而这是当前分析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前文已经说明,艺术的人工制品是可感知的。我们感知一个发生性作品或客体性作品通过感知这个作品的一个发生或一个客体,只有如此,才能感知到作品。在看一个印刷品的时候,我们立即看到了两种东西,即印记和它的印刷品。在听一首交响曲的时候,我们立即听到了两种东西,即交响曲和演奏。为什么要如此区分呢?沃尔特斯托夫说,对于批评家,这些区分很重要,因为同样的一个论断对于某个演奏是正确的,但对于那个作品可能是错误的[1]41。
分析了具体艺术门类的艺术本体论后,沃尔特斯托夫辨析了当前西方学界关于艺术本体论的几种观点。首先,沃尔特斯托夫认为,艺术品不能等同于任何物质客体。比如一个音乐作品等同于什么物质客体呢?是乐谱吗?但是在乐谱,我们必须区分乐谱和它的一个拷贝本,这就是另外一个客体和客体性作品的区分的事例了。那么是等同于作曲家的那个乐谱的签名副本吗?音乐作品不能等同于这种物质客体是基于两个事实,即不存在这种客体,因为许多音乐作品从来没有被谱曲过。还有,即便存在着这种客体,它可能被毁坏了但作品仍然存在着。在图像性艺术,有很大的诱惑力去把印刷品等同于艺术家准备的金属板(plate)。但这种等同也不可行,因为那个金属板可能被毁坏而印刷品仍然存在。因此,艺术品不能等同于物质客体。那么,能够说艺术品等同于意识单元吗?英国当代美学家科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1889—1943)就是这么认为的,即艺术品是某种想象性的东西,是存在于艺术家的头脑中的音调,然后他安排这种音调在某个观众面前演奏,这就形成了真实的音调。但是,这两个东西中的哪一个是艺术品呢?哪一个是音乐呢?答案是作曲家头脑中的音调。这种观点认为,听众听到的声音不是音乐,它们是听众重新构造的位于作曲家头脑中的想象性的音调的媒介。这样,音乐作品不可被感知到,它们是意识行为即想象的客体。设想科林伍德认为艺术品是意识性的单元,是一种特殊的存在类型,但它们不是位于私人意识之中,而是在意识之间可分享的,那么问题就有很多了。当某个人在想象某个四重奏的第二乐章,而且没有其他人在想象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那么第一乐章不再存在了吗?当某个人在想象第二乐章的第二个主题的第一个发生,而且没有其他任何人在想象它的任何一部分,那么第一个主题就不再存在了吗?简言之,当他只是想象了这个作品的某个部分,那么整个作品存在着吗?还只是他在想象着的那个部分是存在着的?虽然后面的解释似乎是最可接受的,但前面的解释可能是最可行的。即便如此,按照这种观点,贝多芬的四重奏、伦勃朗的印记、叶芝的诗歌,都消失不再存在了。因为在某些时刻,这些是某种意识行为的客体,在其他时刻则不是。沃尔特斯托夫认为,这种结论是错误的,问题是“这些艺术家的作品,难道至少在它们被创作以后就没有存在着吗?”[1]42-43
蒙牛并购雅士利作为乳制品产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并购,并且是一次强强联手的双赢并购,蒙牛在并购中的税收筹划做得很好,在发现自己的缺陷之后,采取并购的形式来快速弥补,并且支付方式和融资方式也达到了一定的节税效果。为企业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进行并购活动中,税收筹划应该考虑到并购过程的每一个环节,并且要充分考虑并购方和被并购方是否都得到了一定的利益,这样才可以促进并购活动的健康发展,努力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局面。
有人认为对于发生性作品和客体性作品来说,它们是其事例的集合。沃尔特斯托夫认为这个观点不可靠,原因是,一个发生性的作品或客体性的作品可能总是有不同的、或多或少的发生或客体,相比它已经有了的。即是说,这种集合是无法估计的、无限的、无法界定的。而且要注意的是,如果集合A没有成员,集合B也没有成员,那么A就等同于B。但是不能说,如果艺术作品C没有事例,艺术品D没有事例,那么C就等同于D[1]44。那么,艺术品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呢?一个作品和其事例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共享论断。比如论断“是C小调”对于贝多芬的第111号作品和其大多数演奏来说都是真实的论断。但是,不是对于艺术品可真实断言的每一个论断,或者是对于某个艺术品的某些或甚至是其所有事例都是真实断言的论断,都能够为作品和其事例所共享。比如“是一个演奏”或“是一个发生”就不能被共享(说的是作品的事例),比如“能够被重复地演奏”和“能够重复发生”或“为亨德尔所创作”也不能如此分享(说的是原作)。关于艺术本体论,沃尔特斯托夫的观点是:发生性作品和客体性作品都是“种类(kinds)”,其事例就是这些作品的发生或客体:一个发生性的作品就是某种类型的发生性的种类,一个客体性的作品就是某种类型的客体性的种类。更具体地说,艺术品都是“标准种类(norm-kinds)”[1]57-58。这里之所以强调“标准”,是因为交响曲能够有不正确的和正确的演奏,一首诗有不正确的和正确的拷贝本。“正确的”就是“标准的”,“不正确的”则是“非标准的”。
沃尔特斯托夫持艺术本体一元论,试图以某一范畴囊括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但问题是:①对于具体的艺术来说,什么是“标准的”?什么是“正确的”?考察具体的艺术品,比如音乐的演奏,“标准的”和“非标准的”是很模糊的,难以明确和量化。②“种类”这个概念,是抽象的而非实体性的意指,它包含了具有差异性的个体作品,以之界定艺术本体论,是否精确存在疑问。
二
音乐是当代分析美学家花费心力最多的艺术门类。在界定了艺术本体论之后,沃尔特斯托夫详细分析了音乐的本体论状况,他认为,音乐创作是作曲家选择一套特质作为“发生”的正确标准。被创作的作品,就是精确地有了那些特质。因此,被选择的正确的作品所必需的那套特质,能够被我们运用为演奏的指南,也可以作为评价“发生”是否正确的标准,还可以作为我们想象某个“发生”的指南[1]64-65。
在音乐,我们不要求某个作品的不同发生都听起来是类似到不可分辨的程度,而是允许其中有很大的差异。绘画则不同,其原因是,画家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选择一套特质作为发生的正确性的标准,相应地,他没有特别地确定某种“标准种类”。委拉斯开兹在创作《宫女》的时候,对于被选择的某些东西,不存在正确与否的要求。即是说,正确的要求这个问题不存在,一笔一画、各种颜料都是画家自己的选择。但是在诗歌中,我们能够确定作者手稿的复制品是或者不是一个正确的复制品,因为我们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原始手稿。沃尔特斯托夫是这么分析的:我们可以选取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这幅画的某些东西,可以设想,存在着一种类型,它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类似《宫女》的特质,《宫女》这幅画本身就是这种类型的一个事例。但是,沃尔特斯托夫说,这就不是一个标准种类。在我们考察绘画时,不存在标准种类这种东西。但是,我们能够在绘画领域构造标准类型吗?当然是可以的。如果不是把颜料应用到画布上,而是要求画家起草一套说明给画作,那么他就构造了一个标准类型。如果他愿意,他还可以依据这个说明画一幅画。实际上,这种现象早已存在于绘画领域,比如有些给孩子的绘画指南,要求孩子按数字涂颜料去作画[1]72-73。但很显然,这种描绘距离真正的绘画还很远。这个问题,借用古德曼的符号理论可以获得清晰的解释,即音乐有乐谱,乐谱是具体符号,作曲家对于自己的作品的声学特质和乐器种类的要求是具体说明了的,音乐是二阶段的艺术,演奏家遵循乐谱即是有了标准种类。但绘画的符号不是如此,因为绘画不是由字母符号构成,用古德曼的术语,其符号是密实性的(dense)、相对饱和的(replete),无需也不能以字母符号那样的东西明确界定之,绘画作品因此不存在如二阶段艺术那样的演奏或表演的问题[2]234-235。即是说,作曲家的乐谱及其对声音和乐器的说明,构成了判断演奏是否正确的标准,但绘画不存在如此标准。
以上是从作曲家的角度看音乐本体论,那么从演奏者的角度看,什么算作演奏了一部音乐作品呢?首先,必须明确的是,某个人演奏了一个作品,只有在他相信他是在演奏一个作品的时候。这么定义,是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即非常偶然性地,他的即兴演奏恰好符合某个先前作品的乐谱和所需要的特质,这种即兴的作品就不是在演奏那个作品,因为他缺乏自己是在演奏先前的那个作品的信念。那么,什么是一个人相信他是在演奏某个作品W呢?人们可能回答说,它是通过遵循作曲家所给出的正确发生所需要的详细说明,去生产一种“声音系列发生(sound-sequence-occurrence)”。但沃尔特斯托夫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对于演奏作品,遵循乐谱既非必要也非充分条件,原因有二:其一是,我们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都遵循了乐谱中的详细说明,但仍然没有能够演奏作品,因为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作曲家在乐谱中给出的正确演奏所需遵循的说明是不完整的,不足以保证遵循它就能够生产发生,更不用说正确的发生了。乐谱出现在西方中世纪,其目的是为了告知人们正确发生所需要的东西。但是,许多东西是假定性的(presupposed,心照不宣的)而非具体说明了的。作曲家常常假定了他的时代里的乐器的种类以及特殊乐器演奏的实践传统,因此,即便我们完全遵循乐谱中的说明,也可能没有能够演奏相关的作品。其二是,为了演奏与乐谱相关的作品,我们没有必要遵循乐谱中的说明。确实,我们能够演奏某个作品而根本无需遵循乐谱中的那些正确演奏所需要的说明,因为可能根本就没有乐谱,或者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如果贝多芬在他的脑子里已经创作了第111号作品,只是在后来才谱曲了,他就有可能暂时性地演奏了那个作品即便还没有乐谱。这只是一个设想的案例,但实际上存在着大量的民间音乐没有被谱曲,因此,我们不能要求正确发生要遵循乐谱中的详细说明。而且,某个作品的正确发生所需要的详细说明能够以乐谱以外的其他方式,以作曲家之外的其他人去传递给演奏者。民间音乐的演奏者能够以语言被告知某些片断要如何发声,或者正确的节奏被脚打出给他。关于演奏,沃尔特斯托夫还说了三点:其一,某个人所相信的那个作品的标准特质可能更接近或不那么接近实际上的那些特质。要说某个人能够演奏那个作品,即便不是那个作品中的所有的标准特质都被他采信如此,这么说是对的,因为在某些点上他可能不确定、忽视或犯错误但仍然演奏了作品。另一方面,某人不确定、不知道或犯错误之于某个作品中的标准特质如此严重,以至于在示例(exemplify)他相信是那些特质的时候,他并没有演奏那个作品,他还可能根本就没有演奏作品。其次,某人能够以或多或少的精确性去示例他相信是那个作品的标准特质。他不必竭力精确地示例他相信为那个作品的那些特质,如果他实际上演奏了他相信是作品W的话。实际上,演奏家,即便完全知晓某个作品中的标准特质,常常会故意远离它们,他们相信这种演奏结果可能会更好,或者有时候他们知道他们不能准确地演奏那些片段。演奏家可能很好地演奏了那个作品,尽管他远离了那些标准特质。另一方面,某人可能故意远离他知道或相信是那个作品的标准特质以至于其结果不能算作那个作品的演奏。第三,某人可能很成功地或不那么成功地试图示例他相信是那个作品的标准特质。他不必完全成功地去演奏那个作品,可能无意地敲击了他知道是错误的音符而仍然演奏了作品。另一方面,他可能没有能够示例他相信是那个作品的标准特质以至于他根本就没有演奏那个作品[1]75-78。
基于这样的复杂性,我们如何界定“演奏”这个概念呢?首先,在设想一个作品的演奏时(不仅仅是一个正确的演奏),我们都操作着这种关于声音系列发生的概念,即在其声学的和乐器性的特质上,它很接近或不那么接近一个正确的演奏所需要的特质。类似地,我们以这种概念去操作,即一个人相信是一个作品中的标准特质,它很接近或不那么接近那个作品中的实际的标准特质。这两个概念,沃尔特斯托夫认为,就是我们演奏一个作品的概念。因此,一个人演奏某个他相信是作品W的作品,当且仅当他奏出一个声音系列发生,它相当接近于示例那个作品的标准的声学和乐器方面的特质。他做到这一点是:①他相信,他的演奏是相当正确地和完整地接近作品的标准的声学和乐器性的特质。②通过生产一个声音系列发生,他试图让那个发生去示例它的大多数特质。③相当成功地生产了一个声音系列发生,并确实示例了作品的大多数特质。概而言之,就是他构造了一个声音事件以契合那个音乐作品的大多数标准特质。但要排除另外一个情况:设想某个人很熟悉某个音乐作品,他做了一个录音,这就生产了一个声音系列发生。但他没有演奏那个作品,这只是那个作品的一个演奏的复制[1]79。
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一个演奏者的目的是尽可能地把作品表演得更美,这就需要他在某些点上不正确地(不符合乐谱)演奏作品。作曲家可能在创作的时候不是这么想的,可能仍然不这么想,但他可能犯错误。正确的演奏可能会更好些,如果演奏家做了其他的事情,即是具有一个微小的不同之处的作品被创作。试图去生产尽可能美的演奏不可避免地需要演奏家在各种重要的事情上做出决定,即便这里正确性不在讨论之时。在这样的事情上,作曲家可能有了一个计划,他可能甚至已经表达了它,他可能已经意图他的作品要如此演奏,因为他认为这么做会产生更好的演奏。但是,他仍然可能犯错误。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作曲家选择了哪些特质去判断发生的正确与否呢?沃尔特斯托夫回答说,我们应该找到最好的证据。首先,我们要去发现作曲家视为理所当然的实践传统的相关部分。其次,如果作曲家已经写出了,或者授权了一个乐谱,我们就要去找到他的原始乐谱中相关的方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如果关于实践传统的精确知识已经失传了,而且可能从来就没有乐谱存在;或者是如果有乐谱,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原始乐谱,也无法获得可靠的证据去获得相关的部分是怎么样的;或者是,我们从作曲家的手上找到了几个不同的拷贝本但不知哪一个是最真实的;或者是我们有了原始乐谱的复制品,但我们意识到它包含了作曲家犯的几个错误,而我们发现不可能去确定正确的复制品是什么样的;或者是,我们有了一个原始的、真正的、正确的复制品但是再也不知道如何解释那些符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应该承认我们在某种程度不确定作曲家到底选择了哪些特质作为发生的正确标准。基于这种无知,我们也不能知道作曲家选择了什么样的标准种类,因此无法得知他的作品的本质。民间音乐则有所不同。民间音乐家群体可能使用某些特定的特质作为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通常,他们会推举某些人为权威,比如某些老人知道某些音乐作品是什么样的。如果他们在某些点上有分歧,那么在这些点上这个群体就缺乏正确的标准[1]82-83。
某个音乐作品是一个“标准种类”,其“事例”是“声音系列发生”。那么,音乐作品等同于哪一个种类呢?比如贝多芬的111号作品的某个事例,它可能不是一个演奏,不是某个人在演奏那个作品。它可能被某个人操作在自动钢琴(player piano)或电唱机(record player)上。任何一个“声音系列发生”,只要它有了某个作品W之内的所有的标准特质就都是这个作品的事例。因此,沃尔特斯托夫得出结论说,音乐作品等同于这种种类:通过演奏或操练(playing)作品W而产生的声音系列发生[1]86。
沃尔特斯托夫认为,种类不是形成的,也不会消失。音乐作品既非形成也非不再存在。一个种类存在着,只要其相关的特质存在着。对于任何特质,比如雅致,某种东西要么是雅致的,要么不是雅致的,但存在着雅致这种特质。很显然,这种观点的结果就是,特质,也因此种类,并非生成(become)也非毁坏(perish)。因此,在沃尔特斯托夫看来,一个作曲家并没有把他的作品带入存在,音乐作品是永恒地存在着。作曲家所作的应该理解为把预先存在着的种类变成一个作品,一个属于他的作品[1]88。沃尔特斯托夫的这种观点其实是特质是永恒存在着的,只要一个特质存在,那么种类就存在着,那么音乐作品就永远存在。这就是西方音乐理论中的柏拉图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创作不是作曲家把某种东西带入存在,它是把某种东西变成一个作品。作曲家做到这一点是通过选择特定的特质作为发生的正确标准。虽然作曲家可能在其选择中具有创造性,但他不是一个创造者。作曲家带入存在的唯一的东西是他的乐谱的一个复制品(copy)、一个记号(token)。在音乐中,创造通常就是记号创造(token creation)[1]89。作为虔诚的基督徒,沃尔特斯托夫拒绝把创造概念运用到人身上,因为只有上帝才能创造。音乐理论中的柏拉图主义在西方历史上影响久远,当前美国美学家杰拉德·列文森和彼得·基维就这个问题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本文认为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①抹杀了作曲家的创造性。莫扎特确实给西方音乐贡献了重要的作品,在他之前和之后都不存在这种作品。②即便是选择特质,也不能抹杀是莫扎特的创造性的选择。③按照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文学家不过是选择了预先存在的文字,只是把已经存在的汉字加以组合,但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文学创作远非汉字组合这么简单,涉及价值观重构、审美意象构造、修辞选择、人物塑造等,这是其创造性的地方。④如果没有创造,那么艺术领域就缺乏天才,艺术品也就没有高下优劣之分,评价艺术就不可能。
关于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沃尔特斯托夫还考虑了诸多复杂情况。前文已经说过,音乐作品的许多事件的发生是基于某个人操作那个作品的演奏的某个录音带的录音。我把一个磁带播放在我的磁带机上,在我的卧室就有了马勒的交响曲的一个事件。现在即便那个被录制下来的演奏是完全正确的,我播放磁带所产生的事件仍然可能是那个作品的不正确的事例,这可能是基于设备的某种缺陷,或者是我未能正确地使用设备。相应地,在我的卧室里发生的事件不是马勒的交响曲的演奏,所发生的只是一个演奏的复制品,是那个作品的一个播放(playing)。还有一种情况是,作曲家可能直接在磁带上创作,这样就生产了一个磁带而不是录制某个声音系列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作品的发生(occurrences of the work)”是为某个人播放原始磁带而引起的,或者是从之而来的一个拷贝本所引起的,这么做的结果是产生了那个作品的真正的“发生”,虽然不是它的演奏。同时,它也只是那个作品的一个播放。关于这后一种情况,有三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作曲家,虽然他选择了正确事件所需要的特质,但他并没有用符号去说明那些特质,他仍然想要他的作品为大众所获得去生产“发生”。因此他生产了一个人工制品,它和其复制品能够被用于生产那个作品的“发生”,但他没有给出指南去生产这样的“发生”。如果标准的磁带或其拷贝本被正确地用于生产某个“发生”,那么那个作品的一个正确的“发生”就出现了。第二,关于如何使用他的磁带去产生他的作品的一个正确的“发生”,作曲家无需说任何事情。他能预设如何操作磁带机以及机器的标准设备,他需要给出的唯一指南是:以常规的方式使用机器。这种指南是一般性的、非特殊的,对于任何个别的操作都是有效的。第三,不仅如此,在磁带机的“实践传统”中,每一件事都是常规性的,调试和反馈是很少的,正确使用一个磁带无需很多知识和技巧。这一点与传统的有乐谱的音乐有很大的不同。在传统音乐,首先,作曲家也预设了正确操作某种类型的乐器,预设了操作那些乐器的实践传统。但是依据实践传统操作那些乐器需要演奏者有大量的调试和反馈。其次,作曲家必须给出细节性的指南之于他自己的特殊创作,以便于实践传统中的那些有技巧的人知道用他们的乐器应该做什么以便于生产作品的正确“发生”。最后,作曲家所生产的人工制品,即他的签名乐谱,不是一个人工产品(production-artefact),它实际上不是用于制造所需要的声音。小提琴和琴弓才能制造声音,乐谱无法完成这种工作。所有这些差异都是这一事实即作曲家提供给磁带的人工制品不是一个符号系列(sequence of symbols,乐谱才是)所导致的,对于生产他的作品的正确“发生”,它不能给出指南,它只是一个能够被用于自身的生产过程的人工制品[1]90-92。
沃尔特斯托夫不赞同古德曼的音乐作品是类型(classes)的观点,他认为音乐作品是种类(kinds)。首先,所有缺乏演奏的作品都是相互等同的。只存在一个这样的作品,因为只存在着一个无效类型(null-class),虽然存在着很多未被演奏的作品。其次,一个音乐作品能够有或更多或更少或不同的演奏,相比它实际所有的。第三,考虑到只有当其成员存在着,一套集合才存在,那么不存在这样的集合,即其成员是所有的而且只是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的演奏。在任何时候,“由所有的而且只是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的演奏所构成的集合”这一表达会选择出一个集合,但它选择出的集合会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依赖于发生在那个时候的诸多演奏。但是,通过这些集合的变迁,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持续存在着[1]100-101。 即是说: ①音乐作品是种类, 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物, 它由乐谱和各种契合之的演奏所构成。 ②没有被演奏的作品不是真正的音乐作品, 只能是潜在的作品。 ③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是种类, 它的各种演奏构成了一个集合, 但这个集合的成员是无限的, 随着时间而增加的, 因此不存在已经包含了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的所有演奏的集合, 但第一交响曲因为这个不断变化着的集合而存在, 依赖其成员而存在。
沃尔特斯托夫分析了音乐作品的本体论状况。在第一部分的结尾处,我们表达了对其“标准种类”这一界定的疑问,第二部分证实了这种疑虑。沃尔特斯托夫自己说,绘画不存在“标准种类”,音乐演奏只需契合大多数标准特质,有时候还需要“不正确地”演奏作品等等,这些说法表明“标准种类”这一概念是模糊的,难以契合各种艺术的存在方式,而且音乐本身的复杂情况,似乎挑战着“标准种类”的存在。如果这一界定并非能够说明各种艺术的存在状况,其含义和存在价值就有疑问。
三
在详细分析了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之后,沃尔特斯托夫以他的理论分析了其他艺术门类的本体论问题。电影作品既类似又不同于磁带上的音乐作品,这里也有正确和不正确的事例。类似的地方是,这里联系到作品的是一个人工制品,它被用于自身的生产过程。要确定那个作品中哪些是标准特质,这部分取决于何为成功的放映,而且,正确使用相关器具即投影仪对于任何电影作品都是一般性的,依据“实践传统”的那些器具的使用也完全是常规性的。电影作品与磁带上的音乐作品不同的地方是,两个人即编剧和导演在负责这个作品,他们选择了正确发生所需的条件,而且他们是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做出他们的选择的。沃尔特斯托夫说,我们可以把电影视为纯粹的视觉艺术。生产一部电影作品的过程开始于编剧的手稿。编剧选择特定的特质之于“颜色模式系列发生(colour-pattern-sequence-occurrences)”。在他的手稿中,他给导演以指南去生产一部规范的电影,即以标准的方式操作投影仪,放映会随之产生,它会展示所被选择的特质。导演的工作就是生产一部电影,把一部电影作品带入存在。直到出现了它的一个投影,直到有人把它带入存在,某部电影作品才真正存在着。相应地,编剧选择了他视为他的作品的规范性特质。在选择中,他并非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作品。导演生产的电影,就如磁带上的创作,是一个人工产品。在生产的时候导演或多或少精确地遵循编剧的指导,但对于作品的特质,他必须做出大量的选择工作,这就不可能不超出编剧的指南。其结果是,对于“发生”的正确来说就存在两套标准,一个是编剧的,另外一个是导演所做出的实际选择。导演的选择相比编剧的更为细化。他们的选择有时候很协调有时候会有冲突,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我们有了两个不同的电影作品。一个电影作品的标准特质指的是,以常规的方式正确操作投影仪的时候,某个放映不能缺少的特质。
导演监制了电影的生产,他要遵循编剧的指南。但即便他没有遵循,作品的放映没有契合编剧的设想,这也并没有生产编剧的电影作品的不正确的“发生”。也确实存在着作品的不正确的“发生”,但这是基于不正确地使用投影仪所导致的,或是使用电影的有缺陷的拷贝本导致的。很显然,这就暗示编剧的手稿可能被不同的电影作品的生产所使用。翻拍一个手稿不是同一个作品的不同的“生产”,它就是生产了一个不同的作品。即是说,同是苏童的剧本,分别由张艺谋和陈凯歌所拍,这就是两部不同的电影作品。电影作品和戏剧作品的差异在这一点上很明显。典型的电影是要演员扮演角色然后拍摄制作而成,但是发生在某个电影作品的某个放映中的事情不是角色扮演的实例,而是包括某种“颜色模式发生”的一个事件,角色扮演本身并没有发生在电影中,演员发挥功能是在把一个电影带入存在的创作过程之中,在作品的“发生”中他们不再出现(出现的是他们的影像)。而戏剧,相反的是,在把作品带入存在的创作过程中,演员没有发挥功能(戏剧剧本的完成就是创作了作品,就是把作品带入了存在,演员在此是不需要的)。毋宁是他们被需要在作品的“发生”之中[1]92-95。
在图像艺术(graphic art),艺术家也准备了一个人工制品,即他的底盘(plate),被用于生产事例。如果一张合适类型的纸,通过合适的墨水和正确行使功能的印刷机,以正确的方式被牵引出来,其中艺术家的底盘作为印刷的底版,这个时候,作品的标准特质就是一个印记(impression)应该有的特质。这种情况下,那个人工制品并无拷贝本,即是说,艺术家的底盘不允许作为其他底盘的原型(prototype)。而且,什么是合适类型的纸张,什么是合适的牵引方式,什么是合适的着墨,都无法以印刷中的“实践传统”去界定,这些都需要艺术家自己确定。他使用底盘的方式,对于其作品是高度特殊化的。在着墨时,也有大量的调适和反馈,这是一个具有高度技巧的领域[1]95。沃尔特斯托夫认为,建筑类似音乐作品。建筑师生产的人工制品即他的建筑蓝图是一套符号,它表明了正确的事例所需要的诸多特质,蓝图是生产正确事例的指南。戏剧的情况要复杂些。戏剧的核心是一系列角色扮演,正确的事例包括那个系列的一个“发生”。一个戏剧作品是某个人选择一套所需要的正确特质之于一系列角色扮演的“发生”。这套特质通常是在手稿中,这也是给导演和演员的指南。在戏剧,导演并没有创造任何人工制品,是手稿的作者把戏剧作品带入存在之中,毋宁是戏剧手稿给出了指南之于产品(production)的构思。一个戏剧作品的产品本身能够有许多表演,它本身是一个发生种类(occurrence-kind)。因此在戏剧中,就如在电影中,我们有了两套正确的标准:一个是手稿作者的,一个是导演的。在后者,如果演员偏离了他的要求,他的产品就被不正确地表演。沃尔特斯托夫强调,在谈到戏剧表演的时候我们是在处理两个不同的作品,各自有正确的要求,一个是作者的戏剧作品,一个是导演的戏剧产品。如果导演并非在所有方面遵循作者的指南,那么两者之间就有了冲突。产品通常包括在戏剧作品之内,因为产品是更为细节化的,导演必须解决戏剧家留下来的悬而未决的所有问题。相比通往戏剧作品的正确表演的道路,通达一个产品的正确表演的道路更为直接和狭窄。但是,一个戏剧表演,作为两个不同作品的“发生”,能够以两套不同的正确标准去评价,即作家的戏剧作品和导演的产品[1]96-97。沃尔特斯托夫指出,文学作品的作家,既没有提供指南去生产正确的事例,也没有生产一个人工制品被用于生产过程。毋宁是,他生产了原型性的事例,即他的作品的一个真实的拷贝本或真实的“发声(utterance)”。对于诗人或小说家签名的版本,无需敏感力,我们就能确定某种东西是否是那个版本的复制品[1]97-98。也就是说,对于文学,辨别手稿与其赝品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作家自己的书写和签名是独特的、唯一性的。
在分析了各门艺术的存在状况之后,沃尔特斯托夫提出了“标准种类”这一界定,然后以之再次分析各门艺术,循环往复,层层推进。在具体分析中,各门艺术存在状况的复杂性被揭示,但同时,“标准种类”这一界定在具体分析中表现出并非“标准”:标准是模糊的,种类是抽象的,模糊和抽象遇到具体,其解释效力就是有限的。但这并非完全否定这种界定的价值:理论需要抽象才有价值,但抽象本身与具体是有距离的,这是思维本身的两难。
四
沃尔特斯托夫的艺术本体论以其细致详实地考察了各门艺术存在的独特方式而给分析美学贡献甚巨。艺术本体论是当代分析美学的重要问题之一,限于篇幅,此处不展开分析和比较其他美学家的艺术本体论观点。沃尔特斯托夫的观点也引起了学界的争鸣和批评,尤以美学家肯达尔·沃尔顿的批评最为详尽深入,此处引入沃尔顿的批评,可见沃尔特斯托夫的理论的效应,有助于我们多维审视其美学观点。在比较艺术品和其“实例”(instances,沃尔特斯托夫反对当代艺术本体论中的这一术语,他用的是“事例”:examples)的时候,沃尔特斯托夫有许多新奇的见解,他说,有些是艺术品的事例,有些是人工制品用于生产事例,或者是指南去生产事例,或者是原型从之推导出其他的事例,或者是原型去生产其他的人工制品。但沃尔顿认为,艺术品的实例中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这是沃尔特斯托夫忽视了的,而对这些实例做出区别是很重要的。有些实例是对作品的解释,如音乐演奏和口头朗诵诗歌,其他的实例则不是对作品的解释,比如电影放映、诗歌复制品、建筑蓝图的具体化通常就不是对作品的解释。要说清楚这种差异包含什么、解释是什么,这是不容易的。还有些事例,如何分类之难以明确,比如爱森斯坦的某部电影的一个放映可能在很多方面不同于另外一个放映,比如屏幕的大小、剧院的黑暗程度、声音的特质、观众观看的角度、在场的不相干的声音等。沃尔特斯托夫在谈到音乐作品的演奏的时候谈到了反馈(feedback)和调整(adjustment),这应该是解释某个作品而非仅仅示例它;在谈到视觉作品的印记的时候,他也说存在着大量的反馈和调整,以及大量的技巧存在的空间。沃尔顿说,印记通常不算对作品的解释,其中的技巧是为了获得作品的清晰和精准,而非对作品的有趣的或满意的解释。而且,我们可以在钢琴上无思考地、机械地弹奏一个奏鸣曲而无反馈或调整,但其结果,即“声音系列发生”构成了对作品的解释(可能是糟糕的解释)。听众欣赏的不仅仅是他听到的声音,而且是被演奏的作品本身。声音把作品呈现给他,它们以某种方式描绘它、解释它[3]。
沃尔顿不赞同沃尔特斯托夫的“我们不能从一个演奏中提取一个作品”这一观点。沃尔特斯托夫的观点是,我们不能以声音特质去界定正确的演奏,声音不能界定一个独特的作品,正确演奏需要乐谱和契合之的一套标准特质的结合才是可能的。他的结论是,即兴表演不是创作,不存在这样的艺术品即某个即兴演奏是它的一个事例。因为即兴表演,不同于创作一个乐谱,不是通过呈现正确的标准去具体说明(specify)一个作品[1]64。在这个方面文学不同于音乐,他认为,某部小说的一个复制品,我们通常能够说出它的哪些特质对于正确性是根本的。因此这个复制品就具体说明了它是其事例的一个特殊的艺术品[1]97-98。但沃尔顿认为,这种对比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错觉。一部小说的复制品的纸张上面的黑色字迹自身并没有呈现正确标准,一个音乐演奏的声音也不能。它们如果能够呈现,是借助相关的惯例,但是在很多音乐传统中也存在着惯例去从音乐演奏中提取正确标准。当然有时候存在着含混的情况。不清楚的是,某个演奏中的某个颤音或某个自由节奏,对于正确性是否是必须的,这样的含混情况经常发生在音乐演奏中,它们在音乐乐谱中也是很常见的,诸如包含了这样的符号如tr,或鲁巴托(rubato,音乐术语,指的是在处理节奏时可自由发挥)的乐谱中。如果乐谱具体说明了音乐作品,我们就没有理由否定演奏也具体说明了音乐作品。如果生产一个原始性的乐谱就是创作,那么,当合适的惯例运作之时,即兴创作也可被视为创作。沃尔特斯托夫区分了某个演奏的正确性和其审美优异,即正确地演奏某个作品并非意味着这个演奏在审美上就是优异的。沃尔顿则进一步分析,在演奏中,还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审美优异,如清晰性或独特性,即这个演奏是如何清晰地呈现了正在被演奏的作品的;演奏作为对作品的解释的价值,即它是否有趣地或以满意的方式解释了作品;存在着演奏只是作为声音系列的审美价值,而不管它是作为对某个既定作品的演奏[3]。
在中国当代哲学界和美学界,本体论这一概念歧义纷纭,含义和所指往往南辕北辙。对这一概念在中西学界的流变以及所导致的学术研究的困境,需以专门文章论述,此处不赘。在西方美学史上,20世纪之前的美学家并没有关注艺术本体论问题,在20世纪,罗曼·英伽登和克罗齐深入论述过艺术本体论。当代分析美学家对艺术本体论投入了巨大的关注,提出了多样化的观点。沃尔特斯托夫最大的贡献,是对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的复杂性的仔细分析。总结沃尔特斯托夫的艺术本体论:①艺术品是“标准种类”。②作曲家是“发现”而非“创造”了音乐作品。③各门艺术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沃尔特斯托夫以“标准种类”概括和界定各门艺术的本体论状况,这一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广延性,但在具体艺术品,“标准”本身是模糊的,“种类”则表明沃尔特斯托夫的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即“种类”类似“理式”。在沃尔特斯托夫看来,种类不是物质性的客体,但它们的事例是物质性的客体,那么难题就如门罗·比尔兹利指出的,这种观点“允许作品和其事例之间存在差异:第一勃兰登堡协奏曲的某个特殊的演奏会有许多不属于其种类的特质, 而且, 可能基于演奏者的失误, 某些演奏可能缺乏属于其种类的特质。”约瑟夫·马戈利斯反对说, 种类是抽象的单元,这样, 不像艺术品, 它既不能被创造, 也不能被摧毁。 这就需要对“创造”和“摧毁”这一对概念作新的解释[4]XXVI。 虽然有这些弊端, 但“标准种类”这一界定基于具体艺术门类的分析, 具有较高的解释效力和理论普遍性, 值得中国学界借鉴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