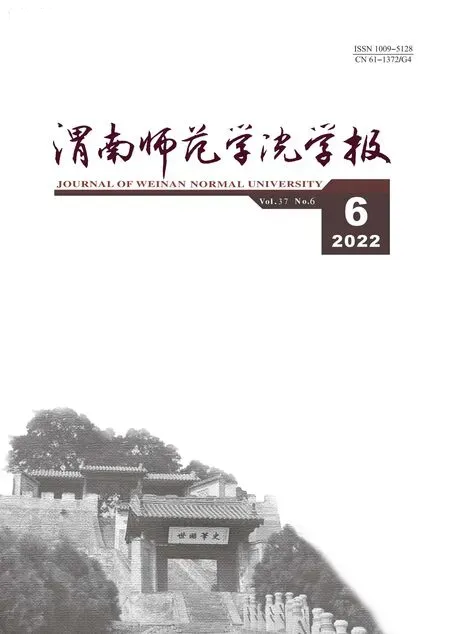司马迁天人思想的五重向度
魏 三 原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南京 211189)
司马迁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的天人观中。然《太史公书》内容磅礴、体裁多样,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思想散落在不同篇章并未有明确体系阐述,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事件、人物、纪事来彰显,因此前后文势必出现不同角度的表达,也从侧面反映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多重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界基于不同角度去审视司马迁天人思想,如侯外庐、任继愈等用唯物认知范式去评价,白寿彝从宗教、自然发展、人事等维度去分析,霍松林、徐兴海等侧重司马迁对“天”的模糊性表达,金春峰、张大可等认为司马迁具有重视人为的巨大进步性等。[1]近些年学界出现了从特定视域探究司马迁天人观的趋势,如张瑞芳、章启群、赵继宁等学者从巫史儒关系传承、占星学、《天官书》考释等具体视角作出新阐述。
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将司马迁天人观视为一个整体,综合学术批判、科学认知、历史发展、政治环境、人生命运等五个向度进行阐释,每一个向度都是立足于对司马迁所处时代背景的回应,它们之间不仅并不冲突,同时具备相当的自洽逻辑。这或许可以进一步补充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哲学研究。
一、“天人之际”学术批判向度
“究天人之际”是司马迁著书的重要旨趣与阐述思想的载体。在《汉书·司马迁传》收录的司马迁给任安的书信中讲“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2735,在《天官书》中讲“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3]1595,《太史公自序》中讲“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3]4027,此三处“天人之际”明确出自司马迁之口,其余有关“天人”关系的论述在其书中更是繁多,此不赘述。既然司马迁本人明确表示关注“天人”关系的思考,那么确定“天”之内涵有利于分析何为“究天人之际”,且先从字源衍变试看其语义。
古字“天”有多层含义:一是与地面相对的上空。“天”不仅被代指天空、天体,还有自然、天气、特定空间等。[5]522受限于远古时期人类文明水平的发展,人们生活在厚重的土地上,与之相对的“天”被人们认为是有意志的神,这带有强烈的宗教主义色彩,但又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条件。二是人的头顶。商朝时期,“天”字是一个人的图形;西周至春秋时期,“天”字最上的符号逐渐由“点”变为“一”。《说文解字》解释:天,颠也,至高无上。颠有顶部的意思,结合“天”的象形,可以看作人的头颅的意思,而通过西周时期“天”的象形也可以将其看作处于人之上的至高无上的象征。《说文解字》释云:“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6]1可见处于人之上的“一”被赋予高层次的统摄与主宰之意。
在司马迁之前,“天”已具备多重内涵。其一,具有宗教性的政治内涵即主宰之天。夏商时期,“天”具有人格的主宰性与宗教色彩的政治统治权威,人们尊上帝、崇祖先,“天命”即为“上帝”。《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尚书·夏书·甘誓》载:“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可知“天”作为主宰性质的人格神,为政权提供合法性担保,对“人”进行宗教性质的约束。其二,具有道德内涵,以用来论证政权更迭与警示统治者。商周之际,“德”“礼”被纳入天人关系之中,如《尚书·召诰》记载:“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商周的政权交替使人们对“天”的主宰性发生质疑,周人对“天”进行了改造,将殷人对至上神“天帝”的尊崇继承并保留了其至上权威[7]13,提出“以德配天”论证周人代殷的统治正当性,而这一内涵的出现可以看出“天”绝对权威的地位下降,并有民本思想的雏形。其三,先秦诸子分别从哲学层面解构了早期宗教之“天”,老子“天道”、孔子“天命”、墨子“天志”、孟子打通“天”与心性、荀子认为“天行有常”等,由此引申出“规律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等内涵,极大地丰富了“天”之哲学范畴。商周、先秦的“天”逐渐成为中国哲学体系中的核心范畴与概念,它伴随着中国原始宗教向理性哲学思考的转型,由此涉及天道观、天命观、天人观成为早期中国哲学的关注重心,这是学界的共识。上述举例大体囊括了司马迁之前人们对于“天”的认知,虽然对一些思想家关于“天”的思考未具体涉及,但大体都是围绕这几种内涵进行研究。
由此我们可知,司马迁之时,关于“天”的内涵已经极为丰富,学界曾就司马迁所著文本中的“天”作了多种解读,其实司马迁作为总结历史、传承思想的大家,其“究天人之际”应当是对上述不同“天”之内涵的回应,“天”之内涵应不出前人理解。司马迁如对“天”有更为别具一格的内涵表达则会在其著作中非常显眼或着重突出。因此关于司马迁思想中“天”的解读,笔者倾向于借用前人已有的“天”的内涵在司马迁之文中对应比照即可。明确“天”之内涵,则“天人之际”不言而喻。基于立场论的不同,人们对“天人之际”也会有不同看法,其实质仍然是对司马迁“天”的内涵定义不同。举例徐复观先生认为,司马迁心中的“天”,只是一种神秘之力,对人的行为不会作出教诫性的反应,因而司马迁所谓“天人之际”,指的是划分“天”与人的交界线。[8]298由先秦至汉初学术发展可见,人们关注的都是“天人”之间如何发生关系,其内在具有何种规律。因此可以讲“究天人之际”就是司马迁对于研究天人关系的表述而已,不需进行过度解读或产生分歧,从广义上讲,即使是探究“天”与人的交界线也仍然是某一种关系而已。
首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具有包容的多元色彩,这与他本人学术积累有关。《太史公自序》记载了司马迁与其父司马谈的从学经历:
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3]3991-3993
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3]3998-3999
可知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二人史官世家,且自身皆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司马迁本人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他以孔子作《春秋》为榜样,还曾师从董仲舒、问学孔安国,且有游学、为仕等实践经历,这为他能够包容接受不同观点提供了先决条件,可见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是继承各家思想精华的基础。
其次,司马迁天人思想具有传承性,体现在他对前人思想的不同记载中。他在对前人天人思想的记载与评述反映出个人的天人观,这不仅是对过往史料的梳理,也是借史表达深刻思想与高明政见。[9]217如《孔子世家》中记述孔子言行:“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3]2327“子不语:怪、力、乱、神!”[3]2349“夫子言天道与性命,弗可得闻也已。”[3]2349“天丧予!……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3]2351司马迁本人对孔子评价极高,不仅作书目的是效仿孔子作春秋,而且去鲁地孔庙,称其为至圣。《论语》中关于“天”“命”等涉及天人关系的言语远不止这几句,因此司马迁所选取孔子言谈绝不是随意而为,它们所代表的天人思想的内涵是被司马迁认可和接受的。司马迁包容性的天人思想也体现在他对前人思想的评价中。如《孟子荀卿列传》:“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王公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3]2848-2849“怪迂之变”“闳大不经”“不能行之”等词表现出司马迁对邹衍五行学说隐晦的否定态度。《儒林列传》关于董仲舒记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3]3798“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董仲舒恐久获罪,疾免居家。”[3]3799“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3]3800所不同的是,《汉书》详细论述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然司马迁在此并未具体提及。司马迁在此处描述董仲舒个人经历的变化以及其后学的情况,呈现出一种历史动态的画面,尽管司马迁曾从师于董仲舒,但未详细记载董子学说,可见对其天人思想的态度是存而不论的。
综上,司马迁“天”的内涵大体是承袭前人而来,“究天人之际”也并非司马迁的专利,而是秦汉时期的哲学主流,当时的学术思想也不乏有迷信、夸张之词。面对汉初思想趋于大一统的环境,司马迁天人观也非某种既定的唯一的观点,他秉持包容性、非排他性的学术态度,对各家不同的天人观进行引用、摘录;同时,司马迁本人的天人观是在吸收前人丰富的符合时代需求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一家之言”对纷杂各异的观点进行回应。据此逻辑去分析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
二、“天象规律”自然科学向度
从社会背景来看,司马迁天人思想具有进步性。荀子曾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惊世观点,然而在汉初经过黄老与董仲舒的发展,“天”作为自然天象的色彩不甚明显。司马迁保留了从客观认知、科学发展的维度去谈论“天”,对当时的天人思想具有一定挑战性。
司马迁天人思想包含着将“天”作为宇宙对象的客观认知维度。司马迁祖上掌管天文、地理等职,即对天象、地表等自然变化进行记录分析,而后转为史官。其父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并对天象变幻、阴阳学说有着明确评判。如《太史公自序》中言:“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3]3995由“未必然”一词,以白寿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史官这个职务与天象历法都有联系,司马迁也学过星象学,在对天象变异的态度上,司马迁和阴阳五行家有区别:阴阳家加以附会,司马迁则保留。司马迁对天人关系持有明确的态度:“天是天,人是人;天属于自然现象,和认识没有什么必然联系;人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去办事,但不存在所谓预兆和吉凶福祸的问题。”[10]23然而在此处,“未必然”只能证明阴阳家的“教令”不是绝对的,不可作为否定天人相联系的论据。我们并不能说司马迁本人完全否定了“天人”之间的吉凶福兆,而是可以肯定他在“究天人之际”时包含着所谓的理性客观认知,从宇宙自然的存在来认知“天”及其规律即“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人如何依此种自然规律进行生活。
司马迁天人思想具有科学精神,这表现在对天文学长久以来的发展予以总结。在《天官书》前半部分,司马迁对汉以来的天象作了系统梳理,并在多处描写了天象与社会政事、自然灾异的相互关联,在此不多做赘述。若抛去天象与人事的附会,则可发现当时人们对天文学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与相对科学的认知,如对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日食、月食的周期变化,北斗星位置以及众多星象的变化等。这种对自然天象的不断认知是与农耕文明的发展相契合的,历经千百年对天象的认知、分析从而总结出现实经验以有利于人们耕作、生活。司马迁在《天官书》后半部分对前人关于天文学的认知以及能否比附于人事给出了自己的态度。“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内冠带,外夷狄,分中国为十有二州,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类于地,天则有日月,地则有阴阳。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而圣人通理之。”[3]1599此处的“三光者,阴阳之精,气本在地”,刘学智先生认为司马迁承继并发挥了荀子的思想,把“天”回归为主要不具有神秘色彩的自然界,是以先秦的“气”论作为其宇宙论的根基的,从而奠定了他的天人论的基础。[11]89然而本体论或宇宙论的说法是今人才有,中国古人的学术旨趣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这段话的重点应表现在人们始终关注天地宇宙的自然变化,且其间的运行规律非圣人不能知。《天官书》载:“幽厉以往,尚矣。所见天变,皆国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时应,其文图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3]1599-1600此段可见司马迁认为历史流传下的很多天象都是“以合时应”,不具备真实性。他举孔子“罕言天命”为例,只作记载而不详加附会与传授,可知对“天”之认知具有谨慎客观的精神。
综上,司马迁天人思想重视“天”作为宇宙对象的客观存在,对天象的变化作了翔实的梳理,严谨地求证天象变异与人事变化的规律,从侧面完善了人们对于天文学的认知。在与当时学术风气相左、尊“天命神授”“天人相与”“阴阳变化”的背景下,司马迁客观科学的天人观维度对于当时流行的天命神学和“五德终始”的神秘主义历史观而言,都是极大的进步。[12]232
三、“岂非天哉”历史哲学向度
天人思想自商周至汉初经历了从尊天的服从、重人的反思、又到尊天的逻辑转变,这一过程中不仅“天人”的内涵在不断丰富,而且显示出与政治需求、社会体制始终保持内在的适应性。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以天人关系为切入点,如郑国子产的“天道”与“人道”之问、老子“天道”、墨子“天志”、孔子“天命”等,进而论述不同政治主张。至秦汉逐步完成大一统体制,天人关系再次转变,重新强调“天”具有主宰性的政治价值,如《吕氏春秋》、董仲舒“天命神授”等观点。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同样没有脱离这一历史规律,其天人思想表现出了与武帝时期大一统思想的适应性,即主动或被动地用“天”支持当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
首先,司马迁认为“天”具有政权来源的内涵。《秦楚之际月表》中司马迁表示:“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3]921“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3]922司马迁认为一统天下之业何其艰难,秦奋发百余年完成一统,实施一系列维护一统之策,却最终为没有封土的刘邦做了嫁衣。所谓“受命而帝者乎”正是受“天”之命的表达,并非由原先的诸侯、世家所获得天下,而是由“无土”的刘邦完成了王天下。这种历史局面自三代以来确属罕见,继而发出“岂非天哉”的感慨。如《魏世家》:“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易益乎。”[3]2252司马迁认为秦之一统大业是应天而出,魏国不得天意无论如何并不能改变历史局面。又如《留侯世家》司马迁描述:“良曰:‘沛公殆天授。’”[3]2475《外戚世家》:“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3]2387“迎立代王,是为孝文帝,奉汉宗庙。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3]2390应当说在涉及汉朝尤其是高祖刘邦等帝王相关事迹时,司马迁对“天”赋予政权来源的作用表现出恳切的态度而不含糊。
其次,“天”具有历史规律的内涵。《高祖本纪》中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汉兴,承弊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3]493-494司马迁认为夏、殷、周的兴起在于实施合理的管理政策,肯定三王之道,否定秦背道而驰,并把这种合理性以“天统”表达。这说明“天”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统治者的合法性来源与实施政策的规律性统一于“天统”。
最后,“天”具有人事制度的内涵。《律书》:“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3]1481“律历,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气,天所以成孰万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气也。”[3]1483-1484“旋玑玉衡以齐七政,即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钟律调自上古。建律运历造日度,可据而度也。合符节,通道德,即从斯之谓也。”[3]1495在此,司马迁的记载表述将朝代兴衰与“用事”归于“天”,表现为沟通五行八正之气、成熟万物的律历与“天”相关。然则律历必定是人之所为所作,在此却仍与“天”相关联,司马迁的记载认可将人为之事附会于“天”的体系,与当时阴阳五行学说以及董仲舒“天赋人数”有内在呼应。他们习惯于给天赋予绝对高度来为人事作支撑,这并非单纯、片面的迷信,也符合当时人们认知能力的发展。尤为注意的是,司马迁重点关注到长久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律历具有合理、符合人类发展的作用,再反之将其与“天”的权威性相关联,并非任意牵强附会。
白寿彝先生认为司马迁要成一家之言,在政治方针上是针对汉武帝的儒家独尊而出发的,与董仲舒代表的正统思想针锋相对,也表明了司马迁的政治主张。[10]19其实应当说司马迁在政治表达上与董仲舒的天人说以及当时政治环境具有内在适应性,绝不是坚决地、完全地站在对立面。通过上述分析,司马迁“究天人之际”在涉及大一统政权来源、规律、制度等方面与时代表现出明显的契合性,尊崇“天”作为最高统摄,其天人观保留了“天”的主宰性与政治价值,这无疑是对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认可与妥协。
四、“天生民本”政治哲学向度
在前文提到,司马迁之前从哲学上考察“天”已具有多重含义,但最具现实性的无疑是伦理道德的“天”。自周代商便已显现出“以德配天”之内涵,先秦以来关于“天”的内涵都保留着伦理的底蕴。[13]8孟子通过“存心、养性、事天”打通了“天”与人性,为人的德性准则赋予神圣来源。至司马迁时,董仲舒突出“天”的概念,把伦理规范上升为“天”,由“天人相通”到“三纲五常”完成了伦理根源至上性改造。司马迁在记载或评述中有大量关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事例,他认可“天”作为伦理的最终根源,并着重强调人君即为政者在中国的伦理世界中的定位与要求,从而凸显出为人民服务的伦理诉求。
首先,司马迁认可“天”是人可以依赖的伦理根源。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感慨屈原人生经历之不遇时,说:“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3]3010司马迁为了类比屈原不堪受辱以担忧和怨恨的态度作《离骚》,认为“天”是人可以追溯的源头,这一表达体现出“天”与人具有本体统一性的色彩,其中就包含了人可将情感与精神诉诸“天”。再如《五帝本纪》中记载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3]16,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3]18,通过“天”引申出“仁义”之理,可论证“天”乃伦理根源。又如在《鲁周公世家》载周公为了诫示成王所作的《多士》《毋逸》,提出了君王应该有的品德:“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在今后嗣王纣,诞淫厥佚,不顾天及民之从也,其民皆可诛。”[3]1839为政者是中国古代伦理社会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德性认知在整个社会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由于为政者所具有的特殊权力,将“明德”的伦理根源付诸“天”,从而使诸如“明德”一类的伦理准则上升为最高意志,对为政者进行有效约束进而达到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其次,司马迁通过“天”为礼仪立法。《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开始对其父太公“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礼”,太公家令说太公:“天无二日,士无二王。今高祖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则威重不行。”[3]481太公再见刘邦道:“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乱天下法!”[3]481高祖因此而赐家令五百金来嘉奖他的行为,说明对这种行为的认同。世人皆知汉王朝以孝治天下,但在忠孝冲突的情境下,通过“天无二日”来比拟人世社会,已暗示出孝服务于忠、君臣高于父子的伦理法则。这样的暗喻一方面反映出汉初“天”具有伦理至高性,也有效解决忠与孝何为优先级的逻辑关系。司马迁还认可祭天求道的国家礼仪,如《司马相如列传》载司马相如进谏武帝:“意者泰山、梁父设坛场望幸,盖号以况荣,上帝垂恩储祉,将以荐成,陛下谦让而弗发也。”[3]3715-3716这一番言论使得武帝思考、认可,且让群臣作颂歌总结:“披艺观之,天人之际已交,上下相发允答。圣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兴必虑衰,安必思危’。”[3]3721此处司马相如对天人关系的论述体现在礼制方面,认为要祭天行礼,随后武帝对天人之际的态度是认可圣王要“兴必虑衰,安必思危”。这段记载是司马相如以及武帝对于天人关系在祭礼和天子之道的明确表述,随后司马迁评论:“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余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3]3722此处对司马相如言辞的肯定,也表现出司马迁本人对祭天行礼的认可。
最后,司马迁天人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民主体意识,体现在要求为政者通过修德注重人民利益的伦理诉求。《天官书》载:
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3]1601
此处司马迁指出想要洞察天人之际,必须对天象变幻进行长达千年的记录总结,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哲学注重经验的总结表达。司马迁认为,天象与人事的关系是“为国者”所需要时刻注意的,当政者是关注天人关系的主体。随后司马迁记述了他所确定的天象与人事的呼应,即秦一统六国,项羽巨鹿之战、刘邦与匈奴战时发生的异象,并肯定了先有天象而后有人事应验。司马迁通过对天体运行和人类历史变易及其特点的探讨,肯定“三五”循环之变是天人之际普遍存在的一种法则。[14]然而,天变与人事是根据什么规律发生呢?司马迁说:
日变修德,月变省刑,星变结和。凡天变,过度乃占。国君强大有德者昌;弱小饰诈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然其与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动。为天数者,必通三五。[3]1608-1609
此处司马迁根据天象总结出为政者应注重修德性、减刑罚,这是与政事息息相关的,由天象到政事的互动实质上是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是重视民本利益的过程。结合司马迁所举秦始皇、项羽、刘邦等例,他们特定时期的行为符合历史进程方向、符合最广大民众利益。正如《孝文本纪》中文帝说:“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3]529司马迁穷其一生究天人之际,天象变化的研究背后具有为政事提供支撑的意义,其中的伦理诉求是为人民的安居生活而服务的,这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殊途同归,具有时代进步意义。
五、“天道无常”人生哲学向度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早期天人思想的发展,其中不仅有满足政权阶级的部分,也部分继承了先秦以来重视“个人作为”的内容。先秦时期,随着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到来和理性思维的觉醒,人们逐渐解构原始的宗教天命观,一些思想家开始对天神的权威表示怀疑,关注核心从“天”转向了“人”。司马迁天人思想在关于个人命运的讨论时既强调人生成败不应单纯归结于“天”的安排,重视个人的积极能动性,又相当程度认可“天”对个人命运的统摄,非人力所能改变,体现出强烈的辩证色彩。
一方面,司马迁天人思想重视人的能动作为。其一,表现在他自身生命中。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讲:“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3]4002司马迁继承其父遗志,修史书乃是其人生志向,且毕生致力于此。当其因李陵之祸惨遭宫刑之后,仍能保持信念而非半途而废。他在回复任安的书信中说:“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2]2733-2735司马迁即使在宫刑后倍受屈辱,但却选择了忍辱负重,用行动去抗衡飞来横祸,根源就在作为个人生命有自我选择的空间与精神动力。“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此司马迁认识到超越人生命体验的价值,这种价值的获得可以由个人努力而得,而不会因偶然的灾祸动摇。司马迁个人生命历程是意气风发、天降大任且又命途多舛的,他自身追求面对现实、迎难而上、奋发有为的经历,看中人的意志力与能动性,并最终完成了旷世奇作《太史公书》,这可成为他天人思想重视人为因素的重要佐证。
其二,司马迁注重人积极作为,在其书中也有所表现。他在《项羽本纪》中评论:“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3]428这是司马迁对项羽的直接批评,根源在于项羽将个人所败归因于“天”,且在仍有卷土重来、东山再起的机会时直接放弃,这为司马迁所不称道。又如在《伍子胥列传》中申包胥使人对伍子胥讲:“子之报仇,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3]2467但伍子胥却说:“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3]2467由此记载可见,尽管申包胥认为伍子胥鞭尸楚王行为有悖天道,且伍子胥之后被吴王所杀的经历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申包胥的言论,但从结果论上说伍子胥通过自己的作为达到了复仇的目的。司马迁并为此作出评价:“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3]2654伍子胥带着仇恨的力量,通过隐忍蛰伏、出楚去吴,得以报父兄大仇,尽管被指责会受天之罚,但司马迁仍对他个人作为予以了积极的肯定。
另一方面,司马迁认为“天”对人的生命又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统摄与约束,这表现在对人物命运经历的记载与评论中。
其一,“天”具有个人生命不可抗力的内涵。如《李将军列传》:“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3]3476李广感慨自己命运不济,虽从军多年威震匈奴,然终无封侯之命。此次随卫青作战又不被重用,因而感慨乃是“天意”所为。并且司马迁还记载武帝对卫青的嘱咐:“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3]3474“数奇”即说明世人认为李广命有定数,人无法反抗。如《留候世家》:“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3]2488此处体现出当时尽管多数学者已经质疑天命鬼神的存在但也无法完全解释,司马迁认为不仅张良获赠书实属奇怪,而且每当刘邦遇到困难张良也可以时时出谋划策、化险为夷,这样神奇的经历应当归于“天”之力。
其二,“天”对人生命的统摄表现为因果报应。如《白起王翦列传》中载:“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杀。”[3]2838又如《蒙恬列传》中蒙恬的自问自答,面对秦二世赐死时感慨:“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思考后不免认为自己当死:“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3]3100如《李将军列传》中李广曰:“吾尝为陇西守,羌尝反,吾诱而降,降者八百余人,吾诈而同日杀之。至今大恨独此耳。”[3]3474当时星象者王朔曰:“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3]3474从上述例子看出,通过司马迁的描述,尽管白起、蒙恬为秦国名将、战功赫赫,李广忠厚不二、保家卫国,然皆不能善终,归根于他们曾经杀降、征役,蔑视他人生命。通过对人生的反思从不甘于死亡到无可奈何的接受。因此,因果报应也是司马迁承认“天”对人的统摄的内涵之一。
其三,司马迁认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外戚世家》司马迁说:“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即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3]2387司马迁在此所言之命,乃“天”之命也。人即使能通过自身作为去改变,但受天命影响的部分却不能改变。配偶之爱非我之有不可僭越,男女交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司马迁感慨这是天命注定,并以孔子为例,认为天命高深、不易认知。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认为:“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3]2585学界多引此处作为司马迁强烈质疑天命存在的例证,如张强引此处证司马迁质疑天命,天只是一种自然规律[15]46。张立文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也举此例说明司马迁反对天命说。但在面对司马迁“天”之其他内涵时,只好将司马迁对天命的态度、天人关系归结于模糊、不易作答。笔者认为应当厘清司马迁在此质疑的“天”究竟是何?其实此处并不能表达为司马迁对“天”“天命”存在的彻底质疑。通过思考不难发现,司马迁质疑的是“天”是否具有德性主宰,人之生命是否会德福一致,而并非质疑“天”的存在,这不妨碍他认可“天”对人的生命有一定空间的约束,只是这种约束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司马迁反对的是这样的天道合理与否,批判的是“常与善人”,而非天道本身。所以当面对伯夷、叔齐、颜渊、盗跖等人现实的富贵命运并不能因自身道德所发生质变时,方才发出了“天道,是邪非邪”的感慨,因此颜渊清贫终生,盗跖长寿享乐的事实恰从侧面印证了“天”对人生命的约束。从司马迁的评述来看,一方面“天”对于人生命运的统摄从普遍性来说是“天道无亲”,如白起、李广杀俘虏导致结局悲惨,但另一方面确实存在“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如伯夷、盗跖的德福不一,人只有在“天道无常”中去探索生命的意义。
综上,司马迁的天人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朴素辩证思想,这缘于天人思想发展的客观历史阶段,也彰显出司马迁本人的哲学思想倾向。他看中人积极作为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明确表明人生命中有关人生结局、财富等方面是受“天”所统摄的,人为难以改变。这些不同角度说明了司马迁对天人关系是多元、辩证的思考,并非不具备哲学反思。
六、结语
所谓“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以往学界对司马迁天人思想研究大多是摘取某一处为立场,如反天命,重人事,或认为司马迁承认“天”具有客观规律等等,面对司马迁不同立场表述内容之时再归于模糊性、矛盾性、局限性,未免会出现相对片面或牵强附会之意。笔者认为应当首先以辩证、包容的视角去审视《史记》中可反映出司马迁天人思想的内容,凡属可作其例证的皆可归于司马迁天人思想的重新建构,不需将其著作中的观点强行划为对立存在。司马迁充分汲取先秦学者的思想资源,前人对“天”的不同释义无疑为他提供了思考空间,从中摘取或评价前人天人思想是其天人观形成的基础;面对“大一统”历史阶段的新形势与结合个人遭遇、历史人物命运的思索,司马迁的天人观既表现出符合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适时性,也显现出人在天人关系中受到的约束和抗争;最终司马迁仍肯定了“天”作为伦理来源的权威性并从科学客观维度进行总结,对当时天人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有力推动,为后世王充、仲长统等人进一步讨论作了铺垫。司马迁面对汉初天人思辨兴盛的学术背景,其“究天人之际”就是通过对前人天人思想分析、反思、批判以形成一种具有个人主观性的再思考,这随着他个人知识积累与命运发展而变化,应将其天人思想放在历史维度解构并重构,或可进一步促进对西汉天人思想研究的补充,这是极具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