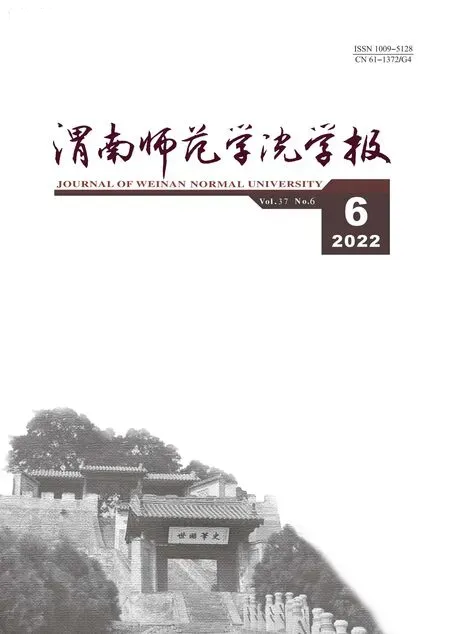论司马迁思想中的“革命”精神
刘 国 伟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司马迁借《史记》所营构的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思想肇定基础,其中独到特出的“革命”思想也大可细陈。所谓“革命”,即是指“革故鼎新,变革天命”[1]337,它自古就与阶级社会的天命、君权关系颇深,当天命生变、君权易位,革命精神就此萌发。革命同时意味着“活力与惰性的交战”[2]64,往往伴随着新旧势力间兵革交斗的曲折历程,是改朝换代、改造现实的重要形式,故《易·革》云:“革,水火相息。”[3]177司马迁不吝笔墨阐扬“革命”观点,肯定“革命”精神,对汤武革命、陈胜吴广起义的事迹大加美颂,对南越立国、东越反秦佐汉的行为给予褒扬,观此种种,都可察知司马迁“革命”思想的深刻内涵与价值,而这种思想的形成更与其天人观大有渊源。
一、司马迁的天人观
天人观是世人对“天命”与“人事”相互关系的看法,随着时代推移,人们对二者在轻重取舍上各有偏重。汉人的天人观中,“受命”思想与“革命”思想并存,他们既放言君权受命于天,又雄谈代立践位乃放弑之举,故而两相争持,聚讼不休。“汉人言天人感应,王者受命之思想,最能成一大系统者,不能不推董仲舒”[4]353,董仲舒推察前朝旧有之国事,“观天人相与之际”[5]562,演绎出一套迎合统治者所需的神学理论,这即是盛行于汉的天人感应说。此学说虽然是从天、人交感互应的关系上推阐立论,但却重“天命”而轻“人事”,昧于神道,为君权覆上一层神秘面纱,因此明显带有愚弄下民的企图。司马迁学从董仲舒,虽然“接受了董仲舒的影响而鼓吹‘天人之学’”[6]141,可他有所扬弃,屡屡针对天命提出质疑。司马迁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因素在人不在天,他直接驳斥“天命有归”这一谬论,敢于肯定人谋,表现出重“人事”而轻“天命”的思想倾向,彰显出朴素而务实的“革命”精神。
早在先秦古籍中,已可见轻视“天命”的端绪。《左传·昭公十八年》言:“天道远,人道迩。”[7]882《荀子》曰:“制天命而用之。”[8]338这些经籍明言天命渺远、难以确知,或言天命可以制御、为人所用,对司马迁思想中的“革命”精神有所启发。司马迁接受并吸收先秦思想中的精妙之处,援为己用,使汉代天人感应说渗透着一层“人众者胜天”[9]1929的论调。
司马迁在《天官书》中言道:“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无之。”[9]1255他将属于“天命”范畴的“修禳”归于次要地位,而将隶属“人事”范畴的“修德”“修政”“修救”次第置于主位,规诫人君要涵养德行、修明政法、补偏救弊,这成为他质疑“天命”、推重“人事”的显例。不难推知,司马迁对“天命”之有无态度是两可的,他既不从根本上否定其存在,也不对其盲目信从,即持守“抽象肯定,具体否定”[1]279的立场,然而他确乎对“人事”的意志力深信不疑,为此抱定信念,大加揄扬。由此而知,司马迁的观念中存在着人胜于天的积极意识,这正是他“革命”精神的思想来源。
秦末中原逐鹿,项羽依仗名族声望聚众起兵,代秦自立,势力席卷天下,然而最终却失利于汉军四面围困之中,落得兵败身亡,对此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评价:“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9]287项羽势去溃败之时,仍抵死不悟,将结果归罪于天命,司马迁直斥其为大谬之人,并认为项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放逐义帝”的不义之举招致众叛亲离,加之他自矜功伐,尚武残暴,又用兵不当,更不欲修正德行,卒酿成军败身死的局面。司马迁借此阐明,导致楚亡汉兴的根源在于“人事”而非“天命”,在这里,人的影响力已然高出天意,这正是他思考天人相与关系所得出的合理认识。
司马迁质疑天命、批判天道,对以往事件的是非因果,往往提出具有理性思维的独到见解。在《伯夷列传》中,司马迁对伯夷、叔齐的不幸遭遇寄托同情,对他们守仁明志的高超品行给予礼赞。他们施善行却不得善果,守操行却未能寿终,孔子褒其二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10]278,司马迁则站在“天道佑善”的角度问难天命,说:“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9]1886天既不能福佑善人,那么天命的存在便失去根基。不独如此,司马迁还对所谓“天道”大加贬斥:“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9]1886他直言所谓天道其实是非难断,可知他是不妄信这些的。
这里需要特加留意的是,司马迁质疑天命的立场未能始终一贯。“司马迁是反对天命的,但他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11]86,当他对事件无法作出超越历史局限的合理解释时,他又不得不借助天命来阐述因果。刘邦兴汉而得天下,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评曰:“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9]704吕后崩,大臣们诛灭吕氏势力,使朝纲拨乱反正,令汉祚得以延续,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评曰:“此岂非天邪?非天命孰能当之?”[9]1759可见对于历史变局、权力更迭等现象,司马迁虽有困惑,但因受到时代观念所限,却也只得求借天命加以阐释,仍未脱王权天授的藩篱,这使其反“天命”的理性思维夹杂一层神秘主义色彩。
司马迁本着“究天人之际”的主旨创作《史记》,确实对天人关系作出许多新的解读。司马迁的观念里明显存在“天人相分”的思想倾向,认为事业的成败不能简单归因为天命,这具体表现为对人事的肯定,对天命的某种否定。然而他却无法完全摆脱“天人感应”之神学思想的束缚,因此,他对所谓天道的怀疑程度也相当有限,未能从根本上否定天命的存在。总之,司马迁的天人观,会通先秦贤哲和汉儒的思想理论,既具有朴素的唯物思维,认识到世界的物质性,又带有神秘意识和历史局限性,承认上天的意志,以及天施加给人的某种制约力量。可是在轻重之分上,司马迁明显表现出重“人事”而轻“天命”的倾向,极力揄扬变旧鼎新这一“革命”精神。非但如此,司马迁对改良国家弊端的变法也一并美颂,他认可商鞅变法、晁错变法,实际上是在肯定革故救弊之变法的正确性,这在当时历史环境下尤显可贵。
二、伐无道、诛暴政的革命精神
与革命精神同生同止的社会事件多是改朝换代,而“与改朝换代相联的是奴隶起义、农民起义”[2]65,司马迁在《史记》中大笔颂扬的革命精神,正体现在此类事件当中。汤武革命、陈胜吴广起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他们伐无道、诛暴政的革命事业秉笔直书:“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9]2866无道与暴政重压之下,唯有迎难而上才能找到出路,正因为他们敢以革命气度挑战风雨晦暗般的现实,才为中华民族的演进史留下雄美的篇章。
(一)明言汤武革命
关于汤武革命的评述自古就有,《易·革》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3]177这是直接将汤武定性为革命的说法。儒家讲“救乱除害”,接受凭借武力治乱安邦、诛除暴政的战争,因此可以认为儒家也嘉赏汤武革命,“儒家颂扬汤武革命就基于此,为司马迁所吸收”[1]324。司马迁接纳前人之说,为其增益新解,使之新具内涵,于是“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1]73,形成他明言汤武革命的坚定立场。
在汉初之时,关于汤武是受命还是革命的观点始终聚讼纷纭,《儒林列传》记载了辕固生与黄生在景帝前面争此事的情景:
黄生曰:“汤武非受命,乃弑也。”辕固生曰:“不然。夫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为何?”[9]2711
辕、黄二人间的辩讼,无非是为汉朝代秦朝寻找历史依据,可是二人观点对立,又各有依据,实难折中调和,景帝一时也决定不下,遂令停罢。经此事件后,学者对汤武受命革命皆“莫敢明言”,而司马迁却在《史记》中屡屡明言汤武革命,显然是站在黄生的立场,称扬其观点。
关于汤武革命,《殷本纪》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9]85《周本纪》中司马迁更是借武王之口道出“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9]112一句口号。“伐桀”“革殷”即意味着诛夷无道之桀纣,变革现实社会,建立新秩序,实带有革命进取精神。“司马迁首先认为武王伐纣是‘革殷’,然后承认其‘受天明命’,但基本认定为‘革殷’即革命。”[12]92司马迁立场分明,认定殷周实属革命,他毫无讳饰地阐述殷周革命的观点,可见他已确乎认可汤武革命,认为商灭夏、周代商乃是革命之举,而历史正是在这些变革中不断向前演进。
《秦楚之际月表》载:“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9]703在《郦生陆贾列传》中司马迁又借陆生之口曰:“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9]2361“放弑”“逆取”之意皆等同“革命”,司马迁之所以屡言“革命”,而弃“受命”观点不用,是出于史学家尊重历史的考虑。秦汉之际历史迭连巨变,王朝新旧气象之间的更替已无恒理可循,司马迁只好抛开君权天授的神学论调,从唯物史观出发,以国政、君德、人谋为考察对象,肯定人君“修仁行义”的重要性,从中得出历史演变的合理结论,即“革命”观点。当世人对汤武革命受命皆“莫敢明言”时,司马迁却毫不避忌,抱持己见,直写其事,体现出他勇敢无畏的史学家气度,遵从实际的唯物思想,以及谋求变旧布新的“革命”精神。
(二)歌颂陈胜、吴广起义
起义意味着用兵起事,是人民被压迫到无以退步境地后的群起反抗,因此不可避免地伴有兵祸人灾,而歌颂起义壮举,正显露出司马迁的革命精神。“陈胜、吴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生命的斗争精神”[2]65,司马迁以史家手笔,条述起义事件从肇始、勃兴到衰亡的过程,用“天下之端,自涉发难”[9]2866允论其功,颂扬他们为剪灭暴秦所作出的历史贡献,并对他们身先死而业未竟的结局表示惋惜。
司马迁讴歌陈胜、吴广起义,集中体现在《陈涉世家》中。陈、吴二人所在的谪戍队伍因遇雨失期,按秦律恐难活命,于是相与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9]1744这次起义是因繁重的徭役和严苛的律法所致,秦统治者毫不恤惜民力,且动辄以峻法相加,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而陈胜、吴广对阶级压迫有着清楚认识,他们举兵起事,是迫于险恶处境下的绝地反击,是生死存亡之际的积极反抗,“四个‘死’字,何去何从,一目了然,而陈胜、吴广的革命精神毕现”[11]160。为壮大起义队伍,他们采用“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9]1745的方法,巧用谋划,激怒部属,策动众人投身到起义大计当中,在此二人身上,不仅具有革命勇气,还且具备革命智慧,司马迁对他们倾注赞美之情,溢于言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9]1745一句疾呼,石破天惊,发人警醒,更被认定是“一道革命的动员令”[11]162,司马迁对此颇为激赏,对他们的起义事迹更是极力褒扬。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革命队伍,正因受到革命精神感召,才形成如此强大的凝聚力,最终积寡成众,发展为破竹之势,对秦王朝的暴政统治造成致命一击,司马迁称扬他们“伐无道,诛暴秦”[9]1746,厥功至伟。
陈胜事败身殒后,司马迁追评:“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9]1753司马迁极力推许其“首事”之功,其实不无道理。正因陈胜首倡起义,才有嗣后秦亡汉兴的历史演变,司马迁将项王灭秦以及楚亡汉兴这段历史变革的源头,追溯至陈胜名下,是颇富见解的。可以认为,“陈胜、吴广的革命行动,开辟了一个历史新时期”[11]168,这让汉家的德治取代了秦朝的暴政,也让革命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场由“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9]1755发起的农民起义,生动写照出中华民族历史变革之实况,具有开创意义。历史证明,陈胜、吴广的揭竿起义实与时代发展趋势相契合,而司马迁如实记载起义过程,歌颂其事,不仅彰显了人民对推动历史进程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更借此呈现出他所极力揄扬的“革命”精神。
司马迁秉承实录原则直书史事,记载人民以有道伐无道的正义战争,以及群氓诛灭暴政的反抗战争,展现出波澜壮阔的历史场面,将革命精神推向人心。司马迁反对倒行逆施的策反与谋逆,而对革命斗争精神极力颂扬,颇具远见卓识,是值得肯定的。
三、各民族同等参与政治斗争的权利
中国自古就是以华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时相征服、时相融合,兵戈交斗之外又能团结共处,因此,只要天下分合之势未有定局,他们皆为中原政治斗争的共同参与者。在秦汉易代、时局扰攘之际,时任南海郡县令的赵佗乘机立国,以图自保,另有东越族人带领部属反秦佐汉,襄助大汉帝业,司马迁一一载录此事,为其立传,实带有“承认周边各民族有同等的‘革命’权利”[1]338的性质。
(一)承认南越立国
在《南越列传》中司马迁对南海尉佗盘踞一隅、自立称王一事抱持肯定态度,并在传记中对他自保图强的行为不吝褒扬。秦末天下纷争,中原龙争虎踞,骚乱未安,此刻正是趁机自图的绝好时机,时南海尉任嚣病中语赵佗曰:“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9]2579赵佗行使南海尉一事后,迅速采取行动,巩固领地,割据独立,顺势“自立为南越武王”[9]2579,这一系列举措无不说明,在赵佗身上有一种逢乱奋起、希图自立的革命意识,他在局势动荡之际立国,虽是时之所逼,却更是这种意识的引导使然。
不难察知,赵佗自立的初衷是为在乱世之中保全自身利益,以防杜盗贼滋扰成患,起初并无篡逆之心。而对于赵佗自立一事,高祖也是认可的,并于“汉十一年,遣陆贾因立佗为南越王”[9]2580,实际上已经承认南越带有藩属关系性质的独立地位。况且赵佗立国后“与剖符通使”[9]2580,即与汉朝互遣使者往来通问,保持两家亲睦关系,并“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9]2580,为改善南越风习、化育民俗、保境安民,作出一番功业,值得褒扬。
对于赵佗施行的一系列有为举措,《汉书·高帝纪》记载高祖诏书:“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今立它为南粤王。”[5]17南海地处偏远,民俗与中原迥异,高祖皇帝特下诏书,以章表赵佗移风易俗之功,显然已认同其政绩,并默许其南越王地位。关于南海尉一职,从“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9]2579可知,南海尉本是秦朝所置官职,汉继承天下后,不仅承认南海尉的合法性,更加封赵佗为南越王,这对本身就是以武力夺取国柄的汉高祖皇帝来说,自然不足为怪。可见在汉初之时,上至帝王下至臣属,都对南越立国事件达成一致认可,这种认可的背后,即代表着对自立建国这一“革命”精神的肯定和嘉许。而随着岁月逾迈,汉、越两国局势转变,南越国的后继者生出二心,意欲叛离汉王朝,最终被汉廷征服,南越因此亡国,对此终局司马迁用“吕嘉小忠,令佗无后”[9]2588数语作评,深表痛惜之情,此处隐约可见司马迁有回护赵佗的用意。
通观《南越列传》可知,赵佗先是趁乱自立为王,后来高祖夺取天下、平定海内,非但不对赵佗追责问罪,反而通过下诏书的形式承认其南越王的合法地位,而司马迁又用史笔详载其事,肯定赵佗自立的正确立场,并对他为保境安民所做出的贡献大加揄扬,说“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给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9]2872,这是肯定了南越族人谋求自立的革命权利。
中国古已有“夷夏之防”的思想,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0]33然而司马迁却能摆落历史观念的束缚,对中华民族和其他各族不分厚薄,等同对待。司马迁并不因南越为蛮夷之族而贬低之,他站在彼方的角度,肯定赵佗立国以图自保的立场,公允评述其功绩。可以说,“南越王的自立完全是出于一种防止盗边侵略的正义行为”[13]101,是富有革命意味的,而司马迁借此揄扬“革命”精神的态度,已然昭昭可知。
(二)肯定东越反秦佐汉
司马迁在《东越列传》中记载东越人“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9]2589参与灭秦,而后“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9]2589击败项羽的事迹,他借此肯定东越族人反秦佐汉的立场,同时也认可各民族同等参与中原政治角逐的权利。
闽越一带多为少数民族群居地,秦朝将其纳入版图,设置郡县,秦末当各诸侯操兵反叛之际,他们也举兵合力抗秦,成为中原政权角逐的直接参与者。先是无诸、摇率领东越族人加入吴芮的反秦队伍,跟随项羽参与灭秦。吴芮作为鄱阳令,颇有一定的号召力,他领导东越人参与诛暴斗争,建立功勋,汉朝定鼎后高祖徙封其为长沙王,在《汉书·高帝纪》记载诏书:“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5]13吴芮统领百越族人加入抗秦事业,颇能洞识政治局势,具备敏锐的革命头脑,汉帝即位后对其策勋论功,施以分封,司马迁核实直录此事,大加激赏:“由此知越世世为公侯矣。盖禹之余烈也。”[9]2593他认为东越能够世世被封为公侯、代代得以相传延续,应归功为大禹所遗留下的勋德,这就将被视为蛮夷的越族纳入中华民族的范畴,无差别地等同视之了。既然东越同属华夏族员的一分子,自然也就有权利参与中原的政治角逐,司马迁此语也是恰当的评价。
暴秦既灭,楚汉纷争继起,由于“项籍主命,弗王”[9]2589,于是无诸、摇转而依附汉营,指挥东越族人加入佐汉攻楚的革命事业当中,立下功劳。汉五年,高祖“复立无诸为闽越王”[9]2589,并下诏令其“王闽中地,勿使失职”[5]13。孝惠三年,朝廷论赏越人佐汉之功,朝吏纷纷推举闽君摇,于是“立摇为东海王”[9]2589。在这场楚汉之争中,东越以外族人身份参与其中,他们审时度势,有所作为,扮演着推动中华民族历史演进的重要角色。他们革命立场坚定,政治见识卓越,竞逐中原的同时也保全了本族人的利益,展示出东越族人的大智大勇与革命信念。司马迁以其能在汉朝之初履行藩属国的职责,“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9]2872,颂扬他们反秦佐汉的正确举措,肯定他们参与政权角逐的革命权利。
《南越列传》和《东越列传》详细记载了越族人民谋求自立、参与中原政变的革命事迹,这不仅如实反映出中华民族勇于变革的斗争意志,同时也成为司马迁革命思想的又一事例。虽然南越、东越两国最后皆因蓄谋逆反而被汉朝攻灭,族民四处迁徙,国家也成为汉廷辖制下的郡县,落得不终结局,但他们当初艰难立国、竞逐天下的革命气度,却永传后世。
四、结语
可视远古时期的汤武革命为革命精神的起源,这让中华民族的人文气质开始具备革命性,到秦汉之际的陈胜、吴广起义,以及南越立国、东越击秦辅汉等事件,嗣承前世革命精神,使之一脉承续,延绵不息。司马迁在接受汉儒天人观的基础上,对天人关系的认识开始有所新变,他不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在某些社会历史事件尤其是除暴力、反压迫的革命事件上,却又极力推重“人事”,认为人具有支配历史进程的决定力量,形成自己独到的革命观念,这与中华民族革命精神相契合。司马迁抛开“华夷之辩”这一囿见,将汉族与越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范畴内,肯定他们共同参与中原政治竞逐的权利。司马迁对伐无道、反压迫的革命战争持以认可态度,对各民族为保全自身利益、推动历史变革所作出的贡献寄予褒扬,他在《史记》中所构建的具有革命内涵的思想体系,影响后世千秋万代,更值得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