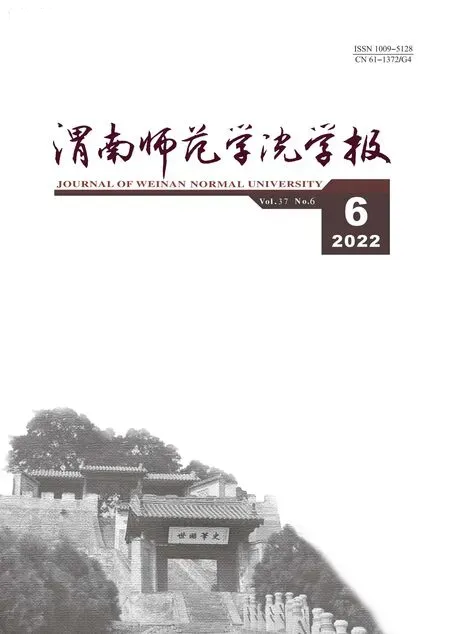《史记》“以吕易嬴”叙事与司马迁的“国嗣”忧思
刘 文 远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2)
“以吕易嬴”,即吕不韦献有孕之妇谋取秦国政权的故事,随着《史记》精彩叙事的传播而广为人知,乃至成为典故,不但屡见于文人诗文,而且上登奏章,为官书所称引。然而,对其真实性,古今学者均有质疑。清代梁玉绳辩驳尤其有力,指出所以有此传闻,是因为“秦犯众怒,恶尽归之,遂有吕政之讥”[1]1308。民国时期,钱穆与郭沫若分别在《先秦诸子系年》和《十批判书》中进行了深入考证。钱穆认为吕不韦自杀之后,其宾客或杀或逐,乃造此诬辞。[2]256郭沫若推测是汉初吕后专制之时吕氏一族吕产等辈所编造。[3]414此后还有不少学者论及,特别是经过李开元的精心剖析,秦始皇为庄襄王亲生之子似已毋庸置疑。[4]33-46司马迁在《史记》之中采风闻之说,巧运史笔,不惜浓墨重彩,言之凿凿,其真实用意到底何在,值得思考。
《史记》是强烈现实关切之下的“发愤”之作,其精心谋篇所力图彰显的主题,也一定是司马迁现实忧心之所在。具体在“以吕易嬴”一案,此事之所以入史,并产生强烈的历史回响,当然是因为涉及皇权血统传承这一根本问题。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国嗣”问题就如梦魇一般相伴而生,王朝兴衰、社会治乱往往与此密切相关,如司马光所说:“治乱安危之几,何尝不由继嗣哉!”[5]504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引用古语:“君终无適子,其国可破也!”[6]2228可见他对“国嗣”问题极为重视。而“以吕易嬴”恰恰提供了有关“国嗣”危机的极端案例,在《史记》的叙事中被特意凸显,也就不难理解。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史记》“以吕易嬴”及相关内容叙事的笔法入手,分析司马迁的历史忧思与现实关切。
一、《史记》“以吕易嬴”的叙事笔法
“以吕易嬴”一事,最早见于《史记》。但《史记》在不同地方的记载有一定差异。《秦始皇本纪》记载:
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庄襄王为秦质子于赵,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6]289
而《吕不韦列传》中则记载:
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6]3045
两处有关秦始皇出身问题的不同表述,令该案显得扑朔迷离,后人聚讼,也多因此起。梁玉绳结合《秦始皇本纪》中对秦始皇出生时间和《吕不韦列传》中对“大期”的记载进行解析,试图弥合其矛盾:“史公于《本纪》特书生始皇之年月,而于此更书之,犹云:世皆传不韦献匿身姬,其实秦政大期始生也。别嫌明微,合于《春秋》书‘子同生’之义,人自误读《史记》耳。”[1]1308梁氏以《春秋》鲁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的笔法作为关键证据,认为《史记》两处看似矛盾的叙述,实际隐含着司马迁保留当时流传的不同记载的同时有为秦始皇出身释疑的用意。但因涉及对《春秋》“子同生”书写的理解等问题,此说仍不无可议之处。
首先,《春秋》特意记载“子同”即鲁庄公出生时间的深意到底何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三传的诠释大相径庭。《左传》的解释是“以大子生之礼举之”[7]92。《公羊传》的解释是“喜有正也”,何休注称“喜国有正嗣”[8]483。《谷梁传》解释:“疑,故志之。”范宁注:“庄公母文姜,淫于齐襄,疑非公之子。”[9]99认为《春秋》书“子同生”是为“正周公之裔,决后世之疑”的观点出现较晚。杨时指出:“人以庄公为齐侯之子,《春秋》安得而不辨乎?此《春秋》所以为别嫌明微也。”[10]288后经过朱熹等人的不断完善,逐渐成为主流。但这种观点并非定论,如程颐即依《公羊传》,解释为“冢嫡之生,国之大事,故书”[11]1106。宋代以后,仍有不少学者信守三传的传统解释。
其次,以兴起于后代的“‘子同生’别嫌明微说”来反映司马迁时代人们的观念,似缺乏有力证据。至少在唐代之前,人们对《谷梁传》“疑,故志之”的理解应该与范宁注释的思路大体相同,何况《公羊传》在庄公元年的叙事中也提及鲁桓公怀疑子同乃齐侯之子:“公曰:同非吾子,齐侯之子也。”[8]628持“别嫌明微”观点的学者多强调文姜私通齐襄公是桓公十八年以后之事,子同出生之时,文姜尚未有秽行。但司马迁在《史记》中就明确记载:“齐襄公故尝私通鲁夫人……及桓公来而襄公复通焉。”[6]1796刘向的《列女传》、郑玄的《毛诗笺》也有类似说法。既然汉代人认为文姜与齐襄公早在子同出生之前就有私情,似乎按照范宁的“存疑”而非后代的“释疑”来理解《谷梁传》对“子同生”的阐发更符合情理。
最后,《吕不韦列传》中有关“大期”的记载如果可信,确实可以作为秦始皇出身与吕不韦无关的证据,却不能证明司马迁留此二字是为秦始皇辩诬。毕竟秦汉时人虽了解常人孕期,但也认为存在超越正常孕期的现象,所以才有“十四月生尧”的说法。关于“大期”主要有两种解释:其一为杜预注《左传》提出的“夫人足月为大期”的足月说,其二为徐广注《史记》时提出的“大期”为“期年”即十二月说。如果司马迁确有为秦始皇“释疑”的用意,更合适的书写是“十月(或十二月)后,生子政”。而《史记》中因为与“自匿有身”相连,“大期”二字所指为“孕期”无疑,言外之意为,即使赵姬嫁给子楚超过十个月以后始皇才出生,赵姬也始终处于“孕期”之中!
由此可知,对于《史记》中有关秦始皇出生年月和“大期”的记载,固然不能依据《谷梁传》“疑,故志之”的传统解释认为司马迁对秦始皇出身持“怀疑”态度,同样也不能单凭“别嫌明微”的“春秋笔法”,认定司马迁有为秦始皇出身辩诬的“微意”。要理解司马迁有关秦始皇出身问题的书写目的,还需要作更全面的辨析。
有的学者从史源学入手考察,认为由于史料来源不同,所以出现观点截然相反的情况。《秦始皇本纪》史料来源于《秦记》等秦朝官方文献,《吕不韦列传》则来自不可信的编造。但如果细读《史记》文本,在《秦始皇本纪》记载中有一点令人不能不生疑惑,那就是如果《秦始皇本纪》的史料来源于秦朝官方文献,在有关秦始皇出身如此严肃的叙述中,怎么会将子楚娶吕不韦姬这样的事情写入?如果这句话本为秦朝官方文献所无,那么司马迁在编写《秦始皇本纪》之时,又是出于什么目的把“见吕不韦姬,悦而取之”掺入的呢?
这就需要回到《史记》一书的体例特点来看。对于《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各体之间的关系,刘知几解释:“纪者,编年也;传者,列事也。编年者,历帝王之岁月,犹《春秋》之经;列事者,录人臣之行状,犹《春秋》之传。《春秋》则传以解经,史、汉则传以释纪。”[12]41章学诚也说:“迁、固本纪,本为《春秋》家学,书志表传,殆犹《左》《国》内外之与为终始发明耳。”[13]111按照这种思路,本纪与列传等其他诸体之间就如同《春秋》经传关系,绝非可以断然割裂。因此,要全面理解《史记》的有关主题,就应该注意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呼应。这种叙事笔法,被称为“互见法”。由刘知几揭其端,苏洵正其名,靳德峻归纳为“互文相足例”[14]13-16,当代学者肖黎、张大可也认为《史记》“纪为纲,传为目,互文相补”[15]92。关于“互见法”的特点、功能与得失,近年学界研究更加深入,“互见法”作为《史记》述史的重要笔法,应无异议。[16]
《秦始皇本纪》与《吕不韦列传》中有关秦始皇出身问题的记载,正是《史记》“互见法”的经典案例,至于本纪为何不明言秦始皇为吕不韦之子,前人已论之甚详。李笠说:“《史记》则以属事比辞而互见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17]236靳德峻称:“本纪据其名,传中记其实,亦互见者也。此亦史家回护之法。”[14]17如果司马迁有意在本纪中强调秦始皇出身与吕不韦无关,那么“吕不韦”三字显然不应出现在秦始皇出身的这个语境中,之所以出现,应是特地加入,以为提示之用。“互见法”在为尊者讳之外,还有“隐而彰”的作用。苏洵就特地强调,其中包含着司马迁的深旨:“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不善也,不亦隐而彰乎!”[18]77本纪中隐晦其事,但提供有关线索,使读者循照“互见”线索寻根溯源,当得出所谓的“真相”之时,反而会获得更为强烈的印象。
但司马迁要“坐实”“以吕易嬴”一案的用笔并未到此而止。除了《秦始皇本纪》之外,“吕不韦”之名又在其他看似毫无关系的地方非常突兀地出现。在《史记》一书中,除《吕不韦列传》之外,“不韦”之名还见于《秦本纪》1次,《秦始皇本纪》5次,《六国年表》3次,《楚世家》1次,《春申君列传》2次,《樗里子甘茂列传》1次,《李斯列传》2次,《太史公自序》2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与吕不韦有一定的关系,唯其出现于《楚世家》和《春申君列传》,则颇显唐突。《楚世家》载:“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悍立。李园杀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吕不韦卒。”[6]2091《春申君列传》出现的2次,一次是在春申君为相后,写道:“春申君相十四年,秦庄襄王立,以吕不韦为相,封为文信侯。取东周。”[6]2908另一次是春申君献有孕之女之后为李园所杀,司马迁紧接其后写了一段话作为全篇的终笔:“是岁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6]2911从中可以注意到:3处吕不韦都和春申君一并出现;3处都强调二者身份相当,都是执一国之政的相国,甚至已被免相的吕不韦自杀,还要写明其为“秦相”。这种对两人身份、命运的强调,显然是提醒读者要将其事迹和命运结合起来理解。
《春申君列传》的后半部分记载了楚考烈王无子,赵人李园将其妹进于春申君,春申君待其有孕献给楚王,楚王去世,李园将春申君杀死灭口,进而把持国政这一离奇故事。司马迁通过在其中两个关键的节点引出了“吕不韦”之名,同样是用“互见法”来提醒读者,注意发生在吕不韦和春申君身上有一个“同质性”的故事。后世的读者也确实得出了这一印象。据《汉书·王商传》载,汉元帝时期,王凤为了排挤丞相王商,阴使张匡上书揭发王商纳女后宫的“奸谋”,张匡即引吕不韦、春申君事例为证:“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意欲有秦国,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19]3372这说明在汉元帝时期,人们已经把两个故事联系起来,“以吕易嬴”的“真实性”也得以强化。
对《史记》的这一笔法,宋人就已经注意到。苏辙在所撰《古史》的《春申君列传》中,不但大体抄录了《史记》的相关内容,连《史记·春申君列传》最后谈及吕不韦的那段话也一并叙入,在赞语中特别强调“黄歇相楚王患王无子而以己子盗其后”的事实,并称:“秦楚立国仅千岁矣,无功于民而获罪于天,天以不韦、歇阴乱其嗣,而与之俱毙。”[20]58将吕不韦、春申君乱人国之嗣同类并举。黄震指出,苏辙的赞语“亦因《史记》并言吕不韦乱秦之微意而发之耳”[21]1683。真德秀认为春申君“以黄代芊”,“其窃国之术与不韦同”,因此共列于篡臣之篇,“欲人君知奸臣用智之可畏”。[22]278钱穆敏锐地指出:“战国晚年,有两事相似而甚奇者,则吕不韦之子为秦始皇政,而黄歇之子为楚幽王悼是也。然细考之,殆均出好事者为之,无足信者。”他经过悉心考证,认定事属子虚,但认为《史记》之所以如此记载,“乃史公之好奇也”[2]566-570,未作深论。周斌举《春申君列传》所见“吕不韦”为例加以分析,认为:“这种互见法之功用就是引起对比,使读史者从比较中得到启发,得到历史的真谛。”[23]41我们从《吕不韦列传》《春申君列传》中对嫪毐和李园之事的夸张表述中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显然是有意通过“互见”之法,互相印证,以取得“互文”效果,使春申君、吕不韦,以及嫪毐、李园等利用血嗣谋人之国的行径得以彰显。
如果明确司马迁倾向于吕不韦乃秦始皇生父这一点,《史记》中将《秦本纪》与《秦始皇本纪》分立,如前人所说,可能其中确有别“吕秦、嬴秦”之意在。[24]91《秦始皇本纪》后所附秦王世系中涉及庄襄王之时两次提及吕不韦之名。其一是叙述至庄襄王享年时写道:“庄襄王享国三年。葬茝阳。生始皇帝。吕不韦相。”[6]363其二是叙述庄襄王的最后一句:“东周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6]364除吕不韦外,秦王世系中出现的另一个人臣就是赵高。在叙述秦二世之时,特别提到“赵高为丞相安武侯”[6]364。赵高既为秦末主政之人,也是亡秦的祸首,此处连带提及其名,“微意”呼之欲出。吕不韦之名在此出现,似属同理。特别是述及秦灭东周而不绝其祀之时提及吕不韦,是否也在暗示,吕不韦灭嬴姓之秦而不绝其祀呢!
二、司马迁有关“国嗣”的历史忧思
毕生致力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当然不会仅为闱闼丑闻耗费笔墨。前人对《史记》中类似的夸诞、离奇之事,往往归于司马迁“爱奇”。西汉末年扬雄首揭此说,称“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25]319。此后,“爱奇”或“好奇”就被视为司马迁的重要风格。学者从“实录”的角度出发,对于《史记》中一些离奇不经的记载,多指为司马迁“好奇之过”。但也有学者认为,司马迁固然有“好奇”的特点,其实尚有“微意”。唐代司马贞说:“其人好奇而词省,故事核而文微,是以后之学者多所未究。”[6]4045清代袁枚也提醒读者:“史迁叙事,有明知其不确而贪所闻新异,以助己之文章,则通篇以幻忽之语序之,使人得其意于言外,读史者不可无识也。”[26]27
近来学者深入探究了司马迁“爱奇”的审美倾向和创作手法,肯定其重要意义。如刘振东认为司马迁“爱奇”,通过对有特异性的历史人物的推崇与偏爱,“为中国文学开创了一条实现典型化的重要途径”[27]112。王明信也认为,司马迁“爱奇”,不是“好奇”,而是为揭露社会、抒发悲愤、寄托理想,所以其“所写之事,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石破天惊,不同凡响,讽世性强”[28]85。对“奇人”的偏好与对社会的关怀其实并不矛盾,后者往往需要通过对“奇人”的典型性塑造,才会得到充分的显示。
这样看来,对《史记》中因司马迁“爱奇”而载入的一些不可信的材料,就应避免纠缠于细节的、个别的“真实”,而应通过对其典型性的认知,来理解其本质的“真实”。具体在“以吕易嬴”一案上,司马迁运用“互见法”,勾连起《秦始皇本纪》《楚世家》《吕不韦列传》《春申君列传》几个不同的文本,将吕不韦、春申君、李园,乃至嫪毐的事迹联系起来,突出了权臣通过改变君主血嗣来谋夺政权的历史主题。《吕不韦列传》的夸张表达,除了前引吕不韦献有孕之姬一事,主要是围绕作为吕不韦“替身”的嫪毐来展开的。在《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八年的叙事中,司马迁写道:“嫪毐封为长信侯。予之山阳地,令毐居之。宫室车马衣服苑囿驰猎恣毐,事无小大皆决于毐。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6]293同样出于“隐而彰”的需要,文字中没有提及嫪毐与赵太后之间的暧昧关系。但在《吕不韦列传》中,不但突出了嫪毐“大阴人”的生理特征,还直书吕不韦“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啖太后”的具体经过,进而通过他人告发嫪毐“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后’”[6]3047-3048的言辞,揭示嫪毐的篡国图谋。通过这样的运笔,嫪毐、吕不韦、春申君等人事迹的“同质性”就更加突出。
但对这三人的叙事中,司马迁没有描述他们一开始就有谋人之国的企图。对吕不韦,只是强调其利用商人“居奇”思维实现商人到政治家的角色转换,其所以献有孕之妇,也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当叙至子楚“因起为寿,请之”时,司马迁描写了吕不韦心理的微妙波动,“吕不韦怒”,但“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6]3045。可见吕不韦的“以吕易嬴”,不过是“顺势而为”。对春申君,司马迁用近三分之二的笔墨,铺陈了他上书秦昭王停止灭楚行动,以及不惜牺牲自身救楚太子归国两事,强调的是其“何其智之明也”[6]2911。但该篇自春申君为相十四年第一次提到“吕不韦”之名后,文风突变,接下来用近三分之一的笔墨,叙述李园献妹以至春申君被杀身死的过程。春申君所以献孕女于楚王,也非主动而为,而是为李园及其妹所挑唆的结果。至于嫪毐,其命运开始时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是作为吕不韦的“替身”,获得了接近赵太后的机会,因为深得太后之宠,最后才萌生了“以子为后”的妄想。三个人都没有一开始就谋人之国的计划,只是得到某种机遇,“顺势”产生相似的图谋。
与三人不同的是,李园从出现时就居心叵测,他想献妹给楚王,知道楚王无法生育,怕其妹日久失宠,就有了一幕精彩的演出:
李园求事春申君为舍人,已而谒归,故失期。还谒,春申君问状,对曰:“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与其使者饮,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对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见乎?”曰:“可。”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6]2909
“故失期”三字,隐含着李园引起春申君注意的意图,之后“齐王使使求臣之女弟”的说辞,更是为了吊春申君的胃口,一步步把春申君引入陷阱,进而达到借助其力量实现个人野心的目的。《史记》有关李园的这部分文字,与《战国策》“楚考烈王无子”章几乎完全相同,应该是来自同一史源。[29]592-594其中无论是李园的精心谋划,还是李园妹的枕边风,都是典型的纵横家文字,“床笫之言不逾阈”,从“信史”的角度来说,极其可疑。司马迁几乎全文照录,定然有其深意。
李园代表的是对最高权力执着追求、精心运筹的一类人。从他作为一个赵人,一心想把妹妹献给楚王就能猜出其动机所在,他处心积虑利用春申君,事成之后抢先发难杀其灭口,同时垄断朝政,更能说明他对权力的强烈欲求。所以,司马迁照录这段并不可信的文字,更可能是用夸张的修辞来彰显这一典型,进而与其他三人相对照,以实现如下阅读效果:无论是一开始就有谋人之国企图的野心家,还是仅仅利用机遇顺势而为的投机客,其改变“国嗣”、危害政权的后果是相同的。反过来也可以理解为,无论是精于计算的商人、寄人篱下的门客,还是忠心为国的亲信重臣,如果有适当的机遇,都有可能做出和一开始就心怀鬼胎的人同样危害“国嗣”的事情来。
但司马迁并没有将夺人“国嗣”的责任简单地归咎于权臣身上,而是作了更深刻的刻画。细绎《史记》行文,不难发现,吕不韦等人企图实现更改“国嗣”的目的,都必须通过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那就是君王身边左右继承权的后妃。这在《吕不韦列传》中得到突出表现。
《吕不韦列传》全文2 000字左右,从内容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叙述了吕不韦如何“钓奇”以及帮助庶出的子楚通过依附华阳夫人而获得嫡嗣身份的具体过程,后一部分重点叙述的是吕不韦与赵姬的特殊关系以及引荐嫪毐进而得祸的始末。如果要对《吕不韦列传》的主旨加以总结,无论是为子楚争取继承权,献有孕之姬以谋人之国,还是赵太后与嫪毐的夺嗣图谋,显然都与“国嗣”有关。而在这种“国嗣”的角逐中,关键环节并不是吕不韦,而是“太后”或者其他能决定“国嗣”的女人。在子楚争夺嗣权的过程中,吕不韦非常清楚地向子楚指出“能立嫡嗣者独华阳夫人耳”,可见起决定作用的是华阳夫人。同样,在向子楚献有孕的赵姬之时,从“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的表述中可以看到,司马迁通过“姬自匿有身”一句,将隐瞒已孕事实的责任转移到了赵姬身上。随着“大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赵姬获得了嫡妻的身份,从而也就确保了其子的继承权。赵姬成为太后之后,宠幸嫪毐并生育两子,与嫪毐密谋“王即薨,以子为后”,进而引发蕲年宫之变,核心仍然是“国嗣”问题,而其中赵太后的角色无疑最为关键。
此外,《吕不韦列传》大量文字叙述的并非吕不韦本人的事迹,而是围绕着华阳太后、夏太后、赵太后展开。在庄襄王即位条下,特别叙述:“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6]3045秦始皇七年条下,记载:“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6]3048涉及赵太后的当然更多,自吕不韦献有孕的赵姬,特别是秦始皇即位之后,赵姬反而取代吕不韦,成为叙事的主体。从开始的“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到“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为免祸而进嫪毐,“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事皆决于嫪毐”,最后发展为蕲年宫之乱,太后先被迁于雍,后复归咸阳。最可疑的是全传的结尾句:“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谥为帝太后,与庄襄王会葬茝阳。”[6]3050这些本来应该在《秦本纪》或《秦始皇本纪》中的内容,却出现在吕不韦的列传中。
表面上作为个人传记的《吕不韦列传》,实际上却隐含了至少两条线索:一条当然是传主吕不韦的荣辱兴衰,另外一条就是当时秦国太后。无论从叙述内容多少,还是叙事的主体来看,“太后”都是《吕不韦列传》中的重要关键词。[30]77-84三位秦王后的主要事迹之所以被纳入《吕不韦列传》之中,显然不仅是因为与吕不韦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还因为她们与秦国“国嗣”紧密相关。
司马迁借着“以吕易嬴”的叙事,揭出了“国嗣”这一主题,通过将在“国嗣”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的权臣与后妃的事迹“耦合”起来,揭示了专制权力传承的内在困境:君王独尊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人为之铤而走险,即使至亲至贵之人也莫能例外。司马迁之所以如此煞费苦心,那是因为“国嗣”也深刻影响着司马迁所处西汉时期的政治生态。《吕不韦列传》中的叙事笔法,已经显露出他对太后与“国嗣”关系的严重关切,在有关西汉历史书写中,这一点就更加突出,集中体现在《吕太后本纪》的设立和叙事上。
三、汉初国嗣危机与司马迁的现实关切
西汉皇权继承发生了多次严重动荡,仅司马迁所能了解的,至少就有汉惠帝废立、吕后专权乃至巫蛊之祸,均与“国嗣”有关。关于刘邦宠爱戚夫人,欲改立赵王如意一事,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并没有提及,而是在《吕太后本纪》特别是《留侯世家》《叔孙通列传》等篇中展开。而由吕后专权所导致的“国嗣”危机,则充分地表现在《吕太后本纪》中。
从《史记》的体例看,在《高祖本纪》之后,不为至少是名义上的皇帝惠帝设本纪,反而设了《吕太后本纪》,显然是用心深刻之举。不少后世史家对司马迁的这种安排持批判态度。如司马贞即认为:“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6]503赵翼也质疑:“岂有嗣主在位,又未如庐陵王之遭废,而竟删削不载者!”[31]96但也有史学家认为,司马迁别有深意。如明代钟惺就称:“吕后入本纪,在《高祖本纪》后,惠帝遂无纪,危诸吕之夺汉也。”[32]1清代牛运震也说:“吕后者,高皇后也,依义例,当称《高后本纪》。今没其高后,而斥称其姓,若以著其王吕锄刘之罪,不与其为高后也。”[33]99徐复观认为,司马迁为吕后立纪“一以著历史之真实,一以著吕后之篡夺”[34]210。
多数史家都认为,司马迁为吕后设本纪,而忽视汉惠帝,主要是因为“政在吕后”,体现了司马迁“寻王者之迹,不求王者虚名,但求其实”[35]59的著史特点。虽然《史记》中有“孝惠帝时,吕太后用事”[6]3270,“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6]521的说法,但更明确表示政归吕氏,是在汉惠帝去世以后,吕后借治丧之机揽权,《史记》明确记载:“吕氏权由此起”,“元年,号令一出太后”[6]508,“孝惠帝崩,吕太后称制,天下事皆决于高后”[6]2428。而且《史记》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概括的时候,大多将惠帝和吕后并列,如《平准书》等篇中说“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6]1712,《吴王濞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6]3416,《朝鲜列传》说“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6]3618,《张耳陈余列传》说“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时”[6]3136,类似的表述在《史记》列传中有十几处。《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间侯者年表》更是按照高祖、孝惠、高后、孝文、孝景这样的次序纪年。此外,据今人研究,汉惠帝也并非仁弱无能之君。[36]15-34从本纪的纪年和叙事需要看,在“孝惠帝本纪”之后再续以《高后本纪》,体例更顺。但司马迁并没有这样做,显然其设《吕太后本纪》,绝不仅是“政在吕后”那么简单,可能还有其他考虑,这就需要结合《吕太后本纪》的内容来分析。
如果细读《吕太后本纪》全文,不难发现,其叙事的内容和笔法均与其他本纪有极大差别,其主体实际上是高祖末年储位危机叙事的延续,吕后由于掌握了“国嗣”的最终决定权,诛戮有竞争性的刘姓子孙,独掌国政,进而“以吕易刘”,危及刘氏王朝。如果将《吕太后本纪》与《高祖本纪》接续来看,线索就显得更为清楚。
《高祖本纪》中,表面上没有提及储位之争,但在结尾之处,写了这段话:
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6]493
主旨显然是介绍高祖子嗣,但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三人注明生母,因为三人或者是嗣君,或者是嗣位有力竞争者,将其生母名字标出,强调生母在嗣位竞争中的作用;其二,梁王、淮阳王均为吕后迫害而死,此处强调在吕太后时徙封,其命运改变因吕后而起,从而揭出吕后影响刘邦子嗣命运的主题,为接下来《吕太后本纪》的叙事埋下了伏笔。
《吕太后本纪》开篇就引出了戚姬得宠进而引发改立太子的风波,接着叙吕后佐高祖诛大臣之功及吕氏兄弟姓名,然后对前揭《高祖本纪》尾句又加以重述。这三段内容,基本上确定了全篇的基调,以“国嗣”之争为开端,核心是吕后排抑高祖子嗣,推动吕氏擅权。本纪有关惠帝七年间的纪事,主要围绕吕后残酷迫害戚姬,处心积虑除掉赵王如意,及齐悼惠王免祸之计这三件事。有关惠帝去世之后的叙事,主要有借惠帝之丧揽权称制,排除王陵等异己,分封吕氏为王,扶持亲吕势力,杀少帝而立刘弘,幽死赵王友,改封梁王恢为赵王并迫其自尽,杀燕王建幼子以除其国,主体是灭刘氏封国,代以吕氏,用齐王的话说,“杀三赵王,灭梁、赵、燕以王诸吕,分齐为四”[6]516。其中除了“封齐悼惠王子章为朱虚侯”[6]509,“置太尉官,绛侯勃为太尉”,“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6]512等纪事为诸吕被灭张本外,其余内容基本可以用“以吕易刘”一语加以概括。
从叙事风格来看,《吕太后本纪》与其他本纪也有很大差别。其一,本纪的叙事主体一般都与国家大政有关,但《吕太后本纪》全文5 000余字,前面3 000多字几乎都是有关吕后迫害刘氏,扶持诸吕,而有关国计民生的大政,几无一语提及。所以韩兆琦认为本篇名为“纪”,“实际上是一篇‘传’,而且只是记载了吕后杀刘氏,王诸吕,和刘氏与功臣元老联合彻底消灭了吕氏家族的过程”[37]75。其二,与其他本纪的叙事笔法不同,这里没有采用“为尊者讳”的曲笔,反而极力地刻画了吕后嫉妒、残忍的形象。特别是对“人彘”的描写,详述“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的惨状,与惠帝的“慈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司马迁还借惠帝作为人子之口,给予吕后“此非人所为”[6]506的恶评。司马迁不惜违背“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非但没有“隐恶”,反而“彰恶”,更说明其之所以为吕后设立本纪,至少有彰显太后擅政所导致的“国嗣”危机的考虑。
所以文中不仅记载吕后如何诛戮刘氏子弟,擅自废立,还记载了张皇后杀美人而名其子,吕后以诸吕女嫁赵王刘友,以吕禄女嫁朱虚侯刘章及少帝刘弘,以吕产女嫁梁王刘恢,吕媭女嫁营陵侯刘泽等事。吕后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加强刘吕联姻以巩固政权,而在刘友等看来,则是“诸吕用事兮刘氏危,迫胁王侯兮强授我妃”[6]512。这种强迫之下的联姻,一方面有助于加强对刘氏宗室的控制,如吕产女嫁给刘恢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诸吕女嫁给刘友后,诬告其罪,至刘友被幽禁饿死。另一方面,吕氏可以实现利用母权掌控刘氏血脉的目的,如吕产女为赵王刘恢王后,“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6]513。
在吕后的主导下,诸吕不但控制了刘氏政权,同时还控制了刘氏子嗣。惠帝之子虽然被立为嗣君,但其身份已经变得非常可疑。此外张皇后无子,佯装有孕,取美人子名之而杀其母。此子为吕后所杀之后,惠帝后宫子刘义被立为帝,更名为刘弘,不仅其母姓名不详,连自己的名字也被更改。“国嗣”完全为吕后所操控,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嗣君是否为刘氏血统也难以保证。如《史记正义》引刘伯庄语称:“诸美人元幸吕氏,怀身而入宫生子。”[6]512当吕后一死,大臣和宗室诛杀诸吕,就提出:“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6]520陈平等拥立代王刘恒之时,“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不当奉宗庙”[6]528就成为关键的借口。尽管司马迁并没有明言刘弘等非孝惠真子,但他两次用“继嗣不明”一语来概括汉朝建立初期“国嗣”未立以及惠帝死后嗣君身份可疑的状况[6]2390,4009,也间接表明了他对吕后掌控下“国嗣”血统的疑虑。
正因为《吕太后本纪》的叙事主题是吕后通过掌控“国嗣”而“以吕易刘”,所以后半篇2 000余字的内容,都是有关大臣及宗室诛灭诸吕,重新拥立高祖子嗣,政归刘氏的内容。在选择谁为天子的问题上,大臣宗室曾有分歧,最后之所以选择代王刘恒而非灭吕有功的齐王、年少可控的淮南王,关键因素就是“疾外家吕氏强”[6]2392。群臣认为,齐王母“恶人也”,淮南王“母家又恶”,如果立此二人,则“复为吕氏”,鉴于吕后“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的教训,才选择了母家“谨良”而且“仁孝宽厚”的代王。[6]520杜绝了太后的控制,使“国嗣”危机得到解决,政归刘氏才真正实现。所以,《吕太后本纪》用“代王立为天子。二十三年崩,谥为孝文皇帝”作为结尾句,本来应该出现在《孝文本纪》的这句话,与开篇形成呼应,也算是为持续了十几年的“国嗣”危机画上了句号。
但这个句号显然并不完美,直到西汉覆亡,太后或后妃掌控“国嗣”的现象几乎成为一种常态。司马迁紧接《陈涉世家》之后,设立了《外戚世家》。《外戚世家》虽兼列后族,“事实上是在‘编太后’”[38]129。司马迁将其列于汉代诸世家之首,不但揭示了西汉时期基本政治格局,也将“国嗣”的忧思接续到了他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外戚世家》并非简单的后妃传,所列入的后妃,大多与“国嗣”有关。司马迁用精练的语言,在其中记载了汉文帝嫡妻所生四子“更病死”,窦姬因“独宠”而使得长子被立为太子,汉景帝时栗姬与王夫人相争致使太子易位,汉武帝时陈皇后被废、卫子夫之子被立为太子等有关“国嗣”的重大事件。而在《梁孝王世家》中,叙事的主体更是围绕窦太后“心欲以孝王为后嗣”[6]2535而与汉景帝进行的较量展开。
虽然事涉当朝,司马迁的用语都极为平实、简洁、克制,但在《外戚世家》叙至武帝诸妃之时,皇帝的宠辱变化成为主线:陈皇后失宠,卫子夫为后,及卫子夫“色衰”,“赵之王夫人幸,有子,为齐王”,“王夫人早卒,而中山李夫人有宠,有男一人,为昌邑王”,“及李夫人卒,则有尹婕妤之属,更有宠”。[6]2401-2402皇帝对后妃宠爱与否,决定着“国嗣”的命运。虽然此时卫皇后之子刘据为太子,但随着其母逐渐失宠,“国嗣”之位能否确保,从司马迁的行文中,不难发现其心怀忧虑。武帝末年发生惨绝人伦的“巫蛊之祸”,又何尝不是按照司马迁叙事逻辑的继续展开!
表面上看,皇帝掌握着“国嗣”的最终决定权。但吊诡的是,皇帝能决定自己宠爱哪位后妃,并进而因宠爱这位后妃而立其子为太子,却也因此放弃了独立确立“国嗣”的权力,致使太子的决定权被变相转移到了能得到皇帝宠爱的女人身上。而这样的女人往往会成为皇后、太后的最终人选,当皇帝去世之后,她们利用母权,可以继续影响“国嗣”的废立。虽然无论是窦太后企图改立梁孝王为嗣,还是栗姬与王夫人为己子争夺嗣位,“国嗣”仍限制在刘氏血统内部,但当“国嗣”的确定权完全为太后或者其他外人掌控之时,局势就很可能会失去控制。西汉末年王莽终于以外戚的身份,实现了另一种“以吕易嬴”式的政权转移,也更印证了司马迁对于“国嗣”的担忧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同时也显示了他洞察历史的卓越见识。
四、结语
司马迁在“以吕易嬴”叙事上的匠心独运,显然是出于对现实“国嗣”危机强烈关切下的深刻历史反省。“国嗣”危机几乎贯穿整个西汉时期,成为影响国家安定的最关键因素,其中以太后、皇后为首的外戚是最大的干扰项。牟润孙指出,西汉时期的太后专权乃至决定国嗣的废立,是母系遗俗的体现。[39]278-284有的学者进而强调汉代的“皇后权”,认为“汉王朝帝位允许太后干涉”[40]38-39。对此,学界已经作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可供参考。[41]
实际上,还应注意到,太后影响“国嗣”进而干预朝政所出现的“母后临朝”现象,不仅西汉为然,而且是与整个帝制时期相始终。对其发生原理,20世纪之初夏曾佑就有深刻分析。他认为“母后临朝之制”,“大约均与专制政体相表里。盖上古贵族政体,君相皆有定族,不易篡窃,故主少国疑,不难委之宰相。至贵族之制去,则主势孤危,在朝皆羁旅之臣,无可托信者,猝有大丧,不能不听于母后,而母后又向来不接廷臣,不能不听于己之兄弟,或旧所奔走嬖御之人,而外戚、宦官之局起矣”[42]44。他从贵族共治政体到君主专制政体的转变角度,揭示了“母后临朝”乃至外戚擅政的必然性。后世不少王朝基于确保“国嗣”稳定的考虑,试图从帝位传承中排除异姓尤其是母族因素的影响,如汉武帝时期的“钩弋故事”,曹魏的“三世立贱”,以及北魏的“立子杀母”,但从汉代以后的政治演进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现象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要破解这一困局,更需要从君主专制政体自身入手,而在这方面,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深入的思考,需要我们通过精细的解读加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