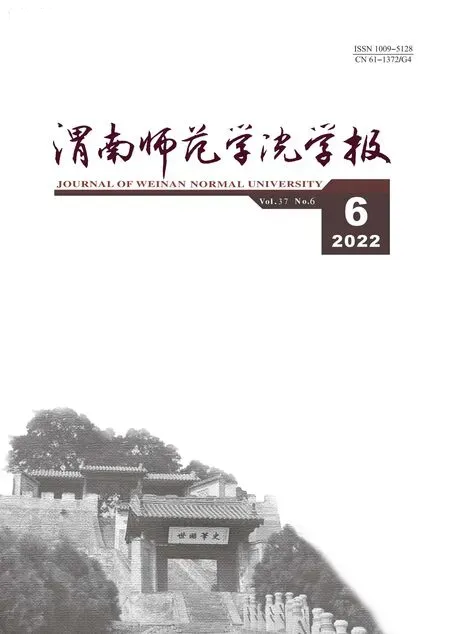合阳“花花”:基于当地女性生活史的考察
孙 萍 萍
(渭南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五四”时期,发端于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一部分的歌谣运动,为中国的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歌谣与生活”“歌谣与妇女”“歌谣与婚姻”“歌谣与农事”成为当时的热点话题,而“歌谣与妇女”的研究正应和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刘经庵在《歌谣与妇女》明确指出:“歌谣是平民文学的极好的材料,这话任谁亦不能否认的;但这样的材料,是谁造成的?据我自己的观察,一半是由妇女们造成的。”[1]绪论1“民众的文艺,尤其是歌谣一部分,妇女的贡献要占一半,且其中又多是讨论他们本身的问题的——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关乎中国妇女问题的歌谣,就是妇女们的家庭鸣冤录、茹痛记。”[1]6歌谣传唱本身就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其内容也记录和表现着女性的生活和情感。
“花花”是流传于陕西合阳一带的民间歌谣。不同于陕北的“信天游”、内蒙古的“爬山调”、甘青宁的“花儿”等等,合阳“花花”没有曲调,主要是“说”的,因此,当地人一直就称之为“说花花”。“花花”的创作群体主要是忙碌于灶台炕头、田间地头的劳动妇女,她们借助“花花”这种艺术形式,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表达她们的日常生活、人生经历及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
从民间搜集到的“花花”样本内容分析,大多是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在当地劳动妇女口耳相传、互相吟诵中流传下来。通过细品一首首“花花”,可以窥见她们的人生、情感及生活情态。笔者依据的“花花”资料来自合阳县文体广电局编印,由梁浩秋、史耀增、王鹏主编的《合阳花花》一书。该书收集的“花花”除了少数是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新“花花”外,主体是新中国成立前的作品,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时期流传于该地区“花花”作品的解读去考察当时当地乡村劳动妇女的生活状况。
一、少女时代的生活情态
在现存“花花”中,描写女性少女时代生活状况的歌谣为数不多,但可以从中窥见其中的苦与乐。“苦”在于女孩子五六岁就要求被裹脚,“乐”在于童年时代黏在父母身边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快乐生活。《打秋千》描述了被家人宠爱的女孩子在家门前打秋千时快乐的情景。“一蔓瓜,两蔓瓜,拉拉扯扯到咱家。年轻女儿巧打扮,咱家门前缚秋千,一溜一串戏秋千。财东家女儿戏秋千,黑缎子鞋来花尖尖,小脚儿蹬住花码关(1)花码关,指荡秋千时固定脚的脚蹬子。,巧手儿缠住花锁链。妈妈出来笑盈盈,大大出来送几送,哥哥出来掮几掮,嫂嫂出来搀几搀。”
关于裹脚,除了这个过程本身女孩要忍受疼痛外,裹脚后行走不便大大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特别是成年之后,女性在参加家务劳动、农业生产时,小脚带来了很多不便,同时这种疼痛也是伴随一生的。《缠脚》:“小女女,六岁半,身上穿的洋花缎。眉又细,脸又圆,一双大脚还没缠。娘叫女,把脚缠,女女防到(2)防,方言,躲藏的意思。邻家不闪面。拉回来,把门关,一盆热水端面前。大针小针磁瓦片(3)瓷瓦片,方言,瓷器、陶器、瓦片等的碎片,棱角较为锋利。,划的脚上血流满,疼的眼泪流一脸。他大一见心疼烂:‘我的女子你甭管!’‘我不管,你不管,寻不下下家(婆家的)谁丢脸’?”《抱上碎脚哭恓惶》:“六岁上,七岁上,我妈给我缠碎脚(4)碎脚,方言,小脚的意思。。剪子剪,磁瓦子戳,把我疼的防到焙角角,把我缠成尖尖脚。尖尖脚,上南坡,阿家(5)阿家,方言,婆婆的意思。叫我担水拾柴禾。把我走的疼的没处搁,抱住碎脚哭恓惶……”《跑秸杈》里描述麦收时节,夫妻在麦场碾麦的情节,其中就有女子小脚劳动时带来的不便,例如:“……秸杈一拉克啷啷,小脚儿顛顛跑的忙。麦又湿来脚又小,打不进麦堆实煎熬……脚一蹬,不好了,把我的鞋带挣断了。鞋跌咧,脚裂咧,裹脚拖下一窝咧!这个秸杈咋打哩,没有鞋带咋绑哩……”除了劳动的不便,还有一步一走的钻心痛。
少女时代,除了裹脚为将来的出嫁准备外,母亲还要教女孩子习得一些为人处世的礼仪及生活、生产的技能。这些技能,一方面为应付婚后家务劳动及生产生活;另一方面,布织得粗疏细密、面擀得匀称薄厚、花绣得如何、鞋子做得怎样等等,也是媒人说媒、婆家挑选媳妇很重要的参考。合阳“花花”中有大量表现这方面的内容。例如,《抓养(6)抓养,方言,生养教育的意思。女》中有:“一岁两岁吃娘奶,三岁四岁离娘怀。五岁六岁门前串,缠脚抹爪扎耳环。七岁八岁学做活,抹桌扫地续机缣。九岁十岁学纺线,十一岁绣花学拐缠。没觉然抓下十二三,十四十五学织棉。十六十七学裁剪,学做茶饭七八年。女娃长大娘心牵,成天提心掉胆胆。同州府里扯鞋面,羌白街里打彩环。脚缠十丈长命布,吊布子手巾早备全。铜洗脸盆儿竹蒲篮,印花布门帘花苫单,四角儿集的黑蝉蝉。儿一半来女一半,大妈都把心放端。叫女儿,走上前,听娘给你嘱托言。从明日你到婆家,小心侍侯女婿再阿家。早梳头,把脚缠,烧火去裙子撩腰间。未拉风匣先搭炭,锅烧煎了(7)煎了,方言,水烧开的意思。再洗案(8)案,指的是厨房的案板。,再问公婆做啥饭。或烙馍,或擀面,下面去水要添宽展,莫叫水少面下粘(ran)。客人来了先问候,然后端茶取水烟。当了媳妇另一重天,侍候公婆理当然。”还有《十姐织布》:“老母教女织绫罗。老母上机织一遍,十个女子都来看。大姐上去显高手,双手穿梭云中走……二姐上去显手段,双手穿梭云中串……只有三姐织的快,给娘织下黄丝带……只有四姐织的好,给娘织下花花袄。只有五姐生的笨,百样花子都织了……六姐要织杨柳叶,织的柳叶上下翻。织的双燕穿梭飞,织的水牛卧沙滩……”这些花花生动叙述了女孩子在母亲的指导下学习织布、纺线、绣花、做饭等,同时牢记母亲的教导,未来到婆家如何侍奉公婆、招呼客人等等。
二、恋爱婚姻中的女性
从现有搜集到的“花花”中可以看到大量描述女性婚恋的作品,作为女性,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女性,选择什么样的结婚对象、选择什么样的家庭等等,女性几乎没有自主权和发言权,大多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性,相对于封建大家庭少了些封建礼教的束缚,反而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更直白勇敢。婚姻对封建社会的女性来说,表面上从一个家庭走入另一个家庭,实际上是从父母亲作为监管人移交到丈夫公公婆婆的手里,所以婚姻的满意与否,就是人生幸福的基础。“花花”以叙述的口吻讲述了女性的恋爱婚姻状况及她们的真实情感状态。
(一)恋爱中的多情的女性
“花花”中有部分作品描述了恋爱中的女性对爱情的向往、对对象的思念,情感热烈直接,也间接刻画出了东府地区女性率真、泼辣、能干的性格特征。如《想郎想的没精神》:“想郎想的没精神,人家说我太痴心。我也思量不该想,只是想的不由人。我的心肝他的心,心儿肝儿情意深。”又如《看家当(9)看家当,是传统合阳婚姻礼俗的一项。女方家的代表前往男方家,一方面双方长辈见面,另一面进一步考察了解男方家境。》:“一进门,好寒碜,柳条子绑的窗扇扇,灯里没油捻子干,焙上没席铺麦秸。炕合没柴又没烟,灶火没柴锅不煎。挣的少,花销多,没田没地难过活。你咋不捎个书信给奴说。这是我做花卖布钱,把咱的日子先过着。等到奴家过了门,再买田地再活人。”虽然夫家穷得叮当响,女子不嫌弃,还立志过门后要好好过日子发家致富。三言两语,一个善良、能干、自信、风风火火的女子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眼前。
另一类“花花”是以男性的口吻诉说对恋人的思念,古时有男子做闺音,此类“花花”借男性的口吻诉衷肠,一方面塑造了婚恋中受欢迎的女孩子的理想形象;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女性希望被珍爱的心理及情感诉求。如《卖田卖地要娶她》:“白白脸儿黑油头发,白白手儿红指甲。到家里要给爹妈夸,卖田卖地要娶她。”又如《隔窗照着我家家》:“回到家要给我大妈夸,卖田卖地要娶她。一为她风流二为她贤,三为她足小两颠颠。四为她脸像银盘盘,五为她身道一箭杆。六为她生的好眉眼,七为她做的好茶饭。八为她侍候公婆贤,九为她生的好儿男。十为她一切都占全,不娶她到家心不甘。”
(二)畸形婚姻形态中的女性
包办婚姻是封建婚姻制度的主要形式,其特点是以门当户对为基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途径,缔结婚约的男女当事人几乎没有感情基础,他们也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除此之外,民间还有其他的婚姻形式,同样女性都没有婚姻自主的权利。
“买卖”婚姻。在关中方言里,民间嫁女儿有“卖女”一说,封建社会,父母在为女儿选择夫家时,对方出的彩礼钱的多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往往忽略了女儿的感受。例如《我姐卖了十两白银子》:“火盆花,火盆火,先嫁我姐后嫁我。我姐卖了十两白银子,我爷要买尿盆子,我婆要买黑裙子,我大要买竹鞭子,我妈要买银签子。我嫂要穿花褶子,我哥要拴细车子。”《我大卖我不商量》:“菜子开花满地黄,我大卖我不商量,银子别到裤腰上,把我掀到坷崂合(10)坷崂合,方言,指墙角。。”《卖下银钱好的太》:“我在灶火烧火哩,我大我妈商量的卖我。卖下银钱好的太,我大要买铜烟袋……卖下女婿就像猪八戒,越看越看越不爱。”买卖婚姻中的女性不受夫家待见,如《小媳妇不是人》:“小媳妇,不是人,起了五更贪黄昏。黑了熬到鸡叫明,婆婆还说是懒妖精。吃的剩饭冽冰冰,穿的补丁摞窟窿。黑了睡觉还没个狗安生。”《小媳妇》:“石榴树,叶叶落,狠心的爹娘卖了我……女婿过来踢一脚,你看我恓惶不恓惶。”
“过空房”式的婚姻。古代社会,一些家庭,儿子在外不归,但为了增加家庭劳力,便早早买来穷人家的闺女举行“缺席婚礼”,这种婚姻形式称之为“过空房”。《过空房》就讲述了在外多年从未谋面的丈夫归来时的情景。“婿:小房子搭的蔑绣竹帘,望见竹帘我心喜欢。男人家是耙耙把钱揽、婆娘是匣匣攒银钱。我在外十年未回转,我媳妇过门已三年。今日初次来见面,褡裢里装的见面钱。揭开竹帘往里浅(11)浅,方言,偷着看的意思。,只见我妻把头钻……”“嫂:他二叔先甭忙我有话言。房中娶下空房女,空房女儿不体面。进门辱没你男子汉,因而价你去把窗钻……”“婿:转面来骂声你陈家女,做此事不嫌丢脸面。你大你妈爱银钱,把你嫁到我家园。过空房不见男人面,不嫌丢人守三年。我铺子小伙计把你编成戏,写出来贴到我门前。我为你丢人又现眼,害的我还要把窗钻。”“妻:叫相公你莫把为妻怨,低下头儿泪涟涟。那一年咱这遭荒旱,三年六料末曾安。坑的我父无其奈,才把奴家卖银钱。我大我妈养活我,把我养活了十三年。自古说养女儿来接困,才把我嫁到你家园。三年没见女婿面,三年眼泪擦不干。”“婿:叫贱人你还敢巧言辩,在丈夫面前把嘴翻。若还再敢一句,休你就在跟目前(12)跟目前,方言,马上、当下的意思。。”“妻:听言相公话不好,双膝跪倒你面前。从今向后再不敢,一句不敢再言喘(13)言喘,方言,说话的意思。。”“婿:叫声贱人你往前站,你给我打火吃袋烟。你给我脱鞋扽袜子,才显得你是我的妻。”“妻:只要丈夫你不嫌,你说装烟就装烟。脱鞋脱袜奴情愿,扫炕暖被奴喜欢。”“婿:打到的媳妇揉到的面,我妻回话我心安……”这首“花花”描述了“过空房”的丈夫回家,因为“空房女儿不体面”,按照当地习俗必须“钻窗户”,而丈夫觉得自己既不是捡来的,也不是后妈生的,为啥要受“钻窗户”这种奇耻大辱。于是丈夫就将这股怨气撒在妻子身上,埋怨妻子的父母爱钱卖女儿,埋怨妻子“丢人现眼”。妻子的耐心解释再一次激怒丈夫,丈夫以休妻相威胁,吓得妻子一声不吭,只能唯命是从。“过空房”中的妻子除了忍受独守空房的煎熬,还要承受被外人、家人瞧不起的屈辱。
“小女婿”式的婚姻。这种大媳妇、小女婿式的婚姻,妻子被当作主要的家庭劳力使用。《说他是儿不叫娘》里描述了大媳妇扮演和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和任务:“二八佳人巧梳妆,房中守着七岁郎。说他是郎太得小,说他是儿不叫娘。黑了枕的胳膊睡,醒来哭的要他娘。不为婆母待我好,背到后山喂了狼。”《十八的嫁了个七岁郎》:“菜子开花遍地黄,十八的嫁了个七岁郎。白日捣榴滚核桃,黑了害下瞌睡痨。人都说嫁下女婿比奴强,又吐又又尿床。吃饭时盘儿上盘儿下,男人的架子不倒仓。吃一碗,舀一碗,舀的不好就吊脸。伺候阿家伺候郎,伺候猪牛伺候羊。东沟里割草喂牛羊,西沟里担水泪汪汪。越思越想越委屈,搁下担担哭一场。不怨爹,不怨娘,只怨媒人瞎心肠。”描述了媳妇虽然在家是主要劳力,丈夫还是个“尿床”的娃娃,依然要看小丈夫的脸色,更别说公公婆婆的使唤,最后媳妇只有将这股怨气撒在媒人身上。
(三)婚后家庭生活的乐趣
合阳“花花”还有大量的描述婚后夫妻一起参加生产生活的内容,表现夫妻一起劳动的乐趣,也间接表达了女性对夫妻间相守相伴相亲相爱平等关系的渴望与诉求。如《嫁郎要嫁中天郎》:“一同锄麦务棉花,一同拔草同打卡。你摇耧,我牵耧,你捉犁把我吆牛,说说话话到地头。你烧火,我擀面,你择菜,我剥蒜。一同搁碗同扫院,同盆洗脸同吃饭,一同去把亲戚串。拉拉扯扯分不开,亲亲热热同安眠。”《跑秸杈》生动地展现了麦场碾麦时夫妻俩充满生活气息的对话:“男:鸡叫一声东方亮,我到场里去推场。场里人儿乱熙熙,把我推的好孤寂。……娃他妈,你做啥哩?女:我在焙上哄娃哩。男:哄我哩可哄娃哩?”“女:脚一蹬不好了,把我的鞋带蹬断了……男:娃他妈你甭心疼,我腰里还有滑子绳……女:男人家说话没正经,鞋带带谁用滑子绳?滑子绳,太浑粗,还不如头上解头绳……男:场里人儿多又多,给你搔头人笑我。哪怕这场推不成,我不给你解头绳……”
《两口子憋布(14)憋布,方言,指用涝池的乌泥抹在布上使白布变黑。》生动地描绘了夫妻二人用涝池黑泥染布的生动场面。“池黑水深泥不多,你快拿镢头勾底窝。憋布的人儿太得多,迟了没黑泥拿啥憋?你也捞来他也抢,董的池泥满随了汤。叫贤妻你快搭手,慢了稠泥满溜走。夫妻二人捞的捞来抹的抹,忙的头不是头来脚不是脚。满身的泥点点赛蜂窝,一脸麻子疙瘩戳。我看你,你看我,把人笑的没死活。一下憋到半后晌,才泛出一匹灰鹑鸽(15)灰鹑鸽,指像灰鹑鸽一样的颜色。。”
三、传统家庭权力结构关系中的女性
在传统权威型的家庭权力机构中,纵向家庭关系是子女服从于家长权威,横向的家庭关系是男尊女卑。“花花”描述的大多是传统权威型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使得传统乡村女性社会关系主要聚焦为以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为主的家庭范围内,即娘家和婆家,社会交往范围也非常有限。婚后更是以婆家为主,依然受“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三从四德的观念的束缚。民间俗语“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生动描述了女性在娘家与婆家被边缘化的生活处境。
(一)回娘家的喜乐哀愁
除了逢年过节回娘家外,农闲时节,收完麦子,当地媳妇还有“回娘家”的习俗。这既是与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团聚的欢乐时光,也是暂时摆脱烦琐家庭事务享受生活的闲暇时光。《想娘家》:“喔儿喔儿纺棉花,车(cha)子怀里挂爷爷(ya)。啥爷爷,土地爷,灶火爷,传辞咱娘咱大叫我啦。出了枉死城,看着撒乐村,裙子一脱手一拍,好大大,实实地到了撒乐村!到娘家,坐三天,睡三天,亲戚六人看三天。”《想娘家》描述女子托土地爷带话给父母接她回娘家,纺着棉花,想象着回到娘家时的放松、酣畅、自由和愉悦。当然,在娘家也不是完全的悠哉自得,若娘家有吝啬的哥哥嫂嫂,难免会受兄嫂的不待见。如《回娘家》:“我大听说我来咧,牵上红马接来咧。我妈听着我来咧,拄上个拐拐搀来咧。我哥听说我来咧,牵着黄狗咬来咧。我嫂听着我来咧,东厦跑到西厦,馍馍扣到盆底下。”
按当地传统习俗,女子不能直接回娘家,一要娘家人来接,二需经过婆婆的同意,而有些婆婆却故意刁难。如《我在屋里扎缯子》:“我在屋里扎缯子,听着门外人叫哩,马铃呛呛响一串。东一瞅,西一看,我叫大哥你坐下。大哥骑马叫我啦,褥子搭到瓮沿上。鞭子挂到门环上(shuo),叫我去问我阿家。这是烟锅你吃呀,妈呀叫去不叫去?后院有个麦秸积,多会烧完多会去。”《我在房里扎缯子》:“看她还要说啥呀!明天叫咱十个哥哥都来呀,一个缯子没扎毕,听着门外苏铃可响哩。十串苏铃呛啷啷,十匹马蹄铛铛铛。十把椅子你坐下,十个烟锅你吃呀,十个茶碗你喝呀。不吃你烟,不喝你茶,十个哥哥问阿家,叫不叫我妹子熬娘家?辈辈娘家停不够?买死的骨头断死的肉,十双袜子十双鞋,今日去,明日来,做不下了就拿鞭子排。”根据合阳的传统,女儿回娘家是有讲究的,一是按传统习俗“看忙罢”,二是农闲时可以“熬娘家”,但得娘家人来叫,且经过婆婆允许方可。而且“熬娘家”期间也不能闲着,要带着手工活去,带着成品回来,多是纺线织布、缝袜子、做鞋子。《我在房里扎缯子》中女子十个哥哥依次来叫都被婆婆借口打发回去了,最后,十个哥哥一起来,婆婆无奈只得同意媳妇回娘家。
(二)婆媳关系中的女性
农耕社会,民间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说,其中隐含了复杂的家庭权力结构的变化。一方面揭示了女性随着儿女成年成家、资历变老在大家庭中权力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传统乡村社会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的性别观念。传统家庭中婆媳矛盾较为突出,媳妇除了侍奉公婆外,时时处处事事都得请示汇报。女性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较多受制于公婆,连最基本的与娘家的情感的沟通和交流都被阻挠。《女看娘》:“正月里有个女看娘,搭茶待客奴身忙,没有工夫看我娘……十月里来女看娘,哭声娘,叫声娘,谁叫你把我卖下个月月忙。左手抓住娘灵堂,右手搭到娘身上……正月里盼你到如今,没见过女儿这磁的心……女儿嫁了是人家的人,自身不能由自身。”嫁入夫家,身不由己,连母亲最后一面也没见上。又如《婆媳顶嘴》:“豆子不顶米,媳妇不顶女。煎水不顶茶,阿家不顶妈。黄谷不是米,媳妇不胜女。鞭杆不是棍,阿家没妈近。媳妇是墙上的泥皮,揭过一层又一层。”用隐喻的方式描述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女性承担着繁重的家务劳动,在婚恋嫁娶乃至家庭中几乎没有话语权。
处在家庭权力结构关系夹缝中的女性很难自主行动并表达个人情感,如《我娘害病我心焦》:“打下药包没银钱,在我头上拔下银簪。人家说银簪太可惜,我说银簪不可惜。双扇门儿单扇开,我离开我娘没回来。一棵白菜不耐黄,我娘生我空一场。做小吃的娘的奶,端娘碗,尿娘床,长大侍候人家的娘。人家吃面我喝汤,人家吃米我吃糠。顿顿鞭子挨到我身上,句句儿骂的我亲娘。”《托生莫“势”(16)势,方言,做个的意思。女人家》:“托生莫势女人家,一辈子孽罪要受扎。三顿儿茶饭伺候阿家,淘米碾米喂面连夜织布带纺花。门户(17)门户,方言,指亲戚之间红白喜事的来往应酬。差使蒸馍,还要抓养娃娃。”
合阳“花花”的主要创作群体是女性,她们在纺着线、织着布、绣着花、纳着鞋、缝着衣服的时候,一起像拉家常似的说着前人流传下来的歌谣,同时也将自己的生活感悟融入其中。这些来自于底层女性的歌谣质朴、真性情、口语化,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质感,诉人生之苦,是“人生的艺术观”而非“唯美的艺术观”。[2]121“她们给歌谣写下了许多生活的故事。她们用爱和泪养育了它”。[3]7歌谣作为“文化遗留物”,不仅是反映乡村妇女生活的镜子,而且歌谣就是生活本身。[4]116在当地,男人们是不屑“说花花”的,且以“说花花”为耻。“说花花”也就成为当地女性表达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借着“说花花”,诉说着她们经历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感悟。我们也通过“花花”这条隐秘的河流,去了解她们曾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