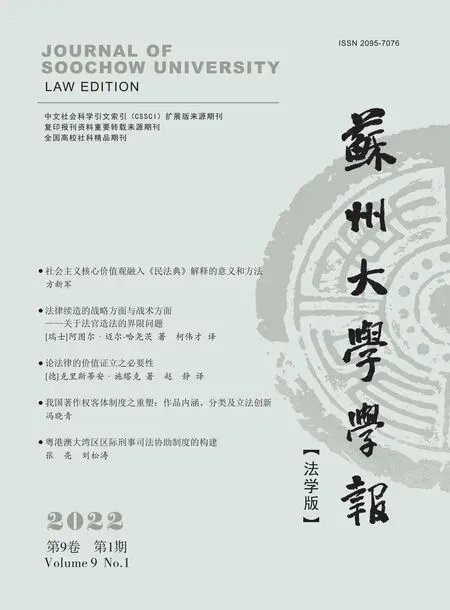阅读障碍者著作权合理使用条款解释
陈 虎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法定的排他性权利,著作权赋予作者及权利继受主体对智力创作成果的绝对垄断权,但保护私权并非其立法的唯一目的,著作权法的价值取向同样在于通过私权确认的方式促进文化公共领域的繁荣。(1)参见杨利华:《公共领域视野下著作权法价值构造研究》,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117页。麦卡锡教授曾提出“公共领域是基本原则”(public domain is the general rule)的理念,主张在专利、商标与作品等客体上设置专有权利是一种例外选择,必须审慎地进行财产权授予。(2)J.Thomas McCarthy, McCarthy on Trademarks and Unfair Competition, Thomson Reuters, 2013, § 1:27.在保护私权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共利益,这在我国《著作权法》第1条有关立法宗旨的规定中也可以明证。通常来讲,著作权法对公共利益的促进并非宽泛式的法律认可,而是通过设置专门的权利限制与例外规则的方式来完成。从制度的设计动因与正当性基础上讲,限制性条文的设置应当出于伦理或政策层面的特殊原因,并且经过充分的利益衡量以确定其所对位的主体、作品类型与作品使用方式,否则将有损于著作权人的利益,进而导致通过著作权法促进公共领域文化繁荣的目标成为“无源之本”。
基于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欣赏作品便利、保障残疾人获得文化层面公平的原因,我国1990年《著作权法》第22条第(1)款第(十二)项就规定了“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构成合理使用,该规定在2000年与2010年的修法中都得以遵循。在2020年现行《著作权法》修改过程中,有建议提出,鉴于我国于2013年通过了《关于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获得已出版作品提供便利的马拉喀什条约》(Marrakesh Treaty to Facilitate Access to Published Works for Persons Who Are Blind, Visually Impaired or Otherwise Print Disabled,以下简称《马拉喀什条约》),为与该条约保持一致,应当扩大受益者的范围,以满足普惠化、通用化和个性化的要求,适应特定人群的需要。(3)我国于2013年6月28日在《马拉喀什条约》上签字,截至目前,该条约在世界范围内已有79个“签约方”。关于条约缔结的基本情况,参见WIPO官方:《WIPO管理的条约:马拉喀什视障者条约》,https://translate.google.cn/?sl=auto&tl=zh-CN&op=translate,2021年8月22日访问。2020年修法采纳了这一建议,将原法“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修改为现行《著作权法》24条第(1)款第(十二)项的“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切实保障了特殊群体的利益。(4)黄薇、王雷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155页。
在协调国际公约的直接出发点之外,此项修法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我国国情与现实中无障碍出版业的困境使然。根据吴汉东教授的解读,在1990年《著作权法》以来的规范中,著作权法设置盲文出版使用条款“旨在发展特殊教育,对弱势群体提供著作权利用优惠”(5)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96页。。盲人是阅读障碍者群体中的一部分,而其他不能被认定为盲人的视力损伤者、听觉障碍者同样无法在事实上与正常人一样公平地欣赏到作品。现行《著作权法》扩大受益主体的修改举措进一步彰显了立法的人文关怀,是立法伦理基础上的夯实。然而,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等配套性法律解释尚未出台之际,现行《著作权法》过于言简意赅的表达亟需学理上的进一步解释,否则将有碍于合理保障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
具体而言,在现行《著作权法》的措辞中,“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存在诸多不明确之处:其一,在客体层面,现行法只是将可提供作品界定为“已经发表的作品”,并没有指明是否要如同《马拉喀什条约》第4条之四的设计一样,规定“已经发表的作品”应当具有商业上的不可获得性;其二,在主体层面,现行法虽然明确了受益主体,但是否应与《马拉喀什条约》完全一致则有待明确,且为受益主体提供作品的“提供者”的规范含义有待进一步解释;其三,从所对应受控行为层面上,相较于旧法中“改成盲文出版”仅涉及复制权与发行权,新法中的“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究竟对应何种作品使用行为则耐人寻味,例如,是否包含向阅读障碍者广播特定作品?是否可以改编原作品并提供改编后的无障碍版本?
以上问题若不澄清,则不免为今后的司法实践带来困惑。本文拟从现行《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的规定入手,结合合理使用规则的体系性规定与《马拉喀什条约》精神,分别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作品所涉及的客体、主体与受控行为三个层面对修法后的解释适用问题予以分析。
二、“已经发表的作品”及其无障碍版本的含义有待进一步明确
旧法“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为盲文出版”的用语说明,向盲人提供的作品类型限于文字等以平面方式表现的作品。制作盲文一般采用“布莱叶点字法”(6)盲文的制作主要采用“布莱叶盲文点字法”,相当于一种密文的制作,特定字母、数字都有其对应的可触摸识别的形状,例如制作者欲将“知识”二字制作成盲文,则需要将“知识”二字所对应的拼音zhi’shi包含的六个字母逐一转化为点状的触觉识别版本。如果是将英文intelligence转化给英语受众的盲人阅读者,则直接将各个字母盲文化。这个转化过程并不会为原文字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将文字从视觉转为可触摸的点状表现形式,由于盲文与原文字具有一一对应性,盲文本质上并非对原文字的翻译改编,而是不增加任何独创性的复制。(7)See Robert P.Merges, Peter S.Menell and Mark A.Lemley,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New Technological Age, Aspen Publishers, 2016, p.74-76.旧法由于受益主体的天然特征所限,在该项合理使用所指向的作品类型上较为清晰。相反,由于现行法增加了受益主体范围,导致向阅读障碍者提供的作品类型是否应限定为文字作品显得并不明确。
(一)“已经发表的作品”应不限于以印刷品形式表现的作品类型
现行《著作权法》规定“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构成合理使用,但并未明言“已经发表的作品”应当限于何种类型。这看似不成问题,但若该合理使用条款所指向的作品类型仅限于文字作品,则阅读障碍者的欣赏作品权益相对于旧法并未得到根本提升。反之,若规定该项合理使用指向的作品类型过于宽泛,则难免有损著作权人的利益。例如,是否应当将可以合理使用的作品扩张到视听作品中?目前,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发展迅速,的确为视觉障碍群体带来福音,但如果《著作权法》未将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作品类型进行扩张,则即使公益性制作无障碍电影也有侵权之虞。
作品本质上就是某种“表现形式”,一般体现为人们所共同认可的意义符号的排列组合,以及这些排列组合所直接限定的要素。(8)卢海君:《版权客体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47-48页。因此,各国立法大都通过表现形式来划分作品类型。美国《版权法》对“文字作品”的定义予以明确,规定其不包括“视听作品”。(9)See 17 U.S.C., § 101.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该规定是否意味着可能承载了文字作品的“电影”(以及录像带和光盘)载体不包括作为“视听作品”形式的电影呢?答案是否定的,其原因在于“电影”仅仅是物质载体,可能包含视听作品和文字作品,而视听作品由“一系列相关的图像”组成,而文字作品由“文字、数字或其他文字或数字符号或标记”组成。(10)Melville B.Nimmer, Nimmer on Copyright, Matthew Bender & Company, Inc., 2003, §2.04.由此可见,视听作品与文字作品的差异就在于表现形式以及对应的受众体验。
从《马拉喀什条约》的全称中可发现,其受益主体为“盲人、视力障碍者或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印刷品阅读障碍者”(Print Disabled)的定位显示了该条约指向的作品类型非常有限,且条约第2条也明确规定了作品的“形式为文字、符号和(或)相关图示”。(11)《马拉喀什条约》(2013)第2条(二)规定:“‘作品’是指《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款所指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形式为文字、符号和(或)相关图示,不论是已出版的作品,还是以其他方式通过任何媒介公开提供的作品。”如前所述,美国法根据作品表现形式将文字作品与视听作品严格区分,以“形式为文字、符号和(或)相关图示”为表现的作品绝不可能属于视听作品,因此其《版权法》也据此原理将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的作品类型限定为文字作品。(12)See 17 U.S.C., § 121(a).我国法上的视听作品的表现形式同样被规范描述为“有伴音或无伴音的连续画面”,在物理属性上显然不可被印刷。(13)参见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第4条第(十一)项,尽管这并不是配套2020年现行《著作权法》有关“视听作品”的规定,但由于“视听作品”与旧法中“电影作品”在表现形式与受众欣赏体验上无任何区别,该《实施条例》的规定仍不失参考价值。如果片面看待条约和美国法,则难免得出如下结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提供给阅读障碍者的“已发表作品”不应扩展至非印刷品外的作品类型。但需要注意的是,著作权国际条约一般只是设定最低保护义务,允许各国内法进行适当变通。(14)Sam Ricketson and Jane C.Ginsburg,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nd Neighbouring Rights: The Berne Convention and Bey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301.《马拉喀什条约》第12条“其他限制与例外”之一也规定:“缔约方可以依照该缔约方的国际权利和义务,根据该缔约方的经济情况与社会和文化需求……在其国内法中为受益人实施本条约未规定的其他版权限制与例外。”
事实上,在条约缔结时,中国代表团就极力争取删除“形式为文字、符号和(或)相关图示”的条件,王迁教授对此主张,我国应当充分利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尽力争取而来的权利,为我国视障者规定更多的版权限制与例外,其中最需要的即是对影视作品的版权限制与例外,有必要扩大版权限制与例外适用的作品范围不再将其局限于文字作品。(15)王迁:《论〈马拉喀什条约〉及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10期,第54-55页。例如,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三维状态的画面呈现,其还会有触觉等一系列感觉的呈现,借用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视觉损伤,帮助不可恢复的阅读障碍者体验相应的观感。(16)周澎:《“VR+阅读障碍者图书”出版的著作权制度困境、价值与展望——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载《编辑之友》2020年第9期,第97-98页。类似新技术对阅读障碍者欣赏作品无疑有重要意义,如果不将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中“已发表作品”进行类型扩张,必然不利于我国发展迅速的无障碍电影等极具公益性质行业的发展。
(二)根据原作品制成的“无障碍格式版”也应不拘泥于表现形式
“无障碍格式版”(accessible format version)是指采用替代方式或形式让受益人能够与无视力障碍或者其他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一样切实可行、舒适地使用作品的版本。(17)参见《马拉喀什条约》(2013)第2条“定义”部分(二)的规定。在我国旧法框架下,提供给盲人群体阅读的无障碍版本仅限于盲文,除此之外的“无障碍格式版”制作则属于著作权侵权行为。在“中国盲文出版社与许进京等侵犯著作权纠纷一案”中,盲文出版社主张其将《脉法精粹》一书录制为录音制品与改成盲文出版的性质相同,法院则否定该主张,认为将已出版作品录制成录音制品并不在法律规定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情形之列。(18)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03906号民事判决书。
旧法的盲人合理使用条款的不足之处在于,即使刻意将受益主体限制为盲人,也不应将“无障碍格式版”限定为盲文形式,盲人并非只能通过触摸盲文欣赏包括印刷品在内的作品类型。相比之下,《马拉喀什条约》对“无障碍格式版”的定义采用的就是“技术中立”的立法方式,不限定其表现形式而只说明能达到的效果。据此任何能够使视障者感知作品内容的版本,均属于无障碍格式版。(19)王迁:《论〈马拉喀什条约〉及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10期,第54页。
现行《著作权法》颁布之前,《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第22条第(1)款第(十二)项采用的措辞为“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与现行法相比,多出了“独特”二字。这一用语,同见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13)第6条:“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通过信息网络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所谓“独特”,指的是专属于盲人能够感知而正常人一般不会采用的阅读方式。除了盲文以外,如大字版、有声读物以及能在盲用软件上使用的各种格式,本身并不属于只能由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使用的格式类型,不仅可供印刷品阅读障碍者使用,也能被没有身体障碍的一般人使用。(20)黄梦萦:《论我国印刷品阅读障碍者著作权例外制度的完善》,载《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7年第5期,第39页。此类版本无法被定义为“独特”,言下之意,上述条文并不会将“无障碍格式版”扩展到除盲文以外的正常人也能够使用的版本。
现行《著作权法》修改时刻意删除了《修正案(草案)》中的“独特”二字,笔者认为,这并非技术性的调整,而是有其特殊的立法目的,旨在为“无障碍格式版”不再局限于只能由阅读障碍者欣赏的独特方式提供解释空间。
(三)不必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为可提供版本的限制条件
《马拉喀什条约》第4条之四规定:“缔约方可以将本条规定的限制或例外限于在该市场中无法从商业渠道以合理条件为受益人获得特定无障碍格式的作品。”此即学理上所谓的商业不可获得性前置条款。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并没有明确该前提,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可提供客体为“已经发表的作品”。无障碍格式的作品如果在市场上已经存在(包括著作权人自行将其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情形),重新制作并提供该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是否还能落入著作权限制与例外的范畴?这在我国理论界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从合目的性解释出发,认为《马拉喀什条约》旨在解决阅读障碍者所面临的无障碍阅读版本匮乏的困局。也是因此,当作品的无障碍阅读版本已经在市场上以合理的价格在合理的时间内流通,便意味着该作品于阅读障碍者而言不存在无法获取的困难,自然也无须重新制作。(21)鲁甜:《我国视力障碍者获取作品之著作权限制研究——以日本经验为视角》,载《国家图书馆学刊》2021第3期,第29页。日本《著作权法》第37条规定,若著作权人或获得其许可的人已通过合理方式向视障者提供了无障碍版本,他人无权再进行此类合理使用。准此以言,我国法应当将商业不可获得性作为适用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的前置条款。另有观点则持相反立场,认为虽然规定商业不可获得性适用前提可以保护已经从事“提供”无障碍格式出版物实践的出版商的利益,考虑到中国出版商尚未全面从事此方面的实践,规定该前提似乎也缺乏现实需求,也不利于有志于从事此方面实践的中国出版商、其他非盈利机构充分利用国外既有资源。(22)王清:《新修正〈著作权法〉的两个思考、一个建议》,载《出版科学》2021年第1期,第26页。
在发达国家,约有5%~7%的已出版书籍能够转化为无障碍版本,让印刷品阅读障碍者得以接触,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数字则低至0.5%。(23)Paul Harpur, Discrimination, Copyright and Equality: Opening the E-book for the Print-disabl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59.我国印刷品无障碍阅读障碍者的数量十分庞大,无障碍出版行业的发展更加需要著作权法为其扫清障碍,加大著作权的让渡力度,具备客观正当性。《马拉喀什条约》第4条之四虽然规定各国可以基于提升对著作权人的保护而设置商业不可获得性前置条款,但这并非强制性的条约义务。我国现阶段基于发展无障碍作品提供事业的需要,不必规定商业不可获得性为适用前提。
三、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中的主体规范化
现行《著作权法》将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受益主体从“盲人”扩大到“阅读障碍者”,改进了旧法受益主体较为狭窄的不足。在该项合理使用的主体层面,现行法虽然明确了受益主体,但是否应与《马拉喀什条约》完全一致有待明确,且为受益主体提供作品的“提供者”以及“代理人”的明确化,也与阅读障碍者现实利益息息相关。
(一)法律解释应填补受益者代理人相关规定的空缺
有学者将《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的相关主体范围从学理上划分为当然主体、当然主体的代理人以及法定辅助人三种,当然主体是作为受益人的阅读障碍者,代理人是条约第4条下特定阅读障碍者的主要看护人或照顾者,法定辅助人则是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被授权实体。(24)参见徐小奔:《论视力障碍者的作品获取权——兼论〈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适用》,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3期,第63页。受益人的代理人从定义上不难理解,在我国国内法上可直接套用民法上的相关制度。从世界范围看,成年监护制度清晰地呈现出从医疗监护模式转向人权监护模式,我国作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宣言》的签署国,应顺应当前国际趋势,确立人权监护模式的成年监护制度。(25)参见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的现代转向》,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2期,第199页。《马拉喀什条约》所规定的当然主体代理人,无疑是符合人权监护模式的法律设定,即:“受益人有权依法使用作品或该作品复制件的,受益人或代表其行事的人,包括主要看护人或照顾者,可以制作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供受益人个人使用,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受益人制作和使用无障碍格式版。”也就是说,如果受益人或其代理人有能力,则可以自行制作无障碍格式版,而无须等待被授权实体的提供。
如前文所述,我国法应当扩张无障碍格式版的范围,使其能够包含普通公众可以欣赏的有声读物等内容。则依据《马拉喀什条约》第4条的规定转化为我国国内法时,代理人将图书录制下来供阅读障碍者使用可以落入合理使用的情形。然而,从我国旧法与现行《著作权法》相对简短的表述中,均无法得知代理人实施此类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理论上讲,“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是现行《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一)项法定的合理使用情形之一,因此,受益人自行制作无障碍格式版供自己欣赏当然不构成侵权(现实操作上可能存在障碍),但代理人制作无障碍格式版供阅读障碍者使用之行为能否构成该条第(一)项的个人使用情形,关乎阅读障碍者的切身利益。
有观点提出,对“个人”作出严格解释固然有利于保护作者权利,但在家庭联系如此紧密的我国,如果将家庭范围内的学习、欣赏和研究也列为非合理使用,在实践中难以实行,且存在较大举证难度。(2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9页。国外法上亦有将家庭视为私人复制主体范围的规定,值得我国立法借鉴并予以明确。(27)日本《著作权法》(2003年修订)第30条规定:“限于个人或家庭及其他与之类似的范围内使用为目的时,使用人可以复制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作为信息获取能力存在障碍的弱势群体,实现“阅读障碍者信息获取权的保障是信息公平的应有之义”(28)唐思慧:《阅读障碍者版权例外制度研究:基于信息公平的视角》,载《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第88页。。我国著作权立法应当填补受益者代理人有关规定的长期阙如,明确赋予其作为“个人”进行合理使用权限,以弥补《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规定的不足,提升阅读障碍者借助其代理人获取信息的能力。
(二)无障碍版本的部分“提供者”的间接营利不应受到限制
我国现行法没有具体指明向阅读障碍者“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的合理使用行为应当由何种主体实施,只能从字面上将其称为“提供者”,对应《马拉喀什条约》第2条第(二)项的“被授权实体”一词,根据条约的定义,“被授权实体”是指得到政府授权或承认,以非营利方式向受益人提供教育、指导培训、适应性阅读或信息渠道的实体。“被授权实体”也包括其主要活动或机构义务之一是向受益人提供相同服务的政府机构或非营利组织。从中可知,该主体不但有其特定的构成资质,还要在行为上具有非营利特征,但这两点是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现行法上有关“提供者”的具体界定则缺乏相应解释。
《马拉喀什条约》作为著作权国际条约,其很大程度上必须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实现利益妥协,其结果往往与各国实际立法需求并不吻合。“动辄引公约为证,逃避说理,是知识产权研究的一大流弊”(29)李琛:《论知识产权法的体系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马拉喀什条约》中“被授权实体”这一关键词更宜作为我国法上“提供者”的解释工具,而非直接对其进行原封不动的照搬。为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无障碍格式版”是具有公益性质的行为,但行为的公益属性并不必然要求该提供者完全不能间接营利。
著作权法上的营利具有多重含义,既包括直接营利也包括间接营利,全盘坚持“不以(任何方式)营利为目的”原则,容易限制法律本应让渡给提供者的间接营利权益。间接营利的允准与否,往往可以作为一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水平的衡量标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Herbert v Shanley案”(30)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Herbert v Shanley Co.(1917), No.427., https://caselaw.findlaw.com/us-supreme-court/242/591.html, last visit: August 28, 2021.中明确间接营利构成侵权,其《版权法》第109条(b)规定:“特定的录音制品所有者不可为了直接或间接的商业利益以出租或出借或属于出租或出借性质的其他任何行为或做法处置或授权处置该录音制品的占有权。”出租权与出借权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出租行为本身可以直接获利,而出借行为本身则不可直接获利。与美国类似,德国法亦规定了一项图书馆版税制度,授予著作权人向出借机构可行使的报酬请求权。(31)参见[德]M·雷炳德:《著作权法》,张恩民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88页。我国著作权立法未设任何关于“出借权”的明文,其主要考量因素便是对著作权的保护水平不宜扩展到限制间接营利的程度。
尽管侵犯著作权不纯粹以营利目的为前提,但从体系化推断而言,在某些方面我国立法对著作权人的保护水平现阶段不可能事事与发达国家同规格。发达国家为提升著作权保护水平,必然要更大程度弱化公众利益,尽量减少合理使用者的间接营利可能。我国立法不必亦步亦趋地做此要求,反而应当限制著作权人控制无障碍版本提供者作为合理使用主体的间接营利行为。
根据我国现行法的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而该作品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获取”,属于可以避开技术措施的情形。(32)现行《著作权法》第50条第(二)项。相比于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在规避技术措施责任豁免的立法设计上,该规定明确增加了“不以营利为目的”和商业不可获得的前提条件。两项规定的微妙差别,存在两种解读可能:其一,在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的规定中,立法者追求表达的简约,留待《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来说明上述“不以营利为目的”和商业不可获得的前提条件;其二,立法者考虑到实施合理使用的“无障碍格式版”提供者的范围更加广泛,特意为其预留(间接)营利空间,这也与不规定商业不可获得前置使用条款逻辑自洽。
有观点认为,提供者的使用目的只要满足社会公益目的,就符合合理使用的立法目的,即使提供者存在较大比例的商业性目的,也不应当被排除在合理使用目的所认可的范围之外。(33)刘水美:《扩张合理使用目的法律适用新规则》,载《知识产权》2019年第8期,第66页。要求提供者完全不得营利,为很多未得到政府支持的经营者施加了过重的道德义务,不利于将无障碍阅读事业市场化与规模化。事实上,我国无障碍阅读事业目前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供求关系不平衡,因而著作权立法应当引导市场发挥作用以解决该困境。基于我国社会公益的现实需求,在我国《著作权法》进一步解释过程中,不能直接与发达国家立法例的做法完全一致,可以适当让利给无障碍格式版的提供者,以激励该产业的市场化参与。
(三)从具体操作层面明确“提供者”的具体范围
对于《马拉喀什条约》中制作无障碍格式版的“被授权实体”究竟指的是哪些主体,学界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已予以探索,如有学者认为,能否被认定为“被授权实体”主要是看其行为的性质而非政府的授权。基于我国现实,残联以及相关的盲文出版机构应是合适的“被授权实体”。图书馆也应是合适的“被授权实体”,其不但可以为盲人的阅读提供便利,基于图书馆的综合优势,也可以让其承担无障碍格式作品的跨境交换。(34)曹阳:《〈马拉喀什条约〉的缔结及其影响》,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9期,第82、87页。在本次著作权法修改前,残联和盲文出版机构已经长期担负盲文的制作,且盲人群体依然是主要的阅读障碍者之一,上述机构在新法出台后理应继续发挥作用。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2017)第34条第(2)款规定:“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应当考虑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特点,积极创造条件,提供适合其需要的文献信息、无障碍设施设备和服务等。”这与著作权法上保障阅读障碍者获取作品权益的精神是契合的,因此,将公共图书馆作为无障碍格式版的主要提供者之一也十分重要。我国《残疾人保障法》同样强调政府和社会的协同作用。(35)《残疾人保障法》第43条:“政府和社会采取下列措施,丰富残疾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二)组织和扶持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及其他残疾人读物的编写和出版,根据盲人的实际需要,在公共图书馆设立盲文读物、盲人有声读物图书室。”
尽管不少国家的立法都要求只有政令允准的主体才属于“被授权实体”,如日本《著作权法》第37条、第37条之二即要求为视觉、听觉障碍者提供作品的主体是“政令规定的人”。(36)参见杨和义编译:《日本知识产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39页。但考虑到我国阅读障碍者人群数量庞大的现实,短期内仅依靠残联、盲人出版社和公共图书馆尚不足以解决无障碍格式版供不应求的局面。为了保障市场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同时规范其提供行为,本文认为,应当从多个方面建立完善的运行机制。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政府补贴机制,帮助市场参与主体实现非直接营利,为其进一步投入资金制作并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本的作品予以回馈,否则无法形成长效的激励机制。其次,应当允许其自行收取部分费用,即使是非营利法人,也有权收取必要的管理费用。例如,此次《著作权法》修改将集体管理组织定性为《民法典》第87条第(1)款意义下的非营利法人,但并不妨碍其可以收取作品许可费用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用于改善服务。(37)黄薇、王雷鸣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导读与释义》,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54-155页。最后,要加强对非政府授权提供者的监督,防止可能出现的权利滥用情形。
四、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中“提供行为”的界定
此次修法将旧法“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改为现行法的“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向其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表面上只是将“出版”改为“提供”,但受提供作品类型与无障碍格式版表现形式变化的影响,新法中的“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的行为性质也变得复杂化。
(一)制成“无障碍格式版”一般须不脱离复制原作品的范畴
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前的条文中使用了“出版”一词,该出版行为的前提是将作品“改”为盲文,容易让人误解盲文制作者实施了改编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前文在论及无障碍格式版的规范意蕴时就阐明,将文字作品改为盲文采用了“布莱叶点字法”,原文字作品与盲文具有对应性,只是受众由视觉欣赏转为触觉体验。(38)有学者指出:“因为汉语文字与盲文符号之间存在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任何懂汉语和盲文的人只要按照规则进行正确的转换,都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7页。因此,“出版”盲文只是将原作品的载体以销售或赠与的方式转移给盲人群体。(39)鉴于提供盲文版本的公益性质,此处的发行主要是以赠与的方式加以实现。尽管很多动漫、游戏公司倾向于采用“本作品已由网络出版”的方式代指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但盲文是以触觉方式呈现的,从技术上讲,通过网络进行的实时或交互式传播均缺乏现实意义,除非新技术开发出可以通过电子屏幕传达触觉信息的传播功能。旧法将受益主体和无障碍格式版分别限定为盲人和盲文,就决定了被授权实体的提供行为属于对作品复制件的发行,并无其他与著作权专有权能对应的行为模式。
现行《著作权法》要求合理使用的实施主体“以阅读障碍者能够感知的无障碍方式”提供作品,由于无障碍格式版可以采用不拘泥于盲文的有声听书、大字版等方式提供给阅读障碍者,该“提供”行为相对于旧法增添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定性现行法上的提供行为,关键在于制成无障碍格式版是否仍属于复制行为。针对有声读物的著作权法性质,我国司法界有观点指出,严格对照文字作品原文朗读形成的有声读物,无论其是否添加了背景音乐、音效,都没有改变文字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因而不构成改编作品。有声读物作为一种录音制品,是文字作品的复制件。(40)张书青:《“有声读物”涉著作权若干问题浅析》,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第22期,第68页。该原理与盲文的性质判定一致,有声转换虽然改变了作品的表现形式,使得受众获得不同感官体验,但作品的内容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仍属于对信息的复制。有学者也提出,获取权的目的仅在于给视障者提供接触作品的机会,而不是要给他们增添“额外的”作品享受利益。(41)徐小奔:《论视力障碍者的作品获取权——兼论〈马拉喀什条约〉在我国著作权法中的适用》,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3期,第64页。原封不动地转换原作品,一般而言更符合该合理使用设计的本意,也避免了不当侵夺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制成无障碍格式版行为的复制属性,决定了后续提供行为一般表现为发行。
(二)现行法中复制作品后的“提供”应包含发行、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
随着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作品的渠道日益便捷,且现行法未明确限制有声读物等内容,印刷品阅读障碍者通过远程方式获取作品成为可能。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2013)第6条第(六)项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以盲人能够感知的独特方式向盲人提供已经发表的文字作品”构成合理使用,鉴于盲人以非触摸欣赏的方式无法欣赏盲文,该条例的立法应理解为具有前瞻性,即通过有声读物等方式让盲人在选定的时间与地点欣赏文字作品。中国盲协盲人有声数字图书馆、中国盲人数字图书馆、文化部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声音频馆等多家数字图书馆为阅读障碍者提供在线欣赏作品的服务。
对于复制原先以印刷形式表现的作品之后以无障碍版本的“提供作品”行为,并非理所当然地可以延伸到无线电和互联网远程传播领域,是否应当如此取决于各国立法的价值基础。作者权法系国家对作品进行保护的法哲学基础主要可以追溯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自然权利理论。田村善之教授将其概括为“支持‘强力型知识产权保护’的自然权论”,即给予作者一种高度的自然权利。(42)[日]田村善之:《田村善之论知识产权》,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28-131页。在作者权法系国家,由于对作者权保护的极端强调与作者本位思想在其立法中的主导,对作者的权利限制与例外规则显得相对谨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法上,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进行复制属于无偿使用作品的一种情形,即用盲文或任何其他方法,但必须是已经出版的作品并得到作者的授权,而且复制不应有营利目的。(43)[西]德利娅·利普希克:《著作权与邻接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81页。德国著作权法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利益,限制了复制权与发行权,只要复制或发行不是为了营利目的,作者仍享有报酬请求权。(44)[德]图比亚斯·莱特:《德国著作权法》,张怀岭、吴逸越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1页。撇开作者尚且享有报酬请求权,上述立法还限制了合理使用主体提供作品的行为方式,除复制与发行之外,并未扩展到其他行为。
从立法的体系基础上,相对于英美版权法系,我国著作权立法在总体理念上更接近作者权法系:一方面,在权利设置上采用类似于法国的二元模式,在财产权之外明确规定了著作人身权;(45)参见吴雨辉、徐瑄:《著作人格权的历史与命运》,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49页。另一方面,在著作权与邻接权的设计中,作品的构成需要较高独创性,而不具有独创性的与作品相关的客体则被归入邻接权范畴。但是,我国著作权法对于作者权利的保护似乎还未到达传统作者权法域的程度,例如,在视听作品中,我国法就将著作权原始归属于作为法人的制作者而非作者。(46)张春艳:《论我国电影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9期,第80-84页。依此逻辑,使作者让渡更多的利益给公众,尤其是出于公益事业的正当理由,在我国法上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相比于作者权法系的一些国家只在复制权和发行权上设置限制和例外,我国法可以尝试将合理使用行为扩张至信息网络传播权和广播权等情形中。《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CT)第8条规定“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将其作品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可获得这些作品”,我国是WCT的缔约国,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中采用了“提供”一词,应当是“向公众提供”的上位概念,而WCT中“向公众提供”无疑指的是我国法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47)刘银良:《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与广播权的界限》,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6期,第97-114页。从协调国际条约的视角,亦足以佐证扩张合理使用行为的立论。
(三)应允许“口述影像”对视听作品的改编提供
在我国现行法下,被授权实体可以向阅读障碍者提供已经发表的作品,包括但可以不限于文字作品,其原因前已述及,兹不赘述。我国近年来无障碍电影发展迅速,为阅读障碍者群体提供了新的娱乐体验而备受好评。例如,成立于2017年的“光明影院”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北京歌华有线、东方嘉影共同发起的无障碍电影制作与传播公益项目,该项目在电影对白和音效的间隙,插入对于画面的声音讲述,制成可复制、可传播的无障碍电影。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蔡雨坦言:“一部无障碍电影的配音工作基本四五个小时就能完成,但讲述稿可能要花上几百个小时,写出几万字的讲述稿。”(48)新京报记者滕朝:《为视障朋友讲电影,探索中的“光明影院”》,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634792814112.html,2021年8月30日访问。
阅读障碍者难以感知电影的画面、色彩来识别其中的人物和场景,这极大妨碍其理解电影的基本情节。电影文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类型十分丰富,可以是有伴音的,也可以是无伴音的。(49)参见《著作权法实施条例》(2013)第4条第(十一)项规定。类似卓别林喜剧就是以黑白色彩的默片形式呈现的,阅读障碍者完全无法感知此类作品,只有将动态影像转换为文字描述并有声播放出来,才能达到向特殊人群提供作品的效果。基于我国保障阅读障碍者文化权益的现实需求,应当赋予合理使用者提供口述影像的特权。在将电影转换为口述影像的过程中,凝结了大量的创造性劳动,不同的实施主体针对同一部电影可能会撰写出表达形式迥异的口述文稿,转换的过程满足独创性判断中的创作空间要求。(50)See Ralph D.Clifford, Random Numbers, Chaos Theory, and Cogitation: A Search for the Minimal Creativity Standard in Copyright Law, Denver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82, 2004, p.272.《马拉喀什条约》(2013)第2条在规定“无障碍格式版”的定义基础上,提出:“无障碍格式版为受益人专用,必须尊重原作的完整性,但要适当考虑将作品制成替代性无障碍格式所需要的修改和受益人的无障碍需求。”为实现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目的,必须实施一些改动作品的中间步骤,有学者将这些中间步骤理解为“如提供配套设备,或对作品进行必要的修改等”。(51)徐轩:《图书馆印刷品阅读障碍人士版权例外研究——〈马拉喀什条约〉述评及对中国图书馆界的建议》,载《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12期,第61页。口述影像虽然并非对电影的复制,但仍属于具有正当性的改编。
将改编后的口述文稿以录制后分发、现场朗诵、网络点播、定时播放等形式提供给公众,属于改编的后续行为还是分别实施了受著作权法控制的发行、表演、信息网络传播、广播行为?在我国法院审理的“观音饼案”中,被告冠素堂公司未经许可将原告叶某某的古文体《观音饼来历》改编为白话体的《观音饼的由来》,且冠素堂公司将改编后的作品用于商品销售,也未向叶某某支付报酬。法院认为,冠素堂公司在其观音饼包装盒上使用的是改编后的《观音饼的由来》,并非被动地再现叶某某作品,或以出售、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叶某某作品复制件,故其并未侵害叶某某所享有的作品发行权、复制权。(52)本案曾入选“2016年度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一审判决参见浙江省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浙舟知初字第3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浙民终118号民事判决书。根据该案的判决理念,一旦改编了原作,改编权就足以囊括后续利用行为。
在旧法的规定下,将文字作品改为盲文的行为虽然也是广义上的改动,但并非受改编权控制的行为,只能理解为一种为实现特定目的的必要安排。与之类似的是音乐作品的改动,例如改动一首钢琴曲以便其能够在笛子上吹奏,由于管乐器与弦乐器的差异,必须对曲谱进行改动,但这是一种必要的行为,著作权法上不将其等同为改编。根据此项原理,由于在大多数情形下,将原作品改为无障碍格式版,都是一种必要的改动,从而属于复制行为,至于复制之后的提供,则需要根据后续行为模式定义其实施了何种受控行为。口述电影类的无障碍格式版是对原作品的改编,其后续提供也属于实施了受改编权控制的行为。
五、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体系性解释
拉伦茨教授在其《法学方法论》一书中点明:“任何规范的解释必须相应地考虑相关规范体的意义脉络关联、上下文背景以及该规范的体系位置,还有就是该规范在相关规范体的整体脉络中的功能。”(53)[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黄家镇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48页。准此以言,现行《著作权法》24条第(1)款第(十二)项的具体规范并非是孤立存在的,与之配套性法律解释必须将其寓于合理使用的法秩序当中。(54)参见[德]罗尔夫·旺克:《法律解释》,蒋毅、季红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95-96页。
现行《著作权法》对整个合理使用制度的修改,一方面体现于十三项具体规定中,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一般条款上,增加规定“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在2013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1条便有相同表述:“依照著作权法有关规定,使用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的已经发表的作品的,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追根溯源,这是我国著作权立法对最初出现于《伯尔尼公约》,后来又被《TRIPs协定》和WCT所延续的“三步检验法”的明文转化。(55)具体条文分别见《伯尔尼公约》第9条、《TRIPs协定》第13条、WCT第10条。《伯尔尼公约》的“三步检验法”最初旨在约束各国立法者,并非一种由法院直接适用的规范,随着实践过程的演变,“三步检验法”发展成为一种对著作权“限制的限制”,它既是一种对国内立法中既存权利限制条款的解释规则,也是在创立新的限制与例外时应当参照的准绳。(56)张陈果:《解读“三步检验法”与“合理使用”——〈著作权法(修订送审稿)〉第43条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第17页。在新法未生效之前,我国法院已经将《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的规定作为判决依据。(57)例如“北京龙源网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魏剑美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民终2701号民事判决书。合理使用一般条款的适用,扩大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充分发挥其对著作权限制之再限制的作用,使利益的天平在社会公众与著作权人之间维持巧妙的利益平衡。(58)刘明江:《著作权合理使用一般条款与特别条款关系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6年第6期,第65页。
有观点认为,使用行为一旦符合具体条款规定的适用条件,则不应再适用三步检验法,否则会导致合理使用的法定豁免范围受到进一步限缩,惟有在具体条款中包含“适当”“必要”“合理范围”以及“合理限度”等抽象用语的情况下,法官才有必要运用一般条款的相关规则进行填补式的合理使用判断。(59)李杨:《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体系构造与司法互动》,载《法学评论》2020年第4期,第95页。原则上讲,一般条款的适用理应具有谦抑特性,但现行《著作权法》中阅读障碍者条款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无论是适用主体、客体与行为模式的规定都极为抽象,在配套性法律解释缺位的情况下,法院在个案中如果不采用一般性条款对其进行体系性的法律续造,则容易导致利益失衡。有观点分析了新法中一般条款的作用,认为其是对明文规定的未经许可利用作品不构成侵权的行为范围进行的再限制,一种未经许可利用作品的行为,如果表面上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不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但该行为影响了对作品的正常利用,或不合理地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利益,则这种行为仍然构成侵权。(60)王迁:《〈著作权法〉修改:关键条款的解读与分析(上)》,载《知识产权》2021年第1期,第29页。因此,必须结合一般条款的价值判断与具体条款的规范要件,对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行为进行双重分析。
在一起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的案件中,二审上诉人认为,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条的规定,涉案软件的开发初衷是为了协助视觉障碍人群阅读,属合理使用。法院认为,没有证据表明涉案软件系专门面向盲人用户,该软件虽有机械朗读的语音播放技术,但读者也可以通过下载阅读方式获得作品内容,且该软件还设置有充值界面。涉案软件并非单纯用于公益目的,上诉人的被控侵权行为不构成著作权法意义上的合理使用。(61)北京天行汇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上海知识产权法院(2017)沪73民终235号民事判决书。在2021年世界知识产权日,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无障碍版侵权纠纷一案引发关注,一审北京互联网法院即根据“是否影响涉案影片的正常使用”“是否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标准而判决被告败诉,并指出即便是在新修《著作权法》施行后,涉案APP对不特定公众提供影片无障碍版点播服务的行为亦不属于合理使用。(62)李锐:《无障碍电影,版权能否无障碍》,载《光明日报》2021年05月19日第13版。上述判决结果具有一定启示意义,阅读障碍者的特殊身份使其应当受法律优待,但仍应防止他人借机寻租以获得非法利益。
现行《著作权法》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的特殊条款极为抽象,没有明确规定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以及能否面向一般公众,法官正是根据一般条款的精神,作出有利于著作权保护的判决。我国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的特殊条款高度简洁特征,不利于法院形成统一的裁判准则,从立法论上,应当适当援引国际公约并借鉴国内外成例,结合我国国情现实,设计专门而详细的法律规则,将一般条款之约束理念转化到特殊条款的配套法律解释之中,方有利于立法的稳定性与可预见性。(63)在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实践中,在专门条款不足以完全适用的情形下,将专门条款向一般条款“逃逸”便体现了这种弊端,不免令人诟病。郑友德、王活涛:《新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顶层设计与实施中的疑难问题探讨》,载《知识产权》2018年第1期,第5页。
现行法一般条款来源于“三步检验法”,有学者指出,对于该检验法有效的条约解释原则要求为每一步赋予确切含义,避免使任何一个条件冗余,三个条件应累计适用。(64)[美]弗雷德里克·M.阿伯特等:《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法》,王清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733页。因此,“三步检验法”抑或我国现行法的一般条款均可以用于检验并完善特殊条款:首先,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本身确属“限于某些特殊情形”下作出的权利限制与例外,无须赘言;其次,向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格式版“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恰如前文我国法院的相关判决所示,如果提供行为以直接营利为目的,导致某一部市场热映的电影被一般公众通过非院线方式所接触,且造成了实质性市场替代,则该种使用行为难言妥当,这也是《马拉喀什条约》要求被授权实体将无障碍格式版的发行和提供限于受益人和(或)被授权实体的原因所在;最后,提供行为“不得不合理地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未标明作者身份、歪曲作者思想等问题都将导致提供行为的非合理性。
对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特殊条款进行体系性解释,同样也是《马拉喀什条约》的要求,条约第11条规定了“关于限制与例外的一般义务”,要求缔约方在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条约的适用时,需遵照《伯尔尼公约》第9条第(2)款、《Trips协定》第13条、WCT第10条前两款的规定,“应将对专有权的限制或例外限于某些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触,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权利人合法利益的特殊情况”。言下之意,各缔约国拥有在《马拉喀什条约》基础之上设置额外专有权利限制与例外的一定程度的自由,但不得违反“三步检验法”。本文主张我国法应扩张制作无障碍格式版的表现形式及其基础作品类型,无疑增加了对著作权的限制,但只要没有越过著作权保护的底线,则超越《马拉喀什条约》为阅读障碍者谋求更大的作品获取权益就不失正当性。“三步检验法”则是衡量特殊条款是否越过著作权保护底线的依据,所谓违反公约义务,是指未达到对著作权的最低保护水平,只要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的解释适用仍囿于“三步检验法”框架内,就不会违反《伯尔尼公约》《Trips协定》和WCT的公约义务。因此,通过一般条款的体系性解释,严格约束特殊条款的适用范畴,也是保障国内法在扩张权利限制与例外时不至于违反公约义务的正当性证成手段。
考虑到《马拉喀什条约》并非直接着眼于著作权专有权利保护,无所谓“最低保护要求”的公约义务之说,综观《马拉喀什条约》全文,其并未明文提及公约本身的执行义务与违反情形,反而允准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在内的国内法根据其特殊需求为受益人设置条约为规定的著作权限制与例外。(65)参见《马拉喀什条约》第12条之一有关“其他限制与例外”的规定。在从现实层面上上讲,立足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充分利用国际公约中弹性规则的转化空间,则是我国国内法与国际法进行互动的应然策略。(66)参见潘皞宇:《论知识产权国际化的保护模式及我国的应对策略》,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第158页。准此,超越《马拉喀什条约》所规定的权利限制与例外规则,将著作权在一定限度内更多地让渡给阅读障碍者并无理论障碍,也符合我国立法的现实需求。
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条款保障了弱势群体的文化权益,是残疾人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我国要充分完善本条立法以与《马拉喀什条约》相协调,条约用了22条来专门规定向阅读障碍者提供作品的著作权限制问题,其中实质性条款就多达12条,无论是我国《著作权法》还是《著作权实施条例》都不可能将其中的要点有效吸纳,应在配套性法律规范中予以全面而细致的解释以明确其适用条件。在立法范式上,有学者建议应仿效《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立法模式,国务院可以根据《著作权法》制定授权立法。(67)王迁:《论〈马拉喀什条约〉及对我国著作权立法的影响》,载《法学》2013年第10期,第63页。该建议符合我国目前著作权立法体系与保护阅读障碍者文化利益的现实需求。
六、结语
现行《著作权法》的对阅读障碍者合理使用规则的修改,进一步实现了与国际公约的一致性,扩大了受益主体范围,具有进步意义。要发挥该条的效果,还需要结合一般条款的体系性规定与我国实际情况,合理转化条约精神,根据第24条第(1)款第(十二)项进行专门立法以将其适用条件具体化。在客体层面,本项中“已经发表的作品”应不限于以印刷品形式表现的作品类型,而根据“已经发表的作品”制成的“无障碍格式版”也应当不拘泥于表现形式,出于鼓励无障碍格式版市场制作与提供主体的参与,不必引入商业不可获得性为适用前提。在主体层面,填补受益者代理人相关立法的空缺,有助于与私人复制条款相结合,发挥家庭在实现阅读障碍者文化权益中的作用。部分无障碍格式版提供者的间接营利不应受到限制,只需限制其不以直接营利为目的进而不合理侵犯著作权人利益即可。在提供行为的层面,配套性法律解释须明确现行法与旧法的不同,提供行为不再局限于复制与出版,复制作品后的“提供”应包含发行、广播和信息网络传播,而在口述影像等演绎了原作品的制作模式下,“提供”应作改编行为理解。并且,根据现行法吸纳“三步检验法”而增加的一般条款,要在上述客体、主体、行为三重适用要件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无障碍格式版制作与提供行为进行个案判断,实现著作权私权保护与裨益于社会公益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