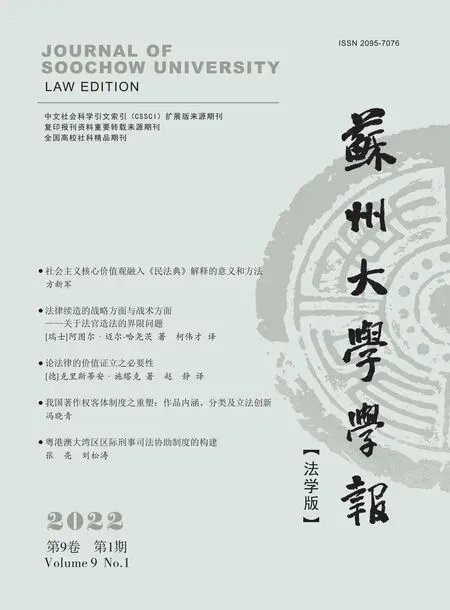法律续造的战略方面与战术方面
——关于法官造法的界限问题*
[瑞士]阿图尔·迈尔-哈尧茨 著 柯伟才* 译
一、导言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想让威廉·克拉克担任副国务卿一职,起初后者对于接受华盛顿的召唤有很大的顾虑。不过,他担心的不是担任新的职务,而是放弃他在此之前所担任的职务。当时,里根以加州州长的身份,用加州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职位来奖励这位保守派共和党的忠实党徒。通过离开这个职位,克拉克此时为现任州长杰里·布朗提供了任命一名自由派法官,从而使法院的“方向盘”转向“左路”的可能性。(1)TIME Magazine vom 19.1.1981, 23; NZZ vom 26.1.1981, 2.—哈勒(Haller)基于“福塔斯、海恩斯沃思和卡斯威尔事件”(Affären Fortas, Haynsworth und Carswell)表明,在美国总统任命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过程中,除了法官的专业资质之外,“狭义的政治考虑”发挥了多大的作用:Walter Haller, Supreme Court und Politik in den USA, 1972, S.80 ff.
为什么——正如非法律人士经常问的那样——个别法官的个性、党派和政治观点会起到如此大的作用?法官应当根据制定法和法律,而不是根据政治偏好作出判决。
在这个问题的答案——甚至有的来自法学家——中经常出现这样的观点:在英美法系中,不存在对法官有约束力的全面法典。我们在旧大陆的情况更好一些,因为在这里法律仍然是法律,而不是政治。
然而,我们当中仍然广泛流行的观念是:法官是非政治性的,他们“仅仅”适用法律。这个观念是否正确呢?
在专业圈子里,毋庸置疑的是,法官除了适用成文法之外,还承担着创造性地续造法律的法政策任务。然而,直到今天仍有争议的是,法官的法律续造活动的程度和界限,此外,创造法官法时应遵循的方法也是有争议的。(2)观点多样性的一个证据是新近的方法论著作所使用的文献呈爆炸性增长。Vgl.z.B.das umfangreiche Literaturverzeichnis bei René Rhinow, Rechtsetzung und Methodik, 1979.需要讨论的早就不再是法官“是否”有造法能力的问题,而只是法官的法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以及制定“多少”的问题。(3)René Rhinow, Rechtsetzung und Methodik, 1979, S.14.
学说上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仍有很大分歧。一方面,人们赞同“立法国家的废黜”,“立法者万能论的摒弃”,希望通过广泛的法律续造职能为法官提供成为“法律的最高价值的守护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人提出要警惕“司法政治化”“第三权力的神话”和日益增长的“对权力分立的忽视”。在1978年一本专门论述法律国家(Rechtsstaat)的文集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句话:“事实证明,法官法是一种慢性毒药。长期不引人注意地进行少量注射,会对法律国家产生致命的后果。”(4)Heinz Düx, Rechtsstaat und Zivilgerichtsbarkeit in Der bürgerliche Rechtsstaat, hrsg.von Mahdi Tohidipur, 1978, S.610 f.但是,不仅是法学界认为难以界定法官的地位和任务;就连法官自己也常常无法确定,难以对自己的角色有一种不受拘束的理解。
下文的论述将围绕这个被我们简要概括的复杂问题进行,但仅限于初步讨论。本文只是为了接近这个复杂的难题,并没有想着要解决这个难题,哪怕只是解决其基本特征的问题。
下一部分旨在将问题置于其历史脉络中。
二、从无漏洞信条,经过传统方法论到现代诠释学
自从有了法官,就有了法官的判决强制(Entscheidungszwang)。禁止拒绝审判(Rechtsverweigerungsverbot)是法律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寻求法律保护的人所求助的法官必须作出判决。但是,判决意味着根据特定的标准支持一方当事人的主张。(5)然而,近几十年来,法官的职责范围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因为法官已经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纠纷裁决领域,成为社会平衡的调解人”: Fritz Baur, Sozialer Ausgleich und Richterspruch JZ 1957, 193.多个世纪以来,司法判决所依据的这些标准已经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变化。
所罗门王利用几乎神圣的智慧以及对人性弱点的理解,对那起关于母亲身份的纠纷作出了判决。在中世纪的法庭程序中,争议各方必须提供的上帝的证明(或更正确地说:偶然的证明)占据着稳固的位置。而在克莱斯特的《破罐记》(Kleist’s Zerbrochnen Krug)当中,乡村法官亚当试图将他的判决建立在哲学的基础上。(6)Heinrich von Kleist, Der Zerbrochene Krug, 9.Auftritt.
随着启蒙运动的展开,成文法作为新的——根据当时的观点,也是唯一的——法发现(Rechtsfindung)标准进入了法官的办公室。根据那时刚刚获得成功、仍然僵硬且毫不妥协的分权原则,法官必须遵守无漏洞的制定法文本。他只是全能制定法的执行者,甚至好比是其奴隶。或者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讲:“帮法律讲话的嘴巴”(7)Montesquieu, De l’esprit des lois, 1748 XI, 6.。借鉴贝格博姆斯(Bergbohms)的表述,当时的主流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需要规范的就由制定法来规范,不受制定法规范的就不需要规范。制定法文本对法官的严格约束因为制定法委员会(Gesetzeskommission)的设立而得到补充,这些委员会必须对制定法模糊的地方和有瑕疵的地方——根据无漏洞信条,理论上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在实践中确实存在——发表意见。(8)法国在1790年还有“立法咨询”(référé législatif),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Friedrich II von Preußen)在1780年还为同样的目的设立了一个制定法委员会: Cabinetsordre vom 14.4.1780.通过这种方式,人们认为可以明确区分这两种权力,并确保立法者的地位高于法官。
但事情远非如此。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一体系过于烦琐,无法确保法院的工作顺利运行。此外,人们痛苦地认识到,法律——就像所有人类作品一样——带有不完美的印记。即使是最有想象力的、将决疑法运用到最细分枝的法典,也无法捕捉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奥斯卡·布洛(Oskar Bülow)对此表示:“事实证明,多卷版的决疑法式法典是最糟糕的、最混乱的、最令人费解的、最不充分的。”(9)Oskar Bülow, Gesetz und Richteramt in Verschiedene Schriften zur Frage der Rechtsanwendung, 1885, S.33.而赫尔曼·康托罗维茨(Hermann Kantorovicz)则说,每一部制定法中包含的漏洞跟它的文字一样多。
随着对法典的完美性要求的放弃和制定法委员会的废除,启蒙运动的分权模式开始动摇。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抓住了这个问题,他说:“分权理论、禁止拒绝裁判和法律的不完美性无法相互配合;这三者当中必须有一个要做出让步。”(10)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Bd.22, 359.
只能在理论上贯彻的过于僵化的分权原则,不得不让步。因为每一条制定法规则都有补充的需要,没有任何方法——无论多么复杂——可以消除这种需要,而且没有人可以合理地接受这样的想法:当要适用的法律规则不明确或不正确的时候,法官可以径直作出“不清楚”(non liquet)的判决。
这种情况导致,例如,《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公开承认法官的法律续造活动,在其法典的开头设置了著名的第1条,该条规定法官有权在成文法和习惯法规范出现漏洞的情况下,根据“他如果是立法者的话将会制定的规则”进行裁决。在什么情况下,法官可以从自己的鞋子里跳到立法者的鞋子里,这个问题对几代法学家当中的方法论学者来说是一个肥沃的工作领域。他们承诺——为了防止进一步破坏分权原则——将法律的适用分为两个明确分开的部分。其中,一个大得多的部分是解释,而另一个相对较小的部分则是漏洞填补。解释被理解为一种无价值评价的、纯逻辑性的思维过程。人们认为,将事实作为小前提涵摄到作为大前提的制定法规范下,可以保证获得唯一正确的结果。法官被认为是一个理性思考的“涵摄自动售货机”,但不是一个独立做出价值评价的“涵摄自动售货机”(黑克)。“法学能被理性除尽,无余数”。(11)Arthur Kaufmann, Die Geschichtlichkeit des Rechts im Lichte der Hermeneutik in Festschrift für Karl Engisch(1969), 256.而且,即使法官在填补漏洞时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立法者,他也不能完全自由地将自己的价值评价引入裁判过程。制定法规则的体系性和立法者预先确定的法政策态度应当可以限制其活动空间。
但是,法官更多地是被他自己的恐惧所限制,即被一种“对真空的恐惧”所限制:害怕自主做出价值评价,害怕不得不公开承认,对于很多案件,在制定法和习惯法中都找不到答案。所有现代立法者都承认他们的法律适用者在面对制定法时享有自由,然而,总是只有少数人有利用这种自由的勇气。其他人则在法发现的过程中,坚持走在整齐铺装并撒过盐的道路上,避免踩到缝隙中的新雪,留下自己的创新足迹。根据解释艺术的全部规则,答案来自于制定法,即使制定法中没有包含答案。有人从适用时的视角来论证,有人从形成时的视角进行论证;有人强调文义,有人强调目的;有人求助于立法资料,有人将其视为无关紧要的东西推到一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不用承认实际存在漏洞,以及不用在公开论证中填补这些漏洞。在被误解的方法论诚实(Methodenehrlichkeit)地掩盖下,所有可用的解释元素都被用来向不诚实致敬。
以严格的真理追求为己任的法学家对真正的方法论程序的隐瞒,不断地促使有批判精神的同行们拿起武器反对传统的方法论。因此,早在1916年,阿道夫·默克尔(Adolf Merkel)就写道:“从一开始,人们就很少采用一种特定的方法;特定的方法将——人们可能会这么认为,如果人们思考过这个问题的话——由工作来决定。采用哪种解释方法,可以说是‘具体情况所要求的’,可以找到起初希望的和最终选择的解释方法。解释的难题要在具体情况中处理。”(12)Zeitschrift für das Privat-und öffentliche Recht 1916, 542.而古斯塔夫·拉德布鲁赫认为:“解释是结论,其结论的结论”。
近来,其他科学领域的代表也参与了传统方法论提出的解释菜谱(用于烹饪唯一可食用的判决书)与司法实践中使用的“辩证-液压解释机(法律适用者可以通过它从每个文本中提取他需要的东西)”(13)Rudolf von Jhering, Scherz und Ernst in der Jurisprudenz, 1912, S.262.之间的争议。最值得一提的是汉斯·乔治·伽达默尔(Hans Georg Gadamer),他关于所有理解的循环性质(Zirkelnatur)(14)Hans 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3.A.1975.和与之相关的前理解(Vorverständnis)(15)“诠释学的理解是根据已经理解的文本的知识对文本进行的解释,它从已经完成的形成过程层面到达新的形成过程,它是与已经完成的社会化相联系的一个新的社会化部分。”Josef Esser, Vorverstä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1970, S.137.的学说,使得方法论者们重新考虑并修正了他们先前所持的立场。
特别是,在这些新认识的印象下,必须放弃“解释有唯一正确的结论”的想法。(16)对于有义务统一适用法律的最高法院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这一点可以在最近的判决中一再得到证明: Vgl.z.B.BGE 95 I 40.今天,人们意识到,只有通过精确定义的概念,才有可能进行逻辑的、完全不涉及价值评价的涵摄。(17)考夫曼赞同,即使有“完全和明确定义的概念”,也无法避免循环推理,因为第二个先决条件只是要提出真理已被证明的断言,而这个断言的先决条件是“真理的证明必须得到论据的支持,而论据也要被证明是真实的......必须无休止地追查下去”,不可能得到满足。Arthur Kaufmann, Über den Zirkelschluss in der Rechtsfindung in Festschrift für Wilhelm Gallas(1973), 15.然而,在法律语言中缺乏完全清晰和全面的定义,这一事实可以用无数的例子轻易地证明。即使是那些乍看之下毫不含糊的词语,比如,“妇女”一词,也会让法学家面临非常不同的概念内容。如果不是这样,瑞士立法者就不会觉得有必要在《刑法典》第110条中指出:“妇女是指任何年满16岁的女性”。然而,仅凭年龄并不能捕捉到一个妇女的所有特征。这个问题无法通过逻辑涵摄来解决。在适用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时,法官必须做出价值判断,而不是从大前提和小前提中推导出结论。考夫曼的这句中肯的话,“作为涵摄自动售货机的法官应该被扔进法律史的废物间”(18)Freirechtsbewegung-lebendig oder tot-ein Beitrag zur Rechtstheorie und Methodenlehre in Rechtsphilosophie im Wandel, 1972, S.268.,应该得到毫无保留的赞同。(19)法官的任务当然不会因此变得更容易——相反;叔本华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健康的人完全没有得出错误结论的危险,但非常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有很多,但认真得出的错误结论却非常少。”
然后,现代诠释学表明,每个文本解释行为不仅包含接受性活动,而且还或多或少包含生产性活动。(20)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4.A.1979, S.231.但是,生产性活动意味着要从自己的源泉中取材,植入自己的想法,做出自己的价值评价。制定法不再是法律景观中不可动摇的古怪岩石,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综合体,始终处于变化之中,由一个文本、在其中获得表达的想法以及随着时间推移通过创造性续造而被纳入其中的想法组成。
如果人们承认,法官的每一次法发现活动或多或少都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那么人们也必须放弃解释和填补漏洞之间的根本区别。(21)Josef Esser, Vorverstä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1970, S.175; Konrad Redeker, Legitimation und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etzung in NJW 1972, 409.因此,如果也处于一个低级的、受制定法文本强烈约束的阶段,那么制定法解释的方法程序与传统方法论对漏洞确定和漏洞填补所要求的程序正好并无不同。(22)Karl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4.A.1979, S.349.“法官的每一次法发现活动”——无论是在法律之内还是在法律之外——“都在规范的当前化和具体化中包含着法律续造”。(23)Hans-Peter Schneider, Richterrecht, Gesetzesrecht und Verfassungsrecht, 1969, S.26; vgl.auch Arthur Meier-Hayoz, Privatrechtswissenschaft und Rechtsfortbildung in ZSR NF 78 I, 118.
只有这些新近的诠释学知识——顺便说一下,它并不声称为法律适用建立普遍适用的规则,而只是询问我们以何种方式理解文本,(24)René Rhinow, Rechtsetzung und Methodik, 1979, S.145; Roger Zäch, Tendenzen der juristischen Auslegungslehre in ZSR NF 96 I, 321.既不能取代也不想取代传统的方法论——才决定性地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官仅仅是规范的执行者从而必然具有非政治性”这项“天真的自我认知”(Ballerstedt)。(25)Konrad Redeker, Bild und Selbstverständnis des Juristen heute, 1970, S.15.由于法官在“解释”的时候就已经或多或少具有创造性,而不是在“填补漏洞”的时候才具有创造性,人们可以同意雷德克尔(Redeker)的说法:“法律创造”——长期以来——“是司法的本质内容,每一次法律创造都是政治”,(26)Konrad Redeker, Bild und Selbstverständnis des Juristen heute, 1970, S.8; gl.M.René Rhinow, Rechtsetzung und Methodik, 1979, S.165.政治被理解为具有一惯性的、目标明确的、致力于创造、维护或改变社会秩序的、贯彻自己的想法并反对其他利益的社会行为。因此,法律适用不是对个案的塑造,而作为对法律秩序的塑造,(27)鲍尔说,法官不再对“谁有权利”作出判决,而是对“法律将是怎么样的”作出判决: Fritz Baur, Sozialer Ausgleich und Richterspruch JZ 1957, S.195.具有法政策的特征,成了社会政策。(28)Konrad Redeker, Bild und Selbstverständnis des Juristen heute, 1970, S.12; vgl.auch Josef Esser, Vorverständnis und Methodenwahl in der Rechtsfindung, 1970, S.175.
“慢性毒药”因此最终生效了吗?现在必须最终告别三权分立的理念吗?
是,也不是。肯定被放弃的是一个已经上升为信仰的信条,它想把绝对不同的职能分配给权力承担者。而剩下的将是一个可变的制衡体系,即相互制约和节制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任务不再是把权力相互划分开来,而是保护公民不受威力无比的国家权力的侵害。(29)Rolf Wank,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1978, S.90; vgl.zum Problem der Gewaltenvermischung auch Walter Haller, Supreme Court und Politik in den USA, 1972, S.322.
各系统组件的功能差异只能渐次掌握。但恰恰是这种渐次变化,已经不能用传统的术语——从法律方面论证的法官和从政治方面考量的立法者——来表示。法官和立法者都在行使政治职能,都在为塑造社会秩序而一惯地、目标明确地工作,通常而言,立法者在更大的框架内工作,法官在更小的框架内工作。
但是,如何更详细地描述这两个政治权力承担者的权限之间的界限?特别是,如何说明对法官的法政策施加的限制?
在下一部分,将尝试使上述界限看起来更加明显,并认识法官职能当中固有的造法限制。
三、法政策的战略方面和战术方面的区分
出发点是瑞士联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判决的一个案件。(30)BGE 106 IV 227.《瑞士麻醉品法》(Das Schweizerische Betäubungsmittelgesetz, SR 812.121)以详细的规定禁止生产和销售毒品,包括大麻制品。违反该法的行为将遭受刑罚。有严重情节的,犯罪者不是被判处三年以下的监禁或罚金,而是被判处一年以上二十年以下的监禁,并处一百万瑞士法郎以下的罚金。(31)Art.19 Ziff.1 letzter Absatz BetmG.
“特别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罪行涉及一定数量的麻醉品,可能危及许多人的健康,则存在严重情节”。(32)Art.19 Ziff.2 lit.a BetmG.
在一个具体案例中,符合该条要求的大麻数量已经被转给了大量买家,但巴塞兰州高级法院仍然拒绝适用这一量刑规范。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是,该制定法规范的措辞要求对健康构成威胁,但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结果,这种情况在大麻中——与海洛因相反——几乎没有发生。(33)Gemeinsames Gutachten von Lichtenhagen, Kielholz und Ladewig, auszugsweise abgedruckt in SJZ, 1980, 100 ff.如果立法者在颁布《麻醉品法》时已经意识到大麻毒品的潜在危害比其他毒品小得多,那么它可能就不会把贩卖这种麻醉品归到第19条第2款意义上的严重情节。因此,法院继续说,该法今后的适用方式应该是,只有贩卖实际危及人们健康的毒品才适用这个量刑规范。(34)Vgl.dazu auch den Beitrag von Guido Jenny, Vom falsch verstandenen Willen des(historischen)Gesetzgebers.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采用了不同的观点。它严格遵守立法者确立的秩序,不管潜在的危害有多小,都把大麻等同于“重”毒品。该法院在1980年6月6日的判决中指出:“但是,如果立法机构本身已经根据当时的科学知识状况对大麻物质的依赖性效果做出了判断,从而对经营这种物质对人类健康的危害做出了判断,那么法官就不应该根据自己的认识作出不同的回答……如果根据目前的科学知识,这种危害并不存在,那么将由立法者来给出相应的结论。”(35)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立法现实的变化需要对法秩序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工作往往由法官进行,这是正确的。然而,关于未改变的事实的科学知识的改变往往与事实本身的改变有同样的效果。自然科学的进步往往促使法官进行法律续造,并为其提供理由。只要想想儿童法中的亲子关系问题就知道了。通过生物人类学鉴定可以得出直接的亲子关系证明,这促使法院违背《瑞士民法典》第315条的措辞,即使在母亲“多次性交”的情况下也允许提起亲子关系诉讼。医学进步解决了立法者设法解决的冲突。Vgl.zur grundsätzlichen Zulassung des biologisch-anthropologischen Gutachtens: BGE 87 II 74; und zur Rechtsprechungsänderung bezüglich der Mehrverkehrseinrede: BGE 89 II 275 ff.法官不必审查,“一种药物的潜在危险是否很大,危害性是否很高,是否明显。《瑞士麻醉品法》第19条第2款a项并不以这样的危害为条件,立法者也有意不对轻毒品和重毒品进行区分。”(36)BGE 106 IV 231.
如何判断联邦最高法院的这种克制行为?联邦最高法院是否不合理地推卸了其续造法律的责任?还是说它正确地认识到了其法政策权限的界限?
让我们从联邦最高法院在1957年不得不判决的另一个案件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37)BGE 83 I 173 ff.沃州(Waadtland)的州宪法(与其他各州的基本法类似)第23条规定,居住在该州的所有20岁以上的瑞士公民都享有积极的公民权,即在州内事务中的投票权和选举权。(38)“积极公民是指所有年满20岁的瑞士公民,他们在该州定居或居住了三个月,并且没有在联邦的任何其他地区行使其政治权利”(Sont citoyens actifs tous les Suisses de vingt ans révolus, établis ou en séjour dans le canton depuis trois mois et n’exerçant pas leurs droits politiques dans quelque autre Etat de la Confédération)。一些勇敢的沃州妇女根据对这一规定的适用时解释(geltungszeitliche Interpretation),要求该州当局将她们登记在选举登记册上。她们认为,不赋予妇女政治权利与《联邦宪法》(第4条)中的权利平等原则相矛盾,也不再符合全世界对妇女政治权利的认可。为了支持这一观点,有人进一步争辩说,州宪法没有明确禁止妇女参与选举和投票。为了批准她们的请求,法律适用当局只需在也包括瑞士妇女的意义上理解“Suisses”一词即可——这也是经常发生的,甚至在同一部宪法的其他几个地方,对“Suisse”一词也是这么理解的。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并不同意下级法院所要求的法律续造。它坚持这项宪法安排的历史意义——因此也坚持以前对“Suisses”一词的理解——并将原告们引向宪法立法的道路。(39)随后,必要的宪法修正案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出台:早在1959年2月1日,沃州的宪法就被修改,妇女现在也享有积极公民权。《沃州宪法》第23条(Art.23, KV von Waadt):“所有的瑞士公民都是积极公民,包括男性和女性……”(Sont citoyens actifs tous les Suisses, hommes et femmes,...)。
这里比“大麻判决”更清楚,法官为什么要躲在立法者后面。20世纪50年代,瑞士公众对妇女投票权仍有很大分歧。1959年,联邦一级拒绝赋予妇女政治权利。(40)Vgl.jedoch die Verfassungsänderung im Kanton Waadt.直到1971年,瑞士全国才开始让妇女在联邦事务中享有投票权和选举权。(41)在阿彭策尔内尔霍登州(Appenzell Innerrhoden)(参见该州宪法第16条)和奥塞尔霍登州(Ausserrhoden)(参见该州宪法第19条),妇女仍然被排除在州级事务的选举和投票之外。在奥塞尔霍登州,她们至少从1972年起就有权在市政事务中投票(该州宪法第19条第3款)。因此,可以理解,1957年我们的最高法官不想通过重新解释宪法条款来回答这样一个在政治上这么有争议的问题。
今天,药物滥用的问题在政治上虽然不那么具有爆炸性,但也有争议。特别是,大麻消费的刑罚化处于批评的射程内。关于大麻药物的潜在危害仍然有很大分歧,尽管最近的研究倾向于“支持”这种成瘾物质;甚至认为相比之下饮酒危害更大。(42)考虑到医学上的模糊情况,法院采取的立场可能会有多大的分歧,通过比较已经引用的巴塞尔州高等法院的判决和巴塞尔州上诉法院的一个判决也可以看出:虽然两个法院都拿到了相同的专家意见,但上诉法院还是认为大麻药物构成了健康危害,在本案中适用该量刑情节(《麻醉品法》第19条第2款)是合理的。Urteil vom 14.2.1979, BJM 1980, 155 ff.
为了解决眼前的冲突,必须作出根本性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不可能建立在相关圈子和公众的广泛共识之上。需要讨论的是——在这里有我对术语的贡献——“战略”问题:战略被理解为政治的一部分,其特点是长期的基本规划和包含全部基本因素的全面准备。与“政治的”这个模棱两可、有些无色的词相比,“战略的”一词可以用来更准确地描述立法者的活动;特别是,它可以用来生动地描述法官的活动界限,因为法官在其法律创造职权的框架内也会采取政治行动。因为被赋予了法政策战略方面的权力,立法机关必须决定根本性问题,制定计划,为司法机关指明大方向。
如何理想地塑造立法者和法官之间的互动,可以用体育界的一个比喻来生动地说明:以一支足球队为例。教练作为球队的战略家,必须在比赛开始前告知球员他的目标和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简而言之:告知要采取的比赛战略。每个球员都必须知道比赛是以防守为主还是以进攻为主,是比赛一开始时就用尽全力还是在比赛快结束时才这样。如果没有这些基本指示,即使是最好的团队也很难将朝着一条统一的路线努力。如果所采取的战略不再适合当前的比赛状况,教练有机会也有责任不时修改计划或制定新的计划。然而,为此,他需要依靠比赛的中断和休息时间;他对球没有直接影响。立法者和法官所处的情况跟这非常相似。法官们时刻关注着球(即关注个案),他们必须了解立法者的战略,这样才能将其法律续造引向正确的方向。立法者,就像教练一样,必须远离比赛行为的细节,把踢球的工作交给球员。用哪只脚踢球,是用头还是用胸部停球,是直接推进还是在其他球员的帮助下推进,对于这些问题,只有控球的球员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他更适合迅速采取行动,利用一时的优势,为灾难性的发展踩下刹车。对于球员的这些行为,我想用“战术”这个词来与教练的战略形成对比。
法官的活动必须在这样一个战术框架内进行。他必须在立法机构划定的战略范围内,在小的、相对无争议的、或多或少能达成共识的领域内推行法政策。尤其是出于以下原因,他完全不能胜任战略层面的政治决策。这些原因部分与个人有关,部分与制度有关。
1.除了本身中立且任何法发现都离不开的前理解之外,个人成见和无法说明理由的主体观念在案件由独任法官和较小的审判团审理的情况下可能会流入法发现过程。其发生的可能性,比在参与人员更多的国会中更大。法官个人的个性与参与立法的人的个性相比,对于规范的建立而言无疑具有完全不同的分量。如果一个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团中有两名法官相当保守,那么其保守性在判决中的反映,将比这两名法官是议员的情况下在法案中的反映更强烈。
2.法官的法政策意思形成(rechtspolitsche Willensbildung)肯定是在一个非常有欠缺的基础上发生。他在很大程度上无法让很多人参与制定新法的准备工作,例如,任命特别委员会或咨询专家。“他被推到了立法者的位置上,而立法者的辅助工具却不能为他所用,他的判决也不能像制定法那样经过类似的形成过程。”(43)Fritz Baur, Sozialer Ausgleich und Richterspruch JZ 1957, S.196; vgl.auch Peter Noll, Gesetzgebungslehre, 1973, S.27.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讨论,是制定法形成过程中的典型做法,其目的是为了全面了解生活现实,了解需要调和的利益冲突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可想到的法律解决方案的实践后果,但法官无法做到。这大大限制了他处理法政策问题的能力,仅此一点,他就必须谨慎行事。
3.其活动的案件相关性对法官施加了进一步的限制。总是只有一个具体的案件被提交给他;他必须解决这个案件;对于这个他只碰到一次的具体案件,他必须作出一个合理的判决。但“合理”的意思是:以规则为依据,按一个体系进行归整,以原则为导向。法官必须将案件分解成典型的组成部分,并解决它,以便可以以同样的理由来解决其他类似的案件。然而,他的努力必须仅限于确立该案所要求的规则,作为裁判理由。(44)对于经常发生的超越具体案件给出扩展意见的迫切需求,法官有时候通过如下方式为其寻找正当理由:在判决理由中加入附带意见——当前案件的论证不直接需要的附带考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可以以不同的确定性指出将来进一步进行法律续造的可能性:从单纯暗示法院将在第一次获得机会时考虑或重新考虑一个问题,到明确承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建议。然而,不能忽视这种善意的额外考虑的危险性。即使只是顺便提到要重新考虑一个问题,也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造成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参考联邦最高法院在BGE 84 II 363 f.中提出的问题,即迄今为止被视为抽象法律行为的债权让与(Abtretung)是否不应该被赋予要因性质——就像物权法上的处分行为一样。二十多年来,联邦最高法院一直在等待机会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首先意味着,法官不能从其以问题为导向的个案观点出发,为全部生活领域制定全面的规则。根据“患病的”情形作出的考虑,决不能以偏概全,使所有“健康的”情形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困难的案件造就了糟糕的法律”(45)Rolf Wank,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1978, S.184.,对非典型案件公平和正确的事情,对典型案件可能是最大的不公正。
4.将法官的法律续造限定在战术性方面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判决的溯及力。虽然有溯及力的法律本身并没有被根本排除;但是,只有在非常具体的、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才允许。(46)Für eine Zusammenstellung dieser Voraussetzungen vgl.Max Imboden/René Rhinow, Schweizerische Verwaltungsrechtsprechung, Bd.I: Allgemeiner Teil, 1976, S.104 ff.这个不溯及既往原则是为了保护公民对“因已完成的事实而产生的法律状况会继续存在”的信赖。相反,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任何规则可以减轻具有法律续造性质的判决的追溯性。(47)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建议有很多;当然,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建议能实施。Vgl.die Zusammenstellung bei Hans-Wolfgang Arndt, Probleme rückwirkender Rechtsprechungsänderung, 1974.在作出判决之前,对于法官将遵从一部制定法的众多解释中的哪一种,或多或少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法官不是根据有关事实发生时已经存在的规则来对案件进行判决,而是根据在裁判过程中才产生的规范来进行判决。在对一个具体案件进行判决时,法官会制定新的法律,并将其适用于该法律制定前已完成的事实。这应促使法官给予特别考虑,尤其是这种情况:受判决约束的人,因为合理地信赖法官的法律续造的一项可能的变体,而进行了安排。(48)鲍尔也赞同,在判决修改问题上,法官应当持克制态度: Fritz Baur, Richteramt und Rechtseinheit i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Weitnauer(1980), 254 f.为了不让公民遭受不可预见的判决修改风险,杜登(Duden)建议取消“《德国民事诉讼法》(DZPO)第91条明显的意外责任(Zufallshaftung)”,因为它“从解释上看,不是误判现行法律的风险,而是误判法官的法律续造倾向的风险”。Konrad Duden in Rudolf Pehle/Walter Stimpel, Richterliche Rechtsfortbildung, 1969, S.33.当然需要考虑,国家是否至少应该承担因当事人无法预计的续造性判决所引起的诉讼费用。
5.然而,我认为将法官造法限制在战术领域的核心原因在于,他——与立法者不同——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民主锚定。如果法官是由政府任命的——例如在德国或美国——他们只是间接地在民主上获得了合法性。他们与人民的联系被多个缓冲层打断了。因此,法官“制定法律的权限,特别是当它们延伸到社会塑造的领域的时候,只能被理解为临时性的,并应限制性地运用。”(49)Jörn Ipsen, Richterrecht und Verfassung, 1975, S.204.关于真正的利益冲突,没有同质化的意见,没有共识,必须进行公开的政治争论,而且往往通过政治妥协的方式解决。这在司法程序中是被排除的。(50)Robert Fischer, Die Weiterbildung des Rechts durch die Rechtsprechung, 1971, S.32; Rudolf Pehle/Walter Stimpel, Richterliche Rechtsfortbildung, 1969, S.3.
此外,法官的独立性限制了法律适用者的政治责任。然而,如果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逃避错误判决的后果,那么他从事法政策活动的权限就必须继续限制在战术领域内。(51)Vgl.auch Rolf Wank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1978, S.214.考虑到自己可利用的微弱手段,法官应该不会去试图回答当今社会的争议性问题。相反,他的工作领域是相对没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大部分人中可以达成共识,或者如维亚克尔所说,“普遍可利用并接受的共同真理。”(52)Franz Wieacker, Über strengere und unstrenge Verfahren der Rechtsfindung in Festschrift für Werner Weber(1974), S.437.
四、为战略制定者和战术制定者带来的后果
所列举的五个原因——1.成见的强烈影响,2.技术和人员配备的不足,3.以问题为导向的视野,4.判决的溯及力,5.不充分的民主锚定——将法官的造法活动限制在战术领域,也给立法者带来了后果。
法官和立法者在其作为规范制定者的职能中,负责在环境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变化中塑造法秩序,使其也能完成新任务。在实现这个共同目标的道路上,立法战略和司法战术必须共同发挥作用。然而,今天经常没有重视这个重点——立法机构的战略,司法机构的战术。
这一告诫特别针对立法者:要保持对战略责任的充分认识,不要过度地转向战术问题。而立法机构的日常工作是令人失望的。有人在谈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情况时说,议程上不再是“关于人类真正关切的基本问题,而是用于满足具体需求的法律”。(53)Rolf Wank, Grenzen richterlicher Rechtsfortbildung, 1978, S.119.雷德克尔(Redeker)甚至声称,关于具体措施和具体情形的制定法已经成了规范的主要类型。(54)Konrad Redeker, Bild und Selbstverständnis des Juristen heute, 1970, S.10.
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在战术领域进行立法,或者让法官搞不清其战略,在这两种情况下,立法者都是在逃避其战略责任。这不仅发生在它完全忽略根本性规范的情形中,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在如下情形中:它通过空白规范和一般条款等所谓的开放式立法,将法政策具体化的核心任务转移给法官。(55)Uwe Diederichsen, Die Flucht des Gesetzgebers aus der politischen Verantwortung im Zivilrecht, 1974, S.5; Franz Wieacker, Gesetz und Richterkunst, Juristische Studiengesellschaft Karlsruhe, 1958, S.5; Fritz Baur, Richteramt und Rechtseinheit i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Weitnauer(1980), S.256; Peter Noll, Gesetzgebungslehre, 1973, S.158 f.“立法机构的不表态往往使法院承担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利益之争转移到了司法审议室,并使判决暴露在败诉方利益集团的攻击之下。”(56)Rudolf Pehle/Walter Stimpel, Richterliche Rechtsfortbildung, 1969, S.3.
法官应该把自己从仅仅是规范的适用者的想法中解放出来,公开承认自己作为规范制定者的职能,承认其个人的前理解,并有意识地让它流入法发现过程。(57)然而,由不完善的立法造成的战略指导方针的缺失,使得“法官的职位迄今为止更加困难和压迫。有一种危险是,法官将被过度消耗,他的灵魂将负担过重;这可能导致他以消耗内在力量为代价进行参与,也可能会导致他产生怀疑的冷漠”。Fritz Baur, Sozialer Ausgleich und Richterspruch JZ 1957, S.196.在清楚地认识到为他设定的界限和潜在危险的情况下,他必须将法律创制的活动限制在战术领域,而将超出这一范围的战略留给立法者。(58)法官不能利用其独立性充当革命者或者改革者: Fritz Baur, Richteramt und Rechtseinheit in Festschrift für Hermann Weitnauer(1980), S.258.
法官应该努力遵守这一界限,即使他并不总是能够像美国法院那样明确、毫不含糊和果断地做到这一点。美国法院应该在越南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上表明立场,因为越南战争从未根据国际法宣战。(59)Vgl.dazu den von Walter Haller, Supreme Court und Politik in den USA, 1972, S.186 angeführten Entscheid Mora v.Mc Namara.在明智的自我克制下,他们拒绝涉足这个有争议的战略问题,因此也拒绝离开法律战术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