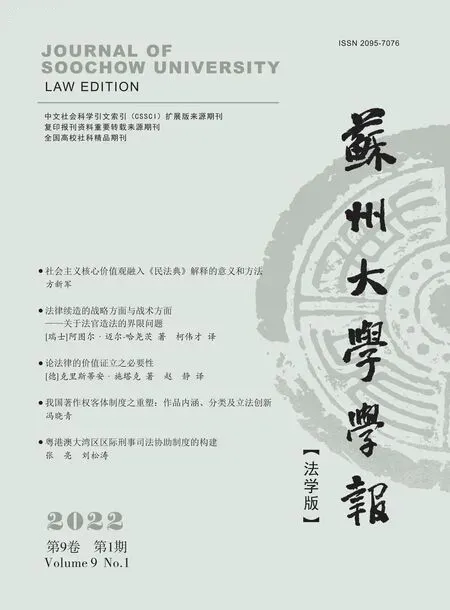著作权法“通知-必要措施”义务的比较经验与本土特色
熊 琦
一、问题的提出
以“通知-删除”义务为核心的避风港规则在20世纪末进入美国版权法后,迅速成为其他国家互联网平台知识产权侵权责任配置的立法蓝本,也为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变革提供了制度基础。(1)See R.A.Ree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SP Safe Harbors and the Ordinary Rules of Copyright Liability, 32 Colum.J.L.& Arts 427(2008).从产生至今,世界上范式著作权制度中设定的避风港规则目标,一直是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免责事由,在满足法定义务之后即可不承担侵权责任,以此激励互联网产业的发展。(2)Megan Smallen, Copyright Owners Take on the World(Wide Web): A Proposal to Amend the DMCA Notice and Takedown Procedures, 46 Sw.L.Rev.169, 169-70(2016).随着互联网传播技术的迭代,加上各国互联网产业和传统产业关系的差异因时间的积累而形成了各自特色,因而对此规则产生了不同的变革需求。(3)2019年6月7日,欧盟通过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改革指令》中的第17条,就跳出了2000年《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的避风港规则,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更为高效的必要措施和更为严格的注意义务,引发了诸多争议。美国版权办公室则于2020年5月21日发布了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的调研报告,系统梳理了DMCA颁布20余年来避风港规则体系的得失,并积极为下一步立法调整做准备。欧盟立法和美国报告的具体文本分别参见Directive(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U.S.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May 21, 2020).我国当前处于一个互联网产业主导传统产业,而非互联网产业和传统产业彼此制衡的产业阶段。因此,随着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的变革,历年立法、修法以及诸多司法解释和判例已经逐渐脱离了借鉴对象构建“避风港”免责条款的立法目标,转而成为形塑归责原则的法源基础,并形成了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必要措施”的转型轨迹。
然而,这种建立在免责规则基础上的归责原则,在司法适用中却出现了种种难以预期的问题。第一,必要措施的范畴尚不明确。从“删除”到“必要措施”的改变,旨在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的义务。但一直以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都是与其网络服务的性质相关联,当现行规则已经无法全面涵盖今天多元化的网络服务性质,且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服务类型早已超越单一的服务性质时,必要措施如何认定,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出现了不一致之处,并对互联网产业商业模式预期产生了消极影响。第二,必要措施与转通知的关系不明确。必要措施乃是在接到合格通知后产生的结果。在《民法典》和《电子商务法》都已经将“通知和反通知”作为法定程序后,如何在案件中认识反通知和必要措施的关系,同样会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运营成本和商业模式风险,进而决定互联网产业的未来。
因此,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体系业已形成的立法基础上,下一步研究应该更多是从法教义学的角度界定必要措施的范畴及其与通知规则的关系。一方面梳理和协调因产生时间和来源不同而导致分立的法源中关于通知、反通知和必要措施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由裁量的标准上充分考虑平台自治的空间和行业标准,避免出现《电子商务法》在反通知后“等待期”期间设定上过于僵化的判断。同时不可忽略的是,作为“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发源地,域外对该制度在概念原意的回溯和实践进展的反思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鉴于我国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变革都尚未脱离“避风港规则”体系,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近年来都在反思“避风港规则”自入法以来于司法实践中总结的丰富经验,而且欧盟已经完成了立法转化,正在逐步落实于成员国的国内法中。研究其中展现的历史经验和在借鉴中被误读的规则解释,有助于解决现阶段“避风港规则”的本土难题。但反过来看,我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域外经验又存在水土不服之处,特别是对于国内讨论较多的是否以及如何增设过滤义务等问题,都需要在充分分析和比较法制及产业基础的前提下结合本土实际加以甄别。
二、“通知-必要措施”义务本土规则体系的形成和争议
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行为的著作权规制,我国立法和司法都经历了一个从全面借鉴到有限自立的过程,并形成了极具本土特色的制度体系。但由于问题应对的及时性需求和立法周期的长期性需要之间难以协调,实践中只能依靠大量的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来解决问题。但在立法完成修改后,其含义是否与上述法律文本一致,在适用范围和位阶上如何彼此衔接,都需要运用法教义学工具去加以梳理和整合。
(一)制度模仿阶段及其问题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版权产业就与全球其他国家一样同步遭遇互联网产业的冲击。但与版权产业和制度较为发达的国家不同,我国当时的版权产业和制度尚处初级阶段,刚颁布不久的著作权法中并无任何针对网络传播的权利类型或其他规定,实践中涉及作品创作和传播的主体有的尚未完成市场化改制,缺乏为经济利益维权的诱因,而刚起步的民营产业主体则在面对网络侵权时缺少基本的维权经验和能力,上述问题的叠加,直接导致传统版权产业在与互联网刚接触时即遭到免费复制风潮的打击。
鉴于网络侵权的紧迫性,我国司法和行政机关在著作权法尚未完成第一次修改的情况下率先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问题进行了回应。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先于立法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5条规定,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经著作权人提出确有证据的侵权警告后,仍不采取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以消除侵权后果的,人民法院应当追究其与网络用户的共同侵权责任。虽然该司法解释现已失效,但仍然可以从该文本的表述中发现,我国司法机关是从“归责”而非“免责”的角度来解释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通知-删除”规则。究其原因,在于设定“免责”须以确立“归责”为前提,而我国当时的立法文本中并无任何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归责问题的规定。立法层面既无“归责”规定,司法层面就无“免责”根基,因此只能暂且以司法解释包办归责条款,也奠定了我国“避风港”规则特殊的制度安排。但即使如此,限于司法解释的定位和当时我国理论层面的有限积累,该条款仅能提供一个原则性规定,不但范围上仅限于“提供内容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而且必要措施只列举了移除一项,在当时的司法审判中起到的作用较为有限。
2001年第一次修改后的《著作权法》虽然加入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但诸多涉及直接和间接侵犯该项权利的规定仍然欠缺,实践中起到指导司法裁判和行政保护的,仍然是相关行政规章。2006年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信网权条例”)通过移植美国版权法在DMCA通过后加入的“避风港规则”,首次较为全面地形成了“通知-删除”的规则体系,在将网络服务类型具体细化为“自动接入和传输、自动存储、信息存储、搜索和链接服务”四种的基础上,根据网络服务的类型来设定不同的义务范围,其中,针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和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适用的就是“通知-删除”规则。在对侵权行为不存在明知或应知的前提下,只要上述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采取了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就不承担侵权责任。“信网权条例”作为国内首次详细规定“通知-删除”规则的法律文本,乃是直接借鉴美国避风港规则的结果,使我国司法机关在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责任时有法可依,也确立了本土“通知-删除”规则的基础。
在此阶段,我国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避风港规则乃是直接借鉴于美国1998年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DMCA)。这种拿来主义,在当时我国缺乏产业基础和理论积累的情况下帮助我们迅速构建了一个基本的制度框架,使得当时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审判能够在域外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应对本土案例,但这种快速移植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新的问题。首先,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化不足。“信网权条例”中基于借鉴DMCA所规定的四种网络服务类型,在互联网商业模式飞速发展的今天已无法满足实践需求。不断出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早已超出制度设计的范畴。(4)在“微信小程序案”和“阿里云租赁案”等案件中,终审法院皆认为小程序和云租赁服务属于新型网络服务。参见杭州刀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公司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终4268号民事判决书;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其次,免责抑或归责定位不明。当时尚有效力的“计算机网络著作权司法解释”(2000)和至今仍作为著作权法关键补充的“信网权条例”(2006),对于同样的避风港规则,在表述上却存在差异,前者采取归责条款的安排,后者引入的则是免责条款,引发了司法认知上的争议。(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20—23条分别针对“自动接入和传输、自动存储、信息存储、搜索和链接服务”四种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了免责规定。
(二)制度生成阶段及其问题
在引入避风港条款的基础上,后来的《侵权责任法》(2009)、《电子商务法》(2018)和《民法典》“侵权责任编”(2020),都是在此基础上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共同侵权责任加以了细化和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规则的最终落实,体现在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中。被视为“互联网专条”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仍然是将未采取必要措施与对损害扩大的部分承担侵权责任相关联,这意味着作为保护私权基本法的民法最终选择了归责条款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避风港规则的法源设定。
针对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和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迭代,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案件中暴露的问题,《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将“通知-删除”规则加以扩张与细化,升级为“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具体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吸收《电子商务法》的经验,将“通知”细化为“通知-转通知-反通知”。这一细化的意义,一方面说明立法者仍然坚守着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中立原则,没有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侵权认定方面的专业判断,而是仅仅需要在判断通知满足形式要件后转通知给相关网络用户。如果相关网络用户能够提供初步证据证明不存在侵权行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可以再将该声明转送发出通知的权利人,而无须自行对侵权事实加以判断。第二,为避免虚假和恶意通知被作为非法损害其他网络用户利益的手段,“侵权责任编”要求权利人须承担因发出错误通知而给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本项规则所针对的,就是以电子商务领域为代表的通过虚假和恶意通知打击合法经营者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虽然在多数情况下因为缺乏证据而没有对其所针对的合法经营者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但在特定时期(如销售旺季和发行期),即使是暂时的删除和屏蔽等措施,也会对经营者造成重大损失。第三,“侵权责任编”将“必要措施”作为所有网络服务提供者都需遵循的义务,原来“信网权条例”中以穷尽列举方式呈现的“删除作品或断开链接”升级为不完全列举式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
本阶段立法和司法的特点,在于我国立法和司法开始根据本土产业的特点和发展来形成自己的规则体系。从归责与免责的规则定位来看,自2012年最高院颁布《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后,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就开始以归责条款来构建,“信网权条例”借鉴的免责条款在立法和司法上都已不再延续。围绕归责条款的司法审判,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种判决中对“必要措施”范围的自由裁量。有法院认为,必要措施的认定,应结合侵权场景和行业特点,秉持审慎、合理之原则,实现权利保护、行业发展与网络用户利益的平衡。(6)参见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维系这种平衡仍然面临着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从对我国《民法典》第1195条的文义解释出发,转通知和必要措施是相对独立的程序。(7)《民法典》第1195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将该通知转送相关网络用户,并根据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和服务类型采取必要措施。文义上表明转通知和必要措施是并列且彼此独立的义务。但实践中有法院在必要措施的认定上又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为必要措施条款在调整为不完全列举后的范围和位阶问题。必要措施的范围是否扩大,甚至是否从事后规则上升为事前规则,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网络服务提供者商业模式的成本高低。随着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管理能力的提高,法院在突破列举内容上存在着分歧,但主流意见是必要措施不应仅限于在侵权发生之后断开链接。(8)参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155号民事判决书。据统计,大量法院将“定位清除”视为必要措施的组成部分,(9)参见李扬、陈铄:《“通知删除”规则的再检讨》,载《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第27页。甚至有法院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有效措施过滤和拦截用户上传新的侵权视频和视频片断”。(10)2021年,重庆一中院在(2021)渝01行保1号诉前禁令中,责令微播视界公司除必须立即删除抖音APP上用户名为“忆三漫剪”等五个帐号中所有侵害《斗罗大陆》动漫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频之外,还应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过滤和拦截用户上传和传播侵害《斗罗大陆》动漫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视频。著作权主管部门在相关文件中,也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一定条件下应该运用有效技术措施对侵权作品加以屏蔽和移除。(11)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2016)第10条,其中指出“网盘服务者应当建立必要管理机制,运用有效技术措施,主动屏蔽、移除侵权作品,防止用户违法上传、存储并分享他人作品。”反之,也有法院坚持必要措施的认定需坚持审慎合理原则和比例原则,实现权利保护、行业发展与网络用户利益的平衡。(12)相关判决参见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天猫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然而何谓“审慎合理”,如何在个案中实现“比例原则”,尚无清晰的认定标准。
二为必要措施与通知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信网权条例”还是《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都明确规定了“转通知”,但对转通知和必要措施的关系却存在不同解读。在早期的“信网权条例”中,立法者在第15条采用了“删除后同时将通知转送”的制度安排,把“转通知”作为“通知-删除”规则中与删除义务相继存在的非独立性程序,并对必要措施的类别进行封闭式列举。相比之下,《民法典》第1195条第2款则将“转通知”义务调整到了必要措施之前,并将必要措施条款改为开放式列举。这种“先删除后转通知”到“先转通知再必要措施”的转换,是否在解释上进行同步调整,也无明确的结论。
三、“通知-必要措施”义务的比较法经验回溯
从当下回看历史,我们当然很容易批评“通知-必要措施”义务所借鉴的域外立法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该借鉴对象是在版权产业和互联网产业皆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并经历两类产业主体充分博弈后的立法产物。虽然各方皆有不满,但毕竟在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各取所需,并广为世界各国所借鉴。我国立法虽然可以通过移植和借鉴快速构建规范体系,但毕竟缺乏一个本土生成和博弈的过程,因此在对相关概念结合立法价值进行解释时,仍然需要回到比较法上去寻找“原意”,方能根据本土特殊的社会与产业情势来重塑规则。与此同时,无论是“通知-删除”规则的起源地美国还是欧盟,近年来对此制度的适用绩效和问题都有相当规模的反思。在互联网产业力量较为薄弱的欧洲,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规则已经在立法上得到体现,(13)Directive(EU)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美国版权办公室对“避风港规则”的全面回顾,也指出了其中效率低下和效果不足等实际问题。(14)Se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因此,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我们一方面可以通过梳理规则本源来正确理解相关概念的原意,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域外的制度反思来印证本土应对路径的可行性。
在对“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反思的过程中,需要首先关注的是规则产生和适用的不同产业背景。“避风港规则”之所以产生于美国,且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所效仿的制度,主要原因在于美国长期处于一种传统版权产业与新兴互联网产业实力相对平衡的背景下,经过两类主体之间博弈所制定的规则,能够最大限度满足双方的利益,协调彼此的矛盾。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同样由于历史和社会基础不同,一直呈现出传统版权产业强于互联网产业的状态,所以立法安排也更多体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义务的增加。上述两种制度取向如何为本土制度调适所借鉴,需要结合我国互联网产业全面主导版权产业的背景来鉴别。
(一)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平衡发展环境下的制度经验
源起于美国的“避风港规则”之所以成为各国应对网络服务提供者共同侵权责任的标准,主要原因在于其较为平衡地兼顾了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避风港规则的特点,即在于要求部分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通知-删除”义务来免除其侵权责任。“通知-删除”义务作为一项事后规则(ex-post rule),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有在得到具体通知的情况下,才须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侵权行为,而无须承担一般性的主动监管或过滤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直接干预网络用户的传播行为,仅发生在其知悉具体侵权行为存在的前提下。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DMCA中坚持这一规则的原因,在于当时作为新事物的民用互联网产业需要扶持,网络服务提供者对是否会因平台上的内容传播而担责深感忧虑。(15)DMCA尚在讨论过程中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相关诉讼中就提出过这一观点。See Zeran v.AOL, Inc., 129 F.3d 327, 335(4th Cir.1997).这种模式后来也为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The European E-commerce Directive)所继承。
然而,随着互联网产业的逐步强大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商业模式对传统版权产业的日趋蚕食,“避风港规则”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那些主流互联网平台因为拥有过大的影响力而被质疑问难。众多版权产业的主体认为,“避风港规则”已经落后于时代的进步,模糊的规则表述和过高的认定标准,使得“避风港规则”成为了侵权行为的掩体,网络服务提供者也因此丧失了打击侵权行为的动力。(16)代表性的批评意见可参见相关产业主体在国会立法听证上的发言。see Jeffrey Harleston et al.(Universal Music Grp.), Reply Comments Submitted in Response to Section 512 Study: Notice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3-9(Apr.1, 2016), https://www.regulations.gov/contentStreamer?documentId=COLC-2015-0013-90321&attachmentNumber=1&disposition=attachment&contentType=pdf; Jennifer L.Pariser(Motion Picture Ass’n of Am.), Reply Comments Submitted in Response to Request for Comments on U.S.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Study pp.3-5(Apr.1, 2016), https://www.regulations.gov/contentStreamer?documentId= COLC2015-0013-90285&attachmentNumber=1&disposition=attachment&contentType=pdf.2021年11月1日访问。更有学者认为,“通知-删除”规则将给版权所有者带来不成比例的负担,而司法机关却以一种限制性的方式解释“避风港”,从而削弱了处理网络侵权行为的能力。(17)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May 2020), p.65.从制度运行至今各方的反馈来看,美国作为一个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平衡发展的国家,其“避风港规则”的适用争议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DMCA将主要类别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纳入了“避风港规则”的范围内,使其免于高额的监管成本,而且实践中法院还在不断通过解释扩大法定类型的范围,特别是针对“提供储存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法院在很多时候扩大解释了四种被纳入避风港规则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求将新出现的网络服务类型纳入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范围。(18)Se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 p.91-94.但持反对观点者认为,法院的这种扩大解释,突破了立法者关于避风港规则的立法意图。有权利人指出,法院对于512(c)条款中存储和托管服务的适用,已经远远超出了立法者对此类服务的定位,并且把范围延伸到了储存空间服务提供者所同时提供的包括流媒体传播和内容下载等其他所有功能。同时,权利人还认为法院错误地把那些修改用户内容或使用算法向其他用户推送内容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纳入存储空间服务的门类下。(19)Se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 p.91-94.如此认定方式,使得新出现的网络服务类型,特别是和内容传播相关的网络服务类型,不断被归入了“避风港规则”的管辖之下,新兴网络服务提供者得以继续享受免责条款的庇护。
第二,DMCA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侵权行为存在的标准较高,使其避免陷入动辄承担共同侵权责任的境地,但随着互联网产业的不断进步,各界普遍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已经显著提高,仍以过去扶持互联网产业发展为目标的侵权认定标准已造成互联网产业与版权产业义务分配的不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仅凭对平台上存在侵权行为的一般性知晓,还不足以构成“知道”,只有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明确识别特定侵权行为的存在时,才能被视为符合“知道”要件的要求。(20)See Capitol Records, LLC v.Vimeo, LLC, 826 F.3d 78(2d Cir.2016).根据DMCA的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被排除在“避风港规则”之外必须是因为“实际了解”其服务上的材料或活动是侵权的,并且“不知晓明显存在侵权活动的事实或情况”。(21)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 p.118-19.这导致对侵权行为的发现只能更多依靠权利人来完成,并耗费其大量的经济成本,但实际效果却不佳。针对侵权行为的控制陷入了“打地鼠”(the “Whack-a-mole” problem)的困境中,网络用户重复侵权现象难以控制,被删除后的作品频频再次出现。(22)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 p.1.
尽管如此,美国法院仍然没有放弃基于传统“避风港规则”的认定标准,也并未降低通知程序中著作权人举证义务的标准。法院坚持既有标准的原因,主要在于实证研究数据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的大量通知中,其实存在很高比例的错误。(23)有数据统计,实践中长年有接近百分之三十的通知中存在错误,由此消耗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大量的成本去应对。See Jennifer M.Urban & Laura Quilter, Efficient Process or Chilling Effects—Takedown Notices Under Section 512 of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22 Santa Clara Comp.& High Tech.L.J.621(2006); Jennifer M.Urban et al., Notice and Takedown in Everyday Practice, UC Berkeley Public Law Research Paper No.2755628,(March 22, 2017).一方面毕竟著作权人并非专业的裁判者,实践中无法准确分辨侵权行为与合理使用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来自著作权市场中的竞争对手发出的恶意通知。(24)See Jennifer M.Urban & Laura Quilter, Efficient Process or Chilling Effects—Takedown Notices Under Section 512 of the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 22 Santa Clara Comp.& High Tech.L.J.621, 655(2006).因此法院坚持要求著作权人提供有明确具体指向的通知,目标就是抑制“通知-删除”规则被滥用的情况。
(二)版权产业优势发展环境下的制度经验
与美国不同,欧盟国家的互联网产业基本由美国所主导,本土仍然是传统版权产业占据优势地位,因而形成了本土版权产业与域外(美国)互联网产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分歧。(25)反对美国互联网平台在各领域的垄断,甚至已经成为部分欧盟国家的一项“共识”。See Steve Denning, The Fight For Europe’s Future: Digital Innovation Or Resistance, Forbes(May 20, 2018).https://www.forbes.com/sites/stevedenning/2018/05/20/the-fight-foreuropes-future-digital-innovation-or-resistance/#722f906948c0,2021年10月3日访问。欧盟国家缺乏本土强势互联网产业的原因,主要在于成员国语言和制度差异所导致的市场碎片化,互联网产业所赖以发展的用户规模无法形成,进而造成域外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本土版权产业主体在经济收益上形成了越来越大的“价值差”(value gap)。(26)See Giuseppe Colangelo, Mariateresa Maggiolino, ISPs’ Copyright Liability in the EU Digital Single Market Strategy, 26 Inter.J.L.& Info.Tech.142(2018).基于这种认知,在2019年通过的《单一数字市场版权指令》(DSM)中,欧盟立法者采取了一种更偏向于版权产业保护的立法选择,在第17条中提升了“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online content-sharing service provider)的义务标准,(27)根据DSM第一章中的定义,“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是指为用户上传至其平台的包含受版权法保护作品的大量用户创造内容提供存储、组织和推广服务,并以此来达到营利目的的社会信息服务提供者。其中包含三项要求:第一,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应当尽最大努力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第二,对于那些著作权人已经向“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提供了必要信息的作品,“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应当尽最大努力保证该作品不被非法使用;第三,在收到著作权人的通知后,“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应迅速采取断开链接或者移除内容等措施,并尽最大努力防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28)Article 17(4)of Directive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1996/9/EC and 2001/29/EC, 2019 O.J(L 130)1-34(EC).同时,为了缓解法定义务提高所导致的矛盾,DSM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规模加以了区分。对于向公众提供服务不满三年且年收益低于1 000万欧元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只须证明其已尽最大努力向权利人获得授权,且在接到通知后迅速采取行动断开链接、移除内容即可获得豁免。但对于每月访问量超过5百万人次的平台,DSM则要求当著作权人提供了必要信息后平台须尽最大努力防止侵权行为的再次发生。(29)Article 17(6)of Directive 2019/790.换言之,在新的指令中,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承担侵权责任的判断,已经不再局限于是否在通知后完成了删除等必要措施,而是是否“尽到最大努力”,以及如何界定和解释“尽到最大努力”。
由此可见,DSM的第17条乃是在提升“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基础上,实质性地增加了作为过滤义务的“事前必要措施”,而不再将必要措施局限于仅在获得通知后才实施的事后规则。根据DSM的要求,如果互联网平台未能获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其行为即被首先预设为侵权,而无论传播该作品的主体是网络用户还是平台自己。(30)Article 17(1)of Directive 2019/790.有观点认为,虽然DSM并没有明文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过滤或审查义务,但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表明自己“尽到最大努力”,只能以借助算法或人工增加过滤和审查环节来避免陷入侵权的指控。(31)See Giancarlo Frosio, Fron Horizontal to Fertical: An Intermediary Liability Earthquake in Europe, 12 Oxford J.Intell.Prop.L.& Prac.1, 11(2017).这种变化也意味着DSM已经脱离了《电子商务指令》第14条以事后必要措施设定为核心的避风港条款,成为一项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防止侵权行为发生的强制措施。
然而,上述义务中的“尽最大努力”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准确界定,势必引起各国在调整国内法后加以适用时出现诸多争议。“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若想证明自己履行了注意义务,则须证明为获得授权“尽到最大努力”并满足“专业注意义务的较高行业标准”。然而,何谓“最大努力”和“专业注意义务”,DSM中并未明确。这种概念的模糊性,在欧盟各成员国将指令本土化后会更加明显,进而更加影响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必要措施设定上的选择。在产业实践中,这种专业注意义务和较高行业标准,则往往被转化为事前对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过滤。(32)Giancarlo Frosio, Why keep a dog and bark yourself? From intermediary liability to responsibility, 26 Inter.J.L.& Info.Tech.1(2018).不容否认的是,该指令带来的一系列欧盟成员国国内法调整,已经给谷歌和亚马逊等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商业模式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33)Karina Grisse, After the Storm-Examining the Final Version of Article 17 of the New Directive(EU)2019/790, 14 Oxford J.Intell.Prop.L.& Prac.887, 893(2019).
四、“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私人创制考察
综合归纳美国和欧盟的制度反思和立法尝试可以发现,随着信息管理能力和经济收益的提升,网络服务提供者越来越被公众视为“不可驯服的怪物”,因而需要通过提升其注意义务的方式予以约束,所以应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和践行更多必要措施已近乎成为版权产业主体的共识。(34)See Giancarlo Frosio, The Death of “No Monitoring Obligations”: A Story of Untameable Monsters, 8 JIPITEC 199, 200(2017).但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看,无论是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发展相对平衡的美国,还是版权产业较之互联网产业更为强势的欧盟国家,都没有将主动过滤义务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即使饱受著作权人一方的诟病,美国法院在司法裁判中仍继续坚持要求著作权人提供具体明确的侵权信息,否则不予认定侵权。(35)已有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提出,“虽然原告经常暗示YouTube拥有发现和定位侵权行为的能力,但其仍然没有法定义务去这样做。”See Viacom Int’l, Inc.v.YouTube, Inc., 940 F.Supp.2d 110, 117(S.D.N.Y.2013).可见DMCA自颁布以来所秉持的避免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主动监管和高额成本的目标,(36)Jennifer L.Kostyu, Copyright Infringement on the Internet: Determining the Liability of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s, 48 Cath.U.L.Rev.1237, 1272(1999).仍然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被司法机关所延续。欧盟2019年的指令虽然在第17条中显著提高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注意义务的要求,但可以明确的是并未提出任何主动审查或者过滤的要求。(37)之所以可以明确,是因为DSM草案的第13条本来是要求互联网平台提供有效的内容识别技术,但最终由于争议过大而被删除,改成了现在第17条的内容。而且第17条的第8款也专门明文规定“本条不会带来一般性的监管义务”。(The application of this Article shall not lead to any general monitoring obligation)DSM同时解释了这些义务“不应导致会员国施加一般性监督义务”。
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显著提升的情况下,美国和欧盟都没有真正推翻“避风港规则”的原因,其实在于著作权人与互联网平台之间已经就侵权过滤技术的实施有了较为成熟的合作。换言之,针对技术和产业变迁带来的问题,发达国家更多是通过私人创制“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方式来应对。(38)See Giancarlo F.Frosio, Why Keep a Dog and Bark Yourself? From Intermediary Liability to Responsibility, 26 Oxford Int’l J.L.& Info.Tech.1, 17(2018).早在2008年,谷歌公司就发布了用于比对侵权内容的Content ID,随后视频分享网站Vimeo也采用了Copyright Match技术来发现视频中的侵权内容。上述过滤技术的特点,在于由著作权人提供作品库,然后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该作品库为基础运用技术手段实现实质性相似内容的比对,部分过滤技术还在著作权人同意的基础上有条件地允许网络用户使用。具言之,私人创制的过滤措施有以下特点:
第一,私人创制的过滤机制是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合作的产物,这使得双方都可以采取符合彼此需要的过滤手段和标准。当然,这种不同类别之间产业主体合作的成型,主要是靠立法上注意义务标准的提升和司法上权利人的规模化诉讼。(39)See Capitol Records LLC v.Vimeo 972 F Supp 2d 500(S.D.N.Y.2013); Viacom Int’l v.YouTube Inc 676 F3d 19(2d Cir 2012).两者的合力,使得互联网平台疲于应对海量通知和承担过高诉讼成本,从而选择与著作权人合作构建过滤机制,借助技术手段从事前抑制侵权行为的发生。(40)回顾在欧洲国家这种合作的历史可以发现,互联网平台最初使用过滤技术所主要针对的是恐怖主义和网络暴力等与公共安全相关的问题。See Google in Europe, Partnering to Help Curb the Spread of Terrorist Content Online(Google Blog, Dec.5, 2016).https://blog.google/topics/google-europe/partneringhelp-curb-spread-terrorist-content-online; Partnering to Help Curb Spread of Online Terrorist Content(Facebook Newsroom, 5 December 2016).https://newsroom.fb.com/news/2016/12/partnering-to-helpcurb-spread-of-online-terrorist-content,2021年11月14日访问。如此安排的结果,一方面可以破除著作权人一方要求在立法上引入过滤义务的借口,另一方面则实现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的合作,为作品传播的正版化和“用户创造内容”的合法化创造了前提。网络服务提供者普遍认为,自愿采用的过滤措施,显然会优于立法上一刀切式的标准提升。(41)See Mark Fiore, Facebook, Inc., Reply Comments in Response to Section 512 Study: Notice and Request for Public Comment at 7(Apr.7, 2016), https://www.regulations.gov/document?D=COLC-2015-0013-90724,2021年11月14日访问。
第二,私人创制的过滤措施得以运作,仍需要以“通知-必要措施”义务为基础。欧盟议会下的经济与社会委员会即提出,对互联网平台责任的强化,应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42)See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the Council,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mmittee of the Regions, Tackling Illegal Content Online.Towards an enhanced responsibility of online platforms,(September 28, 2017).换言之,这种过滤措施乃是“通知-必要措施”机制的延伸。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著作权人提供的作品库作为采取必要措施的前提,相当于著作权人提前将可能被侵权的内容提供给了网络服务提供者,当侵权行为发生时,已经被确认权利归属的作品库即可被视为合格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可以直接启动必要措施。从整体看,“通知-必要措施”中的通知因作品库的预先提供而相当于被提前到了具体侵权行为实际发生之前,而必要措施则在技术的帮助下得以快速实现对侵权行为的隔离。所以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适用的现有过滤措施并非是从责任上升为义务,而是从强制转换为自治。
无论是版权产业处于优势地位的欧盟,还是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势均力敌的美国,都没有真正采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过滤的立法安排。相反,从立法史出发,其实无论是欧盟2019年的指令,还是1998年美国的DMCA,新旧制度的立法目标中都包含着借助立法设计来推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著作权人的合作。(43)Se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May 2020), pp.71-73; Béatrice Martinet Farano, Internet Intermediaries’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and Trademark Infringement: Reconciling the U.S. and EU Approaches, TTLF Working Paper No.14, http://www.law.stanford.edu/organizations/programs-and-centers/transatlantic-technology-law-forum/ttlfs-working-paper-series,2021年11月14日访问。欧盟已通过的立法,旨在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提高必要措施的标准和效率,并非直接增设过滤义务。以YouTube为代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借助算法识别侵权行为,一方面是针对频繁诉讼和必要措施标准要求提高的应对措施,另一方面则是与著作权人合作的结果,是一种私人创制规则的体现。之所以选择平台自治的方式来实现事前过滤,乃是因为如果将法定过滤义务纳入必要措施,并将其前置,反而会进一步增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力量,使其拥有类似司法裁判的权力。如果立法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主动过滤平台上的内容,可能会导致合法的言论被不当删除,损害网络用户的表达自由。从法律裁判的角度看,主动过滤义务如果法定化,其中必然包含着利用算法对作品传播行为合法性的判断,进而使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了实质上的裁判权。(44)以YouTube的Content ID技术为例,该过滤技术基于著作权人所提供的作品库,将网络用户上传的所有视频和音频内容与该作品库加以比对,若上传内容与作品库中的内容在一定“量”上达到匹配的程度,就再通过系统设定的算法进行技术分析并判断是否构成侵权。Paul Resnikoff, 99.5% of All Infringing Music Videos are Resolved by Content ID, YouTube Claims,Digital Music News, 8 August 2016, https://www.digitalmusicnews.com/2016/08/08/copyright-problems-resolved-content-id/,2021年11月14日访问。一旦技术手段对用户的传播行为产生误判,不但可能损害用户的经济利益,更会破坏著作权法所设定的合法与非法边界,让机器和算法变成了法官,裁判规则也由透明变为不透明。(45)See Katrina Geddes, Meet Your New Overlords: How Digital Platforms Sustain Technofeudalism, 43 Colum.J.L.& Arts 455(2020).
当然,即使是通过私人协商代替法定方式来创制过滤机制,也并非没有弊端。至少从互联网产业的规模效应看,拥有大量作品的著作权人当然会倾向于和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合作,这就意味着对于小规模的著作权人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这种机制难言友好。首先,用户规模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无论是在作品库来源还是过滤算法的投入上,一方面难以获得著作权人在作品内容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则难以承受其中的高额成本。其次,如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早期的效果一样,过滤机制所依赖的作品库也一般由掌握大量作品的著作权人主导,小规模和个体的著作权人则容易被排除在外,或者被要求服从一些对其不利的合同条款以获得过滤技术的支持。(46)See statement of Maria Schneider, Before the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Subcommittee on Cour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the Internet, Hearing on “Section 512 of Title 17”(March 13, 2014).长此以往,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就会在必要措施的效率上因过滤技术的适用和差异而出现分流,法院在统一适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时,一方面会对规模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利,进而因过滤技术的优势导致对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进入市场造成障碍;另一方面则会导致没有进入作品库的著作权人得不到这种过滤机制的保护。换言之,过滤技术的适用不但会形成市场准入的反竞争壁垒,还会使掌握优势过滤技术算法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因此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另外,更为严重却又更为隐性的问题,则是“技术沙文主义”给表达自由造成的消极后果。互联网带来的积极效应之一,是“用户创造内容”所带来的多元表达。由于内容识别技术仅仅是根据正版数据库与上传内容进行“量”上的比对,而用户上传内容是否合法通常是“质”的问题。(47)Matthew J.Sag, Internet Safe Harbor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pyright Law, 81 Notre Dame L.Rev.187, 548(2017).所以至少在现阶段,过滤算法中存在大量的误判,使得“用户创造内容”动辄被侵权通知或必要措施所干扰。(48)例如YouTube采用的Content ID只能标记出所有“未经授权”使用的作品内容,但却无法区分合法和非法使用,这种由私人企业开发的算法程序,相当于创造了一个“黑箱”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著作权的裁判被透明度和问责程度最低的机器来实施。较为全面的描述可参见Katrina Geddes, Meet Your New Overlords: How Digital Platforms Sustain Technofeudalism, 43 Colum.J.L.& Arts 455(2020).参与“用户创造内容”的“二次创作者”由于缺乏有效纠错机制来保护自己被误删的作品,从而只能服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算法剥削。
五、“通知-必要措施”义务范畴的本土设定
与司法上的频繁诉讼和立法上的注意义务标准提升所形成的倒逼产业合作不同,我国版权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尚未在此问题上形成共识,彼此之间仍然是斗争和博弈要远多于合作。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本土版权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发展状态与域外极不相同。我国现阶段已经形成了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互联网产业极为强大,而相比之下版权产业的发展却较为落后。两个产业之所以未能同步发展,是因为我国版权产业市场化进程开始得比较晚,而且在转型之初就直接面对迅猛发展的互联网产业。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互联网产业作为新兴产业,相关法律规制和行政管制都没有及时跟上,这使得互联网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商业模式中,出现了诸多侵害传统版权产业而未能得到及时制止的情况。作品被网络用户数字化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在互联网平台上被任意传播,一方面给互联网产业主体带来了巨大的流量,并使其借助流量获得了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则让版权产业主体的市场收益大幅降低,并丧失了原有的著作权市场。线下市场的急速萎缩和线上市场的盗版泛滥,导致我国版权产业在市场化转型之初即遭遇挫折,而且无力通过诉讼来达到与互联网产业达成妥协的目的,因而既无法形成如美国那样版权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势均力敌的产业形态,更不可能达到如部分欧盟国家那样具有强势传统的版权产业,最终形成了本土互联网产业全面主导版权产业的现状。几乎所有能够以数字化方式欣赏的版权产业类型,现阶段都全面以数字化方式传播,并主要由互联网产业掌控。
任何著作权制度绩效的实现,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与产业形态和特征相契合。对我国“通知-必要措施”义务的解释,同样需要符合本土互联网产业全面主导版权产业的现实。鉴于我国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现状,美国和欧盟的既有经验借鉴存在以下困难:
首先,由于本土互联网产业的强势,很多主流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的未来发展目标,都包含了从单纯的网络服务延申发展到内容提供。由于互联网产业主体期望自行经营版权产业,两类主体之间就构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我国版权产业主体至今为止并不愿意接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作条件,而网络服务提供者则更希望自行进入版权产业,著作权人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过滤机制的私人创制上难以达成合作意向。如果著作权人不愿意向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作品库,并就互联网平台上的相关使用行为的收益分配达成一致意见,这种私人创制的过滤机制就无法在本土成型和实践。这是我们在考虑借鉴美国模式时需要留意之处。
其次,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已促使版权产业各个领域全面包含互联网基因,作品传播和收益模式与传统版权产业的商业模式相比已有明显差别,互联网产业对传播效率的追求,已经深刻影响数字环境下由互联网产业主导的版权产业,并明显体现在作品传播和收益的方式上。从我国现阶段在线内容的商业模式看,各种类别作品的点播和下载主要采取的是会员制收费,即网络用户支付固定会员费后,即可在单位时间内不受限制地获取作品。这是一种典型互联网产业以传播效率为目标的许可模式,旨在保证网络用户尽可能自由地使用作品,而有别于传统版权产业按次付费或者按件付费的许可安排。因此,欧盟国家那种优先保障版权产业的制度设计,在借鉴时可能会与我国已有的商业模式产生隔阂。
鉴于上述本土产业特点,我国应围绕业已形成的互联网产业优势来适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在保障著作权人合法收益的前提下,发挥互联网产业的传播效率优势。从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责任”条款在正式通过前所经过的三次修订即可以发现,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完善,始终集中于其程序的细化上。同时要求有效通知需要包括通知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要求采取必要措施的网络地址或者足以准确定位侵权内容的相关信息,以及通知人要求删除相关信息的理由。(49)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也是一致的。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及网络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指南》第22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权案件审理指南》第9.21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浙高法民三〔2019〕33号)第8条。这说明立法者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定位,也仍然维持为不具有专业辨识和信息管理能力的中介组织,并未实质性增加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必要措施和注意义务上的负担。
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和人工智能技术以及算法过滤技术的发展,利用人工智能取代人工通过算法程序自动发出通知或过滤侵权信息已经成为可能。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为了保持用户粘性,都引入了不同的推荐算法来为用户量身打造符合个人需求的个性化推荐服务,为其在选择物品或商品时提供决策帮助。在技术的帮助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确实有快速的提高。但鉴于版权产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合作尚难以达成,加之域外私人创制的过滤机制所产生的弊端,我国在如何提高必要措施的效率问题上,短期内在“主动性”上难以取得实质进展,但在“及时性”上显然有完善的空间。而在“通知”与“必要措施”的关系上,则应该在解释中坚持“反通知”和“必要措施”彼此独立的制度安排。
(一)必要措施的范畴界定
基于《民法典》的现行规定,现阶段对必要措施的界定,不应继续考虑将其通过司法解释扩展为事前规则,也不应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缺乏明知或应知的前提下主动承担过滤或审查义务。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版权产业和互联网产业因彼此竞争关系的问题尚未能实现合作,导致源于美国的那种全面涵盖审查、授权和付费的私人过滤机制无法实现,而在立法和司法中强调主动过滤又违背了我国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特色,所以今后解释学上的重点,应集中在正确解释必要措施的“及时”性上。网络服务提供者所采用的必要措施,应避免拖延导致侵权严重化,并在其信息管理能力的范围内有效地控制侵权。
必要措施中的“及时”,实践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发出通知的时间、侵权通知的内容等,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权利人的侵权通知后,“应当在技术可能做到的范围内采取必要措施。(50)参见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部分部门规章基于其行政管理的对象,将必要措施的及时性具体到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24小时内。(51)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规范网盘服务版权秩序的通知》(2015)第4条;国家版权局:《关于加强网络文学作品版权管理的通知》(2016)第6条。也有调查认为,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从发出通知到采取必要措施之间间隔不超过7天即一周属于及时。(52)在目前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从发出通知到采取必要措施之间间隔不超过7天即一周属于及时。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网络侵权责任中的通知规则》,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37-149页。由于行业和技术的巨大差异,在及时性的判断上可以引入平台自治的空间。例如,阿里巴巴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已经开始尝试应用与现行规则相协调的平台自治规范,其在平台知识产权投诉网站上提供了两种投诉方式。第一种是通过阿里巴巴的投诉系统,通知后采取一定措施,但是平台可以实质性地参与到纠纷解决中来,并作为判定者的角色。采取这一方式的结果是纠纷能够尽快得到处理,而且一旦判定不侵权,商品链接就能够恢复,减少了平台内经营者的等待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风险,并具有“便捷、快速”的优势。(53)阿里巴巴知识产权投诉选项如下:选项一,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平台为线上操作系统,您注册账号并验证身份信息和知识产权证明材料后,可在线提交侵权商品链接发起投诉,投诉成立后,相应商品链接将被移除;卖家可以提交申诉,平台将结合双方的材料对商品情况进行判断,并决定是否恢复商品链接。选项二,如您无需阿里巴巴提供前项便捷、快速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而需要在投诉后进一步以向有权机关投诉、司法机关起诉的方式来解决本次知识产权争议的,请通过邮箱进行投诉,即将投诉通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发送至邮箱,我们将根据相关法律程序处理。参见《阿里巴巴知识产权投诉指引》,载https://ipp.alibabagroup.com/instruction/cn.htm,2021年10月16日访问。如果此类自治规范能够达到停止侵权和防止损失扩大的效果,就应该被视为是及时的。
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对现阶段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做一个类型化梳理,并针对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认定必要措施的范畴。基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以删除措施为基准线,将必要措施类型化为三类。第一类为提供经济保证等效力弱于“删除”或“断开链接”的必要措施。在天猫案、小程序案和阿里云案中,法院均表明采取删除措施过于严厉,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性质和信息管理水平,可在转通知之外采取要求提交保证金等必要措施,以便在侵权行为没有被最终证实的情况下不影响被通知人的经营行为。(54)司法实践中已有的做法,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指南》(浙高法民三〔2019〕33号)第14条,其中浙江高院即提出将保证金作为一种必要措施。根据审理指南第14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收到合格通知后,可以要求被投诉的平台内经营者提供保证金。保证金保证的是权利人而非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损失,如果后续可以证明平台内经营者确实侵权,那么这部分保证金可以用来偿付权利人的损失。第二类为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关闭网络用户获取渠道的必要措施。本类型的必要措施主要针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和搜索、链接服务”这两类网络服务提供者,但在适用时,应该严格核实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对于超出单纯提供信息储存空间的服务类型,则不得因为存在此类服务而对主体范围进行限缩,而是应升级适用。第三类为消除服务资格等效力重于删除的必要措施。此类必要措施主要以终止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为目标,即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再给网络用户提供服务,例如采取“关闭店铺”“查封账号”等措施。三类必要措施的依据,一方面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管理能力上的差异,另一方面是侵权行为的程度。原来“信网权保护条例”所列举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可以作为第二类必要措施的适用主体,亦作为必要措施类型化的基准。
(二)“通知-必要措施”规则的内部关系梳理
在“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内部,需要着重梳理的是“转通知”与“必要措施”关系问题。在我国的司法审判实践中,有法院将转通知视为一种必要措施。(55)参见威海嘉易烤生活家电有限公司诉天猫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浙知终字第186号民事判决书。其原因在于包括小程序平台服务、云服务器租赁服务、电子商务平台服务等在内的新服务类型,并无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用户之间那样的关联性,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像传统的网络存储和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那样直接对内容进行较为便利的控制和审查,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导致发生侵权行为时其所能采取的合理必要措施受到极大限制。所以,如果仍然采用“删除、屏蔽、断开链接”这一类的必要措施,将有违审慎、合理原则,损害用户其他合法权益。在“阿里云案”中,鉴于用户将涉嫌侵权的游戏软件服务器端程序存储于阿里云管理的云服务器上,法院认为,考虑到强行对服务器采取关停或删除数据的措施会殃及云服务器中其他合法内容,所以在不适合直接采取删除措施的情况下,转通知具有“警示”侵权人的意图,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损害后果扩大,应该被作为“必要措施”从而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达到免责条件。(56)参见乐动卓越诉阿里云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7)京73民终字1194号民事判决书。
但与司法实践不同的是,如果从文义解释出发,无论是“信网权条例”还是《民法典》,转通知和必要措施都是彼此独立的环节,不同的只是《民法典》把“转通知”规定于必要措施之前,使“转通知”由原本在采取制止侵权必要措施时应同时履行的辅助措施(“删除并转通知”),转变为在采取制止侵权必要措施前履行的独立环节(“转通知并采取必要措施”)。将“转通知”独立于“必要措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转通知”作为必要措施的前置程序,立法目标在于保护网络用户的知情权和起到警示作用,并无制止侵权的效果。如果将“转通知”纳入必要措施中,可能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实施转通知之外的必要措施,导致侵权行为得不到阻止,损害权利人的利益。而将两项义务分立,则使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以其他必要措施代替转通知,必须在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之外同步履行转通知义务。换言之,“转通知”乃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必须履行的一项独立义务类型,而不具有可选择性。第二,“转通知”能够保障网络用户的合法利益。“转通知”作为独立程序,使被通知人得以知晓被采取必要措施的原因,以便其在未实施侵权行为时可以要求恢复服务。另外,“转通知”的独立,也迫使网络服务提供者为降低成本必须探寻有效送达“转通知”的方法,并倒逼其严格审核权利人提供的初步侵权证据,客观上降低了通知被滥用的可能。
六、结论
我国“通知-必要措施”规则在经历了从域外借鉴到本土生成的过程后,最终形成了以《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诸项司法解释、指导意见为主体的制度体系。网络服务类型扩张,算法深度介入,以及“用户创造内容”的普及,都使得如何解释“通知-必要措施”以适应移动互联网的商业模式成为新的课题。虽然美国和欧盟针对这一问题在司法和立法上多有创新之举,特别是私人创制的过滤机制,能够实现审查和授权合一,但鉴于本土互联网产业主导版权产业的格局,该机制在我国尚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此,对“通知-必要措施”的解释论完善,只能集中于“必要措施”范畴的合理界定和“通知-必要措施”的程序衔接两个方面。前者可以引入平台自治规则,允许互联网平台来安排具体必要措施,后者则应该在解释上坚持转通知和必要措施的分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保障权利人合法利益的同时,避免通知成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