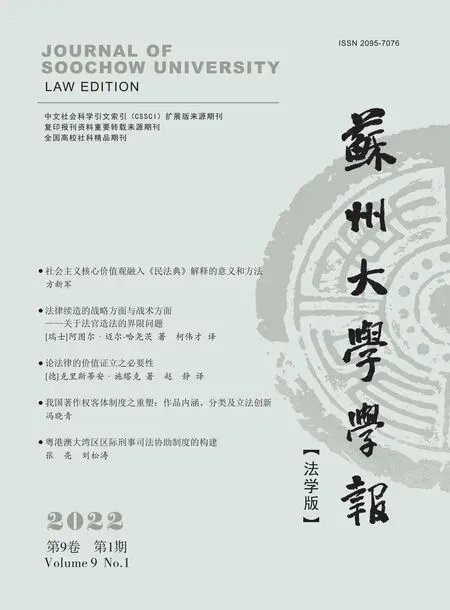论法律的价值证立之必要性*
[德]克里斯蒂安·施塔克 著 赵 静* 译
一、关于价值在法律中的不可避免性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价值证立之必要性这一问题涉及先在于法律的基础。“价值证立”(,,Wertbegründung“)一词将价值视作法律赖以成立的基础。就其结构而言,价值即是人的观念、理念和视角,借此得以在世界中自我引导并形成关于世界的经验。在此暂且不论是否有可被认知的客观价值,也不论是否始终只有得到主体间承认的、超越时代的主观价值观念。就其内容而言,价值即是命题(谓词),借以判断或评估某种物质或精神——往往是在与其他物质或精神的次序关系中——是好的或者有价值的。(1)Vgl.Victor Kraft, Die Grundlagen einer wissenschaftlichen Wertlehre, 2.Aufl.1951, S.10 f.; Heinrich Henkel,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2.Aufl.1977, S.326 ff.; ähnlich Adalbert Podlech, Wertungen und Werte im Recht, in: AöR 95,(1970), S.185, 195: Wertungen als Vorzugsregeln.某物或某项劳动的经济价值,即此评估之一例。
规范制订者并非直到确定法律后果(Rechtsfolge)时,而是早在对现实进行必要的概念表述,即形成法律构成要件(Tatbestand)时,便已经被要求进行评价;该评价由借以观察现实的指导性理念(2)Christian Starck, Die Bindung des Richters an Gesetz und Verfassung, VVDStRL 34, 1976, S.60.以及立法机关想要实现的价值观念所决定。评价既涉及法律应当实现的目的,也涉及用于实现目的之手段。就此而言,所有法律都得到了价值的证立。(3)Günther Winkler, Wertbetrachtung im Recht und ihre Grenzen, 1969, S.42; Henri Batiffol, Problèmes de base de philosophie de droit, Paris 1979, S.130; Bernd Rüthers, Rechtsordnung und Wertordnung, 1986, S.19, 26.因此,法律规范也能够在价值上得到衡量。
该主题涉及了法律的哲学基础这项一般认知问题。价值概念之所以取代了自然法中的自然概念(Naturbegriff),是因为那个被自然科学从因果关系的视角来理解的自然已经丧失了其追求的目的(Telos)及其形而上学关联性。(4)Robert Spaeman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Utopie, 1977, S.184 ff., Gerhard Luf, Zur Problematik des Wertbegriffe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FS für Verdroß 1980, S.127, 129 ff.; Rupert Hofmann, Die Zumutungen des Grundgesetzes, ZfP 27(1980), S.129, 147;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3 f.上述恰切的观察证实了,价值问题关系到法律的基础。为了避免用语狭隘和自相矛盾,我在探讨本文主题时将不囿于价值哲学的相关术语,而是将其理解为对于法律的哲学基础之追问。
实在法在内部将回溯到宪法;而根据诸国的国家法学,宪法乃是最高的、实证法上的法律渊源,至于超越宪法的则是不再能通过实在宪法(das positive Verfassungsrecht)得到把握的制宪权。对制宪权边界的追问,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实在法基础的追问,是法学的(juristisch)、尤其是法律科学的(rechtswissenschaftlich)提问方式,因为法律科学不仅限于处理实在的法律质料,还延伸到了法律的基础。这一点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假使将法律科学限制在实在法领域的话,人们就会潜意识地在以下意义上提出关于实在法的命题,即认为实在法总是可以从自身出发得到理解、解释和适用;人们甚至会进一步认为,基础问题对于法律科学而言显得收效甚微且毫无必要。上述假设显然无法得到证成。
(二)价值批判
法律的价值证立,在其价值哲学形态下(5)Vgl.die Darstellung von 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1 ff.遭受到了双重批评:从哲学视角来看,不同的价值学说会使法律最终受制于主观的任意性;(6)Podlech, Wertungen und Werte im Recht, in: AöR 95,(1970), S.185, 205 f.从方法论视角来看,对价值的援引会掩盖法官对宪法与制定法所作的解释,并遮蔽司法决断论(richterlicher Dezisionismus)。(7)z.B.Helmut Goerlich, Wertordnung und Grundgesetz, 1973, S.133 ff.基于这种方法论视角,法律的价值证立的批评者大多试图根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指明,回溯到价值学说——无论是以主观价值学说还是以客观价值学说为依据——将会导致非理性的裁判。
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与尼古莱·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的客观价值学说遭受了某种极其严苛的评判(Verdikt),被认为是基于某种直觉的价值直观(intuitiver Wertschau),借此据说能够把握作为理想存在的客观价值。主观价值学说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所有被评价人所援引的优先规则都是主观的,故而在理性层面上都是不可证立的,即使这些规则符合某种文化标准并且具有经验依据。(8)So 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5.诚然,这两种价值学说在表达价值时,的确将某种苛刻的、压榨的、挑衅的或专制的特性归给了价值,(9)C. Schmitt, Die Tyrannei der Werte, in: Festschrift für E.Forsthoff, 1967, S.37, 55 ff.; 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8 f., auch zum Folgenden.因为价值迫切需要被实现,它们要求必须被置于某种先后和层级秩序中,并互相竞争。(10)So auch Theodor Geiger, Die Gesellschaft zwischen Pathos und Nüchternheit, Kopenhagen 1960, S.145 ff.
假使基础的、哲学层面的价值学说关乎的是为法律秩序奠基的学说的话,上述批评或值赞同。因为人们既不能将法律秩序建立在客观价值学说的直觉直观之上,也不能将其建立在主观价值学说的恣意评价之上。对以下观点的强调倒是正确的:一种哲学学说如果完全缺乏“一种理性的、着眼于商谈调解的基础”,也就不适用于法律的证立;因为法律,作为和平秩序,只能建立在某种普遍可沟通的、可理解的哲学基础之上。(11)Podlech, Wertungen und Werte im Recht, in: AöR 95,(1970), S.185, 208(m.w.H.FN 102); 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11.
哲学层面的价值学说首先关注伦理行为的条件(Bedingungen sittlichen Handelns),(12)Luf, Zur Problematik des Wertbegriffe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FS für Verdroß 1980, S.141 f.即某种规范秩序。该秩序之所以不能等同于法律秩序,是因为它不具有任何强制特征。因此,价值伦理学中的应然(Sollen)——用尼古莱·哈特曼的话来说——只不过是“要求对价值的自由决定”以及要求对价值的实现。(13)Nicolai Hartmann, Ethik, 3.Aufl.1949, S.774.就此而言,上述价值学说便可以从以下基本权利的角度得到理解,即应当保护人们形成信念、实施评价、对人们赖以生存并为之奋斗的价值进行排序的自由,只要不僭越共同合意(Gemeinverträglichkeit)的界限。然而,价值的上述面向在此可以追溯到它自身,因为这一面向与探究法律的哲学基础无关。在此令人感兴趣的仅仅在于指明并非所有价值都是法律价值。因此,法律保障艺术自由,但法律本身不得以美学——即艺术的价值学说——为基础。同样,法律应当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但法律不得始终以邻舍之爱的价值为基础,并依此来规定义务。(14)Dazu treffend Peter Stein/John Shand, Legal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Edinburgh 1974, S.3.
价值思维面临如下批评:(15)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20(einerseits in den,,geistigen Bewegungen“), S.5, 11(andererseits zu Erfahrung und Kulturstand); vgl.auch Ernst Forsthoff, Zur heutigen Situation einer Verfassungslehre, FS für Carl Schmitt, Bd.I, 1968, S.209.即价值思维会导致法律总是建立在社会的明确价值观念之上,还会导致法律受制于每日评价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us der Tageswertungen),还会导致法律不再必然地基于理性,而是建立在价值意识的事实给定之上。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运动,随着它们对价值的贬低与重估(Ab-und Umwertung),能够充分证明作为法律之基础的价值的不稳定性。这种判断也明确延伸到了那些由经验与文化水平来决定内容的评价。
(三)不可避免性
对基于价值哲学的价值学说的反对并不适用于其他价值学说,(16)So zutreffend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985, S.137.尤其不适用于通过论证来承认或确立价值的价值学说。例如,库萨的尼古拉(Nikolaus v.Cues)认为,理性的衡量力(messende Kraft)是价值评估与价值存续的基础。(17)Semoto enim intellectu: non potest sciri, an sit valor; zitiert nach Ernst Cassirer,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 der Neuzeit, Bd.I, Ausgabe 1974, S.57 f.
价值学说的批评者们也认为,国家与法律的目的是保护与支持个人自由,(18)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Der Staat als sittlicher Staat, 1978, S.31 ff., 33: 以个人的自由与自我实现为导向的国家,人文主义不可剥夺的遗产;S.35: “对于精神与伦理生活来说,需要获得临界点、制度性前塑造与规范的支持。从而使得存在的普遍精神与伦理态度得以依附在它们之上,获得公共关联性,并找到与‘报酬-功绩社会’的个人主义-功能性动力相对立的支持与确认。”且是一种和平秩序。在这种目的设定中,自由与内在和平被视为法益,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或基础。但是,这种目的设定需要获得人们的承认。
通常而言,民主制的国家形式被视为那种持相对主义与价值不可知论立场的国家理论的表达。事实上,许多人已经遗忘了这种民主制方案的理想性与价值性根源,或者对他们而言民主制或民主制的国家形式只是非理性的神话。(19)Vgl.dazu kritisch Helmut Steinberger, Konzeption und Grenzen freiheitlicher Demokratie, 1974, S.207.法律的价值证立的坚决反对者,包括西奥多·盖格(Theodor Geiger),均宣称所有关于正义的谈论都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已;他们支持个人的信念自由是民主制不可或缺的自由权,(20)Th. Geiger, Die Gesellschaft zwischen Pathos und Nüchternheit, 1960, S.192.但不承认在民主制的平等观念中存在某种评价,也不承认这种评价是民主制中有效权利的基础;同样,他们也试图通过无涉价值的方法来证立宽容思想。(21)Th. Geiger, Die Gesellschaft zwischen Pathos und Nüchternheit, 1960, S.145.但事实是,在信念自由与宽容这两种情形中,价值是相互对立且彼此限制的。(22)Steinberger, Konzeption und Grenzen freiheitlicher Demokratie, 1974, S.214 ff.
而且,即使一国之最高法律规范仅限于管辖权规则与程序规则,这些规则也是基于评价而被制定的:多数决规则基于以下评价,即应当由多数而非由少数来确定决策的内容,即使少数比多数更聪明;公开规则与咨询规则(Öffentlichkeits-und Beratungsregeln)基于以下评价,即程序确实应当尽可能协助理性取胜,但至少也应当令人满意;再比如管辖权规则基于以下评价,即一个机构能够做出比另一个机构更好的决定,或者一个团体(Körperschaft)能够做出比另一个团体更适合的决定。
然而,法律秩序所依据的上述评价具有以下特殊性:这些评价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其法律效果已经经过了检验与探讨;它们在特定情形中是否以及如何经受住考验,是可以被确定的,等等。任何法律秩序都奠基于一些标准,这些标准最终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基础上,即某些行为方式比其他行为方式更有价值。不存在价值中立的秩序,(23)So Karl Larenz, Richtiges Recht, 1979, S.158; ferner Hans Ryffel,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 1969, S.278 ff., 287.因为如果不找到法律规范背后的价值,这些规范是无法被理解的。(24)Christophe Grzegorczyk, La théorie générale des valeurs et le droit, Paris 1982, S.265 f., 271.既然我们的法律依赖于某些特定价值,而且我们也无法逃避价值,那么唯一重要的便是要将法律秩序建立在正确价值之上,并通过法律解释把这些价值确定下来,同时在法律适用中把它们传达出来。对价值的评价、贬低与重估在本世纪并不稳定,无法作为反对法律的价值证立的论据;这跟福斯多夫(Forsthoff)的观点相反。鉴于最终所有人都能辨别那些作为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基础的评价,并证明它们是不人道的,所以我们不必对所有作为法律基础的评价予以根本性批评。(25)Vgl.dazu auch kritisch Rüthers, Rechtsordnung und Wertordnung, 1986, S.25 ff.已被证实的是,法律总是建立在评价的基础上。因此,反对一切评价的彻底中立性简直匪夷所思,它只是基于幻觉罢了。
1930年,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上台的近三年前,里查德·托马(Richard Thoma)在《关于作为民主制的帝国》一文(载于《德国国家法手册》(HandbuchdesDeutschenStaatsrechts),第193页)中,与厄尔·比尔芬格(Earl Bilfinger)展开辩论,并写下:魏玛宪法始终建立在对民族大多数人可随意撤回的宽容的基础上。有一种观点认为,第76条规定的双重(26)这里指修改宪法的两种途径:立法方式(三分之二多数决)尤其是公民投票的方式。制宪权(doppelte pouvoir constituant)不可能是毫无限制的,用比尔芬格的话来说,人们或许确实不能“在魏玛做出如下决定,即支持某种看似合法化的政变方法的体系”;这种观点误解了那种或许是大胆的、却又合乎逻辑的对如下理念的理解方式,即自由的、民主的自我决定的理念(Idee der freien demokratischen Selbstbestimmung)。当然,这种自由可能会被煽动性地滥用——否则又怎么能称其为自由呢?但是,从作为法律解释之出发点的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我们无法将那些由坚决的、不可置疑的大多数民众通过合法方式所希求并决定的结果(甚至是推翻现行宪法的基本支柱)评判为政变或叛乱。
托马的上述命题基于以下明确评价:修宪权尤其是制宪权可以为所欲为;也就是说,在实践中,这种权力(Gewalt)可以废除或保留基本权利、少数派保障与法院独立。据此,压倒一切的标准是强者的力量,例如由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法律,而无须顾虑任何限制。
这就引发了关于作为法律秩序基础的评价的正确性问题。我们从哪里获得标准?
二、关于评价的正确性
法律建立在价值的基础上,关于价值的正确性标准问题,我将探讨:
1.价值的主体间承认,并结合价值对于历史进程中人类共同生活而言的、经验上可证明的实践检验;2.在为法律奠基时,对人类学的基本事实(anthropologische Grundgegebenheiten)(人的本性)进行考虑的必要性。
(一)历史标准
我们首先探讨法律的价值证立之历史经验面向。即使人们不能将这些事实——它们在历史进程中已获得验证,或者当前得到了众多法律秩序的承认——作为严格的哲学意义上的正确性标准,(27)Ryffel与Luf均准确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详见Ryffel,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 1969, S.284; Luf, Zur Problematik des Wertbegriffe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FS für Verdroß 1980, S.143 ff.但在我看来,诉诸上述对价值进行承认以及对价值进行实践检验的事实,既在历史的深度维度又在比较法的广度维度上具有法哲学旨趣。原因如下:首先,人们以这种方式获得质料,而哲学家也需要这些质料。其次,仅仅证明特定价值获得了承认尚不充足,更令人感兴趣的是这种对价值的承认所依据的理由。在此可以参照自然法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一种在经验意义上可确定的现象,其特点即是给出理由(Anführen von Gründen),尽管这一特点经常被忽视。人们只需联想亚里士多德(Aristotles)、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v.Aquin)、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和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即可。最后,历史发展与比较法中的差异可以为价值难题的哲学思考提供重要信息。
比较法特别清楚地表明,不同国家的法律均建立在共同价值之上,这些价值无一例外借由不同的、大多在历史中演化而成的制度,以不同的方式获得实现、促进或支持。(28)在制定欧洲行政法时,欧洲法院借鉴了成员国的个别宪法与行政条例背后的共同价值观。vgl.Ulrich Everling, Rechtsvereinheitlichung durch Richterrecht in der Europäischen Gemeinschaft, in: Rabels Zeitschrift 50(1986), S.193 ff.; ders., Auf dem Wege zu einem europäischen Verwaltungsrecht.NJW 1987, S.1 ff.; Christian Starck, Rechtsdogmatik und Gesetzgebung im Verwaltungsrecht, in: Behrends/Henckel(Hrsg.), Rechtsdogmatik und Gesetzgebung, 1989, S.106, 109 f.比较法还确证了法律秩序之间存在哪些评价差异,这一点在对法律秩序(比如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秩序)进行基本评价时,尤为明显。
彼得·斯坦(Peter Stein)与约翰·尚德(John Shand)于1974年出版了《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LegalValuesinWesternSociety)一书,就其书名对我们的主题而言,尤其值得注意;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本书首先尝试“对西欧的法律秩序自古以来便意图实现的价值作出描述,然后试图解释这些价值在我们现行法律中的影响”(29)Stein/Shand, Legal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1974, S.V; vgl.auch Franz Wieacker, Voraussetzungen europäischer Rechtskultur(Bursfelder Universitätsreden 4), 1985, S.28 ff.。作者以三个基本理念作为出发点,这些理念也被称为基本价值:秩序、正义与个人自由,即和平、正义与自由。(30)Vgl.auch Ryffel, Rechts-und Staatsphilosophie, 1969, S.219 ff., 228 ff.; Larenz, Richtiges Recht, 1979, S.33 ff.; Christian Starck, Frieden als Staatsziel, in: FS für Carstens, 1984, S.867, 874.法律对和平的保障功能作为一种价值,构成了法律的依据,这一功能已在上文中有所提及。该功能体现在众多法律制度中,并通过这些制度获得实现;此外,几乎所有这些法律制度也都以自由价值为基础,而且大多也以公正的利益平衡为基础。
法律制度的这种多维性源于以下命题:上文提到的三个基本价值相互之间成三角关系,(31)Starck, Frieden als Staatsziel, in: FS für Carstens, 1984, S.874; 从某种辩证关系出发给出的类似论述参见Larenz, Richtiges Recht, 1979, S.41 f.并彼此制约。如果建立在法律和平基础上的秩序被普遍认为是不公正的,那么从长远来看,法律和平也将无法获得保障。例如,在最终作出了生效判决的民事诉讼中,只有当这些判决通常为公正之时,民事诉讼才有助于和平。(32)Vgl.auch zum Folgenden mit Nachweisen Starck, Frieden als Staatsziel, in: FS für Carstens, 1984, S.876 f.也就是说,民事诉讼既没有自我目的(Selbstzweck),也没有与实体法分离的、内容上不确定的单纯和平目的。因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通过那些极端情形(如内容上错误,但生效的判决)来理解民事诉讼这一法律制度。为了第三方的权利以及和平,我们也可以限制那些旨在保护自由和限制国家权限的基本权利。社会平衡削减自由与财产(仅需想想累进税制),但维护了和平。相反,自由价值限制了社会平衡,而如果过分追求自由,也会扰乱和平。
一些重要法律制度(其中某些历史悠久并得到广泛认可)显示了自由、和平和社会平衡这些基本价值是如何获得实现的。当事人(Rechtsgenossen)签订契约时,他们自治地,即自由地制定适用于彼此之间的法律并“和平相处”(,,vertragen“)。在罗曼语言中,和平-和平(Frieden-pax)与契约-契约(Vertrag-pactum)之间的联系从词源上来看,是显而易见的。订立契约的自由意味着受契约的拘束。民法通过规范对财产的分配以及规范基于契约产生的义务,通过补偿损害和不当得利造成的损失,从而使一方的自由与另一方的自由相协调。然后在民事诉讼中——正如我们所见,它为(实体)民法服务——国家将执行判决所确定并证立的胜诉方的诉讼请求,从而避免私力救济。这种对私力救济的禁止乃是出于对内在和平的考虑(例外情况除外)。
国家以刑法的方式对极其严重违反共同合意的行为做出反应。因此,刑法是和平的保障。一旦公民之间的和平在个案中无法通过蕴含在实体刑法中的一般预防得到保障,诉讼和刑罚就会随之而来,这表明国家对维护和平是严肃的。刑法首要关涉和平价值;但正是由于其严厉的侵犯特征(Eingriffscharakter)以及相关历史经验,国家也通过以下方式给予自由价值以重视:用制定法的形式尽可能精确地规定刑法构成要件(即罪刑法定原则,nullum crimen sine lege)、对刑事诉讼进行法治塑造、罪责相适应的刑罚以及人道的刑罚执行。
警察法支持制定法的刑罚威慑所产生的预防效果,这使得预防或制止犯罪行为成为可能。刑事诉讼主要是对犯罪发生后导致的和平紊乱作出镇压性反应,但警察法是维护和平的工具。除了民法上的利益平衡之外,行政法还关心社会平衡。对公共和私人利益进行保护的可能性有多种多样。它们的范围从经典的警察与治安法到公共财产法(öffentliches Sachenrecht),再到受福利国家影响的社会法和税法。
保护自由的重要工具是:对公权力的各项权能进行普遍、精致的法治塑造(rechtsstaatlicheDurchformung);立法者同样受到他们制定的法律的约束,直到他重新修改这些法律;权力的分立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基本限制。(33)Vg1.dazu grundsätzlich z.B.Hartmut Schiedermair, Das Phänomen der Macht und die Idee des Rechts bei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970, S.322, 333 ff.; 针对联邦共和国的具体法律制度所作的基础性论述参见Ulrich Scheuner, Die neuere Entwicklung des Rechtsstaats in Deutschland(1960), in: Forsthoff(Hrsg.), Rechtsstaatlichkeit und Sozialstaatlichkeit, 1968, S.461, 488; 作为来自实证主义时代的声音参见Gaston Jeze,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administratif, 1904, S.17 f.与之相对应的是相对于国家权力的个人基本权利的效力、受独立法官予以法律保护的诉求或对专制的公权力的前合宪性(vorverfassungsmäßig)反抗权。(34)In diesem Zusammenhang vgl.Léon Duguit, L’Etat, le droie objectif et la loi positive, 1901, S.316.通过观察现代基本权利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随着1776年和1789年的多个宣言的颁布,这些基本权利进入法律制度。这表明,在此之前,尤其是在西班牙晚期经院哲学中,对国家权力之绝对与相对界限的设置源自人的个体性与社会性,而且人的自由价值也由此得以实现。(35)Heribert Franz Köck, Der Beitrag der Schule von Salamanca zur Entwicklung der Lehre von den Grundrechten, 1987, S.55 ff.与此相应,在英格兰,根据中世纪的模式,王室及其仆从通过法律上的行为(Rechtsakte)明确地将其自身置于法律之下;(36)关于“法律高于国王”的相关论述参见George B. Adams/Robert L. Schnyler,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London 1938, S.311 ff., 359, Stein/Shand, Legal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1974, S.5, 13.今天,制定法只能按照法治原则被解释和适用,在这个意义上,该原则对英国议会主权起到了纠偏作用。(37)P. Craig, Administrative Law, London 1983, S.29 ff.unter Berufung auf Dicey; H. W. R. Wade, Administrative Law, 5th ed., Oxford 1982, S.38 f.
迄今为止的经验研究结果可以通过参考关于制宪权的学说得到证实。制宪权是前合宪性权力,它本身在实证的法律的意义上是无法建构的(konstituierbar)。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内容上完全不受限制。这些限制来自历史经验,它们作为合法性的标准不应被低估。(38)Peter Badura, Verfassung, Staat, Gesellschaft, in: Starck(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und Grundgesetz, Bd.II, 1976, S.1,9.在与那些针对制宪权的机构与程序而逐渐形成的基本原则的内在联系中,存在制宪权所追求的结果,即宪法之内容的标准。(39)v. 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3.Aufl., Bd.I, 1985, Präambel Rdnr.9, 10 m.w.N.宪法的概念已经蕴含了对国家权力进行的某种程序性或实质性限制,否则宪法以及与宪法相关的、对那些权力服从者们所拥有的权利的承认将是多余的。民主国家也必须遵守基本权利及其制度保障中包含的自由价值以及相应地对国家权力的原则性限制,因为在民主国家,所有的国家权力均来自人民,并由人民代表根据多数决原则行使。如果缺失个体权利和对少数群体的保护,多数人统治将不受限制,而且一旦有必要,就会偏离自由的价值,但一开始这可能是难以察觉的。
(二)人类学的基本事实
这里所谈到的在历史发展的意义上作为我们法律之基础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法哲学层面获得证立,以致于法律的价值证立超越历史-实用主义检验(historisch-pragmatischer Bewährung)的事实性,从而能够被用作评价法律秩序的严格标准?
这里对法律的价值证立之必要性问题的讨论并非旨在寻求某种超实证的法律秩序、某种自然法体系或价值体系,因为它们在法律与国家思维的观念史中已被确立,且对实在法产生了显著影响。本文所追求的目标更少也更为基础。(40)hnlich Spaemann, 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Utopie, 1977, S.183 ff.; Steinberger, Konzeption und Grenzen freiheitlicher Demokratie, 1974, S.203 ff., 221 ff.; Luf, Zur Problematik des Wertbegriffe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FS für Verdroß 1980, S.145 f.; Otfried Höffe, Politische Gerechtigkeit, 1987, S.382 ff.
本文以人(Mensch)作为出发点,关于人,我们知道:(41)我对关于人的本性的知识的质疑(vgl.Starck, Das,,Sittengesetz“als Schranke der freien Entfaltung der Persönlichkeit, in: FS für W. Geiger, 1974, S.266, 268 f.)参考了已被深入研究的自然法学说。人在世代相传以及个人的生活史中拥有发展可能性;而且人拥有自我决定能力。我们还知道,用理性科学的手段无法完全理解人;人本身比人对自己所知道的要更多(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人在形而上学层面上是开放的,(42)Walter Schulz, Philosophie in der veränderten Welt, 1972, S.642, auch zum Folgenden; vgl.auch Hans Jonas, Organismus und Freiheit, 1973, S.69 ff.; Steinberger, Konzeption und Grenzen freiheitlicher Demokratie, 1974, S.217; Martin Kriele, Befreiung und politische Aufklärung, 1980, S.53 ff., 250; Christian Starck, Menschenwürde als Verfassungsgarantie im modernen Staat, JZ 1981, S.457, 463.这一点也最终被那些“与所有形而上学作斗争”(43)Th. Geiger, Die Gesellschaft zwischen Pathos und Nüchternheit, 1960, S.190 ff.; H. L. A. Hart, Der Begriff des Rechts, 1973, S.256 ff., 259; Ota Weinberger, Über schwache Naturrechtslehren, FS für A.Verdroß, 1980, S.321, 336.的学者所承认。比如哈特意图“将基本真理……从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用更简单的表达方式重新表述它们”。瓦尔特·舒尔茨(Walter Schulz)恰当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伦理学已经明白,人涉猎(übergreifen)了所有的科学知识,包括人自己在科学中的定位。但这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是人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历史承担责任的前提。
并非所有人都在同等程度上——尤其不是在所有年龄段和所有情况下——被赋予了自我决定能力;然而,对于将自由视为每个法律秩序都必须具备的基本价值而言,这已经足够了。自由的价值特征作为法律秩序之基础,必须与自由的价值指向性(Wertgerichtetheit der Freiheit)严格区分,(44)Böckenförde用建立在价值哲学基础之上的自由价值取向,作为反对法律的价值证立之论据(Böckenförde, Kritik der Wertbegründung des Rechts, in: Festschrift für Spaemann, 1987, S.18); vgl.v. 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3.Aufl., Bd.I, 1985, Art 1 Rdnr.129.根据后者,只有有价值的自由活动才能得到保护。而忽视或打击人的自我决定能力的法律秩序会与人的本性发生冲突。
以上命题并没有将人的本性宣称为法律渊源。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学的基本事实起着价值设定之参照点(Bezugspunkt)的作用,该参照点又成为了塑造法律的标准与界限。就人的自我决定能力而言,如果一种法律秩序会导致人完全地或在很大程度上为外部所决定,则禁止塑造这种法律秩序。这样的法律秩序将会是极其矛盾的,因为它必须赋予个别的人(即统治者)以更高程度的自我决定,由此其他人将为外部所决定。诚然,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进行统治,但它不能证立以下观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人并赋予他们统治权,就准许这些人对其他人进行不受控制的、全面的外部决定。如果人们不想将纯粹的犬儒主义(Zynismus)提升为法哲学的最高原则,那么行使权力的这一单纯事实就不足以作为证立理由。
人们仅仅拥有自我决定能力,尚不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冲突。可是人们一旦开始行动,自由之间的冲突就可能出现。这使我们想到一个问题:一个人的自由如何与另一个人的自由相一致?我们从哪里可以获得限制自由以保证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标准?
在哲学中,人们试图在没有外部决定的情况下,对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条件予以证立,其途径是:自治意志摆脱了感官冲动与自然律的因果性,进行自我立法,即根据那个能够同时作为一条普遍法则的准则去行动。(45)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1798), hrsg.von Vorländer, 4.Aufl.1922, Einleitung, S.22.于是,进行非外部决定的理性行动时,一方的自由与另一方的自由实现了平衡。康德(Kant)从定言命令式(kategorischer Imperativ,一译绝对命令)中推出了法律的概念:“[法律是]以下条件的总合,据此,一个人的决意(Willkür)能够依据一项普遍的自由法则与任何其他人的决意相一致。”(46)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1798), Rechtslehre, Einleitung § B, S.34, 35.康德认为,自由只有在立法者制定普遍性规则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对所有人以及所有人对每个人都做出同样的决定。(47)Kant, Metaphysik der Sitten(1798), Rechtslehre, § 46.卢梭(Rousseau)提出的上述命题在康德那里具有原则上的重要性,因为意志自治是先天的,它先于所有的经验存在。
黑格尔(Hegel)已经看到,定言命令式以传统自然法中遗留下来的实质内涵为前提。(48)Hegel, Über die wissenschaftlichen Behandlungsarten des Naturrechts, Sämtliche Werke, hrsg.von Glockner, Bd.1, S.444 f.信仰犯(Überzeugungstäter)并不违背定言命令式,正如盗贼普遍地或者鉴于特别的表现形式(Erscheinungsformen)不承认所有权一样。然而,如果有几个相互矛盾的理性法则同时有效,那和平(Friedlichkeit)就不能以定言命令式所确立的方式获得证立。如果寻找其他更强的法哲学理由来支持某种关于保障自由行动之共同合意的较弱命题,那就必须事先弄清要走的路,以免误入歧途。歧途之一是那种以实现零统治(Herrschaftslosigkeit)为目标的观念,它认为法律不再需要确定自由的界限,甚至法律本身都是完全多余的。随之出现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强者对弱者的统治,是一种向自然状态的倒退。不过诉诸当时有效的法律秩序作为对和平的保障,即法律实证主义,也是一条歧途,因为自由会因此受到质疑。这一立场的荒谬之处尤其需要强调,因为基本法中包含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近代宪法学说的大部分成果,从而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即法律实证主义者是无害的。这里讨论的是,如何在自由行动的共同合意的意义上,以一种超越实证主义立场的方式获得和平这一基本价值。
个人的行动自由可能会与行动自由甚至与他人的存在之间发生冲突。个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正如行动自由——属于人的存在条件(condicio humana),因为被赋予自我决定能力的人可能会与他们的行动发生冲突。假定人不意欲成为另一个人的受害者,(49)Höffe, Politische Gerechtigkeit, 1987, S.384 f.那么可以推出:个人的行动自由在同胞性(Mitmenschlichkeit)中发现了其先天的限制,这是任何法律秩序都无法绕过的(50)在这个意义上,Geiger谈到社会的相互依赖,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Th. Geiger, Die Gesellschaft zwischen Pathos und Nüchternheit, 1960, S.154)。另一个人类学的基本事实。(51)So Ronald Dworkin, Bürgerrechte ernstgenommen, 1984, S.19; Luf, Zur Problematik des Wertbegriffes in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FS für Verdroß 1980, S.145 f.这意味着行动的自由必须考虑人类同胞,至少必须考虑同时代的人类同胞。因为人类同胞的行动自由也要求彼此的行动相互让步,以此作为维护各自自由的基础。正因为考虑了同时代人,法律所依据的和平价值得以实现;当然,和平价值的实现还需要进一步的由具体的法律秩序所决定的法律手段(正如上面所解释的)。(52)Starck, Frieden als Staatsziel, in: FS für Carstens, 1984, S.867.然而,这些法律手段会受到来自法哲学的批评,尤其是考虑到自由的价值时。
是否存在其他为每个法律秩序所预先规定的直接来自人的存在条件的基本价值?举个例子:幼儿的无助与对孩子的保护需求不仅仅是基本同胞性的表现,也是对人类生存其间的自然条件的提醒,(53)Hans Jonas, Das Prinzip Verantwortung, 1979, S.234 ff.以及对关怀的直接呼吁——就此而言,关怀是每个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
对幼儿的关怀是人类得以延续的条件;此外,我们可能还会问,对成年人的关怀是否也是所有法律秩序先天地应当包含的基本价值?即使保持在共同合意的框架内,人们的行动自由也总是会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天赋、兴趣以及勤奋程度都不尽相同。人们在行动或等待时,运气和时机的青睐也有所不同。人与人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似乎完全能够在人类学上得到证立,因此不能将对这种不平等的废除或削弱宣称为所有法律秩序的先天标准。
如果历史向我们表明,重大的事实不平等会发展为有规律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会让人感到不公正,然后威胁到内心的平静),那么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平衡一再地在过去或未来被设定为法律价值,且今天它也被视为现代国家的永久任务。(54)Dazu Starck, Frieden als Staatsziel, in: FS für Carstens, 1984, S.873.还有很多支持社会平衡的其他理由。然而,社会平衡不能被评定为一种必然产生于人类学的基本事实的价值。
在本文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已经通过例证明确了那些在历史上被证明了的价值,这些价值但绝非所有价值都是法律秩序的基础。从严格意义上讲,一个法律秩序是否回溯到那些在历史上被证明了的价值,并尝试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去实现它们,完全是一个合目的性问题(Zweckmäßigkeitsfrage)。
在人类学的基本事实中能找到参照点的那些基本评价,包含对每个法律秩序都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标准。由于人有自我决定的天赋,因此人对自由有着某种原始的诉求;同时,从共同合意的角度来看,为了人类同胞同等的自由,这种对自由的诉求是受到限制的。
三、关于价值对于司法裁判的重要性
价值作为法律秩序的基础是如何在法律中做出决定的?首先是在宪法和制定法中。制宪者和立法者回溯到那些早先在法律中已经得到表达的或已经存在于社会中的评价,抑或他们自己做出全新评价。跨越时空的根本价值通常都十分笼统(allgemein),从而为法律中的具体化保留了很多的塑造自由。这一点更适用于那些考虑到人类学之基础给定性的价值。实在法中的必要的具体化无法从价值中推导出来;相反,这种具体化需要考虑的因素更为广泛,即它需要对来自于历史情境中的各种因素以及其他价值判断进行额外考虑。(55)Larenz, Richtiges Recht, 1979, S.42.法律秩序并未在积极的意义上对其所依据的价值作出详细规定。这些价值只是在一种消极的排除的意义上,决定法律秩序不得如何进行规制。
2018年10月2日凌晨5时30分许,范某某在他提前部下的网具上收鸟时,被蹲守在山上的民警当场抓获,其违法猎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3只(2只存活,已放生),省重点保护动物5只。
由于被制宪者或立法者所承认的价值或实施的评价是通过解释的方式从法律中被提取出来的,价值总是以一种被裁剪过的、特殊的、具体的形式出现。例如,法律被修改后依然保留相同的评价。
价值确定的位阶(Hierarchie der Wertfestlegung)与法律渊源的位阶相适应。在承认宪法优先(56)Christian Starck, Vorrang der Verfassung und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Starck/Weber(Hrsg.), Verfassungsgerichtsbarkeit in Westeuropa, Bd.I, 1986, S.13 ff.的州中,立法者的评价必须保持在宪法的框架内,并借此保持在宪法所依据的价值框架内;而不能认为立法机关只须保持在宪法所依据的价值框架内,这种错误认识将导致立法者失去与宪法以及与根据宪法进行的特殊的价值具体化的联系。立法者将取代制宪者,并绕过现行宪法去自己实施价值具体化。
相应地,这也取决于判例与制定法以及宪法之间的关系。(57)Starck, Die Bindung des Richters an Gesetz und Verfassung, VVDStRL 34, 1976, S.43, 64 ff.法官受制定法约束。通过制定法表达的价值实现的方式和方法对法官有约束力,(58)Winkler, Wertbetrachtung im Recht und ihre Grenzen, 1969, S.51.因为未公开的条款、对法律续造的需求或具体案件中出现的法律矛盾,都使得法官必然诉诸立法者的评价(目的解释)。法官对正在适用的规则的目的之直接渗透(Durchgriff),使得他们也参与了法律的塑造,但这必须以法律的评价为基础,并在宪法框架内进行。
任何一个法律规范都以评价为基础,即每个道义逻辑语句都是在价值论层面上获得证立的。这种奠基关系对于理解、解释和适用法律规范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一个法律规范脱离了它的价值锚定,就会徘徊不定,并很快找到一个新的锚定,再从那里获得一个新的道义逻辑命题,即成为一个不同的法律规范。举几个例子: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评价嫁接到1933年之前的部分法律;对东欧国家的战后宪法进行社会主义式的重新锚定;反过来,也可以想象东欧新宪法中所包含的“基本权利”重新获得防御性权利的意义。当然,这须以全面的重新评价为前提。
联邦宪法法院对作为宪法基础的价值的引用经常受到批评。我在其他地方也表达过我的批评;但在这里,我想将自己的论述限制在以下方面:我将试图阐明,在某些类型的裁判中,价值术语并不构成对公认的解释原则的侵犯,从而为联邦宪法法院辩护。
1.在社会主义帝国党判决(SRP-Urteil)和德国共产党判决(KPD-Urteil)中,以下观点首次获得了表达,即基本法并不意图成为价值中立的秩序;(59)BVerfGE 2, 1, 12; 5, 85, 139; vgl.auch 6, 32, 40; 7, 198, 205.根据上文所述,只要尚未表明基本价值的内容,这个观点就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完全中立的法律秩序是一种幻觉。与立法者一样,当制宪者在制定法律规范时——这些规范无论如何应当具有某种意义——都必须实施特定评价,亦即追求目的。只不过这种理所当然不应该在裁判中明确表达出来。
相反,法院以某种特定价值秩序或者说基本法的某种价值体系为出发点,该体系的特征进一步表现在:“其核心在于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的人之人格及其尊严”(60)BVerfGE 7, 198, 205.。在社会主义帝国党判决中,法官援引了基本法所包含的宪法-政治决定(verfassungspolitische Entscheidung)——据此,“人在神造秩序中拥有自身独立的价值”,该决定反对极权国家(totaler Staat)所依据的评价。(61)BVerfGE 2, 1, 12.在德国共产党判决中,这一宪政决定“被置于自由的法治的民主制的伟大宪法历史发展中”,(62)BVerfGE 5, 85, 134.其价值体系——详细参考《基本法》文本——的特征表现为:它呈现出“对所有政治观点之宽容原则与对国家秩序的某些不可侵犯的基本价值之信念的某种综合”(63)BVerfGE 5, 85, 139.,尤其要将人的尊严和人对自己生活负责的能力考虑在内。(64)BVerfGE 5, 85, 204.,由此可以看到,联邦宪法法院在基本法中所表达的观点与文章开头引用的托马的观点之间的距离。
当联邦宪法法院将这种价值秩序或(65)BVerfGE 7, 198, 205.受价值约束的秩序(66)BVerfGE 6, 32, 40.——这种秩序由基本法所“确立”——称为某种客观秩序时,它显然无法与哲学的客观价值说挂钩;因为根据后者根本不存在任何有意(willentlich)去确立的东西,而只存在需要观察的东西。相反,“客观”一词与主观相对立,因为基本权利,正如联邦宪法法院反复论证的那样,主要是主观的防御性权利,它们通过自身的客观面向强化了它们的有效性(Geltungskraft)。(67)Vgl.z.B.BVerfGE 50, 290, 337.与价值秩序相关联的“客观”这一属性稍后在下文将作为基本权利规范的属性出现。(68)So in BVerfGE 7, 198, 205.这只是对基本权利的特征进行了刻画,而没有诉诸价值哲学。
2.基本权利的客观法特征源于价值秩序的观念,这一特征被联邦宪法法院所援引,作为该秩序影响私法(EinwirkungindasPrivatrecht)的出发点。基本权利之价值秩序的核心在于社会共同体中自由发展之人的人格及其尊严,这必须作为基本决定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因此也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民法;(69)BVerfGE 7, 198, 205.也就是说,民法的那些规定(Vorschriften)——出于公共福祉的考量——也应当对个体之间法律关系的形成具有约束力,并因此剥夺了私人意志的统治地位。根据其目的,这些民法规定与为它们提供补充的公法密切相关。(70)BVerfGE 7,198, 206.
以上论证也并非旨在将哲学的价值学说在法学中予以应用,而是将宪法的优先地位或基本权利的直接约束力延伸到私法中那些需要更精确定义的部分。如果将那些用来评价人们行为的、建立在法外标准(如“善良风俗”)之上的一般条款,描述为基本权利“入侵”民法,将导致宪法与私法所依据的评价相一致(Wertungsgleichklang)。但这始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些构成基本权利基础的评价可以适用于私法关系。对此我们不作更详细的讨论。(71)Vgl.v. 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3.Aufl., Bd.I, 1985, Art.1 Rdnr.191 ff.; Alexy, Theorie der Grundrechte, 1985, S.475 ff.
3.如果我们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中考虑基本权利之客观法面向的另一个功能,则可以证实上述内容。因此,联邦宪法法院运用基本权利的价值秩序进行论证,以证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EinschränkungvonGrundrechten),这些限制并非明确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
在关于《禁止联络法》(Kontaktsperregesetz)的决议中,联邦宪法法院总结道:(72)BVerfGE 49, 24, 55 f.
“基本法并不是简单地禁止国家以牺牲其他法益为代价来维护受宪法保护的法益,因为那些法益的存在也为宪法所保障,无论它们是基本权利还是其他受宪法保护的利益。这种权衡在宪法上是无法证明的,否则国家机关将再也无法按照基本法与合宪性秩序妥善履行其职责。根据联邦宪法法院的一贯判例,必须假定合宪性秩序构成了某种意义整体,必须根据基本法的价值秩序并兼顾该价值体系的统一性,进而解决受宪法保护的利益之间的冲突(BVerfGE 28, 243[261]; 30, 1[19]; 30, 173[193]; 34.269[287]; 35.202[225])。在该框架内,不受限制的基本权利也会受到限制(BVerfGE 28, 243[261]; 30, 173[193]);因为受价值约束的秩序不会承认绝对无限的权利(BVerwGE 49, 202[209])。”
“基本法的价值秩序”是体系解释的主题(Topos),借助该秩序可以解决具体的冲突。以上所引段落的最后一句话,即“受价值约束的秩序不会承认绝对无限的权利”,毫无疑问来源于这种观点,即权利会触及他人领域,这种权利的冲突刚好是裁判所处理的问题。因此,这里只涉及限制权利的教义学推论。为此,与上述所有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相类比——回溯到在其他基本权利中所表达的评价(即受保护的法益)——基本权利教义学并不会将其交付与某种难以捉摸的价值学说,而是通过论证的方式与成文宪法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3)v. 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3.Aufl., Bd.I, 1985, Art.1 Rdnr.176 f.即与其他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相类比,尤其是与《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的三项限制(74)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权受到三项限制:不得侵害他人权利,不得违反宪法秩序或道德规范。——译者注相类比来说。
在后续裁判中,联邦宪法法院避免使用“价值秩序”与“价值体系”这种表述方式,而以宪法统一性取而代之;(75)Vgl.z.B.BVerfGE 34, 165, 183; 55, 274, 300.除非同时使用这两种表述方式。(76)BVerfGE 19, 206, 220; 28, 243, 261; 30, 1, 20; 30, 173, 193; 47, 327, 369.基本上,这里只涉及宪法内部的推论(verfassungsimmanente Ableitung),即从作为客观规范的其他基本权利以及其他表达法律价值的宪法规范中推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对“价值秩序”或“法律价值”这种表述方式的使用——无论在肯定还是否定意义上——不会影响论证的正确性。该正确性取决于在具体的个案冲突中是如何进行论证的。(77)例如,成功平衡了积极的宗教实践与沉默二者之间关系的判决参见BVerfGE 52, 223, 247; zum Problem ferner v.Mangoldt/Klein/Starck, Das Bonner Grundgesetz, 3.Aufl., Bd.I, 1985, Art.1 Rdnr.129.
4.此外,价值秩序概念也被用于决定是否允许法官进行法律续造(richterlicheRechtsfortbildung)。法律的续造必须与基本法相一致,(78)BVerfGE 34, 269, 286 ff.; 38, 386, 396; 49, 304, 318 f.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是否允许参照“新宪法的价值观念”(79)BVerfGE 34, 269, 290.进行违背制定法的(contra legem)法律续造;抑或,鉴于基本法所确立的功能秩序,法官在以上案件中是否满足于仅宣布制定法规范无效或不予适用,而必须等待立法者作出新的规定。由于保护自由人格的价值存在多种法律可能性,法官不得自行作出普遍性决定。这些决定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是否使用了价值术语,而在于它们通过诉诸基本法去作出违背制定法的裁判。
上述例子表明,价值秩序的思想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判例中具有极为不同的功能。这一思想表明,基本法以特定评价为依据;在对个别基本权利规范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这些评价。对基本法所进行的不同解释大多基于基本法的发生史(Entstehungsgeschichte),并为基本法文本与体系所证实。这些解释要素也经常通过论证被接受,或者被先前裁判所引用。以下命题或值期待,即基于自我负责的人的人格(selbstverantwortlichemenschlichePerson)这一价值观念,人的自由应当受到保护,国家权力应当被予以原则上的限制。
当我们摆脱以下观念,即价值术语必然来自价值哲学、且只能在其框架内被理解,转而在价值术语的语境中更详细地分析论据,便经常可以找到严肃且可理解的裁判理由(Entscheidungsgründe)。
顺便说一句,即使联邦宪法法院没有使用价值术语,它们给出的裁判理由也并非都是成功的。当然,假如不使用价值术语将丝毫无损于论证,我们大可始终避免使用它们。然而,此处对借由价值概念予以限定的事项(Sache),值得做一番彻底处理,以便提醒我们记住那些我们法律中所蕴含的价值基础,并将其传达给年轻一代。(80)Dazu deutlich Stein/Shand, Legal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 1974, S.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