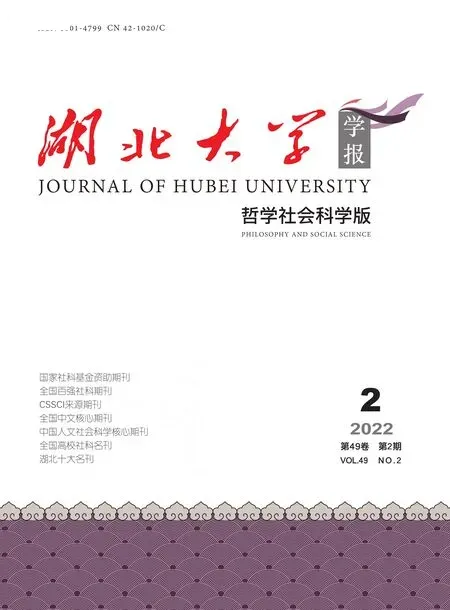论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自由思想
朱松峰, 邓 欢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黑格尔曾经说过:“没有任何思想像自由思想这样被公认为不确定、模糊和易于遭受最大误解的了。”(1)G.W.F.Hegel,Philosophy of Mind,tranlated by W. Wallance & A. V. Miller,Oxford:Calrendon Press,2002,p.215.这句话尤其适用于人们对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的理解状况。虽然人们早已知道在他那里,尤其是在他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折时期,“自由”这个术语不但常常被谈起,而且在其“真理的本质是自由”这一断言里意味深长,但是由于通常人们不加辨析地把存在问题看作海德格尔终生的唯一问题,由于海德格尔自己的纳粹经历及其独白式的言说方式,虽然关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二手研究文献已经不胜枚举,可是相对于其思想的其他方面而言,他的自由思想依然可能遭受着最大的误解。比如,弗兰克·沙洛(Frank Schalow)就曾指出:“在海德格尔那里,没有其他概念比自由概念更加模糊了。”(2)Frank Schalow,The Renewal of the Kant-Heidegger Dialogue,Albany: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2,p.267.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甚至愤而直言:海德格尔不能理解自由概念,因而他关于自由的谈论仅仅是“哲学上的伪饰”,根本不是对人来说自由是什么及其条件的严肃反思(3)Richard Wolin,Politics of Being: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Heidegg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0,pp.153-157.。在这种情形之下,当把“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作为主题来讨论的时候,很多人依然会感到惊讶和不解,甚至是反感和蔑视。
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早在1967年,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J. Richardson)就已洞见到:“存在问题带着海德格尔一再地在路上探索自由的观念,所以在这一方面考察他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扭曲。”(4)William J.Richardson,“Heidegger and the Quest of Freedom”,Theological Studies,Vol.28,No.2,1967.著名的海德格尔研究专家弗雷德·达梅尔(Fred Dallmayr)则进一步指明:海德格尔的思想“从最早到最后的著述都弥贯着把握‘自由’范畴的努力”(5)Fred Dallmayr,“Ontology of Freedom:Heidegger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Political Theory,Vol.12,No.2,1984.。理查德森和达梅尔的判断尤其适用于海德格尔的马堡时期(1923—1928),因为在这一时期最后的讲座(即1928年夏季学期的课程《从莱布尼兹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自由问题甚至取代存在问题成了基础问题,一种“自由存在论”的建构被提上了日程。不过,海德格尔思想的这一变化并非无源之水或随意而发。实际上不但学生时期的海德格尔就是以反自由主义的形象登上学术舞台的,自由问题一开始就是他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6)参见朱松峰:《论海德格尔学生时期的“自由”思想》,《社会科学》2020年第4期。,而且在其马堡时期,自由问题一开始就成了其讲座课程的专题性讨论对象。本文就试图专题分析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7)从1923/24年冬季学期到1928年夏季学期,海德格尔在马堡大学执教。本文将他从1923/24年冬季学期到1924/25年冬季学期的这段时期称作他“马堡时期的初期”。的自由思想,一方面展示他这一时期的自由思想与其此前和此后的自由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展示他这一时期的自由思想与他的其他重要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呈现出自由思想对于海德格尔的“存在问题”及其整条思路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于他突破西方传统的自由思想从而突破整个西方哲学传统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现象学研究导论》中的自由思想
受聘到马堡大学之后,海德格尔举办的第一个讲座是1923/24年冬季学期的《现象学研究导论》。在这个讲座中,他的思想悄悄地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自由问题第一次成了专题性讨论的对象。
在该讲座的前言中,海德格尔告诫学生们:讲座不会提供基础、规划或体系,甚至不会提供哲学,因为它给自己设定的全新任务与传统哲学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讲座不需要以对哲学观念的熟识为前提,它所需要的前提是真正而恰切地追问的激情(Leidenschaft)。但是,这“激情”不是任意地发生的,而是有其时间和节律。所以,激情必须有准备(Bereitschaft)。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摆脱(frei)偏见,因为要求没有偏见的想法本身就是最大的偏见,是一种乌托邦。激情需要的不是摆脱偏见,而是“对于如下的可能性成为自由的:基于与事情(Sache)的争执(Auseinandersetzung),在关键时刻放弃偏见”(8)Mari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4,S.2.。这意味着为追问的激情所做的准备在于生存的某种成熟,即常年经受不稳靠的状态,能够自由地拒斥任何过早的答案。为此,“必须松脱(frei machen)曾真实地存在于古希腊哲学之中的传统,即作为理论之科学的关联行止(Verhalten)”(9)Mari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3.。
根据海德格尔的上述阐释,“自由”是一种追问的激情和准备状态,但不是准备着摆脱所有的偏见,而是准备着经受与“事情”之间的不断争执,而这就是真正的哲学。而且,根据该讲座的前言,此时他显然已是有意识地从突破西方哲学传统的角度来提出他的自由思想。换句话说,当海德格尔在马堡时期第一个讲座中专题性地讨论自由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把自由问题作为一个偶然的、临时性的话题,而是一开始就明确地将之纳入了其解构存在论历史的宏大任务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海德格尔这里所提出的自由思想对于传统的西方自由思想很大程度上已是突破性的:它与主体对客体的任意选择和操控或摆脱无关,与原因和结果以及二者的关系无关,它离不开人但又不完全取决于人,而是从根底上关乎一个超出了人的意志而又离不开人的维度,从而突破了主客二元分立的理论立场和姿态,突破了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必然与偶然、相对与绝对、自由与命运之间二元对立的框架,突破了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基础主义、本质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由的理解,突破了奠基于个体主义和意志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海德格尔此后的自由思想都是走在这个突破的道路上,而且它与海德格尔其他主要概念之间的关联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
基于对自由哲学或哲学自由的上述理解,在该讲座的第一部分中,海德格尔讨论了亚里士多德对逻各斯的规定,从而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其自由思想。其中的关键在于他引证了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相对立的如下观点:“言说……根据其本真的存在,生自人的自由估量(frei Ermessen)”(10)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8.。所以,亚里士多德把逻各斯看作人的一种存在可能性,从而把生活看作具有特定可能性的能在,即:可能性的能在(Möglichsein)。海德格尔指出:在这种言说中,世界的存在从根本上得到指引,就其自身而得到把握,从而给出来拥有世界的可能性,即它自身有通达和葆真的可能性,但同时欺骗和假象即“自由漂浮的(freischwebend)言说”的可能性就一同在了(11)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33-34.。简而言之,欺骗和假象的可能性在于人或此在(Dasein)在世界之中的自由存在。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与真理根本相关。
但是,海德格尔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古希腊人那里一个演变过程就已经开始了,这个过程是由这样一种理念的优先性引导着的,这种理念关乎确定性和明证性,是空洞的、幻想的。这种理念的优先性支配着如下可能性的所有自由给予(Freigabe)(12)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43. 海德格尔给“自由给予(Freigabe)”加了着重号,其含义有释放、松脱等。本文这里突显其字面意,故将之译为“自由给予”。:遭遇哲学的本真事情。因此,在后来的哲学对意识和认知的操心中,被研究的是把握存在者的方式,而不是自由地被给予的从存在者自身那里遭遇存在者的方式,从而“对于事情自身不够自由”(13)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59.。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明确地指出:胡塞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把有效性的意义和实在的、时间性的意义从形式上纯粹地对立起来,因而“这种批判是完全不自由的”(14)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96.;胡塞尔对于普遍约束性的操心,使得“面向事情自身”的自明吁求对于如下的更加根本的可能性置之不理:“如此自由地给出存在者”,以至于只有被追问的存在者才决定了哲学的初始对象,而“只有这种从事情之自由给予而来的决断才首先实现了认知的真正意义”(15)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02.海德格尔给“如此自由地给出存在者(das Seiende so frei zu geben)”加了着重号。。在海德格尔看来,寻求确定答案的追问不是本真的追问。本真的追问会把自身带向一个存在者本身。生存、此在这种存在者在做着追问的时候,同时也规定着被追问的对象的存在,反之亦然。在这种特殊的意义上,答案消失了,它转变成了追问,“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得通往存在者的道路变得自由敞开了(freimachen)”(16)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76.。在这个意义上,怀疑主义反而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远眺到了不稳靠的此在。海德格尔这里的意思很明确:胡塞尔那奠基于绝对理性主义之上的第一哲学是不自由的,即不能让其现象学的现象自由地被给出来。
一方面,海德格尔此处的自由思想乃是承上而来:对“准备”和“追问”意义上的自由的理解,显然是从他早期弗莱堡时期(1919—1923)对期待基督再临意义上的本真自由的阐释而来,“自由给予”与“委弃、献身(Hingabe)”之间显然是内在统一的;把自由理解为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并把哲学理解为此在自身的一种本真样式,与其早期弗莱堡时期对“在自身之中并为了自身的(即自由的)实际生活经验”的阐释也是一脉相承的;把自由等同于此在的不稳定性,与早期弗莱堡时期所阐释的实际生活经验的两个基本特征之一,即“动荡”(Bewegtheit),是完全一致的;把自由与真理(从而与虚假和错误)、自由与存在内在地关联在一起,把本真的自由与“自由漂浮”意义上的自由对立起来,也是海德格尔一贯的思路。另一方面,海德格尔此处的自由思想也取得了不同以往的重要突破:他第一次把自由与追问的“事情自身”关联起来,将之理解为与事情的“争执”;他第一次把“自由”作为引导性的视点和线索,把“本真的自由”作为标尺,来审视和衡量在他之前的哲学;他此处把自由规定为一种真正而恰切地追问的“激情”,而在早先他把“激情”归给了漂浮无据的虚假自由。比如,在1909年11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万灵氛围》中,海德格尔就谴责现代人虽然“还在口口声声地谈论自由”,但是他们的自由是一种随波追流、漂浮无据的自由,毫无疑问地将冲动的激情当作了生活的法则(17)阿尔弗雷德·登克尔、汉斯-赫尔穆特·甘德、霍尔格·察博罗夫斯基主编:《海德格尔与其思想的开端》,靳希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0-12页。。在1910年3月发表的《由死向生(对约尔根森〈生命谎言与生命真理〉的思考)》一文中,他批判“个体主义”、肉体之意志意义上的自由所意愿的是情绪和激情,这种“真理”事实上乃是一种“虚假的生命准则”(18)Martin Heidegger,Reden und andere Zeugnisse eines Lebensweg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0,S.4-5.。
当然,无论是“承上”还是“突破”都显示了海德格尔此时的自由思想在更大的程度上、更深刻地超越了传统的自由思想,并启示着他接下来的自由思路。比如,他此处的自由思想通往《存在与时间》中为本真去死的可能性而敞开意义上的自由,也通往他后期所谓的期待最后一神和天命(Geschick)之转变意义上的自由。事实上,无论是海德格尔谈论的“真正的哲学”,还是他所谓的“本真的思”,这种追问、争执、承受、敞开、放弃意义上的自由自始至终都是其关键因素和标志。也正因此,在《存在与时间》“失败”之后,他在其思想“转折”时期才会也才能把自由问题作为其寻求新的“道路”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海德格尔1923/24年冬季学期讲座的第二部分追溯了笛卡尔和决定着笛卡尔的中世纪存在论,在其中他上述的突破了西方传统的自由思想和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突显和贯彻。海德格尔指出:对于“现象学”这个术语及其所标示的东西的刻画并不以一个先行被给予的学科为导向,相反恰恰是要离开学科而走向一个特殊的现象关联:此在。他称此为“为了此在自身而摆脱学科成为自由的”,它意味着抓住如下的可能性:让此在自身成为由此在自身所决定的一种研究的主题。而这研究无非就是此在自身的一个可能性(19)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12.海德格尔给“为了此在自身而摆脱学科成为自由的(Freiwerden von der Disziplin für Dasein Selbst)”加了着重号。。也就是说,海德格尔的研究目的是让研究和此在自身都成为自由的。因为,真正的研究本身就是此在的自由实现自身的一种本真方式。
“对于此在成为自由的”这一任务需要通过松脱流传下来的规定存在的可能性和传统方式而实现,因此自由地给出此在自身以及获得对它的解释之任务必然与如下任务结合在一起:动摇、拆解(abbauen)当今处境,因为它由古代的存在论和逻辑学支配着,在存在论上被破坏了。所以,所有对此在的存在论研究都是解构性的。在这一视域之下,海德格尔指出:狄尔泰“就其整个倾向而言根本尚未进入‘自由领域’(Freie)”(20)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13.。不过,海德格尔认为,虽然解构是批判性的,但被批判的不是解构所敞开的过去,而是我们的现在。所以,解构使得过去那真正的、原初的、积极的东西成了可见的,过去首次作为我们真正地曾经拥有并能够在此拥有的东西而成了可见的。于是,“对历史的敬畏(Ehrfurcht)这种东西就产生了,而我们就在这历史中经历着我们自己的“命运”(Schicksal)”(21)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19.。由此可见,当海德格尔把“自由”当作主题来讨论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是明确地将之系缚于其存在问题的,一开始就是将之与对存在论历史的解构关联在一起的。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这里,“解构”作为哲学的方法从根本上也是与自由相关联的,它是自由的此在实现自身的一种方式,从而也就是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历史性的和命运性的。这乃是他的自由思想里面贯穿始终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一个环节:自由即命运。可以说,“命运”乃是理解海德格尔自由思想的关键视角和核心线索。
接下来海德格尔谈及了真理观念的命运。他指出了传统上的五种真理观念,即为真之物、命题、有效性、正确性和价值。真理的这些可能性显示着离本真地构成真理的东西(即在其被揭蔽状态中的存在者自身)越来越远,而这一远离之路是由希腊人开出来的。希腊哲学没有严格地对待真理的原初意义,一开始就把真理带向了命题的确定性。“由此,真理观念此后的命运便不可更改地被决定了”(22)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25.。海德格尔要做的工作则是去追问:何谓生活和此在的真理?这意味着他在真理问题上的突破。《存在与时间》及其后的自由思想表明:真理之命运与自由是内在地根本相关的,存在的真理也即存在的自由。海德格尔在真理观上的突破与他在自由问题上的突破是并驾齐驱的。
基于以上的自由思想,海德格尔在这个讲座中接下来对笛卡尔的自由概念的分析,第一次以专题形式集中对自由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他指出,对于笛卡尔来说,自由的形式存在在于:能够做和不做被置于我们面前的同一件事情构成了自由。因此,笛卡尔心中所想的是自由的一个传统规定,即它可以被标画为不被强迫和决定,即不以某物为特定的目的或方向。他把这种自由规定为绝对的漠然无别(Indifferenz)。
但是,海德格尔认为作为漠然无别的自由实际上是笛卡尔的“自由存在”概念所拒斥的,只不过是为了把他的哲学介绍给他的耶稣会士同事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另一方面,笛卡尔又认为,成为自由的并不只是漠然无别,而是在某个东西被确认或否认、被追索或逃避的意义上,要被理智所提供的东西决定。对于某个确定的东西的这种倾向,而不是漠然无别地掌控着可能性,才是意志所固有的。所以,为了成为自由的,并不要求我能在两个方向上运动,而是我越倾向于一方,我就越自由。漠然无别、形式上的可能性恰恰不是自由,至多是最低级的自由。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后一种意义上的自由概念来自奥古斯丁。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决定是自由的构成性因素,是自由意志的真正存在方式,朝向善的倾向越原初,行动的自由就越本真,一个将自身完全置于上帝意志之下的行为就是绝对自由的(23)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50-151.。
奥古斯丁的自由概念又来自中世纪的神学背景,在那个背景中,自由问题是以恩典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为形式而得到讨论的。对于神学研究来说,“人是自由的”这一事实是不可置疑的,但就意志自由的本质如何被理解而言则是有争议的。当时主要存在着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这两种解释路径。对于亚里士多德主义这种解释路径来说,强迫和决定的缺失对于自由存在来说是必需的。而对于奥古斯丁主义这种解释路径来说,被最高的善决定恰恰是构成性的,只要意志被指向最高的善,它就不是服从于奴役。这两种解释路径今天依然争论不休,上帝之预知与预定就与此争论相关(24)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53.。
吉比厄夫(Gibieuf)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强调了奥古斯丁的自由概念,认为恰恰是“被最高的善决定”构成了人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存在,恩典不可能对自由有害,因为它自身首先创造了真正的自由。后来,莫利纳(Molina)看到,一个人的行动被称作自由的,是因为即使对那行动来说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备好了,他依然可以行动或不行动,或者他在决定一个具体方向的时候,依然能够意识到抓住其他方向的可能性。被漠然无别地置于两种可能性面前乃是这种自由存在的真正意义。当我作出选择的时候,我就不再是自由的了。自由被取消了。真正的自由在于漠然无别状态。莫利纳认为,奥古斯丁却恰恰在被决定状态中看到了人的自由,这自由是在如下的意义上被理解的:自由存在并不意味着顺从于世界的要求和恶魔的诱惑,而是意味着将自己的意志置于上帝的意志之下。海德格尔由此获得的一个洞见是:“漠然无别并不属于自由,虽然它出现在行为之中”(25)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156.。在此,自由与承受、约束、必然性、命运之间根本性的内在关联清楚地呈现了出来。
但是,海德格尔又指出:虽然笛卡尔认为意志是自由的,将自由看作人的一个基本规定,他对自由的这种规定来自作为纯粹行动的上帝的自由,其中蕴含着奥古斯丁主义的因素,但是奥古斯丁对自由的规定又可回溯到古希腊的存在论,因为对人之自由存在的规定是由新柏拉图主义的双重运动理论决定的。所谓“双重运动”即灵魂内在地返回到它所从出之处的运动。借此,笛卡尔才能通过去神化的方式,提出了自己对自由的规定:自由存在意味着在判断中保持朝向清楚明白的知觉的倾向,自由的一般原则是清楚明白的知觉。但是,如果这种自由不被正确运用的话,就会出现错误。因此,错误不是由上帝导致的,而是源自意志自身的自由。在笛卡尔看来,只要人作为认知者而存在,那么作为判断的认知的存在就是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存在具有犯错的可能性,需要原则的引导。这原则就是科学认知的原则,即确定和明白。在怀疑的彻底化、普遍化中,这作为判断的认知的基本特征显现出它的自由是这样的:认知越是持守于作为确定性的真理,怀疑就越是自由,因为不确定被转换成了虚假。笛卡尔最终获得的是一个有效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题。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对确定性的操心就是对“安宁”(Beruhigung)的操心,而这对安宁的操心一开始就阻断了根本性的“存在的不稳靠性”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归根结底,笛卡尔所谓的自由是虚假的。所以,海德格尔说,虽然笛卡尔一开始就把思理解为在其存在中一同拥有自身的独特存在,但是他却将这“一同拥有自身”错置于一个形式存在论的命题之中。笛卡尔的研究倾向一开始的目标根本就不是在如下的意义上提出存在问题:“如此自由地给出(frei geben)其所追问的东西,以至于它从它自己的存在特征那里进行言说”(26)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256.。海德格尔认为,笛卡尔的形式存在论的命题应该形式指引地被理解。根据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对“形式指引”(formal Anzeige)方法的阐释,形式指引就是自由地表达自由的实际生活经验的本真方式,所以他对笛卡尔的这个断言也就意味着笛卡尔的哲学并没有理解和表达真正的自由,从而自身也是不自由的。
显然,海德格尔此处对自由概念所进行的第一次专题式的理论分析,对于其后来的自由思想来说意义重大:虽然他从哲学的基本立场上批判笛卡尔的自由观念是虚假的,但是“自由是被决定的”“自由是艰难困苦的、动荡不安的”是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始终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无论是《存在与时间》中的“向死决断的自由”,还是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应合存在之天命的自由”,也都不是在诸多可能性选项之中进行选择的自由,而恰恰是只有一种选择的“命定的自由”,虽然其间他对“命运”、“天命”(Geschick)的理解发生了变化;虽然后来(尤其是《存在与时间》之后)他很少再直接谈及方法论问题,但是对于理解其自由思想来说,其方法所内蕴的自由意涵必须始终被牢记。不过,意志问题在这个讲座里是成问题地未被专题化的,从而为《存在与时间》中出现“决断论”的苗头埋下了伏笔,也为海德格尔的在其政治事件之前和之后的几年里形成戴维斯(Davis)所谓的“政治意志论”(27)Bret W. Davis,Heidegger and the Will:On the Way to Gelassenheit,Illinoi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7,p.137.开了头,这体现了海德格尔此时自由思想所存在的重要缺陷。
然后,海德格尔关联着笛卡尔再次讨论了胡塞尔。海德格尔指出:笛卡尔对“我思”的研究处于天主教信仰体系的视域之中,其目的是要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而胡塞尔的考察更加根本,他对作为绝对存在的意识的研究为一门绝对理性的科学奠立基础,为人性之完满的、“自由的”发展确立规则,但是老旧的形而上学依然在他的研究中潜在地存在着,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依然试图在把意识的存在看作确定性的意义上把意识确立为核心,而意识的存在却是自由漂浮的。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更加原初地忽略了存在问题,生活没有在其本真的存在中得到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为了达及事情自身,它们必须自由地被给予,而且这自由给予(Freigabe)本身并不是一时的兴起,而是根本性的研究”(28)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275.。这进一步从理论上表明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不自由的。海德格尔的这一讨论启示我们:从自由的角度来把握他对笛卡尔、胡塞尔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乃是一项意义重大且急迫的工作(29)何况,就笛卡尔的哲学来说,自由意志是他通过普遍怀疑这一起点所确立起来的第一个自明的概念;对于胡塞尔的现象学来说,自由观念也是基础性的(Felix Murchadha,“Hegle,Nietzsche,Heidegger:Thinking Freedom and Philosoph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13,No.2,2005)。。
在讲座的最后,海德格尔刻画了对确定性之操心的三个特征:存在的远离,即远离世界的存在,远离此在自身;此在的时间性之缺席,笛卡尔一点儿都没有谈到在生与死之间的时间性伸展;存在的平整化,即把所有的存在都摆在同一个平面上。这表明对确定性的操心是此在在其自身面前的逃离,是此在对它的在一个世界之中存在的被揭示状态(Entdecktheit)的逃离,而它在其面前逃离的东西最终无非就是其“无家可归状态”/“阴森可怖状态”(Unheimlichkeit)。而且,海德格尔在这里看到:无家可归/阴森可怖的状态是此在被揭示状态的可能性条件(30)Martin Heidegger,Einführ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Forschung,S.317.。这些概念,尤其是“时间性”、“被揭示状态”、“无家可归状态”、“阴森可怖状态”的出现,表明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了,也表明他离《存在与时间》中的自由思想越来越近了。
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中的自由思想
海德格尔1924年夏季学期的讲座题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关于这个讲座的目的,海德格尔明确讲道:它毫无哲学目的,它涉及的是对基本概念之概念性的理解,是为进一步解读哲学家做练习。这个讲座对自由概念涉及不多。但是,尽管如此,从哲学理论上来讲,仍有与自由问题相关的如下三点值得关注:
首先,在讨论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中庸”学说的时候,海德格尔将之解释为选择的“时机”(kairos),认为选择以整个的“瞬间”(Augenblick)为导向,持守于中庸无非就是把握瞬间。亚里士多德把觉知(vernehmen)本身界定为一种中庸。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觉知为了其对象而在独特的情境中自由存在(Freisein)”(31)Martin Heidegger,Grundbegriff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002,S.187.黄瑞成的中译本将此处的“自由存在(Freisein)”译为“敞开的存在”(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黄瑞成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209页),而本文的翻译取其字面义。,在这“自由存在”中有一种从两个终点而来的确定的选择定向,而且选择就是“总是-重演”(Immer-Wiederholen),所以此在具有由独特的时间关联所规定的历史性。而且,海德格尔此处还特别地挑选了在周围世界中并没有直接诱因的“怕”,研究了“情感”对于中庸之时机选择的重要意义,认为“情感”并非“灵魂的遭遇”,也不在意识之中,而是人的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的一同裹挟,是“抉择”发生转变的契机(32)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第279页。。在这里,借助亚里士多德之口,自由与时间、历史、情绪之间的内在关联得到了显明。《存在与时间》中在畏的基本情绪中不断重新进行瞬间决断的、有历史从而有命运的自由存在已经呼之欲出了。但是,虽然海德格尔在这里是在讨论《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时候涉及自由问题的,但是其中也显示出了他自由思想中的另一条基本原则:自由并不首先关乎伦理,更不首先关乎政治。这一原则也是很多人不愿讨论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这恐怕也是他为了突破传统的自由思想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其次,在论及亚里士多德的《论动物的运动》的时候,海德格尔指出:科学关乎与事情的恰切关系,这不能强求,而是在最高的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自己,但从根本上来说,事情在何种程度上到来和出现乃是命运的事情(Sache des Schicksal)。所以,虽然存在着诸多的理论,研究者们还是逐渐地被真理自身所迫而去观看存在者。这真理本身就是无蔽(aletheia),它不是依附于命题的有效性,也不是误入歧途的逻辑,而是在其被揭示出来的存在之中的存在者(33)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第270页。。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理就是存在的命运,而人的自由则取决于此命运,从而内蕴着一种主动的被动性。可见,海德格尔此处所谓的“存在”、“真理”、“命运”、“自由”都已突破了其流俗的和传统的含义,它们之间差异化的同一已经初露端倪了。这种差异化的同一乃是他克服西方传统自由思想的关键之所在。这也是他20世纪30年代“思想转折”时期和后期的自由思想所坚持的基本观念,在“自由与命运之间”为人的自由寻觅恰切的所在乃是他在自由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思路。
最后,在根据手稿内容编订的讲稿中,海德格尔指出:讲座的目的是按照其概念性来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基本概念,也就是说追问亚里士多德在运动现象中觉知到了什么?他是否是从原初地得到理解的事情自身出发来获得他的理解的?他是否自由地给出(freigeben)了事情自身?(34)Martin Heidegger,Grundbegriff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S.338. 黄瑞成的中译本将此处的“自由地给出”译为“保持开放”(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第380页)。如此地追问就是从根本上完成科学研究,但这意味着每个人必须自己完成决定性的工作:“根据每个人的职分和位置,对每个人自己通过自由选择而置入科学之中的东西变得警醒”(35)Martin Heidegger,Grundbegriff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phie,S.339.此处的“变得警醒(aufmerksam werden)”海德格尔自己加了着重号,黄瑞成的中译本将之译为“要关注”(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第381页)。。对于这“能够成为警醒的”来说,前提条件是:人立于事情之中。所以,讲座绝不是要接受和应用亚里士多德的概念,不是重述亚里士多德的概念,而是重做(nachmachen)亚里士多德的概念(36)参见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第382页。。可以说,海德格尔的整个讲座无非就是随亚里士多德一起警醒着自由地进行追问,以便自由地给出事情自身,由此海德格尔及其哲学才依据事情而获得了职分和位置,从而实现了自由。这当然也是海德格尔所有哲学追问的根本共同点,也是他批判和标衡以往所有哲学家和哲学观点的最高尺度。当然,“警醒”也是他所有时期的自由思想中贯彻始终的关键内涵之一。哪怕是对于他后期思想中作为本真自由之最终化身的“泰然任之”来说,也是如此。也正因此,“泰然任之”才不是“容易的”、“轻浮的”(leicht),而是“艰难的”、“沉重的”(schwierig)。
三、《柏拉图:〈智者〉》中的自由思想
海德格尔1924/25年冬季学期的讲座课程题为《柏拉图:〈智者〉》。在一开始的“先行考察”部分,他提出要解释柏拉图的对话必须进行双重的准备,首先就是现象学的方法和目的。所谓现象就是在其得以展开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如其自身所显示的那样的存在者,而现象学的最大困难在于:各种现象领域身后都有一个丰富的研究史,“因而我们无法自由地接近这些对象,相反,我们总是已经在各种特定的问题提法(Fragstellungen)和视之方式(Sichtweisen)中看到它们”(37)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熊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0页。。这样,就有了不断地批判和坚持的必要性,而柏拉图的对话尤其适合于进行这样的不断批判和检查。由此可见,对于海德格尔,“现象”作为如其自身地显现自身的对象是自由的,而现象学的方法和目的就是要让自由的现象自由地显现。与此种自由相对立的是理论命题的“自立性”(Freiständigkeit),由之人们处身于闲谈(Gerede)之中,根本不能原初地居有一切(38)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92,S.26. 熊林的中译本将“Freiständigkeit”译为“超然性”(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30页)。虽然“超然性”这个翻译也很好,但是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视域来看,没有体现出这个词字面上含有的“自由”的含义。。这“闲谈”显然是“自由漂浮”意义上的一种虚假自由。正是依据上述的现象学方法,该讲座的“引导部分”首先阐释了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部分内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技艺具有让自己从使用那里松脱(frei machen)出来成为独立自主的知识的倾向。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这种倾向就存在于此在自身之中。也就是说,此在具有揭示存在者的倾向,而且不顾任何用处。独立自主的纯粹揭开只存在于此在摆脱(frei)了对各种必需品的操劳的地方。于是,在“智慧”中就显现出此在的一种可能性:此在“于其中将自己显露为自由的、显露为完全对准自己本身的”(39)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180页。。但是,如果此在偏向于不做这必要之事,摆脱了它的约束,从而“观望变得随便(frei)了”(40)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98. 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frei”也译为自由。从字面上看,这自然没有问题。但是,本文为了区分开海德格尔这里谈到了两种不同的自由,将之译为“随便”。,那么此在就总是停留在感觉之中,即轻浮、自明地在最切近的东西之中进行活动。相反,超出切近之物推进到本真存在的东西那里则是艰难的、沉重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海德格尔把此在揭示存在者的倾向看作是自由,也就是说,自由乃是此在自身的存在方式,这乃是《存在与时间》所谓的生存论/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但另一方面他意识到由于这种自由是艰难的,所以此在总是又有追寻轻松的、不受约束的虚假自由的倾向。这意味着,此在具有不同的存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能被看作空洞概念性的、逻辑的可能性,它不在“随意性”(Beliebigkeit)的意义上是自由的。可能性、潜能是特定的、先行被标划的,总是在自身之中携带着一个方向。因此,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把此在规定为在通往未被遮蔽之物途中的存在,它就是存在着的不(Nicht)(41)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643.。自由与“不”“无”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第一次清楚地显现了出来。这意味着本真的自由在存在者层次上总是无用的。《存在与时间》中此在之“能在”意义上的自由和后期海德格尔所谓的“应和存在之召唤的自由”显然都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可以说,以“无”来观“自由”,乃是他在自由思想上取得的根本性突破。
该讲座的主要部分对柏拉图的《智者篇》进行了阐释,重新聚焦于方法问题,详细阐述了苏格拉底的方法。在对话中,苏格拉底提出来两种方法:如果遇上一位完全自由地对要加以谈论的东西敞开的人,就采取彼此对谈的逻各斯,即辩证法;如果不是这样,就只对自己言说,并以一种长的言谈方式来阐述事情。《智者篇》中的客人则采取了一种混合处理方法:既是对话又具有独白式的风格。海德格尔认为,原因在于事情的难度。在后面的讲座内容中,海德格尔指出:被标划为辩证法的这种知识被柏拉图称为“自由人的知识”、“自由人的科学”,因为它无需一种切近的、可见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独特的自由概念(即无外在目的、只为自身的自由概念)即是来源于此(42)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690-691页。。
由此可见,对于海德格尔来说,一方面“辩证法”原本无非就是自由地敞开所谈论的东西的方法,因此“如果人们要在柏拉图的意义上来理解它的话,就得对历史进程中和今天所赋予它的种种规定保持彻底的自由”(43)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337.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保持自由(freigehalten)”译为“摆脱”(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39页)。,由此我们可以从根本上理解海德格尔对流俗的“辩证法”向来秉持的敌视态度;另一方面无论是对话还是独白都是完全自由地以面对事情为准的,人们不能以其他标准来判断它们是否是自由的,由此我们可以避免如下的误解:海德格尔往往以独白方式表达的晦涩思想本身就是专制的、独裁的,天生就与“自由”无缘,甚至本质上就是“自由”的敌人(44)与海德格尔有着多年思想交往的雅斯贝尔斯就曾断言:“海德格尔的思维方式对我来说本质上是不自由的、专断的和没有交流的”(Martin Heidegger,Karl Jaspers,The Heidegger-Jaspers Correspondence(1920—1963),Edited by Walter Biemel and Hans Saner,Translated by Gary E. Aylesworth,New York:Humanity Books,2003,p.210)。。
上述的对事情自身完全自由的敞开,海德格尔称之为“事情性之自由”(Freiheit der Sachlichkeit)。它是真正的研究和追问的依靠,因为只有在事情性自由形成的地方,在生存状态上从事科学才是可能的。然而,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哲学沉沦了。在公共生活中,普遍精神娱乐的需求对哲学的估价来说成了最终的决定因素。这预示着我们完全是无根的,无力从事追问,失去了真正认知的激情,希望着哲学或科学成为像某种依靠一样的东西,这意味着我们成了不自由的或虚假自由的(45)在这个地方,海德格尔有一条边注:参见《真理的本质》(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256.)。这条注释显明了他此处的自由思想与其后来自由思想之间的关联。。
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从上述的“事情性之自由”出发才能克服历史主义,因为它首次给出来如下的可能性:我们在真正的意义上是历史的,即知道我们生存的可能性就存在于那里,而如果历史得到了理解,那么它就因此而被克服了。这其中就有一种事实研究的任务。与此相反,所谓的“体系性的”哲学则是自由漂浮的,即凭借着从历史而来的偶然刺激成了一份舒适的工作。自由漂浮的逻各斯不能“把朝向事情的视域为它自己本身自由地置放出来(freilegen)”(46)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345.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自由地置放(freilegen)”译为“展露”(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50页)。。而柏拉图的《智者篇》就是完全自由地、没有任何体系性背景地从事情开始的,所以它以及对它的准备,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就成了对如下事情的检验:“他在多大程度上于自己那儿具有实事性之自由(Freiheit der Sachlichkeit)”,对于这篇对话的冲击力,他自己本身是否具有接受和收纳能力(47)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343页。。在这里,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就是事情性的自由。这是海德格尔首次明确地突显历史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一关联内蕴着自由与接受、收纳之间的内在关联,因而根本就与历史主义无关。这关联显然也是他后期所谓的“存在之天命的自由”的关键所在。
在讲座中讨论哲学与传统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海德格尔再次提及了自由与历史、时间、命运之间的关系,以及“解构”的自由内涵。他指出:甚至是在当时,尤其是在现象学中,存在着一种浪漫主义,即“相信在进入‘自由领域’(Freie)的路上,人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一跃而摆脱历史”(48)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413.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自由领域(Freie)”也译为“自由”(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536页)。。然而,海德格尔认为,重要的不是摆脱过去,“而是使过去对我们成为自由的,让我们从传统中解脱(frei zu lösen)出来”(49)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413.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使……成为自由的(frei zu machen)”译为“开放出来”(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537页)。。只有当我们帮助我们本己的过去取得其权利,我们才能在它那儿成长,才能“在如此地被自由置放的(freigelegt)研究那里,将我们自己提升到追问和研究的水准上”,而对传统的无情解构就是对过去的敬畏居有(50)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413-414. 熊林的中译本将此处的“被自由置放(freigelegt)”译为“解放”(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537页)。。在这个意义上,在这个讲座里海德格尔再次提到:巴门尼德作为希腊哲学的开端决定了西方哲学的“命运”(51)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25-26页。。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在讨论关于“智者”的第六个定义即“盘问者”的时候,海德格尔对第六种拆分方式进行了描述,论及了自由与教育之间的关联。这种拆分方式被称作“净化”,它不仅仅是把某种东西从另外的东西那里抽离出来并让被抽离出来的东西保持原样,而且要使被抽离出来的东西成为自由的(frei zu machen)(52)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357. 海德格尔给“使……成为自由的(frei zu machen)”加了着重号,熊林的中译本将此之又重新译为“使……自由”,而不是“开放出来”(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65页)。。通过这样一种“自由置放”(Freilegung),被抽离出来的东西自身进入到它本己的可能性之中,自身保持和居留于此。这样一种净化就是一种公开(Offenbarmachen),就是“把χει¨ρον[较差的东西]抛出去,从而让βε'λτιον[较好的东西]变得自由”(53)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67页。。而本真的、真正的看即去蔽(aletheuein)是美好的东西,因而“是那真正停留在灵魂中并要变得自由的东西”(54)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79页。。教育则是这样的一种技艺:清除无知,“让'ληθευ'ειν[去蔽]本身变得自由”(55)马丁·海德格尔:《柏拉图的〈智者〉》,第487页。,即向着去蔽解放(befreien)此在。而且,在这个讲座中,海德格尔即已明确指出:“真理(aletheia)=存在,在被揭示状态(Entdecktsein)这一最本真的意义上”(56)Martin Heidegger,Platon:Sophistes,S.618.。在这里,一方面,我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心目中教育的根本目的和任务与自由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且这些关联都是贯穿在他此后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中的,所以“自由”乃是透彻理解他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一个不可忽略的角度;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去蔽意义上的真理、存在与自由之间的根本关联变得更加昭然了。
四、结语
在马堡时期的第一个讲座中,海德格尔第一次把自由问题作为一个主题或专题来讨论。该讲座中的自由思想一方面承继着他早期弗莱堡时期的自由思想,另一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第一次把自由与追问的“事情自身”关联起来,将之理解为与事情的“争执”,第一次把自由问题作为引导性的视点和线索,把“本真的自由”作为标尺,来审视和衡量在他之前的哲学,把自由规定为一种真正而恰切地追问的“激情”。海德格尔这种追问、争执、警醒、承受、敞开、放弃意义上的自由思想,蕴含着他此后自由思想中的关键因素和标志。也正是凭借着这种自由思想,他在这个讲座中对笛卡尔和胡塞尔的意识哲学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在接下来的两个讲座中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阐发,在其中自由与存在、命运、真理、历史、时间、无(用)、现象学方法、情绪、教育等等之间内在的、根本性的关联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
在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如上自由思想中,自由问题与存在问题是通过对存在论历史的解构而勾联在一起的,因为解构的基点是作为此在的“自由存在”。但是,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由已经成了海德格尔讨论的一个明确主题,但是存在问题却还没有作为一般存在问题或“基础问题”(Grundfrage)而被明确提出来,这为后来在他急于找到新的思想出路的时候自由问题短暂地“篡夺”存在问题的基础地位提供了可能性。这也显示了存在问题和自由问题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复杂关系。但是无论如何,海德格尔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方式或方法是同一的,即都运用了其现象学的方法,具体而言,就是形式指引、解构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动机和目的都内在关乎自由问题。
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所谓的“自由”同时意味着承受、敞开,甚至是放弃,“自由给予”同时就是“委弃、献身”,从而表明了他在自由问题上自始至终秉持的基本原则:不断地重新为自由寻找属于其自身的但不受其自身操控的约束性,即在自由与命运“之间”思考和寻找自由,从而力图克服以孤立个体的优先性为基础的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之自由漂浮的、无根的自由。这意味着,它同时也显示了海德格尔自由思想贯彻始终的理论旨归:突破主动与被动、积极与消极、理性与非理性、意愿与非意愿、必然与偶然之间的二元分立,从而突破意志主义与命定论的二元对立。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这种总是在“之间”摆荡的自由,一方面总是有根的、沉重的,另一方面同时也总是不稳靠的、艰难的,从而也总是意味着生死之间伸展着的时刻准备着的警醒,从而总是关联着时间、历史和真理。而实行着这种基本原则和理论旨归充满激情地追问着自由问题的哲学,作为与“事情自身”的争执,本身就是本真自由的典范。
虽然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自由思想只是第一次明确把自由作为了一个重要论题,其本身是初步的、片断性的,但是它通过现象学的方法与存在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它所贯彻的基本原则、理论旨归等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接下来的思想道路:在马堡时期的最后一个讲座(即1928年夏季学期的课程《从莱布尼兹出发的逻辑学的形而上学始基》)中将“自由”作为核心“事情”之一,使之对于其整个思想具有了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从而深刻地影响了他思想的转折及其后期思想。但是,海德格尔马堡时期初期的自由思想所显露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意志”、“命运”、“天命”概念未得到充分讨论,“自由首先与伦理、政治无关”的基本信条,也造成了其后来自由思想的“先天”不足,从而最终导致他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转折之后放弃了建构“自由形而上学”的企图。就此而言,无论是对于透彻地理解海德格尔的整条思想道路来说,还是对于突破传统的西方自由思想和哲学传统来说,把“海德格尔的自由思想”作为一个专题来深入讨论都是一项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