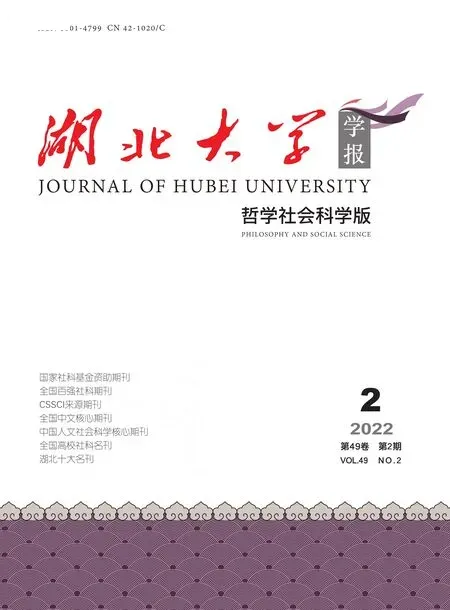凤凰与早期中国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
邹福清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西周初形成的天命观不仅建构起西周政权的合法性,奠定了德治主义的传统,还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以至汉代理想士人人格合理性的来源。中国文化在此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定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轴心时代始于殷周之际”(1)郭沂:《从西周德论系统看殷周之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对于天命观在政治论、人性论场域的内涵,学界讨论得比较充分。但天命观由政治论场域进入人性论场域发生的转换与衍变,还有细节有待厘清,特别是,虽然孔子、庄子、屈原等先秦诸子乃至汉代士人建构的理想士人人格不同,但都与天命观存在深刻联系,且都被赋形为凤凰,凤凰成为早期中国(2)学界常用“早期中国”指东汉灭亡以前的时期,如闫月珍的《作为仪式的器物——以中国早期文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李峰的《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有其合理性,故出于行文的方便,本文沿用这一表述。的重要文化表征,其深刻的内涵与重要意义有待揭示。考察《尚书》、《诗》、《山海经》、诸子散文、楚辞、汉代散文等文献,梳理理想士人人格的建构与赋形,可以深入揭示凤凰这个文化表征与中国文化进程的内在关系,从而深刻了解早期中国士人对于人生选择、人生价值的思索,并进一步窥见所谓“中国轴心突破”(3)参见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的轨迹以及中国文学士不遇书写传统的形成。
一、凤凰作为理想士人人格表征的源起
西周初,蕞尔小国打败大邑商,然而,武王灭商之初特别是成王执政时期,执政者面临殷商旧族及其联盟的反抗,以及周人内部的叛乱,建构政权合法性成为最紧迫的问题,周公在一系列针对不同对象发布的诰令中阐发的天命观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傅斯年曾概说周公阐发天命观的政治动机:“以此说(天命)说殷遗,将以使其忘其兴复之思想,而为周王之荩臣也;以此说说周人,将以使其深知受命保命之不易,勿荒逸以从殷之覆辙也;以此说训后世,将以使其知先人创业之艰难,后王守成之不易,应善其人事,不可徒依天恃天以为生也。”(4)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79页。尽管商代中期商王盘庚曾语及“天命”,如“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5)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37页。,“天命论中有些必要的因素肯定在《盘庚》篇中已经存在”,但是,“天命论之完成与理性化的工作当然是周公的贡献”(6)何炳棣:《何炳棣思想制度史论》,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06页。。殷商的“天命”以君权神授为核心内涵,不涉及价值观,周公阐发的“天命”除继承殷商的君权神授观念外,又注入了以德配天的新思想,既建构了周人执政的合法性,还强调了周人恰当执政的必要性。所谓以德配天,就是周天子因其德行获得天的眷顾并执掌天下,即“皇天无亲,惟德是辅”(7)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09页。。可以说,周初的执政者接过商代以君权神授为主要内容的“天命”,注入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对执政者的德行提出要求,将天定与人为结合起来,从而为其代商而有天下建构合法性。春秋战国时期,天命观也被诸侯用来建构执政的合法性(8)罗新慧:《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后来的政权更迭中常见新的帝王声称自己是天命所归。
在周代商而立的历史语境中,凤凰被形塑为天命的传达者,代表天临鉴人间君王的“德”即德行,被视为“明王”出现的祥瑞而受到崇拜,成为君权神授、以德配天政治观的表征。首先,从西周初开始,凤凰成为青铜器纹样选择的重要对象,可见其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性。彝器的纹样具有“协于上下,以承天休”(9)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71页。的宗教意义。商代青铜器的主要纹饰是饕餮。然而,自西周初开始,青铜器纹饰中的饕餮纹几乎全部消失(10)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13页。,代之而起的是凤纹,出现了所谓“大凤纹时代”(11)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温天河、蔡哲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78页。。马承源进一步解释:“商末周初及至西周中期昭、穆之时,青铜器纹饰中凤鸟纹大量出现,西周早期到穆王、恭王,有人称之为凤纹时代。”(12)陈佩芬、吴镇烽等编撰:《中国青铜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其次,在先秦文献中屡见天帝曾派凤凰之类的使者传达周人代商而立的旨意的说法。如“赤乌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13)吴毓江:《墨子校注》,孙启治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221页。,“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14)徐元诰:《国语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页。,“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15)高诱注:《吕氏春秋》,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7页。。起初,这些文献所载充任天的使者或为赤乌,或为赤雀,或为凤凰,并不统一,后来的解释与转述逐渐集中于凤凰。由这些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凤凰曾降临周族故地岐山,前来传达周人代商而立的天命的开国神话一度被盛传。最后,以凤凰降临显示并标榜执政者之“德”的直接表达亦见于先秦文献。《逸周书·王会篇》载西申献凤鸟于周,说是“归有德”(1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858页。,实际上也是以凤凰显示周天子之“德”。《尚书·周书·君奭》录周公曾称“耇造德不降,我则鸣鸟不闻,矧曰其有能格”(17)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尚书正义》,第654页。,是说周公以凤鸟降临诱导召公与其一起进德,辅佐成王。可以说,以凤凰作为天帝的使者传达政权更迭的天命,在周初执政者建构政权合法性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诗》的雅、颂部分使用“命”字的频率较高,也屡用“天命”一词,大谈文王乃至武王、成王“受命”、“配命”,充分体现了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天命观,特别是《大雅·卷阿》不仅表达了周王受命于天、德配天命的观念,还开始以凤凰作为理想人格的表征。《竹书纪年》载“三十三年,(成)王游于卷阿,召康公从”(18)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47页。,尽管由于无法断定此则材料是早期史官的记载还是后人据《卷阿》进行的杜撰,无法据其断定《卷阿》创作于周初,更无法断定其本事。但是,《卷阿》体现的政治观清晰可辨。首先,周王受命于天。诗句“尔受命长矣”意指“周王受天命为天子”(19)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833页。,后来的诠释将此诗与周的兴起并代商而立联系起来也就不奇怪了。如三国韦昭注《国语·周语上》“周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曰:“三君云:鸑鷟,凤之别名也。《诗》云:‘凤凰鸣矣,于彼高冈。’其在岐山之脊乎。”(20)徐元诰:《国语集解》,第29页。《韩诗外传》卷八上溯此诗本事至黄帝(21)韩婴:《韩诗外传集释》,许维遹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77-278页。,不可信,但将凤凰降临与“明王”出现相联系是符合《卷阿》语境的。其次,周天子以德配天。《卷阿》中的“君子”系指周天子,该诗用了大量笔墨来表现周天子的德行,既有对周天子人格境界的描述,如“岂弟”、“如圭如璋”等,也有对周天子人格内涵的描述,如“孝”、“四方为纲”、“四方为则”等。君王德行最重要的内容是礼贤下士,该诗描写大臣从游周天子的盛况实际上是赞美君王礼贤下士之德。可见,《卷阿》产生于天命观念以及凤凰崇拜盛行的文化语境,其主旨是:周天子执政是天命所归,凤凰降临以传达天命;凤凰既是天命的传达者,又是“明王”的预示;凤凰传达天命的内在逻辑在于君德,君德最主要的内容是任用贤臣。
孔子将天命观中政治面向的君王德行转换为人性面向的士人德性,并以“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赋予“知天命”以道德、政治实践的担当和进取精神的内涵,实际上是将天命从政权合法性来源转换成士人理想人格合理性来源。《论语·子罕》开篇就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22)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43页。《墨子·公孟》曾批评儒家“以命为有”,可见孔子并非不言“命”(吴毓江:《墨子校注》,第706页);又宋代史绳祖《学斋佔毕》说:“盖‘子罕言’者,独利而已,当以此句作一义。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与,此句别作一义。”(史绳祖:《学斋佔毕》,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笔记》第8编第3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59页),《尧曰》还以“知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即“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季氏》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为政》称“五十而知天命”(2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1、177、12页。。学界已经认识到孔子所谈论的“命”包含“有限性”和“可能性”(24)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52页。两个方面:清代刘宝楠曾指出“天命,兼德命、禄命言,知己之命,原于天,则修其德命”,并将德命定性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学”(25)刘宝楠:《论语正义》,国学整理社编:《诸子集成》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60页。;史华兹区分“命”为宿命和使命,认为“知天命”就是“对于力所不能及的东西,以及真正属于他的自主行动领域内的东西有了清楚的理解”,并指出“‘命’被一般性地运用人类时——它首先被运用于君子身上——尤其指的是要他去实现其道德性、政治性使命的‘人格性的命令’”(26)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23-124页。。孔子将寿夭、穷通都归因于命,即“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27)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58、157页。,此所谓“命”仅就人的“有限性”一面而言,相当于刘宝楠所谓“禄命”、史华兹所谓“宿命”。如果作为君子人格本质的“知命”仅是“知道这些东西是不可求的,便不必枉费心思”(28)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页。,显然不符孔子心目中的君子人格。孔子所谓“命”还有人的“可能性”这个更重要的一面,也就是刘宝楠所谓“德命”、史华兹所谓“使命”,还有徐复观解释“畏天命”、“知天命”为“出之以敬畏、担当的精神”,“证知了道德的超经验性”(29)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第53-54页。,也是有道理的。寿夭、穷通属于天定,人只能被动接受,正可谓宿命;而徐复观所说的证知道德的超经验性、刘宝楠所说的“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学”本属于人为的,恰是人的“自主行动领域”,的确可谓“道德性、政治性使命”。后者为何也被说成是天之所命呢?孔子并非对人的自主性的否定,而是强调“道德性、政治性使命”对人而言的神圣性和普遍性,从而使其具有人性的价值和地位。因此,孔子将“畏天命”、“知命”、“知天命”作为君子人格的核心,是强调君子的担当和进取精神,正如《国语·晋语九》所谓“君子哀无人,不哀无贿;哀无德,不哀无宠;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30)徐元诰:《国语集解》,第453页。。孔子的贡献在于,将天定的、有限的寿夭、穷通悬置起来,存而不论,而将人的自主的、可能的道德、政治实践的一面注入天命之中,将其普泛化为人性,并作为君子人格的本质。同时,孔子继承了周初以凤凰作为“明王”预示的观念,还将凤凰降临与否,和“明王”出现与否以及士人的穷通联系起来。《论语·子罕》载孔子曾哀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3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89页。孔子发出“吾已矣夫”的哀叹固然是哀叹年寿将尽,也是哀叹功业未就,流露出道德、政治实践的紧迫感,从孔子“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32)王文锦译解:《礼记译解》,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86页。的感叹可以窥见他赋予自己的责任感。《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33)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第193页。接舆道破了“凤鸟不至”,“明王不兴”,孔子生不逢时,功德未竟的窘境,实际上是将凤凰与政权更迭相关联的链条中加入了士人穷通的环节。总之,孔子将天命的指向由君王的德行转换为君子的德性,相应地,凤凰由“明王”的预示转换成君子人格的表征。
《山海经》等文献将凤凰形态与仁、义等德目一一对应起来,将君子人格赋形为凤凰并逐渐定型。如《南山经》载:“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皇,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34)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第14-15页。《海内经》载:“凤鸟首文曰德,翼文曰顺,膺文曰仁,背文曰义,见则天下和。”(35)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第383-384页。《逸周书·王会篇》也将凤凰与仁、义、信等德目联系起来:“凤鸟者,戴仁、抱义、掖信,归有德。”(36)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858页。现在无法判断这些材料的先后次序,不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凤凰形态与德目的对应关系在战国时期已经基本建立。汉初韩婴《韩诗外传》卷八论及《卷阿》时融入了《山海经》将凤鸟形态与德目对应的观念,强化了天命观念的道德指向: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之象,鸿前而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37)韩婴:《韩诗外传集释》,第277-278页。
此则材料亦见于略晚的刘向《说苑·辨物》,其中,天老对“凤象”的形态、习性的全方位描述倒很能代表儒家的君子人格和政治思想。应该说,时至汉初,凤凰作为儒家理想人格的表征已成为普遍的知识和信仰,这才有东汉许慎所谓凤凰“出于东方君子之国”(38)许慎撰、徐铉校定:《注音版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3页。的说法。汉代托名师旷的纬书《禽经》也是将凤凰的形态与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德目一一对应,还呈现出越来越精细的趋势:“凤雄凰雌。凰,鸿前麟后,蛇首鱼尾,龙文龟身,燕颔、鸡啄、骈翼。首载德,顶揭义,背负仁,心抱忠,翼挟信,足履正。小音钟,大音鼓。不啄生草。五采备举。飞则群鸟从,出则王政平,国有道。”(39)师旷撰、张华注:《师旷禽经》,《师旷禽经相鹤经续诗传鸟名》,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页。不过,关于凤凰形态与儒家德目的对应关系,说法不一,后来还掺入了五行思想。
在战国时期凤凰形态与道德相关联的知识和信仰语境里,庄子建构理想士人人格虽然跳出了天命观的框架,但也利用有关凤凰习性的想象。《太平御览》录《庄子》佚文云:
老子叹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宝。天又为生离朱,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玕。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40)李昉编纂:《太平御览》第8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323页。
所谓“凤鸟之文,戴‘圣’婴‘仁’,左‘智’右‘贤’”与《山海经》的表述类似,晋代郭象《庄子后语》曾指出《庄子》“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梦书》;或出《淮南》;或辩形名……”(41)王叔岷:《诸子斠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4页。王叔岷已怀疑此佚文是郭象《庄子后语》所谓“或似《山海经》”之类(42)王叔岷:《庄学管窥》,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43页。,加上这里大谈仁、智等德目与道家思想不符,应该是郭象疑其为窜入《庄子》的内容而将其删除的。不过,该文献关于凤凰习性的描述“吾闻南方有鸟,名为凤。所居积石千里,天为生食。其树名为琼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为宝。天又为生离朱,一人三头递起,以伺琅玕”是不同的赋形方向,与传世《庄子》关于凤凰习性的表述类似: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43)庄周著、郭象注:《庄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就此两则材料来看,道家以凤凰不同凡俗的习性隐喻其不合时世的独特人格,并注入了新的内涵——高洁,这是道家理想人格的重要内涵。庄子是利用凤凰的独特习性来建构理想士人人格,同时期略晚的屈原与其有相通之处。
二、凤凰与战国骚人人格的赋形及士不遇的书写
屈原虽不言天命,但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思考,并没有完全超越周初形成的君权神授、以德配天的政治观,如《离骚》云“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44)洪兴祖:《楚辞补注》,黄灵庚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8页。,就是“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翻版。屈原更关注士人人格,十分强调德对士人的重要性,只是很少用君子一语——只有《九章·怀沙》出现两例,而是主要通过剖白自我、批判党人呈现其理想士人人格。屈原也将理想的士人人格赋形为凤凰,并建立了凤凰与众鸟对立和错位的士不遇的书写模式,旨在反思才德之士何以不容于世。
屈原称其所处的社会为“浊世”,其特点是对立和错位,如《离骚》说:“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4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2页。。《九章》措辞更激烈,情感更悲愤,书写更显豁,如“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46)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99、218-219页。。类似的表达还有:“世溷浊而不清,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47)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80页。屈原将自然、社会、政治乃至历史切分为阴与阳、香与臭、黑与白、美与丑、高贵与庸俗、善与恶、贤与愚、忠与奸等两极,并极度彰显二极对立和错位的荒诞。
屈原将浊世的荒诞赋形为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剥掉了凤凰的神性,使其只剩下高洁。首先,屈骚中的凤凰依然担当使者的角色,不过,不再是上帝的使者,而是抒情主人公的使者。凤凰或者充当抒情主人公的先戒,如“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魂乎归徕!凤皇翔只”(48)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7-38、366页。。或者为抒情主人公伴行,如“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凤皇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雌蜺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49)洪兴祖:《楚辞补注》,第63、268、273页。。或者为抒情主人公传递信息,如“凤皇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50)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8页。,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唐代五臣注《文选》都解读为以凤凰为聘娶之媒;“祝融戒而还衡兮,腾告鸾鸟迎宓妃”(51)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73页。也是以凤凰为媒。或者充当抒情主人公的坐骑,如“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鹥即凤凰,洪兴祖认为是“以鹥为车”(5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7、39页。。值得注意的是,屈原笔下的凤凰作为使者,往往没能完成任务,如陪伴抒情主人公远行或受命聘娶有娀之佚女,都是无果而终。其次,屈骚中的凤凰处于无所栖止的境地,沦为孤傲的流浪者,如《九章》的《涉江》、《怀沙》两篇中的凤凰被形塑为流浪者。《卷阿》中凤凰集于茂盛的梧桐,即“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53)关于《卷阿》“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毛传不言众鸟,而郑笺称“凤皇往飞翙翙然,亦与众鸟集于所止”(毛亨传、郑玄笺:《毛诗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44页)。又,许慎《说文解字》曰“凤飞,群鸟从以万数”(许慎撰、徐铉校定:《注音版说文解字》,第73页)。揣摩文义,今从郑笺。,《山海经》中凤凰自歌自舞于安宁的沃野,即“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54)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最终修订版)》,第335页。。屈骚中的凤凰尽管高贵,但被置于放逐、囚禁的境地,处于寻觅栖止之所的远翔之中,不再栖息于乐土,不再自歌自舞,而是栖栖惶惶,孤独地流浪。这一点深刻影响了屈原的后继者宋玉,其笔下的凤凰彻底沦为一个孤傲的流浪者,如“凤独遑遑而无所集”,“谓凤皇兮安栖”,“凤皇高飞而不下”(5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5页。。最后,屈骚中的凤凰处于众鸟如燕雀、乌鹊、鸡鹜等的对立面,其高洁、孤傲且不肯降格以求,如“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56)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99、219页。。宋玉和屈原一样也将凤凰置于众鸟的对立面,并反复将凤凰与众鸟的处境进行对比,凸显二者的巨大反差,如“凫雁皆唼夫粱藻兮,凤愈飘翔而高举”,“众鸟皆有所登栖兮,凤独遑遑而无所集”(57)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5页。。先秦道家已经开始强调凤凰不同凡俗的习性并将其与众鸟对立起来,如《太平御览》录《庄子》佚文载惠施嘲弄庄子云“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58)李昉编纂:《太平御览》第4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857页。,还有《庄子·秋水》将鹓鶵(即凤凰)与鸱对立。孟子、荀子亦曾如此,如“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59)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4页。,“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皇”(60)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82页。。可见,凤凰与众鸟的对立与错位已是战国时期普遍的知识和信仰,只是特别为屈原所张扬。
屈原将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跟自然、社会、历史中的对立和错位现象并置,形成了一个隐喻网络,并指向士不遇的主题。《九章·涉江》就将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跟自然、社会中的对立和错位现象并置:“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時不当兮。”(61)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99页。《怀沙》也是如此:“玄文处幽兮,矇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6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18-219页。当屈原将这些自然、社会中的对立和错位现象跟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一再并提时,也就建立起二者相互指涉的关系,后者变成了前者的隐喻,并共同指向高洁者不得其所而污浊者占据高位的士不遇主题,建立了一个以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为表征的忠奸、贤愚不分的士不遇文学主题的书写范式。屈原在其隐喻网络中还引入鲧、比干、箕子、梅伯、伍子胥等古人作为同道,“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6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97页。,使个体不遇的命运具有沟通古今的张力,凸现出士人的宿命与历史的荒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功能和历史反思价值。
宋玉强化了凤凰与众鸟对立和错位的士不遇指向,并明确标出悲士不遇的主旨。宋玉《九辩》也屡屡罗列现实、历史中的对立和错位现象,如“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众踥蹀而日进兮,美超远而逾迈”,“尧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险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伪名”(6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4、315、313页。,并将其跟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并置。《九辩》开篇直接表明悲士不遇的主旨:“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惆怅兮而私自怜。”(6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93页。《对楚王问》则点明并阐发了凤凰与士的隐喻关系:“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66)吴广平编注:《宋玉集》,长沙:岳麓书社,2001年,第89页。可见,宋玉笔下众鸟唼夫粱藻、凤凰无所栖集就是庸人进用、贤士远离的隐喻,虽无所栖集却不贪喂妄食的凤凰就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士人的隐喻。刘永济就曾指出宋玉“以凫雁比小人,凤鸟比贤士。言小人得势,则贤士退处”(67)刘永济校释:《屈赋音注详解屈赋释词》,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4页。。宋玉对屈原不遇的命运感同身受,其创作受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68)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81页。的影响,高扬个体生命的高贵与卓越,猛烈批评整个社会阴阳易位,黑白颠倒的失序,并表达“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69)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99页。的绝望。屈原和宋玉形塑的凤凰与《诗》中凤凰的文学意蕴与文化内涵差别很大,与《山海经》乃至战国时期其他文献也不同。屈原不言天命,重视人力。刘永济曾指出:“吾人细读屈子《天问》,凡以天地灵怪设问者,皆有见其幽玄难测,非智力所能穷之意,凡以人事祸福兴亡设问者,皆有信其有必然之因果,实人之所自召之意。于是屈子心中乃形成一种但尽人力而不委任天命之基本思想。”(70)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馀义》,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22页。因此,屈原和宋玉笔下的凤凰不再是《卷阿》所显示的西周文化中传达天命的使者,也不是《山海经》中一方乐土的守护者,而从神界坠入凡间,失去了神性。如果说《卷阿》中的凤凰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远古以来关于凤凰作为上帝使者的神话思维,屈原和宋玉笔下的凤凰则对接了周初以来对于凤凰形象道德内涵的想象,特别张扬了担当和进取精神,其建构的理想士人人格可以称为骚人人格,与孔子的君子人格气脉相通。难怪王逸称屈骚“虬龙鸾凤以托君子”(71)洪兴祖:《楚辞补注》,第2页。。屈原《离骚》及《九章》的《涉江》、《怀沙》诸篇中的凤凰不论是使者还是流浪者,都被后来的注家作为理想士人人格的赋形。东汉王逸、宋代洪兴祖都将屈原笔下的凤凰解读为贤德之人。王逸注《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称凤凰“喻仁智之士”,注《涉江》“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句云“以兴贤臣难进易退也”(7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3、199页。;洪兴祖注《离骚》“吾令凤鸟飞腾兮”称凤凰“喻贤人之全德者”(7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3页。。他们都强调的是道德内涵。
战国末期的屈原和宋玉对士不遇感知强烈,在凤凰与众鸟的对比中张扬凤凰的高贵、孤傲,将其形塑为洁身自好、取义成仁的骚人人格的表征,并批评世俗特别是群小对才德之士的摧残,开创并发扬了以凤凰与众鸟的对立和错位隐喻忠奸、贤愚不分的士不遇文学主题的书写范式,富有感染力,影响深远,总能引发后人深沉的共鸣。但是,他们没有深入思考如何应对不遇的困境、如何消解不遇的焦虑。屈原没有走出不遇焦虑的困境,最终选择了自沉,也就未能寻求到现世性的消解士不遇的方式。洪兴祖说:“为人臣者,三谏不从则去之,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7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73页。的确,当时摆在不遇士人面前的道路是或者退隐或者赴死。赴死毕竟不能作为群体的选择。如果选择退隐又该如何调适内心的焦虑?他们在自伤不遇时除了引古人为同道,以“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7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97页。来暂时慰藉内心的痛苦,其实没有找到出路。
三、凤凰与汉代新君子人格的赋形及士不遇焦虑消解的书写
汉代士人面对大一统的政局,与战国末期的屈原和宋玉相比更是毫无选择的自由,“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7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十分强烈,生不逢时的感受也比较鲜明,普遍认识到“时有遇否,性命难求”(77)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99页。,“知命”、“委命”,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从而适应大一统局势的生存智慧,便成为新的君子人格的核心内涵。汉代士人侈谈凤凰祥瑞,对凤凰的形塑沿袭了凤凰与凡鸟对立和错位的基本框架,并表现出新的取向——强调凤凰根据环境或降临或远翔的举动,同时也将凤凰形塑为理想的士人人格,潜藏着吁求君王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
汉代士人常以战国为参照体验和思考时势,基本判断是“时异事异”、“世异事变”(7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2865、3571页。、“风移俗易”(79)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610页。、“世易俗异,事势舛殊”(8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906页。,不能“处皇代而论战国”(81)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10页。。在汉代士人看来,汉代与战国的时势到底有什么不同呢?首先,汉代政治一统,没有游说人主以取卿相之尊的空间。虽然战国时期的纵横家苏秦、张仪、范雎、蔡泽等在汉代士人内心还有市场,但是他们清醒地认识到汉朝已经没有游走列国、纵横捭阖,说人主以“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82)何建章注释:《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5页。的可能。其次,汉代君权至高无上,谏主风险很大。西汉初中期的政治还算清明,士人的政治压力感主要源自至高无上、笼罩一切的君权。西汉初贾山云:“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83)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330页。西汉中期东方朔云:“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84)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865页。时至东汉,班固亦云:“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养之如春。”(85)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610页。这些都是对汉代君权至高无上的描述。对汉代士人而言,不受限制的君权的灾难性后果就是进谏艰难,正如西汉初贾山《至言》云:“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用其言而显其身,士犹恐惧而不敢自尽,又乃况于纵欲恣行暴虐,恶闻其过乎!震之以威,压之以重,则虽有尧舜之智,孟贲之勇,岂有不摧折者哉?”(86)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330页。东方朔《非有先生论》用“谈何容易”一语表达君权压力下难以进谏的无奈,并申说:“夫谈有悖于目拂于耳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说于目顺于耳快于心而毁于行者,非有明王圣主,孰能听之?”(87)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868-2869页。西汉初邹阳《狱中上书自明》明确表示君权加剧进谏难度:“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笼于威重之权,胁于位势之贵,回面污行,以事谄谀之人,而求亲近于左右,则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88)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2352页。总之,“历九州而相其君”(89)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士人不能再以“道”与“势”抗衡,只能哀叹生不逢时。西汉初贾谊《吊屈原赋》中“乌虖哀哉兮,逢时不祥”(90)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0页。是感叹屈原生不逢时也是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另有“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时”(91)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28页。,“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92)欧阳询:《艺文类聚》,汪绍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541页。,“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93)欧阳询:《艺文类聚》,第541页。,“丁时逢殃,可奈何兮”(9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99页。,“哀余生之不当兮,独蒙毒而逢尤”(9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08页。,“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汉氏之中微”(96)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705页。,“天生我兮当闇时,被诼谮兮虚获尤”(97)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27页。等等,都是生不逢时的哀叹。
汉代士人基于对时势的体验与思考,常秉持“知命”、“委命”的人生态度。贾谊《鵩鸟赋》四次言及“命”:“命不可说,孰知其极”,“迟速有命,乌识其时”,“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德人无累,知命不忧”(98)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6、416、418、418页。。他认为命不可求,“知命”、“委命”才是明智的,《鵩鸟赋》既有命不可知的无可奈何,也有认命的故作旷达。显然,汉代士人所谓“命”主要是指宿命,是“命”之“不可求”的“有限性”的一面,遗落了“命”之“政治性使命”的“可能性”一面。他们普遍践行“为可为于可为之时”(99)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3573页。,“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退无主,屈申无常”(100)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985页。的政治选择,称依循此原则处事的人为智者,贾谊称为“德人”,也有称为君子、大人、圣人的。汉代士人所说的“君子”与《卷阿》以及儒家的“君子”内涵不同,反而更接近道家,“德人”就更是道家庄子的概念。因此,汉代士人侈谈命运,在政治理想不能施行于现世的情况下,往往退而求其次,著书立说,“聊朝隐乎柱史”(101)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908页。,也就不难理解东汉扬雄主张“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102)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3515页。,班固哀叹“君子道穷,命矣”(103)洪兴祖:《楚辞补注》,第73页。,以及他们对屈原自沉的批评。王逸于东汉末年大一统政权濒临崩溃之际,彰显、倡导道义精神来为国分忧,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极力称许屈原,实属例外,但恰是强调担当和进取精神以拨乱反正。
汉代形塑的凤凰继承了屈原和宋玉的凤凰与众鸟对立和错位的基本构形。其一,汉代骚体作品普遍采用凤凰与众鸟对立和错位的书写范式,如东方朔《七谏》“枭鸮并进而俱鸣兮,凤皇飞而高翔”,“众鸟皆有行列兮,凤独翔翔而无所薄”,“鸾皇孔凤日以远兮,畜凫驾鹅。鸡鹜满堂坛兮,鼁黾游乎华池”(10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07、422、423页。;还有王褒《九怀》“痛凤兮远逝,畜鴳兮近处”,“凤皇不翔兮,鹑鴳飞扬”(10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45、465页。;王逸《九思》“桂树列兮纷敷,吐紫华兮布条。实孔鸾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鸮”(106)洪兴祖:《楚辞补注》,第551页。等。其二,汉代骚体作品常常沿袭屈原《九章·涉江》“鸾鸟凤凰,日以远兮”之意书写凤凰的孤独无依,如贾谊《吊屈原赋》云“鸾凤伏窜”(107)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0页。,冯衍《显志赋》云“鸾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鸣而求其友”(108)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1001页。,特别是东方朔《七谏》反复表现凤凰远翔:“凤皇飞而高翔”、“凤独翔翔而无所薄”、“鸾皇孔凤日以远兮”。其三,汉代骚体作品往往将凤凰与众鸟对立和错位跟贤愚颠倒的社会现象并置,从而建立起二者的隐喻关系,并最终指向士不遇的主旨,如“贤者蔽而不见兮,谗谀进而相朋”,“众比周以肩迫兮,贤者远而隐藏”(109)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07、431页。等。董仲舒《士不遇赋》是最早以“士不遇”为题的文学作品,司马迁也创作有《悲士不遇赋》。汉代士人“以屈原的‘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怨’,象征着他们自身的‘怨’;以屈原的‘怀石遂自投汩罗以死’的悲剧命运,象征着他们自身的命运。开其端者厥为贾谊”(110)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1卷,第168页。。贾谊对屈原不遇的命运感同身受,“以命世之器,不竟其用,故其见于文也,声多类《骚》,有屈氏之遗风”(111)程廷祚:《青溪集》,宋效永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67页。,如《吊屈原赋》云:
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溷兮,谓跖、蹻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罢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112)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0页。
汉代形塑的凤凰还表现出了新的动向——强调凤凰基于环境判断作出或远翔或降临的举动,所谓环境实际上就是人间君王的德行,并将凤凰形塑为审时度势而选择进退的新君子人格的表征,潜藏着吁求君德和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汉代士人在至高无上的君权笼罩一切的政治背景下也不是没有约束政治权力的冲动,其表现就是对君德的吁求。班彪《王命论》的观点可谓代表:“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鬼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倔起在此位者也。”(113)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718页。班彪表面上是谈天命,实际上是言君德,认为鬼神护佑的前提是帝王的“德”与“功”,与周初天命观遥相呼应。而且,汉代盛行以凤凰为“太平之瑞”和“圣王始生之瑞”(114)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728-729页。的信仰,时人对汉光武帝刘秀“生于济阳,凤皇来集”的解读就是凤凰“为光武有圣德而来”(115)黄晖:《论衡校释》,第729页。,与周初凤鸣岐山开国神话的逻辑都是以君权神授、以德配天为核心内容的天命思想。贾谊虽不明言天命,但在天命观盛行、侈谈凤凰祥瑞的时代,其笔下的凤凰形象未能跳出天命观念,而是在天命观的框架下强调凤凰的至与不至和君主有无德行的关联,从而将对天命观的解读导向对君德的吁求。贾谊《吊屈原赋》明确指出“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然后称“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渊潜以自珍;偭枭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螾”(116)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2页。,也就是凤凰高逝、神龙深潜都是主动退避;又说“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增击而去之”,“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后下”(117)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2、447页。,一再强调凤凰作出去与留决定的依据是人间的君德,其形塑的凤凰潜藏着吁求君德的文化动机显露无遗。在这一点上,他越过此前不言天命的屈原、宋玉,而上接周初的天命观。宋玉曾将士的进退与君王之“德”联系起来,如“鸟兽犹知怀德兮,何云贤士之不处?骥不骤进而求服兮,凤亦不贪餧而妄食。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118)洪兴祖:《楚辞补注》,第305页。,可谓是贾谊的先声。只是此“德”的内涵与上下文联系起来看,偏重于君王给与恩惠之义。东方朔《七谏》后来曾重复此义:“经浊世而不得志兮,愿侧身岩穴而自讬。欲阖口而无言兮,尝被君之厚德。”(119)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22页。贾谊明确将出仕与退隐视为士人判断君王是否具有“盛德”作出的选择,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保全自己,主张君王有德就留,无德即藏,即其所谓的“知命”、“委命”。因此,他在《吊屈原赋》最终引出“所贵圣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120)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12页。的人生主张,又在《惜誓》中重申“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121)王洲明、徐超校注:《贾谊集校注》,第447页。。可以说,贾谊“凤皇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一语可以作为士人审时度势而选择进退的隐喻,其人生观不断得到后人的回应,如扬雄所谓“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冯衍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都是贾谊“知命”、“委命”观念的翻版。而且,贾谊所谓凤凰“自引而远去”的表达也有后来者回应,如严忌《哀时命》云“鸾凤翔于苍云兮,故矰缴而不能加。蛟龙潜于旋渊兮,身不挂于罔罗。知贪饵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宁幽隐以远祸兮,孰侵辱之可为”(122)洪兴祖:《楚辞补注》,第438页。,崔寔《答讥》云“麟隐于遐荒,不纡机阱之路。凤皇翔于廖廓,故节高而可慕”(123)欧阳询:《艺文类聚》,第460页。。当汉代士人将凤凰的高翔或降临与士人基于时势作出行与藏的政治选择反复并置时,凤凰就被形塑为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以全身远祸为目的的智者,这样的智者就是汉代的理想士人人格。
汉代士人形塑的凤凰没有褪去传达天命的使者身份,而主要是审时度势以选择进退的智者的赋形,潜藏着吁求君德、消解士不遇焦虑的文化动机。战国末期,屈原可以离开故国,为其他君王所用,但他最终没有离开,而是“自尽其爱君之诚”,“死生、毁誉,所不顾也”(124)洪兴祖:《楚辞补注》,第73页。。时至建立了大一统政权的汉朝,皇权笼罩了每个角落,可以延揽人才的封国留给士人流动的空间也极其有限,不遇的士人只能选择退隐的道路。为了保持高洁,屈原选择了死,贾谊则主张隐。贾谊全身远害、明哲保身的主张与屈原“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125)洪兴祖:《楚辞补注》,第72页。的选择相比,显得缺少社会政治批评的锋芒。
综上所述,源出原始信仰的凤凰,在殷周之际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与巫文化的关联被弱化,被注入以君权神授、德配天为核心内涵的天命观,以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又弱化凤凰与天命的关联,注入道德内涵,以建构理想的士人人格。战国末的屈原、宋玉以及汉代的贾谊等书写士不遇的文学主题时消解或改造凤凰与天命的关联,建立起其与士人关于现实体认与政治选择的关联。屈原将凤凰形塑为高贵的流浪者,贾谊将凤凰形塑为审时度势的智者。还原凤凰形象背后的知识与信仰以及文化动机,才能充分认识不同文学作品中凤凰形象的共相与变异。早期中国的凤凰形象一直处在不断被祛魅与赋魅的动态之中,而且,这个动态过程远没有结束。凤凰与士不遇文学主题联姻以来,在历代士人关于政治环境的体验、个体人格的矜扬、不遇的焦虑及消解的文学书写中,二者形影相随,凤凰最终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经典形象,成为士人才德的表征,也成为士不遇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