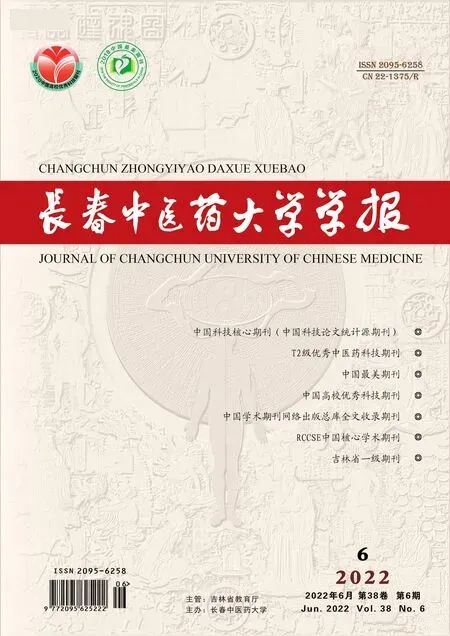中医运气学与疫病临证辨析
沈娟娟,张文风,魏 岩,马 丹,姜立娟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五运六气之应见。”有了运气的具体名称。 运气理论主要包括五运和六气两个部分,运气理论是以“天人相应”的整体恒动观为指导思想,五运、六气、三阴三阳为核心理论,运用天干、地支为演绎工具,研究天体运动,气候的变化规律,生物的生化及疫病流行之间的关系[1]。
1 《内经》运气理论对“天地人”三体的认识
《内经》运气理论运用“天人相应”的整体恒动观思想认识和研究人体生命活动节律及发病规律,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自然四时六气是一个有机整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阴阳四时者,万物之始终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责不起。”自然界有四时阴阳的对立统一,五行五方之气的生克制化,六气的胜复变化,以维持整体的动态平衡,为万物提供生、长、化、收、藏的气候条件。但气运异常,或太过或不及,故而产生各种胜、复、郁、发的气象因素,影响人体正常生理活动[2]。自然与人是一个有机整体。《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天元纪大论》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自然界气候变化是五运六气相互作用的结果;五运六气变化可以直接影响人体的五脏六腑之气。《内经》运气理论将天之六气、地之五运、人体之脏腑紧密相联,形成了“四时五脏阴阳”的理论体系,认为自然界天地万物,四时六气,人体的生命活动是一个运动的整体,对于人体生命规律和疾病规律应从整体运动观来认识和分析。
2 《内经》运气理论与疫病
在现存的文献古籍中,关于疫病的最早记载可见于《内经》,《内经》以运气理论的角度阐述了疫病的发病规律及因机证治。《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记载:“瘟疠大行,远近咸若。”“疠大至,民善暴死。”《素问·刺法论》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内经》指出在不同纪年的运气变化中,随着岁运的递迁、客主加临,胜复,郁发,出现德化政令,气候异常变化,万物失序,形成了疫病流行的时空环境,为疫病的发生创造了外在环境条件[3]。运气理论运用干支甲子推导不同纪年的气候物候变化,分析气候物候变化对人体生命节律及发病规律的影响,可预测疫病的发生及流行情况,为指导疫病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2.1 《内经》运气理论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
《内经》运气理论对疫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和阐发是重要精髓。《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自然界有风寒暑湿燥火六气的变化,六气的异常变化是导致人体发病的外在气候因素。《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岐伯曰:应则顺,否则逆,逆则变生,变则病。”随着四时阴阳消长变迁,出现相应的气候物候变化,当实际出现的气候与应有的气候不相应,或“至而不至”,或“未至而至”,出现应温反凉、应寒反温等异常变化;人体生理不能适应这种骤然发生的气候变化,导致一时、一地的人群多人罹患疾病,形成流行态势,即为疫病[3]。
运气理论中主运、主气变化可以说明气候的常规变化,推测各年各个季节的一般发病规律,可以分析对于人体脏腑功能的影响。岁运太过、不及和客气的变化,能推测气候的异常变化,预测每年疾病的特殊规律[3]。岁运太过之岁,本气流行,不胜之气受戕,相应脏器受累。岁运不及之岁,本气不足,克气盛行,相应的本脏之气不足和他所不胜的脏器受累。在岁运太过或不及的情况下,可导致运气中的胜气和复气,进而影响相应的脏腑病变。《医学入门》曰:“医之道,运气而已矣,学者可不由此入门而求其蕴奥耶”。
2.2 《内经》运气理论对疫病防治的认识
2.2.1 调养正气为本 根据运气理论预测到自然界气候的异常变化,固护人体正气,积极采取相应的防病措施,可达到预防疫病的目的。《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明确提出“治未病”预防学思想,根据五行生克制化原则,在治疗中治所病之脏,并且防治其传变,治其未受邪之脏,以达到预防疾病传变的目的。《灵枢·本神》曰:“故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内经》中关于预防疫病的基本思想为提掣天地,把握阴阳,强调合于阴阳,调于四时,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法于天地。
2.2.2 调和阴阳,祛除疫邪为要 运气治则的特点体现在运气气化治则,即把脏腑失调和运气气化失常密切联系,宏观地整体地对人体脏腑进行调治。《内经》根据四时的常变,提出“必先岁气,无伐天和”法时而治的思想。《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无失天信,无逆气宜,无翼其胜,无赞其复,是谓至治。”阐明治疗疫病不要违背天时规律,故在遣方用药之时应注意“时必顺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提出在临证治疗时要考虑自然环境及地理环境对疾病的影响。提出“法天则地、从容人事”的论治思想[4]。
3 《内经》运气理论对疫病医家的启示
《黄帝内经》运气学说,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唐宋以后医家受到运气理论的启示,将运气理论结合医疗经验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想。宋金元时期,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医家从运气学理论角度研究疫病的流行特点,分析疫病的致病机理,丰富了疫病的治疗原则和方法。明清时期,医家对于疫病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受到《内经》运气理论的影响对疫病的辨证论治,总结出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5]。
理论逐步发展阶段。南宋时期著名医学家陈言推崇《内经》,故辨治时行民病以《内经》之论为本,根据《素问·气交变大论》中对于五运太过、五运不及之年的描述,提出了五运时气民病,并制定五运证治方10首。阐述岁运太过不及对于人体五脏功能的影响,以药食五味补泻五脏虚实,调整人体阴阳盛衰,将五运六气理论落地于临床辨证论治,并对外感类流行疾病的防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金元时期医家刘完素运用运气学说,将疾病分为五运主病、六气主病,阐述不同纪年司天、在泉胜复变化的证治,重视病机学说和运气学说的联系,探讨亢害承制的病机理论,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学术观点,治疗善用寒凉之品,善治杂病,后世称其“寒凉派”代表医家[6]。元代医家朱震亨运用“天人相应”的理论通过分析天地、日月、阴阳动静状况,借以说明人体生命活动的阴阳消长规律,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观点。在病机方面,从湿热相火入手,提出“气有余便是火”的观点,治疗上从气、血、痰、郁着眼,为治疗杂病的大家[7]。
理论深入阶段。明代医家吴有性以天地变化之“常”“变”区别致疫之杂气与六淫邪气,认为疫病发病为感染天地之“异气”即疠气。将疫病与一般外感进行区别,并揭示疫病的传染方式、侵犯部位与传变特点,提出疏利募原,分消表里的治则,创立瘟疫学说的辨证论治体系。清代医家薛雪重视运气学说的临床实用性,薛雪擅长结合运气分析病因病机,指导诊断和处方用药。对于疫病发病病机及治疗的探索,主张结合分析三年中客气的变化规律;对于内伤杂病,则侧重研究值年客气的变化,继承《内经》气化理论,论述了湿温发生发展规律、病症特点、病机转归[8]。
4 疫病临证辨析
丁亥五月,监生李廉臣女,年十八,患温,体厥脉厥,内热外寒,痞满燥实,谵语狂乱,骂詈不避亲疏,烦躁渴饮,不食不寐,恶人与火,昼夜无宁刻。予自端阳日诊其病,至七月初三始识人,热退七八而思食,自始至终以解毒承气汤一方,雪水熬石膏汤煎服,约下三百余行,黑白稠黏等物,愈下愈多,不可测识,此真奇证怪证也。廉臣曰:若非世兄见真守定,通权达变,小女何以再生。治法方药:白僵蚕(酒炒,三钱)、 蝉蜕(全,十个)、黄连(一钱)、 黄芩(一钱) 、黄柏(一钱)、栀子(一钱)、 枳实(麸炒,二钱五分)、 厚朴(姜汁炒,五钱)、 大黄(酒洗,五钱)、 芒硝(三钱,另入)(《伤寒瘟疫条辨·卷二·里证》)[9]。
按语:本医案于丁亥年五月发生,丁亥年岁运为木运不及之年,司天之气为厥阴风木,岁运五行属性与司天之气五行属性相同为同天符年。逢天符之年,气候变化剧烈,易引起气侯和物候的异常变化,患者五月发病,气温炎热。《素问·举痛论》曰:“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热为阳邪,可致腠理开泄,营卫大通,津液外泄,见大汗出,气随汗泄于外,此时受虚邪贼风侵袭,人易发疾病,即为“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火热之邪内通于心,热邪内迫脏腑,内扰心神,扰乱神志,则见瞀闷、烦躁;心中有热,煎熬成痰,痰火上扰神明,则谵语狂乱,骂詈不避亲疏。热邪下注于肠胃,腑气不通可见腹胀、痞满、不食、大便不行。
治疗应以辟秽解毒,通腑泄热为主。方用解毒承气汤,为大承气汤与升降散加减化裁而成。方中僵蚕味辛苦气薄,喜燥恶湿,得天地清化之气,轻浮而升阳中之阳,故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 蝉蜕气寒无毒,味咸且甘,为清虚之品,能涤热而解毒;黄连以清心火,黄芩以清胃火,黄柏入肾经以清下焦之火,黄连黄芩黄柏合用清泻三焦火热;栀子轻清,沟通上、中、下三焦,清热凉血;枳实、厚朴、大黄、芒硝为大承气汤组方,大黄、芒硝泻热通便;厚朴、枳实行气散积,消痞除满;方中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此方是也。”故用解毒承气汤以行辟秽解毒、通腑泻浊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