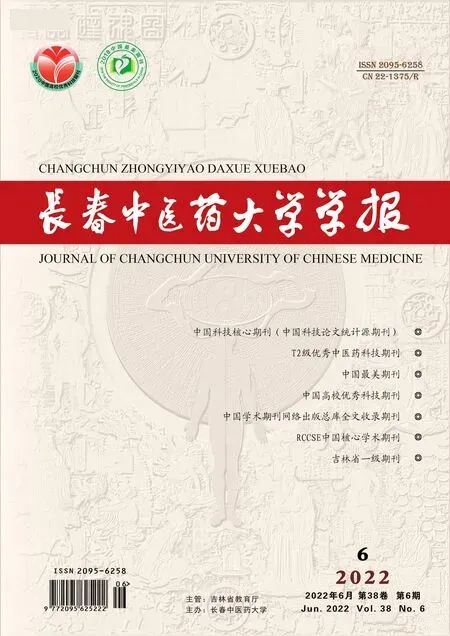祛秽解毒理论在中医疫病治疗中的运用
张钤奥,黄钲淇,刘 果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中医认为,疫病是具有强大流行性和传染性的一类外感疾病。如清代莫枚士《研经言·温疫说》[1]谓:“疫者役也,传染之时,病状相若,如役使也。”传统中医在治疗疫病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对此类疾病的认识有了相对完善的理论认识。从中医角度看,疫病的治疗与普通的外感时气同中有异。同者,脏腑经络气化无二,同需随证辨治;异者,疫病有疫毒之气侵犯人体,因而逐疫思想贯穿始终。现从理论和医案两部分详细论述。
1 理论部分
1.1 五行邪毒说
在《黄帝内经素问·刺法论》中将疫邪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疫。其谓:“寒暑燥湿风火,天之阴阳也……木火土金水,地之阴阳也……”即暗示疫病之邪属于有形之地气。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避温第二》中即从五行分类之法论疫病,称其为“五脏阴阳毒”[2]。而其用药也多有解毒、攻逐之品。如升麻、芒硝。可惜从现有文献来看,五行毒邪理论自唐宋以后未见使用,也无医案保留下来。
1.2 三焦秽浊毒邪说
三焦之说来自仲景《伤寒论·辨脉法》:“寸口脉阴阳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于上焦,浊邪中于下焦……。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里气微急。三焦相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藏气相熏,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3]。因其论中描述之疾病病状险恶,与疫病无二,故后世医家以此为据论治疫病,他们认为,疫邪为清浊之邪侵犯三焦。清浊之邪为口鼻吸受,不同于六淫。如杨栗山论:“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恶秽既通,乘势追拔,勿使潜滋”[4]。主以升降散透血分热毒,通解三焦,逐邪解毒为治。又如吴又可、戴天章等主张以达原饮溃达膜原(膜原为三焦膜系近于胃口的一部分),令邪气从表里分出而愈。盖三焦膜原为人体半表半里。邪气在此无出路,故需达之而从表里分解。又如吴鞠通论:“温毒者,秽浊也。凡地气之秽,未有不因少阳之气而自能上升者”[5]。此少阳即指三焦。
仲景之所以不言风、寒,而以清浊之邪命名者。提示了疫邪不能完全等同于六淫。而将邪气分清浊两种,又分别中于上下二焦。更是提示了疫邪侵犯广泛。遍及上下,既伤无形之气(清邪),也伤有形之体(浊邪)。浊邪还鲜明的指出了疫邪秽浊的特点。而之所以以三焦立论者。手少阳三焦属相火,又主水道。水火胶结的气化特点最符合疫邪秽浊而易于化热的特点。且三焦为人体半表半里,能连接人体表里内外。符合疫邪侵犯部位广泛的特点。但三焦毕竟以相火为其气化,而相火与湿热、火热同气相求。故三焦毒邪说适用于湿热、火热浊毒在心包三焦之分者,是逐疫法最具代表性者。
1.3 其余疫邪类
除三焦火毒秽浊外。尚有邪犯阳明少阴为主者,毒在无形之气血,治疗以清热凉血为主。因其非少阳秽浊之邪,无以攻逐,故重在解毒为治。代表如余师愚《疫疹一得》所载:“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6]。疫疹指以发斑疹为主症的疫病。因为手少阴心属火主血脉,足阳明属燥金主肌肉。故受邪毒侵犯多从其气化而表现燥热之象。在于体表则血脉肌肉大热,初则头痛如劈、腰如被杖,继而发为斑疹。郁于阳明胃肠则“腹如搅肠,呕泄兼作”。还有寒湿类疫,不宜攻下,可以发散温通、化湿祛浊兼以解毒治疗。代表如东坡圣散子“治伤寒、时行疫疠、风温、湿温,一切不问阴阳两感,头项腰脊拘急疼痛,发热恶寒,肢节疼重,呕逆喘咳,鼻塞声重。及食饮生冷,伤在胃脘,胸膈满闷,腹胁胀痛,心下结痞,手足逆冷,肠鸣泄泻,水谷不消,时自汗出,小便不利,并宜服之”[7]。盖足太阳属寒水,主一身之表及小便(膀胱)。足太阴属湿土,外连四肢,内主运化。寒湿邪毒与此二处同气相求。太阳伤则发热恶寒、周身拘急疼痛而小便不利。太阴伤则手足逆冷、肠鸣腹泻、水谷不消。故原文虽说“一切不问阴阳两感”,但参合诸症,显然是寒湿类邪气所致之疫。余杂疫如《松峰说疫》所言:“三曰杂疫。其症则千奇百怪,其病则寒热皆有……”[8]即是。
1.4 鬼毒说
葛洪《肘后备急方》说:“其年岁月中有疠气,兼夹鬼毒相注,名为温病”[9]。古人观察到疫病的传染性,如鬼毒中人,故以此名之。与现代微生物传染致病异曲同工。古人在此基础上探索了大量“治鬼邪”之药。此类药物不仅治疫,还多用于防疫、净化疫区。如升麻,《本经》认为,其可“主解百毒,杀百老物殃鬼,辟温疾、障邪毒蛊。”此处温疾传染类疾病。而其中所说的解毒、杀鬼、除邪毒蛊即是古人认为升麻发挥作用的原理。正是因为升麻对这类鬼毒、障邪毒蛊具有祛除的作用,故可用以“辟温疾”。
2 治疗概要
由于五行疫毒的案例不见记载。故下面将列举风火疫、燥热疫、寒湿疫以及古人以鬼毒法治疗疫病的案例,并加以分析,以示理法。
2.1 风火疫(少阳厥阴类疫)
2.1.1 三焦秽浊逐疫案 壮热神糊,陡然而发。脉数大,而混糊无序。舌垢腻,而层叠厚布。矢气频转。小溲自遗。脘腹痞硬。气粗痰鸣。盖是症也,一见蓝癍,则胃已烂,而包络已陷。迅速异常,盍早议下,尚可侥幸。(《柳选四家医案·疫邪门》[10])。
药用厚朴、 大黄、黄芩、枳实、 槟榔、草果、知母、陈皮。
再诊,神志得清,表热自汗。腹犹拒按,矢气尚频。便下黏腻,极秽者未畅。小水点滴如油。脉数略有次序。舌苔层布垢浊。胃中秽浊蒸蕴之势,尚形燔灼。必须再下,俟里滞渐楚,然后退就于表。
药用大黄、枳实、银花、知母、细川连、丹皮、滑石、玄明粉、厚朴。
三诊,大腑畅通,悉是如酱如饴极秽之物。腹已软而神已爽。表热壮而汗反艰。舌苔半化,脉数较缓。渴喜热饮,小水稍多。此际腑中之蒸变乍平,病已退出表分。当从表分疏通。先里后表之论,信不诬也。
药用柴胡、枳实、通草、紫厚朴、法半夏、连翘、橘皮、赤苓、大腹皮、藿香。
四诊,表热随汗就和。舌苔又化一层。脉转细矣。神亦倦矣。病去正虚之际,当主以和养中气。佐轻泄以涤余热,守糜粥以俟胃醒。慎勿以虚而早投补剂。
药用桑叶、石斛、扁豆、神曲、丹皮、豆卷、 甘草、橘白、薏仁、半夏曲。
此案初诊患者即有舌苔垢腻、脘腹痞满等秽浊阻滞三焦之象。而濈濈自汗是热已伤及阳明之分。神昏者,三焦心包相表里,三焦秽浊邪热犯于心包,蔽其神明所致也。然而胃与心包之热都是由于三焦秽浊瘀滞所致。故症状上以秽浊、满闷之象为主。若独攻其胃,则三焦之邪不能顺传入胃中。若用凉开心包之药会加重三焦秽浊之闭阻。故治疗以达原饮溃达三焦秽浊,重用大黄逐邪外出。二诊,神志得清,是三焦秽浊得下,心包得安。而舌苔未尽、腹仍拒按、秽浊不畅是邪气未尽。故需下之又下。只是膜原阻滞已溃,病入胃中,故去溃达膜原之槟榔草果等,而加重清热利湿、解毒通下之品如黄连、芒硝、滑石等,令邪气从前后分消。三诊患者里证已解,表热反壮而汗出不畅。故用柴胡、连翘、藿香升散解之。此时患者小水仍旧不畅。故加赤苓、通草导邪于下。同时佐以厚朴、枳实、大腹皮、橘皮等,令三焦通畅,则邪易外出而解。四诊汗出热退,脉虚神倦。以和中气并佐轻泄以涤余热。桑叶透热于外,扁豆、神曲、半夏曲、豆卷、薏仁化湿祛浊于内。石斛、甘草、橘白益气阴以和胃,并能解余热。此时病邪大势已去,正虚显现,却不早用补益,而是寓调养于轻泄之中。正是逐疫思想贯穿始终的表现。
2.1.2 毒秽入于心包案 朱某,疫疠秽邪,从口鼻吸受,分布三焦,弥漫神识。今喉痛丹疹,舌如朱,神躁暮昏。上受秽邪,逆走膻中。当清血络以防结闭。然必大用解毒。以驱其秽。(《临证指南医案·疫》[11])。
药用犀角、连翘、生地黄、玄参、菖蒲、郁金、金银花、金汁。
本案病因为“上受秽邪,逆走膻中。”病已入心包膻中血分。心包为心之宫城。而心主血舍神,其经又过咽喉。故热毒疫邪犯此,可见神躁暮昏、喉痛丹疹。治疗除了清血络、防闭结以调心包之功能外。还需要大用解毒、祛秽。此方生地黄、玄参凉润而不滋腻,故能凉血而不留邪气。菖蒲、郁金不仅可以宣通心包之气血、开心窍。同时菖蒲气味芳香,具有芳香化浊之效。金银花、连翘清热解毒,同时可以引邪外出,且金银花气味轻清,亦能以清化浊。吴氏认为:“犀角灵异味咸,避秽解毒……”。在此使用,除通心以外,尤能以其灵异之性而辟毒邪。金汁败毒,是以秽解秽之法。此方药仅八味,而芳香解毒、灵异辟邪、以秽治秽、泻火解毒,诸祛秽解毒之法具备。此方用药还能紧扣心包,宣心气、开心窍、泻心火、通润血络。可称为治法典范。
以上二案,一在三焦膜原气分,一入心包膻中血分。气血治法不同,但祛秽解毒则一也。
2.2 燥热毒疫案
安徽富藩台堂夫人病疫,初起但寒不热,头晕眼花,腰体疼痛。……诊其脉,沉细而数。稽其症,面颜红赤,头汗如淋,身热肢冷,舌燥唇焦。予曰:非虚也,乃疫耳。……暂用凉膈散,清其内热,次日斑点隐隐,含于皮内。吾见骇然曰:几误矣。即投败毒中剂,加大青叶钱半,升麻五分。次日周身斑见,紫赤松浮,身忽大热,肢亦不冷,烦躁大渴,即换大剂。石膏八两,犀角六钱,黄连五钱,加生地一两,紫草三钱,大青叶三钱,连投二服,斑转艳红,惟咳嗽不止,痰中带血粉红。此金被火灼,即按本方加羚羊角三钱,桑皮三钱,棕炭三钱,丹皮二钱,又二服,嗽宁血止,色转深红,热亦大减。照本方去紫草、羚羊、桑皮、棕炭;减生地五钱,石膏二两,犀角二钱;加木通钱半,滑石五钱,以小水不利也。又二服,诸症已减十分之六,犹用石膏二两四钱,犀角二钱,黄连钱半,生地四钱,去木通、滑石。又二服后,用犀角钱半,黄连八分,石膏八钱,加人参一钱,当归一钱,麦冬三钱,五味子五分。连服二帖,饮食倍增,精神渐旺矣。(《疫疹一得·附验案》[12])。
此案即余师愚所载燥热疫。燥热之疫因不夹三焦秽浊疫邪而无满闷之证。故治疗上重在清热泻火解毒。燥犯阳明之气,热伤少阴之血,为病则多发斑疹。此案初不见斑疹,而外但寒不热。合参色脉中热象,余氏以热郁投以凉膈。凉膈散本为治胸膈之间热邪。而此证在少阴阳明。故余氏次日见疹,认为“几误矣”。凉膈散虽然不甚切证,但毕竟可疏解郁热。故也有利于热邪外达,不为大逆。遂改用清瘟败毒饮大剂。此方除石膏辛寒以治阳明燥热外,黄连、犀角、栀子、竹叶、黄芩等合用可以遍清三焦气分、心与包络血分的火毒。此案还在此基础上加入大青叶、升麻、紫草等凉血解毒托斑。经两次治疗斑疹从紫黑转艳红,是热毒之势已折。但仍旧见咳痰带血,知其木火刑金,而用羚羊角、桑叶等清金泻木火。见其小水不利,是心火移于小肠,故用木通滑石导热从小便而去。善后如人参、麦冬、当归、五味子等亦不忘清热解毒之犀角、黄连、石膏。其解毒之法贯穿始终,从此可见一斑。
2.3 寒湿类疫案
王元双患寒疫。人事倦卧,饮食不进,满口布白,牙龈、上腭以及喉间皆无空隙。余验其证,舌上滑而冷,四肢厥冷,小便色白,其为寒疫也明矣。即令浓煎生附汁,绵蘸频搅口舌。遂用人参、白术、茯苓、故纸、干姜、白蔻、生附、熟附,大剂煎饮二剂,温醒胸中冷痰,呕出碗许,而人事稍安。前药再投,冷痰渐活,布白渐退,旬日而痊。(《齐氏医案》[13])。
此案为寒湿类疫,疫邪与寒湿相抟结。其“满口布白,牙龈、上腭以及喉间皆无空隙。”显然提示寒湿之邪停聚不散。治疗需要逐邪,却不可清热解毒等寒凉逐邪药。故用生附子汁,取其辛热,化开寒浊。而后治疗以人参、白术、茯苓、干姜温中阳而化湿浊。配合补骨脂补火助阳,制附子温阳散寒。这些药可温阳散寒化湿以扶正祛邪。但疫邪以邪实为主要矛盾,故配合白蔻芳香、生附雄烈走窜以温醒胸中冷痰。此寒湿疫,虽然用药大有不同,而逐疫之思想无二。
2.4 除鬼邪得效案
汉建宁二年,太岁在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有书生丁季回从蜀青城山来。人各惠之一丸。灵药沾唇,疾无不瘥。(《备急千金要方·避温篇》[14])。
雄黄、雌黄、曾青、鬼臼、真珠、丹砂、虎头骨、桔梗、白术、女青、川芎、白芷、鬼督邮、芜荑、鬼箭羽、藜芦、菖蒲、皂荚。
此方雄黄、雌黄均是古人用于避秽、驱鬼之药。芜荑、藜芦则有杀虫(虫亦是古人对于致病生物的一种称谓)之功。以上药物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看来确实无法理解。但却能取得“疾无不瘥”之效。纵观此方,独以驱邪为要旨。可见在疫病的治疗中,驱邪之重要性。与现代医学发现传染病是由致病微生物引起,从病原体入手进行防疫、治疫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此类理法现已少人论及、使用。但毕竟是古人宝贵的实践所得,也能很好体现其逐邪思想。未必不能成为探索中医药祛疫专药的入手处。
3 小结
以上诸案包含了不同种类疫病的治疗。均体现了古人在疫病治疗中逐邪的思想。不难看出,古人在疫病的治疗中,通过审查疫邪的性质及侵犯部位选择相应的药物逐邪解毒。既能观其性而折之,又能因势利导、逐邪外出。疫病的重症往往治疗旬日乃可痊愈,故古人治疗上将逐疫解毒思想贯穿始终,而能随其症变,圆机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