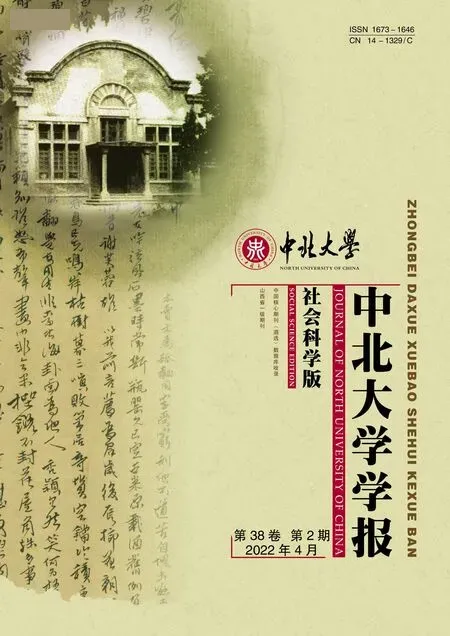先秦诗歌的体式特征及其生成机制
吴大顺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诗歌的体式是在诗歌具体的运行活动中逐渐形成的, 诗歌的运行机制是诗体建构的重要因素。 先秦诗歌的运行机制是指诗歌生成、 发展、 流变等运行活动中各种构成要素及其功能的相互关系。 如运行的空间、 动力机制、 功能和行为主体、 接受对象等, 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决定着诗歌的社会功能、 文化属性, 从而对诗歌的体式产生制约与促进的作用。 在此, 笔者重点对先秦诗歌的运行环境、 文化功能、 传播方式以及影响先秦诗体建构的主要机制进行分析。
1 先秦诗歌体式的诸种类型
从现存典籍保留的韵文材料看, 先秦韵文体主要有四言、 五言、 杂言和骚体四种。 在此, 以《诗经》《楚辞》及先秦古歌谣为例, 对先秦几种主要韵文体式及其结构做简略梳理。
1.1 四言体式
四言体式是先秦韵文的主要体式, 《诗经》最为典型。 从现存《诗经》的句式看, 305篇中共有诗句7 297句, 其中四言体6 612句, 杂言体685句, 四言体占全部诗句的91%。(1)本文对《诗经》的断句, 以王力《诗经韵读》为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雅诗的四言句比例最高, 占比超过95%; 颂诗的四言句占87%; 十五国风中的四言句占86%, 相比雅诗、 颂诗都低。
先秦典籍存留的古歌谣, 大致有几种类型: 第一类是史前原始宗教仪式中的祝祷之辞及咒语, 如《墨子》载商王驱旱祷辞曰:“万方有罪, 即当朕身。 朕身有罪, 无及万方。”[1]77第二类是《周易》中的“爻辞”。 第三类是历史叙述语境中的“古歌”。 如《尚书·虞书·益稷》系名虞舜皋陶的《赓歌》:“股肱喜哉, 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 元首明哉, 股肱良哉, 庶事康哉。 元首丛脞哉, 股肱惰哉, 万事堕哉。”[2]144第四类是先秦诸子与早期“小说”话语中的“古歌”, 多为书写者依托历史记忆的虚构。 这些古歌谣的真伪问题须作甄别。 史前原始宗教仪式的祭歌当是历史的真实反映; 《周易》卦爻辞中的古歌谣反映了先周歌谣的部分历史片段; 《尚书》中传录的一些歌谣, 显然是书写者在历史叙述语境中对虞舜远古历史记忆的记录, 歌辞的语言特征是书写者当下语言风貌的反映; 先秦诸子与早期“小说”话语中的“古歌”, 多是书写者依托历史记忆的虚构之辞。
综合以上因素基本可以判定, 这些歌谣与《周易》 《诗经》应大致同时或稍后。 如《国语·晋语》载《暇豫歌》、 《左传》载《狐裘歌》《梦歌》《乡人歌》《莱人歌》《齐人歌》等, 均以四言为主, 兼杂五言杂言。
1.2 五言体式
目前, 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五言”韵语, 当属殷商甲骨卜辞中的一则求雨龟占辞:“癸卯卜, 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369
占辞的前两句记载占卜时间和求雨事象, 后四句是一组五言韵语, 预示下雨的方位, 有学者称其为“最早的五言诗歌形式”[4]14。 现存文献传录的先秦古歌多有“五言”句式。 如《礼记·郊特牲》载《蜡辞》“草木归其泽”; 《尚书·夏书》载《五子歌》“郁陶乎予心, 颜厚有忸怩”等。 《周易》卦爻辞的“五言”韵语句式也较多。 《左传》 《国语》等文献记载的春秋战国歌谣中也有较多“五言”句式, 《诗经》除四言主体句式外, “五言”是最多的。 如《魏风·十亩之间》几乎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十亩之间兮, 桑者闲闲兮。 行与子还兮。 十亩之间兮, 桑者泄泄兮。 行与子逝兮。”在四言中夹杂五言的作品共115首, 多出现于“大雅”和“三颂”部分。
先秦时期“五言”韵语在殷周甲骨卜辞中就已出现, 可见自语言产生起, 二言、 三言、 四言、 五言等语言表达所需的基本句式就已经存在, 先秦古歌的“五言”句是当时语言风貌的真实反映。
1.3 杂言体式
在先秦时期, 杂言歌谣当是一种基本状态, 从《尚书》《周易》《左传》《国语》等传录的歌谣看, 完整的齐言占少数, 多数是四言间杂三言、 五言, 还有四言间杂三言、 四言、 六言、 七言等句式。 如《左传》载《梦歌》曰:“济洹之水, 赠我以琼瑰。 归乎归乎, 琼瑰盈吾怀乎。”《庄子》载《相和歌》曰:“嗟来桑户乎, 嗟来桑户乎。 而已反其真, 而我犹为人猗。”这些歌谣都是杂言体。 《诗经》在仪式咏诵及文本化过程中不断被齐言化, 但还是保留了《周南·螽斯》《卫风·木瓜》《王风·缁衣》等杂言作品。
1.4 楚辞体式
楚辞体, 主要指战国时期, 以屈原《离骚》 《九歌》 《九章》、 宋玉《九辩》 《招魂》为代表的文人诗歌体式。 屈原、 宋玉现存作品的句式大体有“6+兮,6”“4, 3+兮”“3+兮+2”“3+兮+3”“4+兮+3”五种类型。 楚辞句式的突出特点是在句子间使用“兮” “些”等虚词以调节句子的平衡。 《诗经》及先秦古歌中也有数量可观的“兮”字句, 特别是“4, 3+兮”句型在《诗经》中较为普遍, 是小雅“兮”字句的主体句型。 可见, 屈原等文人楚辞体, 不仅借鉴了楚歌, 也吸收了《诗经》“兮”字句型。
综上可见, 先秦时期的诗歌在体式上是四言、 五言、 杂言和骚体等多种形式并存的。 其中, 四言体是经集体确认的一种正统、 规范和普行的主流体式, 与之相应形成了诗歌典范形式的“齐言意识”。 先秦诗歌体式多元并存的格局以及逐步齐言化的趋势与先秦诗歌生成的文化环境及其运行机制是密切相关的。
2 先秦诗歌的运行环境及其文化属性
早期的韵文体是在舞、 乐、 诗合一的原始宗教和巫术实践中孕育而生的。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歌舞之兴, 其起于古之巫术乎。”[5]2在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中, 巫术能够沟通神灵, 达到“神人以和”的目的。 《说文解字》曰:“巫, 祝也, 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6]201《说文解字》释雩曰:“雩, 夏祭, 乐于赤帝以祈甘雨也, 从雨, 于声, 雩, 舞羽也。”[6]574舞的第一义项通雩, 指求雨巫术仪式中的羽舞。 甲骨文中有“辛已卜宾乎有雨”[7]630的记载。 《商书》曰:“恒舞于宫, 酣歌于室, 时谓之巫风。”[2]163可见, 在早期社会“舞” “巫”所指是同一事项, 即女巫师的巫术仪式以及巫师祈祷神灵的姿态, 后用舞蹈指巫师姿态, 而巫专指巫师这一类职事人员。
当然, 巫之上通神灵、 下接民意的行为是通过乐舞等仪式实现的。 所以, 中国韵文体之源头可以追述到原始宗教和巫术活动, 中国韵文体是在乐舞仪式活动中产生的。 夏、 商、 周以来, 因管理国家的现实需要, 逐渐将原始宗教的内容政治化、 人文化, 于是, 诗歌拓展了许多新的文化内涵, 但其本质属性和功能没能脱离礼乐文化和仪式、 政治和教化等基本功能。
总体而言, 先秦诗歌的文化属性大致有五类: 一是“饥者歌其食, 劳者歌其事”的民间歌谣, 如《击壤歌》《涂山氏歌》《麦秀歌》等。 二是宗族及国家的祭歌, 如《墨子》载商王驱旱祷辞、 《荀子·大略》载商王祷雨辞, 以及《礼记·郊特牲》载《蜡辞》。 三是反映政治的讽谏之歌, 如《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载:“太康尸位以逸豫, 灭厥德。 黎民咸贰, 乃盘游无度, 田于有洛之表。 十旬弗返。 有穷后羿, 因民弗忍, 距于河。 厥弟五人, 御其母以从, 傒于洛之汭。 五子咸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2]156四是占卜之谣辞, 如《周易》卦爻辞中保存的“古歌谣”等。 五是外交聘问中的用诗。 如《左传》《国语》中的大量引诗等。
《诗经》作为先秦诗歌的代表, 从其“风”“雅”“颂”的分类中体现了三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属性。 “十五国风”是周南、 召南、 邶、 鄘、 卫、 王、 郑、 齐、 魏、 唐、 秦、 陈、 桧、 曹、 豳15个地区的地方民间歌谣。 朱熹《诗集传序》曰:“凡《诗》之所谓《风》者, 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 所谓男女相与咏歌, 各言其情者也。”[8]2“风”大致为下层文化圈。 “雅”指朝廷的正乐, 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歌谣。 朱熹《诗集传》曰:“雅者, 正也, 正乐之歌也……以今考之, 正小雅, 燕飨之乐也。 正大雅, 朝会之乐也。”[8]155大雅31篇, 作者大多为周代上层贵族, 主题多数为“述祖考之美”, 其余有刺也有美, 但多针对当朝之王。 小雅74篇, 作者多为周代贵族, 其主题部分为“宴劳嘉宾”“亲睦九族”的燕飨之辞, 部分为颂美宣王之辞, 大部分则为刺幽厉王的讽谏诗。 “雅”属于上层文化圈。 “颂”作为王室祭祀歌辞, 是由宫廷乐人唱奏的神圣庄严的仪式之辞。 “颂”属于典型的上层文化圈, 具有权威性。
从《诗经》的分类可以见出其国家祭祀、 社会政治、 民间娱乐等雅俗文化的分野。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不同的文化属性不是截然区分的, 其间存在着交织、 互通与融合。 周代以观风为目的的呈诗、 献诗和采诗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是“诗三百”雅俗文化互通、 融合的重要机制。
3 先秦诗歌的活动空间及其功能
诗歌在具体的运行机制中所承担的功能, 对其节奏、 语言、 结构, 甚至语体等提出相应要求。 早期诗歌往往在仪式、 娱乐等活动中实现其政治、 教化、 教育等多种功能, 诗歌体式在诗歌的功能运行以及诸功能相互支撑、 相互渗透的关系中得以确认。 尤其在文体发轫初期的先秦时代, 一定的文体总是运用于一定性质的行为之中, 从而形成以功能来确定文体的传统。[9]
与韵文体母体、 原始宗教和巫术相关联, 先秦诗歌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仪式活动。 《诗经》的“颂”诗对周王朝开疆拓土历史的颂赞、 对周王朝“祖宗”盛德的赞美, 都是在仪式咏歌活动中进行的, 具有鲜明的仪式功能。 二“雅”中也有一部分是“宴劳嘉宾” “亲睦九族”燕飨仪式中的咏唱, 其仪式性特征明显。 “十五国风”也多是地方诸侯国的民俗仪式歌辞, 如《周南》《召南》。 《仪礼·乡饮酒礼》载:
乐正先升, 立于西阶东。 工入, 升自西阶, 北面坐。 相者东面坐, 遂授瑟, 乃降。 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 卒歌, 主人献工。 工左瑟一人拜, 不兴受爵……笙入堂下, 磬南北面立, 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 笙《由庚》; 歌《南有嘉鱼》, 笙《崇丘》; 歌《南山有台》, 笙《由仪》。 乃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 召南《鹊巢》《采蘩》《采蘋》。 工告于乐正曰: 正歌备。 乐正告于宾, 乃降。[10]985-987
《仪礼》之《乡射礼》《燕礼》《大射仪》等皆有相关仪式用乐的记载。 这些用乐记载所及曲调主要有《周南》《召南》和小雅, 其中有奏有笙, 也有歌。 关于其仪式功能, 《左传》《国语》多有提及。 如《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如晋, 晋侯享之。 金奏《肆夏》之三, 不拜。 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 歌《鹿鸣》之三, 三拜。 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对曰: ‘《三夏》,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使臣弗敢与闻。 《文王》, 两君相见之乐也, 使臣不敢及。 《鹿鸣》, 君所以嘉寡君也, 敢不拜嘉?《四牡》, 君所以劳使臣也, 敢不重拜?’”[11]932-933
最能体现先秦诗歌政治功能的当属《诗经》二雅中的美刺类诗歌。 如《大雅》之《假乐》乃“嘉成王也”[12]540; 《泂酌》《卷阿》乃“召康公戒成王也”[12]544-545。 《小雅》之《裳裳者华》《采菽》“刺幽王也”[12]478等。 西周中叶以后, 特别是西周末年到平王东迁时期, “王道衰” “周室大坏”, 政治怨刺之诗也随之增多。 如《大雅》之《民劳》《板》《抑》《桑柔》等“刺厉王”[12]547-558; 《瞻卬》《召旻》“刺幽王大坏”[12]577; 《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等“刺幽王”[12]440-451; 《巧言》《巷伯》之“伤于谗”[12]453-456。 这些政治美刺作品, 直接体现了诗歌的政治功能。
从其运行的机制看, 一是先秦时期献诗、 陈诗的制度。 《国语·周语上》载邵公言于周厉王曰:“故天子听政, 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瞽献曲, 史献书, 师箴, 瞍赋, 矇诵, 百工谏, 庶人传语, 近臣尽规, 亲戚补察, 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13]11-12二是诗歌的仪式、 娱乐等活动。 二雅诗多是“宴劳嘉宾” “亲睦九族”等燕飨活动的乐歌。 如上所举, 燕飨活动也是周代礼乐活动的重要内容, 具有很强的仪式性质, 如周代的燕飨诗原本是燕礼、 乡饮酒礼等典礼仪式上的咏唱曲, 因此, 燕飨之诗“并非纯粹表现欢聚宴饮的活动场面, 而是用诗歌的形式告诫人们要遵循宴飨礼仪, 重在突出宴飨能够联络情谊、 巩固统治的政治功利作用。”[14]59
对于《诗》教化功能的理解, 《诗》中“风”诗的采集和结集是最好的说明。 朱熹《诗集传》曰:“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 谓之风者, 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 而其言又足以感人, 如物因风之动以有声, 而其声又足以动物也。 是以诸侯采之, 以贡于天子; 天子受之, 而列于乐官。 于以考其俗尚之美恶, 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 旧说《二南》为正风, 所以用之闺门、 乡党、 邦国, 而化天下也。 十三国为变风, 则亦领在乐官, 以时存肆, 备观省而垂监戒耳。”又曰:“武王崩, 子成王诵立。 周公相之, 制作礼乐, 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 被之管弦, 以为房中之乐, 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 邦国, 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 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者, 皆得以取法焉。”[8]1朱熹对“风”诗的解释, 突出了风诗的教化功能。 “十五国风”不断地被采集和文本化, 其实也是出于周王朝教化的需要。
诗之教育功能既与诗的教化有关, 也与诗的政治功能有关。 在周代的礼乐教育中, “诗”是士子教育的“四术”之一。 《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 立四教, 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 春秋教以礼、 乐, 冬夏教以《诗》《书》。”[15]1342其中又有“瞽矇之教”与“国子之教”的分工。 以大师、 小师、 瞽矇、 眡瞭、 磬师、 笙师等职官构成的“瞽矇之教”系统, 其实质是培养服务于国家礼乐仪式的乐工, 重在培养音乐表演的技能。 如《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 曰风, 曰赋, 曰比, 曰兴, 曰雅, 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 以六律为之音。”[16]796而以乐师、 大胥、 小胥等职官构成的“国子之教”系统, 其目的是培养国家礼仪主持者、 布政聘向的使者等精通礼乐的政治人才, 除音乐技能外, 音乐之德义和言语是其重要内容。[17]23《周礼·春官·大司乐》载:“以乐德教国子, 中和, 袛庸, 孝友; 以乐语教国子, 兴, 道, 讽, 颂, 言, 语; 以乐舞教国子, 舞《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16]787
《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8]2525《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赵衰曰:“《诗》《书》义之府也, 礼、 乐德之则也。”[11]445《国语·楚语上》申叔时语曰:“教之《诗》, 而为之导广显德, 以耀明其志。”[13]489可见, 春秋时代, 人们对《诗》之教育功能是特别推崇的。
4 先秦诗歌的传播方式及其转化
先秦诗歌有的源于民间采诗, 有的来自公卿士大夫“献诗”, 也有的直接出自邦国史官, 成分多样, 其传播形态也十分复杂。 在此, 重点梳理与先秦诗体建构关系密切的几种方式和传播现象。
4.1 音乐传播及其“乐歌”性质
《诗》伴随周代礼乐制度而产生, 作为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诗》的早期传播主要伴随周代礼乐活动展开, 具有典型的“乐歌”性质。 在周代礼乐制度下, 《诗》在生成过程中, 形成了“风”“雅”“颂”的音乐分类; 又因周代礼乐制度之需, 西周形成了以传授音乐演唱技能为主的“瞽矇之教”和以传授“诗”之意义的“国子之教”两种方式。 瞽矇之教是注重“诗”之“声”的诗歌传授系统, 国子之教是注重“诗”之“德义”“言语”的传授系统, 二者施教的职官、 对象和内容多有不同。 从“诗”的传播历史看, 随着周代礼乐文化制度的发展变革, “诗”的两种传授方式也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即以“声”教为主导的西周时代, “声教”和“义教”并重的春秋时代和“声教”衰落 “义教”盛行的战国时代。[17]36西周时代, “诗”文本的编辑目的主要是为了仪式配乐的演奏; 春秋时期, “变风变雅入诗”, 使“诗”的讽谏目的逐渐取代其仪式功能, 乐歌开始出现于仪式之外的外交、 聘问等许多场合, 使“赋诗言志”成为仪式乐歌之外最特别的诗歌传播方式。
在此要强调的是, 春秋时期, 尽管“诗”文本编辑的目的由仪式乐歌向讽谏怨刺转化, “赋诗言志”以断章取义的方式大大彰显了歌辞的德义内涵, 但其传播的具体环境还是在具有仪式氛围的聘问、 燕飨等音乐演奏活动中, 其“乐歌”的性质并未改变。
4.2 文本传播及其“文学”身份
梳理《诗》的文本传播, 不能不关注西周中后期就已出现的“引诗”之风。 《国语·周语上》载, 穆王将征犬戎, 祭公谋父谏曰:“不可。 先王耀德不观兵。 夫兵戢而时动, 动则威, 观则玩, 玩则无震。 是故周文公之《颂》曰: ‘载戢干戈, 载櫜弓矢。 我求懿德, 肆于时夏, 允王保之。’”[13]2此外, “文公”, 周公旦之谥, 诗乃《周颂·时迈》。 此为现存文献所见最早的“引诗”之例。 “如果说歌诗偏重注意诗的乐章义, 赋诗偏重注意诗的情景义或象征义, 它们所实现的是交际功能和仪式功能, 那么, 引诗所强调的是诗句的思想内容, 实现以道德陶冶人的伦理功能。”[19]31-32可见, 引诗是摆脱了音乐和仪式的限制, 而立足于歌辞文本意义的相对自由的用诗方式, 这也是“诗”文本传播的早期形态。 春秋末期, “赋诗”之风随着“礼崩乐坏” “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而逐渐消亡, 只有独立于仪式歌咏之外的“引诗”之风兴盛不绝。
关于《诗》文本传播的另一重大事件是孔子“删诗”。 春秋末年, 孔子“删诗”并以之传授弟子的行为, 使“诗”文本最终定型。 孔子的这次“删诗”, 虽是出于复礼、 正乐目的, 但事与愿违, 此举进一步加速了“诗”与乐的分离, 使“诗”的文本传播最终取代了音乐仪式传播, 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 由此, 诗教也最终摆脱乐教, 走上德义化、 伦理化之路。 “诗”的“文学”身份则在德义化、 伦理化的阐释中得以凸显。
5 先秦诗歌体式建构的主要机制
从某种意义上说, 诗歌的体式建构, 是诗人在使用语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实践中, 对口语和书面语、 雅言与俗语选择和取舍的结果。 这种语言的选择和取舍既涉及语言自身的发展状态, 也关系到诗人的审美追求和诗歌的运行方式。 就先秦诗歌体式建构而言, 有几条重要的机制不容忽视。
5.1 诗歌的口语传播与雅言翻写
从传播史看, 先周的远古时期, 是以口传为主的时代。 黄帝使“仓颉作书”, 文字才孕育产生。 在此之前, 上古先民交流和记事的主要方式应是口耳相传的口语, 因此, 口语是上古先民使用的主要传播载体。 口语具有生动、 鲜活、 及时的特点, 其不足是稍纵即逝, 难以记忆和保存。 为了解决口语的记忆问题, 先民充分利用口语语音特点, 把生活中的重要事项和部落历史编成韵语, 以歌谣形式进行传播, 远古歌谣当是在这种传播语境中产生并活跃起来的。 殷商时期, 甲骨文的产生和使用增强了文字记录的精准性, 但书写载体和书写工具没有得到改进, 书写十分困难, 记录也十分有限, 口头歌谣仍然是先民记事的重要方式。
随着文字的演进、 书写载体和书写技术的发展, 文字记载的功能日渐强大, 开始出现了口语与文字两种传播方式并存的局面, 并形成了各自的语法规范, 即所谓口语和书面语、 雅言与俗语系统。 由于交流和记事的需要, 两种传播方式彼此之间又有互相吸收与转化的传播态势, 出现了雅言对俗语的吸收借鉴、 书面语对口语的影响等互动和渗透现象。 《诗经》“十五国风”, 来自15个语言风俗各异的地区, 而现存十五《国风》的语言体式却大体一致, 四言句达到80%以上, 特别是《曹风》四言句达到100%, 《桧风》四言句达到96%, 四言句最低的《魏风》也达到71%。 对此现象, 钱穆先生曾有过精辟的分析:“《诗经》里的十五国风, 乃当时西周王室随时分派采诗之官到各地去, 搜集一些当时在各地流行的民间歌谣, 再经过西周政府一番‘随俗雅化’的工作, 始得成其为诗的。 所谓随俗, 是说依随于各地的原俗, 采用了它的原辞句, 原情味, 原格调, 原音节。 所谓雅化, 则是把它来译成雅言, 谱成雅乐, 经过这样一番润饰修改, 而于是遂得普遍流传于中国境内。”[20]107
十五《国风》体式以四言为主, 间杂五言的语言体式和复沓的结构模式, 当是在采诗、 献诗实践中, 对各地民间歌谣雅言化翻写的结果。
5.2 仪式咏诵与“四言”诗体的生成
周代礼乐文化制度下, 诗歌被广泛使用于仪式咏诵行为, 周诗体就是在这种文化行为中生成的。 目前, 学界研究发现的关键性证据有两方面: 一是产生于西周中期的“一钟双音”技术与西周中后期青铜铭文的齐言化、 韵语化现象基本同步。[21]14二者的逻辑关系是, “一钟双音”技术规定了仪式咏歌的双音行进节奏, 而四言连句是双音节行声最简要的规则化形式。 二是仪式咏诵行为早在商代就已产生, 周代将之提升为一种专门技艺。 周诗“颂”类的韵化, 是在渊源久长的传统仪式歌咏活动中成熟的。
5.3 周代文士群体的审美追求与四言诗体的确认
先秦“诗”的创作有群体性创作和个体性创作两种类型, 十五《国风》 《颂》大致属于集体性创作, 二《雅》中的仪式歌辞及史诗性作品属于集体创作, 其中美刺性作品当属个人创作。 《毛诗序》对个人性创作的作品多有提示, 如《小雅》之《白驹》《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斯人》《角弓》等诗。 《大雅》之《公刘》《泂酌》《卷阿》《民劳》《桑柔》《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诗。 “诗”文本中也有关于作者的提示, 如《小雅·巷伯》曰:“寺人孟子, 作为此诗。”《大雅·崧高》曰:“吉甫作诵, 其诗孔硕。”这些诗歌的作者涉及召康公、 召穆公、 苏公、 大夫, 以及尹吉甫、 芮伯等人, 包括上层贵族、 王室成员以及诸侯各级中下层官吏, 是周代的“文士”群体。 这些文士群体对整饬化、 美感化的共同追求, 成为写作中一种集体行为, 从而使“四言”诗的体式得以确认, 成为一种范式。 可以说, 雅言诗的个人写作和民间歌谣的雅言翻写, 是周代“四言”诗体范式生成的直接行为机制。[22]
6 结 语
总之, 先秦诗体从句式上说有四言体、 五言体、 杂言体和楚辞体, 从语体上说有口语体和雅言体, 但总体趋势是, 句式上以“四言”诗体为主流, 语体形态上则口语与雅言兼备, 并逐渐雅言化。 这些体式特征的生成与先秦诗歌运行的空间、 功能和运行动力等机制关系十分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