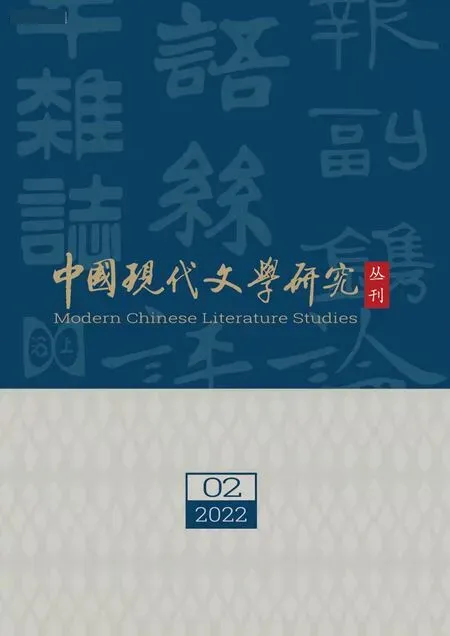论新文学与活体解剖之关系
邓小燕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新文学解剖学形象问题的补充,主要讨论新文学与活体解剖的联系及其相关伦理问题。在近代中国,解剖学观念是启蒙者文化批判的重要资源,新文学因之也具有强烈的解剖学特征,但启蒙者观念中的解剖学具有显著的科学主义色彩,这在围绕活体解剖的讨论中表现得尤其突出,要全面理解新文学的解剖学形象有赖于对此作出分析,文章通过对“人的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分歧,以及鲁迅有关《昆虫记》的评价等问题的分析来展开论述。
引 子
在讨论国民性话语时,刘禾曾提及新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医学及解剖学术语充斥在有关现代文学的讨论中”,她意识到新文学家肩负的一项重任,即“‘解剖’一国的病弱心灵以拯救其躯体”。①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9页。新文学的这种解剖学(医学)品格,绝不仅仅意味着启蒙者—大众间的某种医—病二元隐喻,而是实实在在地表现为与解剖学(医学)的深层联系,这种联系既体现为新文学对医学资源的广泛征引,也表现在医学意识形态对新文学品格的塑造上。
在讨论“新文学解剖学形象的兴起”时①见拙文《新文学解剖学形象的兴起》(未刊稿)。,笔者曾对解剖学如何参与新文学的社会文化批判以及如何塑造一种解剖美学问题做过专门讨论:作为一种以暴力方式打开身体的知识实践,解剖学长期不被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接受,只是到了近代,在空前严峻的社会危机下,解剖学暴力才最先在民族主义革命者那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现代解剖学的文化批判性进一步凸显,作为一种科学资源,解剖学成为新文化知识分子清理畸形的传统身体文化,尤其是展开对身体暴力史批判的最有力的知识支撑。同时,作为美学元素的解剖学也成为新文学的识别特征之一,新文学初期的文学思潮中,无论是近于浪漫主义的作者,还是近于写实主义的一派,都带有强烈的解剖意识。解剖学成为新文学之所以为“新”的因素之一,是其文化追求科学性的一种证据,使之与以往任何形态的文学区别开来,一种带有强烈分析性、批判性,以及反思和怀疑精神的文学伦理由此形成,这极大地增强了新文学回应个体与社会危机的能力,新文学的这种解剖学品格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新文学的解剖学形象还存在一个较少引起注意的问题,也即活体解剖,考察新文学与活体解剖的关系是全面理解新文学解剖学形象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西方有关解剖学的人文讨论中,活体解剖一直是个核心主题,它与后世有关生态伦理、动物解放的讨论也密切相关,并成为当前生态主义的重要精神资源,但在“五四”新文学场域中,这却不是特别受到关注的主题,有关材料相对零散,分布在创作、翻译与评论中,在后文中,我试着利用这些分散的信息,对新文学的解剖学品格作进一步讨论。
一 暧昧的开端:《生人解剖之魔王》
1914年《礼拜六》杂志第2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人解剖之魔王》的短篇小说,署名为黑子,这篇“医学轶闻”记载了一桩恐怖的解剖学故事:兰紫男爵退出行伍后,醉心于活体解剖术,开始只屠及“两翼四足之属”,遭到解剖的动物不知其数,后来动物已不能满足“研究”要求,竟开始以活人做解剖实验,这位男爵前后娶了六位妻子,全部死于活体解剖。文中特别讲述了男爵砍断妻臂与一黑人妇女换肢的实验,手术大获成功。在这段记录之后,“黑子”写道:“男爵当时笔录中自述如是,然诸君思之,四百年前学术尚在幼稚时代,男爵独能有此成绩,吾人不能不赦其残忍之罪恶,而佩其事业之光荣也。”①黑子:《生人解剖之魔王》,《礼拜六》1914年10月24日第21期。
《生人解剖之魔王》是值得注意的一个过渡性文本,作者并不否认男爵行为的残酷性,同时又对活体解剖试验持进步的价值评判,没有意识到道义与“科学”之间的紧张。尤其在谈到男爵最后被判绞刑的下场时,牵出教会因素,这和19世纪以来所形成的解剖学史图景——认为历史上科学发展之所以滞缓,是受到了保守的教会力量的阻遏——正好是契合的。这篇作品发表于1914年,作者对解剖学的态度不仅与早期中医界将解剖视为残酷的异端行为根本不同,与晚清出访外洋大臣参观解剖场景后发出“忍哉西人”的感慨也不可同日而语。
民国建立之后,解剖学合法化被推到舆论中心。先是1912年留学日本学医的汤尔和(1878—1940)在北京建立了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积极推动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制定解剖法案。1913年11月13日,江苏医学专门学校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尸体解剖,当时称为“中国破天荒之举”,由西医周威、汪企张主刀,江苏教育司长黄炎培亲自前来致辞②牛亚华:《中日接受西方解剖学之比较研究》,西北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158页。。在这“破天荒之举”后不久,11月22日,经汤尔和一再陈请,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解剖条例》获得通过。这两件与解剖学相关的事件,在民国建立初期的1913年前后,引起了舆论界的广泛关注,解剖学作为代表文明方向的一种现代知识,成为显示时代新气象的一个符号。这可能也是《礼拜六》这样一份面向大众的通俗文学杂志在讨论中世纪背景的活人解剖事件时,会呈现出伦理评价与科学判断上的价值分歧的原因,解剖行为的残忍性逐渐被淡化,科学进步的因素则被凸显出来。
虽说《生人解剖之魔王》或许只称得上文学版图中“旧派”的声音,但这里所显示的现代以来解剖学形象的阴暗面,却并不见得只在“旧派”中才有,这一点可以从“人的文学”与解剖学的关系中得到证实。
二 “人的文学”与解剖学
1926年朱自清在《文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飘零》的短篇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位留美归国,欲以学术为国服务而四处碰壁的青年W君,小说中有一段描写,是由P君转述出来的:
他(P君)说W在研究行为派的心理学。他几乎终日在实验室里;他解剖过许多老鼠,研究它们的行为。P说自己本来也愿意学心理学的;但看了老鼠临终的颤动,他执刀的手便战战的放不下去了。因此只好改行。而W是“奏刀然”,“踌躇满志”,P觉得那是不可及的。P又说W研究动物行为既久,看明他们所有的生活,只是那几种生理的欲望,如食欲,性欲,所玩的把戏,毫无什么大道理存乎其间。因而推想人的生活,也未必别有何种高贵的动机;我们第一要承认我们是动物,这便是真人。W的确是如此做人的。①佩弦:《飘零》,《文学周报》1926年8月1日第236期。
朱自清突出W的人格魅力时,特别谈到作为“真人”的动物性,并且设置了一个无法直面这一点的P君来作参照,通过解剖学认识到人性,认识到“真人”,这也是西方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显然这也是周作人“人的文学”的标准文学形象。在《人的文学》这篇文学革命时期的理论纲领中,周作人对“人”就有如下定义: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颅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有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该排斥改正。②周作人:《人的文学》,《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6页。
无论是周作人从动物进化的角度讨论人的位置,抑或是朱自清从动物解剖学的角度透视人的生理属性,都是从动物中确认人,这里就有一个微妙的矛盾,即新文学在确定其人文主义品格时,是通过降低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来实现的,而这正是比较解剖学的结论,行为派心理学对人的研究也有赖于此。鲁迅在《人之历史》中,也特别谈到这一点,他写道:“……人猿生猿人,不能言语,降而能语,是谓之人,此皆比较解剖个体发生及脊椎动物所明证者也。”①鲁迅:《人之历史》,《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由解剖学所呈示的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的论证逻辑,有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即人既是与动物无所区别的存在,但又是进化链条上的胜利者。关于这一点,周建人的说法则是一个更好的注脚,在回答“猿猴到底可以变成人吗?”这一问题时,周建人写道:
猿猴种族,以后是没有大希望的。因为它们到今天还没有变换成人,进步太迟了。它们要永远沦为畜类的。人是世界主宰,有千万年了。各种生物都操持在人的手掌中。世间有四种猴子,它们组成一个特别的团体,叫做似人猴类。有两种住在刚果树林里,不久恐怕就会给人扑灭的。还有一种住在马来西亚,它们的命运,暂时虽不敢断定,但是终究不免灭绝的。②周建人:《有趣的动物问题》,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2页。
达尔文的物种演化观点并不能指向人在物种中的优越性,它只是强调具有环境适应性的物种的优越性,那么就进化论的本意来说,适应环境的物种,无论是虫豸还是人类,谈不上等级上的优劣。因而,当鲁迅引用尼采的话:“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③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247页。,尼采认为超人是在进化的链条上对于人的超越,这观点当然也是鲁迅认同的,但它也掺杂了现代时期新文化知识分子对于进化论的误解。因而,从比较解剖学的角度探索人的本质时,认为一切生物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低等的,这种内在的矛盾通过一种被曲解的进化论弥合了,这一历史观念也参与并塑造了现代解剖学隐喻的形象。与活体解剖有关的道德争议,实际上也经常是指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本质,它与科学主义在价值观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文学中有关活体解剖的讨论就与此有关,新文学有关活体解剖的这种矛盾,较为突出地体现在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的翻译中。
三 译介中的分歧:爱罗先珂童话
1921年12月29日,鲁迅将所译爱罗先珂的童话《为人类》发表在《东方杂志》上,又特别附上一行“译者附记”:“这一篇原登在本年七月的《现代》上,是据作者自己的指定译出的。”①鲁迅:《〈为人类〉译者记》,《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藤井省三谈到“爱罗先珂本人‘想从速赠与中国的青年’而坚请鲁迅翻译”②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陈福康编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也透露了某种来自作者的“强迫”因素。在鲁迅的翻译生涯中,有作者本人在旁亲自指定具体篇目的,这是绝无仅有的,目前似乎还少有人意识到这可能造成的作者与译者的分歧,这里与本文主题相关的,是童话《为人类》和《鱼的悲哀》两篇。
童话《为人类》讲述了一个名叫K的享誉国内外的解剖学家,专门从事脑和脊髓研究,为了解剖,饲养了几百匹兔、白鼠和狗,因为K的解剖室就在大街上,因而在从事活体解剖的时候,动物的惨叫会引起路人的驻足惊叹。而K的儿子哥儿每闻动物惨叫,便要掩耳逃避,并且感到极大的痛苦。这种行为往往招致父亲的叱骂。为了研究在短期内取得极大的成就,K甚至将妻子和哥儿解剖了,他发表的脑髓研究“不但在本国,简直是给全世界的科学者一个大革命般的惊人的事”③爱罗先珂:《为人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309页。。在童话的最后,爱罗先珂以反讽的姿态,让一位学者说出活体解剖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现在社会上,为了土地和商业的利益,为了政治家和军人的野心,杀死了多少万年青的像样的人,毫不以为怎样。然而为人类为人间的幸福,为拼命劳作的科学者的实验,却不允许杀一个低能儿。这是现代的人道。这是我们自以为荣的二十世纪的文明。……④爱罗先珂:《为人类》,《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9、309页。
在另一篇童话《鱼的悲哀》中,爱罗先珂以鱼的视角,观察到人类哥儿将池塘周围的兔和尚、黄莺、蛙诗人、胡蜂们都捉了去,一一解剖,小鲫鱼出于巨大的绝望和哀愤,自投到哥儿的网中,当鲫鱼被解剖之后,它的心脏却早已破裂,但解剖者并不知道鲫鱼的悲哀。
这哥儿,后来成为有名的解剖学者了。但是,那池,却渐渐的狭小了起来,蛙和鱼的数目也减少了,花和草也都凋落了,到了黄昏,即使听到了远处的教会的钟声,也早没有谁出来倾听了。①爱罗先珂:《鱼的悲哀》,《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0页。
爱罗先珂的这两篇小说,都对动物活体解剖(包括针对人的活体解剖)作了激烈批判。在《爱罗先珂童话集·序》中,鲁迅谈到“依我的主见选择的是《狭的笼》,《池边》,《雕的心》,《春夜的梦》,此外便是照着作者的希望而译的了”②鲁迅:《爱罗先珂童话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上面有关活体解剖的篇章,都不是鲁迅主动选择的。在《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中,鲁迅也谈到翻译时“至于对于他的作品的内容,我自然也常有不同的意见,但因为为他而译,所译总是抹杀了我见……”③鲁迅:《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1页。这里谈到的“常有不同的意见”,恐怕就有对于活体解剖的批判问题。鲁迅在学医期间,从事过专业的解剖训练,在其归国后编写的生理学教科书《人生象敩》中,也设置了多处解剖实验方案。如在讨论胃部受胃酸腐蚀融化的现象时,鲁迅谈到这一结论可以通过解剖予以证明:“此其为说,可以实验,即取一犬,束缚胃之小动脉管,使血绝流,则其胃则自化”④鲁迅:《人生象敩》,《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3页。,在《生理实验术要略》中,鲁迅也谈到活体解剖实验,如“血之循环”的实验设计为:
……以醉蛙(须二十分时,或用针破其小脑亦可)令卧于板,剖腹展其肠间膜,蒙于孔上,四围固定以针(或树刺),令不皱缩。乃就显镜视之,可见循环之状。……①鲁迅:《生理实验术要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3、274页。
在“生物失空气则死”下,设置的实验为:“取鼠或小鸟入排气钟内,去其空气验之”②鲁迅:《生理实验术要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3、274页。,又如“脑及脊髓之作用”下,设置实验为:
用以脱醉蛙,取锯切开头骨,去其大脑。置半身于水,察其举止。当见姿势不失,其他器官,亦无障碍,而意志已亡,任置何处,决不自动,惟反其身,令腹向上,或直接加撄,乃运动耳。
次去其小脑及延髓,则姿势顿失,呼吸亦止。然以脊髓尚在,故取火焚其足,则举足以避。或用醋酸滴于肤,亦举足欲除去之。此其反射作用也。……③鲁迅:《生理实验术要略》,《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3、273、274页。
鲁迅在教材中列举的动物活体实验,在现代医学系统中无疑拥有绝对的合法性,但作为解剖学的阴暗面,活体解剖无疑也显示了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冷酷无情的一面。
西方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新型的医院医学模式便从法国开始逐渐推广到主要欧洲国家,动物实验被广泛应用到临床相关的研究中,活体解剖也越来越不可或缺。与此同时,活体解剖也遭遇了科学共同体以外的,自大众到精英阶层普遍的批判和抵制,并逐渐形成声势浩大的动物保护运动,这尤以英国最为突出,甚至英国女王也是反对活体解剖的支持者,《虐待动物法》以及其修正案也在19世纪通过,这都主要针对的是实验室动物活体解剖。④相关研究参见 Nuno Franco, “Animal Experiments in Biomedical Resear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imals 3:1 (2013): 238–273。在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两位在医学史上最为杰出的人物——贝尔纳(Claude Bernard)和巴斯德(Louis Pasteur)——先后成为反对活体解剖运动的头号敌人。现代实验医学奠基人贝尔纳是活体解剖的支持者,在他那曾对左拉的文学观产生过深刻影响的经典著作《实验医学研究导论》中,就将《论活体解剖》列为专章讨论,论证在活体人类和活体动物身上展开医学解剖的合法性和必要性。贝尔纳认为在人类身上的“活体解剖已经确定地成为生理学与医学研究的惯例,并且是不可缺少的方法”①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夏康农、管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7~118、119、120页。,贝尔纳认为:“生命的科学只有靠实验才可以建立,我们只有牺牲一部分生物,才能救活其余的生物,这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②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夏康农、管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7~118、119、120页。因为这一理由,贝尔纳认为“先在一只动物上作对人有益的实验就是最道德的行为了;虽然对动物来说,也许是痛苦的和危险的”③克洛德·贝尔纳:《实验医学研究导论》,夏康农、管光东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17~118、119、120页。。活体解剖,尤其是针对动物的活体解剖,是现代实验室医学研究和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现代医学史上卓越的生理学家和科学进步的信仰者,大多都是活体解剖的支持者。
即便是贝尔纳本人,也遭遇了来自家庭的反对,“被反对活体解剖的妻子和女儿们所唾弃”④帕特里斯·德布雷:《巴斯德传》,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2、485~493、475、486~488页。。这位在现代生理学领域声名卓著的人物,曾一度是反对活体解剖的民众攻击的目标,贝尔纳逝世之后,人们又将巴斯德视为头号敌人,因为他所从事的狂犬病研究,使用了大量动物活体解剖,并且他坚定捍卫活体解剖在生理学中的基础性地位。⑤帕特里斯·德布雷:《巴斯德传》,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2、485~493、475、486~488页。
作为反对活体解剖的最大的“敌人”,也是在医学界具有世界影响的两位科学泰斗,贝尔纳和巴斯德在解剖学中的活体解剖实践,与爱罗先珂童话《为人类》中的很多细节十分相似,两者间的关系是值得注意的。《为人类》中,K也是卓越的解剖学家,“在国内的学者们之间不必说,便是远地里的外国学者们之间也有名”,也是从事“脑和脊髓的研究”,而巴斯德的解剖学实验中,特别棘手的问题便也是“对大脑和脊髓的操作”⑥帕特里斯·德布雷:《巴斯德传》,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2、485~493、475、486~488页。;K的实验室“虽然离街道还很远,但走路的人们的耳朵里,时常听到那可怕的惨痛的动物的喊声”,巴斯德实验室的场景也极为恐怖,让闻见者感到震撼,“疯狗的狂吠在整个街区回荡”⑦帕特里斯·德布雷:《巴斯德传》,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402、485~493、475、486~488页。;且K的“家里养着许多狗”,研究中解剖过“几千匹的动物”,巴斯德则专门从事狂犬病的研究,也解剖过数量巨大的活犬;在童话中,K的妻子和儿子都对K的活体解剖感到恐惧和不安,这与贝尔纳的境遇也很相似,他的妻子和女儿“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用在反对活体解剖者组织的各种活动上”,他的婚姻生活“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噩梦”⑧哈尔·海尔曼:《医学领域的名家之争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10场争论》,马晶、李静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等等。由贝尔纳与巴斯德引起的反对活体解剖的行动,在19世纪后期的反活体解剖浪潮中曾形成很大的声势,围绕贝尔纳和巴斯德的有关活体解剖的争论,尤其产生了很强的社会影响,爱罗先珂有关活体解剖的童话不排除就是以此为背景创作的。
接受过专业解剖学训练的鲁迅,无疑是现代医学的信仰者,可以说就是贝尔纳、巴斯德传统下的人,作为文学家的鲁迅虽然并不就与作为解剖医生的周树人重叠,但解剖医生的身份无疑对前者有深刻的影响,这种科学身份与创造自然童话的爱罗先珂显然是有分歧的,要理解他们之间的分歧,还需要进一步讨论无政府主义在他们身上的不同影响。
四 无政府主义伦理学
讨论爱罗先珂童话中对活体解剖的批判,一个更重要的伦理学资源是无政府主义。爱罗先珂的思想构成中,无政府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思想底色,早年在伦敦时(1912年),爱罗先珂曾亲自拜访过克鲁泡特金①藤井省三:『エロシェンコの都市物語―1920年代東京·上海·北京』、みすず書房、1989年、第60頁。转引自熊鹰:《世界语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以鲁迅“一战”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后来他又“从日本的青年那里受了洗礼”②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376页。,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自称是无统治主义者”③江口涣:《忆爱罗先珂华希理君》,《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6、376页。,并因为这个身份多次被驱逐。爱罗先珂在中国也最受无政府主义者的欢迎,他在北大的课堂上最后剩下的也只有两个无政府主义学生。爱罗先珂童话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很密切,如《世界的火灾》这篇对鲁迅《长明灯》的创作产生过直接影响的作品中的主人公,便是一个“亚美利加的有名的无政府党”,《狭的笼》中的虎的形象,也是一个反抗的无政府主义者。特别重要的是,爱与互助的观点在爱罗先珂的自然童话中也是最核心的主题,如《桃色的云》中,自然母与众生灵讨论何谓强者时,当众生灵认为强者即那“有强有力的手脚的,有锋利的爪牙的,有可怕的毒的”,自然母则认为强者并不是这些,而是那些:
对于一切有同情,对于一切都爱,以及大家互相帮助,于这些事情最优越的,这才是第一等的强者呢。同情,爱,互助,全都优越的,这才永远生存下去。倘使不知道同情和爱和互助的事,那便无论有着怎样强有力的手脚和巨大的身体,有着怎样锋利的爪牙,有着怎样可怕的毒,也一定,毫不含胡,要灭亡下去的。①爱罗先珂:《桃色的云》,《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5页。
爱与互助精神正是爱罗先珂对那些残暴对待自然物的人类展开批判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
爱罗先珂的童话具有强烈的博物学色彩,所体现的自然伦理,与克鲁泡特金有高度的相关性。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极少讨论伦理学,无论是蒲鲁东还是巴枯宁,于伦理学方面都未能有所建树,克鲁泡特金晚年未完成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就成为早期无政府主义最重要的伦理学著作。克鲁泡特金作为一个具有博物学家身份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矿物、动物、植物以及地质学等领域,都有相当的建树,写过不少讨论石油地质、古代地磁学的专业著作,算得上19世纪博物学传统中的人物。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互助论——进化的一个要素》就是建立在博物学基础之上的,他看到无论是在蚂蚁、蜜蜂、鸟类到猛兽、猿猴等动物中,还是各个阶段的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互助在生存中都具有基础性地位,他的基于互助的进化论与达尔文、赫胥黎等人基于生存竞争的进化论,都是建立在一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更进一步地贯彻了他在《互助论》中的逻辑,他认为“自然界不是无道德的”“人类从自然界获得最初的道德教训”,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采用了一种道德比较法,把人与动物混在一起,他把社会与自然等同起来,以研究动物的关系来研究人,动物所具有的互助情感同样适应于人,两者并无差异,只是进化的阶段不同,这背后有否定宗教和传统哲学道德观的意图②张业清:《论克鲁泡特金的伦理思想》,中国人民大学198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7~28页。。克鲁泡特金认为:“人的第一道德教师便是自然界。”③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巴金译文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也因为对互助品格与爱的道德的强调,克鲁泡特金所阐发的伦理学,成为后来生态主义的重要源头,以至于后来的生态主义者将之与发表过《论公民的不服从》的博物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联系起来,在当代生态主义中,最激进也是最富战斗性的绿色安那其主义(Green Anarchism)便是无政府主义的现代生态版。生态学家戴维·佩珀(David Pepper)就认为:“克鲁泡特金的思想通常被认为代表无政府主义的人性观点,并贯穿在许多现代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中。”①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9页。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观念的爱罗先珂,成为克鲁泡特金自然伦理的文学表现者。
爱罗先珂童话中的自然主义,渗透着无政府主义的伦理精神,作为译者的鲁迅,在精神上虽然同受到无政府主义的深刻影响,但两人却存在相当大的分歧。鲁迅思想中的“个人的无治主义”②1925年,在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袒露自己的富于矛盾的思想,“我的意见原也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着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确为别人,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希望将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6页)因素,体现在他对斯蒂纳、尼采、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以及易卜生等人的接受上,更多指向无政府主义彻底的怀疑与批判精神的一面,而无政府主义的另一面——爱与互助精神——则与鲁迅距离较远,正是在这一点上,构成了鲁迅与爱罗先珂的分歧。熊鹰在分析鲁迅小说《鸭的喜剧》时,敏锐地注意到了鲁迅对爱罗先珂“泛爱主义”的质疑,他认为“《鸭的喜剧》是一个有关生物竞争和反省‘无所不爱’的故事”③熊鹰:《世界语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以鲁迅“一战”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并进而认为鲁迅在谈到爱罗先珂时说的“有不同的意见”的地方,可能正是爱罗先珂的这种泛爱主义④熊鹰:《世界语文学中的民族问题——以鲁迅“一战”后对爱罗先珂的翻译为例》,《文艺研究》2016年第9期。。爱罗先珂对活体解剖的批判正是基于这种泛爱主义,对此,包括鲁迅在内的新文学知识分子,都还未能找到足够有力的思想资源正视这种来自科学的暴力,而这是与现代时期的科学主义倾向密切相关的。正如吴国盛指出的:
在传统被彻底抛弃之后,人们却依然以一种传统的方式来对待新的权威。中国大一统的传统思想观念用于“科学”之后,就成了一元论的科学主义。由“独尊儒术”到“独尊科学”具有内在一致性。⑤吴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与科学传播》,“科学的历程”公众号,2018年10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OikyjfdO2Jeo_gbyedkRRA。
在西方,当科学与人文二分之后,就一直存在着一股强劲的人文传统,与作为新贵的科学传统相抗衡,这一点在有关活体解剖的论争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与鲁迅有过一饭之缘的英国作家萧伯纳便是西方反对活体解剖的代表人物,他曾敏锐地指出其中的科学主义的问题:
然而,活体解剖的致命弱点并不在于它所引起的痛苦,而在于它被证明是合理的。……实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罪犯像任何一个活体解剖医生那样厚颜无耻地争辩。……(活体解剖者)不仅称他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也宣称没有其他科学方法。当你对他的残忍表示出你本能的厌恶,对他的愚蠢表示出天生的轻蔑时,他就认为你在攻击科学。①引自萧伯纳戏剧The Doctor's Dilemma,参见https://gutenberg.org/files/5069/5069-h/5069-h.htm。
但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一直是人文传统的瓦解和崩溃②吴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主义与科学传播》,“科学的历程”公众号,2018年10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OikyjfdO2Jeo_gbyedkRRA。,因而,当解剖学以科学的形象被确立之后,解剖刀下的暴力很难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传统文化中有关身体禁忌,无论是儒者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观念,还是释家的戒杀,都在科学的名义下被重新评价,这既体现为具有强烈解剖学色彩的新文学对解剖学暴力的某种无意识,也体现在对于西方博物学传统内部潜流着的强调生命主义的科学方法的隔膜,正如上文萧伯纳所指出的科学主义者不相信存在一种有情的科学,这一点也清晰地体现在对法布尔《昆虫记》的评价上③如周作人在评价英国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时,便特别强调其科学性,这与现代化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参见邓小燕《“草木虫鱼之学”视野下的梭罗与怀特——一场围绕自然书写的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7期。。
五 有情的科学:《昆虫记》的缺点
法布尔的《昆虫记》是鲁迅和周作人非常喜欢的著作,鲁迅晚年还有翻译它的计划,周作人也曾一再向读者介绍,论者在谈及周氏兄弟与博物学关系时都会对此大书特书,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对《昆虫记》缺点的批评:
……现在中国屡经绍介的法国昆虫学大家法布耳(Fabre),也颇有这倾向。他的著作还有两种缺点:一是嗤笑解剖学家,二是用人类道德于昆虫界。但倘无解剖,就不能有他那样精到的观察,因为观察的基础,也还是解剖学;……但倘若对这两点先加警戒,那么,他的大著作《昆虫记》十卷,读起来也还是一部很有趣,也很有益的书。①鲁迅:《名人和名言》,《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5页。
实际上,并非法布尔不知道解剖学的作用,法布尔也绝非在观察中从来不使用解剖,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曾接触解剖学,并在很多场合利用解剖学作为自己观察的辅助,还曾通过解剖掌握了千足虫的生殖器构造②乔治-维克托·勒格罗:《法布尔传》,杨金平、马雪琨、乔雪梅、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104页。,在他的《趣味化学》一书中,也曾设置过一个将麻雀放在氮气瓶中观察其窒息而死的活体实验③法布尔:《趣味化学》,顾均正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87~88页。,法布尔甚至被视为贝尔纳传统中的伟大的科学家④乔治-维克托·勒格罗:《法布尔传》,杨金平、马雪琨、乔雪梅、邢克超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40、104页。。
同样是重视实验,甚至也不绝对地排斥解剖学,法布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倾向于形成一种有情的科学:生命既然是依赖具体的环境而存在,那么实验室解剖也就算不得最好的研究方法,即便有实验的介入也不能脱离其生境,这种介入研究对象生命史的方法成为培养研究者与对象情感关系的契机,“昆虫诗人”的头衔当然不是法布尔的某种文学情感造成的,而是来源于这种有情的科学,实际上给法布尔带来最高成就的发现,都不是从实验室解剖台上得来的。在西方,以观察方式理解生境中的生命,不仅是传统博物学的基础方法,它也是动物行为学和生态学的重要科学资源,后来生物学领域的诸多名家,如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等人都属于法布尔所属传统中的杰出代表,生态主义则尤其强调这一传统所具有的科学与生态价值。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优长,不过在现代实验室科学强势崛起的背景下,法布尔的传统越来越式微,甚至被贬低为“集邮者”。⑤爱德华·威尔逊:《大自然的猎人:生物学家威尔逊自传》,杨玉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95页。在回忆录中,威尔逊谈到分子生物学兴起之后,一批实验室生物学家越来越瞧不起传统生态学,威尔逊特别谈到DNA结构发现者之一的科学家沃森(James Watson)的傲慢,他认为“生物学必须转换成由分子及细胞所主导的科学”,还认为“从前所建立的‘传统’生物学(也就是‘我的’生物学),当中充斥着一批才智平庸的人,这批人没有能力把研究主题转换成现代科学,只能扮演集邮者一般的角色”。
依赖解剖学的巴斯德和依赖观察的法布尔,曾有过一次精彩的交锋:在《昆虫记》中,法布尔记载过一件事,巴斯德曾前往荒石园拜访法布尔,伟大的生理学家的造访让法布尔倍感意外,巴斯德是特意来向法布尔索取蚕种,因为法国蚕农多年来遭遇严重瘟疫,巴斯德想要对蚕病作出研究。令法布尔错愕的是,巴斯德“对昆虫的蜕变一窍不通,今天才第一次见到蚕茧,才知道里面有东西,这东西将会变成蛾,他竟然连我们南方农村小学生都知道的事情也不懂”①法布尔:《昆虫记》第9卷,梁守锵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173页。。无论是巴斯德对法布尔工作方法的傲慢,还是法布尔因巴斯德对昆虫生命史的无知而感到的震惊,这背后正是实验室解剖与动物行为观察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分歧。法布尔写道:“我决定采用一种从未有人采用过的方法对昆虫的本能进行研究”,这种方法就是“坚持不懈地与我的研究对象单独待在一起,直至让它们开口说话”。②法布尔:《昆虫记》第9卷,梁守锵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173页。在研究朗格多克蝎子时,法布尔也谈到“解剖刀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蝎子的生理结构,但据我所知,没有一位观察家敢于坚持对他隐秘的生活习性进行观察。在酒精中浸泡后被解剖的蝎子已为人们熟知,至于它的本性,却几乎无人知晓”③法布尔:《昆虫记》第9卷,梁守锵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5、256、173页。。法布尔不仅指出解剖学的限度,同时,还因其长期与研究对象待在一起,和动物直接的亲密的情感相伴而生,这与那种排斥情感甚至将残忍合法化的实验室活体解剖是完全不同的。
周作人在谈到《昆虫记》的方法时,认为法布尔“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普通的昆虫学里面已经说得够了),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的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与愚蒙”④周作人:《法布耳〈昆虫记〉》,《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页。。认为法布尔不采取解剖的方法,是因为普通昆虫学已说得足够了,也是以肯定解剖学的权威性为前提的,但法布尔正是因为解剖方法与真正了解昆虫离得很远才不选择的,“观察与试验的方法”主要还不是出于文学和诗的目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有情的科学。
在西方科学发展中,不仅有其自身的人文传统与科学主义倾向相抗衡,在科学系统内部,也有更富于生命意识的路径(如相对于机械论的生机论,相对于适者生存的互助论),与实验室科学传统形成对照。但在中国,科学主义的兴起却显示出强烈的排他性,不仅本土的文化资源(儒家的身体观、传统医学、宗教观念、民间观念对解剖的抵制等)受到整体性的彻底否定,西方传统内部的抗衡性力量也不易被理解,新文学的解剖学形象背后所呈现的这一思想命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
尾 声
1920年6月25日,沈雁冰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由他翻译的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短篇小说《为母的》,小说写了一位母亲去医院取她已死女儿的遗物,她的女儿或已被医院解剖,因而只领到生前的衣物,小说主要部分是以自然主义的笔法对医院活体解剖场景的描绘,满目是动物遗骸的解剖室,以及被缚在台上的被开膛的猫,母亲在目睹此景后引起对女儿深深的悲伤。小说通过母亲的心理活动对活体解剖的逻辑表示质疑:
……我们该问他们,他们如何“能”磔,割,裂这样小的东西呢?……当魔鬼似的病症降到小儿摇篮上的时候,总有几个医生寻小猫的晦气,挦筋剥皮到底,而这条遭难的命,这个没人援助的东西,连高声哀鸣几声也不能呢!①巴比塞:《为母的》,沈雁冰译,《茅盾译文全集》第1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47、135页。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为母的》在内,茅盾同时翻译了巴比塞的四篇小说,其中有三篇(《为母的》《复仇》《错》)都在反思人与动物间的道德关系:《为母的》是在解剖学场景中将仁爱垂注于受戮的动物,《复仇》写一位驯兽师妻子被戏狮所杀,驯兽师杀狮复仇后却从以命易命中感到极大的痛苦,并呼吁人们“知道生物的可贵,对于凡能感知痛痒的生物,实在不容有什么歧视”②巴比塞:《为母的》,沈雁冰译,《茅盾译文全集》第1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47、135页。,《错》则谈到人类对动物施加的残忍罪行,其中也包括实验室中的惨酷行为。茅盾在翻译这些作品时有过一段按语,他写到:“巴比塞小说的体裁算得是写实派,但思想却绝不是写实派,可说是新理想派。……巴比塞的体裁虽仍是写实,但大概都含有一种新人生观在文字夹行中。”③巴比塞:《为母的》,沈雁冰译,《茅盾译文全集》第1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37、147、135页。作为一位优秀的批评家,茅盾敏锐地意识到巴比塞小说中的某种“新人生观”,但他似乎还无法说明这人生观的具体内容,倘以后见之明观之,在以启蒙主义为目标的文学时代,茅盾是不大容易超越“人的文学”的时代规定性的。
从解剖书写中显露出的新文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是具有普遍性的时代文化特征的一个表现,这是由人的发现与科学的兴起之间的密切联系所决定的,正如吴国盛所说:“作为一个正在渴望现代化的弱势民族,中国人渴望弘扬唯‘人’的精神和唯‘科学’的精神,因为‘唯人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恰恰是‘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分。”①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新文学所承担的人的解放的主题与解剖学对人的发现的主题是互相支撑的,人的问题是此时文化领域的核心,与解剖学相关的自然伦理主题,实际是对解剖学(实验科学)阴暗面的正视,但在新文学时期,这无疑是相对超前的命题,无论是茅盾与巴比塞的隔膜,还是鲁迅和爱罗先珂的分歧,以及周氏兄弟对《昆虫记》“缺点”的说法,一定程度上都与此有关。在相对整饬的新文学创作中,这种隔膜与分歧或许还稍显含混,但在作为跨文化实践的翻译和批评中,其中的裂痕就显得较为明显,这裂痕既体现在空间上的东西之间,也存在于时间线的今昔之间。
当然,这种反思意识并非要以一幅简化的思想图景宣示某种历史的后见之明,这容易造成对相对混沌的文学作品的简化,因为也有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新文学书写中还隐藏着一个“执拗的低声”,比如《生人解剖之魔王》中未能引起作者足够注意的道义与科学的两难问题,并不是一个可以永远不去面对的问题,所以到了朱自清的《飘零》中,便有了W君与P君在解剖室中不同的人生选择;又比如,《人生象敩》所体现的科学精神与爱罗先珂的童话间虽具有很强的张力,但鲁迅怀着很大热情主动翻译的《小约翰》又显示了与爱罗先珂童话相似的生命温情,在这看似矛盾的思想中蕴含有丰富的思想资源,也说明对科学主义的反思未必是后来才有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品格。不妨仍引吴国盛的说法来说明这似乎分裂的二者间的关系:“我们对唯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检讨与启蒙精神本身拥有相同的思想来源从而享有同样的正当性,那是因为在这一切的背后是自由的精神。”②吴国盛:《科学与人文》,《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要全面理解新文学的解剖学形象及其文化意义,不能不对此有所着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