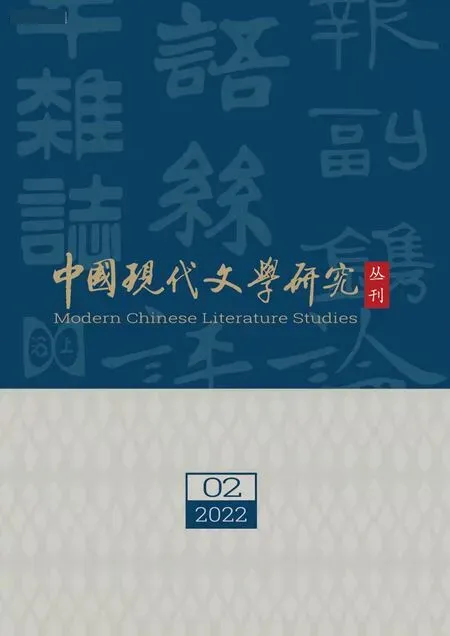《流俗地》解字说文
徐 炯 徐德明
内容提要:黎紫书《流俗地》 1语言精湛,浅俗字面下融冶精练多种语源。小说的时空观聚焦于“流”和“地”,前者是各种时段叙事,后者“在地”写实,以南洋华夷地域历史为背景,展示锡都市井生活。时空交互,人物皆活动于世俗情境中,又有不同层面的自主追求与升华。本文诉求于语文学阐释,体现为“解字、说文”的连贯,意义顺着字、词、句、章、结构与“文心”不断延展,人物、章节皆可作为释义的起点或节点,穿插、回溯、延展到多元/多义空间。
小引:语文学方法
本文随《流俗地》银霞等几个世代的市井女人,进入南洋华人及多元民族文化语境,探究小说华文夷地语用特点与在地华人女性生活之若合符契。这一目标难以由现成的批评理论与阐释途径达成,但《流俗地》有其自在的理论探讨空间:小说浅俗叙述的文字表层下潜藏着深邃文心,须细读其字句,分剖其文章肌理,溯源人物生活/生命的文化源头,庶几窥破作者的市井小说诗学主体,于南洋在地华人历史和普泛习俗的一贯与变动中珍视凡俗生命。当代中文小说有为数不多的文本,它们召唤论者解读其字、句、文章,从而明晰文义,参悟文心,解析这类文本就是接受语文学的挑战,论者可在现代文论基础上作一次回归,以“字”为出发点,利用“诗话”品鉴古代诗歌、金圣叹评点才子书的传统,把解字、说文、阐发文心主体作为批评的重要范畴。马华作家如黎紫书,于中国传统或现代白话小说不偏倚轻重,将外来资源有机融合于在地华语叙述中,浸润汲取古今中外而后产生独特自我。
如何对《流俗地》解字与说文?《流俗地》标题三字相互生发,蕴蓄深厚。本文采用诂读方式剖析“流、俗、地”三字,是谅及黎紫书小说语用不分畛域的有机融冶,马来华人生活用语的古今雅俗皆可由此得窥浅深。本文在细读本文的基础上,先行深究文题的单独字义,进而论析三字之间的文化结构,考察独立的女性书写主体与独特区域的华人市井文化及生活对象之间的契合与协商。“流”字在文本间的洄游沿溯,包括马来西亚华人一百数十年的生活史;“俗”字直击在地(锡都怡保)市井习俗,小说家聚焦清晰明确,粤文化生活是靶心,一圈圈地扩展,又一层层地深入到华语人文的核心;“地”字包蕴的空间性,与“流”的时间指涉为一体之两面,指向一种特定区域人类文化的“在地人的生存( Locals Being)”。围绕马来华人的在地生活,将其时空、种性与文化作圆融而非分析性呈现,《流俗地》在当今华文文学中堪称重要范型。下文就“流、俗、地”三字,分别阐释字义(或曰义理),扪历文心。
一 时间溯“流”
“流”字当从粤语说起,内证有马票嫂考虑“成世流流长”,银霞不能一辈子编织网兜。锡都人的华语应用,日常是粤语,国语为次,粤语“流”字的时间属性很明确。另一内证为习俗,蕙兰想要让父亲警戒大辉已在锡都,顾及和父亲叶公都是本命年,“流年”太岁当头,便打消念头。两个例证,一为人生长时段,一指或为生命节点的年头,皆时间流动。
人们感受时间的流动往往是相对的。银霞久久寄怀于一只电子手表,那是少年拉祖得自邻居关二哥的竞猜奖励而转赠的。时间与关二哥职业相关,“在他的钟表铺里,镇日对着满壁停摆的挂钟,店里似乎因此囤积了过多的时光,他只有不断找人聊天,近乎无助地将时间一点一点消耗了去”。店铺内时光有相对性,时间的流动成为人之意愿的可控对象,与小说叙述利用时间相一致,写实基础上的时间可实也可虚可长亦可短,具有象征性。时间与象征修辞之间的关联,让小说家的整体构思与细节处置得以便宜行事,可穿插藏闪、可回溯、可呼应,可免去小说人物生活似水流年的平淡叙述。
“流”之所自与所往,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属性,生活于历史流脉中的一代代俗世凡人经验着她/他们的“生活流”。女主人公银霞迎面走来,她穿透黑暗寻求光明的生活路途正长,身后的母亲梁金妹、谊母马票嫂、楼上紧邻何门方氏乃至马票嫂的妈妈邱氏,注解着锡都华人女性曲折暗昧的过往,映射着马来西亚华人在多元社会中百年以上的艰辛。“流”字义理在文本内转化为带有时间指向的诸多叙述。小说开头就在银霞的倾听与想象中设置了一个时间与行为象域:疑似往生了的大辉,在百年历史的宫庙地点,打电话召出租车到往昔的生活场所去。大辉“打电话来召德士:南天洞停车场上车,要到坝罗去”。南天洞是百年老庙,“‘坝罗’是旧街场的旧称,那是一个快要被遗弃的古词了。在锡都这地方,除了一些七老八十,记忆停留在人生某一阶段再无法更新的老人以外,已经很少有人使用它了”。这个叙述,意在建构不惑之年的银霞与锡都华人百多年历史的对话。小说以穿插藏闪笔法,叙述小说主人公银霞从十岁女童到四十岁“霞姐”的一段成长、成熟的市井女人历史。这主人公的三十年史及其与锡都百年史千丝万缕联系的构架,从小说开端就确立了。而大辉煞神再世,一再归来,就成为一种时间与性别装置,把几十年来的锡都市井女人生活史嵌入这个装置,为百年来的四世不同堂的女人谱写的南洋华人史找到一个叙事框架。
流动的物质历史写入小说而悄无声息。物化的时间标志,那“古庙(大伯公庙)建于19世纪,早晋百年身,要比坝罗华小年长四十岁以上”;锡都深深打上矿业历史标记,使得这个城市有了个性。华人最勤奋的矿物出产是在霹雳州的怡保,也就是上演小说的主场锡都。马来西亚乃至整个南洋的商业资本主义时代以出产锡标记,现代南洋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是华人开采锡矿带去的风俗习性。19世纪淘锡(洗琉琅)为前现代工业,进入汽车工业时代,转出老古的德仕(出租车)、奀仔的罗里(货车)、拿督冯的马赛地与捷豹,顾有光的莲花精灵。和女人相关的“锡米”则写在了银霞经过的路上,通往坝罗国小、大伯公庙的锡米巷、锡米路打下早期华人的生活、生产的印记,“锡米”这矿产淬炼名词带有女人属性①费信作为通事随郑和下西洋,著述《星槎胜览》记载15 世纪马来人已使用琉琅淘洗锡米,华人19世纪涌入马六甲开发锡矿业,20世纪上半叶华人女性也成为锡矿业主要劳力资源,普遍担任淘洗锡米。。物之更新、流动与生活、生命的时间之流合二而一,有意无意地阐释小说题名的“流”字。
在小说文类中历时性流动以“成长小说”显著,青年人物继续走向成熟,由于人际社会与空间的变化多端,叙事不拘泥于时间流程,于是给结构处置以多种可能性,穿插藏闪的技巧于焉逞能。银霞生命中成长、成熟两阶段,与《流俗地》市井叙事历程一致,表明女人的生命是主流。古家的银霞和邻居的两个男孩何细辉及其华文小学同学印度人巴布之子拉祖青梅竹马,到他们读大学去才分开。如歌德笔下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银霞的成长也是个学习的“流程”,以心迹为文。银霞的学习时代以被侵犯而终结,怀孕、堕胎、幽居之后,银霞进入德仕电台(出租车声讯),小说叙述选择的开端,她已经以强记锡都所有道路而闻名全国。其间二十年之久所发生的大小事情,性侵、堕胎的场面由银霞自述或叙述者交代,其他的事情都被解析、穿插着叙述,灵光乍现又遁迹无痕,或彼此映照藏而不露。四十岁的银霞进入不惑之年,她的生命旅途“一路上”走入与顾有光的婚姻。成长小说的时间流动,到了成熟期渐渐因多样的人际互动而事件更迭,时间之繁复交错需要用叙述语句来切割或分段,而下一代生命活水般流过来,直接以时间节气的流动命名,蕙兰的孩子春分、夏至、立秋接踵而至。
传统女人成熟期首在女大当嫁,银霞将来靠什么吃饭或者说嫁什么人,是母亲梁金妹、干妈马票嫂的大心事,何门方氏戒慎恐惧,不让儿子细辉与银霞的青梅竹马继续发展。这些女人七老八十而离开了人世,像河流拐弯从眼前消逝了。何门方氏委屈着身躯、呕心沥血离开人世,治丧的灵牌上才第一次有了完整姓名和籍贯。同籍贯的马票嫂母亲邱氏,她更早从广东被拐骗来马来西亚,一嫁再嫁。梁金妹住上和女儿银霞铢积寸累购置的美丽(家)园,完成了女人有自己房子的独立人生。原罪观是小说中女人的代际差异,银霞视被侵犯罪不在我,勇敢开启德仕电台的新生活。银霞辈的“更新”让女人河流转了个大弯。
这“流”字的修辞,其实历史悠久,《诗经·蒹葭》“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溯洄者岂非这四代不同堂的女人道路?那宛在水中央的,不就是银霞?
二 华“俗”情形
知识阶级于“俗”,往往避之唯恐不及,原因不外有二:由上而下的“风”俗,立于道学或主政者立场,会陷于“情伪”;细民俗众曼衍之“习”俗,琐屑芜杂,有识者未必服膺。小说写特定族裔人群的习俗固然有民俗学价值,难得见人之真性情者。“俗”字语用,历史既久,作为文化、人群乃至空间的概念,屡经转易/异。其与小说论述相关者有二。
其一,知识精英话语区分“雅/俗”从来泾渭分明。“雅”士历五四文化语境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道德高尚的标格转变为新文化启蒙姿态。无论是古代高洁诗人还是现代启蒙者,都不是一般小说家的态度。宋代的说话传统不避俗人立场,说书人/小说家有时是淑世者,有时又是骂世的人;小说经说话、拟话本而文人化,市井活泼真意渐淡,士大夫主体渐行取代“说话”认同的凡俗。新文学小说即使涉及市井也禀赋不俗,老舍写骆驼祥子买车“三起三落”,证实人生努力白费,有几分叔本华的悲剧意识,祥子的“个人主义”源于尼采,不是老舍幼年熟悉的北平评书的市井人生。
其二,作为风俗地理与王化政治层面上的“俗”。①“俗”在成篇文字中始见于《毛公鼎》,用如“欲”,假借字。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与班固《汉书·地理志》取义基本一致:习也,凡相效谓之习,相关水土风气。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康熙字典》【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小说家笔下“俗”情与舆地相关,在小说特征即为“在地性”;在王化政治层面,小说是个谬种,说书人与作小说的文人重视庸众“下所习”而不介意君王朝政“上所化”。现代小说谈俗,又加上两个外来语义项:一个是与神圣对举的世俗(secular),一个是通俗流行(popular),印证外国小说而言,前者用于《神曲》《天路历程》等,后者则如英国维多利亚小说哈葛德一路,趋于类型化的侦探或浪漫故事。从舆地习俗中产生人情,既带地方性又有普遍人情,《金瓶梅》《红楼梦》《海上花列传》皆能写透习俗人情。鲁迅说《海上花列传》“近真”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第349页。,“近”字的评判已逊让《金瓶梅》《红楼梦》之真切几分;“真”字是小说要害,鲁迅自评其小说内容之真为“表现之深切”②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见《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2005年版,第246页。此语源于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其师章太炎把“真/俗”关系说得透彻:“转俗成真,回真向俗。”③章太炎:《菿汉微言》《章太炎全集 菿汉微言、菿汉昌言、菿汉雅言札记、刘子政左氏说、太史公古文尚书说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0~71页。章太炎提炼的这真、俗八字,意谓在凡俗中精神不坠,反而转化生成求真的态度,达到真理境地回观与把握世俗人生。这个境界适合分剖《流俗地》,小说成功塑造的女性人物皆程度不等地“转俗成真”,而叙述者直面锡都华人习俗的主体性特征正是“回真向俗”。
“转俗成真”接近《流俗地》小说诗学中的人情与人性。人物在自然流转的俗世人生中淬炼得“真”,是小说引人入胜的保证④黎紫书在《流俗地·后记》中讲这小说写什么和怎样写:“一群平凡不过的人……最平凡的(可能也是庸俗的)人生故事。……说得引人入胜……”。马票嫂走过世俗人生“所有的路”(第十三章题)而修炼得一份真心走近她/他人,她无时不在关心着银霞。由俗转“真”比形而上的求真更切实,不让“真”束之高阁而失了血肉寄托与精、气、神。小说中女人在凡俗现实中活得不容易,她们既俗且痛苦却不失真,小说对马票嫂、梁金妹、何门方氏、蕙兰的叙述朴实无华而叩击人心。在真实生活基础上,会产生德仕司机们对银霞的超越性猜测:“前世一定是个传教士,天天对人讲耶稣。”银霞的前世不必与神职有关,今生确是在痛苦中炼就人格,在真实中求真理。银霞若非经过“恶年”(第三十六章题)、没有身心之“囚”(第三十七章题),就不会体谅在华夷凡俗生活中女人的真切痛楚,也不会有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的超越。境地退一步有蕙兰,她和姑姑莲珠、女儿春分去谈判,无功而返的车中蕙兰心头郁结,欲以笑化解,说着笑着掉下眼泪,哭诉着自问何时是个尽头,把莲珠一张张递过来的一盒面纸都擦完了。蕙兰终于挺直腰杆,正视这一地鸡毛的日子,女儿生了,她堂堂正正地给亲戚报喜,就这样不回避真实,在凡庸琐碎中练就直面真相的能力。从俗世中练就对生活的承担、直面人生的坚定态度,她们就脱俗成真了。
“转俗成真”的小说诗学落实于人物,“回真向俗”可归结为叙述主体如何结构处置凡俗生活内容,小说家将市井人生赋予入俗的形式感,对形式感的把握是审美主体之真,形式给予市井中人表现的舞台,把林林总总的事件归置到形式中,小说才有了美的统一。银霞的形象戛戛独造为全新,但小说结合着世俗生命的形式不必是全新的。求签拜神不新鲜,但它富于特定语境中的生命启示;衣食住行可以千篇一律,沉浮或执着于一律的生活,却可有不一样兴头与趣味;生活可以是一个俗套,然而套子里的人诸般十调,小说家用不同句式去叙述,就有了不一样的调性;打字原本是一个机械过程,如果传达的是银霞深心里的新鲜感受,那就如赋格音乐的抒情。
俗世解字如解签。银霞随去大伯公庙,莲珠代她求得一签:“三姓俱相伴,祥光得共生,更宜分造化,百福自然亨。”说是签文,其实是构思逻辑,讲的是银霞、细辉和拉祖她们三人的青梅竹马组合,三人相伴,终须“分”造化,各自走出人生道路。签文也可卜解银霞一人,盲目是她的先天造化,百福亨通却有待心的修炼;也可以解为银霞、细辉终不可走到一起。求签本属虚妄,又非银霞本心欲求,然而可以造就一种灵氛、暗示与预感。文人小说写世家高门巨族,可以设置太虚幻境、拟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市井中的预示不是求签就是问卜打卦,《流俗地》市井人当然求签,小说家有意无意安排,解签也在虚实之间。
“俗”字与人的生活经历是什么关系?多选答案之一是许多人的生活轨迹都不免是个俗套。细辉的生活可阐释小说之“俗”,他是个凡庸细暗缺乏主体独立的俗套男人。看他从小,幸亏拉祖觅得偏方上的翠鸟,治好他先天气喘,下棋依靠银霞而仅有一次对拉祖的胜绩,青春期自渎时想的是银霞,却没有勇气表达爱。小说叙述他长成之后的历程:“几乎每年一件大事——便利店开张,新居入伙,与婵娟结婚,生下女儿小珊,细辉马不停蹄,连着当了老板、屋主、丈夫和父亲。”这个句式,看似流水账,却是庸人一生的重要节点,细辉没有时间与能力反思:走过这些节点之后的生命意义何在?然而,这又的的确确是要消耗了许多精力才能完成的人生步骤,走完一步就获得一种新的身份,把事情和身份分为两截叙述,一边感叹四年奋进的不容易,一边是庸常成就感的展示。这个句式,上半是并列的存现句,下半把每一种身份作为成就目标,“当”字联动四个宾语构成并列从句,作为比喻句的本体说明“马不停蹄”的性状。这句式无论事情、身份都在表述细辉,两个不同主语句子绾系一处,不需要英文的such as,也没有从句标识that,短句简便灵动却不失逻辑谨严。这样的句式,需要四面八方去调度着写上三四遍,却看似得来全不费工夫。
《流俗地》里六根未净的俗人俗事时时是感官呈现的仪式,眼耳鼻舌身意,有对空间的感知,也感受口腹之欲。银霞的感官中缺少“眼睛”,她用耳朵努力倾听,知悉“楼上楼下左邻右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日子的声息”,她由镇流器声音倾听光源的存在。俗人最大的信仰“以食为天”,银霞习惯妈妈梁金妹,“房间被她每天用桂皮八角黄豆酱黑豆豉辣椒糊咖哩末蚝油生抽绍兴酒花生油和其他许多香料熏出了一股复杂难解的油烟味”,楼上来自广东的何门方氏的家传——豉汁凤爪、咸鱼蒸肉饼和香芋扣肉,异国风味则有细辉家苏门答腊女佣的家乡菜肴。
“近打组屋的各族人家”有自己的文字读物,也有跨文化之俗。理发店巴布通常看印度文的《淡米尔日报》,何门方氏订华文报,专门留心莲姑的新闻。巴布老婆迪普蒂坐在店后,……有时候低头在翻《大伯公千字图》。这是实用类书样的博彩押注文字图册,银霞小时候背下来过,其999种物事映现马来社会多元文化与生活习惯,对应赌博的下注号码,无须识文断字,能读图即可写票,更兼有马票嫂专门指导。册中的文字与图画符号,相关华裔有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等,与马来人伊斯兰教信仰相关的往麦加朝圣及回教堂,而与巴布老婆相关的日常印度饮食则有研咖厘、卖娘惹糕等。细辉的超市仍在卖这图册,其汉字缘《幼学千字文》,图像与物事关系源远流长①此类书所谓雏形是元代木刻插图的《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它是一种“日用百科全书”,把近七百年前的种种风俗习惯、礼俗游戏都记录下来。此书由福建建安书肆刻印。见郑振铎著:《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24页。,清朝道光年间广东人用于博彩目的由锡矿工人带到马六甲②19世纪广东盛行“白鸽票”,投注符号选马来华人从小熟悉的《千字文》从“天地玄黄”到“鸟官人皇”80字。华人矿工及后的马来人发展出“百字票”“千字票”的赌法。马票嫂到楼上楼来写“万字票”,给银霞带过一本日历状“厚如松糕”的《万字解梦图》。。此书冠以大伯公联结华人信仰,市井人家将此书安放在家神菩萨位下。
小说中的大伯公,非止现于纸上印刷,还是华人一方聚落的神祀,大伯公庙也正是见证银霞听戏与黯然神伤的地方。建立一百多年的大伯公庙几乎是马来华人文化一种制式,华文国小往往相与土地公为邻,“银霞以为坝罗国民型华文小学与坝罗古庙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二位一体”。马票嫂介绍银霞上盲人院,“就在她的母校密山华小附近,离福德祠不远。”大伯公庙、福德祠只是一个身份的两个符号,《流俗地》里的这个符号,堪比《阿Q正传》里的土谷祠,居于社稷之神庙的阿Q之与国运的关联在辛亥革命;清代中期以后下南洋的华人,远离了中国皇权政治,却随身携带了社稷(福德、土地、客家语伯公)正神,顺便让它也兼差财神,管辖范围也没遗漏了博彩,《大伯公千字图》一身众任而名正言顺,黎紫书让大伯公始终踞于市井,贴近民生,也不让它失了文化之根。大伯公可谓写实而兼具文化象征,往上说寓有风化之意,朝下看呈现下层民众习俗,它活在黎紫书《流俗地》里,也无处不在地立于马来西亚华人住所。
三 在“地”生存
书中“地”字何解?下文释义不以一般辞书上抽象义敷衍塞责,而是立足于小说语境多方辩证,定义它在特定时空和凡俗人群中的对话功能。
“地”即空间,小说在地为锡都,南下吉隆坡住着蕙兰一家和嫁过去的银霞妹妹银铃,拉祖亦丧生于此,大辉在这里生活过,曾经去过日本和东海岸,现在成为江湖浪人。银霞最了解锡都本“地”,她的行为是有效的在地定义方式。地以路显示它与人的行旅的关系,也测绘出来路上行人的心地与理路。银霞盲目,不能用她的脚步去测量,然而她把这块土地装在心中,放在脑子里,任谁都不如这个盲目的霞姐了解锡都全城的路,了解这些路由马来文排斥华文的过去和现在。小说叙述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生存发展,尤其重视女人,《流俗地》是历史的也是女性的表述。小说家祖籍广东,出生地怡保(锡都)是马来西亚霹雳州重要城市。华人是当年开采锡矿的重要力量,而今锡都民风仍浸染中国南部习俗,粤语深入此地民间,不时地在小说叙述和人物语言中露头。如何将生身之地作一个富有生命和情感经验的呈现?黎紫书找到了银霞。银霞的锡都是市井的,是出租车遵行的网络,也是抽象的地图。银霞的存在凝缩华人几代人在南洋的生存。
银霞在“地”的行动能力,设定了小说的叙事限度。《流俗地》写南洋马六甲而几乎没有海的叙述,完全是“地”,唯一提及海的叙述关涉一个不同凡俗的人物:“拉祖的遗体已被火化,骨灰也已经撒到了浊黄的客朗河,随河水漂流到马六甲海峡了。”小说以路来联络各色人等,最重要的人物的章回标题也是“路”:马票嫂“所有的路”和银霞“一路上”,这对谊母女代际传承之路把生命空间化了。银霞的听力中活跃着日常的生活,幼时的楼道空间供她和细辉谈心,行动的限度加深她体验坐地织网的生命局促;在抽象的棋盘空间里,银霞下盲棋实现智性的超越。背诵《大伯公千字图》证明银霞的“象形”想象与抽象思维综合的能力,她在心灵空间里编织着物象“指事”和命运“会意”,较之编织各种声音的想象更上层楼。空间想象的能力结合德仕电台的职业需求,形塑银霞的在地价值观——了若指掌的全城路径,让所有要到达自己目的地的人有径可循。
银霞的人生经验定义着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市井细民也各自以其生命方式来定义它。楼上楼传播着“鬼话”,跳楼殒命的女人定义它为“鬼”地,女鬼们在此寻找“丢了的眼珠”,引申义是此“地”正是女人丢失主体性的场所,小说银霞主体性建构的意义是针对性的。《红白事》一章,关二哥在三个小孩面前考验拉祖:“道出铁三角和金三角的来处,我送你一个手表。”拉祖说出“铁三角”是桃园三结义,银霞的“金三角”答案“是泰国、缅甸和老挝……种鸦片的地方”。关二哥看似不公地对银霞答案不置可否,奖品给了拉祖。
这两个“三角”,一为显而易见是人际关系,一为“在地”关联,叙述将答案藏起(穿插藏闪笔法,一如闪过蕙兰母亲弃家出走原因)。“金三角”谜底是三个小孩没去过的吉隆坡主要商业区,有一条大街用伊斯兰苏丹国之前的朱罗王国的命名,那是泰米尔拉者(拉祖名字的发音与印度裔王族的统治者拉者【Rajah】非常相近)的起源,后来那是霹雳苏丹国(Perak Sultante)。关二哥是一个功能符号,他的钟表店象征时间,也指向在地空间,符号所指既为显示拉祖非凡,也暗示和排华一样的心理,马来统治者不愿人们记起前伊斯兰的印度文化。
拉祖读华文小学而成绩超群,族裔上联古印度,骨灰流向马六甲海峡,他和银霞、细辉的铁三角是一个小小的印度支那(Indo-China),他还把“地”的释义引向南洋历史范围深广的华夷互动。看南洋文化史,惯以“地”命名来确认空间、种族关系,早在中国元朝时期(南洋满者伯夷国王朝1293—1500年曾经统治马来半岛南部、婆罗洲、苏门答腊、巴厘岛)就有“爪哇之地(Bhumi Jawa)”和“马来之地(Bhumi Melayu)”的名称①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明永乐年间穆斯林苏丹国宫廷正改宗伊斯兰教,郑和下西洋屡次在马六甲海峡瞭望“甲地”。19世纪的马来西岸,怡保所在的霹雳州是英国势力范围,再往上的吉打则是暹罗的“南地”(Nam Tien),却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②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
黎紫书岂能不关注历史而富见地。当欧洲势力进入南洋地区,荷兰人并未显示出巨大的传教热情,继而进入的是英国人,19世纪的英国传教士从海上登陆,将陆地居民作为传教对象,这块土地上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信众,传教士致力于填补华人文化中的宗教空白。英国传教士在南洋办了三种最早的华语传教刊物,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在《特选撮要每月纪传》(1823—1826创办于雅加达)创刊号上撰文作地理介绍《咬畱吧总论第一回》,文字之前有《中国往吧地总图》。这份地图南北标有“中国地”与“中国海”,马六甲海峡地名在海岸阴影线上标“槟榔屿”,陆地则标记“甲地”,此外现在为东帝汶及其北分别有“……地”字样不清晰。麦都思拟华人口吻逐条述其眼中的爪哑,呼名条目记述:“唐山各处人常呼其地曰‘咬畱吧’、或曰‘吧地’、或曰‘吧城’,唯其本地人名之曰爪哑”……全屿名曰爪哇地;方向条目指示:“中国人要开船到吧地,必在年终或正月里起身。”大小分条目细述:“爪哑全地大概分为两分:东一分,名曰,爪哑地;而西一分,名曰,孙大地。”
荷兰殖民者在19世纪中期以后,“为非欧洲的外国群体设置了‘甲必丹’一职,正式确立了华人——至少是说中国方言的人——有独立的社会身份。”③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1891年至1931年间,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增加了三倍,同一时间马来人口只多了50%。因为锡矿开采之故,1891年的霹雳人口已经有44%是华人。”④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1820—1930年代,“在马来亚容易开采的锡矿已经枯竭,……资本密集的锡矿泥开采也开始出现。”⑤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1921年,马来亚国家有43%的居民是在国外出生,新加坡的数字则是70%。中国人和印度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以劳工身份来到马来各国,最后留在当地,……落户生根的仍然是少数。”⑥Philip Bowring(菲利浦·鲍灵):《风之帝国》(Empire of the Windows The Global Role of Asia’s Great Archipelago),冯奕达译,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21年版,第177、333、346、345、356、359页。算起来,马票嫂的母亲邱氏就是这时候来到马来,她的同辈与前行女人也会参与淘洗锡米。隔了两代人,拉祖、细辉“在一个下午放学后,将银霞从近打组屋偷渡出来,沿着锡米巷转到锡米路,一路偷偷摸摸地行到坝罗华小。”不长的路,她们走了好久,那一刻路不是空间而是历史时间。
“地”字寓人情。南国男人,尤其是广东人,经由香港来到马六甲开采锡矿,他们来挣一笔钱,年轻的为娶妻,稍长的谋造屋。家乡撇在身后的妻子恋人的异地/夷地想象,或如南管古曲《百家春》所唱:“当春芳草地/万物皆献媚/为着什么事/抛了妻/游远地/长别离……/多望春花开来深闺地
深闺终日泪滴成伤哀……”邱氏的丈夫回转芳草地,去和妻子团聚,抛下马来再娶的邱氏,成就另一段夷地的哀怨。邱氏成了锡都市井女人的凡俗之根,一段四世不同堂的在地寻根便是《流俗地》,黎紫书一朝回望唐山便成了寻根小说家。金枝芒表述“马华文艺独特性”,指出没有在地关怀的文学不能被称为“马华文学”,充其量就是“侨民文学”①王德威:《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60年〈饥饿〉与马华文学中的左翼叙事》,台湾麦田出版社2021年版,第125页。,黎紫书《流俗地》空前体现了华语文学的马华在地性。
结 语
逐字解来,便呈现《流俗地》主题:在20—21世纪的南洋时空中探究市井凡俗生命尤其是女人的价值。索解主题以后,“解字、说文”的论述方法值得进一步质询。批评黎紫书小说,因其语言文字左右逢源于说书、文人小说、中西现代文学,多源“解字”诚不容易,但得其心源便可一窥究竟,明晓其“文心”之独造,即可入其堂庑。解字与文心之互动互用,如排列组合而变化万端,可让批评和创作一样拥有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