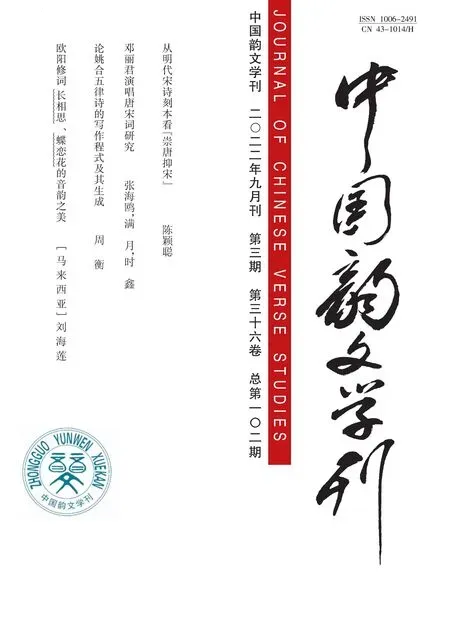敦煌《月赋》的诗体特征及其生成原因
梁凤连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敦煌写本《月赋》未见载于唐人诗文集,只见于敦煌法藏文献伯2555V号残卷内,首题“月赋”,未属作者姓名,存9行,每行18—20字不等,字体为行书。按照写本原貌并辅以文意及用韵来看,该赋首尾完整。全赋如下:
阴之精,月之体,初出海中净如洗。半轮已挂剑山头,一片仍关汉江底。山头山底何朣胧,坐见风尘飒已空。光浮万里关河外,影入千家户牖中。天既青,月弥萤,夜未兰(阑)兮北斗正。睹此光晖胜魏珠,照兹肝胆胜秦镜。庭庭兮秋夜,皎皎兮新秋。鹊飞爱绕千年树,蝉影偏宜百尺楼。自怜遘疾独歌(歇)卧,耳闻寒蝉心欲破。岁时总向愁处抛,风月偷从病中过。城下捣衣声彻天,百忧从此更相煎。所恨不如台上月,徘徊常在列卿前。
该赋前抄七言诗,诗题残缺;后抄《从军行》,亦不署作者姓名;伯2555V全卷所抄,几乎皆为诗歌。唐人将该赋与诗歌抄录在一起,说明该赋与诗有着某种关联,具有诗的某种特征。本文拟从句式、抒情等方面探讨《月赋》的诗体特征,并分析这些特征形成的原因。
一 七言为主的杂言句式
句式,是诗文中最为直观的形式,也是区分不同文体的重要依据。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称:“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句式于文章,犹如人之外貌形体,句式的变化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体的变化发展。通观历代辞赋,四、六言为最常用的句式,三言的使用频率也较高。这是中国古代赋体的三种基本句式。汉代散体大赋的主体部分,以四言一顺的句式为主,偶有三言句式,十分紧凑。而六朝骈赋、唐宋律赋,则以整齐而对仗的四六句式为主,或四四相对,或六六相对,或四六与四六、六四与六四相对。正如赵成林先生所云:“其(辞赋)字数以四言、 六言、 三言为基干, 形式以对偶为主而骈散结合,既有散文的灵动之气, 更有诗歌的整齐之美。”
敦煌《月赋》的句式与常见赋体句式有较大差异。该赋共有28句,其中22句为七言,占总句数的80%左右,在形式上舍弃了辞赋的基本句式,以七言句式为主,杂以三言、五言。《月赋》的七言大都符合七言诗句的基本韵律节奏,即2—2—2—1或2—2—3(或2—2—1—2)的诵读节奏,如“半轮—已挂—剑山—头”“山头—山底—何朣胧”。易闻晓师说:“诗之所以为诗,乃在句式如三言、四言、五言、七言的限定,这种限定是严格的,在此严格的句式限定中,才有诗的体制如三言体、四言体、五言体、七言体的生成和确立。而且诗的句式形成于韵律节奏的组合,五、七言由于具有单音的存在,才使节奏顺畅明快,合于声气吐纳,利于唇语,五言2—2—1或2—3、七言2—2—2—1或2—2—3的诵读节奏,才是五、七言句式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葛晓音先生论七言诗的形成,也是本于句子的节奏分析,她指出:“考察一种诗体的产生,首先应着眼于其基本节奏的形成。”“七言的基本节奏是前四后三,这一点已经毋庸论证。”同时,葛先生亦有言:“四言以二二节奏为主,统率了许多不能变成四字句的散句。”这也就是说,七言“四三节奏”的四言,其实可以看作是“二二节奏”,4—3节奏,即2—2—3节奏。基于此,从句式形式与节奏上看,敦煌《月赋》已基本符合了七言诗的诵读节奏,具备了七言诗的句式特征。
敦煌《月赋》中三言与七言组合的“三三七”句式亦显示出其诗体特征。《月赋》只有四句三言,每两句三言与一句七言组合“三三七”句式结构,如“阴之精,月之体,初出海中净如洗”。三言与七言的组合句式,先秦时已有,汉魏时主要出现在民间歌谣、谚语、铭文之中,文人诗中极少,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被文人采用于乐府诗中,逐渐成为乐府诗的一种固定体式,如曹操、曹丕、陆机、谢惠连、鲍照、江总等人,皆有不少含“三七言”句式的乐府诗,直至唐人李白的歌行体诗、白居易的新乐府诗等,仍喜使用这种句式。敦煌《月赋》的“三三七”句式与乐府诗的“三七言”体式相一致,但与乐府稍有不同的是,敦煌《月赋》的三言句和五言句在篇章结构上起到了分层作用。开篇“阴之精,月之体,初出海中净如洗”几句,凝练地点明赋的主题为“月”,并写了月初出海面的情况;在赋的三分之一处用“天既青,月弥莹,夜未兰(阑)兮北斗正”几句,进一层写月上中天的情景。如果说三言句部分是对月色景象的描写的话,那么五言句以下则是该赋的情感所在。敦煌《月赋》两句五言,皆为骚体的“兮”字句。“兮”字在中间,作为语气词拉长声气,增强抒情性,使得赋中的情感基调更为鲜明,其沉闷和哀叹之情也更为浓烈。且两句五言句断分两大部分内容,前半部分要在写景,后半部分主在抒情。与此同时,赋中的五言句还达到押韵平衡的效果。五言句之前有三组韵:“体”“洗”“底”为叶上声荠韵,“胧”“空”“中”为叶平声东韵,“正”“镜”为叶去声敬韵;之后亦有三组韵:“秋”“楼”为叶平声尤韵,“卧”“破”“过”为叶平声个韵,“天”“煎”“前”为叶平声先韵。这种利用三、五言句式层分内容并在用韵上达到平衡效果的赋篇,在历代赋作中是极其罕见的。
二 抒情言志的表达方式
《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诗大序》又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既强调了《尚书·舜典》“诗言志”的特点,又强调了诗“吟咏性情”的功能,初步形成了情志统一的观点。至于赋,司马相如言:“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曹丕亦云:“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这些都清楚地指出了赋铺陈物态、以类相聚的描写特征,与“重意而轻词,重情而轻物”的诗体迥异。对于陆机《文赋》所言“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冷卫国认为:“(这两句)显然在于强调诗赋的不同。陆机的赋作以写志者少,以体物者多,可以看出实际上它是以后者为正体而以前者为变调的。”显而可见,“缘情”乃为诗之特点,“体物”才是赋之所长。
“体物”既为赋之所长,敦煌《月赋》又以“赋”为题名,其当宜为一篇用辞赋之体来呈现的咏物赋,如谢庄之《月赋》,对“月”的铺陈叙写为全篇的主要部分。然而,敦煌《月赋》的核心却是抒情言志,月的描写只为抒情铺垫和服务。敦煌《月赋》先写月出山海间的“朣胧”景象,然后写月上中天时“光浮万里”“影入千家”的景象;后又化用曹操的诗句,直扣主题。“蝉影偏宜百尺楼”一句,明面上写百尺楼上之蝉影,实则正如伏俊连所言:“此句……以蝉的哀怨启下文‘自怜遘疾独歌卧’之意”,联系刘删《咏蝉诗》与卢思道《听鸣蝉》,不难看出“蝉声可入上林、随侍臣,直抵太液龙楼,故启下文希求朝廷重用之意”。至此,《月赋》所抒发“怀才不遇”的入世思想已十分明显,然作者的情感并未到此而止,而是接着写清冷月色中不断传来的捣衣声,暗衬作者内心的孤寂。失志的同时还被病痛折磨,更是加深了作者内心的痛苦与煎熬。赋中由月出到月上中天,再由山海关外到千家万户的开阔之景,忽而转入到“百尺楼”和“蝉影”的细微之象,实则是作者内心的变化历程。“所恨不如台上月,徘徊常在列卿前”与“光浮万里关河外,影入千家户牖中”紧密相呼应。“万里关河”和“千家户牖”,实则暗含着作者封侯拜相的愿望,然而现实却是壮志难酬,同时还要深受病痛的折磨。这清冷的月亮尚且能在百列公卿面前徘徊,而作者却只能在月下独自哀叹。赋中情感缠绵婉转而深刻隽永,抒情性极为浓烈。
敦煌《月赋》形同于诗,在隶事和语言上也显出向当时诗歌趋近的态势。隶事上,敦煌《月赋》浅显凝练,并没有像骈赋、律赋那样用典堆积、生硬难索,其所用典皆为寻常熟识之典,且造语自然凝练,如“睹此光晖胜魏珠,照兹肝胆胜秦镜”。“魏珠”和“秦镜”皆为唐人诗歌常见典故。“魏珠”是战国魏惠王的宝珠,珠光能远照。《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魏惠王对齐威王语:“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秦镜”乃传说中秦宫内的一面宝镜,能照人心肝。《西京杂记》卷三云:“高祖初入咸阳宫……有方镜广四尺,高五尺九寸,表里有明,人直来照之,影则倒见,以手扪心而来,则见肠胃五脏,历然无碍。”光辉与魏珠相符,肝胆与秦镜相应,皆表明了月的明亮与通透,暗喻着作者对朝廷的赤胆忠心。寥寥数语,便将典故和月之特点及其暗含的深意表达清楚,可见其用典艺术之娴熟。
语言上,《月赋》不似汉赋好生僻繁难的字词以显示才学,而是用平易浅近的语言来表达深远宛曲的情感。这既是作者才情的展现,亦是当时诗歌创作的一致追求。南北朝后期至盛唐间文人的诗歌创作,普遍受到沈约“三易”说的影响。《颜氏家训·文章篇》云:“沈隐侯(沈约)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沈约“三易”说的影响及于所有文体,而在诗歌中的体现尤为明显。《月赋》与诗歌关系密切,必然也有所体现。如“城下捣衣声彻天,百忧从此更相煎”,语言平白浅显,如同口语,但其中的情感却抑郁沉婉。
敦煌《月赋》既具如此明显的诗体特征,与诗无异,那么它是否还属于赋呢?首先,从敦煌写本《月赋》的原貌上看,作者明确将作品题名为“赋”,为尊重作者意图与作品原貌,应将其归为赋作。其次,这种以“赋”称名却明显有诗体特征的赋作,在文学创作史上并不是孤例,尤其是魏晋以来,诗体与赋体的互化日益加深,赋体虽借鉴了不少诗体的创作技巧和艺术手法,若于细致处寻绎,仍可发现其与传统赋体的关联。最后,句式形式和抒情功能上的诗体特征,并不能完全消解赋的特质,咏物赋虽以铺陈为特征,但亦不排除有抒情言志之作,如贾谊《服鸟鸟赋》、祢衡《鹦鹉赋》等,而且赋并没有什么必须严守的形式规范,也未曾限定不能使用五、七言的诗体句式。综上所言,敦煌《月赋》虽有着诸多的诗体特征,但它仍然属于赋。
三 赋体诗化的时代风尚
如上所述,敦煌《月赋》虽有着“赋”的题名,却有着明显的诗体特征,形成了一种“名虽曰赋,体实为诗”的文体形态,是一篇不折不扣的诗体赋。究其原因,这是汉魏以来“赋体诗化”结果。
“赋体诗化”是一个历时的现象。据徐公持先生《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两汉魏晋诗赋关系之寻踪》一文,诗和赋本是两个文体系统,东汉时诗和赋逐渐靠拢,汉末魏初开始出现诗的赋化与赋的诗化,赋的诗化主要在于赋对诗歌精练性、抒情性和韵律性的借鉴与吸收。程章灿先生亦云:“诗的赋化几乎与生俱来,赋的诗化则自建安以后渐著。建安诗赋同题现象即是诗赋二体靠拢的表现。”诗、赋二体虽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但汉代经学盛行,辞赋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以《诗经》为主的“古诗”系统的影响,东汉时已有四言句赋作,即学界所谓的“诗体赋”。马积高先生在其《赋史》中最早提出“诗体赋”的概念,认为诗体赋最早从《诗经》演变而来,《左传·隐公元年》“大隧”、屈原《天问》、荀子《佹诗》《遗春申君赋》、扬雄《酒赋》《逐贫赋》等,皆属诗体赋。现代学者也有不认同这一观点的,但不可否认,文学经历汉朝一代的经学昌盛后,作为与经学同时发展的辞赋,尤其在东汉时期,赋家的身份往往兼有经学家的身份,赋作与经学同出一人之手的现象十分常见,赋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经学“古诗”系统的影响,使得赋体逐渐与诗体靠拢,产生了“诗化”的现象。
诗体赋不仅仅指由《诗经》演变而来的四言赋,还包括随着五、七言诗的兴起和成熟而产生的五、七言赋。程章灿先生在《魏晋南北朝赋史》中指出:“南朝赋在四,六言句式之外,又开始大量试验并终于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五、七言句式,使赋的语言形成和辞采情韵向五、七言诗体靠拢,表现出一种诗化的趋势。”郭建勋、曾伟伟也说:“所谓‘赋的诗化’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五、七言诗体赋演进和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肇端于东汉,经魏晋南朝,至初唐基本终结,跨度长达数百年。”诚然,五、七言诗体赋肇端于汉末五、七言句的产生和成熟,至梁、陈和初唐时较为兴盛,但此类赋作,并非纯粹的五言或七言,大多还杂有三言、四言或六言,不过愈成熟杂言愈少,至初唐王勃、骆宾王等人的赋作,基本与诗歌无别。与四言诗体赋的典雅质朴相比,五、七言诗体赋恣肆流丽,更适合抒发激深之情,与歌行体诗极为相近。
赋体诗化,最明显的莫过于文本形式之句式的“诗化”。其最先开始于四言体,汉代时已有扬雄《酒赋》、刘歆《灯赋》、蔡邕《青衣赋》等与四言诗无异的赋篇,随着五、七言诗体的产生和成熟,五、七言赋随之产生,齐梁时渐著,以庾信为代表,其为较多的引五、七言句入赋。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庾信《春赋》, 间多诗语, 赋体始大变矣 。”实则,除《春赋》外,庾信《灯赋》《对烛赋》《镜赋》《荡子赋》等也有杂用五、七言句,同时期的徐陵《鸳鸯赋》、江总《南越木槿赋》等,亦以五、七言为主,隋朝则有萧慤《春赋》、刘思真《丑妇赋》等,唐时赋的诗化更进一步深化,王勃《春思赋》、骆宾王《荡子从军赋》等,皆似七言歌行。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言:“《荡子从军》,献吉(李梦阳)改为歌行,遂成雅什。子安(王勃)诸赋,皆歌行也,为歌行则佳,为赋则丑。”清王芑孙《读赋卮言·审体》亦云:
七言五言,最坏赋体, 或谐或奥,皆难斗接;用散用对,悉碍经营。人徒见六朝、初唐以此入妙,而不知汉魏典型,由斯阔矣。然亦自汉开之,如班固《竹扇》诸篇是也。但是短章,初无长调,作俑长调,则晋宋而来,醴陵(江淹)倡其端;南北之际,子山(庾信)启其弊。
王世贞与王芑孙所言,虽然是对五、七言诗体赋的否定,但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六朝隋唐时期赋体高度诗化的现象。唐人赋高度诗化的结果就是造成了某些赋与诗歌界限十分模糊。敦煌《月赋》自不必再多言,更甚者如刘希夷《死马赋》和高适《双六头赋送李参军》,皆通篇七言,与诗歌无异,王重民将它们一并收入《补全唐诗》中。此外,敦煌赋如刘长卿《酒赋》、卢竧《龙门赋》、无名氏《秦将赋》等,亦几为七言而杂以三言,近乎唐人歌行。敦煌写本《酒赋》共有七个写卷,各写卷题名不一,或题为《酒赋》,或题为《高兴歌》,或题为《高兴歌酒赋》,这说明在当时,其既可称之为“歌”,亦可称之为“赋”,今人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认为:“七本相较,以丁本最善,讹夺最少,故借其所题《高兴歌》三字为此套歌辞之拟调名。盖其辞之情调气氛正‘高兴’一类。本辞并非赋体,‘酒赋’二字,义为‘赋酒’,不说明其为赋体……从知唐人所谓‘赋’,不拘一义,运用灵活。”此说虽未必尽然,但亦可体现出《酒赋》与唐人歌行相近的特点。
四 乐府诗对《月赋》影响
敦煌《月赋》之诗体特征的形成,从文体发展上看,是“赋体诗化”的结果;若从文学创作上看,则明显受到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影响。
首先,敦煌《月赋》的“三三七”句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受乐府创作影响。三、七言组合句式在先秦时已有,《乐府诗集》卷六十收录的秦百里奚妻《琴歌三首》的第一首和第三首的末尾皆是“三三七”句式结构,又《异苑》所录《秦世谣》篇尾亦为“三三七”句式。更甚者,荀子《成相杂辞》全篇以“三三七”句式为主,杂以四言和七言组合的“四七”句式,且讲究押韵;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为吏之道》的句式结构与《成相杂辞》相同,这说明在先秦时“三三七”句式可能已经成熟且广泛使用。两汉时期,这种组合句式常见于谚语、谣歌和乐府的舞曲歌辞,至魏晋时被文人引入乐府诗中并逐渐成为乐府诗的一种固定体式,更甚者如曹操《陌上桑》,全篇由六组“三三七”句式组成,且每组“三七言”句的语意完整,又由每组语意的关联与递进组成一个完整的主题。这样的乐府诗还有不少,如陆机《顺东西门行》、谢惠连《鞠歌行》、鲍照《雉朝飞操》、徐勉《迎客曲》《送客曲》等。晋陆机《鞠歌行》序云:“三言七言,虽奇宝名器,不遇知己,终不见重。愿逢知己,以托意焉。”又唐代吴兢《乐府古题要解·西门行》云:“诸家乐府诗,又有《顺东西门行》,为三七言,亦伤时顾阴,有类于此也。”据陆机和吴兢所言,这种句式可能还有着“三七言”的名称。这是“三七言”在乐府中的使用情况,至赋则不然。汉赋作品中虽已有三言,但并未与七言形成“三七言”句式,至南朝时期,五、七言乐府诗成熟且兴盛,有了影响其他文体的可能;而骈赋于时却形制臻至极致,亟须新变以延续生命力。两厢因素相遇合,诗体赋由是兴盛。随之,兼有诗人与赋家身份的文人尝试并逐渐成熟地将乐府的“三七言”句式运用到赋作中,出现如刘义恭《桐树赋》、庾信《对烛赋》、傅纟宰《博山香炉赋》等赋作。
“三七言”句式虽为乐府所常用,然民间的谚谣、歌辞等亦有不少。那么,如何判定敦煌《月赋》的“三七言”句是受乐府创作影响而不是民间的谣谚呢?从赋中的用典和意象上看,敦煌《月赋》的作者当是文学素养较高、离政治中心文坛未远的文人。赋中所用典故“魏珠”“秦镜”,皆为文人诗歌所常用。使用“魏珠”者有南北朝贺力牧《乱后别苏州人》、唐韦嗣立《酬崔光禄冬日述怀赠答》、杨炯《和刘长史答十九兄》等。唐代诗人李白、刘长卿、杜甫、刘禹锡等,皆喜用“秦镜”典故,仲子陵、张佐等更是直接将诗题名为《秦镜》。“秦镜”典故的引用在唐代达到了高潮,并被赋予了政治的色彩,如刘长卿《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何辞向物开秦镜,却使他人得楚弓”,借“秦镜”以暗喻朝政不明;杜甫《赠裴南部》“梁狱书应上,秦台镜欲临”,以“秦台镜”为喻,表明袁判官会秉公明断、公正无私;钱起《送钟评事应宏词下第东归》“蛾眉不入秦台镜,鹢羽还惊宋国风”,以“不入秦台镜”喻科考落第;元稹《谕宝二首》其二“秦镜无人拭,一片埋雾月”,以“秦镜蒙尘”比喻贤才被埋没。敦煌《月赋》对“魏珠”“秦镜”典故的引用,也寄寓着与这些诗歌相似的政治愿望,可见其作者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且与唐代政治中心的文坛相去未远。同时,赋中对“蝉”意象的描写亦能体现出这点。“蝉”是历代文人常用的意象之一,常寓以孤高清洁之意或思悲之情。赋中两处提及“蝉”,一为“蝉影偏宜百尺楼”,与李商隐《霜月》“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南水接天”所描写的情景和情感不无相通之处;一为“耳闻寒蝉心欲破”,与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所表达的情感亦较为一致。可见,《月赋》与政治中心文坛的创作风格极为相近,且赋中作者所表现的封侯拜相的愿望,说明其有接近政治中心的可能。综上所述,《月赋》受民间谚谣创作影响的可能性较少,而受文人乐府诗创作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其次,敦煌《月赋》对乐府诗诗句的化用亦体现出其受乐府的影响。“鹊飞爱绕千年树”一句,明显是化用了曹操《短歌行》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之《平调曲序》云:“《古今乐录》曰:‘王僧虔《大明三年宴乐技录》,平调有七曲:一曰《长歌行》,二曰《短歌行》……武帝“西周”“对酒”,文帝“仰瞻”,并《短歌行》……是也……其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据此,《短歌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宴乐的曲目之一,常配以笙、笛、琴、瑟等乐器演唱。又《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贞《索隐》:“案:古乐府《长歌行》《短歌行》,行者曲也。”“武帝‘对酒’”即指曹操《短歌行》,其为乐府诗无疑。《月赋》直接化用曹操《短歌行》的诗句,其受乐府诗的影响显而易见,而且从乐府《短歌行》的句式发展来看,唐前《短歌行》多是四言,也有五言的,至唐朝时期则多为七言,且不少有“三七言”句式,如顾况《短歌行》(其一):“城边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江水今人家。今人昔人共长叹,四气相催节回换。明月皎皎入华池,白云离离渡清汉。”顾诗以两组“三七言”句式开篇,后接整齐的四句七言,这与《月赋》前半部分的句式结构十分相近,皆是“三七言”句后接整齐的七言句,故《月赋》与乐府的关系亦可从中窥见一二。
最后,敦煌《月赋》的用韵也显示出与乐府的关系。《月赋》无论是前面的“三七言”句,还是后面的七言句,都十分讲究押韵且很有规律,基本是每句用韵与隔句用韵相结合,一篇之中多次换韵且有平韵和仄韵。这与晋宋以降的文人拟乐府的押韵极为相似。早期的谣谚多是每句押两个韵或每句押韵,也有不讲究押韵的;早期的七言诗亦常为每句押韵。从现存作品来看,当是到刘宋鲍照《拟行路难》和汤惠休《秋思引》等作品,才正式形成隔句用韵并多次换韵的押韵方式。虽在鲍照《拟行路难》之前已有如拂舞曲《淮南王》之类“三七句”相循环且每句押韵的谣辞,但民歌谚谣一般篇幅较短,每句押韵和隔句押韵相组合且一篇之中多次换韵的则几近于无,而如梁元帝《燕歌行》这样隔句押韵且多次换平、仄韵的长篇拟乐府,则在齐梁以降的文人乐府中渐多出现,初唐时成为常态。再看《月赋》的用韵,很难说其没有受到齐梁以来文人乐府用韵的影响。
五 余论
敦煌《月赋》虽然题名为“赋”,然体制和内容皆与诗歌无异,形成如此文体形态的主要原因是诗、赋二体发展过程中的互渗与越界,是“赋体诗化”的结果。文人乐府诗创作对《月赋》的影响,实则是赋体对诗体创作技巧的接受,也是“赋体诗化”的一个方面。如同《月赋》这样文体形态的赋作,即所谓的“诗体赋”,是赋体发展过程中形成并兴盛于六朝至唐代的一个特殊门类,《月赋》只是这类赋体发展演变中的一道剪影。
赋是韵文,是介乎诗、文之间的一种体裁,其押韵如诗,以散句行文则又似散文,后加之骈偶则又似骈文。总体上看,赋体的“诗化”虽从东汉开始,然赋体在形成之初便已有了诗的基因。郭维森、许结在谈及辞赋用韵特征时说:“辞赋文学是介乎诗、文间的体裁,其通篇用韵或韵散夹杂,既是我国早期韵文(原始诗歌)诗、乐、舞合一形态的发展变化,又与先秦散文多串杂用韵之现象符契。”可见,赋体从渊源上就与“诗”有着莫大的关系。赋的起源众说纷纭,踪凡《赋源新论》一文将赋源旧说归纳为“诗经源”“《楚辞》源”“纵横家言源”“隐语源”“俳词源”“民间说话艺术源”“多源论”等,并提出了“赋源于民间韵语”说,认为:“这里所谓民间韵语,既包括先秦隐语,也包括早期的说唱故事(后世多种说唱文艺之源)和下层艺人的单独口诵或多人表演(后世相声、戏剧等多种曲艺之源)。由于先秦时期处于中国文学艺术的萌芽阶段,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界限尚不明确,且都大致押韵,琅琅上口,所以我们统称之为民间韵语。”隐语,“它是一种雏形的描写诗。民间许多谜语都可以作描写诗看。中国大规模的描写诗是赋,赋就是隐语的化身。”“下层艺人的单独口诵”,不乏民间诗歌之词,今所见《诗经》和乐府诗中,即有不少是当时民间下层艺人单独口诵之词。故而,赋源,无论是单源论,还是多源论,似乎都绕不开诗的影响。
赋体的形成取法于“诗”。班固《汉书·艺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王逸《楚辞章句序》亦云:“其后周室衰微,战国并争,道德陵迟,谲诈萌生,于是杨、墨、邹、孟、孙、韩之徒,各以所知著造传记,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独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班固和王逸所谓“恻隐古诗之义”和“独依诗人之义”,不仅在于“诗”的讽谏传统,还在于比、兴的继承与发扬。屈原的作品虽大都已为辞赋体,然实质仍属于“诗”的范畴,其“香草美人”喻与“诗”之比、兴不无关系,且屈原一再自称其作品为“诗”,如“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九歌·东君》),“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九章·悲回风》),“二八接舞,投诗赋只”(《大招》)。不仅如此,在汉人的仿作中,亦多称其作品为诗,如庄忌《哀时命》:“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属诗”;王褒《九怀》:“悲九州兮靡君,扶轼叹兮作诗”;刘向《九叹》:“舒情陈诗,冀以自免兮”等。很显然,屈原的作品实质上仍为“诗”,况且人们历来也都承认屈原“诗人”的身份。
楚辞本属“诗”之范畴,抒情赋承于楚骚,自带“诗”之属性。东汉末,辞赋转衰,五、七言诗歌形成并兴起,文坛中心由辞赋转向诗歌,赋家创作亦缘此影响,出现向诗歌靠拢的趋态,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骈偶与声律的发展,赋体“诗化”更甚,南朝以降,赋因取法不同而厥分两途:取法五、七言之句式,则愈与诗歌无异,即所谓五、七言诗体赋,其最终因与诗太近而走向衰亡;取法骈偶、声律之形式,则愈与骈文相近,即所谓骈赋及其后之律赋,其最终因骈偶、声律的形式之美,独成一体,成为唐朝以降的科场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