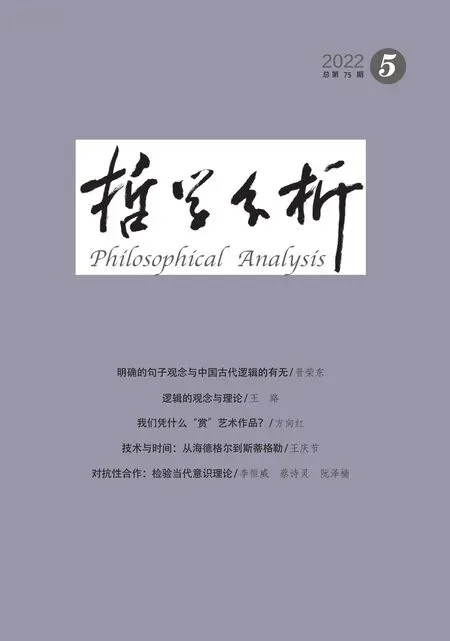我们凭什么“赏”艺术作品?
方向红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自如地使用着“赏”字,一般不会有任何违和感。我们看到历史上皇帝对文臣武将的赏赐,海报上发布了某个悬赏或某笔赏金,我们请人赏光,网络上有人请求打赏,我们自己也赏花、赏月、赏艺术。可是,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里面“赏”字的种种使用及其含义,就会发现这个字的使用似有不妥之处。一个直接的感受是,“赏”字有强烈的空间宣示,它有居高临下之意。皇帝对大臣、将军,机构对个人,都是上位者与下位者的关系,敬辞和谦辞也可以从上下位的关系来理解,因为说者已主动把自己降为低位者。至于面对自然景观时,我们也许勉强可以将自己置于上位,然而,对艺术的“赏”却与此大为不同。在我们和艺术作品之间,艺术作品显然是居上位者,而我们是来受感染和熏陶的,当然是下位者,从敬辞或谦辞的视角来看,更是如此了,可作为下位者的我们依然不断地在说“欣赏这幅画作”“欣赏那部作品”,我们凭什么可以“赏”它?
字典的解释比我们的日常理解更加全面准确:“赏:(1)指地位高的人或长辈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财物…… (2)敬辞:赏光(请对方接受自己的邀请);赏脸。 (3)奖励……(4)奖赏的东西:领赏;悬赏。(5)玩赏,因爱好某种东西而观看:欣赏;鉴赏;雅俗共赏。[赏识]认识到别人的才能或作品的价值而予以重视或赞扬。”可上述问题依然存在。义项(1) (2) (3) (4)具有明晰的空间显示和正常的高下尊卑之间的关系,但义项(5)的解释似乎游离于其他解释之外,一方面,在“赏花”“赏月”等“欣赏”活动中哪有什么财物被赐?另一方面,如果引入空间关系,在我们“赏阅”“欣赏”作品时,我们“鉴赏”的艺术对象难道不是高于,甚至远远高于我们吗?我们不是高位者,凭什么可以“赏”它们?
类似的质疑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指瑕》中也提出过:“夫赏训锡赉,岂关心解;抚训执握,何预情理。《雅》 《颂》未闻,汉魏莫用,悬领似如可辩,课文了不成义,斯实情讹之所变,文浇之致弊。而宋来才英,未之或改,旧染成俗,非一朝也。”刘勰承许慎《说文》对“赏”字的解释(“赏,赐有功也”),训“赏”为“锡赉”即“赏赐”或“赏赐之物”,认为与“心”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浮薄的文风和移情的视角所致,历代英才对此竟浑然不察。
刘勰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痛心疾首之意究竟指什么呢?有学者经过考证指出,嵇康的《四言诗》“钟期不存,我志谁赏”、曹植的《求自试表》“夫临博而企竦,闻乐而窃抃者,或有赏音而识道也”是最早让“赏”“关心解”的诗文,而到了谢灵运那里,“赏”和“心”以从未有过的方式紧密联结在一起:“赏心不可忘”(《田南树园激流植楥诗》)、“心赏贵所高”(《入东道路诗》)、“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登江中孤屿》)。刘勰明确地指之为瑕,而当时和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我们)都无视刘勰的批评和禁令,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刘勰不能理解“赏”字在恪守既有基本框架基础上的创新性使用,还是当时的文人墨客由于“旧染成俗”而导致的误用?
同样的问题也潜藏在字源学的考察中。查《字源》可知,在西周金文中,“賞”字读“偿”,本义为“偿还”“补偿”,作为赏赐的“赏”字在那时还没有出现,当时多借用本义是地名的“商”字来表示“赏赐”(有时也用“”和“”字表示,此两字后来完全消失)。春秋以后“賞”字开始取代“商”字被借用作赏赐之“賞”,而作为“偿还”的“賞”则通过增加单人旁变成了“償”字。在训诂学的解释中,“赏”和“偿”不过是假借关系而已,至于它们之间为什么可以假借,似乎没有人再问起过。然而,根据训诂学的“音近义同”原理,这两个字之间难道没有亲缘关系?它们读音相近,字形相仿,具有假借关系,即使字义不是完全相同,至少有某种程度上的相通关系吧?可是乍看起来,一个表示赐予,一个表示偿还,彼此意义相去甚远。我们针对刘勰的观点提出的问题在这里也适用——“赏”对“賞(偿)”的借用是在恪守既有基本框架基础上的创新性使用,还是由于时代的变迁而导致的误用和误借?
这些问题有的明显,有的潜藏,有的是相似关系,有的是包含关系。让我们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尝试作出回答。
现象学的方法多种多样,各家各派也众说纷纭,难以定于一尊,我们这里只挑选被广泛接受的、最重要的,且与我们目前的主题密切相关的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现象学还原”。在现象学创始人胡塞尔那里,“还原”的意思不是否定或抛弃,而是悬置判断、保持中立。对现实世界中的时间—空间对象和事件进行还原,我们就在本质的意义上完成了现象学还原,这时我们可以直观到本质。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在不同的语境中,“赏”字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些解释相互冲突,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挑选我们自认为合适的解释,而是对它们进行还原,就是说,不对它们的对错作出判断,而是将它们的观点悬置起来放到一边。这样,我们会看到,对各方意见保持中立以后,“赏”字的意义会自然而然显现出来。
第二个方法是“相关性先天”的确立。“相关性先天”也是胡塞尔的术语,它指在我们完成现象学还原之后,本质并不仅仅以普遍对象的方式向我们显现,更重要的是,它还以与意识活动相关联的方式显现,而且这种关联性不是一种经验的或偶然的关联性,而是一种先天的关联性。就我们的问题而言,我们在完成现象学还原之后不能仅仅停留在“赏”字所自行显现出来的含义上,我们应该调整目光,寻找含义和它的关联者并确认这种关联关系的先天性。如果存在多种关联关系,我们还要确定它们之间的发生序列和奠基顺序。
带着这两个方法,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赏”字含义的字源学现象。“赏”与“偿”的意义相去甚远,可为什么在这里发生了假借呢?我们先人的意识对这两个字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联想,让它们建立了怎样的关联,以至于不仅发生了假借,而且对另外两个表示“赏”的字弃之不用?我们设想一下。甲借了乙物品,甲便有欠于乙,将来在某个时候甲归还物品、填补自己对乙的亏欠就叫“偿”;异邦大军压境,国之将危,皇帝派将军抵御外敌,将军大获全胜班师回朝,皇帝要赏赐有功之将,这在某种意义上不正是一种“偿”吗?当然这不是一种等价的“偿”,皇帝不可能把社稷补偿给将军,他只能赐给他官职和田地等。但这不正是一种象征性的偿还、补偿吗?
若果如此,则在先贤的意识中,“赏”和“偿”所关联的体验内核是完全相同的,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亏欠的填补或亏欠物的归还,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个是以等价或溢价的方式,一个是以象征的方式。可是,并非所有以象征方式予以补偿或偿还的行为都叫“赏”。朋辈之间、下级对上级、晚辈对长辈的这种行为都不能被称为“赏”。根据日常生活的直觉或通常字典的理解,“赏”的行为应该发生在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的关系之中。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新华字典》对“赏”的定义作出进一步的完善:赏,是指地位高的人或长辈(高位者)出于某种补偿的目的以象征的方式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低位者)财物。
刘勰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认可这里的定义的。他训“赏”为“锡赉”,明面上承认了“赏”中所存在的上下尊卑的关系,暗里也不会反对所赏之物与被赏人所作出的贡献未必甚至不必相等,他反对的是赏“关心解”。赏,总是跟财物有关。如果与心相关,与心之情和理相关,如何还能称之为赏?对于这样的不解和质问,嵇康、曹植或谢灵运等一大批文人墨客或许可以回应道:既然赏是一种象征性的补偿,财物难道囊括了所有的象征性方式?与心相关联的情、志、道、理难道不能算作一种象征性方式?与财物相比,它们不是更抽象、更具象征性,并因此更能体现“赏”的含义?
伯牙鼓琴,钟期“赏”之以知;某人听到音乐,偷偷地跟着打拍子,或许遇到人“赏”之以识;趋正绝的乱流,媚中川的孤屿,相辉映的云日,共澄鲜的空水,谁能“赏”之以表和传?
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究竟“赏”的是什么?是情志道理,还是知识表传?很明显,知识表传是心之活动,情志道理是心之所关联者。两者有根本不同,但两者总是紧密关联在一起,例如在这里,知是对志的知,识是对道的识,表是对灵的表,传是对真的传。心失去所关联者,其活动不能展开;心的关联者失去心的活动,它自身也失去价值和意义。钟期不在,鼓琴何用?因此,伯牙破琴绝弦,而今如钟期者皆不存,有志有何意义?我志谁赏?道需要识,所以曹植虽心里“必知为朝士所笑”,但仍“敢冒其丑”向“陛下”进言,其目的不过是希冀音可赏、道可识而已;乱流与孤屿、云日和空水,如果不是因为有了诗人,其中的灵秀谁能赏识?其中蕴藏的真人和仙人又如何得到传颂?
因此,我们可以说,赏既指心之活动,又指心之对象;心的每一次活动方式可能不同,但都指向心的对象,同样,心的对象每一次可能都不同,但都关联心的活动。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说,心的活动与其对象是一种“相关性先天”。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赏的完整定义:赏,是指高位者以象征的方式给低位者心理的偿还。
“赏”的这个定义是最完整的,因为这个定义可以向下兼容其他定义。它一方面指出了最早的定义(指地位高的人或长辈给地位低的人或晚辈财物)缺乏对其中所包含的象征性意义以及偿还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在较为完善的定义(指高位者出于某种补偿的目的以象征的方式给低位者财物)中“财物”的狭隘性。所赏之“财物”是一种心理活动的结果,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心之对象。为什么可以这么说呢?因为财物只是对心理负债的一种偿还形式,还有许多非财物、非实体的偿还形式与之并列;每次赏的财物可以不一样,甚至同样的事件所赏的财物也可以不一样,这说明赏的活动奠基在“心的活动—心的对象”这对“相关性先天”之上。从高位者的心理活动的发生来说,首先出现的是心理上的亏欠,接着出现的是心理上的补偿要求——当然这种补偿是象征性的,然后出现的是对各种补偿形式的考量,考量的最终结果表现为对赏品的选择。
现在,有了“赏”的这个最完善的定义,上述各种“赏”就可以贯通了。无论是日常的直觉还是普通字典的解释以及字源学的变化都符合这个定义,连刘勰的批判我们也知道他的局限之所在了,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以嵇康、曹植、谢灵运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墨客的继承和突破之处了。“赏”的所有用法都符合其基本的要素和结构:一个高位者、一个低位者,低位者为高位者作出了某种贡献,高位者产生了一种以非对称、非对等的方式对这种贡献给予补偿的心理机制,高位者经过考量以象征的方式给出实体性的或非实体性的赏品。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高位者,有时是以敬词谦语的方式呈现,如“赏脸”“赏光”等,有时是以潜在或缺席的方式出现,如“我志谁赏”“赏音而识道”等。
但是,这个定义在解释对艺术作品的“赏”的时候,似乎仍有扞格不通之处。我们凭什么可以“赏”一件艺术作品?难道欣赏者是高位者,而作品反而是低位者?对于二流或三流的作品,也许勉强可以说,我们是高位者,我们倾身下顾去“赏”它们,但这时我们往往反而不愿意用“赏”字。然而对于世界名作而言,我们如何称得上是高位者?无论在历史、商业还是审美价值上,名作似乎远远高于我们。在欣赏过程中也是如此。名作以自己的美引领着欣赏者,给他们以安慰或震撼。前者当然是高位者,后者一定是低位者。
凭什么可以“赏”一件艺术作品?皇帝可以赏大臣财物、可以赏音以道并进而赏其忠以位,诗人可以赏山水情理,作为低位者的我们拿什么赏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本身不需要财物,不需要地位,其中的情理和美正是它自身要展现的,根本无需外求,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赏作品?难道我们只能通过一种象征的方式以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赏它,并美其名曰“欣赏”?可作品不是自然景色,观赏者的心情是无法投射到作品之上的。
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我们是带着自己的生存状况、经验积淀和知识背景来理解作品的,我们总会为作品打上我们自己的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我们对作品的赏。这是一个具有一定迷惑性的回答。何谓“赏”?虽然在其定义中没有明确出现,但其中隐含着这样的设定:赏出去的东西原则上是不能再收回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赏出去的东西在赏这种心理活动正在进行的时候是没有收回的打算的。如果我们在欣赏艺术作品时看到的只是自己投射到其中的生存状况、经验积淀和知识背景,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给出印记的同时又收回了印记,这样,赏在发生的同时又取消了。
如此一来,面对艺术作品,我们既不是高位者,也不能、更不该在最终的意义上把自己的背景、状况或心情给予它,“赏”又从何谈起呢?究竟是我们在这里把“赏”字用错了,还是其中包含着尚不为人所知的维度?德里达关于翻译、马里翁关于艺术的现象学思考可以给我们的问题带来新的视角。
德里达在一篇讨论翻译的文章中指出,翻译的动力来自文本自身的吁请,因为文本之“我”不该被遗忘,因为“我”必须继续生存,“我”必须死后重生。这里说的“文本之‘我’”不是指文本的作者,而是指文本自身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性的东西,如爱、真、美、善,等等。德里达此处讲的是翻译,但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也同样适用。艺术作品的美并不是直接可见的,这种不可见性需要借助于创作者和作品才能显现出来,不仅如此,这种显现是极其脆弱的,它还需要观众。不可见的美即使获得了文字、图像或声音等表达,但在无人观看时它仍处于被遗忘的状态。只有在观看者的审美注视下,它才会活过来。我们可以说,观看者正是艺术作品的拯救者。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品不仅脆弱而且卑微。
关于艺术作品的这个特点,马里翁有过很多精彩的比喻。他有时把它们比作犯人和病人:“画作之所以变得可见,并不是因为我们成群结队地参观它,认认真真抑或漫不经心地观看它。相反,我们之所以去参观它,正是因为它固有的可见性迫切地召唤我们。正如有必要去探望犯人和病人,尽管他们命运不济,但是仍然享有人际交往的权利”;有时他也把艺术作品比作俘虏、难民和婴儿:“在画作那里,未见者洋溢着可见性……也正如一位俘虏在获得奇迹般释放的时候洋溢着自由……画作依旧享有简单的暂住许可,可以作为审美意义上的难民逗留在白天的光明之中。就像裹着羊水的婴儿,刚刚从质料(uyn)中诞生的未见者,还带着质料的无形无色的暗昧。”显然,引文中提到的这样一些人不具有独立性,生存能力极其脆弱,地位非常卑微,他们有的等待着探望,有的盼望着释放,有的期待着救助,有的嗷嗷待哺。如果艺术作品具有这些特点,那么作为观看者的我们不恰恰是高位者吗?于是,在这里,我们获得了赏的资格。
然而,即使我们有资格赏艺术作品了,可是我们拿什么赏给艺术作品?上文说过,我们无法把自己的心情、自己的生存状况、经验积淀和知识背景赏给艺术作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赐予艺术作品?马里翁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画作使凝视活跃起来,而不是凝视让画作活跃起来。正是画作使得凝视能够穿过它,能够穿过未见者朝向可见者的上升……严格说来,并非我们学会观看画作,而是画作通过自我给予,教会我们去观看它。”如果我们把此处的“凝视”和“观看”换成“欣赏”,那么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马里翁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赏给艺术作品,作出赏之行为者不是我们,而是艺术作品本身。
可是,假如即使在象征的意义上我们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赐予艺术作品,那么,我们有何资格谈论对艺术作品的“赏”?然而,我们却无数次地用“赏”来表达我们对艺术作品的观看!也许我们确实给予了艺术作品什么而不自知?让我们回到汉语经验中来加以考察。当嵇康说“钟期不存,我志谁赏”时,他可能暗暗希冀能够得到某个高位者的赏识和重用,但就嵇康引用的这个典故本身来说,俞伯牙鼓琴,为钟子期所赏,此处的赏与任何现实的财富或地位无关,否则,钟子期死,俞伯牙也不至于破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在这个传说中,在人们对这个传说的言说中,钟子期始终是俞伯牙的知音和赏者。我们不禁要问:钟期凭什么、拿什么“赏”伯牙之琴音?或者,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在钟期赏音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钟期死后,伯牙做出如此决绝的事情?
借用德里达、马里翁的思考,我们可以说,伯牙的琴音虽然精妙绝伦,但它依然是卑微者和脆弱者,它出现又消失,随风而逝,方生方死,它在世界上逗留的时间是如此之短,以至于连通常意义上的犯人、病人、俘虏、难民和婴儿都比不上,更像是即将接受死刑的犯人、奄奄一息的病人、难产中的婴儿、马上要被坑杀的俘虏、炮火声中的难民。它的处境极其危险,它需要得到释放、抢救、解救、接收,且刻不容缓,需立即执行。钟期就是这样的执行者。当伯牙刚刚鼓琴而志在泰山时,钟期便说“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当伯牙旋尔志在流水时,钟期马上又说:“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在钟期的执行活动中发生了什么?这里面有赏吗?如果有,他赏了什么?难道是泰山和流水?它们只是比喻而已。又或者是泰山或流水所体现的志?可这志并非钟期所赏,而是伯牙通过鼓琴所要表达的心志。乍一看,钟期似乎赏无所赏,可他确实是执行者,其活动的重要性连伯牙也是认可的。岂止是认可?没有钟期的执行,伯牙不仅不愿意鼓琴言志,甚至连琴也不要了,因为他的志转瞬即逝,其存活仅在分秒之间。
钟期的赏就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无论钟期执行哪一种活动,释放、抢救也罢,解救、接收也罢,伯牙的志都必须有个去处,有个落脚之处,哪怕此落脚处只是个立锥之地。钟期就赐予了这样的地方。他将伯牙之志接纳于自己的世界之中,有时将它安置在泰山的表象上,有时安置在流水的表象上,而且可以通过记忆和语言一再地重复这种安置。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伯牙之志在另一个世界里存活下来了。当然,这个世界是个体的世界,是钟期的心灵世界,随着钟期的死亡,这个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相关性先天”正是这个世界的结构。伯牙之志以类似于泰山和流水的方式存在于钟期的主观世界里,但这种存在方式不是独立的,而是作为心理对象先天地与心理活动关联在一起,就是说,与钟期的自我、意识或心灵密不可分。
现在我们可以断言,钟期虽然弹奏不出泰山流水,但他确实赏了,他以普通人的身份赏了伯牙一个可以让其志生于斯存于斯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钟期显然是高位者,是有赏的资格的。当然,钟期之所以愿意赏出自己的世界,还是出于偿还的心理,而且这种偿还还是象征性的。伯牙之志那么高尚、那么急迫,钟期受到震撼和感动,他多么希望这么美好的事物能得到实现,但他无法帮助伯牙做到这一点,他能做的其实很少,他只是把这种美好接纳到自己的世界里,让它免遭稍纵即逝的命运。
也许我们需要对赏的定义再次进行更新。我们曾经给出了赏的最终定义:赏,是指高位者以象征的方式给低位者心理的偿还。现在根据上文对艺术作品之赏的分析,我们尝试给出一个新的定义:赏,是指高位者以象征的方式偿还给低位者一个心理的世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高位者和低位者不是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上,而是从主动和被动、强者和弱者的视角来说的;低位者就是前文所谓的犯人、病人、俘虏、难民或婴儿这样的受困对象或弱势群体,高位者就是那些主动对这些人群实施释放、抢救、解救或接收的人;这里的偿还是真正意义上的还债。通常,低位者的出现会给高位者带来极大的震撼,因为它会照亮高位者的世界,改变他的世界版图,丰富他的心理图景。在这个意义上,高位者是亏欠于低位者的,他不得不偿还自己的债务。当然,这种偿还无论如何都是象征性的,因为就高位者而言,即使他拯救了低位者并把自己的世界出让给低位者,可这与低位者给他的心灵带来的影响和效果相比,这种拯救和出让仍是微不足道的。
我们不妨把这个定义称为赏的现象学定义。它是最终的定义,也是最彻底的定义。既然是最彻底的,那么它虽然在发现的时间上位于最后,但在逻辑上应是最先的和最基础的,就是说,原则上也应该可以应用到此前的例证之中。我们来尝试一下这种应用,譬如说,将军驱逐了外敌,班师回朝,通常情况下皇帝会将此事昭告天下并记入史册。这其实已经是赏了——将军的胜利对王朝的存亡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此事无论如何已经成为过去,皇帝的做法是让朝廷上下以及历史都记住将军的功劳和事迹。尽管这种记忆与将军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但皇帝和王朝毕竟以象征的方式对将军给予了补偿。至于后面的晋官加爵赐地,虽说也是赏,但那不过是此前的心理活动的物化而已,这种物化的方式和程度受制于历史的参照以及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作为敬辞谦语的赏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况。比如,“赏脸”和“赏光”,虽然赏的是现实意义上的“(露)脸”和“光(临)”,但其基础还在于邀请者希望自己的盛情能受到被邀者的重视,并在其心理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一点我们从拒绝邀请的“心意领了”这样的措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至于景色之赏,这个定义就更恰当了。在此前的定义里,我们只能说,文人墨客把自己的情理赏给自然景观。根据这样的说法,似乎自然景观本身并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或者至多不过是触发诗人心中情理的机缘而已。然而,从现在的定义看来,自然虽非人类,但其秀色灵气是自在具有的。于是,谢灵运登江中孤屿时所看到的自然景观之“灵”和“真”就不是或首先不是他从诗人的情怀出发赐给自然的,而是景观本身就蕴含着的。实际上诗人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诗中明确地说:“蕴真谁为传”。自然景观,放眼望去,乃乱流与孤屿,云日和空水,孤屿正向着河水献媚,而河水已流向远方渐趋消失,云日交相辉映,水天一色清新明澈。其中所蕴含的灵气与真意给人以无尽的慰藉与希望,但若无人予以表传,也终将消散于黑暗和虚无之中,唯有诗人感其“灵”、解其“真”,并将其接纳于心中,且表之于诗、传之于世。
这是赏的通用定义。我们凭借出让自己心理世界中的一方土地,去赏他人和自然;为了赏艺术作品,我们更是如此。我们甚至会出让自己全部的心理世界,以象征性地偿还作品对我们心理世界的照亮和对这个世界版图的重塑,以及对我们心理图景的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