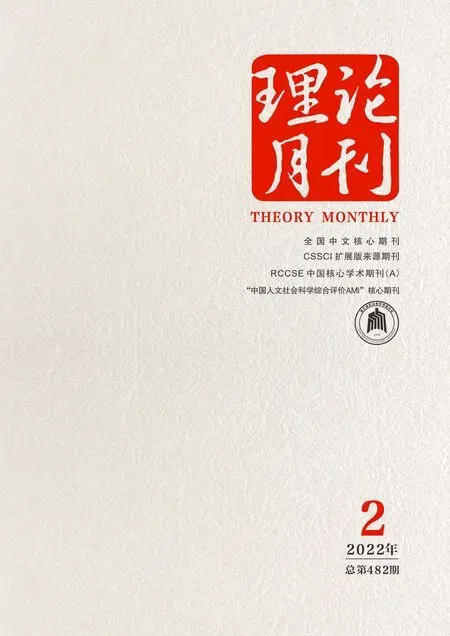真理与在场
——以胡塞尔的时间意识为线索
□刘逸峰
(广西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0)
对胡塞尔而言,现象学起始于对“可靠性”的执着,以及对真理——只能被发现而无法被发明的“自在存在者”——的追求。在他看来,只有直观在充实中获得体验上的“明见性”,成为“对本原被给予性的意识”,被意指的观念才会以“自身当下的被给予”的姿态展示自身,真理才能被揭示出来。然而,“在没有真的地方也就明察不到真,换言之,也就没有明见性”。真理先于直观,就算真理现身于体验中,它作为不受时间规定的东西仍然超出了“当下”(Gegenwart),观念或真理只能以表象或含义的形态在当下呈现。即便如此,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对真理的把握也只有直观这一种方式。除非我们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当下”问题进行彻底的分析,否则真理与直观的关系问题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理解。而且无论是列维纳斯、德里达,还是马里翁,都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解读中指出了诸多问题,而这些质疑也只能在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中予以回应。
一、对象性在场与原感觉困境
利科将胡塞尔现象学比喻为“布满脚手架的工地”,胡塞尔实际上试图以体验为砖石,想要建造一座名为“直观”的庙宇,其中供奉着含义或表象,朝拜着“观念”这个偶像,这整个境域可以被称为“当下”。对此,德里达与马里翁各执一词。德里达认为,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含义虽然把对象召唤出来,使其在场,但只有明见的直观才能把握观念的同一性,含义可被视为将观念带入直观的方式。因此对德里达而言,胡塞尔现象学靠“单独的直观就完成了在场化”,庙宇先于供物。但在马里翁看来,含义召唤了观念,不同的直观只是充实了含义。这就说明含义“不需要借助于任何一个充实性的或说明性的直观的出现就可以构造起自身”,其“稳定性便足以把自身展现(sich darstellt)在在场之中”。因此对马里翁而言,含义成就了在场,庙宇是围绕供物建造起来的。
两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分别对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了责难。对于德里达而言,含义、表象与符号都是以自身的在场指向不在场的观念,观念的同一性本不能在与直观的首次接触中实现,而是要通过表象或符号在重复、比较与认同中构建起来,否则含义与符号就会“被抹去”(effacement)。然而,胡塞尔现象学却不凭借符号,仅仅“在同一时刻对自身在场(présence à soi)的体验的同一性”中完成了对观念的证明,这导致任何当下都是超越性的彻底的在场化。马里翁则提出,胡塞尔将“真”视为体验的明见性,而观念是非时间性的,那么,只有直观体验到的“原初被给予性”才能够给出观念的“自身当下被给予性”,体验“证明了它先于全部(超越的)世界实现完美在场的特权”。两人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疑虑其实是一致的:直观作为“一切原则之原则”,占据了一切,没有留下任何余地,以至于“胡塞尔的现象,作为在场的完美的显现,可以被称作平面的现象”。可以说,庙宇已经许诺了被朝拜者的全然在场。
胡塞尔现象学的在场甚至比马里翁、德里达所想的延伸得更远。胡塞尔指出,“如果我感知一段旋律……在结尾相位则拥有这完整的旋律。在这里每个对象性的相位(每个自为的声音)都被立义了,都出现在一个立义的瞬间里”。因此,他不仅要求不同的相位要素都作为独立对象“在一个瞬间中同时地(gleichzeitig)被意识到”(自为的声音),也要求作为这些相位的统一体的表象被意识到(刚开始的旋律、完整的旋律等)。当然,同一性也必须在每一个相位被意识到(旋律)。胡塞尔现象学并没有像德里达担忧的那样抛弃含义,毋宁说它在“同时性”这一最彻底的在场中,毫无遗漏地让曾经的每个瞬间相位的独立要素与那些相位的表象方式全部呈现,它一次性给出了全部的供物。在场作为涵盖一切时刻的“同时”,就是呼唤观念、承受真理的现象学直观之“当下”。
“对象性”(Gegenstandlichkeit)一词指明了这种极度丰富之在场的实现方式。对象性“受到一个完整的行为的朝向”,而此行为可以囊括“受到各种不同的、构成这个行为的部分行为的朝向”的“对象”(Gegenstände)。这意味着,当一个相位成为对象性行为的承载者时,其他相位就可以被一起把握。同时,每一个相位的“对象性—对象”关系就是意向对象在此相位的表象。曾经的“对象性—对象”结构融入新相位的结构中,使每个相位不仅是属于该相位的独特表象,也是蕴含着之前表象的统一。意向对象的真理同一性就是这样显现的:“被表象的对象性的统一以及与它相关的意向关系的整个方式并非与部分行为相并列地构造起来,而是在它们之中并以联合它们的方式构造起来,通过这种联合得以成立的不仅是一个体验的统一性,而且是一个统一的行为。”在此,胡塞尔仍然将在场的构建归功于超越的对象性。
没有任何东西被遮蔽于对象性在场中,一切都各安其位地显露于同时性之中。滞留以均匀的流速把属于特定时间相位的原感觉“映射”(Abschattung)在每一个当下的瞬间。这些滞留与当下的原感觉形成“并存”(Koexistenz),且一同被排列于时间图示中的同一条垂线上。即便胡塞尔强调在这里只是采取了一种“类—空间”的描述手法,但“映射”一词却表明,这条囊括了一切的唯一的线性在场并不是随意的修辞。原感觉是绝对“自身在此的”“现时现在的”,它不可能与属己的当下相位分离,滞留则被视为原感觉的“再现”(Repräsentation):“这个声音本身是同一个声音,但那个‘以此方式’显现着的声音则是一个越来越不同的声音。”这也正是胡塞尔使用“映射”概念的原因:在数学里,对几何图形或空间在连续改变形状后还能保持不变的一些性质的研究被称为“拓扑”,而持续变异的滞留与原感觉的关系可以被看作“拟—拓扑”。只不过拓扑中的持续变化者处于互逆的连续映射之中,而原感觉与滞留之间是不可逆的连续映射。胡塞尔采取了空间化的数学表达,于是,在场为了同时囊括先行后续,也就只能被描述为朝特定方向延伸的线性“并存”——“在场的完美的显现”甚至不是“平面”。
胡塞尔拒绝了坦塔洛斯的命运,现象学是把握一切真理的伟大许诺,只要走上现象学的直观之路,人们就会因真理而满足。在此,超越性不是不可穷尽的旅途,而是观念的绝对明晰且完全的被给予方式。只要人们进入直观的庙宇,它便给出全部。胡塞尔就像尼采笔下的赫拉克利特,“他拥有真理:尽管时间之轮在转动,但无论它转向何方,它绝不会逃离真理”,“这里的真理是直观中的真理,而不是沿着逻辑的绳梯向上攀缘的真理”。当胡塞尔将迎接永恒真理的时间意识称作“一条永恒的赫拉克利特之流”时,他也一定感受到了那团被点燃于古希腊的火焰。
可以说,在场与观念通过直观签下契约,使“存在于这些瞬间的一切真正的本质都是同时在此的、不变的和不灭的,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然而,真理和观念仍然需要使之降临的原初瞬间,原感觉承担起了这个被胡塞尔称为“充实”的时刻,它是“绝对未变异之物,是所有进一步的意识和存在的原源泉”。真理在原感觉的不断充实中绽放,用尼采的话说就是:“在那种生成中,表现出神奇的秩序、规律性和确定性。”胡塞尔现象学就是要征服这一生成,让真理现身的一切瞬间都处于同一个在场之中。为了让此瞬间成为在任何当下都必然有效的契约,绝对被给予的原初瞬间放弃了自己的唯一性,以此换取持续的“在场化”(Vergegenwärtigung),因为只有将原感觉的唯一性转化为在各相位都能意指的同一性,它才能超离自身的现时当下,滞留是对原感觉越来越遥远且永不可能实现的回返。
显然,对胡塞尔来说,构筑朝拜真理之庙宇的材料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毕竟,“真理……作为一个相合的认同的(Identifizierung)相关物便是一个同一性(Identität)……这种一致性是在明见性中被体验到的,因为明见性就是相即认同的现时进行”。正是“相即被感知的东西,才构成了那个最先使明见性成为可能并为明见性提供论证的核心”。原感觉在亮明自己身份(Identität)的同时,也认同着诸滞留在真理的同一性中的地位,因此原感觉在显露的瞬间就已经转变为对象的同一性:“当对象实项地包含在感知本身之中时,这种感知就是相即的感知。”可以说,在以唯一性兑换“在场化”之前,原初被给予性就已经把自身献祭给对象性了,它先于德里达要求的表象之互相认同而确认了自身的身份。对此,列维纳斯敏锐地察觉到:“现象(phénomène)一旦被触碰,就会退化为外表(apparence),并在这个意义上,会处于歧义之中,处于对恶魔的疑惑之中。”这一歧义就是,现象作为绝对被给予者,当其试图于对象性在场之中给出自身时,却反而越发地与自身疏离。
马里翁的看法很贴切,胡塞尔现象学确实“使得体验的现象性本身成为对象的现象性”,而对象性在场无疑是一座致敬同一性的祭坛。原初被给予性从未被对象性在场捕获,但这个注定逃避目光的幽灵却总是冲击着同一性。列维纳斯指出:“胡塞尔……在这种自身呈现的本质性的未完成中,和那把事物的一系列‘映射’总括在一起的‘综合’之总是可能的破裂中,又重新发现了这种歧义性。”而这个如同恶魔游戏般的“被给予与现象之间隔”,正是马里翁开启“被给予性现象学”之处。
原初绝对被给予性作为基石,决定甚至超出了这座被称为对象性在场的庙宇。对胡塞尔而言,将明见性置于不可把握的原感觉之上就等同接受了一种被给予性的神话。他当然不愿意将真理置于自身无法直观的地基之上,也不接受自己审视一切的权力遭到拒绝,更何况,将被给予性对象化还隐含着更深刻的困境。
二、非对象化的同一性危机
为了在对象化中捕获原初瞬间的同一性,胡塞尔现象学的两种表象行为陷入了相互冲突纠缠之中。再回忆与滞留的“共同点在于:被表象的对象‘不是现在本身在此’”,因此在理论上对它们进行区分就非常困难。虽然胡塞尔在1893—1901 年就已经指出了两者的差别,强调滞留“直接与感知相衔接”,再回忆与感知则是“一种分立的(diskreter)区别”。但是,再回忆作为过去之物的表象与感知的区分如此显著,以至于人们很难理解为何另一种过去表象能够融入感知行为。
毕竟,原感觉在其被给予的现时现在中就已经被穷尽了,它“并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而是通过自发的发生(gensesis spontanea)才形成的,它是原制作。它是不会生长的(它没有萌芽),它就是原创作(Urzeugung)”。滞留不接受任何新的东西,并且总是比原感觉“更少”,只有这样才能“在每个现在回坠到过去的同时,它也持留着它的严格的同一性”。然而,当原感觉被视为再现之物时,它就已经被看作相对于滞留而言的超越之物了,在这个意义上,列维纳斯准确指出,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对原感觉的记忆是“第一个超越性”。这种超越关系之所以是“第一个”,恰恰在于原感觉的绝对原初性与其滞留的必然性,当然,这也意味着胡塞尔必须面对比前文的危机——原感觉被不可赎回地献祭且无法对象性地在场——更危险的境况,他似乎不得不承认原感觉与其滞留所维持的同一性之间的断裂,接受原初被给予性从未被绝对地,因此也是内在地获得这个事实。“超越的内在的同一性”这种说法虽然怪异,用在此处却是恰如其分。
滞留所执着的同一性同样问题重重。原初瞬间就已经是真理的显明,那么滞留又有什么理由将在场中的核心地位让渡出去呢?滞留以再现的方式指向着原感觉的同时,后者不就已经被赐予了不可动摇的封闭的同一性了吗?当胡塞尔试图在理论上区分余音与滞留,并努力地解释为何滞留与原感觉之间形成的是旋律而非混响时,这种对象化的、封闭的同一性之间的冲突就已经走到了台前。这些封闭的同一性孤独地自我运作着,直到消弭。继原感觉的危机之后,胡塞尔现象学的在场也在既看不见源头,也望不见终点的境遇中破碎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着不同种类的清晰性和透明性,其中有这样一种透明性,它的存在乞灵于以下事实:看来透明的东西其实是空洞的,对此要尽可能少作思考,以此方式来排除模糊性的危险”。封闭的同一性就是这种透明性,胡塞尔甚至放弃了相即感知所给予的与唯一性最为亲近的同一,将之一并投入空乏之中,就像他本人所说的:“意识之所以能够成为客体,乃是因为有滞留。”显然,胡塞尔能够接受不可实现的回返,却无法忍受从未获得,他指出原感觉虽然“也已经被意识到……却又不是对象性的”。只是,如果现象学的直观诉诸以再现为基础的对象性的在场,那么原感觉在现象学中就只能在推论中得到说明,除非胡塞尔承认,对原感觉的意识超出了现象学直观的能力。
胡塞尔当然不会接受推论中的“模糊性的危险”,他强调原感觉是“完全像滞留一样可以作为构造性相位而在对被构造的体验之反思中被直观到的东西”。为此,他首先必须克服对象化的鸿沟,承认“滞留本身不是一种将已流逝的相位当作客体的回顾”。如此一来,滞留的表象特征被取消了,它只是“在当下化中充实自身:这个作为刚刚曾在的被给予者表明自身与再回忆之物相同一”,可以说,对滞留的充实就是再回忆。正是在反思中,滞留被充实为一种对象化的活动,由此才使再回忆与感知行为的差异渗入由原感觉与滞留构成的感知行为内部,从而导致感知行为的分裂。在此,胡塞尔实际上已经踏入非对象性直观的现象学领域,超出了马里翁所指责的对象性在场的框架。
虽然滞留不再被视为再现,但在1909 年胡塞尔仍强调“持续的自身映射属于绝对意识的本质”,滞留与原感觉之间曾被描述为“表象—对象”结构的同一性转变为了非对象性的同一性。如果说,把滞留设定为立义行为实际上是通过赋予原感觉以超越性而换取变异过程中的稳定的同一性,那么,立义结构的瓦解虽然恢复了两者关系的直接性,却又动摇了滞留中的同一性。因为,滞留既不是原感觉的表象,也“不是一个在一系列滞留相位中构造起来的内在持续统一”。它不是一个持续增殖的整体,不保存原感觉,所以从未在自身之内保留描画其已行进之路的地图。它只能意识到前一个相位,除了最初的滞留相位,后续相位和原感觉并不“直接”相关。实际上,滞留根本无法保障同一性不在其持续变异中被消耗掉。
更进一步说,甚至将滞留视为由一系列“对前一个相位的意向”形成的连续都是可疑的看法。既然滞留不是对象化,那么滞留绝非通过对比相位的差异而间接领会变异,即它不是借由自身所意向者的不在场与自身在场之间的差异来理解相位变更,而是直接呈现了变异本身。正如胡塞尔所说,它只是“一个可以用来标识意识相位与意识相位之意向关系……的表达”。对滞留相位的把握是间接的,这实际上超出了滞留本身的能力。我们虽然可以凭借反思勾勒出一条由各个相位所标识的滞留路径,但在胡塞尔经典的时间图式与描述中,滞留的各个相位显然是由与其共同在场的原感觉所标识的。现在,在讨论不同的同一性如何相互作用之前,胡塞尔迫切需要重建滞留中的同一性。
三、两种在场与作为融合的同一化
然而,这种重建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常来说,滞留既然指意识相位的变更,那么原感觉进入滞留,当然指其失去了在场的核心——“现时”的位置,它被一个“新”的原感觉驱赶,并且在另一个“新”的原感觉的挤压下进入那条描绘在场的垂线的更深处。对此,克里斯蒂安·迪米特里(Cristian Dimitriu)指出:“滞留本身并不是任何主动性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被动的。”因此,一开始就不存在自我运作的封闭的同一性,它们之间如何相互作用本身就是个伪问题,“作用”(wirkung)是滞留的前提:滞留虽然不指向与之共同在场的原感觉,但其本身却已经与“新”的原感觉相关,它以自身的变化持续地反馈着在场中的原感觉的作用效果,而非仅仅标识着特定原感觉的变异。显然,原感觉被另一个“新”的原感觉推离“现时现在”的作用是奠基性的,但悖论在于,如果没有滞留为对象化的反思奠基,我们根本不可能指出“什么”在作用,所以,只要我们将“作用”视为前提,原感觉就是被构造的东西。
因此,原感觉与其被视为某种尚未加工的原初材料,倒不如被看作作用发生的最初瞬间,滞留就在那“现时现在”的作用中被“创造”(wirken)出来,通过反思,人们凝固了这个时刻,就像人们将滞留把握为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相位。“现时现在”不是被某种原初者占据的位置,它只是作用发生的标记,因此,胡塞尔将“现在—存在”(Jetzt-sein)称为“现实—存在”(Wirklichkeit-sein)。
胡塞尔现象学的当下或在场可被区分为两个层次:(1)对象化反思或直观中被固定了的、由原感觉与诸多滞留相位构成的“具体当下”。这也被胡塞尔称为“横意向性”,人们能够以这些对象性在场为标志,勾勒出原感觉与滞留之间的变更路径,即被视为“原感觉—滞留”系统的“纵意向性”。对共同在场的原感觉或滞留的对象化描述,实质上是以不同的视角切入在场,因此该当下被看作不同对象的关系整体或表象的集合,而这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同一时刻”。(2)非对象化直观中被视为作用本身的流变的在场,即“活的当下”。滞留被视为作用造成的被动效果,因此,人们通过滞留所把握的原感觉也只是原初瞬间被动性的一面。在列维纳斯看来,由于原感觉已经是滞留可追溯的极限,既然滞留是意识对象化的前提,那么原感觉仍然可以被授予“原创作”之名,即便他认为原感觉是完全被动的东西。
在尼采眼中,胡塞尔现象学在场的第二个层次或许如同叔本华的学说一样,再一次遇见了赫拉克利特之流:“在时间中,只有当一个瞬间吞噬了前一个瞬间即它的前辈,从而自己也同样迅速地再一次被吞噬时,这个瞬间才会存在。”因此,对尼采而言,胡塞尔将“现时现在”规定为“现实—存在”也是必然之事了,毕竟,谁要是看到了赫拉克利特与叔本华关于时间的真理,“他也必然马上得出赫拉克利特的结论,宣称现实性(wirklichkeit)的全部本质只是活动,对于它来说,没有其他方式的存在”。正如扎哈维所说:“胡塞尔不再试图去寻找一个最终奠基的意识作为对意识流如何能够自身—意识的解释,而是将自身—意识置于此意识流的结构关联之中。”
凭借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对真理的同一性问题进行说明。当胡塞尔现象学放弃封闭的同一性之时,“相即感知”,即以原感觉本身作为对象而对直观进行印证式的充实,就已经成了伪称,无怪乎胡塞尔后期完全弃用了这个概念。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写道:“我们不能将两个事物标示为相同的,同时却没有给明这两个事物在哪个方面(Hinsicht)是相同的。我说的这个‘方面’就是同一性之所在……同一性是绝对无法定义的,但相同性却并非如此。相同性是隶属于同一个种类的诸对象的关系。”这意味着同一性本来就是不可对象化的东西,也不是对象之间的关系,它是看向关系的视角(Sicht)或者说是关系呈现的方式。原感觉是整个当下被给予的方式的标志,是在场以特定方式展开的中心,由于它仅表明持续生成的作用,所以真理的同一性在根本上就是“同一化”(indentifizierung)。同样,因为视角的持续变更并不属于对象化的关系,那么这里就不存在新的视角对曾经视角的“认同”(etw.als j-n/etw identifizieren),而是两者之间的“融合”或“参与”(sich mit jm/etw.identifizieren)。据此,胡塞尔现象学摆脱了德里达的指责,所谓的“在同一时刻对自我在场的体验的同一性”,只是通过现象学直观对持续变更的在场进行抽象的产物。毕竟,在胡塞尔现象学的分析中,无论是“同一时刻”还是这一时刻的诸多表象,都只不过是在第一层次的在场中被奠基的东西。
由此,真理与同一性不再是漂浮于在场之上的东西,而是时间意识自身的成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内在性,普遍本质是不可设想的。”胡塞尔现象学的真理不再是海德格尔指责的那种空洞的透明性,而是其肯定之物:“假如真理之本质(Wesen)是变化的,那么这个变化的东西就可能总是一再成为对杂多有效的‘一’而无损于变化。可是,在变化中坚持下来的东西乃是那个在其变化中表现出来的本质的不可变者……这样一来,本质的本质特性,本质的不可穷尽性,就得到了肯定,因而本质的真正自身性和同一性也就得到了肯定。”正因为本质是在视角转换的时间意识中不断生成的东西,胡塞尔现象学的在场就不仅是时间意义上的当下,而且是本质意义上的“在场”(Anwesen)。
然而对胡塞尔现象学来说,对在场的进一步追问仍然是可能的:在对“活的当下”进行追溯时,我们在原感觉这座界碑前不能再向前半步了吗?
四、在场的界限与内在性
胡塞尔现象学通过对前摄的研究,完成了对被动性在场的突破。关于前摄概念的演进,笔者曾撰文详述,不再赘述,在此我们只需要注意“贝尔瑙手稿”中的一个关键论述即可。胡塞尔在这一时期将原感觉、滞留与前摄视为“原过程”(Urprozess)。原感觉是变异的“零点”,而这必须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如本文第二节所示,原感觉对滞留而言是原初的被动性、变异的最初时刻;其二,从前摄来看,原感觉是象征,被象征的是在反思中视为“将来”的东西,但其本身又是对当下产生作用的非对象化之物,是完全超出直观界限的东西。原感觉虽非其意向者,却正好表明前摄所意向的东西仍处于“尚未”之中。换句话说,如果原感觉标识了原初作用瞬间的被动性方面,那么前摄就标识了该瞬间纯粹生成的主动方面。
对此,胡塞尔指出原过程超出了直观的领域,并以此将之划分为直观性与非直观性两个部分,两者之间的界限是“直观性的零;达到顶点是直观性的持续充盈,这就是说,是在强度阶段的持续提升中,是在E这个当下点上”。E是原意识,变异的“零点”就在直观性最为充盈之处。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处于直观领域中的原过程才能支撑一个对象化的直观,而非直观性的领域则处于“空乏表象”中:“在空乏表象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东西发生,实际上没有对象的意义被构造起来,说到底,没有任何东西通过现时的意向结构在它们中被构造起来。”
前摄当然是空乏表象,但滞留也被胡塞尔区分为两个阶段,即处于直观领域内的“近滞留”(Nahretention)与最终迈向“无差别的统一性”(unterschiedslosen Einheit)的“ 远 滞 留 ”(Fernretention),后者是另一种空乏表象。沃伦认为,远滞留所标识的直观界限,如同“非清醒性”(Unwachheit)和“无力性”(Kraftlosigkeit)的黑夜,在彻底的无差别中无法分辨,不可呈现。胡塞尔为直观性的具体在场划定了两条“不在场”的界限,而这又与海德格尔在其晚期文章《时间与存在》中对不在场的说法惊人一致。黑尔德指出,在海德格尔那里“对于这个‘不在场’我们从两种形态上加以经验……我们在‘曾在’中所遇到的‘不在场’,是‘不可再现’的过去。而称作‘未来’的不在场,是一种总不可扬弃的、恰恰使我们吃惊的未知性……只是那种从前瞻性地预期到的充实中抽身而去的东西……”
直观中的具体在场处于“绝对不可同一化”与“最彻底的同一性”之间,在场化也能够被看作从最大差异——拒绝同一化与同一化本身的差异——向最彻底的同一性的运动。但是,原过程也没有消除两个“不在场”之间的距离,就像海德格尔对未来与过去之间的描述:“到来”(Zukunft)递予和提供“曾是”(Gewesen)。“递予”一词意味着“不可消除的裂隙”,它将未来同“当下”隔开。显然,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原感觉就是这个裂隙,它是时间意识在不断“抽身而去”的前摄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或者说,它就是前摄对在场的持续出离,而这也正是本文第二部分所指出的原感觉之被动性所在。原感觉是原初“被给予性”(Gegebenheit),但这也是一种自身给予:“给予(Geben)由自身出发而发生的(sich ereignet)。”对直观而言,这确实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原感觉的被动性在胡塞尔这里必然意味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发性,尽管胡塞尔在早期时间分析中混淆了两者。胡塞尔通过上述两种“不在场”为具体在场划下界限的同时,他就已经跨过了原感觉这座界碑,揭示了“活的当下”:“活的当下”就是纯粹的生产与创造,对“不在场”的说明,实际上表明了它作为起源溢出反思的最终的隐匿性。
胡塞尔将“无差别的统一”的“不在场”视为“睡着的”视域,而另一个“不在场”又是清醒的“吃惊”。列维纳斯正确地指出,在胡塞尔现象学中“苏醒就是睡着又不在睡的我: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对他在内在性中发生了……”真理与对象性在场就是这种持续的苏醒。只是在列维纳斯看来,只有外在的他异性才唤醒发生一切的内在性,但胡塞尔却指出,这种唤醒本身是由时间意识自身完成的,是完全的自身触发。虽然列维纳斯从他异性的角度提出:“施行唤醒的自由比被固定成原则的关于开端的自由更自由。”但对已经在内在性中突破并不断生产固定开端的胡塞尔现象学而言,却反而表明内在性是最为自由的,真理就是它的自由创造。
于是,胡塞尔现象学已经不可避免地走向看似与其大相径庭的尼采哲学了:“世界的价值就包含在我们的解释中……;以往的解释都是透视性的评估……人的每一次提升都伴随着对那些比较狭隘的解释的克服;权力的每一次增强和增长都开拓出让我们相信新视域的崭新视角和手段——这种想法遍布于我的著作中……它是‘流变的’,就像处于生成状态的东西,就像总在变化却永远无法接近真理的虚假:因为——根本就没有‘真理’。”除了最后的结论,胡塞尔显然可以认同尼采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说明,似乎就连“没有‘真理’”的结论对胡塞尔现象学来说也不是完全匪夷所思的:“一种道德命令开始发挥作用:没有生物会想要欺骗自己,没有生物会欺骗——所以,有的只是求真意志。”当胡塞尔如尼采笔下的赫拉克利特一样骄傲地宣称自己对真理的掌控时,当其揭示了时间意识的内在性对真理的无限生产时,现象学几乎就是最强力的求真意志。这也意味着,胡塞尔现象学不得不面对真正使之惊恐的东西:难道现象学真的没有在看似淡然的中立性直观中热忱地制造真理吗?
结语
马里翁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指出了胡塞尔与尼采的密切关系,胡塞尔与尼采之所以是“最生疏、然而无疑也是最无法回避的孪生兄弟”,并不在于他们都将一切带入了对象性在场,而是因为他们都将一切看作内在性的无限生成,将真理视为在内在性的自我克服中所完成的超越。两种哲学的亲近,不仅体现在“内在性”方面,也体现在胡塞尔哲学与尼采本人所肯定的哲学观念上的亲和。然而,胡塞尔现象学也在尼采哲学中看到了自己不愿意接受的威胁,例如由内在性导致的唯我论的危险。为了克服它,胡塞尔一边坚守着超越论自我,一边不断从交互主体性与生活世界中寻找出路,而尼采哲学却对此安之若素:真理是强力意志的产物,而强力意志就是“自我的提高和强化”。无论如何,对胡塞尔现象学与尼采哲学进行比较研究,既有助于加深对两者的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领会西方现代哲学,而“内在性”概念则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